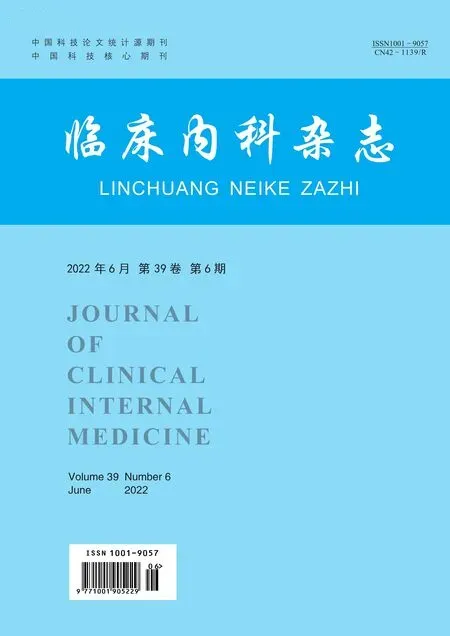脓毒症相关急性肾损伤
张宇慧 杨莉
急性肾损伤(AKI)是由于不同病因所致的肾功能短时间内急剧下降或丧失,其发生率高,在住院患者中约为10%~25%,在重症监护病房可达16%~67%,是临床常见的危重症,与危重症患者的死亡密切相关,一旦发展为重症AKI,临床救治困难,死亡率居高不下(50%~75%)[1-3]。脓毒症(Sepsis)是由于机体对感染异常反应造成的以器官功能障碍为特征的危及生命的临床综合征[4],是临床常见的危重症,亦为重症患者发生AKI的首要病因[3]。脓毒症相关AKI(S-AKI)指同时满足脓毒症及AKI的诊断标准,且排除了其他可解释AKI的原因[5-6]。重症监护室(ICU)的脓毒症(ICU-AKI)患者约60%发生AKI,而在全部ICU-AKI中,约40%~50%与脓毒症密切相关[7-10]。脓毒症患者一旦发生AKI,其死亡率显著升高(与非AKI脓毒症患者相比升高2~3倍,53.3%~74.5%比21.3%~28.4%)[8,11-14],临床救治困难,因此加强对S-AKI的早期识别和防治对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S-AKI的流行病学特点
脓毒症患者是ICU中最为常见的AKI患病人群[13,15-16]。然而,由于危重病患者中可导致肾损伤的混杂病因很多,因此诊断S-AKI存在一定难度。目前尚缺乏全球范围的S-AKI流行病学研究,一项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多中心研究显示,120 123例ICU危重症患者中S-AKI发生率为11.7%[17]。来自加拿大、美国、沙特阿拉伯、葡萄牙及比利时的研究显示,在ICU脓毒症患者中,AKI发生率为37.4%~64.4%[9,11,18]。随着脓毒症严重程度的增加,AKI发生率也相应增加,在脓毒症休克患者中,发生AKI的比例最高[19]。在一项来自美国的多中心研究中50.4%的脓毒症休克患者在入院时即合并AKI,另有18.7%的患者在入院后7天内发生了AKI[20-21]。既往多项研究根据美国脓毒症的发病率进行推算,估计全球每年有1 900万例脓毒症患者,如果按照每3例脓毒症患者就有1例发生AKI估计,全球S-AKI的发病率约为600万/年,而实际发病率可能更高[22-24]。在我国,脓毒症也是ICU患者发生AKI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内报道的ICU内S-AKI发生率为4.5%~6.9%[25-28];而在脓毒症患者中,AKI发生率高达47.1%[29]。
二、S-AKI的病理生理机制
S-AKI的病理生理机制非常复杂,目前尚未完全阐明,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炎症反应:脓毒症引起大量炎症介质的释放,包括病原体本身的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S)和受损组织产生的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这些炎症因子通过与免疫细胞、内皮细胞、肾小管上皮细胞表面的模式识别受体(PRR,如免疫细胞表面的Toll样受体等)相结合,启动下游级联信号,引发大量促炎因子释放,从而导致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引起炎症反应和组织损伤。此外,近端肾小管上皮细胞表面的Toll样受体与炎症介质结合后还会出现氧化应激,产生活性氧及线粒体损伤,加重细胞和组织损伤[24]。
2.微血管功能障碍:由于内皮细胞损伤、自主神经反应、多糖包被脱落、凝血级联反应的激活等机制,机体微循环发生非均质性变化(即血流连续的毛细血管比例降低、血流间歇或停止的毛细血管比例增加),血管通透性增加,加速了白细胞和血小板的滚动和粘附,降低了血流速度,极易引起微血栓和毛细血管阻塞,造成局部肾脏组织的微循环灌注不足,延长了肾小管上皮细胞暴露于炎症介质的时间,从而引起肾小管细胞的损伤[24]。
3.代谢重编程:脓毒症早期发生的代谢重编程是一种以牺牲功能为代价而生存的适应性改变,是由线粒体介导的以优化能量消耗、改变底物利用、抑制细胞凋亡为特征的过程,从而减少非关键功能的能量利用(肾小管溶质转运减少、细胞周期阻滞),以维持关键功能的能量利用,从而避免细胞死亡[24]。其机制可能与细胞处理能量底物方式的切换有关,这种切换分为两个阶段,在脓毒症损伤的早期阶段,肾小管上皮细胞从正常状态下的氧化磷酸化代谢转变为有氧糖酵解代谢,进入以合成代谢为主的促炎阶段,产生足够能量避免死亡,在此阶段后,再切换回氧化磷酸化代谢,进入以分解代谢为主的抗炎阶段[30]。
三、S-AKI的早期识别
S-AKI与危重症患者住院时间延长、治疗费用增加、死亡风险增高均密切相关,早期识别与干预对避免肾功能进一步恶化和改善预后至关重要[31-33]。传统的肾脏功能减退的判断依赖于血肌酐及尿量的变化,然而用血肌酐的变化评估肾脏功能具有滞后性,且脓毒症时由于肌肉灌注不良,血肌酐产生相对减缓,因此对反映肾功能的变化更为延迟。尿量也并非一项敏感指标,在非重症监护室的病房较难准确记录,且极易受到诸如液体复苏、利尿剂等因素的影响[24]。除血肌酐和尿量外,还有许多方法可以辅助早期诊断肾脏功能下降。实时的肾小球滤过率(GFR)监测指通过经皮传感器检测能够经肾脏滤过的荧光标志物在血浆中的清除率,从而实时监测GFR,该方法可在血肌酐升高前6~12小时检测到GFR的变化,不仅可协助AKI的早期诊断,还可通过监测补液后GFR的变化来协助判断AKI病因,不过这项技术的临床应用效果仍有待探索[34]。多普勒超声对AKI的早期诊断也有重要的意义,其中,肾阻力指数(RRI)是一种评估肾脏血流动力学的无创检查方法,通过超声对肾内动脉波进行检测,可用于评估肾脏灌注,预测AKI的发生和恢复[35]。在脓毒症休克患者中,入院时RRI>0.74可预测AKI的发生[36]。一项Meta分析结果显示,RRI偏高与持续性AKI密切相关[37];但也有研究结果显示,在危重症患者中采用RRI预测持续性AKI的灵敏度较低,预测准确性有限[38]。动态对比增强超声(DCE-US)也是一种无肾毒性、可用来定量评估器官灌注的方法,在脓毒症中,DCE-US下肾脏灌注减低可能提示AKI的风险增加,但急症状态下患者的肾脏灌注可能有较大个体差异,其准确性有待进一步验证[39]。
尿沉渣镜检对S-AKI的肾组织损伤诊断具有重要作用。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显示,S-AKI患者的尿沉渣中肾小管上皮细胞及管型明显多于非S-AKI患者,尿检评分>3分的患者发生严重AKI风险明显增加,且与肾小管损伤标志物水平升高相关[40]。然而,尿沉渣镜检对预测AKI恶化的敏感度较低,迄今尚无公认的预测S-AKI的尿沉渣评分标准[41]。近年来,寻求S-AKI早期诊断的无创性生物标志物研究越来越多,最受关注的有以下几种:(1)尿液中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2(TIMP2)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7(IGFBP7),均由肾小管上皮细胞表达,属于G1细胞周期阻滞中的调节蛋白,是细胞应激中的一种保护机制。[TIMP2]×[IGFBP7]是目前证据最强的AKI早期诊断生物标志物,已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上市用于评估发生中重度AKI的风险(商品名为“Nephrocheck”),在早期诊断AKI、预测死亡风险和肾脏预后方面均优于其他生物标志物[42-43]。Nephrocheck在除肾脏以外的脏器衰竭的脓毒症患者中不升高,因此对预测脓毒症患者发生S-AKI也具有较高的特异性。据一项多中心研究结果显示,脓毒症休克患者在液体复苏前如Nephrocheck阳性则发生AKI 3期的风险显著增高,而复苏6小时后仍为阳性则与不良预后(死亡或接受肾脏替代治疗)密切相关;此外,与复苏前后Nephrocheck均为阴性患者相比,由阴性转为阳性的患者复合终点事件(AKI 3期,接受肾脏替代治疗或7天内死亡)风险增加3倍,而由阳性转为阴性的患者较持续阳性的患者相比其复合终点事件风险显著降低[44]。另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患有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KDIGO)AKI 1~2期的脓毒症休克患者中,Nephrocheck>2 (ng/ml)2/1 000的患者在24小时内进展至AKI 3期风险较Nephrocheck<0.3 (ng/ml)2/1 000的患者增加4倍[45]。目前已有研究根据Nephrocheck进行分层做治疗干预[46],其临床治疗指导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据积累予以确证。(2)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其由激活的中性粒细胞和上皮细胞(包括肾小管上皮细胞)分泌,在肾小管损伤时其在尿液和血浆中的水平均会明显升高,对预测AKI、接受肾脏替代治疗及住院死亡均有较高的敏感性。NGAL在S-AKI患者的血清和尿液中均显著高于其他原因所致的AKI患者,在非AKI脓毒症患者中也会升高。但有研究表明,无论在脓毒症还是非脓毒症患者中,血浆NGAL水平均可预测AKI发生,只是在脓毒症患者中其截断值更高[47-48]。然而,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24]。(3)尿肾损伤分子-1(KIM-1),其在近端肾小管受损时也会升高,可较好的预测AKI,然而其在S-AKI中的研究并不多。有研究显示,入院24小时尿液KIM-1水平可预测早期S-AKI,未存活的S-AKI患者在入院24及48小时尿液KIM-1水平显著高于存活者[24]。(4)尿肝脂肪酸结合蛋白(L-FABP),在近端肾小管受损时其水平也会明显升高。有研究显示,入院时尿L-FABP水平可预测S-AKI死亡风险[24]。(5)血浆白细胞介素-18(IL-18)、前脑啡肽和胱抑素C也与AKI密切相关,在危重S-AKI患者血肌酐升高前即升高[4]。未来仍需更多大规模研究来验证这些生物标志物对S-AKI的预测效果。
在一项多中心观察性研究中,Basu等[49]在214例ICU住院的脓毒症患儿中探究了肾绞痛指数(RAI,即AKI的风险等级和临床特征评分的乘积,其中风险等级根据是否气管插管、使用血管活性药物、器官或骨髓移植、入住ICU等进行分级并赋予评分,临床特征根据肌酐清除率的变化程度及液体超负荷的程度进行评分)及几种生物标志物对AKI的预测作用,后者包括血浆NGAL、基质金属蛋白酶-8(MMP-8)及中性白细胞弹性蛋白酶-2(Ela-2),结果显示,使用RAI及其中任何一种生物标志物对AKI的预测作用均较单独使用RAI显著提高。在临床中将临床指标和生物标志物联合用于预测S-AKI可能会比单独使用其中一种更能准确的早期识别S-AKI。
四、S-AKI的防治
1.早期识别脓毒症,立即起始脓毒症集束化治疗(Sepsis bundle)[50-51]:脓毒症是临床急症,对脓毒症患者应立即(分诊1小时内)启动治疗和液体复苏。
(1)抗感染治疗:早期、有效的抗生素应用和感染源的控制是治疗脓毒症的基石,应在使用抗生素前需留取血培养,并于1小时内开始经验性、静脉使用广谱抗生素。有证据表明,脓毒症休克患者延迟使用抗生素会显著增高AKI的风险[9]。在抗生素的选择方面,应尽量避免使用肾毒性抗生素,如万古霉素、氨基糖肽类抗生素等,也要尽量避免造影剂的使用[52-53]。
(2)液体复苏:早期液体复苏是治疗脓毒症的关键,液体复苏首选平衡晶体液,如乳酸林格氏液,对低血压、乳酸>4 mmol/L或脓毒症休克患者,起始3小时至少输注30 ml/kg的晶体液[51]。此外,也要避免补液量过多造成的容量超负荷,通过动态监测容量状态和血流动力学状态来指导液体复苏。动态监测指标包括进行被动抬腿试验及补液试验,监测每搏量及其变化、脉压变化或超声心动图等。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也可以作为辅助手段指导复苏。相比于生理盐水,等渗晶体液含氯化物浓度更接近生理状态,且有证据表明,使用平衡晶体液复苏组的S-AKI患者30天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使用生理盐水组[54-55]。羟乙基淀粉应避免使用。在多数研究中,液体复苏中使用白蛋白是安全的,当需要大量晶体液维持血压时,可使用白蛋白增加胶体渗透压[51]。
(3)监测乳酸水平:对于怀疑脓毒症的患者,需要测量乳酸水平,对乳酸水平>2 mmol/L的患者需重复测量,监测乳酸水平的变化。在临床可疑的脓毒症患者中,乳酸水平还可帮助鉴别诊断脓毒症。此外,在脓毒症患者中乳酸水平与死亡率密切相关。
(4)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维持血压:对于低血压患者,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维持平均动脉压在65 mmHg以上,首选去甲肾上腺素。当去甲肾上腺素不足以维持血压时,可加用血管升压素。在一项随机对照试验(RCT)中,使用血管加压素的患者比使用去甲肾上腺素的患者接受肾脏替代治疗的比例略低[56]。如仍无法维持血压可考虑加用肾上腺素。对于容量、血压尚可,但持续低灌注的患者,可在去甲肾上腺素基础上加用多巴酚丁胺。在没有去甲肾上腺素的情况下,可使用多巴胺或肾上腺素,但需警惕心律失常[51]。
2.监测肾功能:脓毒症是AKI的高危因素,应对脓毒症患者密切监测血肌酐和尿量变化,尽早发现AKI。鉴于多数新型的生物标志物尚未在国内应用,可通过监测尿N-乙酰-β氨基葡萄糖苷酶(NAG酶)、尿α-微球蛋白、尿沉渣等或通过多普勒超声动态监测RRI等方法,尽早发现肾功能损伤。
3.肾脏替代治疗:至今对脓毒症患者启始透析时机、透析剂量和透析模式的选择仍存在争议。尽管部分研究显示,早期启始肾脏替代治疗有益,但近年来各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57]。多数观点认为,在AKI 3期时应开始肾脏替代治疗;在AKI 2期时,应综合患者一般状况、并发症情况进行评价,原则上应在出现明显AKI并发症前开始透析。有证据显示,在外科术后的S-AKI患者中,早期启始持续性的血液透析滤过治疗可降低死亡率[57-58]。持续性血液透析滤过治疗对血流动力学影响较小,且有助于清除炎症介质,更适合在S-AKI患者中进行。在一些RCT中,虽然高流量血液透析滤过(>35 ml·kg-1·h-1)更好地改善了患者血流动力学指标、器官功能,降低了炎症因子的水平,但这些提高并未改善患者的最终结局[59]。此外,高流量血液透析滤过可能会增加抗生素的清除。KDIGO指南推荐的流出液总量应达到20~25 ml·kg-1·h-1,即需要设定25~30 ml·kg-1·h-1的处方剂量[52]。
4.新型药物治疗:目前尚无特异性药物,多种新药正处于研发阶段。(1)人重组碱性磷酸酶(AP)是一种可在脓毒症时通过对内毒素去磷酸化来保护肾脏的内源性酶,可减轻炎症反应。在最近一项临床试验中,AP并未显著改善S-AKI患者1~7天的肾功能,但降低了28天及90天的死亡率[60]。(2)血管紧张素Ⅱ(ATⅡ)是一种血管收缩剂,对肾小球出球小动脉的收缩作用大于入球小动脉,从而改善肾功能,此外,ATⅡ不会像去甲肾上腺素一样引起肾髓质缺血缺氧。在一项预试验中,对儿茶酚胺耐药的脓毒症休克患者使用ATⅡ后血压好转,尿量增加;在另一项RCT中,ATⅡ可有效升高血管扩张性休克患者的血压,减少其他升压药物的用量,事后分析结果显示,ATⅡ组患者28天死亡风险降低了23%,且脱离透析的患者更多[61-62]。在最近发表的一项动物实验中,脓毒症小鼠肾脏血管紧张素1型受体(AT1R)表达下降,随后很快出现肾脏血流量增加、尿素氮及血肌酐水平升高及尿量减少,而静脉使用ATⅡ可预防该损伤,提示AT1R介导的ATⅡ信号传导对预防S-AKI具有重要作用[63]。(3)硫胺素(Thiamine)缺乏与无氧代谢及乳酸增加有关,在脓毒症患者中补充硫胺素可改善线粒体功能。在一项单中心的RCT中,接受静脉使用硫胺素的脓毒症休克患者AKI程度更轻,接受肾脏替代治疗的患者数量也更少[64]。(4)其他可能有效的药物,如Reltecimod(CD28拮抗剂)、左卡尼汀等,均正在进行临床试验。苯硫代丁酸是一种小分子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在动物实验中可促进斑马鱼和小鼠S-AKI模型的肾功能恢复,并减少肾脏纤维化,其临床应用前景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观察[65]。
五、S-AKI的预后
相比于非脓毒症AKI,S-AKI患者住院时间更长、院内死亡风险更高,其死亡风险随AKI严重程度的加重而升高[17,19,66]。在肾功能恢复方面,许多因素都会影响AKI后肾功能恢复,如基础肾功能情况、AKI严重程度、持续时间、AKI复发次数等。S-AKI与非脓毒症AKI患者肾功能恢复的比例接近,但S-AKI患者更易再次发生AKI,也更易进展为慢性肾脏病[4,67]。有证据表明,在曾患有严重脓毒症的患者中,90天内再次因AKI入院的风险显著高于未发生脓毒症患者[68]。现有研究结果认为,脓毒症中持续的炎症状态可导致持续的肾组织缺血缺氧,促进肾脏纤维化的发生与进展[21]。迄今为止,改善纤维化的药物,如缺氧诱导因子激活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等,仍处于动物实验阶段。因此,改善S-AKI肾脏预后的关键在于预防、早期识别与治疗,以及长期随访以进行合理的肾脏监测和肾脏保护。
综上,S-AKI是危重症患者中常见的合并症。尽管我们对其认识不断深入,至今仍无特效治疗方法,早期识别与预防是改善患者临床结局的关键。对发病机制的探索可为S-AKI的治疗提供新思路,各种生物标志物的研究有助于帮助临床医生尽早识别S-AKI并进行干预。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希望对S-AKI的治疗能有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