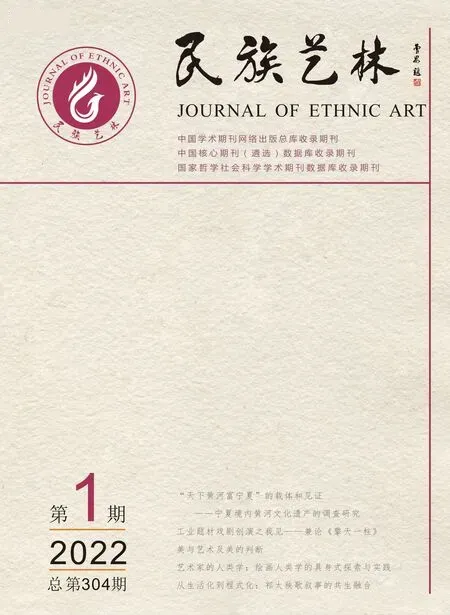从金批本《西厢记》分析金圣叹的戏剧批评观
盛雅琳
(山东艺术学院 艺术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揭开厚重的历史帷幕,在熠熠闪光的万千星辰中,金圣叹先生好似一颗启明星,点亮了中国文艺批评领域甚至是中国文艺创作领域。金圣叹出生于1608 年,在1661 年因卷入哭庙案被斩首,是我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名采,字若采,号圣叹,后改名为人瑞,自称作泐庵法师,江南长洲(今苏州)人。金圣叹好读书,更喜批书,常常直接嘲讽其他秀才的世俗和蠢笨,性格颇为孤高,为人率性爽朗,少年时便已经名声在外,以才子自居。[1]金圣叹自小学佛,劝人向善,倾向于佛、道二家的洒脱和自由,向往安逸平和的田园生活,与此同时也认同儒家学说中体现的入世思想。金圣叹赞同人生虚妄的观点,认为生命短暂似一瞬,一切都不可恃。
由于金圣叹在政治思想上仍旧具有一定的保守性,所以他虽然十分同情被欺掠的普通百姓,反对苛刻的官府政策,甚至支持民众的反叛行为,对强盗土匪表示强烈的不满,尤其厌恶水泊梁山的首领宋江,但最终还是认为礼法不可违抗。金圣叹宣扬儒家道德规范中的“忠恕”“孝悌”等礼法,然而又能够敏锐觉察并揭露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迫害,他认为男女之情与其他感情应当有所区分,其中圣人礼制不能强制废除情欲,所谓色欲之心也是出自自然的。《庄子》《离骚》《史记》、杜甫律诗、《水浒传》《西厢记》六部著作被金圣叹并称作“六才子书”,成为流传于世的经典,其中《西厢记》更是金圣叹重点推崇的作品,认为《西厢记》不是淫书,而是妙文。金圣叹褒扬张生和崔莺莺对抗现实的反叛之举,以其独有的戏剧批评观为《西厢记》立言,将《西厢记》的艺术表现性和时代抗争性进行了最大化的诠释。
古往今来,作为天下夺魁的《西厢记》,在封建社会的浪潮之中不断地被遗弃,又不断地被淘洗,总集本、丛书本、合刊本、单刊本等版本在文学界均有流行,其中在所有的批注版本中,金圣叹的《第六才子书》(即金批本《西厢记》)是流行最广的,在20 世纪50 年代以前国外汉学家的译本也大都是翻译的《第六才子书》本。因此当代学者对于金圣叹和金批本《西厢记》的讨论和研究也从来不曾停驻,综合相关著作和中国知网文章可见,在与“金圣叹”和“《西厢记》”有关的研究中,有直接研究金圣叹戏剧理论和戏剧审美批评的,有对比研究李渔或其他文艺批评家和金圣叹戏剧观的,还有研究金批本《西厢记》与王实甫《西厢记》异同的,也有框定背景进行多元视野下的金圣叹研究的,等等。
作为当今大众视野定义下的“清代才子”,金圣叹名扬历史的贡献还是在于他对相关著作的评点,也正是由此金圣叹独树一帜的戏剧批评观得以渐渐清晰彰显。不管是从戏剧情节的把握、戏剧人物的描摹,还是戏剧语言的处理上,均可从中提炼出带有金圣叹独特烙印的戏剧批评标准和原则,以金批本《西厢记》为着力点,可以细致梳理出金圣叹在戏剧情节、人物刻画及戏剧语言等方面的批评准则,从而完善金圣叹研究中关于戏剧批评观的空白,充实对金圣叹的文艺研究。
一、戏剧情节应许“因文生事”
吕效平教授在《戏曲本质论》中提及戏剧的艺术理想时表示,明清传奇的剧作家在完成一部剧作时,需要涵盖拥有各色特点的人物形象,从而建构出一个足够复杂曲折的故事,然后以此为基础来编织故事里的悲欢离合与嬉笑怒骂,借此传递出剧作家内心亦庄亦谐亦褒亦贬的审美感受和人生态度,他们以这个繁杂但是有内在秩序的世界架构为豪。由此可见,明清传奇的剧作家追求的是能够网罗整个世界的艺术,而不仅仅是征服戏剧舞台的艺术。[2]这就不难看出戏剧的情节设置对一部戏剧作品的重要性。传统元杂剧的体制应该是一个故事分为一本四折出演,而《西厢记》则是用五本共十二折来演出一个故事,情节上的独树一帜使得金圣叹也不禁赞叹《西厢记》的传奇体制与结构篇幅简直是令人惊异的。从金圣叹批注《西厢记》中,可以看出他对于戏剧情节方面的思考和探索,在具体的评点中也清晰地体现出他允许戏剧情节“因文生事”,强调情节间的前后承接,以及不要画蛇添足、狗尾续貂的批评标准与原则。
(一)“因文生事”
“因文生事”是金圣叹提出的在小说写作时运用的一种艺术虚构的方法,也就是他在金批本《水浒传》中所说的“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3]。而对于讲求史实的史书写作方法,金圣叹则提出“以文运事”,既强调作者要尊重“事”,同时又强调作者要注意运用“文”的技巧,是“因文生事”的对面。金圣叹“因文生事”的观点承认了小说创作的虚拟架构性,对戏剧故事的完成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其相关思想在金批本《西厢记》中就有所体现。
例如在“后候”一篇的总批中,金圣叹提到本无事忽有事的问题,认为“如方春本无有叶与花,而忽然有叶与花,曰生。既而一切世间妄想颠倒有若干事,而忽然还无。如残春花落,即扫花;穷秋叶落,即扫叶,曰扫”[4]。他以花和叶的开落盛衰入文,指出《西厢记》中“惊艳”一篇是“生”,最后“哭宴”一篇为“扫”,得以更加形象地说明“因文生事”中包含的“生”与“扫”的意义,也因此确立起小说戏曲等虚构的合理性。对照金批本《水浒传》中的情节发展,“因文生事”更是可见一斑,例如《水浒传》第九回,在被发配沧州的途中林冲被陆谦等人预谋陷害,幸亏有李小二的通风报信才使得林冲得以脱险。由此金圣叹认为,为了在后文能够照应“扫”的部分,所以先前“造出”了一段林冲搭救李小二的事情,李小二这样的人物设置也是因情节而生发存在的,随文起灭。再有第四十五回中的三打祝家庄事件,是因为时迁偷鸡被抓所导致的,金圣叹批注认为偷鸡被抓都是为了触发后文情节。学者张永葳认为金圣叹提出的“因文生事”的虚构论是把在文学中应用的虚构观念放置于小说领域,这和现代小说写作的虚构性是一致的。[5]金圣叹“因文生事”的理论论述无疑是将小说文体的虚构性进行了理论性的强化夯实。
(二)“承接前文”,有呼应有逻辑
一方面,金圣叹提出的“因文生事”观点确实对小说与戏曲故事虚构成分的合理性有一定的承认度,但与此同时“因文生事”的释义还需要包含在“削高补低都由我”之前“顺着笔性去”。由此,与“因文生事”类似的是金圣叹在情节上强调的“承接前文”遵循逻辑的原则与标准,情节的流畅性得益于整个故事的构造与连接,因此,在情节上的呼应性与逻辑性对整部戏剧作品的完成是十分重要的。
如金圣叹在《酬简》一折[赚煞尾]中写张生幽会崔莺莺后的不舍之情,“然此正是巧递后篇夫人疑问之根,最为入化出神之笔”[6]。由此,不难看出金圣叹对于“承接”的重视,认为此处是为后文老夫人生发疑问做了铺垫。同是在《酬简》一篇中,金圣叹分别在“猛见了可憎模样,早医可九分不快”和“先前见责,谁承望今宵相待”后批注:“紧承前患病一篇,妙。”及“紧承前前《赖简》一篇,妙。”[7]也不难看出金圣叹关于戏剧情节承接连贯的艺术批评原则与标准,极力赞美“紧承”前文的妙处。
对于戏剧情节和结构方面的探索,明代的曲论家王骥德在其著作《曲律》中对戏剧的整体结构问题着重进行了阐释,强调布局结构上的裁剪和凝练,认为戏剧布局应当井然有序,剧本整体应是有机统一体,要突出重点,要次序分明,要整体合一。李渔也将结构放置在第一位,认为“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后顾数折”[8]。具体的实现方法有“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由此可见,王骥德和李渔在戏剧情节上的美学思想与金圣叹所强调的戏剧情节应承接前文,有呼应有逻辑的观点是相统一的。
关于戏剧戏曲情节,吕效平教授在《戏曲本质论》中也有大篇幅的论述,对《西厢记》以及金圣叹的观点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在古代戏曲文学数百年的历史中,没有一部长篇作品像《西厢记》这样实现了戏剧性的情节整一;在古典曲学数百年的历史中,也没有人像金圣叹这样意识到情节应当具有的“整一性”。他赞美说,金圣叹的观点达到了中国古典戏剧情节艺术论的巅峰。[9]
(三)忌狗尾续貂
狗尾续貂是说将不好的东西接续在好的东西之上,现在多用在文学作品中,指作品的前后部分不相称。在金圣叹眼中,《西厢记》的后四篇便是狗尾续貂之作,他在《惊梦》一篇的最后一段批注中,连续发问:如何用得着续写?怎么可以续写?如何能够实现续写?都体现出金圣叹认为不必要有续篇的观点。在《泥金报捷》一篇的整体评点中,更是直言《续西厢记》的四篇他本来是不想收录的,但是为了警醒学者世人,也为了说明前十六篇到底超尘脱俗在何处,所以也进行了中肯的评点。[10]相比之下,从“芗”“螺蛳蚌蛤”等字眼也不难看出金圣叹对《西厢记》续篇的厌恶之情,对比前十六篇评点中出现最多的“妙”字,在《续西厢记》四篇中出现最多的字眼则是“丑极”等嫌憎之语。
金圣叹将《西厢记》结束在张生草桥店梦莺莺处,使其按照原小说《会真记》“始乱终弃”的情节走向否定了“大团圆”的结局,将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平添了一层悲剧色彩。虽然有人将《西厢记》定义为我国古典戏曲抒情喜剧的典范之作,但仍有不少学者也由此判断金圣叹戏剧思想中的悲剧意识较前人来看是有进一步发展的。对此,姚文放教授认为《西厢记》的情节发展已经将崔莺莺和张生对传统封建藩篱的冲突变成了张生对抗反面势力的斗争,这使得该剧的情感倾向与前文凸显的主题出现了严重偏移,虽然金圣叹还没有把戏剧主旨问题放到斗争对象的转移上来认识分析,但他显然已经意识到大团圆的结局与《西厢记》的本身意旨“其相去悬远,真未可以道里为计也”[11]。金圣叹不仅仅在对《西厢记》的批评中怒其续文“丑极”,在金批本《水浒传》中金圣叹也将原文改写,只留前七十回,将好汉的穷途末路淡化甚至删除,把英雄聚义梁山泊当成故事的结尾部分,试图只保留其认为能够反映作者思想和才情的精华部分。情节的过分冗杂赘述,显然是不入金圣叹眼的,在最精彩恰当的地方戛然而止,不是遗憾,而是意味悠长。
同样是抨击封建传统礼教的明代著名评论家李贽,除了闻名遐迩的“童心说”和“化工说”之外,戏剧评论的观点还有他在戏剧情节上追求繁简合宜的剪裁之美。裁剪之美即应当详细的部分就重墨描写,但不能累赘;应该粗略的部分就简单提及,但不可缺少。戏剧剧本不加裁剪,片面卖弄辞藻,重复堆砌,必然使人因烦冗生厌。李贽在批评《杏园春宴》时提及对《西厢记》的褒扬,认为烦冗到使人生厌的句子,是比不上《西厢记》繁简得当的语言的。由此可见,金圣叹对戏剧作品狗尾续貂行为的厌恶之情不无理论渊源。
二、戏剧人物需要强化个性
黑格尔在《美学》关于戏剧的部分里强调,人物的性格是戏剧形象的核心所在,他认为伦理的力量和个人结合成为情致,情致虽然是人物性格的核心但并不是人物性格的本身,只有处于具体活动中的情致才是人物的性格。[12]对于戏剧人物的个性化刻画,金圣叹在金批本《西厢记》中也有明确阐述,此观点是与很多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相同的。戏剧同电影等艺术表现形式一样,可以看作一种讲故事的方式,而戏剧人物承载戏剧情节的发展,所以一部优秀故事的完成自然不能缺少对典型人物的塑造。总结来看,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就是需要对人物个性进行重点强调,有个性的人物形象才能成就典型的戏剧故事人物。而强调人物性格的个性化,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物的动作语言等应当与其性格相匹配,从而使得戏剧典型人物得以成功塑造。
(一)强调人物性格个性化的重要性
显而易见,《西厢记》中的主要人物有崔莺莺、张生、红娘三个人。他们各具秉性气质,不管是崔莺莺的知理千金气,张生的蹁跹君子气,还是红娘的活泼豪爽气,都是这个人物所特有的性格气质,也是这个人物树立在字里行间的自我标识。例如在金批本《西厢记》的“惊艳”一篇中,有描写崔莺莺的句子:“宜嗔宜喜春风面。偏宜贴翠花钿。宫样眉儿新月偃,侵入鬓云边。”[13]金圣叹评点说,这仿佛是双文侧转身来,“翩若惊鸿”的形象跃然纸上,不禁赞叹到这才是鲜活的崔莺莺,而不是泥塑一般的崔莺莺。[14]“春风面”“新月偃”“鬓云边”都成为崔莺莺这个人物最灵动的写照,既为相府小姐,便不能是“躁秋风”,或者“残月升”之类的形容,混淆了人物性格的鲜明性。
李渔对于戏剧人物的刻画也是要求重视人物性格的,他具体论述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市浮泛”“欲代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着重强调所塑造人物性格的个性化,认为应该避免雷同式的罗列。[15]想做到如此,便要求剧作家充分融入角色内心,感触人物的所思所感。
关于戏剧人物个性化的塑造在西方戏剧中也有所体现,古代悲剧重视动作和情节,近代的悲剧则是把人物的性格放在首位,着重强调人物性格完整细致的刻画。黑格尔认为,古代悲剧中的人物性格是简单的,缺乏个性和对人物个性的发展,是“雕塑性”的。然而以莎士比亚悲剧为代表的近代悲剧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是“高翔于他人之上,达到一个几乎不可企及的顶点”[16],其中的人物性格甚至是能够左右戏剧情节推进和发展的,例如哈姆雷特的性格优柔寡断犹豫不决,这就使得他为父报仇的情节一再延宕,最后成为一出性格悲剧。不管是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提高,还是戏剧人物性格的坚定性保持,都体现出戏剧人物性格个性化的重要,由此而言这与金圣叹的戏剧批评标准是不谋而合的。
(二)动作语言与人物性格相匹配
因人生百态,万物皆不同,由于生活背景、家教涵养、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所以必然会导致每个人都是一片不同的树叶,这里的“不同”不仅包括外貌、形态,也包括为人处世的方式,面对问题的处理等许多或大或小的方面,因此在进行人物刻画时一个人的动作语言与其性格的匹配度必然是需要一致的。简单说来就是,大家闺秀断不会说出市井屠夫之语,而街头商贩也定然不能做扭捏小姐之态。
在金批本《西厢记》的“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的第五十五条中,金圣叹对此进行了较为明确的阐述。例如描写张生:“便真是相府子弟,便真是孔门子弟。异样高才,又异样苦学;异样豪迈,又异样醇厚。相其通体自内至外,并无半点轻狂、一毫奸诈。”[17]关于张生的人物形象,彭隆兴在《中国戏曲史话》中也有描述:“张君瑞——亦出身没落贵族家庭,但他热烈追求爱情,表现了他对封建礼教的不满与反抗。他具有大胆、天真、坦率、真诚的性格。但是,由于他受封建教养的熏陶,表现出知识分子软弱与平庸的一面。”[18]在“惊艳”一篇中的“尽人调戏,着香肩,只将花笑拈”是写张生与崔莺莺的初次相见,金圣叹于此处评点崔莺莺见到客人便走开这一行为,认为:“此是千金闺女自然之常理,而此处先下‘尽人调戏’四字,写双文虽见客走入,而不必如惊弦脱兔者,此是天仙化人,其一片清净心田中,初不曾有下土人民半星龌龊也。看他写相府小姐,便断然不是小家儿女。笔墨之事,至于此极,真神化无方。”[19]由此能够看出金圣叹关于人物刻画中对人物动作语言与其性格相匹配的准则和要求。张生不轻狂不奸诈,莺莺是千金似天仙,也正是张生和崔莺莺如此的人物性格,所以才恰到好处地使得《西厢记》中的一见钟情、弹琴赋词、私订终身等故事情节的推进成为可能。
与之类似,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于人物性格也在其戏剧美学思想上有所概括。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6 章中表示,悲剧是对行动的模仿,模仿这一动作的完成便需要人物,其中这些人物的思想和性格能够体现他们所处的“属类”,人的成功和失败取决于自身行动。[20]由此能体现的便是金圣叹批评观中戏剧人物语言动作与其性格的高匹配度。亚里士多德也对戏剧人物的刻画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物性格的完善最好是满足好、适宜、相似、一致等四个方面。虽然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性格”与现在所述性格有异,但仍能从中读到其关于人物及人物性格的重视性。
三、戏剧语言当要“清丽”含蓄
写《太和正音谱》的明初戏曲评论家朱权用“花间美人”四字高度评价王实甫的艺术风格,认为王实甫的斟字用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21]。对此吴国钦先生也认为这个评价一语中的,“花间美人”这四个字准确概括了王实甫的语言艺术风格,达到了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的精妙境界。[22]金批本《西厢记》被有些学者定义为“非演出本”,从金圣叹对《西厢记》的改编视角来说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戏曲戏剧的剧本原本是为了搬上舞台演出而作的,金圣叹则不考虑演出问题,将其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出发进行了文学性的改编,所以应该说对戏剧语言的评点是金圣叹评《西厢记》的重要部分。
(一)同而有“变”为妙
“和而不同”在很多场合中被提及,其中“和”传递出“和谐”的含义,千篇一律相同的描述是固然不能成为妙文的。王实甫作为中国戏曲史上“文采派”的杰出代表,其作品中绮丽清新的词句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对此金圣叹自然是毫不吝啬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例如在《酬简》一篇中金圣叹认为“伫立闲阶”“只用四字,便避过三之三[乔牌儿]‘日出时想月华,捱一刻似一夏’等文。”[23]两处都是写崔莺莺迟迟不来,张生久久等待,金圣叹认为“避过”为妙,而不是继续相同的重复与复制为妙。《西厢记》的故事可以说在“长亭送别”之后便是充满思慕与等待的,若全篇的等待之情皆用“捱一刻似一夏”便无法体现出人物心理层次的变化,所有的等待就会沦为寻常,自然也无法体现出语言的表达层次,更无法戳中读者的心情。在续之二《锦字缄愁》一篇中的[耍孩儿]“放时须索用心思,休教藤刺儿抓住绵丝。高摊在衣架上,怕风吹了颜色;乱穰在包袱中,怕挫了褶儿。当如是,切须爱护,勿得因而。”后金圣叹批注“惜与前文‘休做枕’‘休便扭’同耳。”[24]一个“惜”字可以看出金圣叹对于此句的惋惜之感,虽然也是可赏佳文,却遗憾与前文的表述相同没有变化和新意。
两相对比之下,不难确认金圣叹对戏剧语言“变化”方面的期待与要求,不管是对人物等待心理的多样表达,还是对前后情境的恰切把握,都需要倾向同而有变的呈现高度才能称妙。
(二)婉转不白为妙
回望古代中国的情感表达,不管是戏剧还是诗歌小说等其他文学作品形式,含蓄婉转的表达方式便一直是主流,虽然《西厢记》的故事在现在许多著作的阐释中均肯定了其冲破传统藩篱的重要意义,但是作为文字表意的艺术品,其语言上的传递却仍旧延续着中国含蓄婉转的传统表达风格,不曾妄自直白,也没有逾越国情的不妥帖。
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金圣叹提及写文章的妙法“是先觑定阿堵一处,已却阿堵一处之四面,将笔来左盘右旋,右盘左旋,再不放脱,却不擒住”[25]。后文他又用狮子滚绣球做比喻,说明文章的语言需要婉转,而不是过分直白地表达,爱慕便说爱慕,想念便说想念。戏剧语言上含蓄婉转的要求,李贽也有与金圣叹相同的评点标准,李贽所追求的蕴而不露的含蓄美便与金圣叹狮子滚绣球的比喻含义一致,他认为通过戏剧情节的安排与戏剧语言的渲染从而设置一种使观众急切期待的悬念和伏笔是一种含蓄之美,铺陈直白的陈述则不能达成这样跌宕引人的戏剧效果。
金圣叹向来推赞张生和崔莺莺冲破封建藩篱束缚的追求和反叛,在《酬韵》一篇中,崔莺莺在听到张生的诗之后便依韵和了一首:“兰闺深寂寞,无计度芳春。料得高吟者,应怜长叹人。”[26]这成为在溶溶月色下崔莺莺最大胆的心意表达,封建礼教压抑下的愁绪泉涌而出,只是再大胆的叛逆宣言也需要以诗寄情,也需要将万千思绪灌注诗中。
再有如《哭宴》一篇中,写崔莺莺等人于长亭设宴送张生赶考,莺莺在临行前叮嘱张生,无论是不是能得官,都要尽快回来。张生十分讨巧地答:“状元不是小姐家的,是谁家的?”金圣叹于此处批点“又妙又妙。谦未必得状元固不佳,夸必定得状元又不佳。状元原是小姐家的,精绝!”[27]不可谄媚,不可不谦,所以说状元必定是小姐家的,让人定神细思后得叹妙绝!这是张生说话的艺术,也是《西厢记》语言千回百转的魅力。
(三)“清”“丽”并举为妙
不管是对人物的生动描摹,还是对环境的有效衬托,《西厢记》中语言的清新秀丽历来被世人所赞,一度被称为“语言艺术的宝库”,其中所涵盖的多种风格的艺术语言,以及王实甫驾驭语言技巧的才能,也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在《酬简》一篇[赚煞尾]中细致描写崔莺莺的曼妙之姿,也正是表现张生的留恋之心:“春意透酥胸,春色横眉黛,贱却那人间玉帛。杏脸桃腮,乘月色,娇滴滴越显红白。”[28]金圣叹赞叹:“奇句,妙句,清绝句,入化句。”“从来丽句不清,清句不丽。如此清丽之句,真无第二手也。”[29]又如“拷艳”一篇中也有对莺莺举手投足的清丽描写,金圣叹评点如此是:“芙渠出水,未有如是清绝,如是艳绝,如是亭亭,如是袅袅矣。”[30]崔莺莺的清丽之感与文字的清丽之感有效融合,跃然面前,金圣叹对其语言风格的喜爱之情可见一斑。
异于金圣叹观点的是明代戏曲家徐渭,他提出戏剧语言的“本色论”,认为戏剧语言要浅白易懂,平实朴素,因此华丽漂亮的语言及过分修饰的修辞字句都成为徐渭批评的对象,因此即便《西厢记》在思想内容上被给予高度评价,也因其字句风格被徐渭直接抨击,在徐渭看来过分绚丽的文字非但不能呈现人物的真性情,反而会削弱戏曲的表达效果。而金圣叹作为立足戏剧剧本本身的批评家,对于戏剧语言有其标榜的特有标准和审美观点是可以理解的,《西厢记》语言上独有的清丽之风也恰好能够描摹一出才子佳人的绝唱。
《西厢记》中平朴清丽并存的句子比比皆是,吴国钦也在《西厢记艺术谈》中直接赞美《西厢记》全剧的语言都是秀丽华美并且通晓流畅的,认为其语言是达到了只见天籁、不见人籁的境界,更是将中国古典戏曲文采派语言艺术最高成就的位置留给了《西厢记》。[31]
四、金圣叹批评观在中国古代艺术批评史上的意义
以金批本《西厢记》为典型代表,金圣叹的戏剧批评观及戏剧美学思想对戏曲地位的成就确已产生了不可替代的推举作用,成为我国古代戏曲理论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时期,对《西厢记》的批注一时蜂起,评点家众多,其评注大多为短小精悍的词句,大多数采用随笔、札记的形式,散落在作品评论家的文集作品中,除了极少的《古本戏曲丛刊》外,几乎没有系统总结的古代戏曲评点本流行于世。从相关批评本作品来看,金圣叹独创了一种紧密靠近文本的批评方法,使得他需要立足戏剧文本自身,从而将自己的批评观点寓于其中。金批本《西厢记》对人物语言、人物心理、环境氛围、情节设置、剧本语言等均有评点,涉及的方面着实广阔,这也说明金圣叹的批评完成是得益于戏剧文本本身的。不管是对《西厢记》文本续作的质疑,还是他在原作基础上进行的“圣叹文字”的改写,都是在考虑其自身的故事发展和人物设置等情况下完成的,尽管有“因文生事”的主张,却也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戏剧故事的本真还原。
吴国钦教授也认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才子佳人的作品是令人不喜的,去掉题材和主旨的原因,主要归结为戏剧家不善于描绘“这一个”才子或是佳人的性格特征,甚至连外貌的描摹也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千篇一律。[32]因此避免千人一面的人物静态描写,重点刻画典型人物,使得人物活灵活现是王实甫经营戏剧人物的成功之处,而金圣叹对《西厢记》中人物详略的评点也正是与王实甫塑造西厢人物的写作特点相吻合的。对人物的批评原则与标准在上文已有详细的论述,关于评点人物的方法金圣叹也有其自己的风格和坚持。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的第四十七条,金圣叹也强调《西厢记》只是写崔莺莺、张生、红娘三个人。[33]与《西厢记》的人物写作技巧类似,金圣叹在评点其中的人物时,也是有选择地突出重点的,对崔莺莺、张生、红娘进行了浓重笔墨的评点。
对于金圣叹这种渗入式的批评方法,有人认为需要更加忠实地贴近文本作品,从而使得对原作的阐释更加精准和有力,而金圣叹却偏偏在立足作品的基础上将原作进行了更加合理化的修改。其一,体现在上文已经写到的“腰斩水浒传”和金圣叹认为的“王西厢”最后的内容为续篇。另外,在金批本《西厢记》中的许多细节中,金圣叹也进行了更加合理化的改写。例如,在王实甫笔下,红娘称呼崔莺莺为“姐姐”,而在金批本《西厢记》中金圣叹均将称呼改成了“小姐”,原因是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相国人家自然会有等级森严的家规,因此,金圣叹认为红娘作为相府丫环需要称相府千金为“小姐”更合适红娘的身份设定。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第七十至七十二条中金圣叹明确提出:“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天下万世锦绣才子,读圣叹所批《西厢记》,是天下万世才子文字,不是圣叹文字。”[34]从中可见金圣叹关于文本内容的理性判定。虽然金圣叹对《西厢记》的原文改动较大,遭到了不少的非议和质疑,但金批本《西厢记》在中国戏剧史上的推动作用是无可争辩的。
五、结语
《西厢记》中千古传诵的那句“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35],传达出的不仅仅是对普天下有情人的美好祝愿,更是《西厢记》作为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檄文,直击人心,也正是因此《西厢记》被迂腐湮灭,被许多朝代定义成淫书。金圣叹坚决反对“淫书说”,直言《西厢记》“乃是天地妙文”[36]。李渔评价金圣叹评注的《西厢记》说道:“能令千古才人心死。”[37]认为自从《西厢记》问世后至今的四百多年中,有数以千万的人推崇《西厢记》的艺术价值,但是能够一一指出其中原因的,确实只有金圣叹一人而已。可见,金圣叹的评点有力推动了《西厢记》在中国戏曲中的地位建立,通过细致剖析《西厢记》浸润在字里行间的艺术魅力和精神力量,使得《西厢记》从禁毁戏曲小说之列得以上升到同《庄子》《史记》等文学经典同样的高度。
在肯定金圣叹艺术成就的同时,李渔作为实践型的戏剧家,敏锐精准地认识到了金圣叹的评点具有忽略戏剧舞台性的弊端,“圣叹所评,乃文人把玩之《西厢》,非优人搬弄之《西厢》也。”[38]虽然金圣叹评点的《西厢记》极其注重细节,每一处都进行了细致地评注,但是戏剧作为一门综合性极强的艺术表现形式,最终需要呈现在戏剧舞台之上,从而使得观众去欣赏和接受,金圣叹的批评片面专注于戏剧文本的自身呈现,在语言表现、情节设置等方面着重强调,忽略其戏剧性,进而影响了其探索戏剧艺术美学规律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另外,由于生活背景和人生经历等因素的影响,金圣叹的部分戏剧乃至艺术思想中仍然有唯心主义的残余。姚文放在《中国戏剧美学的文化阐释》里谈到金圣叹的悲剧观和离别思想,认为金圣叹已经敏锐地觉察到离别的结局具有更符合封建社会的现实性,在封建礼教的摧残和封建家族的阻挠下崔莺莺和张生的离别是必然的,于情于理都更切实,但是佛家所讲的因果轮回、五蕴皆空思想和超脱凡世思想也在其中有所体现,趋于用虚无主义和神秘主义来解释这种生离死别,因而最终不能够揭示其社会根源。[39]呈现出金圣叹观点阐述的一些弊端。
虽然在时代语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金圣叹的戏剧批评观仍然存在一些局限,但是瑕不掩瑜,金圣叹作为中国批评史上不可缺少的一个维度,他独树一帜的批评观弥补了中国古代批评史上的空白,使得戏曲戏剧的批评更加清晰地进入大众视野,引起众多关注,他在中国戏剧批评史乃至艺术批评史上的地位至今仍然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