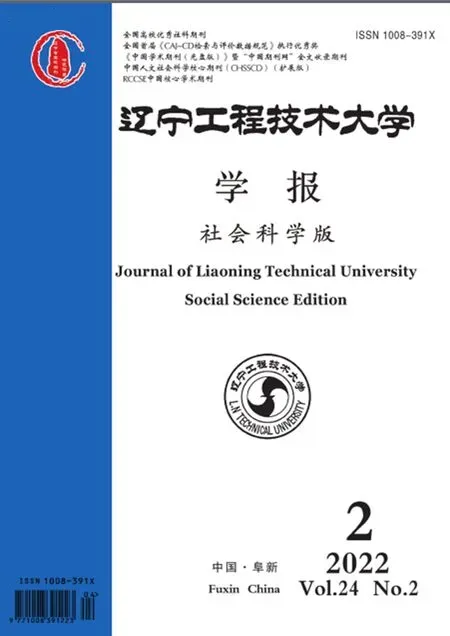《大金国志》研究综述
刘思辰
(渤海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0 引言
《大金国志》是一部有争议的史书,20世纪80 年代以来,关于这部书的点校整理、作者与成书年代、史料来源、价值等多有探讨,试作综述如下。
1 《大金国志》点校整理
《大金国志》共40 卷,是记载金朝始末较为系统的史书。20 世纪80 年代,崔文印以扫叶山房本为底本,除对校了天一阁钞本外,还吸收了章钰、傅增湘等人的校勘成果,完成了《大金国志》的点校工作。崔文印的点校整理还恢复了明钞本诸帝纪年的天头标目,补录了明钞本的3 个重要附件,即《经进大金国志表》《金国初兴本末》《金国世系图》,又新增《金国九国年谱》。为了便于研究,还附录了《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之《女真传》、卷二四四之《金虏图经》、卷二四五之《族帐部曲录》,以及一些重要题跋[1]。点校本《大金国志》的问世,为人们了解《大金国志》提供了较为清晰的版本,有力地推动了学界对《大金国志》的研究。
2 《大金国志》作者及成书年代
《大金国志》署名宋宇文懋昭,但宇文懋昭在《宋史》中并无记载。最早提及宇文懋昭的是元代学者苏天爵,他在《三史质疑》中第一次提及宇文懋昭的名字:“叶隆礼、宇文懋昭为辽金国志”[2]。苏天爵与宇文懋昭生活在同一时代,而且对辽、金史籍较为了解,他仅是陈述宇文懋昭撰写《大金国志》这一事件,并不怀疑宇文懋昭是《大金国志》的作者。
近年来,许多学者也对《大金国志》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进行了考证。崔文印认为《大金国志》并非后人假托宇文懋昭之名杂抄诸书而成,它确实出于宇文懋昭之手[3]。赵葆寓认为虽然此书疑点较多,但宇文懋昭确有其人。在探讨作者的同时,赵葆寓还指出《大金国志》引书较多,标明出处的只有《松漠纪闻》和《契丹国志》,而明代黄居中曾记载,《契丹国志》的作者叶隆礼是元朝人。余嘉锡和李锡厚也先后对叶隆礼生平进行考证,认为《契丹国志》应为元朝时期所著,那么大量引用《契丹国志》的《大金国志》只能是出自元朝人之手。因此,赵葆寓提出以下两个观点:首先,《大金国志》成书于元朝,但具体时间还需新材料确定。其次,《大金国志》的作者是宇文懋昭,但《经进大金国志表》并非宇文懋昭所作,而是至正三年以后他人伪作[4]。崔文印在点校《大金国志校正》后又提出补充认识,即 《大金国志》由两部分组成,宇文氏的“原作”和元人的“续作”,并指出原作者写法有纲有目,而续作者缺乏必要的常识和史学修养,导致后面部分错误百出[5]。都兴智并不认同“原作”与“续作”这种观点,他认为《大金国志》一书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一样,都存在对史料进行歪曲和篡改的现象,但他指出《大金国志》当为宇文懋昭所著,不是后人假托其名伪作。另外,都兴智还提到引起大多数人质疑的《经进大金国志表》与书中内容矛盾,应当是后人伪作而成,其中所述的宇文氏生平是不可信的。他在考证两书史源时发现,《大金国志》卷一误记阿骨打为“杨割太师之长子”与《契丹国志》卷十“辽主延禧初立之年,杨割死,阿骨打立”的内容是一致的,说明该书辑成时间为《契丹国志》之后。而关于《契丹国志》一书,经学者考证刊行于元代,所以宇文氏应是元朝人而不是宋朝人[6]。邓广铭在考证 《大金国志》史源时,前后撰有两文,一文认为《大金国志》是由编书人从许多书册中拼凑而成的,而不是作者凭空编造出来,还是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7]550。另一文认为《大金国志》一书全部出自一人之手,其前后卷的编辑水平之所以有高有低,参差不齐,是由于抄录的资料程度不一,并不是前十几卷为宇文懋昭所撰,后面若干卷是他人假托宇文懋昭之名伪作[7]558。另外,邓广铭发现钱大昕曾为《大金国志》一个抄本所写的“跋语”,断定其书应是元初人所著,而宋人的著作中没有体现有关这部书的任何文字,也能证明这一点,且清代学者李慈铭也对该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进行考证并提出怀疑。自此,邓广铭断定《大金国志》是伪书,包括作者宇文懋昭也是宋元间人编造出来的[7]559。刘浦江在探究《大金国志》作者时注意到,王士禛“或云宋人伪造”为最早论及《大金国志》真伪问题的人,还提出“恐经后人窜乱,非复(宇文)懋昭原本”的结论,作者肯定钱大昕、李慈铭和余嘉锡提出《大金国志》出自元人之手的看法是正确的[8]。艾慧认为,作者在《经进大金国志表》中自述的条件与撰写《大金国志》所需的条件是相符合的,坚持宇文懋昭为《大金国志》的作者[9]。
关于《大金国志》的作者问题,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宇文懋昭所作,另一种是元人假托宇文懋昭之名所作,前者认为历史上确有宇文懋昭其人,只是史料中无记载,后者认为《大金国志》只是元人杂编之作,并非一人之书。至于《大金国志》成书年代,多数人认为是元代成书。
3 《大金国志》史源及史料价值的分歧
《大金国志》杂抄各种书籍,史料来源复杂,史料价值多被质疑。元人苏天爵评价《大金国志》,“其说多得于传闻,盖辽末金初稗官小说中间,失实甚多”[2]。崔文印对《大金国志》进一步探究,发现在十五卷以前,其纲类文字主要取材于《中兴小纪》《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以及《宋十朝纲要》等书。而目类文字,即大段史文的征引则以《金虏节要》《松漠纪闻》为主。崔文印认为宇文懋昭的原书并不是一部记述金朝始末的全史,它只是一部记述从金太祖到金海陵王四朝的开国史,但确实有参考价值,然而“续作”部分出现了很多的错误,如歪曲史实、无中生有、疏于考证、浅陋无知、抄书错误等,使这部分的史料价值大为降低[5]。都兴智指出,本书前十五卷诸帝纪部分、记载典章仪制的诸卷主要取材于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洪皓的《松漠纪闻》《大金集礼》等著作,而《三朝北盟会编》又主要摘取赵良嗣的《燕云录》、马扩的《茅斋自叙》、张汇的《金虏节要》《正隆事迹记》《炀王江上录》等著述中有关金人和宋金关系史事的记载。在对史料来源进行考辨时,都兴智发现其取材的著述基本都是作者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之事的纪实,除了作者出于某种目的对原史料进行篡改、歪曲和误记以外,基本可视为信史,有可参考性[6]。邓广铭从《大金国志》中摘取一部分史料,发现作者把《南迁录》的绝大部分进行稍加改动,如改换年号,把史事加以割 裂,化整为零,分别插入金世宗、金章宗、卫绍王和宣宗的《本纪》当中。编书人还摘抄了《四库总目提要》中的许亢宗《奉使行程录》、元好问《中州集》中的小传,其中《海陵炀王纪》采自张棣的《金虏图经》。另外,本纪各卷或采自《三朝北盟会编》,或采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或采自刘时举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等[7]545。编者在撮抄这些书籍时,对其中的文字进行颠倒或删减,导致《大金国志》中的史料存在一些问题。刘浦江肯定王士禛的看法,即《池北偶谈》卷一八《契丹、大金二国志》中的说法,“《金志》记载与《南迁录》多相合,与史所谬。其《文学传》则全节取元好问《中州集》”[10]。同时刘浦江指出,此书内容歪曲史料、疏于考证、缺乏常识、混淆史实、断章截句而且辞不达意,实在是错误百出。他认为《大金国志》是杂抄旧史而成的一部伪书,虽不能全盘否定其史料价值,但其内容真伪杂糅,应该非常谨慎使用[8]。李秀莲在探究《大金国志》资料来源时,推测其来源复杂,有来自话本小说中的“传闻”、宋人和金人的史籍,以及一些金朝廷官方的资料。虽有诸多不足,但不能因此否定《大金国志》的价值,她认为《大金国志》体例多变,根据资料取舍选择体例,资料丰富有事可记时使用纪传体,史料缺乏无事可记时使用编年体,这样才能在资料缺乏的情况下撰成“首尾完具”的金朝历史,而且与《金史》相比记录更为详细,补充了《金史》不足之处[11]。潘瑞国认为《大金国志》的若干内容来自《松漠纪闻》,部分内容直接抄录,稍作修改甚至颠倒顺序,肯定《松漠纪闻》是《大金国志》的史源之一。不过因为《松漠纪闻》内容较少,大多是对金国初期的记载,所以占的比重很小。他指出《大金国志》的大量文字来自于《九朝编年备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宋通鉴》《松漠纪闻》《南渡录》《南迁录》等[12]。冯俊认为《大金国志》对帝王进行论赞,与《金史》对帝王的回护相比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也使后人重新重视正史、编年中忽略的事件、人物,充分肯定了《大金国志》的史学价值[13]。
综上,古今学者对《大金国志》的史料价值褒贬不一,有关该书史料价值主要集中在作者对史料的修改上。一部分学者认为作者对史料进行篡改后使史实发生了变化,参考价值不高。一部分学者认为此书虽是杂抄各种书籍,但里面也保存了许多已佚的书籍和文献,还是具有可参考性的。
4 《大金国志》与《契丹国志》的关系
大多数学者认为《契丹国志》与《大金国志》有较多相似之处。都兴智在考证其史料来源时,发现《大金国志》部分内容抄录了《契丹国志》一书,并且毫无改动地沿袭了原文的错误记载[6]。邓广铭认为《契丹国志》与《大金国志》不但可能出于同一时期,还极有可能是同一人或同一伙人所伪作,前后各卷之间的水平参差不齐是由当时的资料所决定的[7]545。刘浦江梳理相关成果认为,《契丹国志》有《经进契丹国志表》,《大金国志》也有《经进大金国志表》,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标榜书籍曾经上奏南宋朝廷,而且两书的体例如出一辙,除了纪传之外,书中的某些内容也表现出非同寻常的一致,缺乏历史常识、篡改史料,以及杂抄诸书也成为两本《国志》共同的问题[8]。所以刘浦江认为,两部《国志》存在着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主要表现在3 个方面:两书存在某些与众不同而且明显与史实相悖的记载;两者在抄录时选择书籍相似;抄书的错误问题相同,两本《国志》可能不仅仅是伪作、相互抄袭的关系,还极有可能出自一人之手[14]。舒习龙在探究《契丹国志》的史学价值时,提到叶隆礼在著书时重视史书体例,根据所撰史事的实际情况和表达意图的需要来进行适当的调整[15],与李秀莲在阐述《大金国志》价值时所提到的没有确立统一体例的观点大致相同。实际上,两本书体例混乱应是由当时的资料决定的,编书人只是根据资料的多少进行撮抄,并没有考虑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两部《国志》体例混乱,极有可能是同一伙人所伪作。
5 结论
近年来学界对《大金国志》的研究,关于其作者、成书时间基本已达成共识,但对其史源与史料价值的认识尚有分歧。学术界普遍认为《大金国志》出自元人之手,除上文提到的论证角度外,还可以从元人编纂史书“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念角度进行分析。在元人编纂的《宋史》《辽史》《金史》中,充分体现其善于总结历史,注重古今之间的关联,并且对3 个政权进行了客观分析。而在《大金国志》中,作者也表达了与之相同的历史观念,如在论述金章宗时,虽对金章宗任用奸佞导致朝廷腐败进行批评,但也肯定金章宗的历史功绩。对卫绍王的评价也是如此,虽否定了他的无为,但也肯定他的个人品质以及在危难关头力挽狂澜的勇气。从中可以看出,其并非简单地罗列史事,而是通过探讨历史人物的行为与思想去辨别是非。此外,书中对宋、金两国事不回避,以及对前朝政权的剖析,目的在于对当朝统治者产生影响,希望其以史为鉴。至于《大金国志》的史源问题,仍存在很大的争议,随着元代文献整理、研究的深入,对其史料来源将会有更深入的认识。《大金国志》的史料价值在学术界仍然存在分歧,其内容和逻辑结构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大金国志》对于史料相对匮乏的金朝历史研究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应该受到金史研究者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