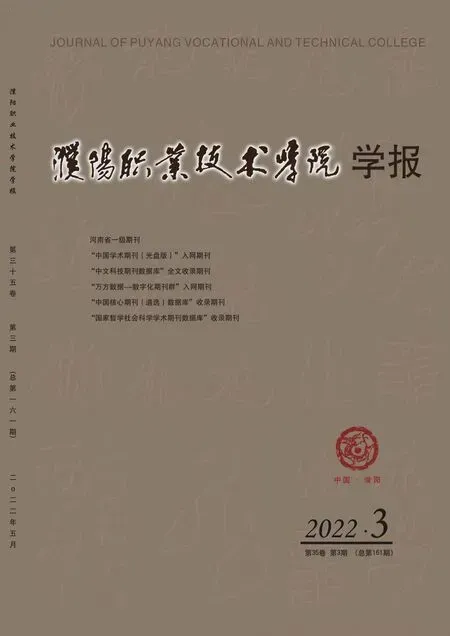主观真实的诞生——《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原点”建构
刘钰洁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1987年,余华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这位先锋小说家自此横空出世。在结束了此前的写作训练后,余华坚定地转向了先锋一派。余华不止一次地谈及这篇小说对其创作生涯的开创性意义:“当我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后,我从叙述语言里开始感受到自己从未有过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一直往前行走,使我写出了《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等作品。”[1]8因此,李雪称这篇小说为余华“整个创作的‘原点’”[2]14,在其中,余华开始建构自身的文学真实观,他将其称为“包括想象、梦境和欲望”[3]147的主观真实。在此种真实观的引导下,他用荒诞的暴力叙事配以陌生化的语言,形成了鲜明的余华风格,凸显了自身精神世界即“内宇宙”[4]11的复杂与独特。自此开始,他一步步走向先锋,其作品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正因《十八岁出门远行》的独特地位,学界对它尤为重视。单篇研究中多着眼于其主题意旨或是文本的延伸含义如文革伤痛记忆等的探讨,而对余华创作的宏观研究也或多或少都会出现这篇小说的身影。
本文在整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图着眼于其“原点”建构过程。余华在这部小说中寻求“内心的真实”,他为何会产生这种想法?他所寻求的别样真实在文本中是如何体现的?一些在先前研究中被忽略了的文本细节回答了这些问题。本文着力分析此“原点”生成的原因、表现、意义,这相较于此前的单篇研究更注重文本研究的整体性与深入性。此外,既然是“原点”,在话语上就不免“稚气未脱”,这也是学者们较少对此小说进行叙述研究的原因。但从细部来看,此中文字的局限更辅助突出了“原点”含义,一些在后续创作中被余华有意隐藏起来的创作意图在这些“初次加工”的文字中能够展现得更加清晰。余华后续创作的光亮实在不应黯淡了此篇文本的意义,以动态的过程完整解析《十八岁出门远行》的生成,从写作起点出发观照他的审美品格与叙事生成,认识与理清余华写作此篇小说的缘起与意义,有助于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余华的先锋话语实践,这在作家创作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阅读《十八岁出门远行》,读者能够重回那从“能指与所指断裂带”[5]48中引申出来的文学时代,去感受业已平静的文学水潭深处经大波动后形成的礁石,回望那场曾经汹涌的文学变革。这不仅仅是一场文学史的怀旧,要知道,80年代的先锋文学“宛如一个象征”[6]1,“正是对80年代的告别才造就了那一时代的繁荣表象”[6]2。对先锋浪潮中的代表作品进行品鉴,体味在历史与当下之间,作家进行了何种颠覆与创造,这是对当前文学创作最好的反思。
一、重塑真实的文学理想:将故事还给“人”
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卡理斯玛”[5]21陷入解体的文明情境。曾经被大家奉为圭臬的社会秩序与道德规范,在经历了文革的洗礼、西方现代思潮的冲击、市场经济洪流的席卷之后,其真理性正在遭到越来越多人的质疑。在这样的状况下,先锋作家们看到的是一个混乱、无序的世界,曾经被大家所坚信的“真实”在这时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传统的文学真实论无法支撑文学创作继续进行,于是一种重塑真实的文学理想应运而生。
莫言用“奇怪”来形容当时的文学真实,他认为当时的作家写作多是为了响应国家的倡导。尹昌龙在其著作中对1985年的文学情状如此概括:“小说家们乐于在小说中讲述人物心理、讲述地方文化、讲述现代意识,而把‘故事性’这一必要的要求给远远地淡忘了。”[7]166可见文学真实性在当时仍然作为表现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而存在,在环境决定论下形成的“遵命文学”[4]21大行其道。
文学应当具有艺术真实,这是文学反映现实人生并具有延伸内涵的先决条件。此种真实被定义为“由来自对象的客观思想和发自作家的主张思想熔铸而成的统一体”[8]8。然而刘勰主张的“为情而造文”却在十七年文学与文革的余波中被扭转为“为文而造情”[8]27,彼时文学真实的天平完全倾向了意识形态一边,“人”在其中是扁平的模板而不是立体的血肉。在这种背景下,刘再复于1985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详细论述了作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他极力主张恢复文学的“人学”内涵。刘再复认为,文学的主体包括作品人物、作家、读者与批评家。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不能囿于“外在概念”的桎梏,“应当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主体力量,实现主体价值”,这就要求作家应当赋予作品人物充分的“主体形象”,而不只是单纯塑造公式化的“偶像”。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充分尊重读者的文学创作,将读者的被动接受还原为主动接受,从而实现整个文学内涵从创作者到接受者对“人”的全面还原。此文掀起了学界的激烈讨论。不论当时对此文的评价如何,它确实将文学真实性摆上了台面供大家评审。在纷乱的探讨声中,先锋作家们对刘再复进行了驰援,他们率先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扩大了恢复文学主体性的声势,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文学真实观。
应当明确的是,先锋派心目中的文学真实绝不是惯常大众所认为的现实存在世界。先锋派认为现实世界具有荒诞性与虚假性,“遵命文学”只是借着真实与真理的外衣来强化思想统治。大众自认为对日常生活真实的认知其实是一种“伪真实”,这是长久以来文学真实被征用为意识形态工具的结果。余华在其写作阐述中不止一次论述过这个问题。在《虚伪的作品》中他指出:现实社会是虚伪的,内心世界才是真实的。若文学的真实性一成不变,若我们将新闻记者眼中的真实用来要求文学,“我们的文学只能在缺乏想象的茅屋里度日如年”[1]5。在余华看来,“伪真实”指“人们被日常生活围困的经验”[1]5,即长久以来文学作品所建构的一成不变的能指、所指体系,它需要被打破。人们对生活的认知大多来源于这些一一对应的能指与所指,但这样的认知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这一点早在鲁迅先生处就已被揭示——“靠事实来取得真实性,一与事实相反,那真实性也随即灭亡”[8]37。先锋作家们只是重拾起了被历史抛弃的先生话语。当文学被完全用来反映特定事实而缺乏主体的情感表达时,其艺术真实性将不再成立,文学的意义建构也就无法完成。
那么,当现实存在的世界不能再被相信,真实又将指向何处?余华在《我的真实》中写道:“我觉得真实是对个人而言的。发生了某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本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并没有多大意义,你只能从个人的角度去看这个事件是怎么一回事。”[1]3在《虚伪的作品》中他又进一步阐述道:“对于任何个体来说,真实的存在只能是他的精神。”因此,余华认为,文学真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等同于“纯粹个人的新鲜经验”以及“对常识的怀疑”[1]5。他想要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打破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坚信不疑,重塑一种能够反映个体精神状态的文学真实。此种定义打破了传统的规约,或许将其称为“主观真实”会更加贴切。
余华文学真实观的形成,其实与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混乱”脱不开关系。各种思潮影响着当时的社会,赫斯列特曾说:“诗人不过是把他所处时代的精神,印在他的作品中罢了。”[8]10《十八岁出门远行》可以视为余华将现代人的精神状况放置到架空的社会环境中来书写的作品,其中人物荒诞虚幻的精神状态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精神情状。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作家在这篇先锋宣言中开始了他建立文学理想国的尝试。事实上,这篇先锋宣言在文本生成前就已显示出强烈的现代性色彩。通过余华的自述可以得知,此篇小说的灵感来源主要有两处:一是报纸上关于抢苹果的新闻报道,二是卡夫卡所写的《乡村医生》。卡夫卡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为当时中国的许多先锋作家提供了写作范式与创作冲动,余华也不例外。他谈及创作初衷时说:“卡夫卡终于让我震撼了。我当时印象很深的是《乡村医生》里的那匹马,我心想卡夫卡写作真是自由自在,他想让那匹马存在,马就出现;他想让马消失,马就没有了。”[1]36《乡村医生》的情节之荒诞、语言之神秘、叙事之自由,在余华看来正是自己寻求已久的理想写作模式。如此看来,创作前的一切条件都已成熟。于是乎,在社会大环境与自身文学冲动的双重驱动下,一场属于余华的“远行”开始了。
二、“远行”的开始:建构梦境的怪异笔触
正如尹昌龙所述,先锋派的文学革命“更像是技术革命,而不是思想革命”[7]164,余华的叛逆也集中体现在讲故事的话语方式与情节建构上。他以少年视角讲述了一个如梦般虚幻的故事,在“非成人化”的叙述角度建构出一场充斥着荒诞、暴力、异景的旅途。此种叙述视角的选择本身就反映出作家重塑真实的强烈愿望,它“被运用于提供那种反抗既定语言秩序的感觉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1]87。荒诞、暴力、异景等元素在这篇小说中首次出现,并延续到了余华的后续创作中,作为余华建构梦境世界必不可少的手段。
(一)叙述上的自由
余华的“远行”首先从恢复文学主体性开始。实现此目标的要求是创作笔触应当跟着“叙述”走,即当一个作家处于“最好的创作心态时”,他往往就进入了一种“无我”的状态,完全浸入到故事中,尊重故事的发展脉络,“服从自己的人物,接受笔下的人物应有的命运”[4]18。余华的启蒙老师卡夫卡正是如此,《乡村医生》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根本没有马”的地方却突然出现了“两匹强壮的膘肥的大马”,只是因为文中的“我”需要它们;一个原本“健康”的孩子身上突然出现了“无药可救”[9]40的伤口,于是病人、上帝与医生的角色发生了混乱的转换。在这些充斥着悖论的诡异情节中,无论是“我”还是读者,都在理性与情感间失衡冲撞着,这是作家放弃了叙述控制权的结果。文中频繁出现的“于是”“然后”“反正”等词让读者无法深究情节的合理性:放松下来,跟着“我”的所见所闻走下去就对了。
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明显借鉴了卡夫卡的笔法,他开始尝试将故事的节奏交由“叙述”来控制,成为了“叙述”忠实的信徒,颇为强势地将文本的一切征用来为此服务,这一点得到了余华本人的亲自认证:“是‘叙述’在指引着我走……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强硬的叙述者,或者说是像‘暴君’一样的叙述者。我认为人物都是符号,人物都是我手里的棋子。我在下围棋的时候,哪怕我输了,但我的意愿是要我输的,我就这样下。我赢了,也是因为我的意愿要我这样下的。”[10]19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余华希望将故事人物主体性与作家主体性完美地结合。他的做法是:首先由自己反叛真实的强烈主体意愿产生一种“叙述冲动”,然后作家部分退场,把故事交给这股“叙事冲动”,让它去充分调动与安排一切。于是我们看到,十八岁的“我”从小说一开头就在寻找旅店,但没人知道“我”要往哪儿走,也没人知道旅店在哪儿。“我”就在一条不知名的路上走着,旅店时而被“我”忘怀,时而又“长”在了“我”的脑袋上,充斥着“我”的头脑。而随着故事的发展,结尾的“我”终于找到了旅店,原来它正是载着“我”寻找旅店的那辆坏车。小说中所描写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让这位十八岁心智未熟的少年找到归宿。然而在整个远行途中,这个目标时而出现时而消失,呈现出一种散漫随意的状态:“你走过去看吧。”“开过去看吧。”“现在我根本不在乎什么旅店。”[11]226余华在各处细部弱化作家的理性,强化小说人物的感性,让一切故事漫无目的、随心所欲地发生,然后归于一处。这更显出与卡夫卡的文字所一致的“宿命感”,这就是他笔下人物逃脱不开的既定命运,作家只是不加干涉地把其展现出来,充分尊重了作品中人物的主体性。而一将“我”与十八岁这个条件联系起来,那些不成熟的心智、混乱的话语、离奇的情节中倒也就显示出了几分合理性与精神真实性。
(二)“黑冷”的温情叙事
除了叙述的自由性,余华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也开始有意地模仿卡夫卡式阴暗、诡异的语言风格。这是由现实秩序的虚假性所决定的,余华热衷于暴力叙事的直接原因也在于此:暴力是打破理性秩序的方法之一。对常识的否定就是关注常识所带来的“不真实”的后果,这些后果就是暴力、残忍、阴谋和死亡。于是,自此篇小说起,血腥与暴力成为余华所钟爱的情节,并在后续创作中逐渐升级,这也象征着他对社会现实的思索越来越深远,从“小荒诞”走向“大荒诞”,逐步“唤起了一个死亡与刑后残肢构成的冷酷麻木的世界”[12]99。如果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中还是略带克制的血腥,对于肢体分离的描写仅止于“鼻子软塌塌地贴着而不是挂在脸上了”[11]226,那么在《现实一种》中,余华血腥的笔触快速升级,从母亲身体里的霉烂写到对山峰尸体具体的解剖。这种客观到近乎冷血的场面描写,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不适感,也将现实理性秩序带来的混乱与反常以最直接的方式呈现到了读者眼前,就好似直接拿着喇叭对着他们大喊道:“看!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真实带来的后果!这是多么愚蠢啊!”
然而,单纯的暴力叙事无法支撑起足够的写作深度,余华必须思考自己该往何处走。刘再复认为“伟大的作家总是选择最难走的路”,这条路能够“使人物表现得更丰富、更深邃、更精彩”[4]19。如何走好暴力叙事这条路,如何让文本具有主观真实的深度而不沦为满足人们猎奇与隐秘欲望的工具,余华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已有了初步的答案。他在其中也表现出了与卡夫卡所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就是没有完全放弃作家的叙述权利,还是对笔下人物的灵魂进行了部分干预。而这恰恰使他走对了这条“难走的路”,使他拥有了作为一名先锋作家的独特性。这种“干预”在刘再复看来并不违背主体性原则。因为正如现实人生一样,小说中的人物也会走入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难以抉择的人生情境。这个时候,为了故事能够顺利发展,作家需要“帮助人物打开自己的心灵,作一种不违背个性的选择”,而如何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出了他们的“眼光和水平”[4]19。余华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通过“公路”“司机”“我”“抢劫者”等一系列意象的塑造,赋予了这条公路以“人生之路”的隐喻意义,文中有一段点明主题之处:“公路高低起伏,那高处总在诱惑我,诱惑我没命奔上去看旅店,可每次都只看到另一个高处,中间是一个叫人沮丧的弧度。尽管这样我还是一次一次地往高处奔,次次都是没命地奔。眼下我又往高处奔去。”[11]224
路好比人生,高低起落循环,背后是余华所热衷的西绪弗斯式悲剧含义。而“我”与“司机”,也代表着个体在人生道路上所处的不同阶段。在小说结尾,一开始天真幼稚单纯的“我”学会了在暴力前沉默,学会了以世故的方式待人。读者不禁要问,“我”最终会变成如“司机”一般冷酷无情的人吗?在人生一个又一个困境来临之时,“我”是否会迷失本心忘却目标?在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上,余华虽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却在小说最后为“我”指明了一个方向:
我感到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它心窝还是健全的,还是暖和的。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11]227
这其实是余华帮“我”做出的抉择:人的外在可能会遭受各种磨难,但是心理的健全十分重要。人生路上虽会陷入宿命般的悲剧,但只要保有健全的内心灵魂,最终总能找到归处。这处细节也给读者心里带来一丝安慰,在跟着“我”经历了一段并不愉快的旅途之后,终于能够感受到些许温情。而正是因为前文的铺垫,这样的温暖才显得更加动人。从这里其实可以初步看出余华写作中的水准与高度了:在暴力叙事中凸显出温情的光亮,这是一种“黑冷”的温情叙事。这种模式自“原点”起,经过余华的不断探索而成熟。在早期作品中,他着力于表现“黑冷”,甚至有些“不近人情”了,代表作品是《四月三日事件》《河边的错误》等。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余华开始转型。他不再刻意描绘“黑冷”,因为这已然是他经过前期训练而信手拈来的东西。正如先锋作家后来的集体叛逃一样,他也开始关注悲惨人生中难得的人性亮光并将更多的笔触投入其中,于是《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闪烁着温情的作品应运而生。
这种用冷静克制的悲剧来反衬温情的方式贯穿于余华的各种创作中,短篇小说也不例外,如《蹦蹦跳跳的游戏》结尾:
他不喜欢下雨,他就是在一个下雨的日子里倒霉的。很多年以前的一个晚上,在滴滴答答的雨声里,他抱着一件大衣,上楼去关窗户,走到楼梯中间时突然腿一软,接着就是永久地瘫痪了。现在,他坐在轮椅上。[13]7
余华在这里用白描式的笔触收尾,客观陈述了“他”的悲惨遭遇,不加渲染地稍施引导,读者就很容易对主角生出理解与同情,也更加珍惜在整个故事中闪烁在细节处的一些生动人性。余华就像一位高超的画家,善于“用阴沉的天空展示阳光”[14]144,《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他的入门画作。
(三)陌生化的语言与“看”的细节
除了叙述手法、暴力悲剧,语言也是余华反抗传统真实的武器。几乎每个先锋作家都发出过创造语言的宣言。余华也不例外,他一身反骨最终还是落脚到了语言的革命上。正如王中所说:“一切文学变革最终就是语言变革。”[15]170不管是无序的逻辑、荒诞的情节、混乱的精神状态,最终体现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就是语言的陌生化,这主要集中在比喻的陌生化上。“余华式语言”在这篇小说中初现端倪并成为余华建立其“独立自由的个体言语体系”[15]170的起点。通过陌生化的比喻,喻体与本体之间传统的对应关系被打破,这就再次向“真实”秩序发出了挑战。这篇小说中有许多经典的“余华式语言”的雏形,当“我”走在无人的道路上,时间流逝:
我就这样从早晨里穿过,现在走进了下午的尾声,而且还看到了黄昏的头发。[11]224
而当车子坏了,司机却漫不经心时,“我”开始担心起旅店来:
那个时候太阳要落山了,晚霞则像蒸气似的在升腾。旅店就这样重又来到了我脑中,并且逐渐膨胀,不一会儿便把我的脑袋塞满了。那时我的脑袋没有了,脑袋的地方长出了一个旅店。[11]226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比喻,但若是放在人的精神状态中去理解,却又不无道理了。结合日常经验来看,当头脑极度专注于一个事物的时候,人们会发觉脑海里充斥着这个事物,没有办法思考其他的东西。在这里,余华运用生动形象的感觉描写,用“脑袋的地方长出了一个旅店”这样的怪异笔触打造出了一种精神真实。
而在“我”一身伤痛,怀着极度沮丧的心情坐到车上的时候:
我闻到了一股漏出来的汽油味,那气味像是我身内流出的血液的气味。[11]227
同样地,人在混乱的状况下会下意识地将周遭的事物与自己身上的东西相结合来感受,因为这时他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思考两种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否合理。这是人在伤痛状态下会产生的最直接也是最不加修饰的想法。
通过对上述陌生化语言的分析,可知这种语言造成了文字的荒诞与离奇,是形成读者阅读障碍的最主要因素,但这却又是先锋作家无限接近精神真实最重要的手段。以余华为代表的先锋作家极擅长制造怪异的比喻,这是叙事陌生化的话语实践成果。这种“再叙事”的尝试是成功的,他们以一种针尖般的锐利锋芒使叙事这件文本外衣“再度被尖锐地意识到”[16]25,在能指与所指的断裂带中引申出了叙事的无限可能。各种离奇的比喻手法,也是作家敲打读者重新思考现实世界是否真如他们所见的最直接手段。
除此之外,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还有特别值得注意的一处语言细节,就是“看”的反复出现。目光在这一篇小说中极其重要。余华在其中多次重复“看”这个动词,其出现的次数多达48次。这一持续而单调的动词重复,强化着本文的视觉特征,并成为自我与现实联系的外在化象征。
“注视”在西方心理学理论中是一个重要的动作。霍顿·库利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中提出的“镜中我”理论就认为,人的自我意识是通过观察即“注视”别人和自己行为的反应而形成的。这一理论揭示了人的“社会自我”属性——人是社会化的人。米德随即根据“镜中我”理论发展出主我客我理论,人的社会评价体系自此完善起来。可见,个体通过观察他人的举动而将对这种举动的感受投射到自我认知中,使得“注视”成为人在社会化背景下形成完整自我意识的重要环节。而《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我”,进行了多次的观察却无果。比如当“我”被打后坐在地上,看着施暴者渐渐远去,看着司机跳到拖拉机上,然后看到他抢走了我的背包,最后看着拖拉机逐渐消失。通过四周一切景象逐渐消失的视觉印象,“我”意识到现在的自己什么都没有了:
这时我看到那个司机也跳到拖拉机上去了,他在车斗里坐下来后还在朝我哈哈大笑。我看到他手里抱着的是我那个红色的背包。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背包里有我的衣服和我的钱,还有食品和书。可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
我看着拖拉机爬上了坡,然后就消失了,但仍能听到它的声音,可不一会儿连声音都没有了。[11]227
“我”虽然一直在看,但这个动作却失去了它丰富人物形象的意义。“我”在“看”的过程中,并没有任何思考性的记忆,也并未向读者传达出某种潜意识的感觉,似乎这只是眼球进行的一项单纯的机械运动。读者甚至通过“看”读出了一种“我”对所处危机视而不见的态度。如果非要说它意味着什么,它只能意味着某种东西的缺乏——“或许感情,或许对现实的认知”[12]101。人物在通过“注视”或“被注视”之后仍旧是一个意义缺失的符号。这一连串的视线观察并没有形成结论,也没有发掘出上述所提及理论中所说的——人在社会观察中形成的自我认知,通过“看”所建立起来的主体与现实的联系象征是虚弱、漂浮且扭曲的。余华在这里解构了自鲁迅开始建构起来的“看客”情节深度,解构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形成的固定意涵,“这转移了的视而不见的注视在符号与所指之间的深渊里成为自我失落的寓言”[12]101。如果说,余华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还似有若无地赋予了“我”在“看”时的无力感,一种对现实的无法掌控感:“可我那时只能看着了,因为我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坐在地上爬不起来,我只能让目光走来走去。 ”[11]227
那么,在后来的《现实一种》中,他就更加弱化了主体与现实间的联系,再也不花笔墨去描写“看”与“被看”之间的因果关系,不给“看”赋予相应的正常的情感反应。两双眼睛之间失去了相遇的机会,“看”再也无法将主体自我意识构建起来,人就这样失去了与他人、与社会的联系,游荡在自我的精神世界中,更衬托出现实人生的荒诞与缥缈。值得一提的是,“看”被余华从厚重的“国民的灵魂”[17]445中解救出来,将这一动作归还于普通人的精神本身,更凸显出动作之自由、精神之自由、叙述之自由,这也是他开始撕破传统语言指涉性的表现之一。
余华就是这样选择了独特的叙述视角与叙事模式,辅之以陌生化语言,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开始尝试将它们融为一体。他从言语的“断裂带”中出发,逐步恢复了作品中作家与对象的主体性,在完成作家自我实现的同时也达到了笔下人物心灵的真正开放,以此解构了传统文学的真实观,建构了文学精神世界中的一种“别样真实”。
三、“远行”以后:“自我”“超我”之融合
通过上述语言分析可以发现,余华的话语叙述实验是他作为先锋作家“与现实过招”[18]263的手段。而这种手段背后,涌动着的是作家内心深层自我意识的存在与觉醒。他之所以要将叙述从宏大意义中解救出来,就是为了重新回到对欲望的表达,即弗洛伊德所称的“自我”①。余华也证实,先锋式的写作“唤醒了我记忆中无数的欲望,这样的欲望在我过去的生活里曾经有过或者根本没有,曾经实现过或者根本无法实现”[19]156。在品鉴余华文字时,若“仅仅关注文本形式上的先锋实验,那实在是买椟还珠”[20]41。因此,其文本研究不能止步于语言的平面分析,还需要深入感悟文字背后所体现的作家内心世界,从精神向度上将文本还原为一个立体空间。《十八岁出门远行》之所以被赋予“原点”的地位,正是因为它的文字底下涌动着的股股精神热流,这热流从这里开始,一步步扩大了文字间的裂缝,最终喷涌而出,将余华捧上高位。用刘再复的话来说,这就是通过话语形式来建构“话语内部的自我指涉”[16]26,即展现作家心灵的“内宇宙”,这也成为了“文学是人学”的延伸含义。
先锋派作为红极一时的文学浪潮,作家群体在经历了大浪淘沙后留下的几个依然活跃在文坛的“珍珠”,都有着自己独特之处。作家的个体精神是具有复杂性的,如果说苏童的文本是充满阴柔诡谲的南方想象,格非的文本是神秘主义主导的命运叙述,那么余华的文本就是在死亡与苦难中上演的人间悲喜剧,他是当年的先锋作家中最接近人生现实的。笔者认为,《十八岁出门远行》作为“原点”之作,格局还未完全打开,个体的悲剧还不足以让集体产生共鸣,但结尾对于“我”在面对暴力与苦难时的温情描写,已然预示着作家未来的道路,这也正是后来的《活着》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许多人在讨论余华转型的缘起,但与其说他是转型,倒不如说是回归。在远行之后,余华逐渐明白,真正长远的写作不能只有“自我”,还需要“超我”②来完善。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余华笔下的人物经历了从人到符号再到人的内涵变迁。早期他的“超我”显然还未成熟,文本更多还处在“自我”的心理初期阶段,这种意识若不加控制,便会使故事“出走”得太远。若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中还残留着一些川端康成对余华的影响,他剥去了故事情节的逻辑链条,却留下了对人物情感、心理、外形等的逼真描绘,这些与后现代主义格格不入的细节真实塑造出了“我”相对立体的天真幼稚的形象,使这个故事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来回穿梭。那么在《现实一种》里,余华就完全放弃了描绘情感的细腻笔触,转而使用冷漠的外部叙述,真实与虚构的天平也完全倾倒。而后先锋批评者们的声音引发了余华的反思:纯粹的后现代主义是否真能支撑起一个文本的“内外宇宙”之建构?于是在追崇西方的热情过后,他又重新找寻到了中国社会中的独特魅力。《在细雨中呼喊》以后,其创作逐渐引入了“超我”,引入了社会元素,以此监控与调节“自我”意识的展现。出走的“自我”终于能够停下来看看周围,看看社会,于是作品中的人物又由叙述符号重归于“人”,《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也正是因此而更贴近大众,多了人性温情,多了人道主义关怀,进而成为当代文学中的重要一环。
上述“自我”与“超我”的融合,是作家创作社会化的结果,也是写作的真正意义所在——作家需要打开“内宇宙”的大门,去感应社会现实即“外宇宙”的脉搏。通过这一方式,余华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19]157。脉搏是深藏在表皮组织下的暗流,正如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一样,社会的表象并不是文学追求的真实所在,因为那通过社会政治学足以反映。文学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挖掘社会内在的精神状态,即化“机械反映”为“主观感应”,由作家对社会进行把脉,创作出洞察社会脉搏的作品,这才是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作家不仅要实现自身精神的充分觉醒,还需要肩负起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这种历史使命感往往以“深广的忧患意识”[4]11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如此看来,从余华用《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自身先锋宣言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他要以荒诞梦境般的创作来恢复从文学到“人”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实现文学主观真实的全方位觉醒。
四、结语
在中国的文学真实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之时,余华以《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了对传统真实的解构,运用独特的“非成人化”视角、暴力叙事与陌生化的语言,透过“现实人生的荒诞”这一主题,赋予了小说“原点”的开创性意义。此后,余华沿袭了此篇小说中的叙述变革,逐渐将小说人物的主体性与作家创作的主体性从传统文学的宏大叙事中解救出来,打破了读者对传统二元对立意涵的固有认知,使“真实”不再一成不变,文学不再是对描写对象“刻板的摹拟”,也不再是作家主观意志“单纯的传声筒”[8]10,“文学真实”这一概念也因为有了“主观真实”这一内涵的注入而逐步度过了接受危机,在新时期文学中迎来了新的转机。然而余华的创作野心不止于此,针对《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不足之处,他也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于是在后期创作中,他保留了“原点”小说中的人性温情,克制了其中的过度“自我”,以普世、悲悯的眼光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做出了回应,“我”的悲剧关涉的不仅仅是个体的生存悖论,更是整个现代社会的荒诞本质。
以余华为代表的先锋派作家各自从不同的“原点”出发,真正实现了作家个体精神自由与人道主义的融合,集体打造了当代文学史中重要的“八十年代文学精神”。所以,诸如《十八岁出门远行》等作家们的“原点”小说都值得被重视。无论是其中的创新性、局限性,抑或是一些不起眼的文本细节,这些都值得成为考察先锋作家重塑真实历程时的宝贵财富。要知道,静止文字之下涌动着的,往往是作家内心深处澎湃汹涌的热流。
注释:
①自我: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是人格结构的中间层,它高于人最原始的本能冲动,但低于社会化人格,可以将其理解为个体意识的存在与觉醒。
②超我:弗洛伊德认为“超我”是人格结构中的最高层,由社会规范、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内化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