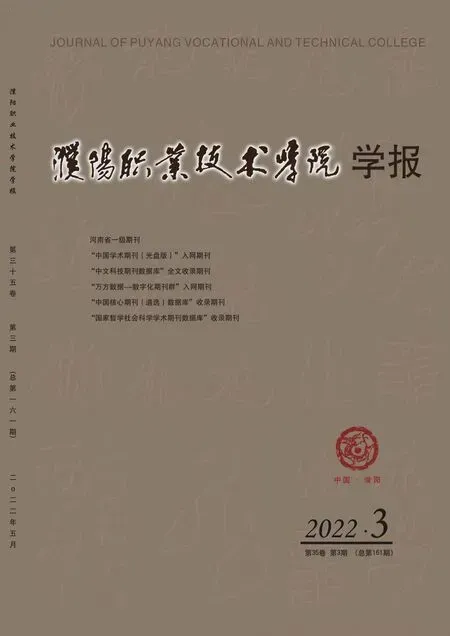明代教化剧中的女性形象
——以《六十种曲》第四卷为例
范晓青,王 斌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俗语云“十部传奇九相思”,《六十种曲》第四卷所录《绣襦记》等十部传奇,从主要内容上看,都属于明代传奇剧中常见的男女爱情题材作品;但从“群像分析”的角度而言,这些剧作在爱情叙事的同时,也刻画了大量女性形象,包括宦门小姐、风尘歌妓、平民主妇、沙场女将等众多人物,从戏曲文本里这些角色的唱词内容、性格呈现、行为设计中,都映射出剧作者自身所解读、所认知的女性教化观念,反映了文人作者群体对女性社会角色、操行品德的规约化定位与想象。在剧作中,不论何种身份的女性,凡是自觉恪守妇道、遵守孝道、固守贞洁、践行“三从四德”,作者就会以激赏的态度赞叹其思想和行为①。
一、女性人物群象
这十部传奇中塑造了包括女主角、女配角在内的大量女性形象,所涉及的人物身份、社会地位、性格特征均多种多样,可以视为多元化的、群像式的社会各阶层女性面貌书写与呈现。其中,剧作中重点描摹的女性形象往往都突出体现了作者所秉持的女性教化观念,在此,我们择其典型,进行分析。
(一)巾帼英雄形象
《赠书记》描述了三个巾帼英雄的矛盾与耦合。杨府女将不堪恶吏欺压而选择落草为寇;将门女裔魏轻烟虽然家道中落,但并不沉沦于逆境,反而一直在做行侠仗义之举,后来也因官府欺压,而入伙了杨府女将的山寨;贾巫云“幼习兵书,粗知韬略”[1]54,为逃脱入宫选秀女的命运而特意假扮男子出门游历,官员傅子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其为义子,一系列巧合之后,她代义父出征、领官军来平叛招抚山寨诸人。最终,杨府女将和魏轻烟表现出本无反意、愿意臣服朝廷的“忠君”思想,接受了招安;贾巫云也功成名就,获得了皇帝敕封的招讨使一职。
《西楼记》中也描写了一位巾帼女杰轻鸿的悲剧:她本就是侠客的妾室,在价值观念上,“慕贞姬,思义女”,渴望有朝一日用自己的壮烈行为来“博他青史千秋”[1]77-78。因此在行动上也追仿古代仁人志士,不仅参与到丈夫的侠义行动中,还为此勇敢地献出生命,换得了事件的成功解决。
固然这些人物的特征中有借鉴前代文学作品的地方,比如魏轻烟在市井中的行侠仗义,未必不受唐传奇的风尘女侠形象的影响;又如贾巫云的女扮男装与代父从军,也能推敲出作者对北朝乐府《木兰辞》的化用。但更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这些人物形象所牵涉的叙事逻辑本身,都有着超脱于原型所在语境之外的新的教化内涵:魏轻烟不仅仅像唐代风尘女侠那样主持正义,更有着个人在困境中固守品德底线、始终忠君报国的意涵;贾巫云的相关叙事也摆脱了单一的孝女代父从军的传奇性,在传奇之上,又覆盖上了义女知恩图报、尽忠报国等意味。
(二)母亲形象
出于教化主旨的需求和对合乎儒家伦常规范的家庭伦理叙事的推重,包括明代传奇在内的大量古典戏曲中,“慈爱”与“严格”成为母亲形象的常见注脚。一方面,作者用“慈母”的形象来诠释母亲在家庭中呵护儿女长大成人的辛苦历程;另一方面,在面对儿女教育问题时,不同家庭的母亲们往往不约而同地用儒家视阈下的社会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来规范子女,并表现出严格、严肃的态度:她们或教育男儿读书科举对于下可光耀门楣、上能报效君王的重大意义,或对女儿以身作则解释遵守三从四德的必要性。
《绣襦记》的郑家老母虞氏,就属于这种“慈爱”与“严格”相参合的典型母亲形象。当她送体弱的儿子郑元和远赴京城参加科考时,内心活动十分复杂:既出于“慈母”的心态担心儿子“孱弱身躯,怎跋涉水远山长”;又从“严母”的视角评价结伴赶考的“那乐秀才抱经纶俭让温良”,符合士大夫的道德标准,认为儿子在这位良友的引导下,也必然“料得意同登龙虎榜”[2]4。
《霞笺记》中李母何氏,剧作者借他人之口称誉她的言行举止是“身沐皇恩,颇称内德”[2]2。前半句表现的是对社会责任的自省,后半句则表达了对家庭场景下女性个人道德的诉求。此外,《玉环记》中张延赏之妻,教育女儿说:“在上不骄,在下不乱,内外颇称贤淑。”[1]23意即地位的高低变迁,都不会带来“骄奢淫逸”或“扰乱纲常”的心性与举止的改变,在社会和家庭中都有“贤淑”的美誉——这在内涵意蕴方面与《霞笺记》的何氏是相通的,都是将社会与家庭两个场景下,女性应有的责任、道德,具象化地呈现在一个母亲形象之中。
(三)妻子形象
明传奇中的妻子形象往往突出呈现了明代特有的理学语境下,文人对“妇德”的理想化设计。
比如,在《投梭记》中,王氏虽然婚前一直是养尊处优的宦门闺秀,却一直有着吃苦耐劳、勤俭朴素的优点;在嫁人后,纵然家中贫寒、丈夫科场失意,她也心态平和,毫无怨怼地积极积攒家业。甚至还主动牵线搭桥,让丈夫与他所喜欢的女子团圆,并打消对方的疑虑。一人兼有勤俭持家、逆来顺受、不妒忌妾室甚至主动促成一夫多妻等多种“妇德”,可谓反映了当时理学视阈下对“完美”女性的性格、行为的样板式想象。
相对于这一刻意将各种“妇德”集合于一人展现的典型形象,《玉环记》中,琼英坚守“一女不嫁二夫”的理学标准,宁愿忤逆逼婚的父亲,也要等丈夫回来团聚;《青衫记》中小蛮、樊素两位夫人赞同丈夫纳裴娘为新妾室,并视裴娘为姐妹;《金雀记》中潘安的妻子井氏也不嫉妒巫彩凤;等等。这些充满封建礼教意味的人物与情节的设置,反而显得平淡、单薄。
(四)妓女形象
妓女形象在这十部传奇的人物塑形中,占据了相当比例,如李亚仙、裴兴奴、谢素秋、桂英、张丽容、穆素徽、元缥风、玉箫、巫彩凤等,甚至可以视为这些剧目的主要角色。
就人物特征而言,这些传奇中的妓女形象多有共通之处:几乎都是年轻、真诚且富有才华、渴望从良的美丽女性,并且对文人表现出极大的爱慕,对商人和其财富则持鄙夷的态度;在剧中,还理想化地设定她们一旦与倾慕的文人书生定下婚娶盟誓,便为了固守贞操而不再接客。
而从叙事上来看,在这之后的故事,往往就进入到这些渴望从良的妓女受尽磨难、终成眷属的格式里:要么被老鸨打骂折磨,要么被发卖给富商或官绅,要么被骗卖到远方做妾或丫鬟;随后再经由诸多巧合,最终由作者将她们与已经建功立业的文人书生再度捏合在一起,构成大团圆的喜剧结局。
从这类固定化的人物设计和叙事框架中,我们能够看到,明代文人传奇对元代文人所创作的诸如《救风尘》这类北杂剧的借鉴与模仿,特别是诸多妓女形象所共同秉持的价值观念中,重文人才学而轻商人财富,与关汉卿、马致远等元人杂剧中妓女的价值观念完全重合。这种价值观念固然有文人脱离现实的自我想象成分,把一系列理想中的人格都安插在一个推崇文人身份、尊重文学才华的风尘女性身上,所以,这些妓女形象在审美内涵上看,都一直在追求“一个正常的女性身份,追求人身自由、追求正常的人间生活和忠贞的爱情”[3]41。
二、道德教化的内容
如果我们对剧中的道德教化内容稍作梳理,就会发现:除了儒学伦理中最为基本、在古典戏曲体系中已属司空见惯的贞洁意识与“三从四德”标准之外,还有勤俭持家、奉行孝道,以及今天看来明显属于保守思想的鼓励家中男性求取功名,甚至还有代表封建糟粕的一夫多妻制下不妒忌其他女眷的“宽容”举止。
(一)勤俭持家
在传统的女性主理家政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勤俭持家实际成为女子无论出嫁与否都应知晓的“必修课程”。明代戏曲中典型地描写了这种出嫁前的修习场景:在《玉环记》中,琼英之母借由古人诗文内容,告诫女儿要“亲箕箒纺绩,谨慎持身无纵逸”[1]23。
《投梭记》中,谢鲲家业萧条,其妻任劳任怨,“操作自甘朝暮,服劳岂惮勤劬”,心态上也是“自分蓬蒿甘淡薄”[1]2-3,而且为了操持家业,夙兴夜寐,“甘劳苦杼轴灯前控。肯贪耍闲虚哄。妾本儒家女。深居绿窗里。结发嫁谢郎。荆钗布为被。抱瓮朝汲泉。挑灯夜针黹。常诵交儆诗。鸡鸣劝夫起”[1]20。不断重复地对家庭窘境和自身辛劳的书写与感叹,一方面出于在男主人公否极泰来之前,对环境和气氛欲扬先抑的文学效果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服务于女主角作为贤内助在家事方面惨淡经营的道德形象的要求。
甚至在对风尘女子进行技能描述时,明代作者也不忘在艺术技能“琴棋书画”之后,再加上“针线女工,无所不通”[2]38,来暗示女性角色在操持家务方面已经具备基本素养,可以适应婚娶后的“男耕女织”生活、生产模式。在《绣襦记》中,妓女李亚仙也说:“古之王后,尚且亲织玄纮。我是烟花,岂可不事女工。”[2]8。可见,在古代作者的审美视野中,女性通晓基本的生活、生产技能,进而使婚嫁后勤俭持家成为可能,是女性美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
(二)奉行孝道
《说文解字》中对“孝”字的释义,最能体现两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下对孝道内涵的诠释:“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4]422讲求的不仅是“子承老”的养老形式,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内核上要完美、恭敬地赡养老人,达到“善”的程度。
因此,在古人的这类“至善”的孝道认知下,类似《玉环记》中所述,琼英为救治父亲,祈祷“减妾身二十年阳寿,添爹爹二十年遐龄”[1]83的内容,就是一个再真诚不过、也是再正常不过的现实情境的再现。与这种真诚的心态相对应,当琼英被父亲杖责后,发觉痛感比上次要轻,意识到父亲身体多病,力量大不如前,“不能使疼因无力,教儿不觉泪溋溋”[1]101。
而在尾声部分,圣旨嘉奖云:“琼英救亲减寿,生死顺存,曰孝曰贤。”[1]129我们不能将其简单视为大团圆模式中常见的、对每个正面角色进行肯定的“套路”或“过场”;它实质上是作者以一种严肃而至高的公文书写形式,提醒读者和观众注意“救亲减寿”这种极端行为背后的崇高动机——孝道。
(三)敦促男子读书考取功名
根据“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读书考取功名才是人们眼中的正途,这是整个社会的共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深入人心,女子们也必须明白男子读书不可懈怠。张丽容婉言相劝李生:“你连日心迷花酒,学业顿忘,秋闱已近,乘此南窗日永、清风徐来,欲效李亚仙故事,勉君诵读一番,不识君意可否。”李生欣然同意并许诺绝不会辜负她,丽容说“转祸为祥,你且看书。你且对芸窗翻阅史书,学充足方成大儒,切莫把光阴虚度,你须下这苦工夫,你须下这苦工夫”[2]22-23。韦生结交朋友被仆人诬陷,惹得岳父大怒,母亲教导琼英“可谏他芸窗苦用功,期早晚步蟾宫,一朝贵显人钦重,肯老林泉守困穷”[1]56,还感叹女婿:“不知他怎生一到我家来,就把诗书丢了,所以你爹爹见责。……他若是埋头牕下攻书史,怎见得旁人讲是非。”[1]58还亲自劝说韦生:“男子汉何不苦志青灯,期登黄甲?终日放鹰逐犬,与一伙无徒为伴,难膳我夫妻之暮年,有堕你祖宗之清名,非痴非呆,不哑不聋,今当改过卓立。”[1]59
李亚仙要求郑元和,“斥去百虑。以志于学。俾夜作昼。今已三载。业虽大就。再令精熟。以俟百战。”面对郑生的狂妄和懒惰,李亚仙耐心规劝,得知是自己的双眼惹得郑元和无心学习后,自刺双目激励郑元和一心向学:“我把鸾钗剔损丹凤眼,羞见不肖迍邅……这般不习上的,管他则甚!我向空门落发,伊家休得再胡缠。”[2]95郑元和内心受到震撼,发奋读书,考取功名。
(四)一夫多妻制下的“宽容”
仅在这十部传奇中,就有《青衫记》《投梭记》《玉环记》《金雀记》《赠书记》五部存在一夫多妻现象,且彼此关系融洽,家庭和睦。这是对封建社会存在的家庭伦理道德的宣扬。为了家庭的和谐,妻妾要和谐相处,居于主导地位的妻子尤其不能嫉妒,这是用“贤德”来做道德枷锁禁锢妻子。表面上是教导妻妾相敬相爱,实际上是在巩固男子的中心地位。作者对于妻妾之间和谐相处持夸赞的态度。尤其是在《金雀记》中,面对彩凤告知丈夫纳妾的试探,文鸾没有嫉妒,认为“那一个做官的没有三两房家小?我相公为当世驰名才子,合配天下出色佳人”,反而“欣然有喜色”,赢得“好贤德夫人”“贤惠”的赞叹[1]73,作者在最后作结:“中闺已称贤,小星尤识礼。鸾凤喜和鸣,皆得配君子。”[1]75这部传奇说教气息浓厚,一直在宣传“鸾凤和鸣”这四个字,连两位女主人公的名字也与主题有关,为了突出主题,“作者又设计了晋武帝和贾淑妃的和鸣以及七夕之夜牛郎、织女的和鸣加以烘托。另外,还通过晋武帝命张华作《莺凤和鸣赋》,潘岳因代张华作《鸾凤和鸣赋》得官,团聚时山涛赠《鸾凤和鸣图》和《鸾凤和鸣诗》等,强调了鸾凤和鸣的主题”[5]29。这类作品之所以会出现并广泛传播,与为统治阶级服务、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的时代背景有关。这类思想在今天已经彻底成为了封建糟粕。
三、女性形象的优秀品质
虽然这十部传奇中的女子与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已经有几百年的距离,但是她们身上也有值得当代女性学习的闪光点,如自立自强,敢爱敢恨和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她们的这些特点对今天的女性依然有启发意义。
就自立自强而言,《赠书记》中的贾巫云、魏轻烟可视为“双璧”式的典型代表。贾巫云本就有心于像男人一样建功立业,当她遭遇入宫选秀的悲剧命运时,并不甘于就此放弃梦想,而是毅然选择了扮作男装、出奔他乡,最后主动代义父从军,在征战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而魏轻烟虽然一时沦为风尘妓女,但并未忘记自己的将门女儿的出身,处淤泥之中而不染污秽,不断践行侠客道义,扶危济困,惩处不轨之徒。依靠个人过硬的武艺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不断赢得他人、甚至是来镇压她的官军的尊重。
在这十部传奇提供的女性群像中,贾巫云、魏轻烟二人真正地以性格力量和超常才干的两者综合为依托,在无法获得他人有力帮助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意志和能力,走出困境,继续生存下去,并最终取得成功。相比较而言,其他剧作中的穆素徽、裴兴奴、李亚仙等人,更多是在别人帮助下或者作者设计的诸多巧合下,才取得了对抗悲剧命运、恶劣生存环境的胜利,她们更令人称赏的是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而不是自立自强于他人之外的非凡才干。
当然,公允地看,贾巫云、魏轻烟二人的才干主要集中于随机应变的机警多谋、上阵杀敌的排兵布阵,以及捉对厮打的格斗技巧方面,实际可以看做在古典戏曲传统的女性阴柔美丽的外形之下,又附着了男性军旅中谋士与武将的混合审美因素,所以她们的形象实际打破了“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的性别思维,表现出了许多超出当时语境的人格闪光点,这不仅使女性形象本身立体饱满,也无意塑造出了伍尔夫眼中的兼具‘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理想人格”[6]139。
这些女子在爱情的支持下,大胆放下女子的矜持,勇敢表达爱情、追逐爱情。张丽容坦白心迹,托付终生;李亚仙自荐枕席:“男女之际,大欲存焉。情苟相得,虽父母之命,不能止也。贱妾固陋,若不弃嫌,须荐君子之枕席。”[2]23《霞笺记》中的李生作为男子也说过差不多的话:“岂不闻男女之际,大欲存焉,两心相得,虽父母之命,不可止也。明当以我心事,禀知家君,再三恳求,决无不可。”[2]22已经有几分离经叛道的意味了,从李娃嘴里说出更显现出爱情的真切炙热。元缥风自忖:西邻有个谢参军,风流蕴藉,时常过来。看他十分留意奴家,奴家若得这样一人,终身事奉,也免了青楼之丑。有了这个想法存在心里,缥风对谢生与众不同,不是冷冰冰爱答不理,而是斗嘴抢白,表现了女儿家的娇嗔。甘心冷淡生涯、讨厌迎来送往的裴兴奴,见到前来的白乐天,表现出非同一般的热情:“久慕久慕,娘,你进去另煮好茶来吃,今日的客不比寻常。”[2]13还主动脱簪沽酒款待来客,暗下决心愿相期谐老,并趁醉留客要求乐天留下陪伴,众人纷纷打趣她今日的不同寻常。
女子敢爱敢恨的性格更为珍贵难得,桂英听信了丈夫休弃自己娶了高门大家女子的消息后十分悲愤,母亲的责骂更让人绝望,她跑到海神庙诉说自己的委屈,语言激烈,感人肺腑。这个表现在《六十种曲》里是绝无仅有的,大部分女子都是柔弱的、沉默的、忍气吞声的,只有桂英如此决绝,寻求正义和真相,为自己报仇。当时评论者同样对桂英的敢爱敢恨印象深刻:“作者精神命脉,全在桂英冥诉几折,摹写得九死一生光景,宛转激烈。其填词皆尚真色,所以入人最深,遂令后世之听者泪,读者颦,无情者心动,有情者肠裂。何物情种,具此传神手?”[7]96“愈出愈奇,悲欢沓见。离合环生。读至卷尽,如长江怒涛,上涌下溜,突兀起伏,不可测识,真文情之极其纡曲者,可概以院本目之乎?”[7]193
她们不只是勇敢地追求爱情,而且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爱情,对待爱情忠贞不渝。尤其是年轻貌美的妓女,与她们往来的也都是相对优秀的男性,“所交接者,皆贵戚豪族。愚夫俗子,不敢往来”,所以会面临更多的诱惑,保持初心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李亚仙在被迫离开郑元和后,又遇到了之前交好的崔尚书和曾学士,但是没有因为之前的交情而对二人稍假辞色,只是为了听到郑元和的消息才短暂接待。看到沦为乞丐的郑生已不是容貌俊美的公子也没有厌弃,只有悔恨;穆素徽的追求者池公子对她委曲求全,答应她各种各样的刁难条件,还租了宅子要和素徽拜堂成亲,但是素徽一心向着于叔夜抵死不从——“自古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奴家生在烟花,志坚金石。”[1]116-117元缥风和裴兴奴遇到的都是殷勤的富商,如果愿意,她们可以生活轻松不受打骂,但她们因为对爱情忠贞不渝拒绝接客,所以受尽苦楚。张丽容借《娇红记》吐露心迹:“君未观娇红记乎?倘有不虞,则申为娇死;娇为申亡,夫复何恨!”[2]22谢素秋也说,如果再来纠缠,我拚得一死便了。因为她们对爱情忠贞,所以在大团圆结局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出又一出的爱情悲剧。
她们自立自强、敢爱敢恨、对爱情忠贞不渝等精神,在古代更多地是一种戏剧舞台上的文学书写和艺术性的故事想象;而在今天,这些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现实性回应:当今女性体现出了更浓烈的自立自强意识,更多的女性积极投入社会活动,实现着自己的价值,这也进一步推动了女性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今天的女性更加自信,可以大胆追求爱情,并在快节奏的时代和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勇敢维护爱情。更重要的是,现代的女性不再需要为了自由和独立穿上男子的服装,不假借男子的身份也能获得同样的权利,女性身份也不再使她们有更多的压力和道德上的禁锢,现代的女性地位相比于古代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四、结语
《六十种曲》是明代传奇的选本,艺术性很高也很有代表性,对于研究明代戏曲非常重要。第四卷的十部传奇都是男女爱情题材,虽然有的故事趋同,但刻画的人物角色非常丰富且同中有异,仅女性形象就包括巾帼英雄、母亲、妻子、妓女。作品还体现了对女性的教化观念,如勤俭持家、遵守孝道、维护一夫多妻制、敦促男子致力于求取功名等。她们身上自立自强、对爱情忠贞、勇敢的优秀精神特质对现代女性思想的解放也有一定的学术参照意义。
注释:
①如在第一出家门中对人物主要性格的评价:“捐生持节敫桂英”“羡杀佳人(穆素徽)节似霜”“元缥风守节几菹鲊”;在最后圣旨中的道德评价:“张延赏之妻苗氏。亲贤敬士。轻财重义。女琼英救亲减寿。生死顺存。曰孝曰贤。”“其所奏元氏女守节沉江一事。闻已幸免。鲲妻王氏收养不妬。并可嘉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