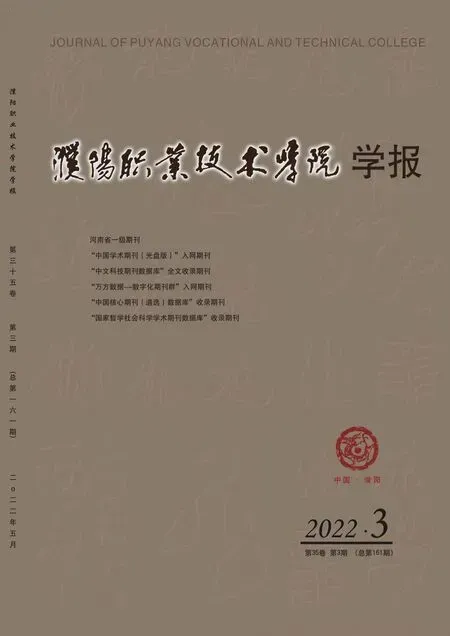曹植作品中的“通天”意识与“龙”意象
夏洵若
(上海大学 美术学院,上海 200072)
一、中国古代“通天”意识及其意象
“通天”意识是上古天人文化的核心概念[1]125,由原始先民出于本能,对“天”和幻想中的“天界”的向往和敬畏而产生[2]172-173。上古人类自发制作有关“通天”的形象造物,以原始意象的形式留传后世[3]73-74。20世纪西方心理学大师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人为,人类自先祖承接下来的某些意识潜伏在脑海中,通常处于沉睡而不自觉的状态,在需要大量灵感涌现的文学艺术创作与梦境、冥想等关联潜意识的活动中觉醒[4]127-129。无疑,像曹植这样的作家,一生之中与埋藏在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始意象”打交道的机会,远高于普通人。古代天人文化埋入集体无意识深层而传承至后世的文化元素,就在曹植的那些华丽清雅、辞采华茂的文字里,时不时呈现出相关的意象。
(一)“通天”意识与龙形象
中华文化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龙,实则是关联于天人文化的原始设计造物。它在人类先祖对于“天界”和光明的向往以及所谓“通天”的心理需求下,应运而生。中华文化中的龙并非真实世界里存在的物种,而是由一代代民众逐渐添加元素构造的具有特定历史文化内涵的人文动物,其重要内涵之一就是上古时期曾经盛行的“通天”观念。古语有云:“龙无尺木,无以升天”[5]133。这里所谓的“尺木”,即龙头上的角,龙创构之初据说取自鹿角[6]51-52。“尺木”还与上古神话传说中的“神树”概念相关,龙角与树木就成为两种具有“通天”功能的意象符号[1]125-126。前者在龙的头上扎根生长,后者则独立成为一种“天梯”式的存在物,如同扶桑、若木、建木等[7]377,在东西方神话以及一些文学艺术作品包括曹植的作品中,都有表现。
由于人类自古产生的对幻想中的“天界”“天神”的憧憬与敬畏,上古天人文化中的“天”之“象”,引导人类勤劳创造了各类造物和精神仪式。考古发现的许多原始艺术品,或多或少都透露先祖对“天”的兴趣。例如1987年考古学家在河南濮阳地区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中华第一龙”[8]115,就是蕴含着“通天”观念的原始遗存。换言之,在原始先民看来,龙就是一种“通天”媒介,寄托着人们对“天”的深厚情感,由古人们依照取象思维创造出来。中华自古即有取象思维,其源头可追溯至《周易·系辞》中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之说。这也是曹植所熟知的。取象原理就是上古天人文化遗留的一种原始思维,也是后世那些受到这一集体无意识浸润的优秀创作者包括曹植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内核。其中首要的“象”就是“通天”,对应的形即为龙。
龙是关联上古先民们普遍存有的“通天”思想产生的意象式造物,具有相当的意识形态内涵[9]153,尤其是龙头上的角,为上古先民在设计其形之时注入其本源之“象”的产物。龙角与楚巫术文化中丧葬明器镇墓兽头上的鹿角是同宗同源的[10]4-5。镇墓兽也是真实世界里不存在的兽类,由古楚地区人民创造的时候融入了“通天”意识。近年已有学者注意到,中国秦汉以前在灵魂观影响之下产生的镇墓兽更应被称为“引魂升天兽”[11]25-26。它首要的职能身份相当于护送墓主人的灵魂通往天界的使者[12]81-82。同理,龙也具备了类似的“通天神兽”身份[9]153。这正是曹植的一些作品取用此意象的深层意涵所在。
(二)曹植作品中的“通天”意象与取象思维
曹植这样顶尖的文学艺术家深谙通天之象,具备抽象思维能力,擅长哲学思考。在他看来,纯粹的文学创作不过是“辞赋小道”[13]433,他关心的是有关天下的大事业[14]前言16,于是将自己的政治理想等意识形态注入文学创作中,这样的过程本身也蕴含了形与象的对应关系,即涉及一种文学表达手法上的取象原理。在他那些以弃妇视角表达被君主所遗弃、政治不得志的哀伤之作如《七哀》《浮萍篇》等篇章中,这类手法十分明显,其中的女性意象较易被人们所理解,已被主流学界认可。不论身处于怎样的环境状态,他都不放弃理想追求,犹如上古先民们对“天”和光明“天界”的憧憬那般[1]125,他要为他心中的“皇天”尽忠、献上自己的“王佐”才干。这就是他作品中时时出现的一种偏向于抽象的“天”意象[15]45。这来自于他所接受的天人文化中的“通天”之象的影响。这个“通天”之象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龙的意象。
曹植这类高超精妙的取象手法,现代学者赵慧在《浅析曹植诗赋中的取象思维方式的运用》一文中进行了分析,充分肯定曹植的这种取象思维方式和和思维能力[16]68-69。虽然该文没有论及曹植对龙及其他“通天”意象的使用,但十分具有启迪性,不同于主流学界那样,将曹植这位卓越文学家的这类创作视为仅仅出于感性层面(诸如“逞气”“使才”等)的表达,或归于时代风气的影响(诸如“建安风骨”或儒家思想影响等)。事实上,像曹植这样一位优异的一流创作者,不可能仅出于感性层面的驱动而创作那些篇章;即便有时代风气和独特经历的作用,若非理性思维的提炼整合,也不足以形成如此出色的文采和存留世间感动一代代人们的作品。对形与象的对应关系和对取象思维的熟练巧妙的运用,是曹植这类创作之的强力支撑。
“通天”意识是曹植承袭自上古文化并融合自身境遇形成的核心意识,是他运用最多的一层潜在的形与象。其“象”万变不离其宗,即对于“天”和“皇天”的向往和崇敬[17]108;其“形”则千姿百态,龙是其中重要的意象素材,扮演着“通天”往来的媒介。
同属此类媒介且与龙关联密切的,还有“神树”这一形象。曹植的诸多作品都有关于“神树”的描写,通常被视为植物意象,得到过一些学者讨论,却忽略了其中的“通天”意识。而同样关联“通天”的龙意象,由于在曹植的作品内以不那么明显的形式呈现,学界历来很少关注。即便偶有注意到曹植塑造过龙意象,也基本限于其现象描述,未将它与天人文化“通天”意识联系起来进行研究[18]5-7。笔者发现,天人文化原始观念中的龙与曹植作品中的龙意象具有共通之处。曹植作品中的龙意象与他的“通天”思想紧密关联,通过龙与“天”的关联,引申出“皇天”作为政治理想的寄托,展现出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及相应的情怀抱负,实属曹植的“一家之言”。
二、曹植“通天”意识的幻化表达:神话“天路”与龙意象
曹植使用龙意象,涉及上古“通天”意识,形成贯穿其创作的“天路情结”[19]13。他对“天”投入强烈情感而产生对“天路”的追寻,将龙和“神树”等作为“天路使者”的媒介,从而产生了与先民共鸣的那种“通天”精神,并借以表达“通天”原理。于是,在曹植的“通天”取象思维之下,龙就构成了其作品中对“天”和“天路”的追求中的核心意象元素。
在曹植前后期的作品中,都有对“天路”的渲染[19]18,表露出他的“通天”意识。譬如,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少年时期作为贵公子曾给当时的文人朋友吴质写过一封信——《与吴季重书》,其中就出现了“天路”一词,还提到“若木”这种中华上古神话中的神树,同时也提到龙。如前文所述,中华上古神话里的神树就相当于连接天地的“天梯”,具备通天功能,而龙则相当于其异化的动态式“天梯”之化身。原文是这样的:
“然日不我与,曜灵急节。面有逸景之速,别有参商之阔。思欲抑六龙之首,顿羲和之辔,折若木之华,闭蒙汜之谷。天路高邈,良久无缘,怀恋反侧,如何如如? ”[20]171
表达出对时间飞驰、相聚短暂的无奈之感。假如换一个并不具有这么高深思想境界、未拥有上古文化浸润和“天人”感怀之人,表达同样的意思显然不会联系到与“通天”相关的意象元素。对写作速度很快、文思泉涌的曹植来说,自然有感而发的成分远大于刻意为之,也恰符合集体无意识理论:灵感迸发打通了潜意识的隔阂,使得那些承载自上古先祖的“原始意象”得以活跃[3]75-76。
在他向吴质讲述的流连于过往美好时间的句子中,将“六龙之首”与“若木之华”置于同等位置,作了隐晦的类比。“华”具有“花”和“精华”的涵义,为“若木”这种神树之中的精华部位。同理,龙首对龙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结合本文此前所述的原理可知,龙之所以能够飞天,从最初的古人思维来看,就是由于龙头上的角具备“通天”功能。如此,曹植一旦描写到此类意象,就直指要害,这决非偶然,这来自他对上古文化中形与象关系的深切了解。
他早期的《七启》还写道:“升龙攀而不逮,眇天际而高居。”[20]10借助智者“镜机子”之口,他介绍了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曲:“歌曰:望云际兮有好仇,天路长兮往无由。”[20]10他笔下的智者“镜机子”向其听众“玄微子”讲述“宫馆之妙”,透露出的则是作者本身浓厚的“天人”意识,视人类在世间的居住为“天界”之下的暂居,最美的居所就是类似于“天路”通向的那种“天宫”之高居了,而龙的角色就相当于往返天宫的媒介与使者。这与在他后期理想不得舒展而囿于狭小藩地之上,愤懑苦闷之时[21]45-46而作的《远游篇》里所谓“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13]121是一脉相承的思路,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在这首《远游篇》中,还“大鱼若曲陵”[13]121这样的句子,并且同时期的其他游仙诗中也多有用到鱼或龙的意象(他笔下的鱼不同于现实中的鱼之形象,龙则原本就是虚构的),这绝非巧合,而是诗人有意为之,是取象思维的结果。再如《五游咏》中的“六龙仰天骧”[13]119、《桂之树行》中的“上有栖鸾,下有蟠螭”(蟠螭就是盘曲状的龙)[13]117、《仙人篇》中的“河伯献神鱼,四海一何局”以及“潜光养羽翼,进趋且徐徐。不见轩辕氏,乘龙出鼎湖”[13]76等,点出了河伯这个在《洛神赋》中也曾登场的上古神话人物带来的“神鱼”及其跳跃至四海、九州的意象,隐约之间可见其内在关联。他后期虽然创作了很多所谓的求仙诗,但依旧心系家国政治,向魏明帝上书奏表以求自试,为吴蜀二地未攻克“寝不安席,食不遑味”而“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13]319。只不过那些虚无缥缈的描写为他的政治理想披上一层虚幻的面纱。
作为一位自幼饱读诗书、熟知上古文化经典的学问家兼创作者[22]21-24,曹植在运用这类与“通天”相关的原始意象时,采取的原理跟上古先民们出于天人文化自发产生的原始观念有共通原理。比如,他的《九华扇赋》在描绘具象化的物品时,运用抽象化的思维,联想到上古神话元素(不周山),又由“效虬龙之婉蜒,法红霓之氤氲”点到龙的意象。这正是曹植受到天人文化及其一脉相承的楚文化思想浸润的结果[23]102-103。
曹植对上古意象和取象手法既有继承,也有他自己的发展和改造,就如同他由前朝乐府“改制新曲”那样[13]87。对于形的改造通常是肉眼可见而明显的;对于象的引申化使用却显得缥缈而抽象,因而时常被读者和研究者忽略。像“天”这样的本就带有抽象化特征和引申含义的意象,就属于意识形态类的虚构物。曹植作品中的这些意象常常融入了想象的绚丽场景,所以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而只是将其视作普通文人的想象性描写罢了。至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曹植不只是一位普通文人,他是有自身哲学体系、擅长抽象化思维的哲学家,因而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就不同于普通文学家的创作状态。他自小饱读诗书而开启了“集体无意识”的通道,受到上古天人文化和相关“通天”意识的感召,在文学创作中注入了“通天”情结,不仅是感性层面的抒发,更有出于理性层面的思考和精巧的取象思维的运用。
三、曹植“通天”意识的世俗化表达:政治“天路”与龙意象
(一)龙的“天梯”媒介身份和曹植“寄心君王”的情结
如前所述,古人赋予龙以“通天”的神力,这种神力最初内含于龙头上的龙角或“尺木”,后来泛化到整个龙形象。事实上,龙之所以在中华文明具有崇高地位,被视为天子的化身,就是因为它拥有一种符号化、象征化的定位,而这象征符号的形成,实际上就源自上古天人文化中的“通天”意识,这种“通天”意识与曹植对“君王”的向往与敬重,即那份建立功勋的情结[14]前言18具有同构性和同质性。因此,龙在曹植的作品中承载的象征意义,除了来自其本源的“通天”这份原始意象之外,还具有由“通天”引申而来的皇天、皇权以及忠君等观念。
中华自古就有“天”代表君主的文化观念[24]3,以致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意识形态传承。曹植在创作中热衷于表达“天”的意象及其由此引申的“通天”意象(例如龙、天路、神树),寄托了他“寄心君王”政治理想和政治热情。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很多作品都显得辞藻华丽、幻想和意象漫天飞舞,具有浓厚的“仙境”氛围,却又同时给人们以现实的联想和启示,透露出他在现实中的政治道路不如意、壮志未展的困境,其作品既饱含矛盾与张力,却融洽而和谐;行文时有跳跃却极其自然。其观感随意识流动而彰显出一股属于他的独特个性与“气”[25]176-177,给人以深刻印象。
在他明确抒发志向而颇具气势的诗歌《薤露行》里,就有“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的句子[13]135,点出他心目中龙的形象,除了源自上古天人文化的“通天”意识那一重象征之外,还有他引申出的附加价值意涵——龙为“鳞”形态爬虫类动物中最为尊贵、位居最高位的一种生命体。当然,这其中带有哲思和隐喻,暗示一种井然有序的尊卑体系,也暗指他的皇族出身和意欲出人头地的夙愿。由此就更能了解,作为曹魏王侯之嫡公子的曹植却郁郁不得志,从而在文学创作中频繁使用龙意象所彰显出那一份宏大的“理想国”式情怀了。
《薤露行》写道:“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13]135为何要从“天”写起,又为何直言不讳称自己拥有“王佐”之才却“慷慨独不群”呢?似乎并不符合主流的儒家思想,而带有些许阴阳家的宇宙观念意识[26]75。其实,如果认识到曹植拥有自己的“曹子思想”,并且具有强烈的“天人”情怀,就易于理解了。作品表达了对时间短暂的感叹,但并不只是人们简单理解的那种及时行乐或所谓建功立业浅层思维。他深知世间生命的短暂,“天”是美好永恒的本源与归宿,世间的“通天”之路就需要“天”之化身与代表——明君和龙,而他要作为“王佐”来效力以达到理想境界。于是,曹植的政治之路就是他的“天路”,龙就是其中的媒介。
他在代表作《洛神赋》里写到的所谓“寄心于君王”[27]29的那一份牵挂也是抽象化的,并不一定实指当时的文帝曹丕,所以后来年少的侄儿曹叡继位,曹植也能一如既往毕恭毕敬。而再早些年份,曹丕初代汉而立,曹植还曾因将汉献帝退位误为死亡而发服哭丧过[28]315。古人把龙代表“天子”的这一概念理想化并发展成为忠君思想,也流淌在曹植的血液中。这也就是他为何受到曹丕的苛待和排挤压迫,依旧不予反抗、怒而不怨,继续保持忠心和孝悌的缘由。
依照此理,《洛神赋》中的“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27]28就是一种抽象化而隐约浮现至水平面上的“天路”之改良版了,对于那位看似美丽却并不同于神话中“宓妃”的“洛神”,曹植的描写也显然以取象手法进行了改造和引申,称她“将飞而未翔”“飘忽若神”“罗袜生尘”[27]29,这与传说中约定俗成的对于神仙行走水面无痕迹、可飞翔等的描写明显不同[13]226,向读者暗示了这并非一位真正的神仙,而是作者曹植内心幻象的投射,暗含他黄初年间苦涩压抑的情感:“通天”无路而哭诉无门,纵然再美丽(如同他自己多才、忠诚又善良)却不得翱翔翔以“通天”。在曹植笔下,这位“洛神”正面登场亮相之际“翩若惊鸿,婉若游龙”[27]28,“体迅飞凫,飘忽若神”[27]29。“惊鸿”与“飞凫”皆为飞鸟,“游龙”和“若神”则相互对应,这显然就是通向“天路”的使者了。事实上,“飞鸟”也是曹植经常使用的意象,已被不少学者注意到,只不过研究者通常并非从“通天”意识的角度与“龙”的意象联系起来进行解读。
对洛神这一“媒介”的向往也源自其“通天”情结,类似“天梯”原理,可视为曹植“天路”情结的引申和变体。他早年创作的《离思赋》说:“虑征期之方至,伤无阶以告辞。”[27]9所谓“无阶”当然是抽象形式的表达了。他对这篇赋作的赠予人——兄长曹丕叮咛道:“愿我君之自爱,为皇朝而宝己。水重深而鱼悦,林修茂而鸟喜”[27]10,也带有比喻成分,用自然事物的状态来形容人的心理状态。在这篇赋的序文中,他赋予“太子留监国”曹丕[27]9-10“为皇朝”这顶高帽,那还是他们父亲尚且健在的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当然不存在曹植向曹丕歌功颂德的意思,而是他本性心理的流露:作为出身王侯之家、乱世中顶级家族嫡公子的“人上人”的天赐地位,需要倍加珍惜和保重自己,待时机到来,方可借助“天梯”而“通天”以达理想境界。所谓的龙就充当这样一种动态化的“天梯”角色。并且,神话传说里的龙在其表象造型之外,还被赋予了身世的内涵,即所谓“鱼跃龙门”。《离思赋》就暗藏着“龙”与“鱼”的意象式关联。而在他的大型作品《洛神赋》中,则更为明显地向着虚幻仙界去发展了:“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鸾以偕逝。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27]29别看这里面动物意象繁多而令人眼花缭乱,其实就是鱼、飞鸟、龙,其象征内涵皆为“通天”。看似虚幻缥缈、幻境斑斓,实际上却是曹植现实意识的折射、政治情怀的表露。
实际上,曹植在带有政治情怀的《鞞舞歌》等一系列根据旧曲改制新歌的五首乐府里,也有“通天”意识和龙意象的跃动。例如首篇《圣皇篇》中的“龙旗垂九旒,羽盖参班轮”[13]88,《大魏篇》中的“玉马充乘舆,芝盖树九华”[13]94,出现了龙意象、龙的变体玉马、神树意象,三者均为“通天”使者。这是曹植为以兄长曹丕为首的曹魏政治集团歌功颂德而作的,这三种意象是他抒发“通天”情结的合理载体。
(二)龙形象的变体与曹植的政治情怀
从龙的本体形态可知,上古先民们塑造这一形象的素材来源,除了鱼之外,还可由马幻化而来[29]12。于是马就成为紧密与龙紧密相连的同类思维的意象造型。曹植多次运用千里马和伯乐的典故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由此就可窥见其政治情怀及对“君王”的那份情结。他在《求自试表》中说:“臣闻骐骥长鸣,伯乐昭其能;卢狗悲号,韩国知其才。是以效之齐、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今臣志狗马之微功,窃自惟度,终无伯乐韩国之举,是以于悒而窃自痛者也。”[9]320可谓“寄心君王”的典范。作为魏文帝曾经重度忌惮的竞争者,曹植在后期只能加倍谦恭以表明忠诚之志,对魏明帝曹叡这位初期延续其父皇政策的年轻君主表示臣服和恭敬,甚至用犬马来形容自己。这与他早些年在曹丕当政期间欲治其罪时为表明心迹所写的《责躬》如出一辙:“踊跃之怀,瞻望反侧,不胜犬马恋主之情。”[9]28
中国自古就有以龙为尊、以龙喻君的文化传统,故作为臣子的曹植在后期上奏时不便用龙喻己,后期创作中的龙意象大多出现在游仙诗和《洛神赋》这类充满幻境的作品中。出于这种缘由,与龙意象紧密相关的马,特别是伯乐和千里马的典故因其具有表达政治志向的象征作用,就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深受曹植的喜爱。他在《矫志》这首通篇使用比喻说理的诗中说:“道远知骥,世伪知贤。”[13]46表达了希望自己的忠心贤才假以时日终能被帝王接纳的美好愿景。在《求自试表》里还特意谈到前人贤主“不废有罪”[13]319的范例,特别写到“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13]320,其中蕴含的政治意图是直接而不容误解的。尤其是,如果考虑到马与龙的关联,就不可能得出“感甄派”的结论,曲解为曹植使用“绝缨”典故是为了表明他曾经跟文帝之妻甄后有过隐情,甚至是要“警告”魏明帝曹叡,如果不重用他,他就要将自己与其母的“暧昧关系”公之于众[30]63-64。这样的理解实为纯粹的臆想。历史上根本没有曹植和甄后有过“恋情”的记载,从曹植本人的德行与志向看,他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行为。他的另一代表作《白马篇》同样使用了马意象:“弃身刀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27]135充分表达了他崇高而忠贞的节操。曹植之所以能够视死如归,除了他宏大的政治抱负的支撑之外,他的生死观、他视世间年岁为“寄居”的“天人”哲学思想,也是其重要内在支撑。
(三)曹植的“天人”情怀与龙意象表达的“通天”心理需求
《白马篇》里流传千古的游侠形象,明显是曹植理想化自我的投射,再联系到马意象在本源上与龙意象的关联,就可了解,曹植就是那位由马意象幻化衍生而来的“白马少侠”;同时,他心中的自我也是与马意象紧密关联的龙,也就是那种怀有“王佐”之才的“天人”。他在二十余岁时与大学者邯郸淳会面之际,“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31]283,令在场者大为惊讶,邯郸淳甚至惊为“天人”[31]283,成为名垂青史的千古美谈[21]35,这是曹植从年少时代就已达到的哲学高度以及他的哲学家资质在正史中的重要佐证。
出于对上古天人文化的了解与尊崇和对“通天”政治理想的追求,曹植十分珍惜和怀念自己被赋予的这份“天人”赞誉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昔日父王对自己的看好和宠爱。那份青春时光一去不复返,使曹植产生了想要留住时间、“抑六龙之首,顿羲和之辔,折若木之华”[21]171的那一份期望。后来他被禁锢于藩地,畅想还能“乘龙出鼎湖”而“徘徊九天上”,或“翻迹登鼎湖。翱翔九天上,骋辔远行游”[9]76、79。这类描写龙飞九天和纵马驰骋的意象,都是他内心深处的那份“通天”式政治理念的表达。
当他欲“通天”而无门、无望之际,龙意象也频繁出现,但表达的却是黯然神伤的情感。他的《当墙欲高行》首句就写道:“龙欲升天须浮云,人之仕进待中人。”[9]107将龙的升天与人的仕途升迁作对比,其政治理想的表达十分明显。其中的龙意象应当引起重视。这首诗作于黄初年间,当时曹丕当政,曹植受到小人谗言陷害而不得志[27]160-161,于是诗中渴求被兄长谅解。后半段“君门以九重,道远河无津”[27]160中的“九重天”也就是传说中的“天界”,此处代指人间帝王的宫殿。可见龙与天的意象在曹植的思路中也是相辅相成的。
在《盘石篇》中,曹植感叹道:“我本泰山人,何为客淮东?……高波凌云霄,浮气象螭龙。”[9]74仍然是“天人”情怀的感发。该诗还写到:“中夜指参辰,欲师当定从。仰天长太息,思想怀故邦。乘桴何所志,吁嗟我孔公!”[9]74其中蕴含着曹植的政治哲学理想,还点到儒家圣贤孔子,与诗中天上的星辰、高波、浮气、龙的这一系列意象互为呼应,均暗指他的政治理念与相应的凌云壮志。
曹植的这类看似带有游仙氛围的诗歌在后期很多,经常出现龙意象,很多论者视之为幻想的产物,以为不过是普通的华丽场景的描绘;甚至,还有学者误以为曹植在后期由于政治不得志、遭受迫害,就转而去信奉道家神仙体系[32]61。在我看来,这无疑是将他这样一位拥有“天人”意识的哲学家[17]108降格以待了。曹植受到来源于上古时代天人文化的浸润,远早于道家方术信仰的形成,更何况他还有诸如《辩道论》《说疫气》等诗文明确表示不相信神仙之说[33]160-161。那些游仙诗实为源于现实的政治情怀的幻化表现,字里行间充溢的是“通天”意识而非宗教观念。曹植作品中的那些龙意象关联于他“寄心皇天”的“通天”诉求,而非追求道家的升仙境界。他的那些所谓求仙诗中的政治指向、警戒讽刺的意味其实是跃然于纸上的。比如,他在《平陵东行》里写道:“阊阖开,天衢通,被我羽衣乘飞龙。乘飞龙,与仙期,东上蓬莱采灵芝。”[27]148可想而知,既然“龙”和蓬莱仙境都是虚幻的,所谓“天衢通”也就是反话了,真正状态下的“天衢”即“天路”是关闭的,即与他在《五游咏》里所说的“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9]119是一个意思,都是对现实的不满与讽刺。又如,他在《求自试表》写道:“顾西尚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使边境未得脱甲、谋士未得高枕者,诚欲混同宇内,以致太和也。”[13]318这样心念九州安危之人,又怎会去追随道家的神仙之说?他自己就明言:“夫自炫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也;干时求进者,道家之明忌也。”[13]320对于道家明确忌讳的,他都要去做,就因为想要尽人臣之本分:“而臣敢陈闻于陛下者,诚与国分形同气,忧患共之者也……是以敢冒其丑而献其忠……圣主不以人废言,伏惟陛下少垂神听。”[13]320将自己奏表的对象魏明帝比作“神”,不也是出于政治需要的姿态吗?又有谁会因此觉得曹植以为曹叡是天上神仙,抱有“真人活体崇拜”的迷信意识呢?道理其实是一样的,他同样认为神仙和龙都不存在,只不过出于政治理想表达的需要,将神仙和龙塑造成为自己笔下的意象,巧妙地让其为己所用罢了。正如《论衡·龙虚》所谓“如以龙神为天使,犹贤臣为君使也”[5]129,这种认知必被“王佐才”[13]135曹植深深刻印在心。龙,就存活在他的思想和作品之中,注入他的“通天”情结和对于“君王”的“寄心”,以及相关联的属于他自己的政治哲学理想[21]80-81,再通过文学手法,经由意象塑造,就变得鲜活灵动,成为承载他的思想情感的载体。
四、结语
龙是曹植作品中含有哲思化感悟的理想象征,就如龙在中华上古先民们初始塑造的形象之中关联了“通天”意识那样。曹植熟读先秦经典而通晓神话造物的来源,古为今用、“为我所用”,注入了他自己的思想。通过对应上古先民创造的形与象的原始观念,采用类似的取象思维,将龙这一种形象背后的“通天”象征作了引申,从最初的物质化的“天”与幻想中的“天界”,到他聚焦的政治理想中的“君王”与“寄心”的那一份帝王家国政治,恰好与龙的“天子”象征相对应,因而在曹植上书奏表给皇帝时则加以避讳、更为隐晦地引申成为与之关联的马意象。他那些看似游仙诗的充满幻想的作品中,也常常和鱼意象相互关联,或与飞鸟、凤鸾之类相匹配。他在流传至今仅剩四句的《言志》诗中写道:“庆云未时兴,云龙潜作鱼。神鸾失其俦,还从燕雀居。”[13]64又在《篇》里这样说:“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世士此诚明,大德固无俦。……雠高念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13]109这是多么高尚而远大志向!
故此,龙是他借以比喻“通天”意识的媒介使者,凤鸾飞鸟是与他的志向及龙意象相匹配之伴侣,“雷音”“猛气”等,则都是与龙意象相辅相成、互为衬映的气势衬托。借助上古天人文化中的“天”意象,曹植用精巧的取象思维糅合成为自身的政治理想的象征化表达,凝聚在相当于“天路”使者的龙意象中。这是曹植超越荣辱的不变的情怀,也是源自他真正的“天人”风采塑造出来的暗含他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的文学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