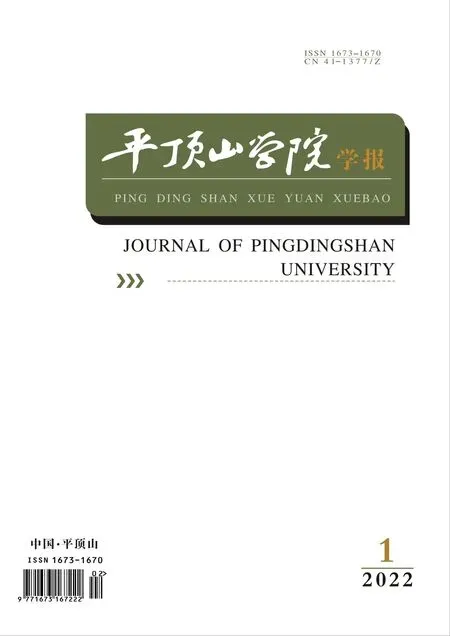清俊和融
——元初名臣程钜夫的题画诗风
王子瑞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程钜夫(1249—1318),原名程文海,字钜夫,江西建昌路南城(今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人。少时与吴澄同学,交谊甚深。时贤多着眼于程钜夫南下访贤、奠定元代科举制等政治功绩及著述考论,进而从政治文化层面评价其对元代文风的影响;然对其诗歌艺术特色的论析尚显粗略,更缺乏对其诗风的凝练概括。检程钜夫文集(1)程钜夫所著《玉堂集类稿》九卷、奏议一卷、诗文三十五卷等皆各自为部。其子程大本将其合辑为《雪楼集》四十五卷,由钜夫门人揭傒斯校正。《四库全书》所收两淮马裕家藏本并作三十卷,乃其孙程世京、揭汯于至正末年重编。今人张文澍以清宣统影刻明洪武本为底本,另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校本,校点《雪楼集》而成《程钜夫集》。此本于原书三十卷后新增《辑佚文》并《附录》章,所载程钜夫资料较为翔实。本文所引程钜夫诗、文皆从此录。,诗歌有六卷,共699首,其中题画诗162首,数量近四分之一,可见题画诗是程钜夫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其诗涵盖山水景物画、花鸟梅竹画、人物故事画等,诸画科皆及,其中不乏赵孟頫、钱舜举、李公麟等历代名家画作。从体裁来看,不仅囊括常规的五七言古体、律诗、绝句,还出现模仿《诗经》体的四言诗、骚体及少见的六言绝句,可谓众体皆备。故程钜夫题画诗不仅独具艺术特色,更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诗歌风貌。本文对程钜夫题画诗加以发掘,以期为尚显薄弱的元代诗歌研究奉添砖瓦。
一、以钦慕归隐为主体的多元情感内涵
程钜夫以南人身份出仕元朝,虽极受元世祖赏识,但其性格“柔顺而秉刚明”[1]478,言行多次“大忤时宰意”[1]473。通南北之选、损行省之权等政治主张皆侵犯了当朝权贵的利益。权相桑哥就因受其弹劾,倒台前曾六次进谗加害他。尽管身居高位,深受元世祖赏识,但险恶的生存环境使其渴望安宁的心灵寄托,因而归隐思想是其题画诗最为重要的内涵,贯穿于各种绘画题材中。危素概括这种心境道:“碧涧红泉,公所游衍。鱼鸟相忘,放怀高远。”[1]476无论是清净朴素的青山流水,抑或热闹纷繁的缤纷春景,诗人在观赏时皆发出“谁能如此住”[1]440的感叹。
反观程钜夫有现实隐喻性的题画诗作,即能体察诗人对世道艰险、俗务缠身的厌倦。如《题九方皋相马图后》:“万里出市骏,九京谁作歅。多因毛色似,误杀明眼人。”[1]342南下访贤是程钜夫最大的政治亮点,他力主对南北人才一视同仁,促成一批江南贤才入仕元廷,这在元初无疑是一种重大变革。因此,程钜夫的角色可以和为秦穆公相马的九方皋相类比,善于“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2]。但世人多因表象而对真正慧眼独具者大肆排挤抹杀,因才招祸的愤懑更令人向往纯净之域。诗人清楚,既陷纷扰中,就算真的避居山林也可能不得安闲,如《夏珪山水》所言:“隐者多依泉石间,结庐相对共悠闲。谁知泉石更多事,日夜斗声来撼山。”[1]451
元代十分重视道教,游仙玄幻之风盛行。程钜夫作为元廷重臣,与道教领袖交往密切,如《洞明祁真人像》《题吴闲闲拟剡图》即是为祁志诚、吴全节(号闲闲)两位著名的全真教、玄教大师题作。受此影响,程钜夫题画诗常将归隐仙化,以表达对放浪形骸、忘却机心的渴慕:或将隐居环境仙境化,或将隐士行止仙人化,常有乘云、蹑浮、居于岩洞、以草露为饮食等超脱凡俗、天人合一的习性。值得注意的是,当画作引发诗人的归隐、思乡意志时,他也善于运用同样虚幻的“梦”意象,如《麓石图》:“我有涧边苍玉笋,如何空寄梦魂间?”[1]391将一腔情思寄于魂梦中。最有特色的是《乔达之画江山秋晚图三首》其一:“遮日西来正暮秋,买鱼沽酒醉船头。如今见画浑疑梦,知是南湖第几洲。”[1]392诗人过于神往画中意境,以致觉得现世才是虚假的醉梦。这种有意无意地将现实和梦境交错、切换,正是他日日煎心的有力证明。
更为可贵的是,程钜夫在诗中对归隐的最终境界有独到的思索。如“谁能如此住,相对两忘情”[1]440“世人那得似,江海永相忘”[1]441“海翁那有机,相忘自应遣”[1]426“名字不须排甲乙,相忘相与坐忘年”[1]407等句,显然是继承了老庄“物我两忘”的思想。程钜夫对归隐的理解无疑是深刻的,如果身在山水,却不停地加以标榜和刻意的选择,那也只是停留在“相对”层面,只有“相忘”才能真正融入身心,只觉一切都是顺应自然而已。同时,他在观画题诗时也意识到,这种状态是世人包括他自己都很难达到的。
二、诗画相资的创作模式
林东海在《中国画款题类编序》中这样评价诗与画的微妙关系:“画中题诗,妙用无穷。画意之未尽者,诗以发之;画境之妙者,诗以评之;画幅之虚者,诗以实之。”[4]深刻地揭示出诗可以扩充、评介、点明画意。查洪德将其概括为“诗画相资”[5],这是由于诗画同体,根源互通,“诗者心声,画者心画”[6]。这在程钜夫题画诗的创作模式中得到鲜明体现。简单地说,诗重在评介景物,可称为评议型;诗重在还原画面,可称为复原型。
(一)评议型
这类题画诗“题”的意味很足。程钜夫经常有意无意地在诗中点明自己在直接或间接地进行观画、题画,明确地把画和自己分隔开,因而具有很强的题画意识。如“参差忽落画图间,白发朝臣惊欲倒”[1]101“老臣抚卷重太息”[1]101“题诗自惆怅”[1]439“诗人不识画师意”[1]365“人间空画本”[1]99“空使闲人画作图”[1]440等诗句,可知诗人是作为一个观赏者在题画。题画意识凸显容易使诗歌具有评介性,评议型是其题画诗中最显著的创作模式。
感画而评是最常见的类型。诗人议论或抒情,与眼前之画关联紧密,如《蜻蜓》:“蜻蜓飞款款,萑苇舞僛僛。欲泊未泊间,漂摇故多疑。甚欲呼与语,小立休嫌疑。枝叶元不动,风波有定时。”[1]100这是一首隐喻政治的童话诗,实际是对时局与贤才之间微妙关系做出判定,隐含为朝廷安抚人才的深意。在观赏《蜻蜓》一画时程钜夫的政治观被触发,进而产生比附联想。《耳鼠食栗》运用白描勾勒出耳鼠的体貌特征,接着严厉斥责其“阴类”品性,程钜夫借此抨击奸佞小人,劝诫君王远离宵小之徒。这类“以笔献箴”的评议诗,不同于士大夫词翰之余的墨戏之作,它以评的形式,或揭明画旨,或发挥己意。
还有一种类型较特殊,尽管诗中内容也是从画中衍生,但与图画本身的联系较松散,基本可离画而读,或全论个人情志感怀,或关注画作本身、画家、作画行为等外在因素。这在程钜夫题画诗中并不少见,如《画牛》:“东华尘里度年年,每见春风忆故园。曾是江南新雨过,闲看稚子引乌犍。”[1]440即直接跳过观画、感画环节,直接进入对风尘生活的感慨和故园的回忆。再如《题李宗师所藏李仲宾李雪菴赵子昂墨竹》对画家及其风格的评述,灵动风趣,精妙恰当:
李侯游戏竹三昧,叶叶枝枝分向背。
却忆王猷径造时,一点清风惊百代。
雪菴笔力老且坚,神藏气密如枯禅。
緐霜彫林雪积野,虚堂宴坐方寂然。
最后数竿更森竦,高节犹含老龙种。
一枝欲费百金求,松雪道人世所重。
羡君一朝得三绝,五月对之若冰雪。
我但从君觅竹栽,满植中庭贮秋月。[1]438
此似仿杜甫《饮中八仙歌》而作。诗人以敏锐的鉴赏力,洞察三位墨竹名手的神趣,精辟到位。如果是仅限于画图物象作意态描摹,则显得笨拙陈腐了。
(二)复原型
苏轼评王维画作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7]元人王冕也指出:“古人以画为无声诗,诗乃有声画,是以画之得意,犹诗之得句。”[8]因此,诗也可以是传达画境的载体,题画诗尤能打破文字与图像的界限,以独特的方式复原图画。程钜夫题画诗的复原型模式别具特色,实画幅之虚,发未尽之画意。
平面、静态的图像通过单一的视觉感官呈现在观者面前,这限制了观者对画境的领悟。诗歌讲求“神与物游”[9],用诗语拟构立体、动态的时空,人用神思感悟之,这就弥补了图画的不足,使其更具生命力。程钜夫题画诗即善于立足于图画本身,以诗的方式“图”其画,将其虚处落实。如《题仲经家江贯道潇湘八景图八首》,八首诗都是在还原潇湘地区八种不同类型的山水景观;《题山水便面》意在复原画之经营层次;《渔翁图》尤为成功,“祝儿休啼手正忙,网成得鱼如汝长”[1]401,最是诗画相资的点睛之笔,还原出民间家庭劳动繁忙而欢快的动态感。图画中无法明确展现的感官方面的内容,只能通过画外之诗来实画幅之虚,实为诗人对通感的巧妙利用。
同样,发画意之未尽,对画境进行横向或纵向的延展扩充又是一种再创造。此种手法并不从属于原有画面本身,也不仅是对画境进行立体化动态处理。最常见的是诗人让自己作为主人公出现在复原的图景中,好似画幅本身的有机部分。例如《舜举梨花折枝》:“一枝独背春风老,尽日巡檐捻白须。”[1]409诗人在复原梨花折枝场景时加入了自己的形象,使得诗中所描写的画面更具个性化的情感内涵。但是,它与画家本意是否一致已无法探明,这种“任性”补添的形象是根据诗人“预设”的情感而塑造的。与对画面的横向扩充相比,更能令画面活起来的是诗人对人物情思意态的观照。如《江皋雪霁图》营造了一种朔风凄凄、无人同赏的语境,诗人无中生有地琢磨这位携琴探梅者具体的心理活动,认为他一定在独自长吟“思郢曲”。这当然不是妄作臆测,而是依据画境,合乎情理地纵向补充画意。
三、清俊和融的题画诗风
今之学者多认为程钜夫不以诗歌名世,但承认他是元初台阁文人之首。与他同时的人或后学也主要推崇他平易正大的文风。如揭傒斯说:“所为文章雄浑典雅,混一以来,文归于厚者,实自公发之。”[1]473危素也说他“以平易正大之学振文风,作士气,词章议论为海内所宗尚者四十年”[1]476。相比而言,四库馆臣的评价显得更客观翔实:
文章亦舂容大雅,有北宋馆阁余风。……苏天爵撰《文类》,亦录其文十余篇,大抵皆制诰、碑版、纪功、铭德之作,而不及诗。然其诗亦磊落俊伟,具有气格。近体稍肤廓,当由不耐研思之故。古诗落落自将,七言尤多遒警。当其合作,不减元祐诸人,非竟不工韵语者。天爵偶尔见遗,非定论也。[10]
对其文和近体、古体诗的评价是符合事实的,甚至将他与元祐大家相提并论,而不依古人选录之成见。题画诗作为程钜夫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延续其整体文学风格的同时,又别具特色,兹概括为:清拔、俊伟、和融。
(一)为诗“清拔”
“清拔”即清雅脱俗。程钜夫清介自守、不与世俗相婴的信念在其题画诗中多有表达。他虽累任朝廷重臣,案牍劳心,但绝无沉湎于声色势利不能自拔之态。如此,他的心才能畅游诸如龙腾虎游、苍松流泉的幽僻仙境。
诗品之清与人品之清又有内在一致性。他在评画家高克恭时就说:“匪徒妙丹青,秀句蔚骚雅。胸中殊磊魄,笔底聊复且。”[1]397唐代诗僧贯休亦说:“乾坤有清气,散如诗人脾。”[11]可见,诗风欲清拔,必有诗人清傲的人格精神。人格清则得天地间清气,气清则思清,贯入诗中,方可清雅不俗。其具体表征在物象和诗境上,正如刘将孙《彭宏济诗序》所论:“天地间清气,为六月风,为腊前雪,于植物为梅,于人为仙。”[12]程钜夫在题画诗中不仅反复描摹仙游之境,更将白雪(20次)、竹(12次)、梨、菊、梅(17次)等景物作为诗歌主体意象。这些物象本身就是天地清气的浓缩,“长松茂竹,雪积露凝为清”[13],可用以构建、渲染清拔之意境,所作诗歌自然清气满纸。
(二)为诗“俊伟”
历代论家推崇程钜夫平易正大之文风,对于纠正宋金季世“文辞率粗豪衰苶”[14]之弊有首倡之功。但“平易正大”是其文风,且直接修辞对象为“学”(即理学),自不能直接套用在题画诗上。但不可否认的是,程钜夫十九岁起,即受学于族祖程若庸,而若庸又是朱熹再传弟子饶鲁的门人。作为朱熹之四传弟子,程钜夫可谓得南宋理学之正统,这无疑会对其诗学思想及诗文创作产生重要影响。
程钜夫在《李仲渊御史〈行斋漫稿〉序》中认为“古人一章一句,该体用,具本末”,文章合乎道,即能“精凿沉郁,不假议论而理自见,不托迂怪而格自奇”[1]181。这是理学思想指导下的文学纲领。对于诗歌来说,何为“道”?程钜夫在《跋安南国王陈平章诗集》中说:“夫本以忠孝仁智之道,博以诗书六艺之文。”[1]322在《王楚山诗序》中说要“抒性情之真,写礼义之正”[1]186。衡以题画诗,其应制颂圣、执艺讽劝、抨击邪腐等作皆合乎诗道,虽显正大之气,似应由“俊伟”予以概括。以《温国司马文正公墓碑老杏图》为例,其诗雄文健笔,句奇语重,气魄似韩愈;笔力驰骤,章法谨严,又似少陵。如四库馆臣所言,此类风格的诗作大多为七言古体,篇中皆有俊伟之句镇压全篇,如“愿天回光继白日,愿地注海供玉觞”“霞骞雾翼天日迷,山童地赭民睽睽”“牵牛左蹲右织女,朝暮日月相吞吐”[1]100-101“门前马鸣君欲归,黄河东去浮云西”[1]419等句,读来混转溜亮,奇气纵横,虽合乎诗道,然俊伟深稳。
(三)为诗“和融”
苏轼、杨维桢等人关于“诗画同体”的理论,揭示了诗与画可以和融的根源。题画诗尤能达到“有诗中之画焉,有画中之诗焉,声色不能拘”[15]的境界。在程钜夫的绘画及诗学思想中,对于赏画及题诗,最重要的是诗心与画心的融合,重其意,次其形。这在其题画诗句中多有议论,如“含毫心欲醉,开卷眼还醒”[1]384“疏枝密干皆有情”[1]448“胸中殊磊魄,笔底聊复且”[1]397“至今图画里,输与眼明人”[1]386等句,诗中从不出现“绘画”或“作画”等字眼,而皆称“写”画。画家将自己的人格、精神、意趣贯注于图画中,观画题诗之人则要感悟这种隐微的画心,两心方能交融,题画诗方能情、景皆和融。
因此,评议型题画诗往往能赋物以情,以己情通其心。如“云烟何惨澹,水木亦潇洒”[1]397,云烟并非惨澹,水木也无潇洒之说,这是由于读懂了高克恭的高逸品格与磊魄胸怀。《题李宗师所藏李仲宾李雪菴赵子昂墨竹》更为典型,其人其竹,意趣跃然纸上。当然,这种心意之通,更多的只是一种单向交流,也即“情吾情,味吾味,虽不必同人,亦不必强人之同”[1]321。
除以情融景外,图景与赏画之人也可完美融合。比如在复原型诗中,诗人善于在诗中让自己走入画境,巧妙无缝地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的前提是诗人能在精神上与画家深度结缘,如《题段郁文所藏钱舜举画两首·白菊》:“黄中虽正色,洁白见芳心。折得无人把,何如晚径深。”[1]381在共通清洁立世之心的基础上,诗人能够走进白菊的世界,折下菊花独自走入幽深小径。反过来说,现实世界亦可对画境产生某种“感应”,如“偶然纵笔作长幅,飒飒坐觉闻风声”[1]448“开缄萧萧朔风起,半幅生绢万钧力”[1]419等。这亦是一种景融,仿佛景物已离开尺幅纸张,融入现实场景中发生效应。它不求形态逼真,重在还原画中活意,这也是程钜夫复原型题画诗没有成为呆板复制品的主要原因。
四、程钜夫题画诗的定位及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程钜夫题画诗的定位及影响可总结如下:
(一)承元初南北诗风融合之果
程钜夫奉诏求贤于江南,延揽汉族儒士,所荐赵孟頫、吴澄、谢枋得等人皆是江南的名士。从文学意义上,江南精致、儒雅的文化为北方诗坛注入新鲜元素,自然引起南北融通,形成新诗风的自觉意识(2)杨镰先生指出,只有到了江南诗坛与北方诗坛成为一个整体,元代诗坛才最终形成。参见杨镰:《元诗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4页。。时人谢升孙即公允地评价道:“中土之诗沉深浑厚,不为绮丽语;南人诗尚兴趣,求工于景意间。”[16]元好问的“中州诗”基本可以代表北方诗风,宗学苏黄,沉挚悲凉,鸿朗高华。程钜夫求贤之前的元廷文臣,如刘秉忠、许衡、郝经、刘因等人皆习此风。反观程钜夫题画诗,以《温国司马文正公墓碑老杏图》这类古体诗成就最高,雄健潇洒之气格贯穿始终,但无北方诗人普遍具有的悲凉粗犷之气,而呈现出重人格、情趣之清雅脱俗的风貌。此外更有大量花鸟虫鱼等具有明显江南风情的用象和题材,语言也相对绮丽绵密。因此,其题画诗总体上以江南风貌为基本,补以北方浑厚雄奇之气,形成清拔、俊伟的独特风格,实际是元初南北不同诗风融合、互补的结晶。
(二)开元中期主导诗风之先
南北诗坛融合的目的在于销尽宋金季世粗豪衰陋之气,建立符合混一海宇之大一统王朝的诗坛新风。对于元中期主导的“雅正”(3)查洪德教授在《元代诗学通论》中指出,传统上流行的“雅正”非诗风概括词,而是诗文创作标准,元代主导诗风应是“清和”。此处兼采两种说法,不做区分。之音,程钜夫实有独特而具体的论述:
夫本以忠孝仁智之道,博以诗书六艺之文……故其落笔如大将治军旅,贤辅立朝廷,纪律严明,条令整肃,而不失舂容闲暇之意……其亦治世之音乎?[1]322
这已基本阐明“雅正”内涵。而程钜夫题画诗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这一时代潮流。内容上,其诗重忠孝之道,抒情、写物皆尚实而黜浮华,理明而正;形式上,五、七言歌行磊落俊伟,章法严明,合于绳墨而雅。此外,其清拔、和融之风貌,在语清、意清、象清的同时,达成情、画、诗相融一体的审美感受,与虞集所提倡的“‘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风来水面’,和之至也”[17]的“清和”诗风相契合。显然,程钜夫题画诗已初步显现出延祐中期主导诗风的某些特点。
这在题画诗领域也具有先导意义。与程钜夫同期的南北方诗人大多还为故国覆灭的悲痛情绪所笼罩,如刘因的大部分题画诗都沉郁伤感至极,远非“治世之音”,抑或把题画诗看作一时墨戏之作,如王恽“因画题画,就画叙事”[18]46,蕴含甚浅。受到程钜夫创作影响的后学中不乏名家,如门人揭傒斯题画诗常“大有寄托”[19],善于将有关民生、社会等内容借助画面景物传达,重道尚实,虽有讥讽不满的情绪,但表达得稳成持重。赵孟頫同样深受程氏知遇之恩,其诗在赋予画面以立体动感的同时,让自己与景物对话,使得情、景自然而然地结合,这种“和融”风貌与程诗高度相似。在诗歌内涵方面,赵孟頫同样把心向林泉、欲归不得的归隐之情作为主要内容。总的来说,从南北诗风融会到步入元诗中期的过程中,题画诗风格转为“或清俊豪健,或蕴藉雅正,毫无纤弱之习”[18]53,程钜夫的引导作用不可忽视。
元代是题画诗真正兴起并成熟的时代,其诗量之大、诗人之众,在题画诗史上绝无仅有(4)清陈邦彦所辑《历代题画诗类》收录唐至清代题画诗近9000首,元代不足百年历史,却有题画诗3798首,约占总数的42%。但元代实际题画诗数量应远不止于此。。近年来元代题画诗研究趋于集中、细致,尤其个案研究方兴未艾。像程钜夫这样诗文才华为政名所掩的文人还有很多,理应将其充分发掘和客观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