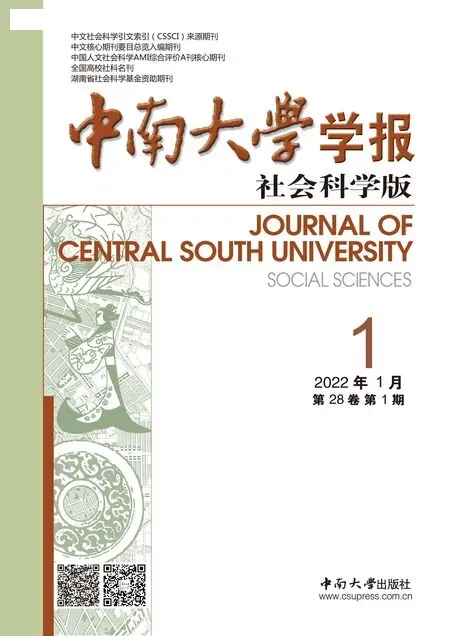阳明心学对儒学传统的重建及其对当代儒学复兴的启示
云龙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在儒学思想史上,王阳明心学有着重要地位。以往研究多关注阳明心学反对传统权威、解放个体思想、倡导自由精神等反传统的一面,而对其重建传统的一面重视不足。笔者认为,立足于批判辞章知识之学来重建儒学传统,才是贯穿阳明心学的核心理念①。通过这种批判与重建,阳明心学消除了程朱理学带来的流弊,接续了圣道传统的精神慧命,完成了儒学在有明一代的重建与转生。
程朱理学在两宋之际曾因重建儒家心性系统这一形上根基,拒斥佛老、传承圣道而为儒家传统的存续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宋元以降,伴随着其作为主流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与巩固,在明初之际已因无法切合世道人心、因应社会生活而逐渐僵化为辞章知识之学。《明史·儒林传》说:“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1](7222)明人李庭机也说:“国初固多才,然而挺然任圣道者寡矣……士知惇质行已矣,于心犹未有解也。”[2](927−928)辞章知识之学直接导致了圣道传统的断裂,“其在俗儒,率外心以求知,终其身汩溺于见闻记诵;而高明之士,又率慕径约,贵自然,沦入于二氏而不自觉”[3](1743),儒家圣道传承岌岌可危。可见,在阳明心学兴起之前,如何批判辞章知识之害以接续圣道传承,实构成最为迫切的时代问题。
作为有明一代最杰出的儒者,阳明对辞章知识之害有着切肤之痛。其龙场悟道前的亲身经历正可看作这一时代问题的注脚。阳明自幼立成圣之志,以承继圣道传统为己任。自娄谅告诉他“圣人必可学而至”[3](1348)以后,他便日夜究心于经史之书,“先生日则随众课业,夜则搜取诸经子史读之,多至夜分”“遍求考亭遗书读之”[3](1348)。不过,其最终结果却是“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3](1350)。阳明亭前格竹的失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3](136)。总之,辞章知识性的“物理”根本无法契合阳明“吾心”学以成圣、承继圣道的现实需要。悟道之后,阳明对辞章知识之学障蔽圣道传统的危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激烈的批判。他在其著名的《答顾东桥书》“拔本塞源论”一节中详述了“圣人之学”“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3](62)这一核心理念,并痛斥时局说:
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其称名僭号,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呜呼!以若是之积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宜其闻吾圣人之教,而视之以为赘疣衲凿:则其以良知为未足,而谓圣人之学为无所用,亦其势有所必至矣
基于如上认识,王阳明以解决时代问题为基本理念,以批判明初的辞章知识之学为基本指向,通过重塑道统、激活经典、会通释老等方式,展开了他“拔本塞源”、重建传统的努力。
一、重塑道统以重铸儒学认同之根基
儒家道统观念乃是儒者基于时代问题、以历代圣王或圣人为线索建构起来的圣道传承谱系,它既是儒者通过塑造理想精神人格所构筑的一种文化传承方式,也是儒者形成文化认同与价值认同的重要根基。儒家道统观念在孔子那里实已初具端倪。《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4](180)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通过“祖述尧舜,宪章文武”[4](38),自觉担负起承继内圣外王之道的时代任务,将儒学的根源追溯至尧、舜、禹三代之上。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基于为儒家心性问题奠定一超越性基础的时代要求,继承并发展了孔子这一观念。他在《孟子·尽心下》末章不仅以汤、文王、孔子来接续道统的传承发展,而且以“闻而知之”与“见而知之”这两种传承方式来表述其道统观念[4](352)。到唐宋之际,作为“异端”的佛、道思想对儒家文化的传承构成巨大挑战。特别是佛、道精微奥妙的心性修养理论,迫切要求儒学建构出一套精深的形上心性理论来捍卫其自身的合法性。在此时代背景下,韩昌黎将侧重讨论心性问题的孟子列入道统之传,明确提出儒学存在着一个异于佛、道的一贯之“道”。他在《原道》中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5](4)虽然形上心性这个超越的价值系统并未在韩愈那里建立起来,但他将孟子列入道统之传,实为后来宋儒“辟佛老”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思路。后来朱子顺着这一思路,面对“老、佛之徒”“弥近理而大乱真”,“先圣之统”“没而遂失其传”[4](17)的文化危机,合《论》《孟》《学》《庸》为四书,构筑起一条由尧、舜、禹、汤、文、武,到孔、颜、曾、思、孟,再到周、程的“圣圣相承”之“道”[4](16−17),有效地完成了辟佛老、明圣学的时代任务。可见,基于时代问题来重塑道统,乃是历代儒者回归与重建儒家传统的一条基本路径。
阳明心学中的圣学道统,正是围绕批判辞章知识之害这一时代任务重塑起来的。相对于宋儒的道统论,阳明的道统论重点突出了颜子的地位。它的最大特点是将自韩愈、朱子以来的“孔孟之传”一变而为“孔颜之宗”②。阳明一方面常将孔、颜并称,认为“孔子无不知而作;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此是圣学真血脉路”[3](118),“至宋周、程二子,始复追寻孔、颜之宗”[3](273),“孔颜心迹皋夔业,落落乾坤无古今”[3](1173);另一方面又多次强调唯颜子独得圣门之传,“当时及(孔子)门之徒,惟颜氏独得其宗”[3](1475)、“见圣道之全者惟颜子”[3](27)、“颜子没而圣学亡”[3](27)。当然,以孔、颜为“圣学真血脉路”,并不是说阳明心学不讲孔孟之传,而是孔孟之传相对于孔颜之宗来说退居次要地位。有学者已指出:“阳明认为……孔颜之学优于孔孟之学,周程之学优于象山学。”[6]由阳明论“孟子三自反后比妄人为禽兽,此处似尚欠细”[7](621),可知阳明对孟子还是有微词的。这迥异于他对颜子推崇备至的态度,也正能说明“颜子没而圣学之正派遂不尽传”[3](27)之“不尽传”义。由此,阳明心学的道统论就呈现出以孔、颜之教为中心,上承羲、皇、尧、舜之道,下开濂溪、明道之学的特点。
在阳明看来,“孔颜之宗”之所以优于“孔孟之传”,其缘由正在于颜子不以知识求圣道。当有人问及《论语》“汝与回也孰愈”章时,阳明解释说:“子贡多学而识,在闻见上用功;颜子在心地上用功:故圣人问以启之。而子贡所对又只在知见上,故圣人叹惜之,非许之也。”[3](37)子贡不如颜回,主要是因为子贡求道的方式是错误的。以闻见知识求圣道乃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阳明认为,由颜子“喟然一叹”可知他对这个道理非常明白。所以当宋儒以颜子“欲从末由”为“未达一间”[4](107)时,阳明明确纠正说颜子“欲从末由”并非“未达一间”,而是文王“望道未见”之意,“道之全体,圣人亦难以语人,须是学者自修自悟。颜子‘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见’意。望道未见乃是真见”[3](27),“所谓无穷尽无方体者,曾无异于昔时之见。盖圣道固如是耳,非是(颜子)未达一间之说”[7](621)。事实上,并不局限于颜子,是否以知识求圣道实亦构成阳明判别宋儒能否继承或能否全体继承圣门之传的根本标准。阳明不把与他同称心学的象山列入“孔颜之宗”,其原因即在于象山之学夹杂着辞章知识性的“沿袭之累”,“其(象山)学问思辩、致知格物之说……未免沿袭之累”[3](202),“致知格物,自来儒者皆相沿如此说,故象山亦遂相沿得来,不复致疑耳。然此毕竟亦是象山见得未精一处,不可掩也”[3](234)。辞章知识性的“沿袭之累”使象山之学无法完全达精一之旨而见圣道之全③。相反,濂溪、明道之所以能够接续“孔颜之宗”,也正在于他们能够以“吟风弄月”等非知识性的态度来体察领会孔、颜之乐[8](66)。由此,通过重塑圣学道统这一文化认同基础来消除辞章知识之弊,也就构成阳明重建圣学传统的第一个方面。
二、激活传统经典以复明儒学传承之依据
每个时代面临的问题不同,经典系统的含义也会随之变化。通过重新激活传统经典来解决时代问题,构成儒者重建圣学传统的另一种基本方式。孔子创立儒学,不仅包括“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道统建构,而且包括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等经典重构;朱子建构其理学体系,也不仅有“圣圣相承”的道统重塑,更包括以“四书”为核心的经典系统的确立及其义涵的重释。同样,阳明不仅通过重塑心学道统的方式来因应时代,更基于以“良知”而非“知识”来解传统儒学之“知”这一核心诠释原则来重新激活传统儒家经典,消除辞章知识之弊。
龙场悟道的过程最能体现阳明通过回归经典传统来消除辞章知识之弊的理念。阳明自述其悟道经历说:“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苶,茫无可入……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3](144)《年谱》也记载阳明龙场悟道时的情形说:“(阳明)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3](1354)合此两条可知,一方面,“溺志词章之习”“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苶,茫无可入”与“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说明阳明悟道之后对他之前以知识求圣道的读经进路非常痛悔,“曾向图书识面真,半生长自愧儒巾”[3](794);另一方面,“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与“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则表明阳明是通过激活“五经、四子”等传统儒家经典来否定他之前以知识求圣道的致思进路的。阳明所著之《五经臆说》,正是他通过激活传统儒家经典所产生的重要理论成果。而后来《五经臆说》之所以被阳明付之一炬,则恰恰表明他对后人以辞章知识的进路来解证《五经臆说》的担忧。
当然,并不局限于龙场悟道,通过回归传统儒家经典来批判辞章知识之害乃是阳明心学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原则。阳明立足于这一原则对孔子删述之义予以诠释说:
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所谓“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3](8−9)
在阳明看来,孔子乃是在否定虚文与批判辞章知识的层面上来确立六经地位的。孔子不是通过增加而是通过削减繁文知识来发明六经之义。反过来讲,以知识性的研究进路来观照儒家经典,则是造成六经分裂失真的根本原因。阳明不止一次强调说,“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芜蔓于辞章业举之习,圣学几于息矣”[3](252),“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3](285),“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3](284)。如果说《五经臆说》之作及其焚毁是阳明通过激活先秦儒家原典来廓清辞章知识之害的源头清理,那么后来其《大学古本》《朱子晚年定论》等著作的诞生则是阳明通过全面激活儒家经典系统来廓清辞章知识之害的全面批判。特别是《朱子晚年定论》的诞生,典型地体现了阳明取法孔子删述之义以激活宋儒经典系统的方法和思路。它正是阳明按照“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说,譬之打蛇得七寸”[3](1303)之只留“七寸”的意义上删述而成的。这样,在激活六经、四子等先秦儒家原典的基础上,阳明通过删述朱子之书,又彻底激活了那被辞章知识遮蔽了的程朱理学真精神。这正是中晚期的阳明为何渐改其前期对朱子的批评态度,而承认朱子与象山“皆不失为圣人之徒”[3](891)的内在缘由。
必须强调,阳明从来不反对阅读经书,他真正反对的是以辞章知识的为学方式去求解经书。当有人问“看书不能明如何”[3](16)时,阳明回答说:“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故不明……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3](16−17)阳明认为在知识“文义上穿求”遮蔽了经书的本真。所以阳明倡导读书与其批判辞章知识之弊不但不矛盾,反倒相辅相成。他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讲得非常明白:“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3](99)阳明不仅不反对读经,而且严厉批评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的时风,并倡导读经要从娃娃抓起,以接续古人“孝、弟、忠、信”等优良传统。这样,通过重新激活传统儒家经典来批判辞章知识之害,也就构成阳明心学重建圣学传统的第二个方面。
三、会通释老之学以重启儒学对异质文化的包容能力
如果说“重塑圣学道统”与“激活传统经典”是阳明通过整合儒家本有的资源来批判辞章知识之害、重建儒家传统的,那么,会通释老之学则是阳明通过点化与消解外部异质文化来批判辞章知识之害、重建儒家传统的。前文已指出,僵化为辞章知识形态的程朱之学在明初之际因丧失传承圣道的能力,已无法阻止释老文化的回流。不过,不同于宋儒把释老之学的盛行归罪于它们“弥近理而大乱真”的特质,阳明更为深刻地把释老的盛行归因为辞章知识对圣学的蔽障,“老、佛害道,由于圣学不明”[3](1352)。所以辞章知识之害远甚于释老之害。阳明在龙场悟道之际就感叹说:“圣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开窦径,蹈荆棘,堕坑堑,究其为说,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厌此而趋彼也!此岂二氏之罪哉!”[3](144−145)高明之士趋向释老,根本原因是圣学本身晦而不明。他在《别湛甘泉序》中更痛心疾首地疾呼:“今世学者,皆知宗孔、孟,贱杨、墨,摈释、老,圣人之道,若大明于世。然吾从而求之,圣人不得而见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爱者乎?其能有若杨氏之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净自守、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杨、墨、老、释之思哉?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而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非复人之所可为,而徒取辩于言词之间。古之人有终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学遂废。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3](257)正是辞章知识对圣道的蔽障,导致阳明心学辟佛老的方式迥然不同于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辟释老、辨异端主要采取大鲧治水式的“堙堵”方式。他们将仙、佛之学视作洪水猛兽,告诫学者要远离佛典以防为其所诱。程子说:“学者于释氏之说,直须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矣。”[8](75)又说:“释氏之说,若欲穷其说而去取之,则其说未能穷,固已化而为佛矣。只且于迹上考之,其设教如是,则其心果如何?”[8](202)事实上,不穷其说而只考其迹,将释老之论当作“淫声美色以远之”,而试图将“异端”堵塞于圣门之外的做法,只能起到扬汤止沸的缓解作用。阳明心学则与此不同,由于它主要是以辞章知识为圣学之大害,所以它并不以三教门户为判别异端的标准。因为,如果仅仅只是以三教门户之见为判别异端的标准,那么势必陷入“我以彼为异端,而彼亦将以我为异端,譬之穴中之斗鼠,是非孰从而辨之?”[3](949)的困境。在阳明看来,是否陷溺于辞章知识之学,才是判别异端的真正标准。阳明常感叹世儒“竞相呶呶,以乱正学,不自知其已入于异端”[3](145),即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这样,释老之学不但不是阳明心学判别异端的标准,反倒可以化为它辨别辞章知识之“异端”的可资利用的手段。所以阳明心学不是以“堙堵”而是以大禹治水式的“疏导”方式,来应对释老之学,以使它们同儒学一道来消解辞章知识之弊。
在阳明看来,儒、释、道三教本来同一根脉,释老之学本为圣学之枝叶[3](1683);三家亦本来同一厅堂,释老之道亦本为圣道之左右间[3](1301)。仙、佛之论本是圣学所固有的题中之义。以“仙”“佛”两概念为例,世儒见人说“仙”说“佛”则辟之,实不知“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3](1301),“仙”“佛”之道本即圣学所本有;再以“虚”“无”两概念为例,世儒亦以“释言空,儒言实;释言无,儒言有”[9](1683)为论,却不知“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氏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3](121)“虚”“无”之本色乃为良知圣道所本有。所以仙、佛之失并不在其说“虚”说“无”,而只是在于“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3](121)。以“养生”“出离生死苦海”为念则会遮蔽“虚”“无”的本色。
进一步讲,如果仙、佛之徒能够真正理解“养生”“出离生死苦海”的本来意义,那么其养生以还“虚”、出离生死苦海以归“无”等说法亦无过错。因为“养德养身,只是一事”[3](208),“果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专志于是,则神住气住精住,而仙家所谓长生久视之说,亦在其中”[3](209);而出离生死苦海的“死生之道”亦只是在“‘息有养,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无一息间断”[3](42)圣学修行工夫中。此二者才是养生还“虚”、出离归“无”的本来意义,才是仙家长生久视和佛家超脱生死之说的本原含义[10]。
在阳明看来,说“仙”说“佛”,说“虚”说“无”,讲“长生”讲“轮回”,实质上亦只是圣学的本有之义。只缘世儒为辞章知识所蔽,看不到仙、佛之道实为吾儒圣道本然蕴含,所以才以彼为异端,“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3](1301);却不知自己“流而为记诵词章,功利训诂,亦卒不免为异端”[3](21),其实自己才是最大的异端。溺于辞章知识,根本无法通晓仙、佛之义,遑论辟仙辟佛了。可见,阳明是通过对释老之学的重新“疏导”会通,来达到他批判辞章知识之学这一目的的。
需要指出的是,阳明这种通过会通释老之学来批判辞章知识之弊的心学建构方式,客观上对释老之学具有致命的消解作用。正与鲧禹治水的结局类似,阳明的“疏导”方式要比程、朱的“堙堵”方式更为成功。不同于程朱理学的“扬汤止沸”,阳明心学这种貌似温和的“疏导”真正从形上义理之根基上“釜底抽薪”地动摇了释老之学。黄梨洲对这一点看得很明白:“程、朱之辟释氏,其说虽繁,总是只在迹上;其弥近理而乱真者,终是指他不出。明儒于毫厘之际,使无遁影。”[11](14)阳明对释老之学的概念作了完全儒学化的阐释与转化,从而在客观上达到以儒化佛、以儒化道的神奇效用。正如阳明自己所说:“王生兼养生,萧生颇慕禅;迢迢数千里,拜我滁山前。吾道既匪佛,吾学亦匪仙。坦然由简易,日用匪深玄。始闻半疑信,既乃心豁然。”[3](808)对此刘宗周独具只眼地指出,阳明对仙、佛的“疏导”乃是“佛法将亡之候,而儒教反始之机”[12](350),其理由是“虽口不离佛氏之说,足不离佛氏之堂,而心已醒而为吾儒之心,从前种种迷惑一朝而破,又何患其不为吾儒之徒乎?”[12](350)所以他由此感叹,“阳明子之道不著,佛老之道不息”[12](350)。
从这一点来看,以批判辞章知识为首要任务的阳明心学并未改变宋明理学拒斥佛老的思想方向。阳明心学在通过会通释老之学来批判辞章知识之弊的时代任务中,继续承负着消解异质文明、传承儒家圣道的神圣使命——只是其消解的方式隐藏在针对辞章知识之弊而使用的“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手段之中。宋明理学辟佛老的任务在阳明心学这里才算真正完成。由此,通过疏导、点化、消解释老之学等异质文化来批判辞章知识之害,也就构成阳明心学重建圣学传统的第三个方面。
四、当代儒学复兴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阳明心学的成功充分表明,传统的继承与现代的重建在儒家文化发展中乃是互为前提的内在关联整体,而其所谓“传统性”与“现代性”亦只是儒家文化共属一体的两个方面。具体而言,重建传统文化,首先就要求我们必须走进传统中去,而不是以知识性的研究方式从外部进行对象性的观照。知识性的研究方式之所以无法复兴传统,正在于它割裂了传统与时代的这种内在关联。一方面,它把传统作为某种已然发生的、与现代生活无关的事实作知识性的考察,阻断了传统的生生之根;另一方面,它又自觉或不自觉地拿某种现成的知识、概念或观念去框定作为知识材料的传统,这又完全遮蔽了传统因应时代、因应现实生活的能力。王阳明以解决时代问题为基本理念,以批判明初的辞章知识之学为基本指向,重建儒家传统的成功实践,对现代儒学的复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关于时代与时代问题的理解问题
时代和时代问题皆是在传统中转生出来而有待我们去发现的。时代本身并不脱离传统,历史上每一时代的儒者都是基于儒家传统找出时代问题,开辟属于他们的时代的。寓“述”于“作”还需先行地“述而不作”,对传统的精神有切实的理解和领会。古人所谓与古为徒、尚友古人的道理即在于此。这正是阳明为何须在“证诸五经、四子”,追溯孔颜之宗等承认传统的基础上始能悟道的内在缘由。没有对传统的真切理解与领会,我们很难发现真正的时代问题,更难开辟属于我们的时代。所以时代问题根本不是现成摆在那里的某种抽象观念,它是在我们对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对传统经典依托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时代和时代问题皆是在对传统的回归中转生并呈现给我们的[13]。
现代很多学者不理解这一点。他们习惯于脱离文化认同之基础,脱离传统经典之依据,抽象地以某些既定的“同质”性的价值观念作为时代诉求。然后以此为依据,来考察儒学中是否有某个或某些价值观念与之相合。与之相合,则证明儒学能够适应时代需要,能够解决时代问题;反之,儒学就不能适应时代需要。好像唯有如此,才是立足时代发展儒学,才是让儒学去解决时代问题,才是复兴传统文化。殊不知,这种“二本”[4](245)性的思维方式不仅遮蔽了传统,更遮蔽了时代。在当今学界,有学者讲生活儒学,讲生存论儒学,想以此强调传统的复兴离不开时代生活或人的当下生存,儒学复兴须立足于时代生活或人的当下生存。这种形式性的讲法本不算错。然而,他们却又仅仅只依据世俗生活的表象,或只依据某些“同质”性的价值观念为表征的世俗生活表象来理解时代生活或人的当下生存,而看不到传统对时代的内在规范制约作用。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本末倒置的误解。这种让儒学为生活而存在的结果,必然导致儒学失去对时代生活的引领、点化与提升作用;这种让儒学为生活而变革的结果,必然导致儒学沦为一种“同乎流俗,合乎污世”[4](351)的乡愿式俗学[14]。现代学术界对传统重建和文化复兴这一话题讨论甚多,却收效甚微,儒学的现代形态迟迟不能建立,其背后原因实与我们脱离传统而只以某种既定的知识观念来理解时代和时代问题这种误解有很大关联。所以,唯有走进儒学传统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发现时代问题,重建属于我们的“新”时代儒学[15](468−472)。
(二)关于传统文化的认同问题
传统文化认同问题所关涉的不仅是价值认同或信仰认同的问题,更是理性分析与理解的问题。不过,理性的理解原则却不是抽象的,而是与价值认同原则相即互成的。当我们谈到时代问题须在传统中转出与发现时,有学者会认为传统本身必须先经过理性的审视,否则由传统转出的现代就是畸形和不切实际的。所以传统儒者那种文化认同先行的思路在当今社会已不再适用。我们不应把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设为前提,而必须理性地分析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然后通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式来实现文化复兴。而如果把文化认同设为前提,就会陷入狭隘民族主义及“原教旨主义”的误区。这是近些年来颇为流行的说法。
事实上,历代大儒从来没有未经理性反思就直接认同儒学的那些价值原则。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前,从来没有把那些既定的“天理”准则及五经、四子等传统经典直接加以认同——尽管他内心非常希望认同这些东西。没有理性的理解作用,从心底里认同这些价值原则本就是不可能的。阳明讲“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3](85),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儒学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化系统,它本身不仅是教化的系统、信仰的系统,也是义理的体系、理性的体系[16]。阳明龙场悟道,正意味着他从义理和理性的维度领悟,而非神秘主义地领悟了儒学的根本精神。唯其如此,他才能真正达成对儒学的认同。
儒学本身即是义理的体系和信仰的系统的统一,它是在理性的考证和自圆其说中来实现自我认同的。这就决定了它不会陷入盲目的信仰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之所以有学者误以为儒学的价值观念经不起理性的考量,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知识性研究方式的作祟。他们不是进入传统本身,以传统自身的义理脉络去理解传统,而是以某种外在知识性的抽象概念架构去框定传统。这当然会导致传统在何谓精华何谓糟粕的碎片化过程中分裂失真。这种研究美其名曰“客观”,实质上却毫无客观性可言。所以,理性分析本来是证成文化认同与文化信仰的好东西,但是如果我们不按照传统文化自身的义理进路去理解和运用它,反而恰恰败坏了理性。用孟子的话说,理性本是“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4](315)。
因此,针对现今无法形成传统文化认同的状况,我们最应该反思和理性分析的是我们自己哪里出了问题,我们的研究和我们的理性陷入了何种误区,而不是反过来以某种外在的知识标准和个人好恶来指责传统,要求传统作出改变。传统作为一个文化精神整体,有它自身的脉络、稳定的内核和自我圆成的合理性,这才是它为何能够走向现代的重要根基。此正如水流之所以能“盈科而后进”[4](273),根本原因还在于它“原泉混混”[4](273)一样。传统之“原”不可能被改变,而只能被遮蔽。而被遮蔽的传统因丧失了自身的连续性,也就不可能盈科后进地走向现代。所以阳明面对时代问题,不是要“变”圣学,而是要“明”圣学,“老、佛害道,由于圣学不明”[3](1352),“圣学之不明,而功利异端之说乱之也”[3](297)。
儒家传统本身作为一以贯之的圣道系统,有着它自身的合理性和超越性。它本是“圣训垂明明”[3](760)的;之所以不明,是被我们的知识、意见或时代遮蔽了。反过来说,它一旦著“明”了,那就意味着它在时代中重建了自身。在这个意义上,回归与认同传统,不但不会导致原教旨主义,反而恰恰能够因应时代之变。可以说,我们愈是能够回归与认同传统,也就愈是能够顺应时代的潮流。归根结底,传统本身虽有着稳定的精神内核,但此精神内核不是某种僵死的教条,而是在时代中展开着的文化辐射源。所以对传统的认同与对时代的关切实相为表里,二者实构成思想建构的“两端”。重建传统无非只是“叩其两端而竭焉”[4](106)。现代很多学者脱离这两端讲传统复兴:一方面,脱离道统、脱离经典等传统认同去讲所谓的新道统,讲新四书、新五经,等等;另一方面,又围绕着某些抽象同质化的西方知识概念这些舶来品兜圈子,而无法发现时代真正关切的问题。用这些“不知而作”[4](96)的方式来重建传统注定是不能成功的。由此而言,在回归经典与道统的基础上,复“明”儒学本有的义理系统,重铸文化认同,不失为重建传统的一条正途。
(三)如何定位西学在传统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中西方文化都有自己的传统和现代,中国传统文化应在疏导、消解西方文化的过程中确立自我认同和恢复自身的主体地位,实现自身传统的复兴。任何一种儒家文化之外的文化系统,对儒学来讲都是异质文化。战国时期杨、墨之道是如此,宋明时期仙、佛之道是如此,现在西方文化亦是如此。国人已经看到,全盘西化与保守拒斥西学都不能让传统得以重建;重建传统,必须“吸收借鉴”(既不全盘照搬,也不完全拒斥)西方文化。不过,在什么意义上实现这种吸收借鉴,以及如何达成这种吸收借鉴,仍有待澄清。阳明疏导释老的方式可以帮我们澄清这一点。事实上,对西学的吸收借鉴和对传统文化认同的确立是内在关联的两面。一方面,对传统而言,西学不是某种现成的知识观念或概念,也不是某种用来框定传统的知识架构,而是资助传统实现转生,可供传统消化的食粮;另一方面,传统也必须在自我认同和自我主体地位确立的基础上才能化解西学的知识、概念,转“识”成智。阳明说得好:“凡饮食只是要养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积在肚里,便成痞了,如何长得肌肤?后世学者博闻多识,留滞胸中,皆伤食之病也。”[3](108)“饮食只是要养我身”,如果没有传统之“我”对自身的认同和主体地位的确立,西学对传统而言只是“成痞”之物。但如果有了传统之“我”,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3](238),皆能化为传统生肌之食粮。
现代部分西学研究者常用西学中的知识观念和概念批判儒学,这和他们离开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而只以西学的知识概念为圭臬的“伤食之病”,是内在相关的。所以我们不是不讲西学,而是要找到属于我们自己讲西学的方式。正如阳明说“仙”说“佛”、说“虚”说“无”一样,在现代我们不仅应该讲西学,而且必须讲西学。只是这种西学概念的具体内涵应是从传统的整体精神脉络中转出,并在这种转出的同时能够保有传统整体性的精神脉络而不失,重新回到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上来,能够形成一个开放包容性的“圆圈”,而不是现成的拿某些抽象“同质”的知识观念去批判传统。所以“吸收借鉴”的前提是有一个文化主体性,有对传统的文化认同。唯其如此,我们在借鉴西学之际才能真正消化吸收它,而不致害“伤食之病”。
当然,我们并不反对有些学者是以西方文化为主体来消化儒家思想,只是这种进路复兴的是人家西学的传统,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传统。这本质上是在讲西学,而不是讲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事实上自西学传入以来,随着它话语霸权地位的日渐巩固,很多儒学研究者都倒向西学而不自知。他们都是以讲儒学的方式来讲西学。这就造成当今学界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只具有单向度的影响,而很少有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有反馈性影响的局面。文化认同的丧失和文化主体性的缺乏正是导致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所以每一种文化或每一个民族文化的复兴,根本上还是要依靠它自身的传统。用海德格尔的话讲,一切本质和伟大的东西,都只能在与它自身同源的传统中才能产生出来[17](1289−1317)。
阳明心学融摄三教,但它却反对“兼取”仙、佛等异质文化的提法,“说兼取(仙、佛),便不是。圣人尽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3](1301)其根本原因亦是在强调儒学作为一有机文化精神之整体系统,本身就具有它自我圆成的精神义理脉络,而无需异质文化的外在修补。这正如庄子所说,“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18](73)。所以“借鉴”西学不能理解为中西两种传统的抽象并列式的“兼取”“杂”合,“兼取”“杂”合只会导致传统的“忧而不救”;而只能理解为为我所用式的“点铁成金”,只能理解为对“我”本有义理的发“明”。儒学何时能够通过激活西学概念的方式来“明本固根”,对西学有反馈性的影响,何时才能言重建与复兴,也何时才能言走向世界。
注释:
① 阳明所批判的辞章知识之学与今人知识性的研究方式在形式上虽表现不同:前者主要表现为中国古人注释、考订传统经典过程中所产生的章句之学;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在西学理论背景影响下所产生的一套思维模式与学术话语体系。然而,就二者对传统的障蔽而言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将传统作为一种已然僵死的现成物进行外在的研究分析,而非把传统理解为一种活的精神而有其时代性的当下呈现。在此意义上,二者皆割裂了传统与现代的内在关联。
② 相对于朱子的道统,阳明道统论的另一个特色是将道统之传从尧、舜之世推至更早的羲皇之世。这和阳明批判知识的进路也是内在一致的。限于文章篇幅,我们在此只以“孔颜之宗”为例来展示阳明通过知识批判来建构道统的致思进路。
③ 陈荣捷先生认为:“阳明对朱子之敬奉,亦可见阳明之沿袭宋学。彼谓象山为沿袭,为粗,恐亦五十步笑百步耳。”参见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274 页。这一论断恐怕未能道出阳明批评象山真正原因所在。阳明批评象山,并不在于象山是否沿着宋学讲,而在于象山之学未能够完全摆脱辞章知识之累,纠正宋儒诸如“知先行后”等错误性的看法,形成一个完善的圣道真理系统。所以阳明评判“沿袭”的标准,在于儒者自身是否真正能够解悟某一观点主张;而不在于此观点主张前人是否提出过。实质上,阳明非常反对世人“人出己见,新奇相高”的做法。具体论述可参见拙作:《和会朱陆如何可能——基于内在与超越的关系对阳明“心即理”思想的考察》,载《哲学与文化》2021年第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