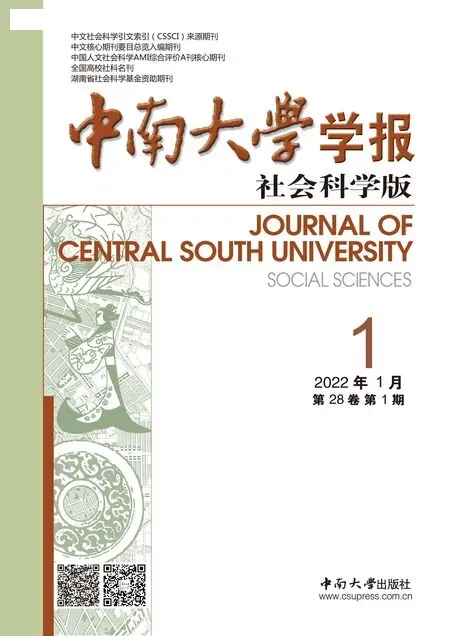反垄断法下超级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合理规制
孟雁北,赵泽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
网络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界定目前尚未达成共识。通常而言,自我优待行为是指平台经营者相对于在平台上的其他经营者而言,通过制定平台规则或者利用自己独特的资源,更加优待自身业务的行为①。这种行为在竞争法框架下的讨论始于2015年的欧盟谷歌在线比价服务案(以下简称“欧盟谷歌案”)②。在该案中,谷歌调整了搜索结果排列顺序的算法,偏袒其自营比价服务Google Shopping,将该业务总是置于搜索结果页面的顶端,造成竞争优势的纵向延展[1]。
近年来,平台巨头经营者(超级平台)③利用自身优势实施自我优待的行为屡见不鲜。例如,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在《数字市场竞争报告》中提到,占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会“通过自我优待、掠夺性定价、排他性交易等手段将市场力量进行传导”④。再如,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KFTC)于2020年10月表示,Naver 在经营网购及视频检索服务的过程中,人为地调整、变更检索算法,将自己的商品和服务(Smart Store 商品、Naver TV 等)提升到检索结果的顶端,同时降低竞争者的相关商品和服务检索结果排序。KFTC 就这一行为下达整改命令并罚款(课征金)。KFTC 明确表示,检索服务平台在决定搜索结果排序时,直接给自己的商品或服务“加分”,或者全面改变算法却不告知竞争者的行为,当影响到竞争秩序时,即违反了《垄断规制与公平交易法》[2]。在我国,是否以及如何规制超级平台的自我优待行为也成了平台竞争治理的热点问题,但在实践中,我国执法和司法机关尚未对此类行为进行查处和裁判。虽然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与工信部一直在关注有明显排他性特征的“二选一”或“平台封禁”行为,但这些行为赤裸裸地排除竞争对手进入市场,自我优待行为则是通过优待自身,并没有直接排除竞争对手。
平台经营者的自我优待行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例如,这种行为是平台行使自治权力的体现:平台通过协议与技术等方式进行内部治理,能够实现正向网络效应,吸引更多消费者[3]。但这种行为也会造成一定的竞争损害,如阻碍数字市场的动态竞争,造成过高的市场进入壁垒。因此,《反垄断法》应当对此类行为予以规制[4]。欧盟在2020年针对某些超级平台发布了《数字市场法》与《数字服务法》草案,意图对构成“守门人”地位的平台进行事前的反垄断规制,对其施加一定的竞争性义务,特别是对第三方经营者开放数据及不得歧视的义务⑤。在国内,有学者以网约车平台滥用自治权对其自营与非自营业务下的司机实施差别定价行为为例,说明这类潜在的自我优待行为需要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5]。
因此,我们将具体阐释超级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规制路径,包括其将会造成何种竞争损害以及具备何种合理性,《反垄断法》为何以及以何种态势规制此类行为。平台的自我优待行为并非当然违反《反垄断法》,应当运用“合理原则”结合个案情况进行分析。我们将提出用“合理原则”规制此种行为的具体思路,使该种行为与《反垄断法》第17 条所列举的行为相契合。然而,严格按照法条中列举的行为进行涵摄的话,会产生条文与行为不匹配的问题,因而需要探究自我优待行为能否构成一项独立的滥用行为,也需要探讨《反垄断法》在实施中应对自我优待行为作出何种回应,以期实现对该行为的合理规制。
一、超级平台自我优待行为之反垄断法介入
对于单边行为而言,判断其是否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首先要判断其是否对市场竞争造成了损害。但对“市场竞争”一词应当秉持较为广义的理解,即涵盖各个市场参与者的竞争法益,包括现有或潜在的经营者和消费者,而非仅限于直接竞争者[6]。在判断单边行为是否损害竞争法益上,我国《反垄断法》在对各种滥用行为进行类型化规定的同时,还在《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第14—20 条规定了滥用行为的考量要素及抗辩理由,而非一刀切地认定某行为不合法。
实际上,不仅我国法律如此规定,《〈欧盟运行条约〉第102 条指南》(以下简称《第102 条指南》)也要求分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竞争损害与经济效率,假如经济效率大于损害,则可进一步考虑该行为是否正当⑥。因此,在分析超级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是否应当被《反垄断法》禁止时,根据该法的分析框架及要求,需要对竞争损害和经济效率进行综合考量,进而判断被禁止的具体情形。
(一)超级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竞争损害
欧盟谷歌案可谓超级平台实施自我优待行为的典型案例。在该案中,谷歌将自营的比价服务Google Shopping 置于搜索结果的顶端。欧盟委员会认为,谷歌的做法增加了自营比价服务的流量,减少了竞争者比价服务业务的用户流量,因而产生了在线比价服务市场上的反竞争效果。欧盟委员会还认为:①该行为可能对谷歌在线比价服务市场的竞争者产生排他性效应,进而提高这些竞争者的经营成本和消费者的支付价格,降低企业的创新动机。经营者与消费者的成本提高是因为其他竞争者对于谷歌这一平台具有强烈依赖性,所以,谷歌可以向这些经营者收取更高的平台管理费,导致企业提供服务的成本提高,消费者获取服务的成本也相应提高。另外,在缺乏用户流量的情况下,这些经营者创新产品和商业模式的动力会降低,其投入产品创新研发的资金相应会减少。在缺少竞争的情况下,谷歌不需要通过产品创新以获取竞争优势,因此也不会主动创新。②该种行为减少了消费者的产品选择,减损消费者福利。由于谷歌搜索引擎的算法逻辑无从知晓或晦涩难懂而非基于消费者搜索时输入文字的相关性排序,导致其自身的比价服务一直处于搜索结果页面的前几位。欧盟委员会认为,这种行为使谷歌的比价服务获得了竞争优势,但该优势并非基于服务质量而是通过搜索引擎服务的市场力量取得的⑦。
法国竞争管理局(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也于2021年6月对谷歌的自我优待行为处以高达2.2 亿欧元的罚款(以下称“法国谷歌案”)。在该案中,谷歌对 Google Ad Manager 旗下的Doubleclick for Publishers(DFP)广告服务器与Doubleclick Ad Exchange(AdX)程序化广告版面销售平台实行了互相自我优待的策略。法国竞争管理局分析了DFP 优待AdX 平台的行为,认为其产生了以下竞争损害:①降低了第三方程序化广告销售平台的吸引力。DFP 通过自我优待的策略,导致第三方平台购买用户清单的能力难以与AdX 平台匹敌,进而在程序化广告销售平台市场上产生排他性效应。②自2015年起,AdX 平台持续制定高昂的产品价格,但并未阻碍总收益的增长,其优待DFP 的行为产生的反竞争效果在于通过削弱DFP 竞争对手对于AdX 平台的技术匹配能力,进而巩固DFP 的市场地位。这是由于该平台独占了Google Ads 和Google DV 360 服务,这些服务对DFP 及其竞争对手而言是无法替代的,基于这些服务所达成的交易也成为它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⑧。
从以上两个案例来看,自我优待行为的反竞争效果可以归结为两点:①通过提高竞争对手的成本或降低自营业务的成本(或品质)达到排除竞争者的效果。②通过排挤竞争对手或降低竞争对手产品质量的方式使消费者丧失选择竞争对手的权利,进而制定高昂的产品价格以诱发剥削效应,享受剥削利润的经营者则很可能减少创新的投入。另外,在数字市场上,自我优待行为还可体现为平台依靠所获取的平台内经营者数据从而个性化推荐自营产品,甚至直接模仿其他经营者的创新产品,通过平台的市场力量、品牌效应及网络效应放大这种竞争损害⑨。这与传统市场的自我优待行为有所不同,因为传统市场中没有诸如平台力量与网络效应等因素的影响。当然,无论在何处,当自我优待产生的竞争损害不容忽视时,就应当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
(二)超级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可能具备的合理性
自我优待行为具备一定的经济效率,某些自我优待行为具有正当性,免于《反垄断法》的负面评价。首先,现代反垄断法并不谴责市场经营者具有优势地位,也不禁止经营者利用优势地位参与市场竞争而不与竞争对手分享优势。换句话说,《反垄断法》并不要求所有的经营者站在同一起跑线上[7]。在IMS Health 案中,欧盟委员会认为“必需设施”与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FRAND)的适用条件必须是经营者拥有的必需设施(代表了竞争优势)对于竞争对手而言是“不可或缺的”(indispensable)⑩。根据此案,欧盟法院开始对拒绝交易案件采用“不可或缺”测试。虽然“不可或缺”的具体标准尚待考究[8],但也说明了超级平台在不构成“必需设施”的情形下,利用竞争优势制定优待自营产品的平台规则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其次,欧盟《数字时代竞争政策报告》也强调,对于自营产品和服务的优待策略可以被视为平台开发与管理的回报,这种策略由此便具有正当性⑪。同时,就自我优待行为引发的“垄断杠杆效应”来说,平台经营者横跨多个市场,在这些市场提供同一品牌的组合产品和服务,有助于增强品牌效应以及减少“ 双重边际效应”(double marginalization effect)所引发的经济效率损耗⑫。虽然平台可能会获取暴利,但从消费者的角度而言,相比于在上下游产业链中有两个不同的巨头企业来说,由一个“垄断者”提供一套组合产品的定价要比两个独立“巨头”的产品定价之和要低,其产生的消费者福利类似于纵向合并带来的收益。反垄断法并不认为该行为“本身违法”。
另外,假设同时存在两个纵向一体化的平台经营者,在都不构成必需设施或者缺乏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双方之间没有帮助竞争对手战胜自己的义务。对于平台自营业务的竞争者而言,尽管其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平台进行经营,但是平台并没有对所有经营者有一视同仁的义务,因而自我优待行为或许合理。因此,在认识到自我优待行为产生许多竞争损害的同时,反垄断法也要基于个案分析,准确识别该行为的经济效率及合理性,不能一刀切地作出判断。
(三)基于合理原则的规制适用
在评判既具有竞争损害又具备一定经济效率的单边行为时,反垄断法一般会适用从美国反托拉斯法实践中产生的“合理原则”进行分析[9],适用该原则时会对行为产生的竞争损害和经济效率进行比较,以比较后的结果作为违法性认定的依据。另外,在进行复杂的经济效率分析时,美国法院也会采用简便的方法,即采用“快速浏览的合理原则适用”(quick look rule of reason)以及“较小限制性替代措施测试”(less restrictive alternative test)进行合理性判断。虽然“合理原则”及相应的“本身违法原则”并非欧盟竞争立法与实践适用的原则,但无论是《第102 条指南》中阐述的合理性与效率抗辩,还是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司法实践,“基于效率”的反垄断评估不但一直被提倡,而且在英特尔案中被明确承认与适用[10]。以上事实表明,欧盟竞争法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分析中并不反对“合理原则”的适用。
以欧盟谷歌案为例,谷歌提出了五点自我优待行为的合理性依据,但遭到了欧盟委员会的逐一驳斥,且其认为:①谷歌在搜索结果栏中的“低质量结果的排除”“相似度关联排序”等逻辑并未体现在搜索结果中。②用户期望看到的搜索结果是根据输入词的关联度而排序的,但谷歌却并没有告知消费者其排序方式有何依据,而在其自营产品或服务的链接处贴上“赞助”的标签并不能满足“告知”的要求。③谷歌不能从对其他经营者的歧视性行为中获利⑬。基于以上原因,欧盟委员会认为谷歌的自我优待行为违反了《欧盟运行条约》第102 条,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从域外的平台反垄断执法案例中可以看出,假如超级平台对依赖平台基础设施运营的经营者实施自我优待行为,特别是在平台企业想要依靠平台本身的竞争优势进行跨市场力量传导的时候,平台提出的抗辩都欠缺合理性。但如果经营者并不依赖于平台,或者具有“多栖性”,平台的抗辩则有可能具备正当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第十次修订后的德国《反限制竞争法》(GWB)中新增第19a 条第2 款第1 项以防止“自我优待行为”,但经营者也可证明自我优待行为具备正当性。因此,已有立法例表明,平台巨头的自我优待行为需经合理原则分析后确认。不过,分析相关市场和认定市场支配地位这两个步骤依然是分析行为正当性的必要前提[11]。
二、平台自我优待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类型
超级平台的某些自我优待行为应当被反垄断法规制,适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鉴于我国《反垄断法》已经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类型化,因此在规制超级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时,应当关注被我国《反垄断法》第17 条涵摄的行为类型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而确定超级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违法构成要件。
(一)拒绝交易
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可能构成拒绝交易行为。拒绝交易是指拒绝向特定交易相对人供货的行为。市场优势企业拒绝对特定对象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将其排挤出市场[12]。在数字市场上,拒绝交易行为体现为纵向一体化平台对平台内竞争对手的营业设置更苛刻的条件,或者故意不告知关键信息,使其无法充分利用该数字必需设施的资源。这会导致“边际挤压”(marginal squeeze)效应,削弱竞争对手的竞争力,进而造成排他性效应。这就是所谓的建设性拒绝交易行为(constructive refuse to deal)⑭。
在hiQ Labs 诉领英案中,hiQ Labs 作为一家初创公司,在创立的数年内不断收集和处理领英掌控的公共数据为自身产品所用,但是领英切断了hiQ Labs 与它的IP 地址关联,并向hiQ Labs发送了停止爬取数据的通知。美国第九巡回法庭认为,领英作为掌控大量公共数据信息的平台,如果选择性地禁止潜在竞争对手收集公共数据,可能导致初创企业无法利用公共资源对自身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创新,这样是不利于竞争的。不过,2021年6月14日,美国最高法院要求下级法院重新审理此案⑮。另外,Authenticom 诉CDK Global 案中出现了协同的排他性行为。市场上的两个平台CDK Global 和Reynolds 达成排他性协议,要求CDK Global 停止向Authenticom 提供数据,Reynolds 则以极高的价格向Authenticom 开放数据接入权限。尽管这三家平台企业在同一市场上相互竞争,但Authenticom 的运行却依赖于另外两家的数据。美国第七巡回法庭认为,该行为构成拒绝交易行为,但是两平台间协议排除与CDK Global 单方排除Authenticom 爬取数据的行为应当分开界定⑯。以上两个案例都表明,尽管无法确定平台或者数据是否构成必需设施,但拒绝数据接入和获取的行为可能构成拒绝交易。显然,HiQ Labs 公司和Authenticom 公司都依赖数据开展经营,被诉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有类似于必需设施的特性。
假设自我优待的实现是超级平台通过拒绝竞争对手的平台接入、数据收集或者设置高价等方式达成的,而这些平台又可能构成“必需设施”,这时,即使没有限制竞争的目的,该行为也会造成较大的竞争损害[13]。从行为的表现来看,也可能构成纯粹的或者建设性拒绝交易行为。诚然,符合拒绝交易的行为特征并不代表该行为违法,还需要经过合理原则的判断。在违法性判断中,欧盟为认定拒绝交易行为违法设定了一项必要条件,与上述必需设施的构成条件类似,即交易“不可或缺”(indispensable),但也需要其他条件的辅助判断[14]。我国《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以下简称《反垄断指南》)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在分析是否构成拒绝交易行为时,可以考虑的因素包括在平台规则、算法、技术、流量分配等方面设置的不合理限制,使交易相对人难以进行交易;还有,掌控平台必需设施的经营者是否拒绝与交易相对人以合理条件进行交易等。由于《反垄断法》下拒绝交易行为的认定比较严格,以至于许多数字市场中的拒绝交易行为,包括平台自我优待行为,似乎都难以适用《反垄断法》中的拒绝交易条款。
再者,平台为了发展壮大自身数字生态圈内的经营实体,自我优待行为可能产生非横向的竞争影响[15],因而如何认定这种生态圈际间的竞争关系也面临挑战。然而,如果将非横向市场的自我优待行为认定为拒绝交易,那么如何界分自我优待行为与“二选一”和“平台封禁”等明显的拒绝交易行为则存在疑问。虽然两者都造成了排他性效应,且经营者也可能意图以垄断杠杆效应扩张平台内的市场业务⑰,但两者的行为方式的确存在差异,因此需要认真区分。如果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涉及与其他经营者的联合行动或者协议,则可以适用横向或纵向垄断协议条款予以规制。这属于规制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另一视角。
(二)搭售
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有可能构成搭售。《反垄断指南》第16 条列举了数字平台搭售行为的具体内容,包括采取一些技术手段使交易相对人以无法选择、拒绝、更改的方式,接受平台所提供的额外商品或服务的行为,使消费者丧失对上下游市场其他产品的选择权。理论上,自我优待行为可能符合搭售的特征。例如一家拥有一定市场地位的、销售A 产品的企业同时销售互补产品B,该企业可以建立A 和B 的独特关联(比如A 只与B 产品完美结合使用,与B 的替代品难以结合使用),使消费者在购买A 的时候往往会一同购买B(购买B 的替代产品会导致A 的效用减损),从而将其在A 市场的力量传导到B 市场,占据B市场的支配地位,这样的行为就可能构成搭售[16]。
实际上,通过平台的技术手段或自治规则搭售或捆绑销售产品,实现自我优待的行为并不鲜见。例如,在欧盟谷歌案中,谷歌在一般搜索引擎服务中提升Google Shopping 搜索结果排名的做法被欧盟委员会认定为搭售行为。谷歌以搭售为“垄断杠杆”,大举扩张其在比价服务市场中的力量,从而在该市场中造成竞争损害,为谷歌的非主营业务攫取了高额的垄断利润[17]。再如在法国谷歌案中,DFP 和AdX 平台互相在价格透明度、平台技术与合同条款实行自我优待的情况下,可能使得DFP 的上下游经营者必须购买AdX服务,因为这是最便宜或者技术上最优的方案。同样,在购买AdX 平台服务时,第三方经营者也必须同时选择DFP 服务器,因为如果需要流畅地使用平台服务,必须通过DFP 服务器进行无缝衔接。这就体现了DFP 和AdX 服务互相的自我优待行为,这种行为可能导致事实上的搭售现象。
反垄断法列举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具体类型,在不同情况下,自我优待行为可能归属于不同种类的滥用行为,但这些类型化的行为在反垄断法下的分析与规制范式并不相同。例如,在《欧盟运行条约》中,搭售行为的垄断认定只需行为在搭售品市场或者被搭售品市场中造成了“反竞争的排除效果”,从而减少了其他经营者销售替代产品的机会。但《第102 条指南》明确表示了排他性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对上下游市场“有极大可能消灭了有效竞争”以及“对于消费者有损害”。很明显,拒绝交易所达到的竞争损害标准要比搭售行为高。因此,这可能导致存在自我优待的两(多)个行为由于归类不同而受到相异的判断与规制,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混乱。综上,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可以依据搭售行为的范式进行规制,但搭售这一类型并不能覆盖所有的自我优待行为。
(三)差别待遇
自我优待行为也可能构成差别待遇。在《欧盟运行条约》第102 条(c)款中,差别待遇被描述为在同等的交易下对交易相对方设置有差别的交易条件,使得交易相对方处于竞争劣势的行为。因此,《反垄断指南》第17 条第1 款对我国《反垄断法》第17 条第6 款中的“其他交易条件”结合数字市场进行了解释,不仅将该行为解释为价格歧视,还包括非价格歧视,例如设置差异性的标准、规则、算法以及付款条件或付款方式。该解释摆脱了传统价格歧视的藩篱,认识到平台实行非价格歧视行为也会造成反竞争效果[18]。这与美国Roommates.com 案的判决相吻合。该案中,平台经营者对不同性别、性取向和家庭状况的消费者提供了差异化的搜索结果⑱。
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明显地体现了非价格差别待遇的特征。在欧盟对亚马逊自我优待行为的调查中,欧盟委员会意图发现亚马逊是否在选择商家进入“购物盒”(Buy Box)时采用一套选择标准,该标准倾向于亚马逊自营商家或者使用亚马逊物流服务的商家。如果商家被选入Buy Box,就会被推荐至亚马逊Prime 会员,而这对于产品销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随着近年Prime 会员数量的不断增多,会员消费者在Buy Box 中浏览与购买产品的频次也会增加。假设亚马逊偏袒了自营商家或相关联的商家,也能构成在选择标准上的差别待遇行为,导致以上两类之外的商家难以获得足够的客户流量,削弱了其市场竞争力[19]。
当然,差别待遇的涵摄也有不周延之处。首先,一般来说,经营者的认定采取的是“控制权”标准,而非“法人独立人格”标准。因此,假设平台的行为仅优待了平台自营产品,未在第三方经营者之间实施差别待遇,因为平台和自营商家并非“交易对象”,则反映了“交易对象”之间并未被区别对待,由此便难以认定该行为为差别待遇行为。不过,在欧盟竞争执法实践中,有案例以《欧盟运行条约》第102 条为依据,认定在价格与资质上偏好自己的附属生产机构的行为构成差别待遇。但该案未曾提及母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如何定性,也未曾将该种行为归类为差别待遇进行处罚⑲。
尽管美国与欧盟的判例中都发展出了“单一实体”原则,即只要某些企业进行同一经济活动,无论其法人人格是否独立或是否归属于同一投资者,都可以被认定为同一经营者[20]。在我国,由于国有企业对外投资与反垄断问题较为棘手,《反垄断法》是否应该在全局上采用这一原则仍需审慎⑳。再者,差别待遇与建设性拒绝交易行为似乎也难以界分,因为建设性拒绝交易行为可能表现为平台对竞争对手设定更严格的数据获取或者其他交易条件,使得竞争对手难以维持经营。然而,差别待遇和拒绝交易行为的损害理论、认定标准以及救济方式都有所不同,这也许会导致反垄断认定和执行上的混乱。总体而言,平台自我优待行为能够符合差别待遇的特征并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但《反垄断法》项下的差别待遇并不能覆盖所有的自我优待行为。
(四)独立的滥用行为的可能性
虽然超级平台的自我优待行为可能被归类为拒绝交易、搭售以及差别待遇,使其被《反垄断法》第17 条第3 项、第5 项、第6 项所涵摄,但这些涵摄并非完美,且这三种滥用行为类型的判断标准与救济途径也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讨论是否需要如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十次修正案一样,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滥用行为类型进行规制。该法在修订后新设了第19a 条,增加对具有“显著跨市场竞争影响”经营者的认定。如果某一经营者在结构和数据获取上占据极大优势,则属于该条的规制对象。这实际上类似于欧盟《数字市场法》草案对于“守门人”平台的认定。该法还禁止两种“显著跨市场竞争影响”的经营者实施的自我优待行为,但赋予经营者抗辩的权利。这两种行为是:①对自己的产品优先展示;②在设备上排他地预安装平台自己的产品或者以其他方式与平台其他产品整合。因此,对于有跨市场影响力的超级平台来说,德国立法在原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的框架下创立了一套新的体系,包括“自我优待行为”的独立类型化,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几项行为类型。
美国也有类似的尝试。美国众议院反垄断小组委员会主席大卫·西西林(David Cicilline)在2021年6月份提出的《美国创新与选择在线法案》(The American Innovation and Choice Online Act)禁止“涵盖平台”(covered platforms)实施自我优待行为,即“与另一经营者的产品、服务或业务相比,涵盖平台不得给予自己的产品、服务或业务更多的优势”㉑。而在当年10月份,美国参议员艾米·克洛布彻(Amy Klobuchar)和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又提出一项同名法案,也明确禁止涵盖平台实施自我优待行为,即“相对于涵盖平台上的其他商家来说,涵盖平台不公平地优待其自身的产品、服务或者产业,以至于实质上损害了涵盖平台内部市场的竞争”㉒。当然,两个法案中的涵盖平台,是拥有一定数量用户或商业用户,同时达到一定年净销售额或市值的平台经营者,此概念的外延也包含了一些超级平台。尽管这两个法案还未经两院表决通过,并无法确定其通过后,美国执法和司法部门如何适用该法案、是否与反托拉斯法框架相整合,但毫无疑问,美国也在尝试自我优待行为的独立化,因为这种行为在美国国内确实引起了极大的竞争关切。
从我国《反垄断法》的修订历程以及最新颁布的《反垄断法(修正草案)》来观察,我国《反垄断法》对超级平台的自我优待行为的处置并未借鉴德国与美国的立法选择,仅在第22 条补充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以及平台规则等设置障碍,对其他经营者进行不合理限制的,属于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因此,在拒绝交易、搭售和差别待遇条款难以有效规制超级平台的自我优待行为的情况下,适用“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这一兜底条款对该行为进行规制,也许同样可以实现《反垄断法》的立法目标。
三、超级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规制优化
反垄断法在规制超级平台的自我优待行为时,应探讨如何进行个案行为分析,如何依据合理原则分析行为的竞争损害和效率,如何准确判断是否应禁止超级平台自我优待行为,以及如何适用现有或潜在的规制工具。
(一)快速有效的合理原则适用
与往常相比,合理原则在数字市场领域的适用模式可能会发生变化。随着新布兰戴斯学派的兴起,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都倾向于采取更激进的甚至结构主义的方式对待构成“数字市场守门人”的超级平台,不再局限于“芝加哥学派”所倡导的反竞争行为的纯粹经济效益分析[19]。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认为,对于数字市场的反竞争行为而言,需要建立一个“亲竞争”(pro-competition)的规制框架,要求事前设立数字企业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期望在竞争损害发生前将行为扼杀于摇篮之中,同时也注重事后执法的迅速性㉓。
我国数字市场反垄断的态度最近也发生了转变。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包含了制止超级平台实施各种反竞争行为之意[22]。我国对数字平台反竞争行为的具体分析路径需要“脱繁入简”,形成更为迅速且有效的合理原则适用方法,且为事前的反垄断规制服务。因此,需要修正合理原则的适用方式,使执法机关能更为迅速地作出决定,避免采取芝加哥学派所倡导的复杂的经济效益分析模式,这种分析往往会导致自由放任的后果。
合理原则的快速适用有两个层次:一是“快速浏览的合理原则”,指的是对于某些行为而言,可以预设该行为由于竞争损害较大而违法,但给予经营者一定的抗辩权,在抗辩有正当性时再进行行为经济效益分析,如果抗辩不成立,则该行为违法[23]。二是在合理原则适用时采用一种替代复杂经济效益分析的措施。该方法要求行为受到被告抗辩时,原告只需要指出一个对于竞争限制更小的行为但能够实现同样的抗辩目的,就可以认定诉争行为不符合“比例原则”而构成违法。这种措施叫作“较小限制性替代措施测试”,简化了合理原则在适用过程中复杂的成本效益分析,在“美国运通”案中被联邦最高法院予以确认㉔。这两个层次的合理原则适用方法,可供执法部门在规制超级平台的自我优待行为时参考。
不过,在第一层次方法的适用过程中,双边或多边平台对于预设违法行为的抗辩并不复杂,只要例证在某一“边”上具有合理性即可,不需要分别或综合地分析所有“边”上的经济效率[24]。这样可以简化平台经营者抗辩的举证责任,在达到同样执法效果的同时,精简了合理原则的适用。不过,市场总体的结构也值得注意,在经营者具有“多栖性”或者经营者没有跨市场重要影响力的结构中,即便是市场份额很大的平台聚合体实施的自我优待行为,也可能具备一定的正当性,特别是其自营产品具有压倒性的技术优势和质量优势时。
(二)关注横跨多个市场的垄断“杠杆效应”
尽管德国立法识别了具有跨市场重要影响的平台,并阻止其实施各种反竞争行为,但并未说明判定行为违法的具体标准。我们认为,需要强调在垄断“杠杆效应”影响下,行为具有的跨市场的反竞争效应。“杠杆效应”或者“垄断杠杆”是指某一市场中的垄断者将其市场地位传导到相邻或者相关的另一个市场之中。该理论在反垄断实践中的应用源于Carbice Corp.案,布兰戴斯法官在该案中极力抨击捆绑销售行为所造成的杠杆效应㉕[25]。经济学的“提高竞争对手成本”理论认为,垄断者欲达到垄断目的,除了直接消灭竞争对手和提高市场进入壁垒之外,还可以通过增加竞争对手的经营成本以获取垄断力量,而“提高竞争对手成本”的效果可通过控制关键设施、建立技术门槛等方式实现[26]。
超级平台的自我优待行为的确提高了竞争对手的经营成本,实现了对邻近市场的垄断效果。例如“苹果税”案中,苹果公司对非自营商家收取30%的应用内购买服务提成,从而提高了竞争对手在苹果应用商店中的运营成本。由于缺乏应用商店的选择(市场另一巨头谷歌在安卓平台同样采取了此种策略,已被Epic Games 诉至美国加州北区法院)㉖,竞争对手就可能由于经营成本太高而退出应用商店平台,没有被征收提成的苹果自营应用便可以挤占市场,进而形成垄断地位。因此,针对“杠杆效应”的分析,美国《数字化市场竞争调查报告》认为,尽管许多超级平台没有通过“杠杆效应”对相邻市场实现垄断,但产生该效应的行为也会造成竞争损害。因此,“杠杆效应”的损害理论应被重塑,首先应推翻“实际上造成相邻市场的垄断效果”这一判断竞争损害的前提㉗。
欧盟《数字时代竞争政策报告》也指出,自我优待行为能够产生“杠杆效应”,并且认为,虽然自我优待行为是否造成“杠杆效应”仍然需要进行个案分析,但是,当平台具有一定的公共规制与管理作用时,平台自身应当承担一定义务,确保其自我优待行为不会对平台内市场造成长期的排除竞争效果㉘。这与欧盟审查经营者集中的 SIEC(Significant Impediment to Effective Competition,即对有效竞争的重大阻碍)标准测试有类似之处。该测试一改以往关注的企业结构,采用“支配地位”以及赫芬达尔指数(HHI)的方法分析竞争损害的模式,转而关注行为的损害效果。虽然许多产生“杠杆效应”的案例还是应用了“组合式垄断地位”(portfolio dominance)这种结构性的分析思路,但这种方法只是为了分析某企业是否有垄断相邻市场的动机和潜力[27],最终的违法性判定还是取决于行为的损害理论。因此,我国反垄断执法在关注超级平台的自我优待行为及其是否产生“杠杆效应”时,也可以参照以上路径,以期达到《反垄断法》规制自我优待行为的最佳效果。
(三)超级平台的自我优待行为是否适用必需设施原则
必需设施原则似乎也是规制超级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有效工具之一。然而,欧盟谷歌案却否定了谷歌搜索引擎构成“必需设施”,并认为平台构成“必需设施”的认定需要“十分严谨”。由于我国尚无成熟的必需设施原则的适用经验,因此我们仍继续以欧盟法为基础探讨“必需设施”的构成与适用。在欧盟法中,必需设施原则并非反垄断法对于反竞争行为的规制路径,而是因为上游经营者掌控着下游经营者开展经营所必不可少的设施,上游经营者由此具有开放必需设施的特殊义务。这并非反竞争行为的常规救济方式,而是类似于行业管制中对于特定企业施加特定义务的阐释。“必需设施”的适用必须非常严格,因为这会对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与竞争优势造成巨大损害[28]。在Bronner 案中,欧盟法院提出了适用必需设施原则的两个条件:一是如果必需设施持有人拒绝交易,会消灭上下游市场的所有竞争;二是必需设施对于相邻市场经营者的营业是“不可或缺”的㉙。在欧盟谷歌案中,法院否认了谷歌搜索引擎具有“不可或缺”的特征,因此不能适用必需设施原则。
就自我优待行为而言,是采用“必需设施”这一规制模式,还是采用《反垄断法》对拒绝交易、搭售与差别待遇这三种行为的常规规制进路(虽然这些行为的规制标准略有差异),仍然难以抉择。结合学者观点与欧盟TeliaSonera 和Slovak Telekom 两个案件来看,除非自我优待行为产生了与纯粹拒绝交易行为相当的排除、限制竞争效应时,才能够将其置于必需设施原则的外延之内(这也表现为必需设施原则不适用于“含蓄的拒绝交易行为”)㉚。在欧盟谷歌案中,执法机构绕开了“必需设施”的认定。由于自我优待行为会产生严重的杠杆效应,因此执法机构瞄准了该行为的滥用本质及反竞争效果,运用常规的反垄断个案分析模式对谷歌进行规制,但规制效果却与适用必需设施原则时无异,都要求具有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对于交易对象一视同仁㉛。显然,在必需设施原则之外,也可以对自我优待行为进行常规的反垄断规制。然而,采用个案分析方法得到的结果并不具有普适性,或许在另一个案例中由于其他因素,无法证明超级平台的自我优待行为违法。但在必需设施原则的路径下,假如被认定构成“必需设施”,经营者就持续背负着不能实施自我优待行为的义务。在数字市场的背景以及愈发主动的反垄断规制的理念下,是否将超级平台认定为必需设施,以及在无法认定时能否要求经营者对竞争对手一视同仁,值得深思。
数字市场中,平台纵向一体化和“生态系统”现象更为普遍,数据和其他平台资源能够使平台通过“杠杆”大举进入相邻市场,进而通过拒绝接入和自我优待等行为排除竞争对手和掠夺市场力量[29]。如果必需设施原则继续按照欧盟的标准严格适用,则会使该原则只适用于如“二选一”或“平台封禁”等明显的拒绝交易行为。由于自我优待与拒绝交易行为的关系仍存疑问,很难认为其“赤裸裸地”排除了竞争对手。然而,无论是欧盟《数字市场法》、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十次修正案,还是两个美国反垄断法案,都从结构的立场而非平台设施的功能性的角度试图创设一个类似于“必需设施”的概念,即“守门人”或“有跨市场重要影响的经营者”,对于这一类平台施加许多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下的义务,例如防止自我优待、数据互操作与可携带的要求,而不仅仅是禁止拒绝交易的义务,这些义务的范围相对于必需设施原则来说有所扩张。如何理解这两种规制模式之间的关系,是否认为“守门人”平台绕开了“必需设施”的认定,却达到了更好的规制效果,这需要继续深入思考。在现行的判例下,“必需设施”的认定及随后的行为认定仍然较为困难,只有在极度严格的条件下(完全剥夺了竞争者的经营能力等),平台的自我优待行为才能被必需设施原则所规制[30]。
当然,对于必需设施的讨论也有新的进展,许多学者都在探讨数据是否构成“必需设施”,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十次修正案甚至直接认定了数据构成“必需设施”,条件为数据是相邻市场经营者营业所不可或缺的㉜。德国立法考虑到了平台杠杆效应的普遍性,采取措施防止跨市场竞争损害的出现,但并未说明必需设施原则和“守门人”平台规制模式的异同。不过,“必需设施”仍是个案的事后救济机制,其对有反竞争行为的平台施加一定的开放义务。而“守门人”平台则是执法机关事前指定的某些超级平台,其背负着不限于提供竞争对手一定数据互操作性的义务[31],一定程度上能够阻止不合理的自我优待行为的产生。
四、结语
超级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既带来了竞争损害,也会产生经济效益。在竞争损害不可忽视时,反垄断法的介入就具有必要性。不过,界定相关市场和认定市场支配地位仍是判定自我优待行为是否违法的前置条件,本文采用的“超级平台”一词,只是预设了平台在相关市场或者横跨多个市场上具有强大市场力量时,可能被认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在此基础上,如果其自我优待行为具有竞争损害效果,就需要进一步分析该行为是否构成以及构成何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种分析应当结合个案情况进行类型化研究,目前有三种行为类型可供执法机关选择。执法机关还需要采用更快捷的“合理原则”进行判断,关注涉及多个市场的垄断“杠杆效应”,决定是否适用“必需设施”还是“守门人平台”的方式进行规制。在此过程中,仍然需要遵循个案分析原则,结合反垄断法的目标、理念和规范,对行为进行准确的认定,以实现反垄断法对超级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合理规制。
注释:
① 关于“自我优待行为”的界定,主要借鉴Michael A Salinger 研究报告中的观点。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受到广泛热议的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并不仅仅源于平台制定的平台规则,也可能源于平台对自身拥有的其他资源的利用,因此,本文对上述自我优待行为的概念进行了完善。参见 Michael A Salinger,Self-preferencing,The Global Antitrust Institute Report on the Digital Economy 10,p.329 (2020).
② Case AT.39740 Google Search (Shopping),27 June 2017.
③ “超级平台”一词表示平台经济体、多边平台和平台聚合体等概念,这种平台如今已经被预设为在相关市场或者跨市场上具有强大的市场力量。参见陈兵:《因应超级平台对反垄断法规制的挑战》,载《法学》2020年第2期,第104 页.
④ See Subcommittee on Antitrust,Commerci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Investigation of Competition in the Digital Markets,(October 2020),396.
⑤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ntestable and fair markets in the digital sector (Digital Markets Act),COM/2020/842 final.
⑥ Guidance on the Commission's enforcement priorities in applying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to abusive exclusionary conduct by dominant undertakings [2009]OJ C 45/7,paras.19 and 28.
⑦ Case AT.39740 Google Search (Shopping),27 June 2017,paras.341,342,593-600 and 606.
⑧ See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Decision 21-D-11 of June 07,2021 regarding Practices Implemented in the Online Advertising Sector,paras.384-391 and 405-409.
⑨ See Jason Furman,et al.Unlocking Digital Competition,Report of the Digital Competition Expert Panel,(March 2019),para.1.64.
⑩ See Jacques Crémer,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 and Heike Schweitzer,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Final Report,(European Commission Report 20 May 2019),66.
⑪ Case C-418/01 IMS Health GmbH &Co.OHGv.NDC Health GmbH &Co.KG,EU:C:2004:257,paras.27-28.
⑫ 双重边际效应指的是上下游市场经营者分别以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对于商品在产业链中的两次加价行为,而且上下游之间的产品流动并非产出最大化的总体效益。See Joseph Spengler,‘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Antitrust Policy’ 5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47,350-351 (1950).See also,Vertical Merger Guidelines,(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June 2020),2.
⑬ Case AT.39740 Google Search (Shopping),27 June 2017,paras.661-664.
⑭ See OECD,Competition Policy Roundtables:Refusals to Deal,(OECD 2007),DAF/COMP(2007)46,26.
⑮ 这是根据Van Buren 案的判例,重新审理领英采取技术手段限制hiQ Labs 的爬取以及停止爬取通知的行为,是否提高或维持了《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案》(the Computer Fraud and Abuse Act,CFAA)对于特定电脑区域数据获取的权限,由此再判断HiQ Labs 的爬取行为是否违法。这种所谓计算机领域的法律也会对于反垄断法对拒绝交易行为(以及该行为实施到何种程度)判断的正当性产生一定的影响。See hiQ Labs,Inc.v.LinkedIn Corp.,938 F.3d 985 (9th Cir.2019),993-994.See also,LinkedIn Corp.v.hiQ Labs,Inc.,No.19-1116,593 U.S.___ (GVR Order June 14,2021).
⑯ See Authenticom,Inc.v.CDK Global,LLC et al.,874 F.3d 1019 (7th Cir.2017),1021-1023 and 1026.
⑰ 有学者提到,拒绝经营者核心设施的接入也会导致垄断杠杆的传导效果,使经营者同时垄断两个市场。参见李剑:《反垄断法核心设施理论的存在基础——纵向一体化与提高竞争对手成本理论的解读》,载《经济法研究》2008年第7 卷,第84-85 页。
⑱ Fair Housing Council of San Fernando Valleyv.Roommates.com,LLC,521 F.3d 1157 (9th Cir.2008).
⑲ Case AT.39388 German Electricity Wholesale Market,30 January 2009,paras.52 and 53.
⑳ 此处指欧盟若适用单一实体原则,可能将我国所有国有企业认定为一个经营者,提高了国有企业跨境并购的反垄断审查的标准。因此,为了国有企业正常经营的需要,我国《反垄断法》整体上不能采取此原则。不过,我国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此原则,例如规定母子公司的合并并不属于经营者集中的外延范围。See Angela Huyue Zhang,‘The Antitrust Paradox of China,Inc.’ 50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 159,162-164 (2017).
㉑ Sec.2(a)(1) H.R.3816 - American Choice and Innovation Online Act,June 11,2021.
㉒ Sec.2(a)(1) S.2992 - American Innovation and Choice Online Act,October 18,2021.
㉓ See UK Competition and Market Authority,Online Platforms and Digital Advertising Market Study:Final Report,paras.7.22-7.27.
㉔ Ohiov.American Express Co.,138 S.Ct.2274,2284(2018).
㉕ Carbice Corp.v.Patents Development Corp.,283 U.S.27,32 (1931).
㉖ Epic Games,Inc.v.Google LLC et al.Case Number 3:20-cv-05671 from U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North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 (2020).
㉗ See Subcommittee on Antitrust,Commerci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Investigation of Competition in the Digital Markets,(October 2020),396.
㉘ See Jacques Crémer,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 and Heike Schweitzer,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Final Report,(European Commission Report 20 May 2019),66.
㉙ Case C-7/97 Oscar Bronner GmbH &Co.KGvMediaprint Zeitungs- und Zeitschriftenverlag GmbH &Co.KG,Mediaprint Zeitungsvertriebsgesellschaft mbH &Co.KG and Mediaprint Anzeigengesellschaft mbH &Co.KG,EU:C:1998:569,paras.37-41
㉚ Case C-52/09 KonkurrensverketvTeliaSonera Sverige AB,EU:C:2011:83,paras.55-58;Case C-165/19 P Slovak Telekom,a.s.vEuropean Commission,EU:C:2021:239,para.59.
㉛ 例如,欧盟委员会在探讨救济措施时,要求谷歌必须使自己的比较购物服务“在谷歌一般搜索结果界面中的显示与定位顺序由与其竞争性比较购物服务相同的计算流程和方法得出”,这些方法包括“对搜索结果的可见性、结果的触发、排名或图形格式等有影响的所有要素”。See case AT.39740 Google Search (Shopping),27 June 2017,par.700.
㉜ 《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十版,第19 条第2 款第4 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