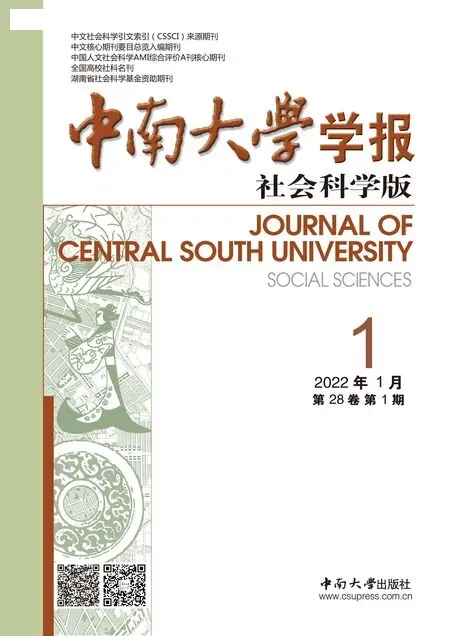传统儒家情论的理路、特质及其当代价值
华军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历史上,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思想启蒙与时代变革都会伴随着人们对情感的不同认知以及相应的价值评判。应该指出的是,作为具体的人生体验与社会历史实践活动,虽然有关情感的特殊性与阶段性的认知与评价彰显了生命的律动与社会历史的演化规律,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向性,但是从全面理解人的情感世界及培育理想人格与社会的角度看,对于情感的认知与评价则不应简单地执一时、一端之见,而应在具体的文化体系中系统了解其一贯特质,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发掘其对构建理想人格与社会的重要影响。
重情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儒家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清代著名学者戴震认为,“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1](159),“合声色臭味之欲,喜怒哀乐之情,而人道备”[1](191)。可见,在戴震眼里,世间王道与人道之备皆需立足于人的情感。对此,今人亦多有反思,如蒙培元先生就认为,“只有情感,才是人的最首要最基本的存在方式”[2](3),“情感是全部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成部分,甚至是儒学理论的出发点”[2](1)。本文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为例,对其情论的基本理路和文化特质进行深入诠释,进而以此为契机,反思当代情感教育中的若干问题。冀图借助传统儒家情感文化之精要,为当代情感教育走出误区、建构理想人格与和谐社会,提供必要的理论借鉴。
一、儒家情论的基本理路
“情”为形声字,从心,青声。作为文字,“情”字出现并不早。从传世文献看,甲骨文、金文和《易经》中皆无“情”字出现。在《尚书》中,“情”字仅出现一例,即《周书·康诰》中的“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3](146),大意是说上天威严,其意不可测知,而民意则可以征见,小民难于安抚。这里的“民情”意为民之实情、实事、实意,这一含义可谓“情”字的本源义,在以后的“情”字使用中乃成为一基础性用法。如《论语》中两见之“情”字,其大意亦为“实情”“实意”,所谓“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4](191),“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4](287)。《孟子》中言“情”亦本实情、实事、实意之意,如“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5](136),“声闻过情,君子耻之”[5](209),“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5](290)等,皆是如此。在郭店竹简以及《礼记》中,“情”字的这一基础性含义则得到了更为明确的体现和肯定。如郭店简《语丛一》云:“人亡能为。”[6](197)《性自命出》又云:“凡人伪为可恶也。”“凡人情为可悦也。”[6](181)《礼记·表记》云:“情欲信,辞欲巧。”[7](734)此皆是在揭示、表彰“情”的真实义。在此基础上,郭店简《性自命出》又言:“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6](181)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情”是善、贵、信的基础,唯实情、实事、实意之情可当此意[8](93)。
由上可见,传统儒家情论的基本理路,大体是基于这两个含义而展开的。“情”字的初始义乃是指实情、实事、实意,表达的是存在的本源性,这一含义在后来“情”字内涵的发展中可谓是一贯的思想基础和价值根基。“情”字发展出来的另一内涵乃指在以上实情、实事、实意基础上的具体情感。对此,我们可从两条诠释路径来进行考察。
一是在性体情用的体用框架下来理解“情”。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9](1457)这段话将人的好恶、喜怒、哀乐之情总归为好恶,以之为“六气”所出;因六气又出于“则天之明,因地之性”,故天地之明性亦为人情之本原。这个说法与郭店简材料亦有相应之处,如郭店简《语丛二》写道,“欲生于性”,“爱生于性”,“喜生于性”,“恶生于性”[6](203−204)。而《性自命出》则云:“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6](179)这里同样是将人情归本于天命之性。此外,《礼记·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7](693)朱熹以为未发是性,已发则是情[10](20)。由此,性为体,情为用,性由情显,二者表里相应,动静相合。《荀子·正名》表之曰:“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11](319)《论衡·本性》再明之曰:“性,生而然者也,在于身而不发。情,接于物而然者也,出形于外。”[12](48)
二是基于存在的立场,以情为思考人之存在的基础、本源,并由此出发思考其内在条理和合理的存在形态。如在《论语·阳货》中,宰我曾对孔子言:“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宰我指出“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4](267−268)。孔子则答以“于女安乎?”“女安则为之”[4](268)。在此,“安”即心安,显为一种情态,为思考行为合理性的基础、本源。同样,孔子还曾言道:“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4](238)好恶无疑是人情,在此则成为孔子思考人的存在的合理性的发端,直至引出孔子“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4](201)的结论。至于《孟子》,则以不忍之情为审视人生之应当的发端。以上皆是就儒学以情感为其思考人之存在及其合理性的基础、本源而言的。在此背景下,所谓“性”即是情理所在,它不能离情而独在。换言之,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人情之外的实体性的性理世界。
历史上,宋明儒曾大力提升性理的地位,突出其价值与意义,相对而言,他们对情感的关注则显不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性理、情感的对立。这固有其具体的思想史发展因由,但也因此导致对人之情感世界的损坏,以致其道德理想亦难以真正落实[8](93−94)。为此,明清之际的学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以致在此间的社会文化中,重情业已逐渐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文化现象。如明代学者李贽曾指出,人之行事,“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13](82)。他认为:“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13](97)可见,李贽在当时反对正统理学形式化的纲常义理的背景下,主张自然舒张人情,勇于展露人的真实情感。李贽的思想对晚明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文学家在大量的文学创作中皆体现了这一艺术追求倾向,如与其大体同时的汤显祖曾言道:“听以李百泉(李贽)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14](1229)又:“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以憺荡人意,欢乐舞蹈,悲壮哀感鬼神风雨鸟兽,摇动草木,洞裂金石。”[14](1050)其代表作《牡丹亭》则可谓是为情作使,呈现出情不知何起、一往情深、至死不渝、其情不可论理而终胜于理的深刻的重情意义。再如明代的文学家冯梦龙亦主张重情,提出情真观,甚至要设立一种“情教”以取代其他宗教。在《情史》卷一《总评》中,冯梦龙言道:“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15](21)至清代学者戴震言“情”则更有卓见。他一面讲“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1](10),一面又言“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1](150)。可见,戴震不主张情、理对立,而是即情言理,力求通情达理,并将其作为理解与调治社会人生的基础,故又言:“古人之学在行事,在通民之欲,体民之情,故学成而民赖以生。”[1](479)他借此批判了宋儒“存理灭欲”“以理抑情”等一系列观念。
传统儒学关于人情的两种诠释路径虽立场不同,却并不必然矛盾。相反,在一定意义上,二者恰可互补,即从把握存在之本源上看,情感可为其理解存在的现实基础;从存在之本质实现上看,性体情用可为其教化架构,由此二者终始相成。概言之,传统儒学言情之大义乃是在实情、实事、实意的基础上论人情百态,并以此为思考人生、寻求合理存在的本源。所谓性理思想亦是由此而出,并以此达成型塑人生之理想。
二、儒家情论的两大特质
在如上两条思考理路的基础上,传统儒学情论对情感的发生、活动、走向以及终极追求等问题形成了整体一贯而又独具特色的认识,呈现出如下两大特质:
其一,儒家情论立足于切己的生存体验。如上所述,传统儒学言情在于“真”。此“真”的基础乃是落实于充满生生之意的切己之体验上而言的。所谓“生生”,指动而不已、神而无方的存在活动及存在状态。《易传·系辞上》有言,“生生之谓易”,“日新之谓盛德”[16](366)。所谓“生生”“日新”皆是就“易”道而言,而大易之道乃备于天地万物,“天地之大德曰生”[16](388)之大生与“曲成万物而不遗”之广生相应,故充满生机[16](364)。此生生之意,就其实存而言,又以生气流行而论之。如《礼记·乐记》云:“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7](504)《礼记·月令》又云:“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7](238)这便是以天地之气的升降变化而言万物生息的。此外,《礼记》还以阴阳、寒暖、刚柔、正邪、顺逆、四季、仁义等来表示生气流行的具体性质。具体到人自身,则《论语·季氏》有云:“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4](250−251)这便是依人的血气变化而论人生气流行之道。对此,传统中医学有着更为丰富的理论阐释。依传统中医学理论来看,“精气津液血脉,无非气之所化也”[17](40),“气……周流一身,循环无端,出入升降,继而有常”[18](59),“先天之气在肾,是父母之所赋;后天之气在脾,是水谷之所化。先天之气为气之体,体主静,故子在胞中,赖母息以养生气,则神藏而机静;后天之气为气之用,用主动,故育形之后,资水谷以奉生身,则神发而运动。天人合德,二气互用,故后天之气得先天之气,则生生而不息;先天之气得后天之气,始化化而不穷也”[19](335)。总之,传统儒学所论的人情世界乃是一个生气流行的世界,灌注着满满的生生之意。
所谓“切己”,乃指自身真实体验,亦即自觉。儒家很看重人“切己”的存在,并以此为一切理解认识和价值抉择的起点和基础。这其中的一个经典范例便是“父子相隐”。《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4](197)孔子的“父子相隐”意指父子相互不称扬彼此的过失,而父子之所以要相隐,显然是出于人自然的切己之情的,父子相隐则是此切己之情的一种特殊表达。传统儒学对此可谓体悟良深。正如皇侃在《论语义疏》中所云:“父子天性,率由自然至情,宜应相隐,若隐惜则自不为非,故云‘直在其中矣’;若不知相隐,则人伦之义尽矣。”[20](183−184)当然,孔子所谓“直在其中矣”的深刻意义绝不止于“父子相隐”这一特殊表达,更在于提示人自然具有的基本而普遍的情感事实,以及基于此的真情流露。传统儒学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文立场来阐发它的价值理念、理想人格与社会建构的。故《论语·雍也》有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93)而《孟子·离娄上》则讲道:“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5](180)
有鉴于此,尽管传统儒学关于人情的理解保有其外在观照的一维,不乏一些分析与归纳性的认识,然而此外在观照下的情感终非一无感怀的纯粹对待之物、一独立外在的客观之物。它必经由自觉而归于生生之人自身上方为真。究其根本,传统儒学所言之情乃是落实在人自身真实的生存体验之上的。换言之,其所言之情皆为充满生生之意的切己之情。此充满生生之意的切己之情才是儒家言情的源头活水,即便儒家所言之道德亦是本此。如《孟子·公孙丑上》中言:“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5](85−86)所谓“怵惕恻隐之心”,即为“不忍人之心”,“怵”者,恐惧;“惕”者,惊骇;“恻”者,伤也;“隐”者,痛也。孟子以为,此乃人见孺子入井之时的切己之情、当下直觉。后人对此广为诠释。如大程子有言:“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21](15)“人之一肢病,不知痛痒,谓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犹是也。”[21](366)在此,仁者的基础就是有生气、知痛痒、有觉情者。另如南宋杨万里在《孟子论》中所言:“隐也者,若有所痛也。恻也者,若有所悯也。痛则觉,觉则悯,悯则爱。人之手足不知痛痒者,则谓之不仁。盖方其不知痛痒也,搔之而不醒,抶之而不恤,彼其心非不爱四体也,无痛痒之可觉也。至于无疾之人,误而拔一发则百骸为之震,何也?觉其痛也,觉一发之痛则爱心生,不觉四体之痛则爱心息。”[22](117)杨氏此言亦是就具有生气的切肤之痛、人生觉情而论道德之仁的基础。总之,儒家所言情感世界皆归本于充满生生之意的存在者的切身体验,绝非一单纯静态的客观之物。
其二,传统儒学情论重在生生、切己之意下寻求“共情”与“通情”的统一,并由此构成儒家言情的超越性基础。
如上所言,生生之意是天道化生万物之功于具体生命上的流行显现,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16](366)。孔子曾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4](267)《礼记·中庸》则言:“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7](710)此生生之意的历程亦可以表述为元、亨、利、贞四字。古人曾把元、亨、利、贞解为春、夏、秋、冬。天地自然有此四时变化,才能生物。与四时之特征相应,元、亨、利、贞又分别意味着开始、发展、成熟、收藏,而后贞下又起元[23](89)。儒家所言之情即由此生生之意灌注。在此背景下,天地万物皆秉天道阴阳生生之意而化生无穷,此为儒家之共情义的基本背景。《礼记·中庸》又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7](693−694)在此,《中庸》表达了一种天地万物以情显性而达于天命的思想。所谓率性之道便是喜、怒、哀、乐发而中节的中和之道。就此而言,天地万物可谓是一体共情的存在。《荀子·正名》亦云:“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11](319)此外,《春秋繁露·如天之为》又云:“阴阳之气,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为好恶喜怒,在天者为暖清寒暑……夫喜怒哀乐之止动也,此天之所为人性命者。临其时而欲发其应,亦天应也,与暖清寒暑之至其时而欲发无异……人有喜怒哀乐,犹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喜怒哀乐之至其时而欲发也,若春夏秋冬之至其时而欲出也,皆天气之然也。”[24](97−98)《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则明确以喜、怒、哀、乐与春、夏、秋、冬四时相配,所谓“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24](64)。而《论衡·变虚》则言:“天人同道,好恶不殊。”[12](69)此皆发明天地万物共情之意。
在此共情基础上,儒家言情又有了进一步的同感共振之通情义。如《论语·述而》中言:“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4](97)《礼记·檀弓上》云:“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7](60)此皆表达了古人体贴人情并与之同感共振之意。至孟子则以“不忍之心”兼人、禽而共表之;宋明学者则可谓兼人、物而共体之。如北宋周敦颐在《通书》中言:“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25](71)其人窗前草不除,以之为 “与自家意思一般”,且云“观天地生物气象”[25](139)。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则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26](62)这里的“民胞物与”可谓彰显了人、物通情之高明见地。另如程颢倡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时,亦非常注重兼人、物之生生之意而共体之,故其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21](15)。据史书记载,程颢从政期间,便将“视民如伤”视为座右铭,常对照自查,并自叹“常愧对此四字”[21](429)。其又言“观鸡雏”可以识仁、“切脉最可体仁”[21](59)、“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21](120),等等。与周敦颐一样,程颢亦是窗前茂草覆砌而不事修剪,意在“常见造物生意”,又养鱼数尾以“观万物自得意”[27](669)。清代的爱新觉罗·永瑆为此曾赋联云:“不除庭草留生意,爱养盆鱼识化机。”[28](223)正因程颢如此同感通情,方有“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21](482)之名句咏出。南宋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在其《立春偶成》中亦有“春到人间草木知”“便觉眼前生意满”[29](528−529)之佳句。至于朱子则云:“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请试详之。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所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30](3279)明代的王阳明在其《传习录》中亦言:“天地生意,花草一般。”[31](26)由此可见,至宋明儒处,儒家之情已经是在共情的基础上演化为人、物同感共振的一体通情之义,而这也同时为儒家情感的超越性奠定了坚实的义理基础。显然,由共情而求通情乃是儒家言情的总趋向,正如《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所言:“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32](5)反之则多所贬抑,如《盐铁论·散不足》云:“古者,邻有丧,舂不相杵,巷不歌谣。孔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与小坐而责辨,歌舞俳优,连笑伎戏。”[33](355)
概言之,传统儒学眼里的世界乃是一个基于深刻的天人一体之文化诠释理念上的充满生生之意的同感共振的情感世界。在此情感世界中,人己、物我由共情而通情,由通情而同情。传统儒学所阐扬的恻隐之心、忠恕、絜矩之道无不贯穿着这一基本认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在《大学问》中言道:“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31](798−799)
三、儒家情论的当代价值
传统儒学言情的两项文化特质,对于我们反思当代情感教育中的问题,以及发掘“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价值理念源泉,皆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一)对当代情感教育的价值
首先,在当代情感教育中,情感常常被作为一外在于己的客观之物而成为人们分析的对象,人们在此对象性分析中逐渐形成有关情感的知识系统。譬如一些学者从心理学、现象学视角出发来审视人的情感,力图探究导致情感发生的内外因素、情感自身的结构、情感的演化条件、情感的演化路径以及展现出的种种形态等问题。如研究“同感”问题的心理学专家巴特森(D.Batson)教授曾区分了八种不同类型的同感现象:①了解他人的内心状态(想法与感受),此为“认知性同感”。②采取与他人的姿态或表情相匹配的姿态、表情,以回应之。此为 “动作模仿”(motor mimicry)或 “模拟”(imitation)。③感受到他人的感受。④里普斯(T.Lips)审美意义上的设身处地。⑤想象他人会如何感想(imagineother perspective)。⑥设想自己在他人位置上会如何感想(imagine-self perspective)。⑦看到他人受苦,自己也感受到痛苦。这种痛苦感受不是针对他人,而是他人的痛苦状态引起自己的痛苦感受。⑧为受苦者的感受(feeling for another person who is suffering),这是一种他人取向(otheroriented)的感受,是一种关心他人痛苦的慈悲(compassion)、同情或同感式关爱(empathic concern)[34](3−16)。这些研究以揭示人的情感世界为目的,其依托经验现象条件和理性分析所建构起来的知识系统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可重复性,其在实践操作上则具有模式化与规范化等特点,从而在根本上展现出一种确定性。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以对象性分析方式顺着时间与空间维度来对情感世界进行追溯性考察的做法,对于把握人的情感世界而言既是基础的,也是必要的。其一,它是立足于人的实然的情感世界来展开的,其所面对的皆是人现实的情感表现、情感活动。其二,这种考察是以对象性分析方式来进行的,即人的情感世界是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呈现出来的,研究者是在此之外的一个存在,他并不现实拥有研究对象本身,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悬隔。但这是人们在拥有自我意识、觉悟自身之后所形成的一种人文分化。所谓对象性认知,恰是在此人文分化下人们了解世界的最一般的认知方式。其三,人们正是在此基础上,依托理性建立起关于情感世界的一系列具有真理确定性的理论、理性实践和技术知识,以回应有关情感世界“是什么”与“怎么做”等问题。
以这一研究取向和由此建构的知识系统来展开情感教育在现当代可谓十分普遍。它固然为人们了解情感世界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然而其极端的发展亦酝酿了深刻的思想危机。
其一,这一研究乃是基于主客二元对立的模式来进行的。由此形成的情感知识所表达的乃是关于情感世界的一种客观确定性。它固然为认识人的情感世界奠定了一定的具有确定性的知识基础,但由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对象性的悬隔,因而研究者并不现实拥有研究对象,以致由此建立的有关知识并不与研究者本身形成内在关联。换言之,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并没有切己的感受。与此同时,这一基于二元对立模式下的研究对研究对象的了解是在特定的有限条件下的静态观照中进行的,故其视域下的情感世界体现为一具体时空中依托特定条件的静态的构成性存在,难以显明情感世界本身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创生之义。而脱离了生生切己之义,则有关情感世界的知识建构,恐仅止于一种外己的无关乎内心生动之情实的有限而客观的情感知识。至于奠基于此的情感教育,则因其执于对情感世界进行对象性分析和知识化建构,沉溺于对有限情感现象得以形成的内外条件进行解析,结果恰恰忽视甚至遗弃了情感世界本身。如此一来,人的情感世界便成为一种特定因缘条件下的具有普遍规定性的聚合之物而失去了本身的生气、自我的意识。在此背景下的情感教育则容易发展成一种流于表面的强制化灌输行为,难以真正拨动人心。这也恰恰是传统儒学以生生切己来言情的当代启示意义所在,即不应脱离生生之切己的立场而言情,否则其所建立的情感知识极易流于一种不切实际的理论抽象,其间的义理正似大程子与王安石所言的“入塔寻相轮”与“对塔说相轮”之意。大程子以为察物当入乎其内、玩索寻味以致自得,方有真情趣,方是真了解。反之,仅是外在观照,则总归不得体贴自家的生气、心底的情实。在此理解背景下的情感教育首要在于拥有真感受,即切己自觉、动乎人心。由此出发的情感教育因其本于生生之意、切入人心,故而真实可信、感人至深。此可谓情感教育得以发挥作用之前提,否则便可能流于空洞乏味的说教。
其二,这一基于二元对立模式下的情感研究乃是源于对经验现象进行追溯性的理性分析,由此所形成的情感认识止于经验现象条件,因而难以达成有关情感世界的本质性认知,其自身更不能导出一种具有实存基础的价值意义上的本然。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沉思录》(Meditations Sacrae)中曾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但更重要的是运用知识的技能”的观点。然而,如果我们深入来看这句话就会发现,所谓“运用知识的技能”亦可谓是一种“知识”。如果从价值实现的层面看,在二元对立模式下所形成的知识与运用知识的技能因与研究者悬隔,故二者皆存在一个价值指向的问题,这是其本身所无法解决而有待研究者赋予的问题。因此,在此语境下,对于研究者而言,无论是“知识”,还是“运用知识的技能”,皆可谓是一种为了实现某种功利目的的工具性存在。以之为参照,与之相关的现代情感知识与运用此知识的技能亦无独立的自身价值可言,极易为外在研究者的价值欲求所左右而成为一种具有功利性的外在价值内化的工具。在此背景下的情感教育亦可谓基于价值内化的情感工具化历程。由此,人的情感世界便成为缺乏自我意志而任人打扮的工具性存在,再无自身的尊严、独立、超越可言。这亦可谓是当代社会工具理性泛滥的表象之一。在此潮流中,人的情感世界一方面被动地成为各种价值利用的工具,另一方面又主动地以“情感出租”的形式来出卖自身,以致情感成为现实人生中至贱而又至贵的矛盾存在,深刻凸显了人生的困顿。
与之不同而又深具启示意义的是,传统儒学以生生之切己言情蕴含着本我的具有超越意义的价值实现指向。当孔子讲“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孟子言“心悦理义”之时,即已点明传统儒学的情感世界内含着明确的超越性的道德指向,正所谓“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明代的王阳明曾言:“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31](14)又言:“万化根源总在心。”[31](653)他以为心体“众理具而万事出”[31](13)。由此可见,传统儒学中的情感世界有着本我自觉的道德超越义。由此出发,人的情感实践便有着明确的自我实现指向。传统儒学言情的这一文化特质对于推动当代情感教育前提的建立、消解当代工具理性对于情感世界的任意装扮、促成情感教育之目标的落实皆可谓意义深远。
其次,今日之情感教育多强调人的同感、同情的充分展现,但是在阐发此同感、同情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在其中发现一种明显的个体主义的理论诠释背景,即阐发者往往以个体自我为中心来讨论同感、同情的发生与构成,进而形成“我如何知他者之心”“我为何需要理解他者之心(利他还是利己)”“我理解他者之心的价值何在”等有关同感同情之发生、构成与价值等一系列问题[35](116)。由此出发,个体自我便成为思考与发掘同感及同情之发生、构成与价值的背景与基点。顺此以往,同情心的发挥(即便是客观利他之举)事实上也就变相地成为个体自我的需要与价值实现。这一理解本身即隐喻了一种个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即自我中心论。在此基础上,其内在地也就隐含着利益的索求或交换(即便它是出于一种个体信仰)。前引心理学家巴特森先生亦认为,在西方思想中,对同感现象的思考背后皆预设了个体主义的自我观[34](3−4)。而陈立胜先生则认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同感理论的批评已深刻揭示了这种个体主义的理论预设。陈先生甚至认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共在”概念的理解亦存在着相应的“偏狭”,即“特指此在之间的生存论的关联,而非此在的存在者并未包含在内,……因此,包括动物在内的一切非此在的存在者就只能被视为‘用具’而归属于‘无世界者’的范畴”[36](24−25)。由此可见,当代情感教育中,个体主义的理论预设的出现当是渊源有自的。这一教育取向虽然体现了对个体情感世界的深切关注,但同时也蕴含着以下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基于个体自我需要和实现的同感与同情虽欲实现与他者的相通,但由于是以个体自我为本位的,故他者在此相通中虽或受益,但实是一工具性存在,而非一本我存在。因此,二者之间仍是一间隔的存在样态,而非真正的相通,这亦是一些歧义、矛盾、冲突得以产生的原因。其二,基于个体自我需要和实现基础上的同感与同情,如展现为一种因关心他人痛苦而忘我的全身心的投入与奉献,则其所依存的往往是一种外在的超越根据,例如因信仰上帝、期望得到终极拯救而力求践行现实的同感与同情。在此,个体自我反而是一背负原罪的被拯救对象,其同感、同情的实现依然是一工具性的实现。以上两方面问题的揭示,皆在说明当代情感教育中个体主义的理论诠释背景的特性与局限。
与之不同的是,当儒家在共情的基础上论己与人、人与物同感共振的一体通情之义时,无不彰显着其天人一体的生存理解背景。在此背景下,人与万物可谓是一体共在,同感共振,通情共处。而所谓“通情”者在本质上更彰显为“觉”,这一“觉”的经历亦为“见独”的历程,是个体生命妙合于道的体现。因此,觉而使生命浑然中处于天地之间而生机无时无处不在、天地之心无时无处不显。在此过程中,个体自我可谓是一个自由与责任相统一的生命体,一个开放的具有通情的独在。在此基础上的“通情”而“同情”不仅是自我本质的表达,更是天地之心的展露,由此人己、物我相通而自成。总之,儒家因共情而言通情之义,乃是将个体生命置于天人一体之生存理解背景下进行诠释。由此,个体生命之情获得了超越性的存在根据和价值实现指向。在“通情”而“同情”的情感进程中,人己、物我不再是一种间隔的冷漠状态,更不是一种别有用心的工具利用关系,而是生机流行、一气贯通的。儒家这一言情义对于修正当代中国情感教育中“个体主义”极端发展的问题无疑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
儒家因共情而言通情之义,能为当代中国提出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文化价值理念提供重要的思想支撑。众所周知,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而现实世界中,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制度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尽管存在着多向度的竞争,然而已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存在状态。如何在此竞争而又交互并存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无疑是一个紧迫而又具前瞻性的问题。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为此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价值理念。2011年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就曾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一文化价值理念的理论核心在于克服资本与人文的对立,寻求由以资本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包容性发展。它既是对现代文明发展的深刻反省,亦表现为人类社会一种新的发展理念。所谓“包容性发展”内含两个原则的统一,即个体差异性原则与可沟通性原则的统一。所谓个体差异性原则意指不同国家与不同民族在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制度建设和发展形式上的差异皆有其自洽性,肯定此差异性乃是寻求交往合作的前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以及由此带来的霸权意识。所谓可沟通性原则乃指在个体差异性原则的基础上,在面对共同关切时,寻求不同国家与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依存、交流互鉴、合作共赢。它所要规避乃至抛弃的则是基于个体本位的各种恶性竞争与霸权思维。
当代中国之所以能够提出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具有前瞻性的文化价值理念,与中华文明密切相关,传统儒学因共情而言通情之义的通情特质亦对此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众所周知,中华文明一贯倡导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和而不同的处世观以及生生不已的发展观。这些观念用中国哲学的话语来讲可谓系统表达了生存三个层面的内容:一者天地之大德曰生;二者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三者民胞物与。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文化价值理念的思想资源。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思想观念又皆灌注于传统儒学的通情特质之中,并由此获得了集中表达。如前所述,传统儒学的通情特质即建立在天人一体的共情基础之上。它在肯定存在个体差异性的同时,又深刻发掘了存在者通而不同、一体共在的通情意识。在此文化实践中,每一存在者的价值实现皆是在个性化与开放化相统一的文化情境下达成的,而这也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文化价值理念的精神所在。唯此,今日之国人才能在漫天批评与挑战中在保有文化自信的同时放眼世界,才能在疫情来临时克己奉公、守望相助,才能在矛盾丛生、分歧迭起时求同存异、融合共生。
综上所述,传统儒学言情具有两点文化特质:一是归本于充满生生之意的生存主体的切身体验;二是在天人一体的文化诠释背景下因共情而通情,由通情而同情。结合时代精神、合理借鉴儒家言情的这两项文化特质,将有助于克服当代情感教育中过度知识化、结构化、工具化以及个体自我化等极端做法,也有助于发掘和建设当代国人生意盎然而又切己自觉的情感生活,以及因共情而通情的同呼吸、共命运、和谐共存的生存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