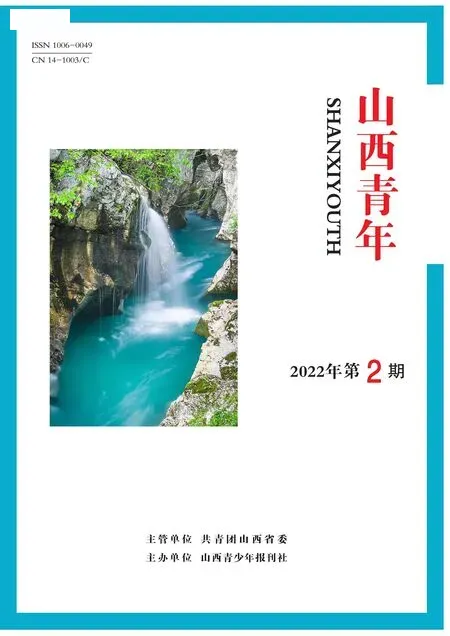探析苏轼词宏大的空间气象
桑 婧
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由此可见,宋词发展到苏轼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仅扩大了词的创作题材范围,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也开拓了词境,同时对词的表现手法也有所变革,笔者认为,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其词作中体现出来的开阔宏大的空间气象,使其作品体现出一种与众不同、开拓丰盈的阔大感。
王兆鹏先生曾总结“东坡范式”相对于“花间范式”之“变”,凡四端:其一为主体意识的强化,即“词的抒情主人公由‘共我’向‘自我’的转变”;其二云感事性的加强,即“由普泛化的抒情向具体化的纪实的转变”;其三乃力度美的高扬,即“词的审美理想由女性化的柔婉美向男性化的力度美的转变”;其四则是音乐性的突破,即“词从附属于音乐向独立于音乐的转变”。[1]笔者认为,王兆鹏先生所提出的第一点和第三点恰恰是形成苏词宏大空间气象的关节点:主体意识的加强,使苏轼与众不同的胸襟抱负与词作混融一体;而高扬的力度美,与其独特精神气质相结合,使其词气势磅礴。
一、主体意识与哲人之思所体现的空间气象
曾有学者对苏轼词中第一人称的运用进行过统计:苏词中第一人称的运用极为广泛,出现次数频繁,即使有的词作并未以第一人称进行表述,也显出了作者极强的主体意识,这更能从侧面印证了其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创作个性,一改之前词人所习惯使用的“代言体”,所以苏轼的词作能够表达其纯真的胸襟见识与情感兴趣。
作者独特主体性思想的打入使词作被赋予一层更加真实且旷达超脱的意味,试看苏轼作于乌台诗案之前的一首作品:
《鹊桥仙· 七夕送陈令举》
缑山仙子,高情云渺,不学痴牛呆女。凤箫声断月明中,举手谢、时人欲去。
客槎曾犯,银河波浪,尚带天风海雨。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
词的题序中虽标明七夕二字,但并非吟咏爱情主题,而是以送别友人为主旨,借缑山仙子王子乔的故事称颂超凡脱俗,飘逸放旷的情怀,通过这种描写来开解友人的离思别苦。[2]上片开篇三句,用高远豁达的缑山仙子王子乔之典故,与被情爱所困而凄凄切切的牛郎织女之典故两相对比,形成时间与空间的反差,营造出一种特别的说服力和开解的效果,词人与友人都是男儿身,相比于和临别的男女一样哭哭啼啼,王子乔般的飘逸心态才更应该是他们所选择的态度,一改之前离别题材作品愁苦凄凉的阴柔基调。
凤箫声止,离人当别。词至下片,描写与朋友泛舟送别的场景,“相逢一醉是前缘”暗示了与陈令举的友情对词人来说意义非凡,待到风雨停歇之后,也不知道会漂泊到什么地方,苏轼在这里并未传达“功成身退醉万场”的豪情壮志,而是含蓄表达了自己对于人生的真切思考,词的意境阔大渺远,空间上的无限延伸与思绪的无涯发散将其哲人之思的面纱慢慢揭开,其词宏大的空间气象也崭露头角。
如果说此时苏轼作品中的哲人之思与主体意识体现的并不是十分明显的话,那么在其经历乌台诗案之后的词作,则更能体现其深刻的人生体验与思考,这一特质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试看经历乌台诗案后,贬谪黄州所作《临江仙》一词:
《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首词以夜饮醉归为由,即兴抒怀,展现了作者谪居黄州时期退避社会,解脱出世的旷达心境。醉而复醒,醒而复醉,继而归家,面对已经熟睡且鼾声如雷,如何叫门都不应的家童,苏轼只好拄杖倚门听江声,此时一个胸襟旷达、遗世独立的苏轼形象仿佛出现在我们面前,以动衬静,以有声衬无声,通过家童鼻息如雷和作者谛听江声,衬托出夜阑人静的寂静,从而为下片历尽宦海沉浮的词人在酒酣之后对人生做出深刻反思做好了铺垫。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看似突兀但却又充满哲理意味的一句话是全词的点睛之笔,化用庄子“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一语,[2]以透彻领悟的哲理思辨,发出了对人生宇宙的质疑和无所归依的悲叹,眼前的江景,并不是客观之景,而是词人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契合的产物,心与景会,神与物游,从而发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心声,韵味深长的一句表达了作者将要把自己有限的生命融化在无限的大自然之中,在否弃了一切外在不合理的价值束缚之后,本真的心灵得以呈现,悲欢离合在人间不断反复上演,作者对人生生命进行深刻的反思,以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实现了精神家园的构建,从而也找到了精神的最终归宿。
这首词作中作者的思想高度得到了升华与提升,已经上升到对整个人类精神世界的反思与关照;已经触及如何面对人生失意,以及如何看待命运不公的终极人文关怀,从而使词作的文本空间无限扩大,具有了包容天地上下宇宙四方的恢弘空间格局。纵观全词诗人的活动范围仅仅局限于自家门前这一极为有限的空间,但作者却摆脱了表层物象空间的束缚,而是以其主体意识与哲人之思,在深层思想内涵层面赋予词作宏大的空间气象,实现了深层内涵对表层空间的冲破,达到了一种张力美。
同样,《鹧鸪天· 林断山明竹隐墙》一词作于作者被贬黄州期间的最后一个夏天: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
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刻画了作者平淡的谪居生活及内心感受,开头短短两句词中描写出林、山、竹、墙、蝉、草、池塘七种景物,但完全是一种杂乱枯萎的景象,生机全无,大抵是诗人被贬之后,心情苦闷郁郁不得志的真实写照。[2]接下来两句的白鸟与红蕖则翻空出奇、清新淡雅,但作者并不是单纯写景,而是通过景物的远与近,动与静相重叠,色彩的鲜明与黯淡相辉映,在不脱离现实层面具体客观事物的特性基础上,实现了各种意象与作者主观意绪的融合,通过这种具体的融合来获得空间深度,形成空间气象。
作者本人出现在词的下片中,夕阳西下,拄杖漫步,回忆起昨夜的一场疏雨,给世间又带来了几分萧凉,“殷勤”一词寄寓了诗人内心的无限感慨,精神空间以物质空间为依托,物质空间同时为精神空间提供归宿,二者共同构成了词中深远的空间气象。
叶嘉莹先生曾指出:“苏词之最值得人注意的一点特色,就是其气象之博大开阔,善写高远之景色,而充满感发之力量。”叶先生这一中肯评价,恰恰指出了苏轼词作中主体意识的蓬勃觉醒,哲人之思的深刻表露,使其词作展现出恢弘阔大的空间气象。
二、豪迈旷达的精神气质所揭示的空间气象
如果说苏轼词中的主体意识与哲人之思是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造成的,那么其“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豪迈旷达的精神气质则是其一以贯之的显著特征。苏轼将自己广阔胸怀中的豪情毫不吝啬的书之于笔,“以己观物,则物皆著我之色彩”,使作品中充溢着阳刚之气与豪情。
在《念奴娇· 赤壁怀古》一词中,苏轼透过广阔的时空背景,为我们展现了乱世英雄的壮志与豪情,营造了极为壮大的空间气象:
《念奴娇· 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苏轼面对“人道是”的赤壁山水与江间景色,通过对三国时期功业卓著的周瑜的凭吊,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怀才不遇,尽管政治上失意,但仍未对生活失去信心的豪迈之情。开篇以宏大的气势起笔,描写壮观的景象,从而联想到三国时期著名的赤壁之战,从“千古风流人物”到“一时多少豪杰”,再到“遥想公瑾当年”,作者的刻画描写范围不断缩小,最终聚焦定格在周瑜身上。[3]作者从周瑜的年轻有为,联想到了自己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但他并没有沉溺于个人世界的痛苦无法自拔,而是把周瑜和自己都放到整个历史洪流之中,从整个人类的发展规律与普遍命运来进行对比,两者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思绪及此,苏轼的精神获得了自由,实现了生命的超脱飞扬,早生华发人生如梦的悲剧感慨在樽酒酹江月的豪放情怀中得到了消解。正所谓现实世界可能荆棘丛生,但精神家园却是永远的乐土。词人随物赋形,从宏阔的自然江山景色,联想到三国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从对乱世英雄的慨叹到对个人早生华发,人生如梦的感慨,将所有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消融在与月共饮的酒中,没有对他人功成名就的过分歆羡,也没有对自己郁郁不得志的过分失意,而是以酒入豪肠的旷达,人生如梦的洒脱,营造了一种超越时空的、阔达的空间气象。
再试看这一首苏轼被贬黄州期间,从沙湖归来途中遇到下雨,有感而发的笑对风雨、笑傲人生的豪迈之情: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词之开篇一方面渲染出风急雨骤,穿林打叶的恶劣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又以“莫听”“何妨”表明自己不受外物影响,不为外物所动的特点,看似是词人对雨中前行道路选择的思考,实则是词人人生态度的写照。他把人生中的坎坷不平,沉浮际遇比喻成风雨,均能淡然处之,不受其影响。即使是竹杖和芒鞋,也丝毫不逊色于别人的高头大马,作者笑对风雨,笑傲人生的豪迈之情跃然纸上,溢于言表。这种与众不同的旷达超脱的胸襟,展现了词人独到的人生感悟,寄寓着其超凡脱俗的人生理想。
与上片疾风骤雨相对应,下片写雨过天晴的景象。词人任性自然的态度再一次展现出来:人生与此次遇雨的经历一样,终将雨过天晴,看到光明。回首望了一眼适才走过的风雨潇潇路,同这刚刚放晴的天气一样,无风无雨,一路晴朗。词人从中顿悟出这样的人生哲理:既然自然界风雨无常,那么社会人生自然也不会一帆风顺,[3]无须过多计较名利得失,一位超然物外、乐观旷达的老者形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苏轼正是通过如此豪迈旷达的精神气质,挣脱了时间与空间的束缚,扩大了词作的文本空间,并呈现出豪放旷达的空间气象。
学界认为最能体现苏轼豪放旷达词风的作品,当属在密州创作的被称为“变体”的《江城子· 密州出猎》:
《江城子· 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上片开篇词人自称“老夫”,这一称谓实际上是词人对自己颠沛流离,流年失所的概括。虽年事不高,但阅历极为丰富,看遍人间沧桑,但即使是这样,词人在郊外打猎时仍像少年英雄一样意气风发。通过对扩大现实空间的描写,使我们感受到了词人心境的辽远与阔大,但文本空间宏大气象的形成并不是基于此,同《念奴娇· 赤壁怀古》一样,作者聚焦于单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即“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自我。[3]
恰恰是郊猎场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英姿飒爽的自我形象,赋予了文本一种豪放旷达的气象,这样阔达的气象并非仅仅是宏伟的郊猎场所建构起来的,更多的是为苏轼阳刚豪迈的气质风神所渲染。纵观全词,从出猎场景的描写,到酣畅娱乐的豪情,到借情抒发胸臆,继而表现自己的一腔热血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这正是一代家国脊梁的写照。苏轼以主观的方式在文本的空间里随物赋形,从而为我们呈现出宏远阔大的空间气象。
通过以上的分析论述,我们不难发现苏轼正是通过具有主观主体意识的哲人之思与自己豪放旷达的独特精神气质进行创作,二者交相辉映,共同熔铸出苏词中宏大的空间气象,这样的空间气象已经超脱了具体物象描写的束缚,不再局限于现实的空间,而是在词人的精神空间中得以释放。归根结底,这样的气象依然源于苏轼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对生活失去信心的独特精神气质,实现深层内涵对表层空间的突破,赋予词作以大格局、大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