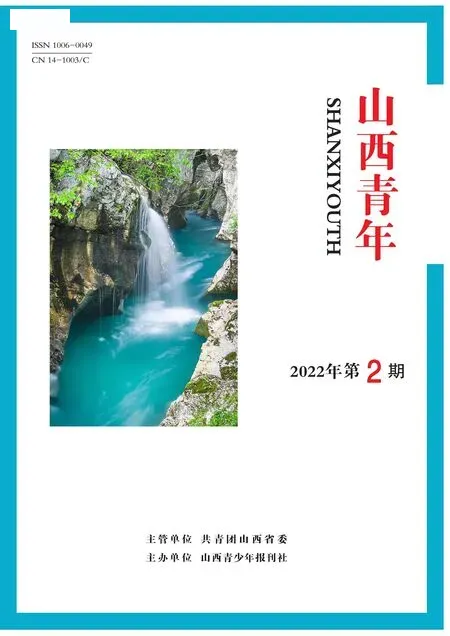旧词新用之名词动用探赜
陈 鑫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2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及新生事物的出现,不少古已有之的词现在产生了新的用法,名词动用是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一种。前人对名词动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词类活用”上,包括词类活用的特点、词类活用的条件等,尤以陈承泽《国文法草创》为代表,对词类活用的类别进行了划分,并区分本用与活用,往后的学者亦沿此路径进行研究,偏重以古代汉语为研究对象,对现代汉语中新生例子关注较少,亦缺乏崭新的理论和视角。现代汉语中出现了很多新例:如“鸡娃”“娃不鸡不成器”“你微信我”“他醋了”“雷柏-无线你的生活”“知乎一下”“今日宜杨枝甘露”“一点都不硬广”等等。沈家煊先生在《汉语里的名词和动词》中提出,由于隐喻的单向性,即用本体隐喻理解动作、活动,动词名用是将抽象的活动看作具体的实体,是较容易的,数目较多的,相反,名词动用是不容易的。据王冬梅统计,现代汉语里动词名化是名词动化的57倍,[1]但在旧词新用中,能看到不少名词动用的例子。名词动用至少战国已有,[2]虽然数量远比不上动词名用,却一直在新词语的构造中“建言献策”,时至今日,仍未消退。
对旧词新用中的名词动化现象进行讨论,分析其表达式建构和理解这两方面所涉及的语义过程,以期对名词动化的深层机理有所揭示,对语言发展、词汇变化有更深的理解,为语法化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材料。
一、名词动用的语义基础
名词动用后,语义上由静态义转化为动态义,这样的意义变化是由何支撑,又是如何实现的?讲汉语语法离不开词类,离不开汉字这种表意文字的特性,以及词义提取中的激活和扩散功能。
(一)名动包含结构
沈家煊先生在《汉语里的名词和动词》中指出,句法范畴的“名词”和“动词”对应语用范畴的“指称语”和“陈述语”,并引入“实现关系”和“构成关系”来对此作出解释。对科学家来说,“病毒”“防火墙”这样的隐喻是解释性的,对普通民众而言,这样的隐喻则构成了对应的抽象概念,脱离这些隐喻,这些概念就无从理解。[3]在此基础上,沈先生继续在《我看汉语的词类》中提出了“汉语是名动包含结构”。汉语里的“名词”和“动词”是语法化程度还不够高的“句法范畴”,它们在进入话语里实现为具体的指称语和陈述语不需要实现过程和实现形式,因为它们的构成就是指称语和陈述语。[4]例如,在“我要买一支笔”中,“笔”是通指,“拿一支笔给我”中,“笔”是专指,名词“笔”入句后就可以构成通指语或专指语,不存在实现形式的问题。同样,动词“出版”可以直接构成陈述语,如“出版一本书”,也可以直接构成指称语,“这本书的出版”,动词“出版”可以直接作指称语和陈述语,并不需要什么实现形式,故而在汉语里,动词就是动态的名词,是名词的一个词类。
名动包含结构为名词动用提供了直接的也是最主要的语义基础。名词包含一个词类——动词,也就是说,在具体的语用范畴上,二者之间的转用不存在实现形式的问题。如提到实体“微信”这一概念,就隐含了它的基本功能——发消息,衍生功能——转账这两种动作性的语义成分,那么,在“你微我”中,听话人明显感觉到“微”本不能作动词,然而说话人却仍然那么用,语义上必然要增加些什么,结合语境,及相关的预设(说话人知道听话人有微信并且会使用),听话人就能提取出“微”在话语中的动作义,再根据语境进行语义选择,是“用微信发消息给说话人”或者“用微信转账给说话人”。
名词包含动词的语义成分,这样的包含关系与dog和bitch的关系类似,在没有特殊语境、特别指称的情况下,dog包含所有的狗,既是[+阴性],也是[+阳性],名词和动词的语义成分也存在着这样的包含关系,名词丰富的内涵意义使它能够向动词义转化。名词指称事物表示的是静态的意义,动词陈述活动表示的是动态的意义,从哲学的观点看,静止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运动是绝对的、永恒的、无条件的,名词指称的事物只是暂时以“静止”的身份运动,一旦有了某种刺激,其运动的一面就会凸显出来,例如笔,单独指称“笔”时,包含了各种品牌、各种类型、各种用途、各种大小的笔,但仍然无可否认,指称笔时也同时在联想到笔的功能——记录,因而古语中有“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转指说法,用笔头这个部分转指它的整体笔,用笔这个实体转指它的功能记录。在空间中处于静止状态的事物,一旦有了某种需要,就会凸显出在时间中运动的状态。
这种转用的语义基础不仅因为汉语特有的名动包含结构,从汉语的记录形式——汉字来说,其见字知言的表意性也为名词动用提供了条件。
(二)汉字见字知言的表意性
《周易》论结绳记事,是“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讲词义变化离不开意义所依附的形体,也就是汉字。从汉字的起源看,由结绳、契刻,文字画,到真正的文字,能清晰地看到早期文字的象形性特征。文字画的产生是为了让信息的传、收双方看到图画后能联想到相同的信息,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图画再现现实生活。例如圣书字用王笏的图形表示统治,因为王笏是统治权的象征。[5]结绳记事和文字画的这种直观性和形象性延续到了真正的文字,象形文字上。如豕和犬,着意突出尾巴下垂与上翘的不同;牛和羊则着意突出犄角上直与下曲的差异。当这些象形字作为基础部件与另外的部件组合成新字时,它们的象形特征也同时带入了新的字中,这就使得许多为抽象概念所造的、原本无形可象的字也带有了浓厚的象形色彩。[6]如“为”,甲骨文像用手牵象,本义是做事、作为。《尔雅· 释言》:作,造,为也。如“取”,《说文》:捕取也。从又耳。取的字符是手和耳,手作为身体的四肢本就是活动的,与“手”相关的事件自然带有动作义。如“及”,《说文》:及,逮也。从又从人。徐锴曰:“及前人也。”用手抓住前面的人即为及。从字形上,能看出带动作义的字,其字义均来自可描摹、可象形的事物。为、取、及均从手。抽象须依托具象方可成像。
汉字的象形色彩造就了它见字知言的表意性,这种表意性从侧面说明,抽象的动作、活动、事件等意义总要在具体的事物中才能成像,这也就是名词动用的语义基础。正如沈文所说,汉语的抽象范畴和具体范畴之间是构成关系,抽象概念由具体概念构成。“吃醋”这个事件总要借助具体的事物“醋”才能先完成“吃醋”的动作,再转指“嫉妒”这种状态。如黑格尔所说:“依照时间的次序,人的意识,对于对象总是先形成表象,后才形成概念”。[7]
语义上的成功转指依托于汉语特有的名动包含结构和汉字见字知言的表意性,也和词义的激活和扩散功能相关。
(三)词义的激活和扩散功能
Collins&Loftus提出“扩散-激活语义加工理论模型”,该理论认为,词义具有激活和扩散的功能。词义在心理词典中的提取并不是交叉的搜索,而是激活的扩展。激活了的节点扩散到其他概念(尤其是那些在词义上有密切联系的概念),牵动整个网络,以致人们想到一个概念时,记忆中相应的节点就会被激活。词义的激活有赖于词义的相关性。王文斌将这一过程比喻为“抛石入池”,泛起的涟漪的中心便是石头的掉入处,其波面受到石头掉入的强度、水池各部位离涟漪中心的位置及石头掉入以后的时间等因素的影响。[8]两个结点间语义相似点越多,联结强度越大,连接线就越短,越容易被激活。
名词表指称义,转用后有了描述义,可以描述事件、活动和动作,这种转用的语义基础可以从词义的激活和扩散功能得到解释。以“鸡娃”为例,“鸡”在“打鸡血”中,是动词“打”的对象,同时又是“血”的主体,“打鸡血”的语义中心在“鸡”,血作为鸡的组成部分不能离开鸡单独存在(*打血?),鸡作为打的对象直接影响整个动作的发生、发展和完成。“打鸡血”的高频度使用使得这个短语有了词汇化倾向,凝固程度较高,只有“鸡”作为整个词的语义中心,才能顺利连贯地完成“从鸡身上抽出血”——“将鸡血注入人体”这个动作行为,激活相邻节点——“打鸡血,使人精神亢奋”这个词义。说它凝固程度较高,是因为已经不能将这个词简单拆分成“*打/鸡血”,会损害原有词义。类似的例子,喝/鸡汤是可以说的,因为鸡汤不常和“喝”搭配起来使用,如“这碗鸡汤我先干为敬”,鸡汤的语义显现对动词的需求并不是那么强烈,因而不会有“鸡娃”——给娃传递正能量的表达。
也许有人会对鸡娃中“鸡”是名词动用产生疑义,鸡明显来自于一个动词短语“打鸡血”,如何能归为名词动用?“打鸡血”的语义凝固,并由鸡承载整个语义是一个认知过程,这样的例子在汉语中并不少见,如偏义复词忘记、睡觉、国家等,再如“你用微波炉把面包微一下”,这些多音节词的语义都仅由其中一个语素负荷,这种语义凝固并由某个语素统帅整个语词意义的现象还值得探讨,王冬梅将这样的关系称为“缺省”,即在知道一定事物后,如没有特殊说明,人们总是按这样的关系来理解。[9]如“手术到午后”,“这样做不太道德”。鸡娃中,鸡是表示一种关系,这是毋庸置疑的。还值得关注的是,“鸡”在承载打鸡血的语义后并没有停止变化,反倒以陈述义更加活跃地参与到了新词新语的构造中,如“娃不鸡不成器”“鸡娃先自鸡”,其中也有不少指称义的“鸡”:素鸡,以素质教育技能为培养方向;荤鸡,以学科类内容为培养方向。鸡在走向指称和陈述两个不同的方向。
二、余论
名词动用的语义基础是汉语特有的名动包含结构,汉字见字知言的表意性,及词义的激活和扩散功能。沈家煊先生提出汉语中零句是根本,名动包含结构亦是这一特点的延伸。[10]名词和动词的区别有限,那动词在汉语中的省略也就有了支撑,因为名词能承担其相应的语义,类似“我电话你”“把相框胶好”这样的表达也就能层出不穷了。从构成关系的层面来看,汉语的抽象范畴和具体范畴之间是构成关系,抽象概念由具体概念构成,沈先生的这个结论在汉字的特征上也有体现,汉字有很强的象形性,从汉字的起源来说,早期的结绳记事、图画字到真正的文字,直观性和形象性延续了下来。现在,网络上新兴的“又双叒叕”“我很囧”等也有很强的象形意味,汉字的这种可视性为语义的转指提供了最便捷的渠道,从手从人的及就是追赶上,从手从耳的取就是捕取。
这种语义上的转指并不是汉语独有的,或者说,不止存在语言这个符号层面,在其他符号层面,也存在语义上的转指。如在交通标志中,“注意儿童”的标志是两个儿童在走动。该标志的图示中只有人物,提示的是地点,要求是减速慢行,司机在看到该交通标志时,能很快根据儿童这个图示,迅速作出减速举动。再举个例子,开车时前方突然出现行人,提示的人第一反应是脱口而出“有人”,而不是“刹车”,这和事物的显著度相关,视野范围内最先出现的是行人,是人最先给大脑带来刺激,从而促使主体作出减速或刹车等相应举措。刹车或减速这样的动作概念是由行人引起的,显著度次于行人,在大脑中的处理时间也会晚于显著度更高的行人。
名动转用的表达古已有之,研究“人类的语言创造能力”不能忽略人的名词动用的创造能力。名词动用提高了表达效果,言简意赅,能够满足说话人求新求变求简的交际需求,花最少的气力,传达了最充分的意思,并且,句子长度缩短后,也减缩了动作在说话人心中发生及完成的心理距离。对受话人来说,句子的新奇与违背常规也引起了受话人的充分关注,吸引了注意力的同时,也促使受话人调动其基础知识对当下话语中的信息进行补充并解释。名动转用的表达符合话语交际的经济原则,能够达到省力的效果。从现有现象看,动化词还可能从原有名词中分化出来,以陈述义继续独立造词,这也是尤为值得关注和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