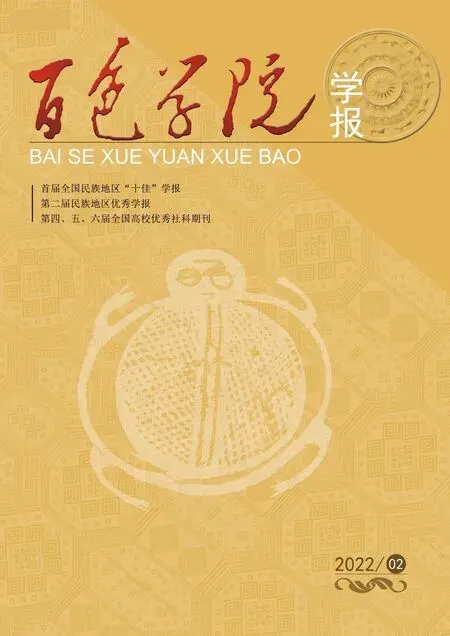敦煌写经仪式考
——以法藏敦煌遗书P.2325 号《法句经疏》为例
张 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佛陀涅槃后,伴随着佛教的几次结集,写经功德被放置在与诵经功德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例如“《大集经》云:‘菩萨有四种施具足智慧。’何等为四?一,以纸笔墨与法师令书写经;二,种种校饰庄严妙座以施法师;三,以诸所须供养之具奉上法师;四,无谄曲心赞叹法师。”①《法苑珠林》(T2122)卷八一,《大正藏》第53 卷,第886 页第1 栏第25 至28 行。作者注:本文在引用文献时,引文中的繁体字、异体字统一改为通用规范汉字。其中之“纸笔施”正是与写经功德相连。又如《增一阿含经》称:“若有书写经卷者,缯彩花盖持供养,此福无量不可计,以此法宝难遇故。”②《增一阿含经》(T0125)卷一,《大正藏》第 2 卷,第 550 页第 3 栏第 5 至 6 行。更有甚者,《大智度论》称:“有人书写经卷与人,复有人于大众中广解其义,其福胜前;视是人如佛,若次佛。”③《大智度论》(T1509)卷五九,《大正藏》第 25 卷,第 481 页第 1 栏第 26 至 28 行。书写经卷者、捐赠经卷者及宣讲经卷者几乎与佛陀本人相等,这已是对写经讲经之人的最高评价。
一、文献记载中的写经仪式
(一)传说中的写经仪式
写经人功德无量。写经仪式更是千姿百态。佛本生故事中有许多关于佛陀以皮为纸、以骨为笔、以血为墨写经之传说。例如《菩萨本行经》中记载:“(佛言:我为)梵天王时,为一偈故自剥身皮而用写经;毗楞竭梨王时,为一偈故于其身上而啄千钉;优多梨仙人时,为一偈故剥身皮为纸、析骨为笔、血用和墨。”④《菩萨本行经》(T0155)卷下,《大正藏》第 3 卷,第 119 页第 2 栏第 14 至 18 行。又如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所述:“(摩愉伽蓝)其窣堵波基下有石,色带黄白,常有津腻。是如来在昔修菩萨行,为闻正法,于此析骨书写经典。”[1]281
佛陀以皮、骨、血等书写佛经的传说,用以证明佛陀本人对于佛法和佛经的敬重,也得到了后世佛教文献书写者不同程度的效法。例如隋代高僧智顗就曾以血写经:“又顗自以身血,书写经而讲,收国清寺真身堂。四邻草木,向堂而低垂。”①《法华传记》(T2068)卷二,《大正藏》第 51 卷,第 57 页第 1 栏第 11 至 12 行。
(二)隋唐时期的写经仪式
写经仪式之繁复,在隋唐时期登峰造极。
如幽州沙门知苑“精练有学识。隋大业中,发心造石字一切经藏以备法灭。既而于幽州西山,凿岩为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磨写,藏诸室内。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镕铁锢之。时隋炀帝幸涿郡。内史侍郎萧瑀,皇后弟也。性笃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绢千匹。瑀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争共舍施。故苑得以成功。苑常以役匠既多道俗奔凑,欲于岩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寐室。而念木瓦难办,恐繁经费,未能起作。忽一夜暴雨雷电震山。明旦既晴,乃见山下有大木松柏数千万,为水所漂积于道次。道俗惊骇,不知来处。于是远近叹服。苑乃使匠择取其木,余皆分与邑里。邑里喜愧而助造堂宇。顷之毕成,如其志焉。苑所造石经已满七室。以贞观十三年卒。弟子犹继其功焉。”②《神僧传》(T2064)卷五,《大正藏》第 50 卷,第 984 页第 1 栏第 3 至 19 行。
定州沙门释昙韵“行年七十。隋末丧乱,隐于离石比干山。常诵《法华经》。欲写其经,无人同志,如此积年。忽有书生,无何而至,云:‘所欲洁净写经,并能行之。’于即清旦,食讫入浴,着净衣,受八戒,入净室,口含檀香,烧香悬旛,寂然抄写,至暮方出。明又如先,曾不告倦。及经写了,如法嚫奉,相送出门,斯须不见。乃至装潢,一如正法。韵受持读诵之,七重裹结,一重一度,香水洗手。初无暂废。梦普贤现前告韵云:‘善哉!如法书写《法华》,即身能离二十五苦。’后遭胡贼,乃箱盛其经,置高岩上。经年贼静,方寻不见。周慞穷觅,乃于岩下获之。箱巾糜烂发朽,见经如旧鲜好。见者谓异矣。”③《法华传记》(T2068)卷八,《大正藏》第 51 卷,第 83 页第 2 栏第 8 至 22 行。
又如雍州沙门释法诚“幼出家,每以诵《华严》为业。因遇慧超禅师,隐居蓝谷,高山仰止,窃有庶几,遂屏嚣烦,披诚请益。后于寺南岭造华严堂,添洁中外,方就抄写。其堂瓦及泥,并用香水,皆诚自踏。庄严既毕,乃洁净图画七处八会之像。又访召当时工书之人,弘文馆学士张静,每事清净,敬写此经。诚亦亲执香炉,专精供养,乃至一点一书,住目倾心。然施慧殷重,两纸,酬钱五百。便感瑞鸟,形色非常,衔华入堂,徘徊旋绕,下至经案,复上香炉。其经当写未终,后方更续。更续之日,鸟又飞来。复造宝帐香函,莹饰周修。自尔精心转读者,多蒙感祐矣。”④《华严经传记》(T2073)卷五,《大正藏》第 51 卷,第 171 页第 1 栏第 20 行至第 2 栏第 3 行。
河东比丘尼练行“常诵《法华经》。访工书者一人,数倍酬直,特为净室,令写此经。一起一浴,燃香熏衣。仍于写经之室,凿壁通外,加一竹筒,令写经人每欲出息,辄遣含竹筒,吐气壁外。写经七卷,八年乃毕。供养严重,尽其恭敬。龙门僧法端,常集大众,讲《法华经》。以此尼经本精定,遣人请之。尼固辞不与。法端责让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端等开读。唯见黄纸,了无文字。更开余卷,皆悉如此。法端等惭惧,即送还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函,沐浴顶戴,绕佛行道,于七日七夜,不暂休息。既而开视,文字如故。”⑤《冥报记》(T2082)卷一,《大正藏》第 51 卷,第 789 页第 1 栏第 18 至 29 行。
综上可知:其一,上述写经以抄写为主,且书写者常为一人;其二,写经仪式常伴神异,所书经卷如有神佑;其三,写经仪式风格各异,并无一定之规,而是或“凿岩为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或“食讫入浴”“口含檀香”,或“造宝帐香函”,或“遣含竹筒,吐气壁外”,每位写经人遵从自己内心最虔诚的声音,尽己所能,以最大的恭敬之心,完成自己的使命。
二、还原P.2325 号《法句经疏》之书写仪式
结合上述佛典所载之写经仪式,再以法藏敦煌遗书P.2325 号《法句经疏》这份独一无二的主体部分以中文草书形式书写而成的写卷为例,择要考察敦煌文献的生成与流传。
法藏敦煌遗书P.2325 号写卷,卷轴装,22 纸,共592 行。⑥参见《国际敦煌项目》数据库(http://idp.bl.uk)P.2325。第571 行“《法句经疏》一卷”之后,至第587 行,为《金刚五礼》一卷。第587 至592 行,是一段介绍佛陀生平和三十二相的文字,其后缺损。写卷背面还有一些包括梵语语法在内的零散文字,笔迹潦草,书写凌乱,间有大量空行,很多地方仅列出标题或关键词,似为尚未补齐的听课笔记。写卷第1 至571 行为《法句经疏》一卷,首尾俱全,不含文侧标注约1.4 万字。写卷起首部分(第1 纸,第1 至24 行)为后补之隶书,纸张颜色较深,无边白,边缘不甚规则。写卷主体部分(第2 至22 纸,第25 至571 行)纸张颜色较浅,有边白,以中文草书形式书写,间有楷书改字或旁注。敦煌遗书出土后,P.2325 号《法句经疏》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85卷,T2902《法句经疏》,第 1435 页第 3 栏第 7 行至 1445 页第 1 栏第 6 行。疏文第 6 行至第 22 行第 19 字未见于《大正藏》录文,且行文断句讹误颇多。这亟待出版更为准确的校勘版本。①笔者2021 年12 月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敦煌草书写本识粹·法句经疏》,计划于2022 年3 月在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法藏敦煌遗书P.2325 号〈法句经疏〉校释研究》,希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弥补这一缺憾。
P.2325 号《法句经疏》主体部分以中文草书形式书写,保留了大量敦煌遗书特色的异体字和草书字,具有如草书字与繁体正字并存,异体字与规范字并存,异体字、通假字、草书字形楷化字频出等特点。以下尝试从书写者与传书方式两方面还原P.2325 号《法句经疏》之书写仪式。
(一)多人主书
在P.2325 号《法句经疏》这部约1.4 万字的写卷中,同一个字出现了多达5 种不同写法。这些异写,主要是使用了不同的异体字和通假字,还包括字体(如隶书、草书、行书、楷书)之别。例如“辩”字,在第 5 行写作“”,第 28 行作“”,第 38 行作“”,第 43 行作“”,第 112 行使用通假字“”(弁)。又如“实”字,第 152 行作“”,第 156 行作“”,第 157 行作“”,而在第370 行作异体字“”()。“论”字,第 14 行作“”,第 29 行作“”,第 96 行作“”。“寂”字,在第 2 行使用隶书异体字“”(),在第 122 行使用草书异体字“”(),而在第298 行使用草书异体字“”()。一些异写的情况,甚至会在同一行出现。例如第76 行,先后使用了“”()和“”(施);第 128 行,先后使用了形同“为”的草书字“”(爲)和繁体正字“”(為)。
据不完全统计,P.2325 号《法句经疏》主书者更换频率极高,数见每行更换写手的情况,甚至同一行内亦可见多人传书的痕迹。有的书写者的笔迹在写卷中数次出现,而有的书写者的笔迹仅出现一两次或极有限次数。这证明其中的一些书写者仅参与了一两行甚至若干字的书写。可见,这些书写者的关注点并不是在于能否尽快完成这份写卷,而是在于能否切实地参与书写的过程。也就是说,几乎疏文中的每一个字都成为人们争夺的“稀缺资源”。
众人合书这部万余字经疏,极有可能是将写经视作无上功德。敦煌《法句经》见于《大唐内典录·历代所出疑伪经录》及《开元释教录·伪妄乱真录》,实为一部中土之人借托佛言编撰之伪经。②敦煌《法句经》的情况见张远:《敦煌遗书〈法句经〉略考》,《世界宗教文化》2020 年第5 期。P.2325 号《法句经疏》则是现存唯一的对于敦煌《法句经》的完整注疏,亦即伪经之疏,事实上与真经之佛言早已大相径庭。然而精深的真经、律、论,或许只是为高僧大德修习之用。普通信众并没有足够的判断力与觉悟。他们或许只是单纯地相信,只要是一部与佛教相关的文献,只要能够参与书写,就已经得以分享佛陀的庄严,就已足够。即使是一部伪经之疏,众人也因得以书写若干字句而福德无量。
若是一人写经,经卷的力量更多来自经文本身。而众人写经,则是将信众信仰的力量悉数汇聚在经卷之上,仿佛投入功德箱的一点一滴的布施,仿佛信众集体供养僧团的百衲衣。众人写经事实上使得书写者与经卷之间产生了某种微妙的互动。其一,并非只有信众在写经过程中获得了功德与满足,经卷本身也因凝聚了信众的信仰力而如同受到加持,并有足够的力量将写经功德分布给写经者。其二,写经的目的并非只为收藏与保存。书写即是一种表达信仰的宗教实践,而写卷本身则是一次次讲习过程中的“活”的文本。
(二)口传笔录
从内容和文体上看,P.2325 号《法句经疏》这种经疏体文本本身就具有口头创作的性质。其书写特征更是将这种口传与书传相结合的特质彰显无遗。
首先,P.2325 号《法句经疏》写卷正文部分字形随意性强,非规范字频出,同一个字出现了若干种不同写法。然而这些同一个字的不同异写虽以形近字为主,但也存在相当大数量的一批字形差异较大的同音字。如人们通常理解的,异写源自笔误或传抄讹误,抑或源自写经生并不太高的文化水平,这对于字形相近或者多笔画、少笔画的异体字或许可以说通,然而对于字形相差较大的异写,则变得难解。很难想象一位写经生会将“寂”一会儿抄作“”,一会儿抄作“”;或是将“喜”一会儿抄作“”,一会儿抄作“”;“”(闇)、“”(暗)混用,“”(辩)、“”(弁)混用,“”(並)、“”(并)混用,“”(藉)、“”(借)混用,“”(衣)、“”(亦)混用,“”(知)、“”(智)混用,如是等等。即使是对于很多位写手接力传抄的情况,这样巨大的字形差异依然难解。
其次,写卷行间旁注中,亦有字形、字体、墨迹深浅等书写差异,并存在对正文文字的误读。这证明不仅写卷正文部分由多人接力书写而成,写卷旁注亦由多人接力书写,且旁注之书写者与正文主书者并不相同。旁注之误,固然源自字形相似,然而旁注之初衷,却极可能是为了注音。草书文本给一些僧人和信众畅习疏文造成了阻碍,故需楷体旁书标注读音,以便反复诵读、宣讲和继续流传。误释旁注反映了注音时出现的偏差,而正释旁注中不仅有大量同字之楷书释文事实上起到了标注读音的作用,亦不乏注音之绝好例证。例如第160 行,疏文正文为“”(纠),旁注为“”(故酉,反切);第 184 行,疏文正文为“”(允),旁注为“”(尹,注音);第 368 行,疏文正文为“”(饮),旁注为“”(盂,注音);第380 行,疏文正文为“”(射),旁注为“”(社,注音)。
结合上述两点来看,写卷正文或旁注中之异写,无论字形是否相近,均为同音;写卷旁注,无论楷体释文或是读若、反切,甚至误释旁注,其初衷均为表音。这表明写卷的生成与传播均以声音为核心。
P.2325 号《法句经疏》罔顾字形,异写混用,通假频出,字形多变,却在读音的一致性上到达高度统一,正是将文字用作表音符号来记录流动声音的表现。无论这些异写的字形是否相似,无论是多笔画、少笔画、字形或字中构件相异之异体字,还是同音借用之通假字,遑论字体差异,其共通之处即音同或音近。无论误释旁注还是正释旁注,这些注释的初衷均为注音。因此,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部写卷在本质上既传承自“讲习”——声音的流动,又生成自“听写”——声音的记录。也就是说,这份写卷是一份对于声音的书写,是“听写”自“讲习”,而非抄写自某个“定本”。
P.2325 号《法句经疏》“口传笔录”的另一旁证是其现存唯一副本——英藏S.6220 号《法句经疏》(残卷)中所保存之异文。英藏S.6220 号《法句经疏》(残卷),长25.5cm,首尾俱残。未出现经名。仅存17行。第1 至5 行、第16 至17 行亦残缺不全。第14 至15 行有“故言《仏(佛)说法句经》一卷也”的表述。所存内容与P.2325 号《法句经疏》第29 至44 行基本一致。①写卷影印版见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45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 年,第135 页。参见敦煌研究院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索引第101 页,正文第192 页。《敦煌宝藏》及《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均拟题名《法句经疏释》。实为与法藏P.2325 号《法句经疏》同本异出之残卷。通过比对二者异文可知,S.6220 号《法句经疏》(残卷)修改了P.2325 号《法句经疏》中的两处错误,并增添了数十字内容,还有少许字词出入,多为同义替换。这证明二者均为在诵读和传承过程中的“活”的文本,应为同时或先后产生,因其形态并未完全定型,并未进行对校等校勘,尚不具备“定本”之稳定性,亦即具有口传文献的主要特征。
P.2325 号《法句经疏》中同一个字的不同异写、写卷中的表音旁注及其现存唯一副本英藏S.6220 号《法句经疏》(残卷)中保留之异文等方面内容,证实P.2325 号《法句经疏》及以其为代表的相当数量的敦煌文献之生成与流传,并非如前人所述“抄写”而成,而是以“口传笔录”的形式“听写”使然,虽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口头文献,却是一种书面文献的口头传播,是民间口传与民间书传相结合的产物。
三、结论:三代威仪,尽在其中
佛陀以言说的方式传法。佛陀涅槃后,“大迦叶贤圣众选罗汉得四十人,从阿难得四阿含。一阿含者六十疋素。写经未竟,佛宗庙中,自然生四名树,一树字迦栴,一树字迦比延,一树字阿货,一树字尼拘类。比丘僧言:‘吾等慈心写四阿含,自然生四神妙之树。四阿含,佛之道树也。’因相约束,受比丘僧二百五十清净明戒,比丘尼戒五百事,优婆塞戒有五,优婆夷戒有十。写经竟,诸比丘僧各行经戒,转相教化千岁。”①《佛般泥洹经》(T0005)卷下,《大正藏》第 1 卷,第 175 页第 3 栏第 2 至 10 行。阿难比丘被世尊佛陀誉为“声闻中博有所知,有勇猛精进,念不错乱,多闻第一”②《增一阿含经》(T0125)卷四九,《大正藏》第 2 卷,第 820 页第 2 栏第 28 行至第 3 栏第 1 行。。相传阿难比丘记忆力超群,能一字不落复述佛言。这里所说之“从阿难得四阿含”,即是由阿难口授,四十罗汉笔录。最初的佛经即是以这样“一对多”的“口传笔录”的方式传播。以P.2325 号《法句经疏》为代表的敦煌文献中多人传书、竞相书录的方式,正是对佛经初现之时流传方式的再现。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很多写卷自始至终书写自一人,而如P.2325 号《法句经疏》这般拥有一个书写团队的情形亦尝可见。从纸张颜色,墨迹深浅,运笔差异,笔画粗细,字体、字形、同字异写及行间注释来看,P.2325 号《法句经疏》为多人主书、多人旁书、集体完成。其中的一些书写者仅参与了一两行甚至若干字的书写。这些书写者所关注的并非尽快完成这份写卷,而是切实参与书写过程。
这部万余字的经疏,却由众人竞相书写,既因一字一句,皆为功德,亦是将信仰寄托于佛教文献之上。即使一部伪经之疏,亦不妨碍普通信众宗教情感的表达。
第二,很多写卷源自誊抄,而如P.2325 号《法句经疏》这般以“口传笔录”的形式“听写”而成的情形亦尝可见。从音同形异之大量异写及表音旁注可知,P.2325 号《法句经疏》是一份以表音为核心的写卷,是对口传文献的书面记录。原不存在一个纸质的“定本”。其生成机制并非凭借“抄写”,而是以“口传笔录”的形式“听写”使然,其流传亦是依靠诵读、讲习等以口传为主的方式。
无论写卷正文中字形多变的表音记录,还是写卷字里行间的表音旁注,楷体字释文、谐音字读若、反切注音,均是以读音为核心,均是为了便于诵读、讲习和传播。而文本形态之不稳定性,不仅是口传文献的显著特征,也勾勒出了其在流传过程中承上启下的状态——既是接受文本,又是输出文本,并非是单纯的记录与保存,而是具有极强的实用性与目的性,注重诵读实践与讲习传承。这种民间口传与民间书传相结合的方式,是以P.2325 号《法句经疏》为代表的相当数量一批敦煌文献生成与流传的重要方式。
第三,很多写卷用于收藏、供养,而如P.2325 号《法句经疏》这般具有宗教实践价值的“活”的文献亦尝可见。从P.2325 号《法句经疏》及其现存唯一副本S.6220 号《法句经疏》(残卷)之异文可见,二者均为在讲习、传承过程中的“活”的文献,不具备“定本”的稳定性。即便不存在一个“定本”,在这部“口传笔录”的写卷中,书写者们依然通过一次次的注释旁书追求一个相对完美的“定本”。在没有其他更完美抄本的情况下,这部口传文献唯一传世的完整笔录甚至已升级成为“祖本”。
敦煌文献沉睡千年,终于苏醒。发黄的故纸将湮没于历史烟尘的文化记忆完整重现。究竟有多少敦煌写经其实是由数目可观的写手接力书写而成,又究竟有多少敦煌写经其实并不是“抄写”而成,而是以“口传笔录”的形式“听写”而成,尚未可知。但这的确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我们对存于书面的古典文献生成与传播方式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