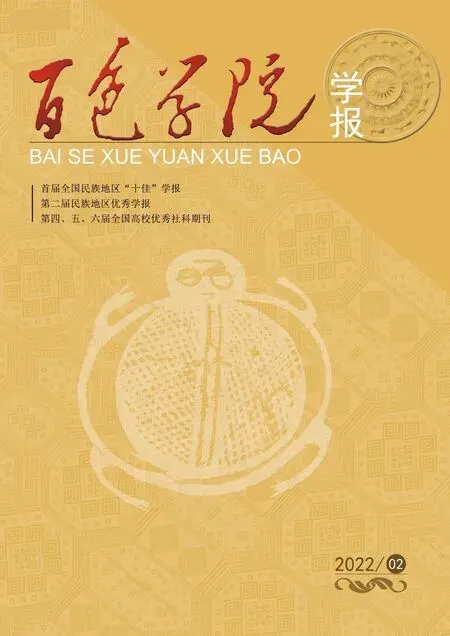一直在路上:民族语言和跨境语言的调查与研究
——戴庆厦教授访谈录
施今语(问),戴庆厦(答)
(1.爱丁堡大学,英国爱丁堡 EH8 9AD;2.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状况
施今语:戴老师,您好,非常荣幸能有机会采访您。我对您的研究领域很感兴趣,为此我最近拜读了您的很多论著和其他研究者的一些相关文章,想多了解一些基本情况。您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是民族语言。我国有很多少数民族,但是一般人对他们的语言使用状况并不是很了解,您能否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国民族语言的使用状况?
戴庆厦:我主要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语法,最开始主攻的方向是景颇语和哈尼语。后来研究领域扩大到藏缅语比较、汉藏语比较这方面,之后又因为工作的需要涉足了社会语言学这些跨界领域。
中国有56 个民族,目前所使用的语言有130 多种,其中22 个民族使用了28 种文字。为什么语言、文字的数目跟民族的数目不一致?这是因为有的民族使用好几种语言。像藏族,除了使用藏语以外,还有嘉戎语、尔龚语、尔苏语等。当然,一种语言也不一定只为一个民族使用。文字方面也一样,有的民族使用多种文字,像傣族就有5 种文字。所以我们中国的语言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这130 多种语言可以分为5 大语系,包括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资源有多方面的特点。一是民族和语言的大小不一样。最多的像壮语有1000多万人,比较少的像赫哲语。我们之前调查过一种语言,叫做仙岛语,原来有一二百人说,前几年我去的时候只有80 个人会说了,现在可能连80 个人都没有了。二是不同民族之间使用的语言有交叉。像壮族,它的北部方言跟布依语比较接近,而北部方言跟南部的方言相差却很大。这就造成了民族界限和语言界限的划分有交叉。三是同一民族不同方言间的差异也有大有小。有的方言差异很大,像彝族、苗族的方言之间互相听不懂,甚至会有十里不同音的情况。但是有的语言内部比较一致,像新疆的维吾尔语。我之前从乌鲁木齐坐飞机到伊犁,中间距离有700 来里,但是这两地的维吾尔语基本上一样。像我研究的景颇语也比较一致,包括境内和境外的使用都比较一致。目前我们没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有的语言比较一致,有的差别比较大。像苗语十里不同音,研究起来就很困难,做语言保护这方面的学者为此研究了很久。除了语音,不同语言(方言)的语言功能也不一样。有的语言功能比较强,像维吾尔语、藏语就是全民使用。有的语言,像南方的一些小语言,只在家庭内使用。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基本上是这种情况:大小不一,功能不一,发展的途径也不太一样。
施今语:只在家庭使用的小语言,有没有书面语的记录?
戴庆厦:这些语言没有书面语。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为十几个民族语言创造了文字。但是后来这些文字投入使用以后不太理想,用起来不普遍。
施今语:为什么用起来不太普遍?
戴庆厦:一来是因为人口少,用这种文字编写的报纸和书比较少,人们读得少,通行度就比较低。还有一个大原因是这些语言的语音差异大。我们创造的文字都是为南方的一些民族语言来使用,而这些语言的方言间发音差异大,用拼音文字来记录语言就不是太适应。不同的地方拼出来的音不一样,如果以一个地方的方言作为基础做拼音文字的话,其他地方的人学起来就很困难,结果发现还不如直接学汉字。这也说明,汉语用汉字记录而不是改成拼音文字,是有道理的,不然方言间发音差别这么大,拼音文字根本无法调和。而汉字则通古今,无论到哪里都可以读,各地方言读音虽然不一样,理解和交流却有很大的方便。
施今语:我看过一些材料,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教育问题一直都很重视,颁布了不少法律法规,出台了不少政策。很多学者都投入到提高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事业当中,并做出了很大贡献,比如帮助一些无文字民族语言创制文字、编写课本,以及培养教师等等。相比过去,您觉得现在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重大进步体现在哪些方面?
戴庆厦:最大的一个进步就是少数民族学汉语,兼用汉语和自己民族的语言。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年轻的时候到云南红河州做语言调查,那时候当地懂汉语的很少,一个村子里没有几个人。现在普遍会汉语了,因为这是社会交流的需要、地区发展的需要,也是个人学习和工作的需要。汉语是国家通用语言,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是要求学汉语的,现在的民族地区都会兼用汉语了。另外一个变化是,有了国家的投入,我们的教育设施变得更好了。
我们国家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比如自2015 年起开始实施“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语保工作肯定是首先要记录这个语言,但是光记录还不行,单纯的记录下来不一定保护得了。我们现在提出必须在社会生活当中去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目前在这方面措施还不够,主要还是记录语言,先作为语言文化资料赶紧保存起来,但关键还在于保得住。所以现在我们就在考虑怎么去做语保,因为语言资源如果不保护的话,将来是一个大的问题。
施今语:会不会有人觉得学民族语言对于自己以后的生活帮助很小,这方面的就业前景也不太好,就不太想学。
戴庆厦:现在就有这个问题。对于使用人数少的民族语言,必须保护,让它传承。但是学完以后又和实际应用发生矛盾,对使用者用处不是太大。所以有的家长也不愿意让孩子学,因为成本太高,学了整个小学、初中,到最后发现求学、就业竞争力没有提升。而且还有可能影响到汉语的学习,进一步影响到考试成绩。面对这种情况,国家正在讨论采取一种什么特殊政策来保护民族语言。
施今语:戴老师,现在民族地区的学生除了民族语,还要学汉语和英语,存在不少困难吧。
戴庆厦:对,现在我们招研究生就出现了这方面问题,有的学生别的方面都很好,就是外语不过线而被卡掉,非常可惜。
施今语:这样看来,他们实际上是在同时学3 门语言。
戴庆厦:是的。这必然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语言负担重。语言负担太重不是个好事,会影响到人才的培养。尤其是这些语言之间差异比较大,不像欧洲的一些语言比较接近,学起来可能相对自然一些。现在还想不出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来解决语言的保护使用和人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施今语:现在学校里的双语教学情况怎么样?
戴庆厦:相比民族语学习,还是多偏于学汉语。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所以需要考虑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有切实的措施来解决学和用的关系问题。这实际也是一般语言学习的根本问题。
二、民族语言研究的根本路径
施今语:到目前为止,您田野调查了20 多种少数民族语言,而且您对每一种语言都了解得非常深入。请问要想研究一种民族语言,需要对它了解到什么程度?
戴庆厦:最好的情况当然是对某一种语言有比较深入研究,成为一个专家。但是汉语研究和民族语言研究情况不一样。现在做汉语研究的人比较多,我之前做报告的时候打比方说,研究汉语的人多,就像在一块土地上精耕细作,大家每个点都可以深挖。民族语言的种类比较多,就像进到一个原始森林,看到各种花草、果子都是新鲜的,但是来摘的人比较少,所以每个人都需要这个摘一点,那个也摘一点。那么就研究一种民族语言而言,对这个语言的了解要达到什么程度呢?我的体会是必须要对这个语言非常熟悉。要能说,要理解,这样才能够深入。我主要做景颇语研究,这几十年做景颇语研究,我一般场合说景颇语都没有问题了。
施今语:您的景颇语是后来学的吗?
戴庆厦:在学校学了一些,但是学得不行,主要是后来在实际工作中学的。我出去跟老百姓调查,跟当地人一起生活,用景颇语沟通。我还被国家派去参加过景颇语翻译,去了一年。这下就可以了,感觉好像突然有一天听到什么都懂了。原来我们跟老百姓讲话时最开始有的听不懂,后来经过这么一系列的调查和翻译,现在虽然有时候不在那个地区工作生活了,但是做报告都没有问题,而且不会忘了。也就是做到了“四会”:会发音,会译,会听,会说。当然还得再学,因为毕竟不是母语人。我和我夫人徐悉艰老师都不是景颇人,是汉族人。我最开始学景颇语,后来我因为要为哈尼语创造文字又去研究了哈尼语,我就也会说哈尼语了。哈尼语比景颇语要好学一点。徐老师后来在载瓦地区搞群众工作做语言研究,最后载瓦语也会说了。
要想研究一门语言,不学是不行的,不学的话做研究也是不容易做好的。我现在对博士生的要求是每个人守一种民族语言,深入一点,然后再扩大,否则就很难有大前途了。所以我的博士生一进来,我就给他定方向。不过现在的学生学语言不像我们当年那样直接到生活中学,随时拿个本子认真记,听不懂还发愁,现在有些学生学语言不太肯学。
施今语: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戴庆厦:外边的事干扰太大。我们那时候下乡,跟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拿本子去记。可是现在有些人下乡调查比较表面。这方面也受国外某些学者的影响。有的国外学者来做语言调查,就是根据需要拿点东西过去,并不好好去学。有的做民族语言做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还是不会说。我就要求学生要会说。
调查民族语言是很需要时间和精力的,需要长时间在那种语言使用的地方生活。这是不二路径。现在很多学生希望读3 年博士就可以毕业,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是不行的,尤其是做民族语言这方面的研究,可能还没有调查、挖掘到很多东西就毕业了。现在培养一个真正在民族语方面研究得深入的学者很难。我们这个领域主要从两个方面做,一个是直接调查使用者讲某种语言的情况,再一个通过比较不同的语言来写文章。现在很多人是利用别人调查的材料来写文章,真正属于自己调查的很少。之前北京有个老师原来是研究外语的,写出了一篇文章,我看了觉得不行。因为他对这个语言并不怎么了解。而日本有位学者研究基诺语,便真的到基诺山待了很长时间,把基诺语学会了。这种研究就很厉害了。仅仅了解一点表面的东西是不行的。培养语言学家,不深入是做不好的。其实,年轻的时候学会了一两种语言,将来的研究就方便了,就是老了也好办,因为真的学会了的话,后来也不会忘得太多。博士生嘛,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施今语:有没有可能去调查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
戴庆厦:当然有,有时也需要。我们调查的陌生语言可多了。比如说比较早期的那批学生,我带他们去调查基诺语、怒语、独龙语等。每个人都调查了几种语言,多的有十几种语言,所以成长得很好,语音进步也快。一个叫傅爱兰的,当时到怒族做怒语研究。刚开始对她来说也是陌生的语言,她特别聪明,也肯学,就去学了,她在怒族地区不到两个月,怒语基本都会说了。
施今语:现在还有这种状况吗?
戴庆厦:现在没有调查过的空白语言不多了。但是有的语言过去虽然调查过,但做得很少,由于各种原因调查得并不细致。所以我让我的博士生再去具体研究。语言调查有时要反复进行,这样才有更多的发现,更准确的认识。比如说云南通海的卡卓语,我调查过3 次;蒙古族所说的彝语,有4 万多人说,我也调查过。
施今语:蒙古族还有说彝语的?
戴庆厦:元朝时蒙古王朝远征云南,后来元朝覆灭了,远征部队就留在那里了。因为部队都没有带家眷,就跟当地的民族(主要是彝族)通婚了,逐渐使用当地的语言。这是研究语言接触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这些留下来的蒙古部队及其后代有民族情感,我去调查时,他们说自己讲的是蒙古语。我说你们讲的不是蒙古语。后来我们到周围山上调查了彝语,调查后和这些蒙古族人现在说的语言一对比,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严整的语音对应,当然肯定会有点变化。但就是这么说他们也不相信。他们还坚持说自己讲的就是蒙古语,还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他们说在讲吃饭这件事时,自己现在讲的话跟蒙古语一样,都是“我饭吃”。我说这种推论站不住,因为所有的藏缅语都是“我饭吃”,语序是主宾动。第二个例子是,他们说自己有个词跟蒙古语一样:兔子是“tù lā”。我说云南的很多语言里也是“tù lā,因为都是从汉语借来的,蒙古语也是从汉语借去的,所以发音相同或相近。但是他们认准了自己的理,因为他们是北方的蒙古族的后裔,有亲情。实际上他们使用的语言已经是卡卓语了。我之前写过一本小书,简述了这种语言的概况,但研究得不深入。像这样的情况,都需要学生去做更充分的调查研究。比如怒语、独龙语,都应该找学生去调查一下。在靠近西藏边界的一些地方还有一些陌生的语言,不太容易去。除了完全陌生的语言,还有一些小语言做得也不多,也要继续做,而且很紧迫。
施今语:如果一下研究十几种语言,不可能对于每一种语言都学到能说能听的程度吧。那么,对于其他的语言要了解到什么程度呢?
戴庆厦:要了解一些基本特点,能够用它的语料来进行语言研究。这是通常的情况,基本够一般研究用了。当然要深入地去做的话,你还得对这个语言有详细的认识。我是有两种语言作为立足点的,对于这两种语言我研究得好些。但是现在我的一些博士没有一个立足点。作为专业研究人员,每个人都要有一两种语言做靠山,这样的话将来就像吸铁石一样,别的语言就往里吸了。现在民族语言研究队伍的培养正面临着这方面的困难,要特别注意培养一些做有深度的研究的学者,而不是只做一些表面的比较研究。
三、田野调查的基本素质
施今语:戴老师,既然研究民族语言的最基本的路径是需要进行精细的田野调查,那么怎么调查就很关键了,尤其是调查者自身的专业素质。您认为进行民族语言调查需要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戴庆厦:做民族语言研究,我们都强调田野调查,所以大家说我们是田野调查派。没有田野调查,就做不出真正的成绩,凡是想做出成绩的学生,都要经过田野调查,而且要经过很多次。过去没有经费,调查有难度。现在国家为语言保护项目拨了比较多的经费,但是很多年轻人下不去,因为有家庭、有孩子,这些都是实际的困难。
语言调查的素质有哪些?大体而言,有两条。第一条是思想素质,要有对民族语文的热爱,下去了要愿意吃苦、能够吃苦。这点非常重要,甚至是根本。有了对民族语文的热爱,再苦也没问题。有些人觉得搞这个没意思,当然就吃不了苦。下去的学生有两种,有的很能吃苦,将田野调查当作到大熔炉里去锻炼;也有个别人不是特别愿意,沉不下去。现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学生考虑毕业以后不知道做什么,便很徘徊。一旦有了这根弦,老是想着这个问题,就麻烦了。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一心一意地热爱语言工作,认准了这项事业,一辈子就干这个。
第二条是业务素质。关于业务素质,首要的是学会记音,这一关不容易过。记音时受母语的影响很大,母语中没有的音,往往记不准;母语中没有对立的音,往往听不出差异。像松紧元音、清浊辅音、舌面音舌叶音,很多学生听不出差异来。原理上知道有它的存在,但就是听不出来。又如声调,说北方口语的人,中平和高平区别不了。我有一个学生,下去调查后写的调查报告中,中平调和高平调总分不出,因为他的母方言里只有一个平声,而且这种感觉很顽固,难改。我让他反复辨别,他还是听不出差异来。还有其他的一些音,比如促声入声、长短音,都有可能区分不了。所以记音的能力很重要。高校语言学的培养,不解决记音的问题,培养不出好的田野语言学家。
施今语:应该怎样去提高记音能力呢?
戴庆厦:一个是要专门上课。光讲学理、大道理没有用,必须教大家如何听音辨音,练语音识别能力,如何整理音系。音听不准,音系就写不出来。我对学生就抓着记音、写音系这两条。通过记音再去挖掘语言的语法特点和其他特点。
现在有些汉语方言调查在这方面问题很大。我们做语言调查的时候,经常要拿前人做的调查材料来对照,有的时候就是找同地区的,甚至是他们找过的发音人来记音。我们将实际调查的结果跟他们出的书一对,发现记音错误太多了。从这些调查材料一眼就能看出,有些学生并没有受到精细的语音记音训练,记音和写音系的能力都很低,有些材料的准确率甚至不超过40%。高校对语言学学生的培养必须解决这一关,学生要是想真正地去搞方言调查、语言调查,必须接受比较好的专门训练,而且不能只是一次。但是现在《语言学概论》课时很短,语音部分教的很少,方言课有老师带着的实地调查不够,所以现在带出去的学生很多都不能准确地记录语料。当然,现在有视频和录音的存档,还好一些。一个语言点的音系整理,精细地做下去的话都要一个月以上。现在有的调查,一个月不到,20 来天就回来了。这样调查的材料肯定是不充分的。现在我招学生,只要有经费我就都带下去调查,去体会体会。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学生的人生观、业务观都会有变化的。
施今语:除了记音,田野调查还需要具备什么其他业务素质?
戴庆厦: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语言要有敏感性:要懂得怎么记录,怎么发现语言的一些问题;而且还要懂得如何从语言系统的角度来看某种语言的现象,不能把一个一个现象孤立看待。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文字能力。现在很多学语言学的文字能力不行,写出来的音系文章不符合规范,也不简练。这些年很多文章不修改几次,都发表不了,甚至有一些文章对基本的语言学概念理解都不够到位。外国也有这个问题,有些博士生在这方面也没有过关。总的一句话,培养一个语言学家很不容易。有一年北大办了一个青年博士生导师的讲习班,让我去给他们讲讲经验。我的重点就放在怎样培养有实际能力的博士生,有实际能力就是自己能够打仗,也就是能够自己调查语言、识别语言、解决问题,并写出好的调查报告。现在有的研究生,连个提要都写不好。所以我讲写作的时候,会讲怎么审题、怎么写提要这些基本问题。现在很多学生都缺乏这个能力,而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培养一个语言学家的道路上需要解决的。
四、民族语言大调查工作的开展
施今语:戴老师,上一次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是在20 世纪50 年代,当时您大学刚毕业就参与其中,贡献很大。您觉得从现在来看,那时的调查与研究是否有局限性?还需不需要再开展一次政府组织的全国性语言调查?
戴庆厦:这个问题很好。我们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是1956 年,国家号召开展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那时候为什么要搞这种大调查呢?第一,很多少数民族语言没有文字,他们的文化教育发展因此受到限制。第二,虽然现在说有130 种少数民族语言,但是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有多少种语言,名称也不清楚。后来党和国家就决定举行一次大调查,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民委两家一起负责。那时党和国家对调查很重视,我们在北京参加调查队的培训班,结业典礼上周总理和吴玉章都来了,我们很受鼓舞。当时我们在大礼堂里面听到后面怎么有点动静,一看是周恩来总理,还想是不是看错了。周总理在台上坐了好长时间,可见国家对民族语言的重视。所以我们叫那个时代是黄金时代。当时7 个工作队一共有700 多人,规模还是很大的。我刚刚大学毕业,在第三工作队。当时学校开研究生班,挑选我去读研究生,后来要参与调查,就先去调查。我在工作队从开始到结束有4 年,后来调查得差不多了,学校就把我调回来了。我去进行语言调查,接触语言,锻炼了一套本领,自己也写了一些文章。当时五六个人住在一间,不好写文章,我就跑到底下一个没人去的厨房写。这次语言大调查主要的收获之一是大体上摸清了我们国家的语言状况:有哪些语言,叫什么名字,方言有什么差别。后来根据调查材料出版了一系列的少数民族语言简志,是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书质量还可以,至少语音描写都还对,可惜的是有些简单了,因为出版时很多材料都被砍掉了。第三,这次调查培养起了一批骨干。我们这一批骨干就是那时候培养起来的,后来基本支撑了整个的调查工作。另一个大的收获是,这次调查在那个时代对民族团结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很欢迎我们为他们创造文字。
当然,这次大调查也有明显的不足。当时的条件比较艰苦,调查队员下乡要一律自己背行李,像褥子、被子,还有书。红河地区山很高,要自己背上去,走几步就在旁边喝几口山泉水再走。我们就是这么调查过来的。当然,成绩还是主要的,党和国家重视,地方也重视,调查队员也肯下功夫,各方面工作做得也比较到位。
施今语:您觉得是否有必要再来一次全国民族语言大调查?
戴庆厦:现在过了50 多年了,半个世纪了,语言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比如有的地方会双语了,有的地方母语有点衰变,还有的地方语言里面的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我们现在呼吁继续开展第二次全国民族语言大调查。大调查的主要目标是研究现代新形势下语言功能的变化和语言结构的变化。近些年我们利用“985 工程”项目也做了一些新的语言调查,出了一些书,但是还不够,如果能大调查就好了。如果好好地组织第二次大调查,就会有很多新的发现、重要的发现,尤其是现在社会发展得比较快,语言与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就更复杂了。
五、景颇语研究及其队伍建设
施今语:戴老师,您在景颇语研究方面付出了很多心血。我查了一下,关于景颇语的语音、语法、词汇等各个方面的研究,发现您竟然写了50 多篇论文,并且出版了《景颇语语法》《景颇语词汇学》《景颇语参考语法》《云南德宏州景颇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景颇语基础教程》等著作。这里想请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景颇语的现状。
戴庆厦:景颇语是我最早学的一种民族语言。我为什么热爱这种语言呢?因为它在藏缅语中有特殊的地位。过去美国一个著名学者白保罗(Paul Benedict)敏锐地观察到克钦语(景颇语在缅甸称为克钦语)在藏缅语中处于中间地位,上承下传。也就是说,这个语言中有的特点是古代的,而有的特点可以和后边的发展连接上,它处于一个中间地位。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支持白保罗的这个观点,因为它确实有古代遗留的特点,当然也处在中间地位。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古代汉语的复辅音是比较丰富的,在景颇语中变成了一个半音节。就是说,景颇语的一个半音节是从复辅音来的。比如一二三的“三”,在古代藏语是有复辅音的,在景颇语中就变成了一个半音节。而其他语言后来弱化、丢失了,像汉语中的san。另外,古代汉藏语中是有很多形态变化的,像人称和数的标记。到景颇语后,这个标记变成了虚词,跑到动词的后面,成了句尾词。现在句尾词又开始衰退了,存在的不多了。这也显示出来语言从形态发达到不发达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景颇是值得研究的,而且我也很喜欢研究它。
现在中国的景颇语使用者有10 多万,主要是边疆少数民族,都在边境线上。但是在缅甸有150 万,在印度还有五六万。景颇语的研究我做了近60 年的研究,与其他学者一起编出了两部景颇语词典:一部《景汉词典》,一部《汉景词典》。《景汉词典》(徐悉艰、岳相昆、肖家成、戴庆厦编著)收了1.5 万多词,约75 万字。这个词典的好处是用国际音标标注音,还标注了词性,所有人都能用。《汉景词典》(岳相昆、戴庆厦、肖家成、徐悉艰编著)所收条目包括字、词、词组、成语等共2.2 万余条、80 余万字,各条目都用汉语拼音方案注音。这两部词典都是年轻的时候上山下乡期间编好的,由我们4 个人共同完成。现在大家可以利用这两部词典来搞景颇语研究。
除了这两部景颇语的词典,我后来写了一部语法书、一部词汇学书、一部教材,另外还发表了四五十篇论文。这50 多年主要做了这些,打下了一些基础,下一步准备继续深入地去做,再写一部《景颇语志》,大约80 万字。但是现在事情太多了,只好慢慢来做了。
施今语:可以组织学生团队来做吗?
戴庆厦:但是现在没有接班人。学生不肯专门做景颇语,说这方面的文章戴老师都写完了。其实,我只是做了个开始,一门语言,值得挖掘的东西太多太多了。现在大家一般都愿意去选一些比较好做的选题。现在给博士生找到合适的研究选题也不容易,让他们自己找更难。如果学生在硕士期间受的训练好还行,如果受训练一般般的话,根本难以找到题目。所以现在招博士,要是基础不好招进来的,毕业都很难。我们民族语言研究,队伍本来就小,一旦断了线,接起来就更不容易了。
我是做南方民族语言研究的,现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研究队伍青黄不接了,后面接班人不足。我想培养几个景颇族的博士生,因此我现在还招生。但是一些小语种的母语人招不上来,每次都被外语卡掉了。应该考虑,我们这一辈老了以后怎么办,没有新的人才怎么办,而且人才培养还有一个过程。
六、保持小语种活力,促进语言和谐
施今语:下面我想了解一些关于小语种方面的问题。您在《语言使用研究在社会语言学研究中的地位》这篇文章中谈到有一些小语种,虽然说的人很少,生命力却很旺盛,比如景颇族波拉支系只有500 余人,却也能稳定使用自己的母语波拉语;而有些民族,虽然人口很多,他们的本族语言却衰落得很快,比如满语。这让我非常好奇,特别想知道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戴庆厦:过去认为语言的活力主要是受了社会条件、民族心理(也就是对语言的认同度)的影响,还有族际婚姻的状况(比如族际婚姻规模小)。实际上或许有些问题还没有认识清楚。为什么有的语言说的人很少却不濒危?像我调查过的波拉语,只有500 多人说,还挺活跃的;云南西双版纳基诺山区的语言也只有约3 万人说,也挺活跃,生命力很强。但有些语言人口并不少,却出现了濒危情况,像满语。这可能跟社会条件、民族认同、杂居分布等相关。我们中国进行语言濒危研究最开始是跟着外国的研究来做的。他们的理论和观点进来以后,对我们重视和研究濒危语言现象当然有推动作用,但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还不能完全用外面的理解来解释。我们中国语言的濒危没有国外估计的那么严重。外国估计在21 世纪可能有80%到90%的语言都会消失,但是我做这方面研究这么多年,感觉没那么严重。像景颇语我去调查了很多次,都保持得挺好的。白族社会比较发达,和其他民族通婚也多,但是白语还是保留得很好的,没有大片大片的人不说了的情况。还有像怒语和独龙语基本上都保留了。这都是用外来理论解释不了的现象。而且我们还提出了“语言复苏”这个概念。像普米语,当时在云南的中间这一代不会说了,但是我们调查发现,现在年轻的一代又会说了。这是因为国家少数民族政策的作用,提倡学他们自己的语言,所以这一代家长让孩子学,小孩学一下就会了。这就是语言复苏了。
在我研究的少数民族语言中,就语音系统来说,普米语是最难的一种,有舌尖、卷舌、舌叶、舌面四套,还有很多复辅音。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提出我们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濒危语言研究体系,不能外面怎么喊就跟着怎么喊。盲目追随,对我们是不利的。网上有的说中国90%的语言都处在濒危状态,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其实,有些濒危的标准并不是根据使用活力来确定,而只是简单地根据使用人数多少,比如日本的标准是使用者在5 万人以下的语言都属于濒危语言。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有很多语言,说的人不到5 万,但并不濒危。这是以实际调查为依据的。为此,我提出判断一种语言是否濒危需要有一个综合的评议标准。这样的话,我们很多语言不能算濒危。像基诺山的基诺族,我问他们基诺语会不会濒危,他们的长老说不会,天天都在用,至少100 年不会濒危,他们和语言是有感情的。有的小孩在家里和爸爸妈妈说汉语,一开始不会基诺语,后来大一点跟别的小孩玩着玩着就又会这种语言了。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后来我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衰变语言和濒危语言的区别。前者虽然在衰变,但是可以救活,真正的濒危语言是救不活的。我们要创造条件保持小语种的活力,最主要的是要让学的人觉得有用,对工作对生活都有用,对维系民族感情传播民族文化有用。这也是语言和谐的重要方面。
施今语:通过阅读您的文章,我认识到语言和谐往往跟社会和谐、国家安全等方面密切相关。请问语言和谐主要指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构建语言和谐呢?
戴庆厦:语言和谐主要指的是语言之间互相尊重,不歧视。语言关系比较好,语言的使用比较协调,这些都是语言的和谐。语言和谐可以研究历史上的语言使用状况。在我们历史上,语言使用有它不和谐的时候,但主流还是和谐的,老百姓的语言生活还是比较和谐的。现在我们研究语言和谐,要建立一套理论,比如怎么区分它的主流和支流。要实现语言和谐,一个很重要的点是社会道德。我去新加坡时发现,当地虽然有多种语言,但是不利于语言和谐的话是不敢说的。当时有位司机跟我们说,人家语言的使用是有自己的道理的。我们目前还没有完全形成这方面的社会道德,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要达到语言和谐很难。所以要多宣传,多采取具体措施来实现民族和谐、语言和谐。比如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一些民族语言的衰退就是必然的,所以没有必要特地去保护它。这样想的还不少。语言资源不保护,将来后代人要给我们算账的。我们要从有利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来考虑民族语言的使用和发展。
七、跨境语言调查与研究
施今语:戴老师,针对跨境语言的研究也一直是一个您很关注的领域,请问对于跨境语言的研究和非跨境语言的研究有什么不同?
戴庆厦:我以前接触过一些跨境语言现象,有过初步的观察。我们开展大规模跨境语言研究是最近十来年才开始的。我对跨境语言的兴趣跟我自己学的语言也有关系。如景颇语是跨境语言,外国叫克钦语,那时候中缅两国人来来去去的没有限制。经过接触,我觉得跨境语言状况和国内民族语言不太一样,应该研究。改革开放以后,我就考虑开始研究了。那时候我当系主任,就组织了一些老师写了一本书《跨境语言研究》。后来经费不够,就出了小小的一本,十几万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 年出版的,没想到这本书就成了我们国家研究跨境语言最早的一本书。这本书出版以后,尤其是到了“985 工程”时期,我们这里进一步组织了跨境语言研究项目,当时是国家语委的重点项目。我们一共做了10 个项目,出了10 本书。到了后来国家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所以就这么展开研究起来了。
我们下一步应该是建立自己的跨境语言研究理论体系。我们国家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多,现在北京语言大学也在做,叫周边语言。周边语言跟跨境语言这两个概念所指的范围有交叉。这些都值得深入地往下做,而且时机也比较好,经费也比较多了。
施今语:我了解到您去过泰国、老挝、缅甸、哈萨克斯坦等好多个国家去做跨境语言调查研究。
戴庆厦:是的,都去了。泰国我去了好几次,现在也还在研究老挝的。跨境语言研究的意义非常重要,不仅是对语言学有好处,对国家安全、经济建设、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都非常重要。
跨境语言研究在方法论上有很大的特殊性。这些语言之所以叫跨境语言,不只是简单地指一种语言跨越边境,而是重在语言的变异是由国家界限造成的。它跟方言不一样,因为方言是国内的地区差异造成语言的变异。在跨境语言研究中,由国家因素造成语言的变异都有哪些、是怎么造成的、跟不同国家的政策有什么关系等,都是我们跨境语言研究的主要的内容。这些是独立于其他研究的,因此研究方法上自然也就不一样。
研究跨境语言,第一条是要换位思考,不能用我们这边的情况去思考他们的问题。比如老挝提出过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中国有少数民族,有主体民族,但是我们老挝没这个提法。我回答说,这可能是因为我们中国的特定条件,我们民族比较多,而且少数民族人口少,汉族多,所以要研究主体民族如何去帮助少数民族,而老挝那里各个民族的人数差不了太多。所以我们要建立自己的跨境语言研究,也要从对方国家的角度来考虑。当然还有具体的问题,比如我们到其他国家以后,要怎么向他们的管理机构交代清楚我们的任务,不交代清楚是不行的,很多时候语言问题牵涉到国家安全问题,而且语言调查是必须直接到当地接触普通人的。这些方面,我们都有一套经验了。
再一个是,在调查跨境语言的时候要克服语言障碍,我们要带好几个翻译下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跨境语言调查和研究,我们做了不少思考。在此基础上,我们团队写了一本《语言国情调查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出版的。最近我在和一些学生讨论写一本《跨境语言调查概论》,再来做一个小结。
目前,在跨境语言中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做的。比如说跨境的汉语,现在做的人少。但是我觉得国外的汉语中的有些特点,对我们研究国内的汉语会有很多好处的。这个领域将来可以好好考虑,现在研究得不多。
又比如我刚才提到的换位思考,在研究语言本身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在研究海外华人的汉语的时候我们要想着怎么从他们的体系出发,从他们那个交际系统来看这个语言的特点,而不能纯粹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像邢福义先生有一个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全球华语语法研究”,在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特区等设点,每个点做一个专题研究,主要就是描写语法。但是他们的海外华语研究和我们的跨境语言研究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海外华语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一个一个独立的点,较少关注相互影响的问题,而跨境语言研究的重点就是看两边如何既相互影响又独立发展的。
施今语:实际上互动性要更广更深入一些。
戴庆厦:是的,重视跨境语言的相互影响,是研究的基础。我们的研究可参考的理论方法并不多,更多地需要自己去探索。
施今语:您刚才也提到为了跨境语言的研究,您到访过很多国家,编了一系列的丛书,如《哈萨克斯坦维吾尔族及其语言》《缅甸民族及语言》《老挝的民族及语言》等十几本。这一系列周边语言状况丛书汇集了那些国家的语言、社会、文化情况,让人们对这些国家有了更多了解。编撰这类书籍有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吧?
戴庆厦:这个问题问得好。一个是要特别注意当地的敏感问题。边境问题是非常敏感的,碰到时要慎重,有的时候要回避。比如画地图,交界处就要很小心。
再一个是,一些年轻学者去写材料时,容易流露出一些看不起小国家的口气。我们在调查之前就和学生(大部分去的都是学生)说清楚,要尊重当地的民族。另外,去调查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必要的手续。比如我们去泰国调查都是经过当地教育部允许的,需要有证书。有的国家还不允许你去搞类似的调查,尤其是语言调查容易被认为和国情调查结合到一块去。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们去泰国第一天,当时陪同的是清莱皇家大学一个教授,我跟他说是不是应该和当地保安局打个招呼,他想想说可能要,保安局的人就不理解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后来有天我们跟他们开会,很客气地解释说我们是响应联合国的号召,做民族调查和语言调查之类的。那个局长很开通,说:“很好,我们也要好好研究。”我们便说:“你们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话,我们一定配合。”这样问题一下就解决了。正好我们这个项目挂靠了泰国清莱皇家大学,他们派人来,这样我们就放心一点。当然还有安全问题,各个国家不一样。当时在老挝比较方便,我有一个博士生和一个硕士生是老挝人,当时还没毕业,所以赶紧在他们毕业前把老挝的跨境语言研究做完。我去调查时,腿不好,学生就帮忙开车来接我们,要去哪个寨子就帮忙带着去。他们也和当地人说我是他们的老师,这样其他的人对我们就都很尊重。
等这个跨境语言调查项目做完,我们准备好好总结一下,搞一个概论,把教材建设提上日程。虽然我们现在的研究很初步,但是可以慢慢完善。
八、语言对比研究的新视角
施今语:除了具体民族语言研究,您还做了很多汉藏语言对比研究,通过与汉语的对比来反观汉语的特征,如您2017 年发表的《再论汉语的特点是什么——从景颇语反观汉语》,对我非常有启发。相较于单纯的汉语研究,汉藏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有什么样的优势?在哪些方面容易有重大发现?
戴庆厦:我多年以来,一直觉得汉语研究要有非汉研究眼光来反观。这条原则实际是我们师辈朱德熙先生提出来的,我们的祖师爷李方桂先生也说汉语里面有多少问题都要靠非汉语来解决。我接受了大师们的精辟理论,将理论应用到我的工作中,确实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我写了好几篇关于汉语和非汉语的结合、反观的文章。汉语里面有的新现象可以借助非汉语来去发现。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马庆株先生关于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的研究。我们当时办了一个藏语学习班,那时候我是班主任。马庆株先生也参加了,我们讲的是藏语的情况,他很有心,听后去研究自主和非自主在汉语中的表现,写出了一篇重要文章,这篇文章最后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又如梅祖麟先生谈到的汉语使动范畴,也参照利用了非汉语中使动范畴所具有的丰富形态表现,这就很好地解决了使动范畴的内部系统问题。还有很多其他的对比研究,都能够揭示一些汉语的新现象。
最近我又从这个角度在思考语言类型的问题。过去我很朦胧地感觉到,动结式可能跟语言的分析性有关系。因为分析性语言动补结构比较发达,比如汉语,但是阿尔泰语就没有动补式,不会说“打死”,只能说“打了死了”。为什么汉语动补结构这么发达,我感觉跟分析性有关系。我们亚洲语言里,有很多分析性语言,单音节比较发达,在这些语言里,有的动结式很发达,有的不怎么发达,为什么?我们发现,形态丰富一点的语言,动结式就没那么发达,而汉语中动结式超发达。后来我们就考虑到可能跟分析性有关系。就是说我们研究这些语言,要从分析性的眼光来研究。由于我懂这些分析性语言,将它们拿来跟汉语一比较,发现它们的分析性程度不一样,因此相关特点就也不一样。
施今语:这就是独特的视角了。别人可能用印欧语的眼光来看汉语的分析性,您是从分析性程度差异来看汉语特点。
戴庆厦:对的。之后这方面就引出了很多想法和论题了。比如为什么汉语离合词丰富,别的语言很少;为什么汉语的虚词丰富,比其他语言更丰富;为什么汉语的歧义现象多,而我研究的其他语言歧义现象就没有那么复杂;还有汉语词类的模糊度问题。这么一想,我觉得汉语可能和其他的语言不太一样,后来就在你刚才提到的那篇文章中提出了“汉语是超分析性语言”这么一个观点。文章发表以后很快就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了,可能他们觉得有一定的道理。现在我的一些学生根据这个思路来做对比研究,看看有什么不一样,比如从普米语、载瓦语、浪速语等来反观汉语,能够看清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准备展开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施今语:有一个大的观念,看问题的角度就不太一样了,因为将程度、层次的观念渗透到类型学研究当中了。
戴庆厦:是的。以前基本上就是分类中即使讲程度也是偶然举例性的,没有一个系统去考察它的程度的差别,阐述这些程度差别背后的机制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就想看能够不能够为汉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挖掘出更多的东西出来,这就比单纯的语言比较进了一大步了。现在回想一下,我们有些做印欧语研究的人来看类型学,很难脱离印欧语的系统来分析汉语这样的分析语,有的观察就会不太准,就是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我不久前去上海开了一个虚词会议,张谊生先生的副词研究做得很好很细致。另外王珏先生做的关于语气词的报告很精彩,说得很细,这里面就体现了超分析性语言里面的特点。分析性语言往往语气词比较发达,词的隐藏语义比较丰富,所以还很值得从类型学的角度去看看。
现在有些问题还得要有一个新的视角去看。像语言接触也是个问题,过去是看不到、看不清,现在有的地方却扩大化了,同样不容易看清实质。所以语言接触怎么做,还需要进一步考虑。
施今语:戴老师,现在民族语言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冷门,很多普通人甚至学者都对民族语言了解很少。您觉得应该如何扩大汉藏语研究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了解甚至参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戴庆厦:我们过去的师辈都在呼吁结合民族语言来研究汉语。从早期的李方桂先生、赵元任先生、罗常培先生,到后来的朱德熙先生都一再呼吁要打破汉语研究和非汉语研究的壁垒。朱德熙先生认为现在的专业设置不合理,汉语和非汉语隔开。他后来把我们请去北大讲了3 年的课,讲汉藏语系中的非汉语情况。这个结合很重要,但确实不容易。我们搞非汉语研究的,汉语的成果我们非常注意。像那些汉语研究的杂志,《中国语文》也好,《语言教学与研究》也好,我都会读的。我后来跟他们说,你们搞汉语的没有像我们这些做民族语言的重视另一边的理论发现。我说你们再重视一点就好了,当然可能汉语的内部工作量太大了。鲁国尧先生有一次跟我说,能不能跟他谈谈怎么利用少数民族语言来研究汉语。李方桂大师是搞古汉语出身的,后来做侗台语之后,成为非汉语研究之父,所以李先生他应该有很深的体会。可惜的是李先生去世太早了,如果再晚几年,可能对整个汉藏语都会有一个新的想法。
所以两边要结合,但是到底怎么结合,可能两边要慢慢向对方靠近才能解决。当然现在有个好处,学生比以前多了。现在做汉语的一批人也来慢慢做我们这个,比如潘悟云、吴福祥、储泽祥等一批学者都做得很好。如果要结合的话,还需要多会一些语言。像李先生他会许多语言,他20 世纪40 年代的记音到现在都还没有被发现有错误,非常厉害。李先生对每个语言都容易掌握,要培养这样的语言学家。我们逐步接近,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要两条腿走路。现在要学科结合,不同语系的结合,必须有不同领域的知识,这样才能成为大家。
九、寄语青年学生
施今语:戴老师,最后再耽误您一些时间。请问作为一位著名语言学家,您能否对我们青年学生表达一些您的希望和心愿?
戴庆厦:现在我们隔了几代了。一些年轻人和我们的想法有时候不太一样,但各有长处。我觉得语言研究大有可为,希望大家求实、勤奋,做一个真正有本事的、有实力的语言研究者。我现在就按照这个来要求我自己的学生。
施今语:做您的学生真幸福,做学问、做人都能受到全面的熏陶。
戴庆厦:其实,其他要管的事还是很多的,找工作,甚至找对象,都要关心呢。师生几年,已经有很深的感情了,学生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了。
施今语:真是羡慕您的学生,再次感谢您能接受这次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