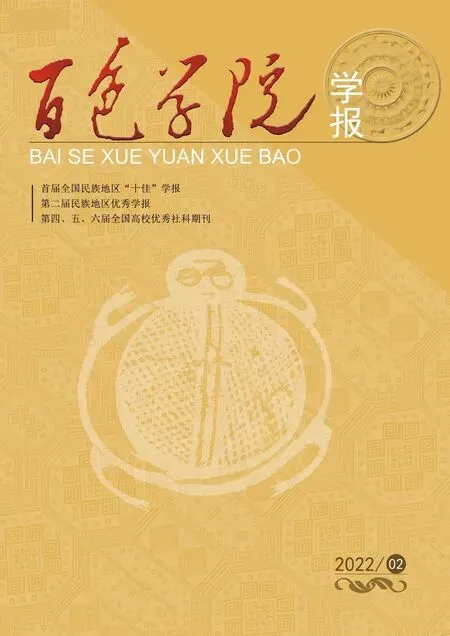文学人类学“四重证据法”的应用实践
——读《禹赐玄圭:玉圭的中国故事》
柴克东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唐启翠的新著《禹赐玄圭:玉圭的中国故事》①唐启翠:《禹赐玄圭:玉圭的中国故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以下引用此书,只标出页码,不另加脚注。于2020 年12 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唐启翠近年来研究“玉文化”的重要成果,也是对文学人类学相关理论的运用实践。我们首先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然后重点对其使用的方法论(四重证据法)进行简要评述,方便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一、著作的主要内容
该书虽题为“故事”,但实际上与民间文学课堂上的“故事”概念有所区别,将其理解为“神话+历史”的新建构故事,才更为贴切。近些年文学人类学派倡导用“神话历史”[1]定义那些在神话观念支配下记载的中华历史叙事,唐启翠此书中的大部分“故事”,均可作如是观。
该书总共有8 章。第一章“禹赐玄圭:创世神话的重演”是全书引论,后面七章的论点皆由此引出。首先,作者论证了治水神话与玄圭圣物在作为古代王权神授、王权更替观念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原型作用,然后结合考古遗存和前人研究成果,对大禹治水神话产生的时代背景作出合理推测。作者认为,始于公元前2400 年至公元前2100 年间的生态环境恶化、气候异常,导致我国多地区发生大洪水灾难。大禹治水神话正是先民对这些灾难进行神话加工的历史记忆,由此可以证明,大禹治水不是文人创作的虚构事件,或有着真实的历史原型存在。
其次,作者对大禹治水神话所体现的开创新纪元意义作出梳理,可简化为“王天下”“袭王位”“立王政”三大要点。西周以降文献中出现的禹铸九鼎、天赐玄圭等神话传说内容,都是对华夏国家级王权初始建立的这三重意义的演绎。
再次,作者对大禹治水所蕴含的创世神话意义做出阐释。作者指出:“通过讲述令人难忘而权威的关于万事万物如何起源,创世神话提供了一个普遍坐标,通过这个坐标,人们就能够在一个更大的框架里想象自身的存在,并且扮演自己的角色,从而满足人类深层次的定位感和归属感。”(第12 页)由这个认识出发,作者认为鲧禹治水神话是对华夏创世神话的重塑,或可称为“二次创世”的神话。其中既有来自原初创世神话叙事的主要母题(如息壤等),也充分蕴含着华夏政治传统和历史开端的核心内容。
第二章“玄圭寻踪:重返夏朝”,具体展开对“玄圭”的实物原型考证。作者指出,玄圭原型与一种被称作“牙璋”的玉礼器有关,其得名“玄”之原因,体现的是史前时期的“玄玉崇拜”传统。而对这种玄玉崇拜的再发现和再认识,构成上海市社会科学特别委托项目“中华创世神话考古研究·玉成中国”丛书的第一部著述的主题:叶舒宪教授著《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能够从第四重证据即考古出土的中原地区玄玉实物标本为证物,提出史前期曾经存在一个延续1000 多年的“玄玉时代”。而夏禹时代的玄圭圣物,已经属于这个“玄玉时代”延续千年后的尾声阶段了。随后,就是大量优质白玉登上中原国家礼器建构舞台的夏商周三代。从石峁遗址到二里头遗址,再到安阳殷墟,以优质透闪石白玉资源为首的浅色调玉礼器新传统,像推陈出新一般,全面取代了史前流行中原地区的“玄玉”老传统。这种对无文字时代历史现实状况的新探索,完全依赖文学人类学派的方法论“四重证据法”。唯有“玄玉”这个名称,是出自第一重证据的先秦古籍《山海经》叙事。把玄玉、玄圭、玄璧、夏人尚黑,玄而又玄,墨家尚墨,龙血玄黄,天玄地黄,所有这些零散的上古文献信息整合为一体,中华文明探源的研究瓶颈得以被突破,文学人类学的学者团队终于打开一片全新的天地。这些知识考古的新认识,确确实实都属于以往所未知的“中国故事”。
该书还尝试从甲骨卜辞中寻找“玄圭”的文字符号,指出圭之祖型为史前手斧,在经历龙山文化晚期至夏商时期的演变后,最终成为考古遗存中常见的三角形标准器。在作者看来,遍布古代中国的中原核心区及边缘地区的深色系牙璋,可能是迄今所见与“玄圭”最为契合的玉礼器。这是非常大胆的一个推论,目前玉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处于比较朦胧的认识阶段。大家比较有共识的观点是,玉璋这样的特殊大件玉礼器,能够出现在距今4000 年上下的历史时期,既不早也不晚,这显然不是偶然现象。玉璋能否成为国际学界始终存疑的夏代是否存在过的重要实物证明,应该是未来学术攻坚的一个主方向。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香港中文大学考古与艺术中心合作编出的大书《牙璋与国家起源:牙璋图录及论集》[2],对这个方向做出先驱性的讨论,值得参考。既然那个时代还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历史信息,我们只能依仗第四重证据来做系统研究,尽可能地让“物的叙事”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第三章“斧始初开:玄圭与创世神话”通过对大禹治水与创世神话文化内涵的解析,为玄圭脱胎于玄钺(斧)的论点提供了神话学证据。作者指出,用斧子劈开混沌世界使天地分离,体现了创世神话的核心要义——时空秩序的形成,这一神话母题在世界范围内也相当普遍。由此神话母题为依据,作者指出在中国各民族广为流传的盘古开天辟地神话和大禹治水神话中,斧凿也是创世和治水的核心工具。至于从斧到圭的转变,作者从文献所载的“析神”“青圭”等圣物的象征意义中找到了依据。作者指出:“新石器时代,一身多能的斧分化出了象征身份权威(父权、军权、王权一体)的钺与璧,龙山文化时代前后,又从玉石钺分化演绎出圭(戈)与璋,象征王权神授、臣权君授的等级序列和人神之间沟通的圣物。”(第50 页)在作者看来,从玉钺到玉圭礼器的转变,反映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武力征服到文明时代的威德兼施的国家权力转变的历史进程,这一过程同样体现了中国古人将创世神话和治水历史熔铸为神话历史,从而为神权—王权统治传统奠定合法性的努力。
第四章“天命符瑞:‘禹赐玄圭’的历史演义”具体分析了传世文献对禹赐玄圭神话的版本演变。从《尚书·禹贡》中的“告厥成功”之圣物到“二十四史”中象征天命转移的“受命”之物,玄圭作为符命的象征意义已经成为古代王权统治的神圣保障。同时,在一些诸子作品和谶纬著作中,也充斥着诸如“赤乌衔圭”“河图洛书”等将圣物显现与王朝兴亡关联在一起的神圣叙事。
第五章“执圭以告:天人沟通的圣器”以《尚书·金滕》所载周公“植璧秉珪”的传说为出发点,同时结合考古实物和经传记载,对古人的“执圭”之礼作了考证。作者认为,圭璧组合在古代中国的玉礼器传统中占据核心地位,其神话内涵与祭祀先祖有关。在作者看来,“祼圭瓒宝”是周人使用的祭祀祖先的玉礼器,虽然目前对这些玉礼器的命名和考古实物还无法完全对应,但它们所体现的通过祭祀与神灵沟通的天人合一思想,却是确定不移的。作者还从“丰碑石函”的文化编码中溯源了玉圭作为中国礼制文明的影响力和渗透力:“祖庙、神主、墓碑、祭器、祼器和系列祭祀仪式都是子孙后代与祖先沟通的重要物化符号和形式”(第124 页),它们无一不体现玉圭、祼圭的文化内涵。
第六章“析圭而爵:禹赐玄圭的人间扮演”重点论述了“析圭”“命圭”等玉礼器在任官授爵时发挥的圣物作用。作者对传世文献中的“执圭”这一个关键词作了统计,指出“执圭”已成为后世任官授爵的代名词。执圭者身份从早期的王侯下移到了唐宋元明清时期的普通官员,这一转变反映了“玉圭”至高无上的神权色彩的褪去以及其作为“瑞器”而彰显君子身份功能的转变。同时,作者考证了西周金文常见的“反入觐圭”,认为其中蕴含了两周时期周天子与诸侯贵族之间的从属关系。在本章的最后两节,作者结合传世文献和考古新发现,对“执圭”之仪的具体细节作了还原。
第七章“神秘土圭:测天量地的玉圭金臬”重点对《周礼》记载甚详而又众说纷纭的“土圭”作了考证。在作者看来,“土圭”之所以频频出现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度量衡词汇中,与其蕴含的深层思维惯性和文化密码有关。土圭、玉圭、玄圭之间存在关联,并且作为度量工具的土圭在王权象征符号体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作者指出,“土圭测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约8000 年前新石器时代,这一行为体现的是先民对“天地之中”的重视。同时,体现“地中”神话地理观的土圭、执中与执圭还包含有创世神话的影子,这一文化密码可能就隐藏在凌家滩的玉龟玉版中,也暗含在《尚书》“建极绥䣭”与“允执厥中”洪范大法中。
第八章“如圭如璋:玉圭与君子风范”对书写文献中“君子比德于玉”的观念如何具象化为圭璋,结合历史人物典故,将诸如圭璋特达、圭璋挺惠(德才卓绝),圭角岸然、圭角不露(不同的两种君子然皆风骨贞洁),白圭之玷(有缺陷的完美),三复白圭(慎于言行),筚门圭窬(贫贱不移)等君子之德进行了钩沉、阐释。与前几章形成了有机关联,前几章为溯源,此章则可谓追流。本章对有关“玉文化”信仰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学人类学派“知识考古”的特征。
二、著作对“四重证据法”的创新性运用
认识到“玉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并对其“神话历史”内涵进行发掘,是文学人类学团队近些年来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在这一方面发挥带头作用的是叶舒宪教授。自2013 年开始“玉帛之路”系列考察活动以来,叶教授先后提出了“神话中国”“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说”“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再统一中国说”“万年中国说”等系列理论命题。[3]这些理论已在文学人类学内部引起巨大反响,并且也逐渐被其他文史领域的学者所关注。
唐启翠的这部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全面运用“四重证据法”的创新性研究实践,其中当然也包括唐启翠个人的理论突破意识,这表现在对玄圭的实物原型——玉璋的探索方面。实际上,在这部著作之前,唐启翠已经公开发表多部(篇)与玉文化相关的研究成果①参见唐启翠:《“土圭”命名编码的神话探源》,《民族艺术》2021 年第1 期;《礼器神话:中国礼制话语建构的信仰之根》,《文学人类学研究》2019 年第1 期;《大小传统互证互释:以“三礼”匕箸进食礼仪为中心》,《百色学院学报》2018 年第2 期。,选择“禹赐玄圭”这一频繁见诸经传的神话历史叙事内容,体现出唐启翠深厚的文献考据功力及其对考古学新知识的谙熟。
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玄”色无疑是具有神圣意味的颜色②参见叶舒宪:《玄玉时代钩沉:四重证据法的新尝试》,《安徽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 年第1 期;《认识玄玉时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年5 月25 日;《夏商周与黑白赤的颜色礼俗:玉文化视角的新解说》,《百色学院学报》2017 年第1 期。,而“黑玉—玄圭—大禹—夏王朝”这一历史脉络在传世文献中也在在可见,《禹赐玄圭》中的相关论述,基本上是按照这一脉络展开的。有些学者对文学人类学近些年提出的各种理论有些不解,但是,当我们了解到当前上古史研究存在的诸多瓶颈和误区的话,就会对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报以尊重和理解。毋庸讳言,在中国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中,当考古资料与历史记载出现冲突时,有的学者们更倾向于用考古资料去迁就文献记载。为了弥补这种方法论缺陷,文学人类学派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增加了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图像两重证据,形成“四重证据法”方法论。
“四重证据法”是一种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它致力发掘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民族志、实物图像之间的证据间性作用①“证据间性”这一概念由孟华先生提出:“所谓证据间性,是指一种证据符号的意义和价值不仅与原点事实有关,同时也与其他证据符号发生关联和交互作用,一种媒体类型的证据符号是在与其他媒体类型证据符号的对比或关联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的。如果说传统三重证据法重点关注的是实证问题,那么符号学的三重证据法更关注异质符号之间的互证即符号间性问题。”详见孟华:《符号学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在证据法学中的应用》,《证据科学》2008 年第1 期。,通过实证和阐释的互动原则,探讨走出古史研究的瓶颈和误区。唐启翠在本书中使用的方法论,正是“四重证据法”。不难发现,促成本书前七章结论的主要依据均来自第四重证据——考古实物,而其他的三重证据只发挥阐释作用,这正体现了“四重证据法”的“物证优先”原则。[4]众所周知,赋予具有象征意义的人工制品以某种含义,在考古学上是常见的问题。一般而言,象征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传统上而非逻辑上的关系,这就要求对这些象征意义的解读不能脱离其诞生的背景。以《禹赐玄圭》所讨论的“玄圭”为例。考古发现的“玄圭”主要集中在甲骨文诞生之前的2000 年内,与具有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一样,玄圭的颜色和形制具有唤起人们特定联想的功能。唐启翠在综合其他三重证据之后,尝试将玄圭与中国史前时期创世神话关联起来。由此可见,在本书论述过程中,玄圭作为物证主要发挥实证的作用,此即“物证优先”原则。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以及民族志资料则主要发挥阐释的作用。实证与阐释的互动,使得“四重证据法”既避免了用考古资料去比附传世文献的先入之见,又突破了古史辨派遗留下来的中国上古史真伪难辨的方法论瓶颈。
“四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中所发挥的“预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在面对众多学科知识面前,难免有人会望而却步,但对于真正想要突破古史研究瓶颈和误区的勇士而言,必将在艰巨的学习过程中获得视野大开的喜悦。笔者相信,只要越来越多的学人投身到这股跨学科潮流之中,相信百年之后“二重证据”或更放异彩,而“四重证据”也必能扬光,不断取得攻坚克难之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