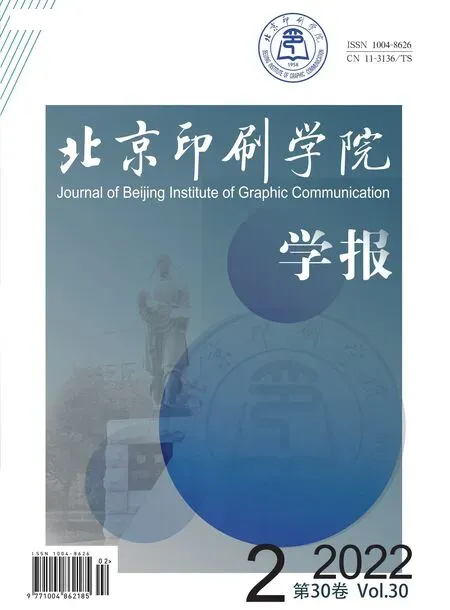王安忆文学作品中服饰书写的艺术张力与思想性研究
曾 雪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商贸管理学院,合肥 230011)
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中所采用的不同艺术张力所体现的艺术价值也是不同的,在刻画一些重要场景的同时,需要借助大量的外在因素描写来衬托当下的复杂面貌和具体形态。一旦人物的性格和时局因素在文字中定格,多角度的外在要素描绘所展现的艺术张力将左右整个故事线的连贯性,并通过艺术气息来烘托作品的主旨和思想描绘。王安忆文学作品中大量服饰书写的文字,不是为了堆砌和滥用优美而浮夸的词语,而是通过一定艺术思想价值来架构这个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在作者的描绘中,跃然纸上的不仅仅是对服饰的刻板印象,同时也是作者生长环境和生活氛围的另一个缩影。
一、王安忆文学作品中服饰书写的格调渊源
(一)从服饰书写的文学内容透视功能性结构要素
王安忆的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穿着、打扮、服饰、配饰等方面的描写,似乎在描绘一个个灵动的人物,同时也涵盖着整个社会的风貌。即便是日常生活和平淡作息,也能够在她的书写中展现无尽的韵味和悠长的思想风貌。王安忆认为服饰是人的另一种精神面貌,同时也是建构人类文化体系的自在逻辑积累。服饰从最原始的人类遮羞和抗寒的指向性工具,而逐渐能够被作家挖掘出其深层的文化要素和成体系化的组织结构。无论是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都可以从文字的描述中找寻服饰的功能性结构要素。服饰书写的文学内容在刻画人物性格、展现人物特征以及凸显人物阶层等方面都能够表现超高的作用力和影响地位。王安忆在文学作品中对服饰内容的具体刻画,展现了其作为现实主义人文关怀者的真实风貌,也使得其较多作品展现出现实主义色彩。
在具体描绘中,借助于服饰和衣着的打扮,王安忆所刻画的具体人物都有着具体的身份和具体地位,在写作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服饰对人物当下特征和人物未来走向的影响,结合具体事件和背景的描述,可以看出王安忆对服饰内容的描写不是随意的内容覆盖,而是从基本的功能性结构出发来探究其真实的人物特性。并从自在角度来具体刻画其真实样貌。这种描述能够让读者明确把握住该人物以及该人物所代表的一类群体,他们所具有的特殊精神和内在特质。
(二)从服饰书写的地域风貌透视标志性民俗生态
对于王安忆的文学作品,其最大的特征以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海民俗风貌的展现,因此王安忆被称为“海派传人”。王安忆的文学作品甚至被用来解读当时时代中上海真实风貌的现实材料。与此同时,也有读者称王安忆为张爱玲风格的传承人。虽然王安忆本人否认这一说法,但毋庸置疑的是,王安忆的服饰书写与上海的地域民俗是紧密相连的。
服饰在王安忆的文学作品中不是单纯的颜色和款式的描绘,而是用来判断和分析阶级构成和社会形态的民俗生态标杆。19世纪末的上海,已经逐渐发展为全中国最为先进和发达的城市之一,在上海随处可见的阶层差异触动着这个城市的民俗风貌也同样指示着每一个生活在其中之人的内在神经。服饰的简陋和精致是判断生活水平的初步标准。服饰也在刺激着整个城市的民风和民意,不管内在是否低贱和没落,一定要光鲜亮丽地走在大街上。在其长篇小说《桃之夭夭》中,即便是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每日起早贪黑摆小吃摊挣一份辛苦钱,但为了出门在外的儿子,也要拼尽全力去为儿子挑选上等的服饰,这就彰显了服饰作为虚伪的外衣已经深入社会风俗中成为人们争相追逐的目标。
(三)从服饰书写的内在韵味透视传承性古典元素
在王安忆服饰书写的内容表现中,其内在韵味和手法的拿捏是如此恰到好处,并能够通过古典诗词等作品来突出人物性格和人物的内在心理活动。在《长恨歌》中更是穿插了戏曲的描绘手法,让作品的整体风貌不断透露出古典元素的精心雕琢。这不仅展现了王安忆才情和创作水平的高超,同时也展现了其对古典文化和古典美学的精辟吸收以及合理运用,这种信仰和尊敬,也透视着对传统古典元素的继承和发扬。
王安忆认为,对于古典元素的吸纳,要保持着敬畏的心态,同时要放弃对古典的质疑和批判,通过吸纳精华来逐渐提升其传承性的历史风貌。在为大学生们上文学欣赏的课程中,王安忆推荐学生们去阅读《红楼梦》,这本书对王安忆作品的影响不仅是长远的,同时也是深刻的。《红楼梦》不单纯是在描述家庭伦理生活,也不是在戏说当时时代中特殊人物的特殊情感,而是具备着丰富文化内涵和雅致风貌的美学艺术品。她的文学作品中所表达的风雅面貌也是渊源于《红楼梦》所带给她的无尽灵感。[1]
二、服饰书写的艺术张力
(一)以服饰书写的视角窥探人物心理因素
在王安忆的作品中,服饰书写作为一个合理的视角能够带领读者来窥探人物的心理发展历程,并充分拓展读者的思维,从艺术影响力的角度来抒发人物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内心独白。[2]从心理因素中烘托出人物的典型形象,并赋予人物在服饰书写的范畴之下更深刻的生命力,为读者打开文学思维的天窗。
在《天香》中,对初次亮相的闵女儿服饰的描写就极其素雅,绫子材质的白色裙子展现了闵女儿单纯、清新的一面,裙底的碎花又呈粉色,这就突出了一个待字闺中的少女清秀得如同含苞欲放的花朵。这时的闵女儿才十四五岁,其心理活动是单纯而害羞的。但在其嫁入申家做妾之后,其心理状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看到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相处模式以及不同的待遇之后,其内心也变得僵硬和冰冷起来。[3]在其外出之时,作者着重突出了其身穿的藕色衣裙,从服饰的描写中突出了其悲凉和孤独的心态,以及深处人事的漩涡之中不知如何自处的茫然与静默。但最终因为其绣工出彩,也在大家庭中获得了一定的地位,所绣衣裳的精美之处的描绘让人物心理不断发展,从人物命运的变迁中提取处心理要素的变化。
(二)以服饰书写的基础刻画人物性格权衡
在王安忆的《荒山之恋》这一作品之中,所刻画的金谷巷女孩就从服饰描绘中凸显了其性格要素以供读者来把握。在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组织时,她身着一袭黄色布料军队服,从精神样貌和精神气魄中显现出人物的特殊性格,是一个勇敢、敢爱敢恨、敢拼敢闯的女孩子。在服饰多变的时代中,她一直紧紧跟随着时代的变化,一旦流行了新的款式和花样她就会第一时间买来并换上。但与此同时,她又有少年含蓄和可爱的一面。就是这样惹人喜爱的人物性格,让其在男女关系中也展现出自己优势的一面。作者通过巧妙的服装描写,跃然纸上的是一个能够合理运用手段和技巧来笼络男性芳心的机灵少女。[4]而这种巧妙的小心思在其为自己量身定做衣裳和裤子的时候就已经被精彩展现出来。同时,也预示着其不安分的性格和心思是永远也不会得到满足的,就像一壶烈酒,在风光无限的外衣遮蔽之下,依然散发着浓烈酒香。
(三)以服饰书写的基调预示人物发展前景
服饰是穿着在人身体上的外衣,不仅是对人肢体的覆盖,同时也是对人外在际遇的拓展。因此面料舒适、衣着得体的描写通常预示着正向的人物发展,暗沉无色、款式老旧的衣着通常会预示着命运的悲凉。
蒋丽莉虽然不是《长恨歌》中的主要人物,但王安忆在对其描写的过程中,能够透露处其日后的发展命运。王琦瑶参加蒋丽莉的生日宴会,王琦瑶穿着大方又不会突兀,因为主角不是自己,所以她精心挑选了素色淡雅为主的衣服。但令王琦瑶没有想到的是蒋丽莉竟然穿着随意,似乎是居家服装并素颜出场,甚至还蓬头垢面。[5]从家中物体以及颜色搭配上来看,主要以灰色、黑色、白色为主,这就显得格外老成,甚至对于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来说,其服饰风格已经老气到令人惊愕的程度。由此作者便埋下了伏笔,暗示着这一人物的结局悲凉以及性格冷淡的后续发展。蒋丽莉虽然出生在工人阶级家庭,家庭还算富裕,但家庭环境所缺乏的温暖和爱,让蒋丽莉性格极为偏颇。同时,也让她在日后的命运发展中不断展现出极端的一面,甚至弱化自己的女性特征并向中性靠拢。但与此同时自己飘渺无力的挣扎是无法与时代所抗争的,只能在抗衡的过程中沦为时代的泡影。
三、王安忆文学作品中服饰书写的思想价值
(一)从城市的真实风貌中展现独特生活状态
随着张爱玲等小说家的作品不断畅销,一时之间在文坛之上兴起了“上海热潮”,这股热潮是以上海这一城市为背景,用文字来探究其独特魅力并展现上海原生态的城市样貌的作品。[6]王安忆的作品大多以对旧时人与事的怀念,抒发着别样的精神情感。这一精神情感中更重要的是从时代的变迁中挖掘出最核心的价值力量,用这股力量支撑人们在未来生活中能够不断抵御风险来进行文化的解构与重组。[7]
笑明明是《桃之夭夭》中的传奇佳人,她从少年时期就在戏台里参与帮腔活动,虽然年纪小,但却学习到了很多艺术实践经验。后又前往香港参加电影演员应聘,很遗憾并没有被录用,但因为其独特的资质和天生属于舞台的气质,让她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员。原文中对其早起梳妆打扮的过程进行了服饰化的描绘,这一描写更加衬托了城市中每个单纯的个体是怎样通过具体的风貌来汇聚为独特的生活状态。进入不惑之年的她,依然保持着对艺术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精致要求,在服饰的选择和配饰的搭配与挑选中都一如既往地秉持着自身的原则。[8]这样的描绘娓娓道来为读者展现了一幅缓慢而又细腻的画卷,即便是文艺气息浓厚,却并不是在卖弄资本,而是从行为的真实面貌入手来切实地反映生活最原本的形态。
(二)从女性的社会处境中挖掘时代际遇与活力
因为作家自身的性别处境,以及其对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观察,让她对女性话题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即便是在中国文坛还并没有特别强调这一话题的基础之上,王安忆依然另辟蹊径,从群体视角出发来展现女性独特的社会魅力。在她看到了社会现象以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思潮在中国大行其道,男性的自我优势又在不断压榨女性的生存空间,王安忆从问题意识入手来更加深入地探讨女性社会处境的时代际遇,将小说里的女性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从而能够突出表现其真实境遇和时代特征。
在《我爱比尔》中,作者将主人翁塑造为一个极其爱美的女性,在现实和精神相互分离的今天,女性对于服饰之美的追求也是在展现自己能够被社会认可的一个方面,以及能够实现自己社会价值的一个方面。因此,服饰之根本在于判定服饰美丑的审判者的眼光,而不在于服饰的根本属性。主人翁为了向心爱的男孩比尔示爱,将身上穿着的开衫、连衣裙、睡裙等一件一件地脱去,着装风格的特色是在向比尔展现其中国女孩的民族特性,将衣服脱去是向心爱的男生宣誓自己的内心的开放和接纳程度。[9]作者正是通过这样大胆的描写手法,进一步批判了社会中某些女性在追逐自我的过程中恰恰丧失了自我,从而沦落为看客眼中没有生命意识的机器。
(三)从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中探究协同融合的可能性
经历了两年的知识青年下乡,王安忆深刻认识到二元对立的差别化存在。这一差别不是理论上的普通描述,而是真实地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特殊结构。而这一二元结构更是让城乡之间筑起了高高的墙壁。对于服饰而言,乡村人的审美和品味一直是跟随着城市人前进的,在城市流行过的衣着和风格会在热潮过后才流入乡村[10]。对于那些想打破这个壁垒、不认命也不想永远留在农村的青年来说,努力踏入城市不仅仅意味着穿上城市风格的衣裳,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融入让服饰这一外衣也被套上了文化交融的具体路径。无论是《妙妙》还是《冷土》,都在通过主人翁对于服饰选择这一行为意识来加深乡村少男少女想奋力冲破二元结构枷锁的外在渴求。而作者对这一认知的描写不是简单的叙述,而是结合起承转合,将更多复杂元素加入其中,来让读者细细品味其中的微妙变化。
四、结语
服饰描写对于文学创作来说一直是经久不衰的,可以说一篇成功的文学作品中,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一定出色的服饰描写语句。王安忆在进行服饰描写的创作中,一直积极践行融合原则,将服饰与人的本质相互关联,进而在吸收相关经典文献和详细内容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做出内容取舍和分类。这不仅彰显了其独特的自我感受能力,同时也塑造了优质的人物形象,为推动时代发展进程提出了动态的自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