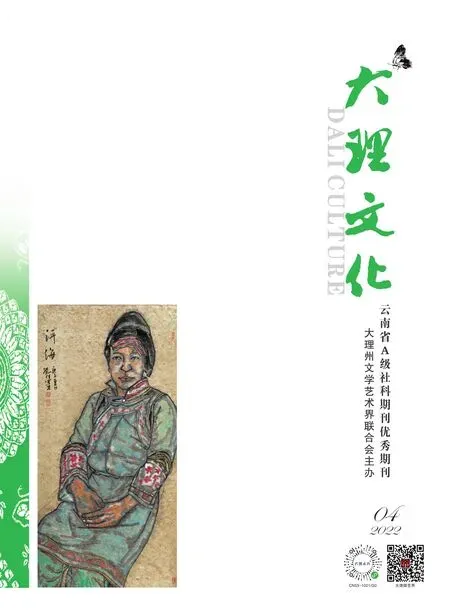巍巍宝塔话古今
●吴艳
巍然屹立于苍山洱海之间的三塔是大理的地标性建筑,沐浴着千年日月精华,穿过流淌的漫长岁月,三座宝塔鼎足而立,具有独一无二的辨识度,犹如三只如椽巨笔,在苍洱大地间写下历史的沧桑和风云变幻。
塔是佛教的重要建筑之一,起源于印度,用于安放佛教僧侣舍利而建,被称为“窣堵波”,汉文又译作“堵波”“塔波”“浮图”,晋代才称为“塔”,具有圣墓的性质。塔随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我国阁楼式建筑相融合,形成了中国佛塔最基本的两种形制——阁楼式塔和密檐式塔。早期,塔多为木构建筑,为了防火,逐渐变为石塔或砖塔。随着佛教在中华大地上的广泛流传,巍巍古塔成为佛寺的附属建筑一起四处开花。明清以后,塔脱离寺院建筑单独出现,并且造型更加多样,以风水塔的形式点缀在山水之间。至今可见的古塔星罗棋布于五湖四海,建筑材料类型丰富,有土、木、砖、石、金、银、铜、铁、琉璃、陶瓷塔,造型优美多样,有楼阁式、密檐式、喇嘛式、亭阁式、金刚宝座式、经幢式等,数不胜数。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应县木塔、开封铁塔、西安大雁塔、小雁塔、北海白塔,还有我们身边的崇圣寺三塔、弘圣寺塔、佛图塔、海东罗荃塔、水目山佛塔、鸡足山楞严塔等等不胜枚举。
作为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塔是艺术文化的结晶,凝结着先人的劳动与智慧。大理地区密集的巍巍古塔呈现出强烈的建筑美和艺术美,与自然环境、人文历史和谐交融,以独特的气质吸引着人们的目光,给人以别样的艺术感受,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值得我们认真审视,深入探寻。
作为大理的地标建筑,崇圣寺三塔可谓大理古代历史文化的一座杰作和丰碑,映照在苍山洱海的碧水蓝天之间,标志着古代大理地区所取得的璀璨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不但是大理举世瞩目的文化名片,更成为大理人民的精神脊梁,千百年来作为鲜明的区域文化符号,熠熠生辉。每个大理人,都有独属于三塔的一份记忆,而今就让我们再次走近三塔,走进三座宝塔背后的历史文化宝库,端详和审视三塔的那些历史瞬间,深入了解和感受这份宝贵的物质、精神财富。
一
崇圣寺三塔位于大理古城北,苍山应乐峰山麓,是崇圣寺的附属建筑,唐宋时期的地方政权南诏、大理国留存至今的三座著名佛塔。据相关文献资料和专家研究考证,崇圣寺三塔主塔建于唐代大理南诏政权劝丰佑时期,南北小塔为宋代大理国民族政权时期增建。三塔为唐宋时期的南诏政权、大理国民族政权皇家寺院崇圣寺的附属建筑,鼎足而立于崇圣寺前,历经千年风霜,巍然屹立不倒,作为唐宋时期的南诏政权、大理国民族政权珍贵建筑遗物的代表,1961年3月,崇圣寺三塔即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塔主塔又名千寻塔,古代八尺为一寻,千寻以指高耸入云。主塔呈方形,为16级密檐式砖塔,高69.13米,耸立于两层高大的塔座之上。上层为须弥座,高1.9米,下层台基高出地面约1米,周围有望柱和石栏杆。一层塔身最高,以优美的弧线形从下往上逐层缩减,密檐亦逐层降低。每级塔身出砖叠涩挑檐,中间的佛龛和采光洞交替上升,每层佛龛和采光洞的两侧各有一佛龛佛雕塑装饰。塔顶立有铜质塔刹,由中心柱、葫芦、伞盖、相轮及莲花座等部分组成,伞盖为八角形,每一角上都挂有风铃。整座塔造型优美,线条匀称,比例适中,呈现出简洁凝练、庄重厚朴、简约大气的艺术风格。
千寻塔是公元8世纪至9世纪我国流行的密檐式砖塔标准样式,整体造型与西安小雁塔风格类似。而南北小塔增建于宋代大理国民族政权时期,属唐代密檐塔向宋代楼阁塔的过渡形式,通高49米,为八角形。塔身装饰繁复华丽,每面砌有不同形状的佛龛,塔檐叠涩曲线向外挑出,雕塑装饰有仰莲、团莲、山花蕉叶及宝相花、佛像和动物纹样。塔身周围还有砖砌的斗拱和仿楼阁式建筑的倚柱、楞窗等结构。塔壁正中隐起小塔,下承卷云或中辟券龛,内供佛像,塔身转角处隐出似重叠宝珠形的倚柱。塔顶和千寻塔一样也有葫芦及伞形铜铃组成的铜质塔刹。就总体外观而言,千寻塔简约流畅,大气端庄,南北小塔精致典雅,富丽堂皇。大小三座宝塔鼎足而立,风格有异,却又和谐统一。
当下,我们眼中的三塔,高耸入云、巍峨壮丽,然而四百年前,明朝末年的三塔,却没有如此美好的景象。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初十的夜晚,春寒料峭,一位风尘仆仆的旅人来到三塔大空山房住下。他不顾旅途劳顿,趁着月色瞻仰三塔雄姿,“徘徊塔下,踞桥而坐,松阴塔影,隐现于雪痕月色之间,令人神思悄然。”言简意赅地记录了初见三塔的感受。这就是明末著名旅行家徐霞客与三塔初遇的场景,寥寥数笔勾画出动人心魄的画面,令人难忘,想必这也是三塔在徐霞客眼中独特的魅力吧。
几天后,徐霞客特意安排了一天的时间畅游三塔,在日记中用500多字精准地记录了当时三塔和崇圣寺的详细情况。
“是寺在第十峰之下,唐开元中建,名崇圣。寺前三塔鼎立,而中塔最高,形方,累十二层,故今名为三塔。塔四旁皆高松参天。其西由山门而入,有钟楼与三塔对,势极雄壮;而四壁已颓,檐瓦半脱,已岌岌矣。楼中有钟极大,径可丈余,而厚及尺,为蒙氏时铸,其声闻可八十里。楼后为正殿,殿后罗列诸碑,而中溪所勒黄华老人书四碑俱在焉。其后为雨珠观音殿,乃立像铸铜而成者,高三丈。铸时分为三节为范,肩以下先铸就而铜已完,忽天雨铜如珠,众共掬而熔之,恰成其首,故有此名。其左右回廊诸像亦甚整,而廊倾不能蔽焉。自后历级上,为净土庵,即方丈也。前殿三楹,佛座后有巨石二方,嵌中楹间,各方七尺,厚寸许。北一方为远山阔水之势,其波流潆折,极变化之妙,有半舟庋尾烟汀间。南一方为高峰叠障之观,其氤氲浅深,各臻神化。此二石与清真寺碑趺枯梅,为苍山最古者。新石之妙,莫如张顺宁所寄大空山楼间诸石,中有极其神妙更逾于旧者。故知造物之愈出愈奇,从此丹青一家,皆为俗笔,而画苑可废矣。其后又有正殿,庭中有白山茶一株,花大如红茶,而瓣簇如之,花尚未尽也。净土庵之北,又有一庵,其殿内外庭除,俱以苍石铺地,方块大如方砖,此亦旧制也;而清真寺则新制以栏壁之用焉。其庵前为玉皇阁道院,而路由前殿东巩门人,绀宫三重,后乃为阁,而竟无一黄冠居守,中空户圮,令人怅然。”
徐霞客记述三塔所在寺院位于苍山第十座山峰(应乐峰)下,于唐代开元年间建造,名为崇圣寺。寺前的三塔鼎足而立,中间的塔最高,方形,重叠十二层,所以崇圣寺也称为三塔寺。塔的四旁全是高耸入云的松树。寺西由山门进去,有钟楼与三塔相对,气势极其雄伟壮丽,但四面的墙壁已经坍塌,屋檐上的瓦片有一半脱落,岌岌可危。钟楼里的铜钟非常大,直径一丈多,壁厚一尺,为唐代大理南诏政权蒙氏所铸,洪亮的钟声在八十里外都能听到。钟楼后是正殿,殿后罗列着许多碑刻,李元阳刻黄华老人王庭筠的四块碑也在其中。碑后的雨珠观音殿,有高三丈的铜像。传说铜像还未铸完,铜却不够用了,这时天上忽然落下如珠子一样的铜雨,众人一道用手把铜珠捧来熔化,不多不少恰好完成了铜像的头部,所以得名雨珠观音。殿左右回廊中的众神像也十分整齐,但回廊倒塌已经不能遮蔽风雨了。从后边沿石阶上去的净土庵,是方丈的住所。正殿的庭院中有一棵白山茶,花朵大小如红山茶,而且花瓣成簇也像红山茶,花还没有开完。净土庵北边的寺庵佛殿内,庭院石阶,全是用方砖大小的大理石铺成,与此类似的还有大理城南门外的清真寺,那里是用大理石来作栏杆墙壁。这座寺庵前边是玉皇阁道院,有殿宇三层,后边就是楼阁,但是居然没有一个道士留守,庙中空空,门户倒塌,冷冷清清,徐霞客为寺院萧条的景象感到惋惜。倒是净土庵大殿佛座后的两方大理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详细地描述了在这里见到的两方大理石的大小、品相、神韵,高度评价大理石“从此丹青一家,皆为俗笔,而画苑可废矣”。徐霞客非常喜爱大理石,在崇圣寺南边大理石工匠家里观赏时,还花了一百文钱买了一小方有着黑白分明意趣的大理石。这块大理石一直跟随徐霞客回到江阴,成为他最为珍爱的为数不多的“旅游纪念品”。
从徐霞客游记里可见,明末三塔周边寺院道观虽然衰败,然而三塔依旧鼎立,这不得不归功于李元阳。李元阳(1497-1580年),字仁甫,号中溪,著名文学家、理学家。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历官江西分宜、江苏江阴知县,户部主事、监察御史、荆州知府等职。为人耿直、刚正不阿,为官清廉,政声卓著。嘉靖二十年(1541年)李元阳为父奔丧弃官回乡,闲居四十余年,寄情山水,热心桑梓,致力地方文化发展。尤其是倾其家财,花费30年的时间重修崇圣寺维修三塔,功德无量。李元阳的诗文著作很多,晚年还编纂了《云南通志》和《大理府志》,成为徐霞客游访云南的重要参考书籍。故而徐霞客在大理期间,于三塔寺后的荒烟蔓草间偶然发现李元阳的墓,立刻下马祭拜。然而,令徐霞客感慨万千的是,李元阳七十多岁时为表示皈依佛教,在三塔寺后营建墓穴,可谁知时移世易,寺院却依旧荒芜冷清成为一片沧海桑田。
李元阳发愿百年后葬于三塔,也确实是对三塔情有独钟。他在《崇圣寺略记》中写道:“大理城之北寺曰崇圣者,自始迄今历千五百年,梵宇悉颓,法席中断。大明嘉靖辛丑予始修复。”曾经崇圣寺作为皇家寺院的辉煌和三塔的壮丽雄姿,令李元阳引以为傲:“盖有千尺三浮图,玉柱标空,金顶耀日,寰中之塔,无与为比肩。高楼百尺,上悬洪钟,声闻百里。登斯楼也,览云霞于襟袖,荡灏气于层胸。西望苍山,四时皓雪;东俯洱水,数点蒲帆;洒酒临风,有足乐者。”这是何等的辉煌,又是令人诗兴大发,何等惬意的景象。在李元阳的努力下,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率子弟罄货财重建崇圣寺,至四十二年(1563年)才完工。历时二十余年,岁月漫长,却不忘初心,竭力兴复,终于使崇圣寺恢复了曾经的鼎盛景象:“一时,钟鱼馨铎,无间晨昏,而学徒衲子,渐以类集。废者以兴,坠者以举。殿堂弘丽,廊庑崇深。松桧蔚乎清阴,花木纷乎盈目。匪直青衿、白衣就以诵习;而风人韵士,撷芳选奇。极寥靓而趣闲,雅者莫不怀铅簪笔来游其间。”
如今,崇圣寺北小塔一侧的塔身上的《重修三塔碑记》就真实记载了李元阳重修三塔的过程。“大理郡城之北有崇圣寺,旧号千厦,创自唐贞观间。寺前三浮屠高侵云表,世传开源癸丑南诏所建,阅四十八年功成。”明正德九年(1514年)、正德十年(1515年),大理接连遭遇两次破坏性很强的地震,“城堞屋庐为摧,独三浮屠无恙,然已罅拆如破竹。嗣是风雨飘摇,日益剥洌。”李元阳于是多方筹措资金,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六日“补甃中塔,复作木骨,凡百日竣工”。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始克重葺左右二塔,秋初经始,首尾历五月。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李元阳撰书”,寥寥数语,却道出了维修的艰辛和不易,就如大理督学吴鹏在《重修崇圣寺记》中说:“郡人李内翰中溪氏,率子弟罄货财,竭力兴复。盖自嘉靖壬寅经始,至今癸亥乃得讫工。凡三阁七楼百厦,其位置之向背,基础之崇卑,片瓦寸木皆出自李公之擘画。”
经李元阳的修葺,崇圣寺达到一定规模,如其在《崇圣寺略记》中描绘的,“高楼之西,佛殿七楹。殿后为雨铜圣阁,唐代天雨铜铸观音像,举高二十四尺。阁后为净土化城,内铸西方三圣像,各举高九尺,左为龙华堂,右为圆通舍楼。南入总持门,行数步,诸院幽闲,迤逦相屑。至杏坛而极楼,北入瑞鹤亦行百步,阶墀栏循,窈窕登陟,至三清而止。此则寺之大概也”。为数十年后远道而来的徐霞客保留了崇圣寺的基本样貌,再经徐霞客的细致描述,令今人得见明末崇圣寺和三塔的真实景况。
李元阳举毕生之力重建崇圣寺,维修三塔,这份深情厚爱凝缩在了他所作的《崇圣寺重器可宝者记》这篇文章中。虽然他在开篇即说“崇圣为寺,其来久远,不可追诘”,但“寺之重器有五,一曰‘三塔’,二曰‘鸿钟’,三曰‘雨铜观音像’,四曰‘证道歌’‘佛都匾’,五曰‘三圣金像’”。这五大重器分别是三塔、南诏建极大钟、唐初所铸雨铜观音像、元代著名书法家圆护手书的《证道歌》二碑和“佛都”两字及明嘉靖年间所铸极乐殿三圣金像,可谓崇圣寺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内涵的集中体现。
位列重器之首的三塔“高入云表,寰中无匹”。自不必赘言,高悬于胜概楼的“鸿钟”铸于南诏建极十二年(872年),“制作精好,声闻百里。自禁钟而下,此为第一”。见到此崇圣寺重器的徐霞客亦夸赞此钟“声闻八十里”。据现存鸿钟款识拓本,大钟为六面,分上下两层:上层每面高二尺五寸许,广二尺二寸余,各铸金六波罗密图;下层每面高一尺三寸许,宽一尺三寸余,各铸梵释四大天王像,以及“维建极十二年岁次辛卯三月丁未朔二十四日庚午建铸”的题记。可惜此钟已毁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如今,崇圣寺新建的钟楼,以“大叩大鸣,小叩小鸣,普觉梦中之梦;一声一佛,千声千佛,遥闻天外之天”的楹联重现了“叶榆十六景”之最的“钟震佛都”,令人遐想。
李元阳记录的崇圣寺第三重器为雨铜观音像。“雨铜观音像,高二丈六尺。唐初,有僧拟募铜铸像。是夜,天雨铜,像成铜尽,无欠无馀。”离奇的铸造过程让崇圣寺的这尊观音像有了更加传奇的色彩。《南诏野史》云,崇圣寺雨铜观音像成于唐昭宗光化二年(899年),即南诏最末一个诏主舜化贞时期。据史料记载和学者研究,这尊观音即为崇圣寺供奉的主尊阿嵯耶观音,在唐宋南诏政权、大理国民族政权时期又被称为圣观音。关于观音造像的铸造年代和尺寸,《南诏野史·舜化贞传》《白古通纪浅述》和万历《云南通志》均有记载,且说法不一。方国瑜先生在《大理崇圣寺塔考说》中写到其本人数次游览崇圣寺,还见此观音像,“高约二丈四尺……其下垂衣缘,刻有‘云南提督蔡标率官绅士庶补铸,光绪丙申年仲秋之吉’等字”。据考证是咸丰六年(1856年)咸同兵燹导致观音像的左臂和部分衣纹飘带被捣毁,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云南提督蔡标统帅官绅等筹款补铸完整并刻文纪念。
重器之四的“证道歌”和“佛都匾”出自以书法著称的元代高僧圆护大师。圆护被大理总管尊称为弘辩大师,李元阳称“其用笔与赵孟頫同三昧,为世所珍。世传,护右手自肘自腕,洞澈如水晶然,则笔之精妙,殆非偶然。”《证道歌》又作《永嘉证道歌》《永嘉真觉禅师证道歌》,为唐代永嘉玄觉禅师(665-713年)撰。玄觉禅师初学天台,后闻禅宗六祖慧能说法,遂改入禅门。《证道歌》即是他悟道后心得精华的文字记录。以流丽的文体叙述禅宗真髓,可谓一个真正悟道者的见解。不但见地高深,而且以诗歌的节奏广为传诵,铿锵有力,朗朗上口,深受禅门喜爱。《证道歌》为古体诗,全文有247句,共1814字。可以想见,圆护大师亲自书写的《证道歌》碑和“佛都”牌匾,不但是精美的艺术品,也是崇圣寺尊崇佛教源流的历史见证。
崇圣寺第五重器为三圣金像,李元阳说:“三圣金像在极乐殿,并高丈一尺,嘉靖间铸。传说,时值盛夏赤日,冶人无措,忽阴云如盖,独覆铸所。像成而云散,众人都很诧异。”时人不着笔墨描述三圣金像的华美精致,就凭传奇的铸造过程就给造像增添了神秘的滤镜和无穷的神力护持,因此受到人们的无比珍视。虽然李元阳也认为“夫此五物在寺,亦有多历年所。累经变故者而独得无恙,非鬼神呵护之力乎?”但在他看来,大理“山则九曲翠屏,水则万顷碧练,其融结环抱,即天下奇胜之地,无与为比”。如此胜境中,寺院与山水交相辉映,而寺院没有重器,亦不能称之为名胜。尤其是这五大重器“虽出于人为,然非人之智巧所能到,亦非人力所能存”,李元阳将其总结为神佛对大理妙香秘境的庇佑,故作此文,刻于石碑,希望后来人共同珍视崇圣寺五大珍宝。可惜世事流转,岁月沧桑,崇圣寺在经历明清两代的衰败和战乱之后,夷为平地,五大重器亦仅余三塔孤悬苍洱之间,岌岌可危,令人痛惜。而三塔,作为历经千年历史烟云的传奇建筑,其价值意义更加非比寻常,值得我们像历代先贤一样,一如既往地珍惜和呵护这份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
二
隋代以前,塔作为佛教寺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居于寺庙的中心位置。唐代开始,寺院建筑逐渐以具有礼佛、诵经、参禅功能的殿宇为中心,塔的地位慢慢下降,退居寺院建筑物的陪衬,多建于寺后、寺旁或另成塔院。
元代大德年间,一位来自陕西的官员郭松年被派往云南巡视,出于对这片蛮荒之地的好奇,他把此次差旅见闻写成了一篇文章,名为《大理行记》,短短数千字,却成为后人研究元代大理的重要史料。在郭松年笔下,大理苍山“条冈南北,百有余里;峰峦岩岫,萦云戴雪,四时不消……”更让郭松年惊讶的是“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记”。元代的崇圣寺,就是这沿山寺宇中最为兴盛的一座。“中峰之北有崇圣寺,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二百余尺,凡一十六级,样制精巧,即唐遣大匠恭韬、徽义所造。塔成,韬、义乃归。”可见,作为崇圣寺的重要建筑,三塔鼎足而立,引起了郭松年的瞩目并记录了三塔的建造时间和建造者。毋庸赘言,因得到朝廷的的支持和保护,延续着唐宋时期南诏政权、大理国民族政权以来的辉煌和兴盛,从几块与崇圣寺相关的元碑中也可以窥见一二。
《大崇圣寺碑铭并序》为元第六代大理总管段隆于泰定二年(1325年)所立,由翰林国史大学士、云南省参政知事李源道撰写,著名书法家圆护书丹。碑文开篇追述元世祖征大理的经过,“昔在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仁圣之姿,贵介之弟,肃振天威,奋扬神武,大举六师,亲征云南。一鼓而出萧关,再驾而克大理。”作为西南边陲屏障之地,元朝对大理有其统治的策略,“惟大理西南夷之巨防,段氏国之馀三百年,天戈一举,望风底定。而居民安堵,不知有兵。段氏族属皆在保宥,使永其世祀。”虽然宋代大理国民族政权被灭,但元朝统治者对大理采取怀柔政策,段氏家族被保留下来,得到重用。“南方既平,悉郡县之,控以大阃。大理亦厘为一郡,以段氏宗子袭为长民。”
碑文记载了第二代大理总管段实因“拳勇大度,留心内典,崇信三宝”发愿重修崇圣寺的经过。“大理崇圣寺者,在郡之点苍下,蒙氏所创也。寺既灾,武定公(段实)为大檀越,出己财,缮治庄严经像,殿庑奂然复新。三塔峙立,金碧交辉,巨丽与山埒,望之如昆阆间物。舍田供僧,日百许人。住持僧曰‘觉性’也,两被玺书覆护,寺益显矣。”通过碑文的记录,可以窥见元代崇圣寺的地位依旧显赫。尤其碑阴所刻《大崇圣寺圣旨碑》,用罕见的白话书写了至大四年(1311年)元武宗皇帝颁发的圣旨,直白浅显地向民众宣告了皇帝对崇圣寺财产进行保护的意图,将统治阶级的最高指示贯彻落实到了最基层。由此可见,元初元朝统治者通过大理军民总管对大理地区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在宗教信仰方面也给予了宽松的政策。在大理总管段实和主持僧觉性的努力下,作为唐宋时期南诏政权、大理国民族政权遗留的大型建筑群,崇圣寺得到朝廷支持和保护,重修后的盛况不减当年。
然而,明清时期的崇圣寺随着故国远去不可避免地逐渐式微,所幸其间除了文化巨擘李元阳之外仍有一些有识之士对崇圣寺及三塔等历史建筑加以保护。如今立于千寻塔东南侧二层塔座之上的一通《起建宝塔栏杆之碑记》就是实物见证。碑刻立于明成化二年(1466年),至今字迹已漫漶不清,文字剥蚀难辨,历史的风霜历历在目。碑由大理府僧纲司都纲、崇圣寺主持释灵撤撰文并篆额,书丹者难以辨识。碑文追溯三塔的历史,回顾了多年来善男信女各输财帛对崇圣寺和三塔维修的功德。最后记载此次由信士陈钦等四十余人捐资鸠集工匠起建千寻宝塔栏杆加以保护之事。千寻塔的东北一侧所立的《重修崇圣寺塔记》记录的则是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对崇圣寺塔重新修葺一事。碑文由大理府杨长桂撰文。碑文记述“榆古称泽国,多水患,昔人置浮图镇之,所在多有,而崇圣寺前者为最。鼎峙云表,俨然六丈金身,承露仙掌,殆不能及。盖西南第一巨观,而龙所敬畏者也。唐贞观年始建,明李侍御复修。”文中详细记述了建塔之缘由和始建年代,并提及明、清两次复修的史实,最后号召后世“同心护之培之,则胜迹常存,水患永息……”是历代对三塔维修保护的历史见证,至今陪伴在千寻塔脚下,一同经历风霜雨雪,成为三塔历史遗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
民国十四年(1925年),农历二月二十二,大理发生百年不遇的强烈地震,城中屋舍倒塌成片。三塔经历了剧烈的晃动后虽然依旧矗立,然而千寻塔塔身被震裂,南北小塔出现不同程度的倾斜,尤其是千寻塔顶高约8米的塔刹在剧烈的震动下折断坠落,将塔下万历十一年(1583年)黔国公沐英后裔沐世阶所书“永镇山川”的照壁砸毁,仅剩“川”字,令时人痛惜。1927年,幸得喜洲富商严子珍捐资,由大理书法名家周仁双勾修补了“永镇山川”四个大字,留存至今。而随塔刹落下的不少文物,则很快被塔下驻军攫取瓜分,随后散佚,不知去向。
地震之后,千寻塔掉落宝贝的消息不胫而走。李根源在编撰《新纂云南通志》的《云南金石目略》中记载了千寻塔上掉落的一件塔模,“高一尺二寸,重六斤四两,七级。顶作亭阁式,四面造佛像三十躯,下层则四夭王托塔,翠色斑烂,精气夺目,当为滇中第一重器。”可以想见,这些掉落的文物令世人惊艳,更让人对千寻塔宝藏遐想连篇,连掉落的铜质塔刹骨架,也因屹立千年不倒的三塔而富有别样的神秘色彩,被附近闻讯赶来的村民零敲碎打用于制作长命锁、护身符而所剩无几。乱世之际,更有胆大妄为的不法之徒觊觎塔藏宝藏,唆使亡命之徒铤而走险,攀塔盗取文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在大理传教的德国女传教士鲍格兰在贵阳被驱逐出境时,被海关查获其携带的两尊佛像即是重金雇人从千寻塔上盗取而来的,幸而被发现随后入藏云南省博物馆。而更多的文物则流散到国外,其中一些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法国集美博物馆等欧美著名机构收藏,引发了外国学者的研究兴趣。
1944年,美国学者海伦查平在《哈佛亚洲研究季刊》发表了一篇名为《云南的观音像》的论文,第一次将三塔出土的佛像文物以学术研究的角度呈现在世人眼前。随刊还首次登载了《南诏图传》的黑白照片,引发了学界的轰动和极大的关注。
《南诏图传》绘制于中兴二年(899年),因此又称《南诏中兴画卷》。全长580.2厘米、宽31.5厘米,由纸本设色的画卷和墨书小楷的文字卷两部分组成。画面构图疏密有序,人物刻画细腻生动,文字书法隽秀飘洒,图文并茂地讲述了观音点化扶助唐朝时期的大理南诏政权建国的故事,显示出较高的绘画和书法水平,是云南9世纪的艺术珍品,更是研究南诏历史文化的珍贵文物,可惜也流散海外,现藏于日本京都友邻馆。
在《南诏图传》中,出现了一尊形象独特的观音,文字描述其为“西域莲花部尊阿嵯耶观音”。他发髻高耸,编辫垂肩,细腰纤臂,袒露的上身饰有项圈、璎珞和臂钏,下身着裙,双腿并拢,裙面呈现U形纹路,整体造型板正平直,显得清瘦秀美,与中国内地常见的观音像风格迥异,引发学者对南诏佛教艺术的研究和讨论。
海伦查平将美国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观音造像与《南诏图传》中多次出现的观音像两相对照,发现这尊风格迥异的观音像与《南诏图传》上的“阿嵯耶观音”如出一辙。而根据观音身上的铭文:“皇帝骠信段政兴,资为太子段易长生、段易长兴等造记,愿禄算尘沙为喻,保庆千春孙嗣,天地标机,相丞万世。”推断其来源就是云南大理崇圣寺千寻塔,是两宋时期的大理国民族政权第十七代王段正兴为太子段易长生、段易长兴祈福而造。
被海伦查平称为“云南福星”的阿嵯耶观音是唐宋时期的南诏、大理国民族政权“滇密”阿吒力教崇拜的主要神祇。阿嵯耶在梵文中的意思是“圣”,译为“圣”观音。阿嵯耶观音在唐宋时期的南诏政权、大理国民族政权地位最为尊贵,同样也受到上至地方政权统治者下至百姓的敬仰。阿嵯耶观音造像身姿纤细,梳高髻双辫,髻中藏化佛,头饰高耸、发型精致。上身袒露,戴璎珞项圈和臂钏,手结妙音天印,下身赤足着裙,腰饰飘带,衣着华美。整体感觉姿容秀丽清俊,面相恬静,貌如时人,有如俊美少年,透露出浓烈的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崇圣寺所崇奉的,就是这鼎鼎大名的阿嵯耶观音。史载,中兴四年,清平官郑买嗣。合十六国铜,命蜀人李嘉廷铸高达六丈的阿嵯耶观音像。传说铸像时铜不够用,幸得天降铜雨得以完工,故又称“雨铜观音像”。也就是说崇圣寺五大重器之一的“雨铜观音”就是阿嵯耶观音。
阿嵯耶观音像独特的造型和艺术风格彰显着大理在唐宋时期的南诏政权、大理国民族政权辉煌灿烂的佛教文化和高超的冶金技术,令世人为之瞩目。而阿嵯耶观音信仰的兴盛,与南诏、大理国民族政权政治文化经济紧密相关,单就造型艺术风格来说,可以说是多种文化交融的产物。大理地处通往印度、缅甸的交通要道,是汉、藏及东南亚文化几大文化板块的结合部和交汇点。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东南亚上座部佛教和本地的原始宗教在这里交融汇聚,形成了各派并存的局面。阿嵯耶观音的造型兼具了时代特色和区域文化特征,以独树一帜的风格成为大理历史文化的珍贵文物代表,可谓云南佛教文化的旷世奇珍。
四
1978-1981年,中央首次拨给专款,对三塔进行了自明嘉靖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维修,清理出塔藏文物680余件,其中包含金、银、铜、铁、水晶、瓷、木等质地的各类佛像,绢、纸等各种材质的写经和刻文金属片,还有中原输入的青铜镜、瓷器、钱币、印章等物,以及制作精美的金银饰品、珠宝药物等,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这些唐宋南诏、大理国民族政权时期的珍贵文物穿越历史的迷雾,向世人展示了唐宋时期南诏政权、大理国民族政权辉煌灿烂的佛教文化。
此次维修发现的一尊阿嵯耶观音像通高26厘米,为纯金打造,身后是银质舟形镂空背光,是为三塔出土的国宝级文物之一。此尊阿嵯耶观音发髻高高隆起,戴发箍,发髻正中端坐化佛。长发编辫垂肩,一头细密的秀发纹丝毕现。脸型方圆,双目微闭,厚实的嘴唇微微抿起,面容清俊秀美。整体身躯扁平,宽肩细腰,上身袒露,佩戴装饰华美的项圈与臂钏,手结妙音天印,腰系一圈圆形花纹腰带,下身着轻薄长裙,腰间饰有花朵形状的飘带,裙两侧垂长飘带。裙摆紧贴双腿,呈现典型的“U”型纹路。赤足,足底有插,原应配有莲座。造像配合身后的精美银质背光,给人庄重娴雅、雍容华贵的美感,独特的造型,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充分彰显着阿嵯耶作为圣观音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与此类似的另外一尊金质阿嵯耶观音立像,珍藏在千寻塔出土的一件长方形漆龛内。造像通高仅7.4厘米,背光亦为纯金打造,显得小巧玲珑。两相对比,造型细节十分吻合,整体秀丽精致,气度非凡。千寻塔塔藏与此类似的还有木雕阿嵯耶观音和银质阿嵯耶坐像,造型也与流失海外和国内收藏的阿嵯耶观音像大同小异。这一系列的阿嵯耶观音造像被认为是唐宋时期的南诏政权、大理国民族政权官造阿嵯耶观音的标准样式。
从《南诏中兴画卷》首现阿嵯耶观音形象,到千寻塔塔藏阿嵯耶观音像的一一现世,佐证着阿嵯耶观音这一信仰崇拜在唐宋时期的地方政权南诏、大理国的兴盛。而到大理国三百余年,共二十二主的统治时期,就有九位帝王禅位为僧,也说明了统治者对佛教的痴迷,佛教与政体紧密相连,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统治局面。
从《南诏图传》中老人铸造圣像的画面让我们联想,唐宋时期的南诏、大理国民族政权,随着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为广留阿嵯耶圣迹铸像成风。据史书记载,南诏王劝龙晟用金三千两铸佛三尊,送至佛顶峰;劝丰佑时仅三塔寺即有佛一万余,还用银五千铸佛;隆舜以黄金八百两,铸文殊、普贤二像,敬于崇圣寺,并改元为“嵯耶”,自号“摩诃罗嵯耶”。到末代南诏王舜化贞时期,始铸崇圣寺阿嵯耶观音像(即雨铜观音)。
在南诏灭亡后,政权频繁更迭时期,无论政治如何动荡,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三个时期的上层统治者均频繁铸佛,直至段思平建立大理国民族政权后更是“岁岁建寺,铸佛万尊。”之前提到的收藏于美国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的青铜阿嵯耶观音立像,根据铭文显示即为1147-1172年在位的大理国统治者段正兴出资为其子段易长生和段易长兴祈福所铸。可见,这些精美的阿嵯耶观音造像是在唐宋时期的南诏政权、大理国民族政权几百年统治期间,王室崇敬信仰的主要神祇。
除了精彩的阿嵯耶观音,千寻塔塔藏文物中发现的众多的佛、菩萨、金刚、明王造像被研究者高度总结概括为大理佛体系,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南诏、大理国这两个地方政权佛教信仰的多元和丰富。塔藏文物中的佛陀造像以五方佛居多,按手印区分有结智拳印的大日如来佛,结降魔印的阿閦佛,结禅定印的阿弥陀佛,结与愿印的宝生佛,施无畏印的不空成就佛。这些佛陀法相庄严,却给人和蔼可亲,朴实敦厚的感觉,具有独特的地域风格。这些金、银、铜和水晶等不同质地的造像,刻画细腻生动,是为密宗造像不可多得的文物艺术珍品。
塔藏佛教造像中数量较多的是风格独特、姿态各异的菩萨造像,以青铜质地的杨枝观音占比最多。这些观音身材纤细,体态婀娜,或提净瓶,或持柳枝,加上周身环绕的飘带,显得空灵轻盈,仙气飘飘。而一些带舟形背光的观音造像则身形笔直平板,面容温厚慈祥,整体显得庄严肃穆一些。
这些菩萨造像有的别具一格,如一尊带金质火焰形背光的银杨枝观音立像,高30.6厘米,头戴宝冠,面目祥和,左手持净水钵,右手杨柳抚肩,长裙曳地,飘带飞舞,造型精美,优雅端庄。
还有一尊39厘米高的铜鎏金杨枝观音,脸型饱满,头戴宝冠,披巾挂帛,满饰璎珞,左手持长颈净瓶,自然弯曲,右手持杨柳抚肩,造型雍容华贵,仪态万方。另外一尊银质的杨枝观音像,呈罕见的坐姿,高仅8厘米,结跏趺坐,左手持净水钵于左膝上,右手持杨柳不搭肩,衣饰纹理生动自然,宝冠和璎珞刻画细腻,显得生动传神。呈坐姿的还有一尊银背光石雕水月观音坐像,通高10.8厘米,舟形镂空的银质背光前倚坐一尊汉白玉雕琢的水月观音。观音身形曼妙,似低头沉思,通身衣带飘逸,体态安详舒适,别具一格。
除了数量较多的杨枝观音之外,千寻塔塔藏菩萨造像还有地藏菩萨、大势至菩萨、虚空藏菩萨、佛顶尊胜佛母等,无不以精美的造型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展现着婆娑世界的神秘风采,同时又带有平易近人的世俗化风格,尤其是地藏菩萨和一些罗汉从形神、姿态上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仿佛当时修行僧侣的再现,亲切而生动。
与之风格迥异的是塔藏佛教造像中造型夸张、特色鲜明的护法天神明王造像。在密宗中,明王像是佛与菩萨的忿怒形身,是显示力量的偶像,尤以大黑天神为代表。大黑天,梵名摩诃迦罗,是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降魔时呈现的愤怒像,也是密宗中最为重要的护法神,大黑天信仰在大理地区广为流传。这尊千寻塔藏银质大黑天神立像三头六臂三眼,通高8.2厘米,头着骷髅冠,头发竖立呈炽燃火焰光,浓眉大眼,怒目圆睁。上身袒露,蛇为络腋,虎皮为裙,四手各执法器,笔直站立,有飘带绕臂垂至脚边。整体形象生动地彰显了大黑天神威猛的气势,令人望而生畏。
与此类似的具有无比神力的明王造像还有铜鎏金毗沙门天像、铜鎏金橛金刚像、铜八臂明王立像等,其中一尊铜鎏金金刚手明王像尤其精彩。因为鎏金保存较为完好,这尊金刚明王像头戴宝冠,怒目而视,手持法器,右手护胸,左手高举过头,两臂和手腕上缠绕蛇形臂钏手镯,右腿弯曲弓步前倾,腰间飘带坠地,脚踏一面目狰狞的小鬼,整体造型生动,威严震慑之势扑面而来。
这些被统称为金刚的护法天神和塔藏佛、菩萨造像,集中反映了佛教密宗的许多特点,造像风格以汉传密宗造像为主,兼具南亚、东南亚和藏式风格,又结合白族本主崇拜的地方风格而创造出的别具一格的“大理佛”,融合与创新,包容并蓄的创举在世界佛教艺术中独树一帜。
三塔塔藏文物的帝释天、毗沙门天、吉祥天、伊舍那天等护法神,都属于天龙八部众的天部。除了天众,天龙八部包括还有龙众、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七部,他们作为各种神道怪物,都是佛的追随者和保护者。塔藏文物中一只精致华美的神鸟就是迦楼罗的典型代表。这只鎏金银质的大鹏金翅鸟通高18.5厘米,重仅125克,显得小巧玲珑却气度非凡。金翅鸟双目炯炯有神,昂首引颈,作振翅欲飞状,通体鎏金闪耀,腹部还有镶水晶珠的痕迹。头饰羽冠,镂空的尾翼向上高耸似熊熊燃烧的火焰,上面还镶嵌有五颗晶莹剔透的水晶珠。大鹏金翅鸟足踏莲座,目光昂然,体态雄健,充满勃勃生机和威赫之力。相传,大鹏金翅鸟非常凶猛,以龙为食,两翼伸展可达三百三十六万里,以巨大的翅膀拨动海水,从中分开,捕龙为食,也能消除水患,皈依佛法后,成为佛祖的护卫神鸟。大理古为泽国,为水患侵害,故信奉金翅鸟能驱龙震水所以将其铸于塔顶。王昶在《金石萃编》中跋曰:“按云南通志,崇圣寺有三塔,其一高十丈余,十六级,其二差小,各铸金为顶,顶有金鹏也,传龙性敬塔而畏鹏,大理旧为泽国,故以此镇之。”《新纂云南通志》也有描述:“塔顶铜器如盂,围五尺许,高二尺许,厚五分,累层置重器于其中,旁如旌旗如翅,塔下仰望不辨为何器,相传为大鹏鸟。”
在云南,与千寻塔外形相似的密檐方塔,如昆明东、西寺塔、官渡妙湛寺塔的塔顶均铸有金翅鸟。可见在塔顶铸金翅鸟是云南密檐式方塔的独特之处,也是区别于中原地区密檐方塔的重要特征之一。
塔藏文物中还发现了与千寻塔造型相同的鎏金供养塔。供养塔又称阿育王塔或金属塔模。相传阿育王历年从事战争杀戮无度,后来皈依佛教因忏悔而广建佛寺、佛塔。供养塔或塔模也可以作为装藏舍利的函盒,塔藏供养塔有三件塔心中空,有的放有一两颗水晶表示舍利子。
千寻塔发现的四尊密檐方形供养塔,其中两尊为七级,一尊为六级,一尊为十级。一尊七级密檐式方塔通高12厘米,通体鎏金,基座四面塔门外铸有四方佛,顶作亭阁式,底为莲花形须弥座,小巧精致。另外一座六级密檐式方塔,也为鎏金铜质,塔刹与千寻塔塔刹类似,由宝顶、宝盖、相轮、莲花座组成,塔的基座为两朵卷缀状的祥云所托,别具一格。李根源所形容的“翠色斑烂,精气夺目”即为此类型的供养塔模。
除了密檐供养塔外,三塔塔藏文物中的一组五色供养塔模也尤其精彩。这个被称为舍利盒的五色塔模高8.4厘米,鎏金铜质圆座。最外层为覆钟形铁罩,打开之后是一个舍利塔模。不同于密檐塔模,舍利塔模为圆形塔身。金色的铜鎏金塔身之上是一方形基座,竖有一圆锥形的银质塔杆作为塔刹,塔身为双层银质莲花瓣所护托。这层塔身打开后,还有一个半圆银罩,揭开银罩又是一层金罩,最里面是一个肉红色琥珀加工成的舍利塔模。整个舍利盒连同外罩,实为金、银、铜、铁、琥珀五种材料所制,代表青、白、赤、黑、黄五种颜色,是密宗崇拜五方如来仪轨的体现。
三塔塔藏文物《梵文金刚界曼陀罗布幅》就更加直观地展示了密宗信仰特点。曼陀罗,是指古印度祭祀的祭坛。这件《梵文金刚界曼陀罗布幅》长143.5厘米,宽137厘米。在一幅纹理细密的方形棉布上,以墨线绘一方框,正中以井字形分隔出九个小方格,在其中各写有梵文佛、菩萨名。这件布幅是以种子代表主尊,将诸佛安置于祭坛之中祭供的示意图,与塔藏金属佛、菩萨造像相吻合,是聚集诸尊成就的一大法门,也是大理地区的佛教是由密教瑜伽派衍生而来的实物证明。与密宗信仰相关的是塔藏文物中数量不少的写经和符咒,包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佛前自心印陀罗尼》等以及单页朱书绢质的陀罗尼符咒。这些写经和符咒的发现说明塔藏佛经种类众多,除密宗典籍之外还深受中原华严宗、禅宗等多种教派的影响。其中文字写法皆承袭中原汉文化传统,深刻地说明佛教的传布是内地与边疆古代密切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纽带。
而最为常见的塔藏佛教文物,还是千寻塔中发现的大量金刚杵和经咒塔砖。金刚杵,又名降魔杵,原为古代印度的一种兵器。通常作手持式,一端或两端有四棱形的杵尖,是一种刺杀类的进攻型武器,后来为佛教密宗吸收演化为护法天神手持的一种兵器,具有“断烦恼,除恶魔”的法力。金刚杵的种类很多,质地不一,有金、银、铜、铁、石、水晶等。杵也分五股、三股、单股等。单股金刚杵又称橛,也分单头或双头,还有指环式的金刚杵,作为法器方便佩戴,多为僧人在仪式中使用。
千寻塔塔藏金刚杵有200多件,多数属于双面五股杵,四周四股则作鹰爪状钩,护卫杵身。杵把装饰莲花纹,精致一点的则铸成天王头像、菩萨半身像或人面鹰嘴的迦楼罗像。一些造型精美的指环式金刚杵还装饰有蛇的形象,别出心裁地以首尾相交的蛇身作指环,蛇头张口吐须,形若游龙,形象夸张。蛇,是古代印度教崇拜物之一,在金刚部造像中,蛇从天王头顶、腋下钻出,以增添天王的威武。密宗中的大蟒神,又称摩睺罗伽,亦是天龙八部众之一,同为佛的守护神。与金刚杵一样数量众多的塔藏文物还有经咒塔砖,有模印汉文、梵文和朱书梵文三种类型,多为《如意宝珠咒》《大佛顶心咒》《佛顶无垢净光陀罗尼咒》等,是密宗祈祷咒文,与建塔修塔等仪式有关。
千寻塔出土的零星的塔藏文物还有各种质地的念珠,包括珍珠、玛瑙、琥珀、珊瑚、水晶、琉璃、绿松石等等以及朱砂、云香、麝香、檀香、松香、水君子等药材,铜铃、铜盂等法器以及铜镯、铜镊子、铜挖耳、铜印纽等生活用品。在这些佛教文物中,有一些具有典型的宋代中原文化特点,如鎏金银质錾花盒、累丝梅云纹金耳饰等带有复杂而明显的中原工艺,而青白瓷普贤菩萨骑象像、文殊菩萨骑狮像,更是来自宋代景德镇的主要产品,还有铸有“湖州念二叔家”“成都刘家青铜照子”等铭文的银锭钮葵花形铜镜无疑是来自中原的生活用品。这些塔藏文物的发现都真实地反应了唐宋时期南诏政权、大理国民族政权与中原文化密切的交流和往来。
五
琳琅满目的宝塔奇珍带我们进入一个千年前南天佛国的神奇世界,这些闪耀在历史长河中的佛教艺术宝藏,为我们提供了生动详细的线索,勾勒出传说中妙香佛国大理的痕迹,徐徐展开了一幅妙香秘境的历史画卷,以物证史,为唐宋时期的南诏政权、大理国民族政权佛教文化的兴盛所叹服,仿佛走进《张胜温画卷》所想象和构筑的那个华美而绚烂的妙香世界。
《张胜温画卷》又称《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大理国梵像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全长1636厘米,宽30.4厘米,134开,是宋代大理国民族政权描工张胜温为大理国利贞皇帝段智兴绘制的佛教题材长卷,长度是清明上河图的三倍。画成于段智兴盛德五年(1180年),卷首即为《利贞皇帝礼佛图》,以巍巍点苍山为背景,描绘了大理国统治者段智兴率领王后、王妃、王子、王亲和文武大臣及仪仗卫士;卷中绘《南无释迦牟尼佛会图》以及各种佛、菩萨、天王、金刚等神像,不但与塔藏文物相对应,还有绘画中的一些宗教法器也能在塔藏文物中找到原型。可以说《张胜温画梵像卷》以精湛娴熟的绘画技术,疏密有致的线条,讲究的用色,塑造了生动活泼、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阐述和诠释着当时对整个信仰系统的视觉理解,营造了心目中金碧辉煌、绚丽灿烂的佛国世界,为后人呈现出一个多姿多彩的妙香秘境,不但是中国西南边疆的艺术珍品,也是世界佛教图像画中的瑰宝。结合画面中的诸多元素与塔藏文物的现实印证,《张胜温画梵像卷》也成为研究唐宋时期南诏政权、大理国民族政权宗教、艺术、民俗、服饰、礼仪、军事的宝贵资料。而在画卷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甚至揭晓了千寻塔建造方式这一千古之谜。
高耸入云的三塔矗立苍山脚下屹立千年不倒,堪称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关于三塔建塔的年代,不同史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1978年的维修发现在千寻塔内壁发现的中兴二年(899年)墨书题记可以确定,千寻塔的修建下限在南诏。那么,在一千二百多年前,人们是如何修建如此高大恢宏的建筑呢?至今,大理地区广为流传着堆土建塔,挖土成塔的民间说法。也就是每修一层塔就沿塔身四周堆土与塔成平面,方便修塔所需的砖瓦灰石等材料过肩挑人抬或者用畜力的运送。久而久之,塔周围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缓坡,直至塔建成之后再自上而下地将土挖掉露出塔身。三塔南北五里桥、七里桥、塔桥村等地名似乎都在印证着这种传奇的建造模式。然而,根据对三塔的考古维修发现,千寻塔外壁上残留着有规律的方孔,孔上下左右的距离大体与脚手架的“步”相近,可以推断这些方孔应该就是当时埋置脚手架水平横杆的支撑点。塔建成之后,再用透空花砖把孔封起来。《张胜温画梵像卷》第七十八至八十开“弥勒经变图”画面的左下角为我们揭晓了答案。画面上一座未完成的高塔和围绕在四面的脚手架还原了建塔的施工现场。由此可见,千寻塔还是采用了以搭建脚手架为主的施工方式。也就是沿着塔身四周用木杆、木板、绳子搭成一座可操作、堆放建筑材料的临时木架,建筑落成后将木架拆掉,这一建造方式已经和现代建筑施工方法基本类似,说明早在唐代,地处西南边疆的大理南诏政权已经掌握了中原主流的建筑技术。而两宋时期的大理国民族政权增建的南北小塔采用的是封闭式空心结构,内有直径仅3厘米的纤长木柱着说明,南北小塔是也是通过脚手架的方式,利用和塔身八角对应的墨线控制塔身保持笔直的形状而逐级搭建的。
巍峨高耸的三座塔顶上,竖立着高达8米的塔刹,维修中,众多精美的塔藏文物即出自塔刹中心柱中,实为“天宫藏宝”的重要发现。通过对塔顶四隅遗留的铁棍痕迹和其他古塔规制推断,千寻塔顶四周应镶嵌有四只金翅神鸟,即迦楼罗,印证了千寻塔震慑巨龙消除水患的思想功用。
高超的建造技术让崇圣寺千寻塔及南北两座小塔三足鼎立,以举世无双的姿态耸峙于苍山洱海之间,经历了数千年来无数次的地震依然巍然屹立,成为大理的千古地标和精神图腾。
通过对塔藏文物的研究,我们了解到,唐宋时期的南诏政权、大理国民族政权把最早传入的阿嵯耶观音奉为圣像,崇拜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五方如来佛,供奉各种形式的天龙八部护法神像;按照《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仪轨广建佛塔,举行祭祀活动;信奉大鹏金翅鸟,接受并融合大黑天作为民间土主庙的主神;集儒释于一身阿吒力,手持各式各样的金刚杵,念诵着各种陀罗尼神咒,在建塔、修葺或法事时将这些佛教艺术珍品置于塔中。三塔和崇圣寺以极具民族特色的宗教信仰,构建众神安宁和谐的精神世界,虔诚地祈祷着神灵护佑美丽的家园。
作为唐宋时期的南诏政权、大理国民族政权的重要历史文化遗存,三塔和塔藏文物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边疆各少数民族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是区域文化内涵的典型代表。这些风格独特的文物珍品,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艺术、文化艺术、宗教信仰、风情习俗等等历史信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是古代边疆各族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的集中体现,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通过对三塔历史文化的追溯和三塔塔藏文物历史价值及内涵的解读,我们加深了对三塔的认识和了解,丰富了唐宋时期的南诏政权、大理国民族政权的历史形象,人们得以更多角度地感受和欣赏文化遗产的魅力。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是文献记载的真实见证,展现了唐宋时期的南诏政权、大理国民族政权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发展水平,不仅是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直观展现,更是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的优秀文化遗产。
1981年,维修之后的三塔恢复了原状,更加巍峨挺拔。随后,为加强对三塔的保护和历史文化研究,1994年崇圣寺三塔文物保护管理所成立并组建三塔公园,引领世人走近三塔了解祖国的珍贵历史文化遗存。随后,围绕《崇圣寺三塔保护建设规划大纲》《祟圣寺保护建设规划修编》和《恢复重建崇圣寺规划方案》,重铸南诏建极大钟及钟楼、重铸雨铜观音及雨铜观音殿的愿望一一实现。直至2006年,崇圣寺恢复重建工程顺利完工,恢复重建的崇圣寺吸取历代经典建筑之精华,将北方建筑的恢宏大气和南方建筑的精巧秀丽融为一体,中轴线上前有三塔、建极大钟、雨铜观音殿,后有山门,护法殿、弥勒殿、十一面观音殿、大雄宝殿、阿嵯耶观音阁、望海楼等建筑,与三塔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尤其是大雄宝殿内由剑川高超的木雕技艺雕刻的《张胜温画梵像卷》,高1.8米,长117米的木雕长卷环绕供奉在大殿四壁内,这绝无仅有的木雕佛教艺术精品,堪称新时代的崇圣寺重器。
当我们伫立在三塔脚下,仰望高耸入云的三塔,漫步庄严的建筑之间,眼前一一闪现那些珍贵的塔藏文物,便是对古老文明的直观感受,这些珍贵的遗存印证和诠释着大理南天佛国的历史地位,展现着大理历史文化的风采和魅力。伴随着对文物价值不断的深化了解,中华先民用聪明才智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已经融入血脉,蕴含和体现着中华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思想感情和共同的心理素质激发的骄傲和自豪油然而生,这就是三塔赋予我们最现实的爱国教材,也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带给我们的精神洗礼和动人心扉的享受与启迪。
编辑手记:
中华民族的形成就如同涓涓溪流汇成江河并最终归于大海一般,各个民族和地区由于紧密联系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不断走到一起,在相对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论是人民大众还是各个民族涌现出的杰出人物,都在不断地强化着共同的民族和历史情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工作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要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并不是简单地把各个民族历史杂糅在一起,而是在尊重差异性中寻求共同的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为了共同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团结在一起,最终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本文所讲的崇圣寺三塔始建于唐代大理南诏政权劝丰佑时期,完成于宋代大理国民族政权时期。作为拥有独立的行政、外交和军事权力的南诏,建塔时仍然采用唐朝佛塔形式,可见大理与中原文化联系之紧密。现在,虽然历经千余年,崇圣寺三塔仍然矗立,因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得到保护。它经历了唐代南诏政权、宋代大理国民族政权的光辉历史,经历了元明清时期的寰宇一统,其初建至今的历史,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形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