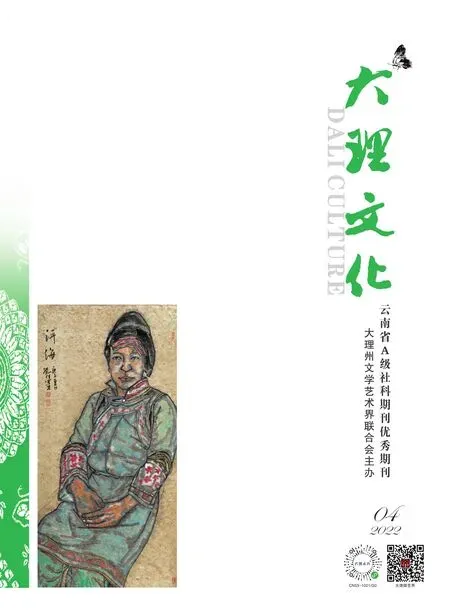后墙,花影,与水光 (组诗)
●杨玉璋
祖传
我们这样的坝子里
绚丽的流言埋在篱笆下
怪异的传说晒在渔网里
最朴素的那一个
往往埋在某户人家的土地里
于是某树叶哔啵轻炸的
夜里
两斤二锅头下去
老头躺倒
田埂上
我和我哥刨了很久
松软土坑里始终
只有一抹月光
七月半
村落不停过
早晨长出古井和草芽
傍晚长出小孩子
小山坡
长满香火
秋蝉乱弹
何识衣帽分量
柿子树和夕阳一同滴进流水
霞色染红草绳
我们伟大的先灵
人群散去后
萧索地
独坐在火堆里
龙抬头
山无名
飞鸟衔来草籽
古衣冠的一道冢
云烟生翠
山林之雨中
神庙现形
荷叶底,水面上
绿色的火焰
无名水
女孩子歪在树干边
青乌乌的一条绿苔
焚香
香炉是翠绿点金肚
镂花黄铜顶
袅袅而起桃花魂
探出半个身
勾在阁楼望了半晌
拈乱外祖母好几针毛线
和外祖父手中书页哗啦乱响
正午时分
小井中,阳光晒得碧水冒烟
几片桃花瓣弄得我鼻子发痒
我听得不无惆怅
在一个民间故事里
白族姑娘化身春燕
从此桃花溅满了这座山头
洱海
洱海其实只是一个不大
不小的水潭
水潭对于穷人的意义
只有鱼
草蓝色的鱼活蹦乱跳
渔民的儿子也活蹦乱跳
突然从某丛枯色参差的长草中钻出来
弦鼓般高亢错落的口音是欢喜的部分
柔软额发和指甲缝隙中的鱼腥味
是厌倦的部分
还有一点惆怅
即使不是最多愁善感的那一个
也发怵于观看满地丧失光泽的鳞甲和这残酷的日常仪式
这悲悯或许来自于一个同病相怜的身份
因此一些儿子在另一些儿子处
找到了“命运”和“意义”它们
一部分被吞入肚中,变成茁壮生长动力
一部分继续,替他们在蓝色更深的地方潜游
避震
有一年地震
我们连夜避回喜洲去
飞檐长草,燕雀啁啾
整日坐在偏院中的我
只看深静的井水无风而晃
素馨花香灌满身体
神魄如风筝起地而去
有人拉一拉线
温柔地喊一两声
于是一段光阴
一笔隐去般
杳然无踪迹
永远搁置于世外
楼间记
阁楼间的幽灵
拈着一线隙中光
司阁楼中万物悬浮
何时身消融于幻
梦消融于空
或者簌簌地生长和经年累月地等待与消磨
在我和我惺忪的回忆之中
木樨花落之时
方显杀伐之气
从那么多山雾蒙蒙中抽离一次
一个旁落的清晨
我亦不敢转身看,来自古老时空的
一片水光在墙上明灭
盘错着二胡声,木轴声,尘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