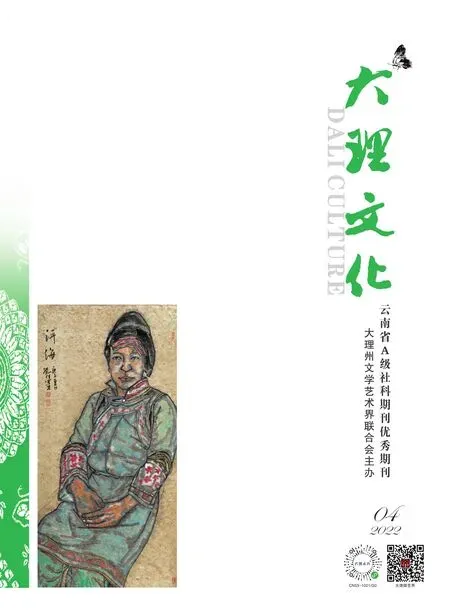月亮带走金质的黄昏(组诗)
●范庆奇
洱海边看鸟
几只海鸟由湖里飞到枯枝上
平静的湖面激起了浪花
在这么巨大的水面上
漂浮的鸟儿就像白色塑料袋
更多的时间它们只在水里
随着水纹的方向任意流动
不得不说我有些羡慕它们
起码拥有这片水
拥有飞翔和落下的本领
走在水边,很少能捡到海螺
只是每当夜晚,那一阵一阵的波浪
敲击着月亮的银币
那些鸟在芦苇丛中窃窃私语
多么静的夜晚
除了海浪声,再也没有什么是响的
再也没有什么值得用诗歌的形式呈现
苍山之上
苍山脚下,天空是远的
只有借助外物才能看清一朵云
四方涌来的游人争先爬上山顶
他们极目远眺,想看清一座城市
从苍山上往下看,城市变得渺小
那踽踽而行的人就像蚂蚁
在大地的心脏上搬运石块
唯有山间的庙宇是广大的
接受善恶美丑的人前来跪拜
常年生活在水边的人
习惯了海风吹拂脸颊
习惯了以一泊水照亮自己
高原上没有海,人们便把想象融入大湖
许多人一生都没有走出高原
也没能见一见海的本来面目
只能站在苍山上,朝水流的方向望去
夜过滇池
滇池对我来说是神秘的存在
在南高原生活了十八年
却从未有过一面之缘
我想它是一面灵性的水域
古滇国的文字融于水中
只要伸手进去便能捞出一卷残帛
行车路过滇池,水面一片漆黑
我本想下去走走
还是算了吧,神秘最是宝贵
也免得惊扰了夜栖的海鸥
南面的夜空被霓虹灯照亮
粼粼波光在微风的吹拂下荡开
“未完成效应”从心理的紧张系统是否得到解除,来解释学生会对“未完成的课堂”记忆深刻:人们对于已完成的工作的心里紧张系统已经解除,因而回忆量少,而未完成的工作所引起的心理紧张系统还没有得到解除,因而回忆量较多。学生们会因“不完整课堂”心理紧张而忧心忡忡,对这样“半途而废”的课堂念念不忘,这样的心理机制驱使着他们主动地完成教学任务。
这个时候的滇池最神秘
水天皆是一块幕布
我身后城里生活的人都是台前人
一条江的慈悲
这个季节适合鼓胀的江水述说悲伤
今年的雨水下了一场又一场
秧田满溢,稻根发黑
玉米地的泥土被冲走,露出粉白的根须
池塘里的鱼儿浮出水面,望断无垠的乌云
什么时候雨才能停下,鸟儿飞过天空
这条江收容四面八方汇来的流浪客
截肢的树木,干枯的茅草
更多是被丢弃的垃圾
这些不被人重视的东西再次出现在眼前
那么明显,那么坚硬地堵住水流的去路
以往犯下的罪行以这种形式强加于他们
我敬仰一条江的慈悲
它从不计较伤害
以最博大的胸怀容纳洪水
只是,一条江的慈悲也是有限的
碎镜子
黑暗中的峡谷,不觉得幽闭
立身此地,风像一匹野马从身旁跑过
身前是山丘,身后是耸立的山峰
中间独留一片平坦之地
人们在上面盖房子,开垦土地
生老病死,将一生托付给山林
如同一棵瓜,遵循瓜熟蒂落
山崖下,溪水暗中涌动
水声惊醒夜宿的鸟雀
失眠的我坐在岸边,数掉进河里的月亮
河滩上每一汪水潭都是一面镜子
或者是,打碎的镜子被人遗弃在这
让我想到村庄,是多么幸福,又多么寂寞
过渡
鸽群隐没是过渡的起始
它们先于夕阳消逝
藏进某个不为人知的空房子
此时月亮正从远处赶来
路灯渐次发光,机器停止痨嗽
温热的路面环抱一天的疲乏
离群索居的人走上偏执的路
潮湿的脚印,是城市的赐予
他们是月亮洒落的星星
散布在城市周围
总有些过渡容易让人忽略
黑白的变化,城市不搭的结构
它的出身和它的名字一样廉价
——城乡结合部
我们行走,从不过问
雨中的香樟在招手
捡起地上的叶片
细数时间的划痕
有一刀指向自己的心脏
有一刀劈向他人的头颅
编辑手记:
何永飞的诗歌有着属于自己的语调,用通俗的语言和不俗的想象力塑造着一个理想的诗歌世界。诗人对诗歌意象的创新在于摆脱了传统的意象群,熟练地驾驭着常人避免使用的意象。那些极端的、看似无法掌控的甚至立场相对的意象,在诗人强大意志的统领下成为一个个乖顺的充分表露诗人精神的符号。诗人心中拥有一轮永不熄灭的太阳,不断吸引着他周围的事物:小草、飞鸟、白骨、弯刀、短命鬼……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芸芸众生被诗人的光照耀着,最终臣服于诗人笔下,跟随他一起反思历史,思索无常的人生与命运,追寻生死终极的意义。而诗人在高筑自我精神世界的同时,也不忘关注人间疾苦,《发现金矿》便有着对村庄发展与生态破坏之间矛盾现实的思考。
也许是受金庸小说的影响,姚瑶笔下的大理既神秘又多了分江湖气。诗人深陷在大理的月光与白族姑娘的舞步里,而我们深陷在诗人浪漫多情的诗句里。诗人是一位到访大理的“诗客”,在推杯换盏间,亦梦亦醒,赋诗明志。大理,留下了旅人的失意、忧愁与叹息,只让他们带走思念与酒醒后的洒脱、平静,再伴随温柔的风声,回到另一个相似的故乡的梦里。
白族民居的后墙、墙上投射的花影与洱海回荡的水光,点染出杨玉璋心中的诗意,迷人的大理坝子成为生长她诗歌的沃土。那些流传在白族村落的流言传说、风俗民情成为诗里最动人的旋律。《七月半》里诗人描绘了中元节祭祖的场面,动词用得极好,柿子树与夕阳的“滴”极具画面感,在流水的投影里,固态的事物具有流动感,如同颜料滴入水中,但却成为无法融化的风景。古井、草芽、小孩子的“长出”,香火的“长满”,“长”意味着生,万物之“生”与逝去先灵之“死”形成对比,村民在万物更迭的自然规律里延续着人类的文化传统,简短的诗句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浓厚且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敬畏自然、敬畏生命,在秋收里暂停脚步,感恩祖先的付出和自然的馈赠,这便是“七月半”的意义。
来自滇东的年轻诗人范庆奇站在滇西的洱海边看飞鸟,站在苍山上俯视这座叫大理的小城,用诗歌的形式带我们感受这座小城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