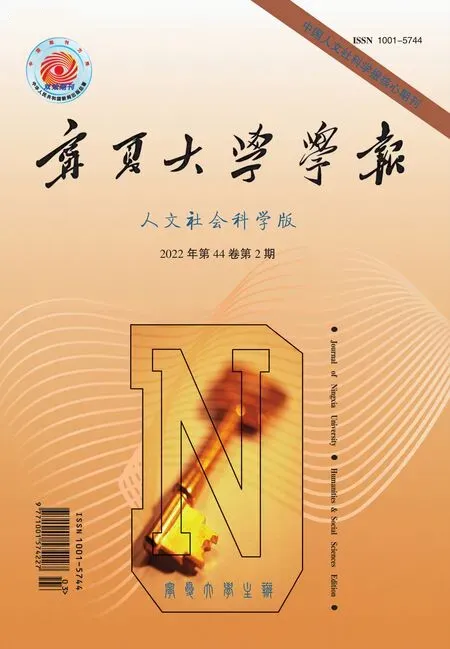女性的缺席与在场:从《使女的故事》看反乌托邦小说的革新与发展
焦红乐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20 世纪以来,反乌托邦文学(anti-utopianliterat ure)作为乌托邦文学的“反方案”而备受瞩目。乌托邦文学往往描写幻想中美好的未来社会,其中包含着对当代现实的批判,而反乌托邦文学则是在乌托邦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个分支,它往往通过描绘阴森可怖的未来社会图景来影射现实社会的黑暗和丑恶。乌托邦文学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到了16 世纪,莫尔《乌有乡》(1516年)的问世则奠定了近代乌托邦文学的基石,之后英国作家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1627年)和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1891年)等,都营造出对未来社会的美好幻想。然而在18 世纪和19 世纪,人们逐渐发现现代性建构过程中出现了与最初科学、理性、民主、自由等完美构想的背离,因此,早期的乌托邦理想逐渐遭到人们的质疑与批判,反乌托邦文学应运而生。20 世纪以来,世界大战、经济危机、政治极权和科技伦理的威胁时刻迫使着人们反思现代性问题,并广泛探寻各种疗救方案。因此,各种反乌托邦文学不断出现,构成了一道奇异的风景。扎米亚京的《我们》和阿道司·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威廉·戈尔丁的《蝇王》等,都是反乌托邦文学的代表作。
《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1985年)是“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的第六部长篇小说。它一经问世,就斩获“加拿大总督奖”“洛杉矶时报奖”等多项大奖,在国际文坛引起了轰动。这部作品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但同时又被奉为独具特色的“女性主义经典”,很多评论家将它与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相媲美,并称之为“女性主义的《一九八四》”。作为一部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承袭了自《美妙的新世界》和《一九八四》以来的推测性社会小说的传统”[1],但不同的是,它融入了作者鲜明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特征,是一部典型的女性视角的反面乌托邦。它鲜明地体现出女性作家介入反乌托邦文学后,对其进行的颠覆与重构。
一 女性话语:缺失与重构
阿特伍德曾在《其他的世界:科幻小说与人类想象》(In Other Worlds:SF and the Human Imagination)中谈到她与乔治·奥威尔的渊源关系:“我是读着乔治·奥威尔的著作长大的。”[2]9 岁时,她便读了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12 岁时读了《一九八四》,这两部书都使其深受震撼,亦使其对专制主义有了最初的了解,而在之后的人生中,奥威尔更是“成为我(阿特伍德)学习效法的前辈”[3]。故而,她创作了自己的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向前辈致敬。虽然《使女的故事》与《一九八四》的故事情节模式大致相似,都是对极权统治下人们生存境遇的描写,但是相似的情节模式,在一个女性作家笔下和一个男性作家笔下却有着截然的不同。在《使女的故事》中不同叙述声音和女性意识的融入,使反乌托邦文学中女性话语缺失的局面得到了扭转,反乌托邦文学从女性意识和女性话语的缺失走向了重构。
一直以来,奥威尔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笔审视和记录着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并通过其作品对极权主义的恐怖揭露和对现实社会的隐喻性批叛而被誉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美国著名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更是称赞其“仅以自己简单、直率、不受蒙蔽的才智来面对世界的美德……他使我们不再需要精神鸦片的麻醉”[4]。1936年7 月西班牙内战爆发,而《一九八四》正是奥威尔在亲历西班牙内战,目睹内战中左翼各派复杂斗争的基础上创作的。作品遥想了极权国家大洋国(Oceania)无所不在的高压统治,描写了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的抗争与失败。从作品来看,奥威尔虽然将其笔锋指向了极权政治对人的压迫,以及对人性的残害,但是其笔下所关注的人,似乎并不包括女性,女性在他的文本中没有任何的权力话语,没有言说自己的可能。
苏珊·S. 兰瑟在其女性主义叙事理论中指出:“我们就可能把叙事技巧不仅看成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且还是意识形态本身。也就是说叙述声音位于‘社会地位和文学实践’的交界处,体现了社会、经济和文学的存在状况。”[5]因此,“叙述声音”不仅是形式结构、叙事技巧,同时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是话语权力的表征。在《一九八四》中,作者使用了全知视角和有限视角的交叉,有效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然而,进一步对作家叙述策略背后隐藏的权力话语进行挖掘就会发现,奥威尔采用的叙述形式暴露出了他男性至上的意识形态和根深蒂固的性别等级观念,它代表的是一种男性的权力话语。按照苏珊·S.兰瑟对叙事模式的划分,《一九八四》属于作者型叙述声音,这是一种单一和强大的声音范畴,叙述者经常通过自我权威化来使其身份等同于作者,成为像上帝一样的绝对存在。在作品中,叙述者对人物的介绍都是采用这种全知视角,比如“凯瑟琳是个头发淡黄、身高体直的女人……要是你没有发现这张脸的背后几乎是空空洞洞的,你很可能称这种脸是高尚的”[6]。对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的描写,使我们感到叙述人掌控了一切权威声音,他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一一向我们介绍着出场的人物。我们所认知的女性形象都是通过男性之口来表述的,女性没有任何自我表达和自我言说的可能性。
此外,除了对全知视角的运用外,奥威尔还巧妙地交织了人物的有限视角,使全知叙述者和主人公温斯顿轮流作为“观察者”来进行叙述。比如文中对妓女的描写就是通过温斯顿的视角,“她一头倒在床上,一点也没有什么预备动作,就马上撩起了裙子,这种粗野、可怕的样子是你所想象不到的”[7]。通过温斯顿这一男性视角,叙述者男性身份中潜伏的优越感和权威性,以及对女性的贬低都在不自觉中暴露无遗。在父权文化传统中,作者的声音往往是被男性占据的,男性作家总是暗示,“语言这种东西几乎是无法由女性的舌头正确地表达出来的”[8]。故此,奥威尔也并没有逃开西方传统父权文化的影响,在作品中剥夺了女性的权力话语,清晰地显示出了他男性身份的叙述立场。
反观《使女的故事》这部作品,它是一部直接从女性视角出发,对男性中心叙述声音进行反叛的反乌托邦小说,是“茱莉娅眼中的世界”[9]。《使女的故事》可归为女性个人叙述声音,它主要是以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作为文本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讲述自己被迫成为“使女”后所遭受的残害和压迫,揭露了该国诸多违背常理的社会现象。同时,阿特伍德还把从奥芙弗雷德的视角描述的她在基列国沦为使女后的感受、情绪、心理作为文本叙述的重心。读者可以跟随奥芙弗雷德一起体验她所经历的一切,她失去丈夫、孩子的痛楚,她被剥夺一切权利沦为生育工具的无奈,她在生存与反抗中的绝望挣扎等等,均使我们感同身受。如在基列国建国时,女性被剥夺工作权、财产权,重新回归家庭,沦为工具化的客体之初,奥芙弗雷德描述到“可是某些东西还是改变了,某种平衡。我觉得整个人在缩小,当他搂住我,拥我入怀时,我缩成了玩具娃娃那么大……如今我属于他”[10];而在被迫成为使女之后,她“开始对自己的裸身感到陌生”[11],并认为自己的“身体似乎已陈旧过时”[12];以至于她终于开始意识到“如今我的肉体为它自己作了不同的安排”[13]。这种从女性视角描述女性自己的切身感受,无疑使小说显示出了作家的性别立场和女性关怀,也鲜明地表达了作者为女性代言的身份立场。
再者,在作品中,作者还让处于男性集权中心的女主人公尝试着不断以各种形式表达自我,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从而夺回女性权力话语。在文中,奥芙弗雷德总是会假想出一个听众“你”,对其进行诉说:“是讲,而不是写……但是,只要是故事,就算是在我脑海中,我也是在讲给某个人听。”[14]文中很多地方暗示出奥芙弗雷德在与一个虚拟的“你”进行对话,这表明她渴望诉说自己,渴望以这种方式反抗男性与极权的压迫。同时在作品中,奥芙弗雷德的前一个奥芙弗雷德也是渴望通过书写来留下自己的痕迹,以示反抗。虽然她只在橱柜底部昏暗的角落里留下了用针或指甲刻出的一小行字“Nolite te bastardes carborundorum”(意为“别让那些杂种骑在你头上”)[15],但是这行字,对后来的奥芙弗雷德来说却意义重大:
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甚至不知道它是哪种语言……不管怎么说,它传达着某种信息,而且是文字信息,这本身就大逆不道,更何况目前尚未被人发现。除了我,这行字就是写给我看的。写给后来者看的。思索这行字令我快乐。想到我正与她,与那个不知名的女人默默交流同样令我快乐[16]。
通过这行字,女性之间取得了神秘的关联,她们意识到,她们的言语终于能够传达给至少另一个人。这也使得奥芙弗雷德在逃出基列国之后,通过录音的形式把自己在基列国的经历讲述出来,让后人了解那段女性的屈辱史,避免自己成为历史的空白。福柯曾在其著名的权力—话语理论中揭示了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共谋关系,指出话语与权力之间存在着同一性关系,话语是权力的话语,权力是话语的权力。《使女的故事》中女性对语言表达的渴望和努力,正是其对女性权力话语重构的一种努力与尝试。
相较于《一九八四》,《使女的故事》从女性视角关注女性命运,让女性来叙述和言说自己的心理世界、身体感受、她们与男性的关系、她们自己之间的关系,以及她们的生存处境等,表现了女性作家在介入反乌托邦文学之后,对女性权力话语的重构,彰显了女性作家笔下反乌托邦小说创作中的女性立场以及女性关怀。
二 女性形象:扭曲与重塑
纵观反乌托邦文学传统,由于大部分的反乌托邦小说都是出自男性作家之手,他们笔下的女性总是作为背景或者推动情节发展的“催化剂”而出现,因此作品中常常有意无意地呈现出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和捏造,体现出明显的性别歧视。尤其是作为反乌托邦文学代表作的《我们》《美妙的新世界》和《一九八四》,它们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要么是无性别的机器人形象,要么是引诱男主人公的“诱惑者”形象,有时甚至对女性形象进行丑化、妖魔化,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家对女性意识的遮蔽和男性中心的观念。
从20 世纪80年代起,乔治·奥威尔就遭到了女性主义批评者的抨击,美国学者达芙妮·帕蒂(Daphne Patai)在其《奥威尔神话:对男性意识形态的研 究》(The Orwell Mystique:A Study of Male Ideology,1984年)中通过对奥威尔作品的系统解读,指出贯穿奥威尔全部作品的一条主线就是其男性中心论思想。在《一九八四》中,奥威尔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明显流露出了厌女倾向和大男子主义思想。在作品中,奥威尔首先借温斯顿之口道出其对女人的看法:“几乎所有的女人他都不喜欢……总是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是党的最盲目的拥护者,生吞活剥口号的人,义务的密探,非正统思想的检查员”[17]。在温斯顿眼中,不管是母亲、妻子还是情人,所有女人都是“最笨、最粗俗、最无脑”的人。一直以来,茱莉亚被认为是奥威尔笔下“刻画的最丰满,最有吸引力的女性主角之一”[18],但其实茱莉娅形象背后隐含的正是奥威尔的性别等级思想。茱莉亚与作品中其他女性相比显得很不同,她主动追求温斯顿,希望自己可以成为真正的女人,并且竭尽全力地打扮自己,取悦温斯顿,努力成为他的爱人。但是由于大洋国一直以来实行泯灭人性本能欲望的政策来统治思想,所以在温斯顿看来,对性欲的释放即是对党的反叛,故而,在他眼中茱莉亚只是他的“附属品”,是他反抗党的工具,是促进他加入反叛行动的催化剂,是他口中的“腰部以下的叛逆”[19]。由此可见,奥威尔从根本上否定女性的存在价值,女性的出现只是与性和工具联系在一起。每一个作家在人物形象塑造的过程中都会无意识地将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流露出来,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虽将批判矛头直指极权政治,但是其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表明了作者并未否定男性对女性命运的随意支配权,作品中充斥着男性中心的性别观念。
社会发展的过程其实也是女性成长的过程,社会地位的缺失、性别歧视的压迫一直以来都直接打击着女性的身心,所以面对社会现实,女性不是在其中沉沦,就是要自寻出路。在《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就一改反乌托邦小说将女性作为写作背景的传统,直接将女性作为中心人物,直面女性问题,把现实生活中女性遭受的各种不公正移植到男性统治的极权国家——基列共和国,并通过使女奥芙弗雷德之口讲述统治者对妇女的迫害和奴役,塑造了一系列真实而具有现实意义的女性形象。
在作品中,奥芙弗雷德既作为受迫害的女性形象,同时又作为反抗的女性形象出现。奥芙弗雷德在被迫成为使女之前是一名相对独立的职业女性,然而在政变之后,她失去了一切,成为了使女,彻底回到被奴役和被压迫的地位。在成为使女后,她甚至被剥夺了真实姓名,被命名为奥芙弗雷德。名字是表征个体的特定符号,是识别一个人最重要、最基本的标志,名字的缺失即意味着身份的丧失、自我主体的丧失。阿特伍德还曾在该作品新版序言中提到:“这个名字来自一个男性之名,‘弗雷德’(Fred),加上前缀‘奥芙’(of)表示从属……这个名字里还隐藏着另一种可能:‘献祭的’(offered),意味着一种宗教献祭,一个作为祭品供奉的受害者。”[20]所以,主人公奥芙弗雷德的名字既表示男性的占有物,又具有受害者之意味。同时,作者还借奥芙弗雷德之口回忆了其沦为“行走的子宫”充当生殖工具期间的生活回忆,虽以平静的口吻表述,但其中却充满了悲凉凄惨之感。尤其是那些令使女们痛苦而尴尬的受精仪式、分娩仪式和“羞辱荡妇”活动,都深刻地揭示了女性的悲惨境遇。
阿特伍德笔下的女性尤其是使女,虽然处于男性极权的普遍压迫和恐怖之中,但是作者并没有对女性的未来失去信心。她塑造的使女奥芙弗雷德虽备受身心折磨,胆怯而懦弱,但并没有彻底地放弃自我成为行尸走肉,而是以一种“身体写作”(“身体写作”是法国女权主义代表人物埃莱娜·西苏在20 世纪70年代提出的理论,在其代表作《美杜莎的笑声》一文中,她指出:“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声音”。她认为,“身体写作”的目的在于反抗强大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文化,从而谋求妇女的解放,是一种新型的女性解放策略——笔者注。)的独特方式讲述故事,重新夺回对语言的控制权,进行反抗。在作品中,奥芙弗雷德通过录音的形式把自己在基列共和国的经历讲述出来,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西苏所提倡的“身体写作”,是对男性社会种种束缚和压迫的反抗。同时在文本的字里行间,也可看到,奥芙弗雷德一直怀揣着与孩子、丈夫重聚的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支撑自己,鼓励自己坚持下去,以此来反抗男性极权政治的压迫。比如她总是回忆往昔的美好岁月,以此作为信念支撑自己,同时还会在没有人的时候在心里自哼自唱一些被认为极具危险性的“禁歌”,并且会时时默念自己的真实姓名,以便有一日使其重见天日,她甚至还会在大主教书房陪他取乐之时趁机进行阅读,要知道在基列国女性是被禁止阅读的。可以说,这些微小的反抗性的举动贯穿全书,正是这些细微且不易被察觉的反抗行为,使得奥芙弗雷德作为女性反抗者的形象更加真实而深刻。
与此同时,作者还借奥芙弗雷德之口描述了作为极端反抗者形象出现的莫伊拉。莫伊拉曾是一个女同性恋者,也是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无视男性的存在,盼望通过女性自身的努力和解放,建立一个女性文化的乌托邦世界,然而小说中她的结局表明她的主张并没有实现。这也表明在作者心中,女性要想获得解放、取得幸福,单靠妇女自身是实现不了的,体现出作者对女性问题的关注。除了呈现以莫伊拉为代表的妇女运动的探索者形象外,作者还塑造了另一类以丽迪亚嬷嬷为代表的“男性帮凶”形象。作为嬷嬷,她们的职责是教化使女,并反复向使女们灌输多多生养的思想,让使女们以自愿成为生殖工具,拯救全人类为使命。阿特伍德对这些充当男性统治者传声筒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从侧面体现了她对妇女自身问题的严肃思考。同时也暗示着在形成男女两性不平等地位的过程中,女性本身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见,阿特伍德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背后都隐含着她本人的女性意识及人文关怀,每一种女性形象的塑造都有其真实性和现实意义。
通过对比,可以看到,以往传统反乌托邦小说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往往充满着想象、扭曲甚至是丑化的成分,而阿特伍德明显对女性形象进行了重塑,她笔下的女性真实而深刻,每一形象背后都体现着作者对女性自身处境的严肃思考,融入了鲜明的女性主题和独特的女性意识。可以说,《使女的故事》一方面弥补了传统反乌托邦小说以男性为中心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将对女性问题的探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不管是从叙事层面还是从形象层面,女性已从“缺席者”逐渐转变为了“在场者”。
三 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革新与发展
阿特伍德本人曾明确表示:“大多数反乌托邦的书——包括奥威尔的在内——都出自男性作家之笔,故而,观点多是从男性角度表达的……而我,想尝试着从女性角度写反乌托邦。”[21]因此,结合前文分析可知,相较于以《一九八四》为代表的传统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是作家对男性中心的乌托邦文学传统的批评和对发展女性主义视角所作出的努力,是一部女性主义和反乌托邦小说结合的典型作品。在它与传统男性作家笔下的反乌托邦小说的对比中,我们看到了女性作家介入之后,反乌托邦小说所呈现出的变化,即伴随着鲜明的女性意识的融入,千百年来西方反乌托邦文学中女性权力话语缺失和形象扭曲的局面得到了扭转,作品中女性意识的缺失现象也得到了弥补与矫正,同时也使传统反乌托邦小说的目光从对全人类命运的关注转移到对女性具体生存困境的关注上,这也恰恰正是反乌托邦小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革新与发展。
事实上,在18 世纪后半叶,在乌托邦小说文类的基础上就已经衍生出了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Feminist Utopias),它最早可追溯到萨拉·鲁滨逊·司各特的《千年圣殿》。露西·萨吉森曾指出:“女性主义也是具有激进的颠覆潜力,正因为如此,它从乌托邦中找到一个得心应手的批判位置。”[22]但不管是玛丽·布莱德里·雷恩的《米佐拉:一个语言》,还是夏洛蒂·帕金斯·吉尔曼的《她乡》等早期女性主义乌托邦文学,都是一种为取代男权统治而提出建构男性消失的乌托邦社会。它们虽描绘了女性乌托邦海市蜃楼般的美好幻景,但是在本质上却是对现实困境的逃避。故而,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20 世纪80年代,出现了蕴含着忧患意识的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它是反乌托邦小说向女性主义的转向,是从“性政治”立场发出的挑战,《使女的故事》可以说是最早一部从女性意识的角度表现反乌托邦题材的作品。这一类型作品的出现与传统乌托邦小说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如露西·萨吉森所说:“在反乌托邦小说中,女权主义者对传统的乌托邦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融入了自我批判,为展望社会变革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23]乌托邦思想和女性主义思想有着共同的人类目标,即重构人类文化,所以二者的结合可以说是大有水到渠成之势。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人口危机、生态危机、性别歧视、种族争端、极权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人类社会,尤其是20 世纪70年代,美国和苏联几乎同时发生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工业废弃物污染事件、放射性物质泄漏事件和核泄漏污染事件等。阿特伍德作为一位具有人文关怀的作家,她认为艺术是个道德问题,艺术手段是她表达对社会感知和思考的中介,“小说创作是对社会道德伦理观念的一种监护。尤其是如今,各种有组织的宗教活动肆虐横行,政客们已经失信于民。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我们所能借以审视社会一些典型问题(而不是特殊问题)、审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相互间的行为方式、审视和评判别人和我们自身的形式已所剩无几,而小说就是仅剩的少数形式之一”[24]。《使女的故事》就是在此基础上开始创作的。作为一个受女性主义思想滋养的当代女性作家,阿特伍德在创作中,既努力揭示极权专制与男权统治之间的共谋关系,同时又呈现出女性作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的现实。因此她在乌托邦小说模式的基础上,努力开辟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反乌托邦小说和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的创作途径,以反乌托邦小说的创作模式来承载她对女性问题和人类问题的关注及思考,促使人们进一步审视现实社会。
《使女的故事》所采用的这一独特的女性主义反乌托小说写作模式,与同样关注女性独特体验的女性主义小说相比,在叙述模式上更具反乌托邦的政治元素和宏观性,是“政治想象作品”,它同时将女性生存同人类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在关注女性问题的同时,又不局限于此。如在文本中,阿特伍德在关注女性的同时,并没有忽略男性的存在,作品中的牺牲品并不仅仅是被物化了的女性。在极权政治下,男性也摆脱不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不管是地位低下的岗哨士兵、充当秘密警察的“眼目”、天使士兵还是身居高位的大主教,他们也都在各个方面受到限制,尤其在性问题上更加严苛。例如他们不准接触色情物品,不允许有婚外性行为,只有立下战功的男性才可以得到婚姻,而且是包办婚姻。总之,作者在受其自身女性意识影响的同时又没有局限其中,而是对女性乃至全人类的命运给予关注和思考,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反乌托邦小说的政治讽喻主题,这也正是《使女的故事》这部作品的独特价值体现,同时也是这种女性意识和传统反乌托邦小说结合后的全新写作模式的价值意义所在,是反乌托邦小说在女性意识介入后呈现出的革新与发展。
综上所述,从反乌托邦文学的传统来看,以往男性作家笔下的反乌托邦小说往往将关注点聚焦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科技革命、全人类的自由和命运等社会宏观性层面,很少涉足社会微观性问题,尤其是忽视女性问题。女性的自由,即使是有所涉及,也像我们上文分析的那样,没有将女性作为独立自由的个体,置于与男性同等的地位,而是将她们作为男性的附属物,男性欲望的投射物和受男性驱使、奴役的客体存在物,女性处于一种失语的地位。传统反乌托邦小说一直以来都是建立在父权体系的性别套路之上,并以这种性别策略作为社会权力结构的基础,所以很难超越性别歧视的范式[25],其对女性的书写也仍是停留在生理层面,并没有真正触及女性的社会性别,这都导致父权文化下的乌托邦及反乌托邦作家根本意识不到自己作品中流露出的“性别歧视”。但是与主流反乌托邦小说不同的是,在《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扭转了传统的性别原型,给传统乌托邦文学史上的性别模式以辛辣的讽刺,通过对女性权力话语的重新建构以及对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不仅唤醒了女性被长久尘封的集体记忆和身体体验,而且也为建构新的社会文化体系,探讨女性权力关系、身体与个体差异等奠定了基础。
阿特伍德作为女性作家,采用全新的书写策略,以突破旧的文类窠臼,面向一种新的人类潜质,对父权体系进行全面的抵制和颠覆。如果说男性知识精英笔下的传统反乌托邦小说创作很难走出性别二元对立的恶性循环的话,那么以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则开创了全新的主题,并带来了多样化的解放路径,为反乌托邦小说的进一步革新与发展作出了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