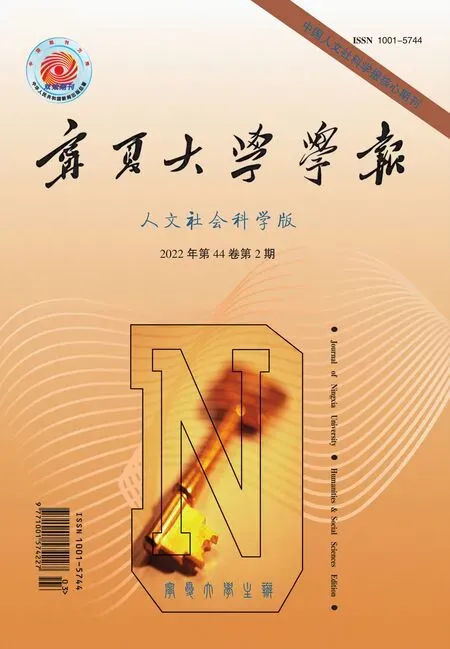厉鹗的文体观念
梁结玲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王士祯是康熙年间的诗坛领袖,他的“神韵”论弥漫于时代诗坛。在他身后,并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诗学流派,各地诗坛宗风不一,以厉鹗为代表的浙派在江南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汪沆称:“吾师樊榭厉先生以诗古文名东南者垂四十年。”[1]吴骞说道:“数十年来,吾浙称诗,皆推樊榭。”[2]厉鹗与沈德潜有过交往,虽然论诗宗旨有别,但并没有影响到两人的关系,袁枚对厉鹗这位同乡也颇多赞和。在清代诗坛由“神韵”向“格调”“性灵”转变的过程中,厉鹗是不可忽视的人物。厉鹗乃一介寒士,游历不广,但学识丰厚,当前,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创作、文学思想上。厉鹗对诗词有偏嗜,其诗词创作的题材其实相当传统,应酬、闲吟之作居多,缺乏健实的社会内容。与他的创作一样,厉鹗的文学思想不重外在的社会内容,而是注重文学内在的艺术性,这与传统重道轻文的文学思想迥异其趣。厉鹗对诗词艺术的辨析是很深入的,他对诗词的分析有明显的辨体色彩,深辨文体是其诗学思想的内核。厉鹗对文体的辨析很全面,既有不同文体间的辨析,又有对某一文体不同风格的辨析,他的文体观念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充分关注,这是很可惜的。
一 “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文体由共性向个性的推进
中国古代的文体非常丰富,从官场应制到乡俗文书,文体种类繁多,明代吴讷的《文体明辨》将传统文体分为127 类,文体的丰富性可想而知了。面对丰富的文体,辨析各文体的体式、风格、表现形式等是文学理论研究的任务,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中国古代文人是非常注重文体辨析的。徐师曾说道:“尝谓陶者尚型,冶者尚范,方者尚矩,圆者尚规,文章之有体也,此陶冶之型范,而方圆之规矩也。”[3]中国古代的文体辨析多是注重文体的共性,即某一文体的类型特征,这与西方的“文类”(genre)相似。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道:“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4]吴乔认为,“文饭诗酒”,意虽同但体制不一,“二者意岂有异?唯是体制辞语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啖饭则饱,可以养生,可以尽年,为人事之正道;饮酒则醉,忧者以乐,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5]。田同之辨诗词之别:“从来诗词并称,余谓诗人之词,真多而假少,词人之词,假多而真少。如邶风燕燕、日月、终风等篇,实有其别离,实有其摈弃,所谓文生于情也。若词则男子而作闺音,其写景也,忽发离别之悲。咏物也,全寓弃捐之恨。无其事,有其情,令读者魂绝色飞,所谓情生于文也。此诗词之辨也。”[6]不论是从体制、风格来看,还是从表现形式来看,中国古代关于文体的辨析多是着眼于文体的共性,试图通过共性的探索为写作提供指南,这与中国文学重实践的传统是一致的。
文学的各种文体有其共性,诗有诗之体,墓志铭有墓志铭之体,寿序有寿序之体,文体的共性是文体合法性存在的依据。虽然各种文体有其共性,但作者在运用这一文体时却表现出差异性,同样是写诗,李白与杜甫不一样,陆游与黄庭坚也不一样,不同的作家在运用同一文体时表现出个体差异。“明七子”注重诗体之辨析,他们严辨汉唐诗体,但其辨体注重的是诗体的共性,正是因为注重诗体的共性,其结果是流于门户之见。厉鹗论诗强调诗体之辨,他的辨体由共性转向个性,注重个体在文体运用上形成的风格。厉鹗的诗体辨析是对“明七子”的超越,他在《查莲坡蔗塘未定稿序》中说道:
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诗之有体,成于时代,阙乎性情,真气之所存,非可以剽拟似、可以陶冶得也。是故去卑而就高,避缛而趋洁,远流俗而向雅正,少陵所云:“多师为师”,荆公所谓“博观约取”,皆于体是辨。众制既明,炉鞴自我,吸揽前修,独造意匠,又辅以积卷之富,而清能灵解,即具其中。盖合群之作者之体而自有其体,然后诗之体可得而言也。自吕紫微作西江诗派,谢皋羽序睦州诗派,而诗于是乎有派。然犹后人瓣香所在,强为胪列耳,在诸公当日未尝龂龂然以派自居也。迨铁雅滥觞,已开陋习。有明中叶,李、何扬波于前,王、李承流于后,动于派别概天下之才俊,啖名者靡然从之,七子、五子,叠床架屋。本朝诗教极盛,英杰挺生,缀学之徒,名心未忘,或祖北地、济南之余论,以锢其神明;或袭一二钜公之遗貌,而未开生面。篇什虽繁,供人研玩者正自有限。于此有卓然不为所惑者,岂非特立之士哉?[7]
个人诗体的形成既受时代因素的影响,又与个人的性情、阅历、学识等因素紧密相关,用共性替代个性,造成了诗派的对立。厉鹗对只求共性的诗派提出了批评,认为真正的诗人应该具备自己的诗体风格。个人诗体风格的形成是诗歌创作成熟的表现,厉鹗将诗派与诗体对举,认为诗派很容易影响到个体诗风的形成,个体诗风的形成必须打破诗派的门户之见。厉鹗认为,要形成个体的诗体风格,必须取法高远,“去卑而就高,避缛而趋洁,远流俗而向雅正”。同时,他还认为,必须熔铸前贤,形成自己的风格,“合群之作者之体而自有其体,然后诗之体可得而言也”。各人各有其体,诗的体性才得以体现,没有个性,共性便无从体现,厉鹗关于诗体的共性与个性之辨是辩证的。关于文体的共性与个性,中国历代多以“通变”进行辨析。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说道:“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睎阳而异品矣。”[8]“通变”论解决了文体的发展问题,注重的是文体的发展方向,厉鹗文体的个性论较“通变”论更具体,更加关注个体文体风格的形成,这是对传统“通变”思想的突破。从明代到清初,诗派更迭不已,这些诗派多以某一诗风或理论相尚,缺乏对个体风格的尊重,厉鹗的批评可以说是深中其弊。“诗不以可无体,而不当有派”蕴含丰富的文体思想,可惜这一理论在当前并没有得到深入剖析。
在具体的诗词批评和创作中,厉鹗能够辨出各种文体的细微差别,体悟到不同作家在文体风格上的差异。厉鹗有《论词绝句十二首》,对各词人的文体能洞察秋毫。“张柳词名枉并驱,格高韵胜属西吴。可人风絮堕无影,低唱浅斟能道无?”[9]张先与柳永齐名,柳永的词较张先流传更广,“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厉鹗不是从作品影响力上来评判两者,而是从词体风格上辨析两者,认为张先“格高韵胜”,柳永的词较低俗。厉鹗论词主要是从风格上论述。他论姜夔:“旧时月色最清妍,香影都从授简传。赠与小红应不惜,赏音只有石湖仙。”他论贺祝:“贺梅子昔吴中住,一曲横塘自往还。难会寂音尊者意,也将绮障学东山。”他论张炎:“玉田秀笔溯清空,净洗花香意匠中。羡杀时人唤春水,源流故自寄闲翁。”婉约派的词风摇曳多姿,厉鹗非常赞赏这一派的词风,认为婉约派词风胜过豪放派词风。厉鹗对婉约派词人的评论细致入微,词体风格的辨析也是其词学理论构建的基础。
诗言志,文风的形成与个体的品性气质关系密切,厉鹗认为,不同的品性有不同的文体特征,他在追溯文体风格时往往能够结合作家的品性进行分析。“予闻道家之说,出于老子,务去健羡,黜聪明,以求其所谓杳冥昏默者。若雕肝镌肾,用力于一言一语之工,毋乃与道远乎?文石有志于道,奚不惮烦而若是?今读其诗,天机所到,自然流露,如霜下之钟,风前之籁,应气则鸣,初无旬锻月炼之苦,而达生遗物,能使人忘去荣悴得丧所在,然后知文石之诗之进乎道,向之以诗人求文石,犹浅之乎言诗矣”[10]。道家重天然,认为天然胜人为,道家之诗体自然也是“天机所到,自然流露”。道家之人有道家之诗体,孝子则有孝子之诗体。厉鹗评友人之诗:“总先生生平不离亲侧,无山川梦寐之阻,故其诗不必如《陟岵》;无‘何食何尝’之戚,故其诗不必如《鸨羽》;无‘我独不卒’之痛,故其诗不必如《蓼莪》;无经营尽瘁之嗟,故其诗不必如《北山》。而念甥侄,笃交游,见云泉而宅心,与缁褐而为侣,凡形于言者,何莫非其情之所甚挚,而先生亦岂肯求闻于后,与世之诗人争工拙哉?”[11]同为孝,而诗体不必如一,人各有其体,不必局限于前人,厉鹗对诗体的辨析是辩证的。
游仙诗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诗体,此体诗多是通过描写仙人、仙界以抒发诗人内心之忧思。厉鹗在19 岁时就写下了《游仙百咏》,后又有《续游仙百咏》《再续游仙百咏》。厉鹗的游仙诗辨于体而又能别出新意,他对此颇为自豪,“游仙诗,自晋郭景纯倡之,逮唐曹尧宾、明马鹤松连篇累牍,奇艳可诵。予闲居寡欢,偶尔缀韵,辄成百章,大要游思呓语,杂以感慨,玉茗先生所谓‘事之所无,安知非情之所有’者也。且灵均作《骚》,尚讬于云中君、湘夫人,其亦庶几不悖作者之意乎?有好事者出而读之,词虽不工,聊当龟兹一觉云尔”[12]。“昔谢逸作蝴蝶诗三百首,人呼为‘谢蝴蝶’。世有知我者,其将以予为‘厉游仙’乎?”[13]厉鹗的游仙诗既秉承了传统游仙诗的风格,又别出新裁,他以“厉游仙”自期,希望在这一诗体上有所建树,其诗体风格创新的意识不言自明。
二 尚雅的语体风格追求
成熟的文体自有其话语的方式,童庆炳在《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一书中认为,“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14]。中国古代注重不同文体的话语特征,元代刘祁说道:“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故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当以奇异自强。四六宜用前人成语,复不宜生涩求异。如散文不宜用诗家语,诗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赋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宜犯律赋语,皆判然各异。如杂用之,非唯失体,且梗目难通。”[15]袁枚认为,古文在语体上必须要“古”,“此体最严:一切绮语、骈语、理学语、二氏语、尺牍词赋语、注疏考据语,俱不可以相侵”[16]。诗、词、小说的文体不同,话语的方式不一样,同一种文体,不同作家的话语方式也不一样,“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17]。语体因文体而有别,也因人而有别,作家的个性气质、审美趣味在语体上得到了影射。刘勰说:“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18]中国古代并没有职业作家,文人的诗词创作多来自个人的雅趣,在语体风格上,文人多崇雅抑俗,雅俗之辨也是文人常论的话题。
厉鹗乃一介文人,生平未仕,没有惊天动地的伟绩,他以诗词及文化活动为职志,东南的诗坛、诗文集会总少不了他的影子。“韩江之雅集、沽上之题襟,虽合群雅之长,而总持风雅,实先生为之倡率也”[19]。厉鹗个性耿介,不谐于俗,诗文创作也不苟于俗,他自称:“予生平不谐于俗,所为诗文亦不谐于俗,故不欲向不知我者而索序。”[20]作为传统的文人,厉鹗反对诗词俗化,认为诗词应该表现出作家的雅趣。厉鹗的诗多是纪游、应酬之作,词也没有跳出传统婉约词的范畴,从审美趣味上来看,厉鹗其实是非常传统的文人。文人尚雅,言语方式是雅趣的重要表现,厉鹗认为,各种文体都应在表述上追求高雅的文风。他还认为,诗与词在文体上并无尊卑之别,都是文人雅趣的表现,“词源于乐府,乐府源于诗。四诗大、小雅之材,合百有五,材之雅者,风之所由美,颂之所由成。由诗而乐府而词,必企夫雅之一言,而可以卓然自命为作者,故曾端伯选词,名《乐府雅词》;周公谨善为词,题其堂曰‘志雅’。词之为体,委曲啴缓,非纬之以雅,鲜有不与波俱靡,而失其正者矣。……予爱小山词,惜沈、陈二子不能词,而不得与小山俱传也;又惜小山必待寄情声律,流连惑溺,而致涪翁有‘鼓舞不厌’之嘲讥也。今诸君词之工,不减小山,而所讬兴,乃在感时赋物、登高送远之间,远而文,澹而秀,缠绵而不失其正,骋雅人之能事,方将凌铄周、秦,颉颃姜、史,日进焉而未有所止”[21]。厉鹗认为由诗而乐府而词,文体虽然不断变化,但各文体求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雅是各文体的通性。他认为,诗词的言语方式除了要符合词体的基本特征,还要用优雅的方式来表现作者超尘拔俗的志趣。张先的词题材狭小,多是文人之情思雅志,柳永的词题材较广,但浮艳低俗,在《论词绝句》中,厉鹗认为,张先的词“格高韵胜”,要胜过柳永,这一评价正是建立在语体风格之上。言语方式及其用语之雅是厉鹗关注的重心,他评友人的诗:“故其为诗,澄汰众虑,清思眑冥,松寒水洁,不可近睨;至琴言酒坐,送别登楼,则往往绵密周环,情不与辞俱尽。使其克永天年,驱使豪牍,殆未可量,而惜乎其仅此也!或谓圣几诗语境冷峭,故非寿征。古固有少日为衰残语,而年与位俱高者。即使圣几以诗征其不永,如长吉之以抉摘致罚,惇夫之以‘呻吟’名集,要为姓氏长留天地间。彼藉荣,享上寿,殁而无一可称,将与蟪蛄蝼蚁同归丘墟者,可胜道哉!”[22“]南宗词派,推吾乡周清真,婉约隐秀,律吕谐协,为倚声家所宗。自是里中之贤,若俞青松、翁五峰、张寄闲、胡苇航、范药庄、曹梅南、张玉田、仇山村诸人,皆分镳竞爽,为时所称。元时嗣响,则张贞居、凌柘轩。明瞿存斋稍为近雅,马鹤窗阑入俗调,一如市伶语,而清真之派微矣。本朝沈处士去矜号能词,未洗鹤窗余习,出其门者,波靡不返,赖龚侍御蘅圃起而矫之。尺凫《玲珑帘词》,盖继侍御而畅其旨者也。尺凫之为词也,在中年以后,故寓讬既深,揽撷亦富,纡徐幽邃,惝恍绵丽,使人有清真再生之想”[23]。厉鹗的词宗尚婉约派,对粗豪、低俗的词风持批判的态度,“中州乐府鉴裁别,略仿苏黄硬语为。若向词家论风雅,锦袍翻是让吴儿”[24]。“尝以词譬之画,画家以南宗胜北宗。稼轩、后村诸人,词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诸人,词之南宗也”[25]。豪放与婉约之分、南宗与北宗之别,这其实是话语方式的差别,厉鹗之“雅”是传统文人审美趣味的表现,厉鹗的词也正体现了这一趣味。徐逢吉评厉鹗的词:“读樊榭《高阳台》一阕,生香异色,无半点烟火气,心向往之。”[26]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评厉鹗:“樊榭词拔帜于陈、朱之外,窈曲幽深,自是高境。然其幽深处,在貌而不在骨,绝非从《楚骚》来。故色泽甚饶,而沉厚之味终不足也。樊榭措词最雅,学者循是以求深厚,则去姜、史不远矣。”[27]厉鹗生活于康雍乾间,这一时期是清代“盛世”的时期,这与清初和晚清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相对承平的社会环境、文化政策的高压、狭小的生活圈子,这些因素使得厉鹗的诗文具有明显的“内指”倾向,他在诗文中讨生活,不去关注外在的社会现实,他对“雅”的追求正是传统文人审美趣味的表现。
诗词是文人雅趣的表达方式,厉鹗对于世俗以功利之心看待诗词持不满的态度,“往时东南人士,几以诗为穷家具,遇有从事声韵者,父兄师友必相戒以为不可染指。不唯于举场之文有所窒碍,而转喉刺舌,又若诗之大足为人累。及见夫以诗获遇者,方且峨冠纡绅,回翔于清切之地,则又群然曰:‘诗不可不学!’夫诗,性情中事也,而顾以穷与遇为从违,即为之而遇,犹未足以自信,使其不遇,则必且曰‘是果穷家具’,而弃之唯恐不速。诗,果受人轩轾欤?”[28]厉鹗认为,诗词是一种审美的方式,无功利性,用功利的眼光来看待它就失去了其应有的属性。对于那些能够跳出流俗的诗人,厉鹗持赞赏的态度,“往时,吾乡士友专攻举子业,例不作诗。乙未、丙申间,予辈数人为文字之会,暇即相与赋诗为乐。酒阑灯灺,逸韵横飞,必推周兄穆门为首唱。……晚与予辈放浪湖山,结吟社,有句云‘白鸥导我有闲意,青柳笑人成老夫’,此其胸中岂有纤毫流俗者哉?后世诵之,可以想见穆门之为人也”[29]。厉鹗反感流俗之志,他将雅志与世俗之志相对,他推崇的雅志无非是“白鸥导我有闲意,青柳笑人成老夫”之属,这其实是文人述志的常见的话语方式。可见,厉鹗提倡雅,既有雅志,又包含符合文人审美趣味的话语方式。
在语体风格上,厉鹗推崇“清”的语体风格。“清”与“浊”相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清”大多是指“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品格,屈原就有“伏清白以死直兮”之叹。厉鹗语体之“清”正是这种超凡出俗的品格,“大抵诗之号清绝者,因乎迹以称心易,超乎迹以写心难。扬州当舟车之会,易溪山而尘堨,易友朋而投谒,易文字而征逐,即有《折杨》《皇夸》之曲,亦奚当于大雅?此如风蝉露鹤,嘘吸霄霭,移而置之咬哇噂沓之区,有咽而不能成响者矣。廉风土断于斯,独能绝去乔溺,就于平中,间发警思,戛然漻然,足以析烦而破寐,可谓力能不囿于方隅也已。昔吉甫作《颂》,其自评则曰‘穆如清风’。晋人论诗,辄标举此语,以为微眇。唐僧齐己则曰‘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盖自庙廊风谕以及山泽之所吟谣,未有不至于清而可以言诗者,亦未有不本乎性情而可以言清者。廉风居声利之地,泊然寡营,而独喜昵就予辈枯槁蕉萃之士,穷日继夕,流连倾倒而不厌。韩子云‘为彼不清作玉雪’,廉风其知之矣!”[30]不染指尘世,用超脱的语调表现出俗之心迹,这是中国传统文人所认可的高雅之举。山林隐逸与尘世凡俗往往被视为雅与俗的外在标志,大凡高雅之文人,多以山林隐逸为尚,陶渊明、孟浩然、王维等人的语体风格是他们推崇的文体风格。厉鹗在《六十生日答吴苇村见贻之作》中总结了自己的一生:“我生少孤露,力学恨不早。孱躯复多病,肤理久枯槁。干进懒无术,退耕苦难饱。怅下第温岐,归敝庐孟浩。风尖耻作吏,山水事幽讨。结讬贤友生,耽吟忘潦倒。”[31]厉鹗有不少山水隐逸类的诗,这些诗歌在语体上与他所推崇的“清”是一致的。厉鹗独标这一风格,从深处而言,既是对寒士高雅诗风的肯定,又是对文人审美趣味的维护。
三 提倡文体的创造
厉鹗认为诗“不当有派”,为何?文体风格的形成是作家创作成熟的表现,“派”则往往抹杀作家的创作个性,让人求同而不求异,这最终会导致诗文的衰亡。正是因为注重个体风格,厉鹗认为成熟的作家必然要“创体”,创造出具有自己个性特征的风格。厉鹗认为,文体的创新应该是推陈出新,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创一格。他论诗之创体,“君之诗,大概格高思精,韵沈语炼,昭宣备五色,锵洋叶六义,胚胎于韦、柳、韩、杜、苏、黄诸大家,而能自出新意,不袭故常”[32]。文体要推陈出新,就不能拘泥于唐宋,应该是融会贯通,厉鹗在创体上的视野是比较开阔的。“往时,吾杭言诗者,必推西泠十子。十子之诗,皆能自为唐诗者也。……夫诗之道不可以有所穷也。诸君言为唐诗,工矣;拙者为之,得貌遗神,而唐诗穷。于是能者参之苏、黄、范、陆,时出新意,末流遂澜倒无复绳检,而不为唐诗者又穷。物穷则变,变则通。当繁哇噪聒之会,而得云山《韶濩》之响,则懒园一编非膏肓之针石耶?”[33]不袭常故,自成一体,厉鹗认为这是文体发展的必然。同样,对于词,厉鹗认为必须推陈出新。“尝以词譬之画,画家以南宗胜北宗。稼轩、后村诸人,词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诸人,词之南宗也。今涪词淡沲平远,有重湖小树之思焉;芊眠绮靡,有晕碧渲红之趣焉;屈曲连琐,有鱼湾蟹堁之观焉。仆读其词,如与今涪泛东泖以望九山,相羊吟啸而不知返,其为词家之南宗,二沈之替人不虚矣。夫张氏之工于词者,前有子野,后有叔夏。今涪为之不已,将掩二张之长而有之,岂独齐名二沈已乎?”[34]词有南宗与北宗两种风格,厉鹗对能打破两种风格,融会、创新的词体持赞赏的态度。在前人的基础上,清人并没有创造出“一代之文学”,清人创作数量虽富,但文体上却面临着前人“影响的焦虑”,面对丰富的遗产,如何超越前人,这是摆在清人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厉鹗认为,文体的创新应该是推陈出新,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这是符合清代文学实际的。
厉鹗认为,作家应该创造富有个性的诗体或词体,这是对作家整体创作的要求。从实际创作上来看,厉鹗认为,某一具体的诗体、词体也可以推陈出新。“唐以来,倡和传者,例不一姓,若令狐楚、韩琪等之《断金集》,段成式、温庭筠之《汉上题襟集》皆是也。独窦氏《联珠集》则为常、牟、群、庠、巩五人之诗,出自褚藏言所编,又非倡和。今沈氏门才甲于浙河以西,而《探梅》一集,用尤延之、苏东坡旧韵,云机月杼,自出新意,实为倡和诗之甲”[35]。明清两代的唱和诗尤多,厉鹗对各种诗体的演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辨析各体,对沿袭前人而能别出新意之作持肯定态度。唱和诗在中国古代是比较常见的,厉鹗的此类诗作数量不少,严肃的文人大多不认可这一诗体,他的友人全祖望对应酬之作多有批评,厉鹗于此体能娓娓道之,这说明他对诗体的辨析是很深入的。厉鹗有《游仙百咏》《后游仙百咏》《续游仙百咏》系列游仙之作,他对此颇为在意,这一诗体前人已有,他的系列游仙诗既是继承,又是创体。他在《续游仙百咏》“序”中说道:“曩作前、后游仙凡二百首,《前游仙》已雕板,不揣荒鄙,颇有嗜痂。《后游仙》藏箧中,未举示人。暇日展玩,自愧凡俗,于仙境犹有未尽,因刻意冥搜,誓脱故常,复成百咏。”[36]厉鹗虽沿袭前人,但能自出新意、别具一格。厉鹗的词在选材上跳不出婉约派之范畴,多为临吊怀古、吟咏风月之作,他的词体重在用语的创新上。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评价道:“樊榭词笔幽艳,盖亦知陈、朱之悖乎古,而别出旗鼓以争胜。浅见者遂谓其从《风》《骚》来,其实不过袭梅溪、梦窗、玉田面目,而运以幽冷之笔耳。然不可谓非作手。”[37]这是比较客观的。厉鹗的一生多是在书斋中度过,这就决定了他的词体只能在艺术性上推衍,不会创造出迥异于传统的词体。
中外均有“文如其人”之说,文到底如不如其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文章的思想倾向、格调上来看,文不一定如其人,梁文帝就认为做人要谨重,而文章却要“放荡”,元好问也有“心画心声总失真”之叹。从文章的文体来看,文体风格倒是如其人。钱锺书认为,“‘心画心声’,本为成事之说,实鲜先见之明。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之人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之人秉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38]。文体风格一般不具有高低之别,作者多能据性而写,不为外界的评论所拘,钱锺书从这一角度论“文如其人”,这是很有见地的。文体是作家综合个性的表现,与作家的学识、品性有密切的关系,厉鹗注意到这些因素对文体的影响。厉鹗是一位传统的文人,博学多才,“于书无所不窥,所得皆用之于诗,故其诗多有异闻逸事为人所不及知”[39]。厉鹗的学识影响到了他的诗词创作,他的诗词有浓重的学问色彩,是学人诗、学人词的代表性人物。在个人文体风格的形成上,厉鹗认为必须要积学,学识丰富才会有自己的文体风格。“少陵之自述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诗至少陵止矣,而其得力处,乃在读万卷书,且读而能破致之,盖即陆天随所云‘轹波涛,穿穴险固,囚锁怪异,破碎阵敌,卒造平澹而后已’者,前后作者,若出一揆。故有读书而不能诗,未有能诗而不读书,吾于徐君柳樊之诗尤信。……夫杉,屋材也;书,诗材也。屋材富,而杗廇桴桷,施之无所不宜;诗材富,而意以为匠,神以为斤,则大篇短章均擅其胜”[40]。向前人学习是形成自己文体风格的基础,厉鹗认为,学习必须丰富、广泛师承。康熙年间,王士祯的“神韵”说影响广泛,这一诗派有明显的宗唐色彩。王士祯身后,宗唐之风仍然有一定的市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道:“吾乡厉太鸿与沈归愚,同在浙江志馆,而诗派不合。”[41]沈德潜以唐为宗,是“神韵”说的继承者,厉鹗对此有所不满:“予尝谓渔洋、长水过于傅采,朝华容有时谢。”[42]厉鹗虽然在诗风上有宗宋的倾向,但他论诗却是主张唐宋兼收,反对拘于一格,这与他重师承的诗学观点有关。
——辨析“凌乱、混乱、胡乱、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