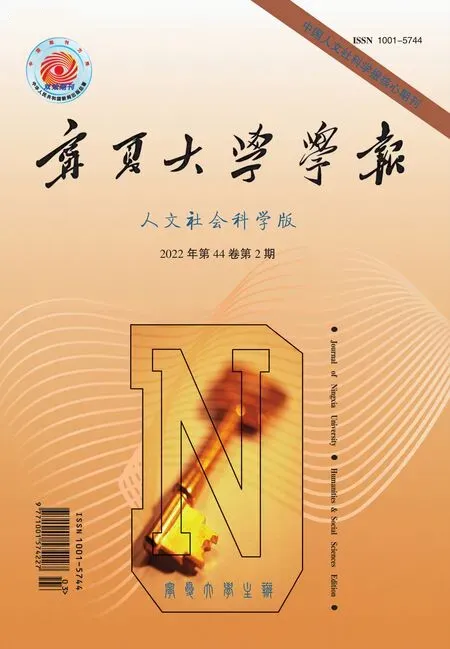明代政治文化与仕宦文人的贬谪命运
刘英波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作为对负罪官员惩罚的政治举措,明代仕宦文人贬谪事件的大量发生与明代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政治文化,按照美国学者阿尔蒙德与鲍威尔的说法:“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政治要求内容和法律的反应。”[1]赵轶峰先生在阿尔蒙德与鲍威尔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明代政治历史特点,认为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政治生态四个基本维度透视出来的特定社会共同体公共权力设置和运作的精神倾向和生态格局就是政治文化[2]。学界对明代政治文化与仕宦文人贬谪命运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我们在认真梳理明代仕宦文人贬谪状况的基础上,立足明代社会的政治历史史实,试将明代政治文化具化为统治政策、政治事件、宦官(权臣)专政、党争、官宦矛盾等几个层面,展开与明代仕宦文人贬谪事件发生关系的探讨,希望能对这类问题的研究有所帮助。
一 统治政策与仕宦文人贬谪的发生
笼统地讲,统治政策包含的内容比较丰富,如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层面。在各项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不同层阶的仕宦文人常是这些政策的执行者。然而,出于加强统治、整治吏治的需要,当他们有意、无意冒犯皇威或触犯相关律条时,往往又会成为被惩罚的对象,而贬谪是常用的惩罚措施之一。譬如洪武初年,余尧臣、顾德辉、徐贲等一大批文人因在张士诚部任职或与张士诚有所牵连被谪戍临濠,其中有的被召回复职或任新职,有的得以释放归田,有的则死于戍所;又如洪武中后期,凌云翰因坐贡举乏人而贬谪南荒、客死他乡,刘三吾因“南北榜”科举事件以老谪戍边地,建文元年才得以召回复职等。这些史实说明,一些统治举措的实施会程度不同地影响到仕宦文人的仕途命运。朱元璋对部分元朝旧臣与张士诚旧部多人的惩处,以及大兴党祸牵连仕宦文人众多的史实,表明统治政策的阶段性、不稳定性特点,有时会使某些举措的实施出现“取决一时”的现象[3]。作为古代帝王,为了维护皇权统治,他们有时不从合法性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以个人独断的方式施策,甚至会以有失公平、牺牲个体的手段达到平息怨言、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体现出皇权统治的专制与任性。
对于整治吏治而言,仕宦文人因工作不力或违法乱纪触犯相关律条受到应有的贬谪处罚,是合乎法律的有效举措。具体贬谪情形则会因当事人的犯错程度、处罚律条与施法者态度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贬谪品秩的多少、距离京城的远近,以及是否附加廷杖、罚俸等。如洪武中期,陈则因审查核实人口落实不力而贬谪山西大同府同知;陆完曾官至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在平定刘六、刘七起义方面有所建树,但因贿赂依附宦官刘瑾,结交反王朱宸濠、坐纳巨贿,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谪戍福建靖海卫,嘉靖五年(1526年)卒于戍所,《明史》:“完有才智,急功名,善交权势。”[4]可谓一语中的,正是急功名、善交权贵害了他;嘉靖十二年(1533年),廖道南因经筵推诿被谪徽州府通判;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张子立抗击蒙古人入侵用兵失利,遭兵科给事中鲍道明弹劾,以“身履疆场,诬功类奏”罪被逮捕讯问后贬至陕西平凉府固原戍边[5];万历年间,周汝登因榷税不如额被贬谪扬州府两淮盐运司判,祁承邺、周献臣因京察分别被谪山东沂州同知、福建布政司检校;崇祯年间,吴钟峦以旱潦征练饷不中额而遭贬浙江绍兴府照磨,吴甡以督师逗留贬谪云南金齿等,举不胜举。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些不同时期因工作落实不力或违法乱纪受到惩罚的贬谪行为起到了维护纲纪、整饬吏治的积极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工作不力或工作失误经过人为的放大后往往成为打击异己的口实,或者成为某些人获取名利的工具,则需要细加考析。如上文提及的廖道南被贬事件,据《明世宗实录》记载,顾鼎臣因疾病不能参加当日的经筵,让廖道南代讲,道南以当捧敕推辞,又让学士蔡昂代,蔡昂也固推不代,张孚敬(张璁)上疏请治其罪,以使各卿安心办事,于是降廖道南直隶徽州府通判,蔡昂贬浙江湖州府通判[6]。而根据廖道南《楚纪·感遇》中所说,因为自己御前经筵所讲的一些内容触犯到了张孚敬,引起张孚敬的不满,于是他便借“不行代讲”为口实,与汪鋐一起诬陷中伤自己,以报冲撞之怨[7]。排除个人情绪,结合张孚敬为人“性狠愎、报复相寻”的特点以及当时朝廷官员之间的斗争状况,廖道南所言很有可能是他遭贬的主要原因。在违纪遭贬的官员中也有受人陷害者,如天启、崇祯年间的袁继咸,《明史》:“崇祯三年冬,擢御史,监临会试,坐纵怀挟举子,谪南京行人司副。”[8]而从他性格刚直、以敢忤逆当权宦官深孚众望的情况看,他放纵举子作弊的罪责应有一定的问题。据他本人所言:“适监临会试第二场,搜获怀挟举子某某等。党乘间谓:‘二场搜出,头场无有,显是疏纵’。奉旨回话,降南行人司司副。”[9]可知袁继咸的遭贬与权宦宵小的陷害有着直接关系。至于《明史》中所记:因失朝礼“大不敬”(唐肃)、失误日讲(蔡昂)、上言宽宥囚犯(田汝成)、以诗连累(朱綝)、言事不达政体(晏铎)、坐奏牍不恭(何乔远)等遭贬事件的发生,既有古代帝王以此警示他人、树立权威的目的,也有可能他们遭贬的实情并非如此,记载的这些因由仅是治罪的口实,均需细加考析。
综上所述,为了避免处理政务时的情绪化与权力运作过程中的人为化,坚持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依据当是执政、治吏、施策的正确方向,而这在当时是难以实现的。
二 政治事件与仕宦文人的贬谪
这里的“政治事件”指与国家政治直接有联系的事件。对于皇权专制时代的仕宦文人而言,作为国家政治体系中的诸多个体,他们的仕途发展、甚至是身家性命都与国家政治捆绑在一起,其差别仅在于捆绑的疏密程度不同罢了。因此,在明代朝廷的一些政治事件中,尤其是影响较大的事件中,有些仕宦文人出于不同的目的或抱有某种政治理想,采取上疏言事或午门哭谏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政见,因此触犯皇威、得罪权臣、违犯律条受到罚俸、廷杖、贬谪等相应惩罚,有的甚至因此丢掉了性命。
如正德十四年(1519年)三月,正德皇帝决意南巡,大量臣工上疏谏阻,如黄巩、陆震等提出图治六事:崇圣学、通言路、正名号、戒游幸、去小人、建储贰等举措,其中“去小人”部分论及宠臣江彬有“可诛之罪”,还有舒芬、崔桐、江晖、王廷陈、汪应轸、马汝骥、曹嘉、夏良胜、万潮、陈九川、孙凤、张衍瑞、姜龙、陆俸、林大辂、周叙、张岳等上疏谏阻南巡,最终的结果是,众人的谏阻行为引起皇帝大怒,加之江彬从中挑唆、阴助,上述谏阻南巡的仕宦文人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处罚:或夺俸禄六月,或遭受廷杖(有的甚至受廷杖而死),或“荷桎梏于阙前,罚跪至晚,仍系俟满五日”[10],或遭受贬谪。其中,有的仅受到一种惩罚,有的则是受廷杖后又被贬谪,如周叙被杖五十降谪永嘉县丞,林大辂被杖五十谪夷陵州判官,舒芬受廷杖三十谪福建市舶副提举等[11]。再如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事件,起因主要是嘉靖帝朱厚熜父母的封号及其崇祀典礼方面的问题,在继“帝统”“宗统”方面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大礼仪”论争,“始而争考、争帝、争皇,既而争庙及路;终而争庙谒及乐舞,此先后凡七争也”[12],其实这次长期的争斗含有嘉靖皇帝树立权威与臣子争权(话语权与职权)的目的。在这场斗争中,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发生的“左顺门哭谏”事件最为激烈而残酷。当时,有二百多位廷臣聚集左顺门,以哭谏的方式希冀嘉靖帝能够坚守祖制,既继“统”也继“嗣”,但事与愿违,嘉靖帝非但没有让步,反而以皇权的威力,依靠“议礼派”的支持,最终平定了这次带有群体性特点的聚集抗议。在这次请愿中,“多数派”输得非常惨烈,十余人被当廷杖死,不少人被编伍充军,多人被贬谪,如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所、客死他乡,王元正谪戍茂州、卒于任上,刘天民贬谪寿州知州等。而且,不仅是“左顺门哭谏”事件,在这次长期持续的“大礼议”事件中,因言大礼议触忤帝意遭受贬谪的仕宦文人数量很多,如邹守益以议礼下诏狱,谪广德判官;夏良胜因大礼议两次分别贬谪茶陵知州、辽东三万卫所;杨言因言礼仪降谪宿州判官;张纶因议大礼被谪戍云南;吕楠以议礼忤旨谪解州判官;胡侍坐大礼议谪潞州判官等。基于对正德年间“谏阻南巡”事件与嘉靖年间“大礼议”事件中明代仕宦文人命运沉浮(包括贬谪)的考察,使我们体认到在古代皇权专制体制运行下的社会中,仕宦文人坚守理念、价值的艰难,皇权威力与对皇权束缚的有限,部分仕宦文人的灵活与投机,以及争夺话语权与职权斗争的激烈残酷等,从中既可睹见皇权专制制度的缺陷,以及具有依附性特点的仕宦文人地位、权利的尴尬与无奈,也可洞察到人性幽微。
三 宦官专政、权臣当道与仕宦文人的遭贬
众所共知,宦官专政并非始自明朝,但明朝却是宦官专政十分严重的历史时段。从某种意义上讲,宦官是皇帝专制制度下调节皇权与外廷权力的重要工具,如果皇帝驾驭能力较强,使用宦官得当,则会利于朝廷统治,否则便会出现一些宦官专政、干政情况,致使外廷、内廷关系紧张,朝政混乱,甚至酿出大祸。《明史·宦官传序》云:“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13]在明朝历史上,除了这里提到的王振、魏忠贤专政、干政影响较大外,正德年间的刘瑾广结党羽,残害异己,败坏纲纪。仕宦文人中间也曾出现过“附丽”“羽翼”“张其势而助之攻”与争先献媚掌权宦官的现象[14],但是,毕竟还有不少知重名节、担忧国运的文人志士,他们与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展开艰苦决绝的斗争,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的被贬谪流放,有的遭迫害致死等。如正统年间王振擅权,于谦不肯俯就、贿赂,他便找人诬陷于谦,关押诏狱,三个月后虽被放出,仍降职大理寺少卿。据相关史料统计,正德年间因罪受贬的仕宦文人有55 人次,其中23 人次是因触忤刘瑾而被降谪的,如靳贵由礼部侍郎降为光禄寺卿,赵鹤由东昌知府左迁南安同知,陆洙获罪戍湖广黎平,顾清由侍读降为编修,唐锦由兵科给事中谪深州知州,蓝章由右佥都御史谪抚州判官,穆孔晖由检讨改为礼部主事等,由此可见刘瑾当时的威权。据统计,天启年间遭贬仕宦文人的13 人次中有6 人次因忤魏忠贤(阉党)遭受贬谪,如赵南星由吏部尚书谪戍代州,邓渼由右佥都御史遣戍贵州镇远,邹维琏由吏部郎中谪戍贵州施州等。宦官专政及对有关仕宦文人的残酷迫害,既反映出他们有恃无恐的猖狂,也反映出皇权专制制度的缺陷与不足。虽然他们短期内对一些仕宦文人的打压起到了震慑作用,以致有些缺少气节的文士拜倒于他们的足下,甚至毫无廉耻地甘称义子,一时出现献媚依附的士风,但同时也激起了部分不愿与专权宦官合作者刚正不阿的气节,如被赞“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的于谦[15],“抗魏奄,拒逆党”“耿介有大节”的邹维琏[16],尽显士人忠贞、正直的风采。
在明代权臣当道、败坏朝纲、排除异己的权臣中,以严嵩父子最为有名。据不完全统计,嘉靖年间因触忤严嵩、严世蕃及其党羽遭受降谪的仕宦文人有22 人次,约占嘉靖年间贬谪数量101 人次的22%,可见严氏父子当时的淫威。譬如宋仪望因弹劾胡宗宪、阮鹗奸贪,阮鹗被逮捕,可因胡、阮二人依附于严嵩,因此宋仪望也就得罪了严嵩。后来,宋仪望受命督三殿门工,严世蕃有所请托,他不徇私情、执意不可,工程完工擢升大理右寺丞,他也不感谢严世蕃,继而惹怒了严世蕃。于是,严氏父子便趁灾异考察京官的时候,坐以浮躁之名把他贬谪夷陵州判官。如沈炼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被调入京师任锦衣卫经历,他深感朝纲混乱、士风日下,更憎恶严氏擅权、贪腐误政,不禁泣涕大呼:“纲纪大坏,贿赂公行,四海民穷,九边政废,实嵩父子罪也!大奸不去,他事未有可议者。”[17]于是上疏斥责严嵩贪婪、卑鄙,并列出他纳贿、揽权等十大罪状,极言严嵩父子为误国奸臣,请求世宗诛之以谢天下。然而,在严嵩的运作、诬陷下,沈炼被以诬诋大臣罪遭廷杖后谪佃保安。谪戍保安期间,沈炼没有改变忧国济民的情怀,他救济灾民、修浚城壕、开办书院、献御敌之策等,而且仍然坚持以各种方式痛斥严氏父子的罪行。最终,在严氏党羽杨顺、路楷诬陷下,沈炼以谋反罪被弃市宣府,同时还杖杀了他的两个儿子沈衮、沈褒以邀功请赏。如张佳胤因不附严氏,以考察属官材料失实为由被贬谪为陈州同知;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赵贞吉提出抗击俺答的举措,非但没有得到时任首辅严嵩的支持,反遭构陷贬谪广西庆元府荔波典史等。
在嘉靖年间的“大礼议”事件中,张璁、桂萼是嘉靖帝的支持者,帮助朱厚熜解决了“统嗣”问题。于是,他们的仕途青云直上,张璁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内阁首辅,桂萼则官至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内阁辅臣,可谓权倾一时。虽然他们在位期间通力合作锐意革弊,反腐倡廉,罢天下镇守内官等,取得显著的政绩,但因张璁“性狠愎,报复相寻,不护善类。欲力破人臣私党,而己先为党魁”[18],桂萼“既得志,日以抱怨为事”,“性猜狠,好排异己,以故不为物论所容”[19],以及“大礼议”中的主张、表现与多数官宦的政见、立场不同,常遭一些意见不合者的上疏弹劾,因此张、桂二人便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异己者大加打击。如张岳与张璁在议大礼时出现嫌隙,被出为广西提学佥事,后来改江西提学而不谢张璁,又被张璁以选贡举之事贬谪广东盐课提举,料理南海盐业事务;邵经邦利用日食上疏弹劾张璁、桂萼曰:“若夫用人行政,则当辨别忠邪,审量才力,与天下之人共用之,乃为公耳。今陛下以璁议礼有功,不察其人,不揆其才,而加之大任,似私议礼之臣也。私议礼之臣,是不以所议者为公礼也。夫礼唯至公,乃可万世不易。设近于私,则固可守也,亦可变也。陛下果以尊亲之典为至当,而欲子孙世世守之乎。”[20]既表达了对璁、萼二人受重用的不满,也含有对嘉靖帝用人不当的批评。当时嘉靖帝闻之大怒,下邵经邦镇抚司诏狱拷讯,卒于戍所;陆粲弹劾张璁、桂萼专权,用词更为激烈:
璁、萼,凶险之资,乖僻之学。曩自小臣赞大礼,拔置近侍,不三四年位至宰弼。恩隆宠异,振古未闻。乃敢罔上逞私,专权招贿,擅作威福,报复恩仇。璁狠愎自用,执拗多私。萼外若宽迂,中实深刻。忮忍之毒一发于心,如蝮蛇猛兽,犯者必死。臣请姑举数端言之[21]。
接着,陆粲列举了一些桂萼受贿与张、桂二人任人唯亲的例子,说他们威权既盛,党羽复多,天下畏恶,莫敢讼言。嘉靖帝闻之,暴璁、萼二人恶行,并罢其相位,但在霍韬的援救下,很快又召回他们,而陆粲却因此被贬贵州都匀(镇)驿丞。至于陆粲所言璁、萼“狠愎”“猜狠”的性格以及“专权”“报复”的行为,有其一定的道理,又说“萼受尚书王琼赂遗钜万”“如蝮蛇猛兽,犯者必死”,则未免带有感情色彩,《明史》中认为张璁“持身特廉,痛恶赃吏,一时苞苴路绝”,便说明了一定的问题。再有,《桂萼传》中言“言官知帝意已移,给事中陆粲极论其罪……”,“极论”二字值得玩味,又据《陆粲传》中所说:“既而詹事霍韬力诋粲,谓杨一清嗾之”,可见陆粲的所劾内容不一定完全出自公心。由此看来,权臣擅权对仕宦文人的命运影响较大,而每位仕宦文人遭贬背后的史实也颇为复杂,我们不能以表面现象或一面之词予以判断,尚需细加考梳、综合考量,才能接近客观事实。
四 党争、官宦矛盾与仕宦文人的贬谪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如汉、唐、宋、明,其衰亡均与党争有关,这是历史的铁律。而明代党争之激烈与持续不息,尤过汉、唐、宋诸朝。”[22]在明代的党争中,自万历朝至明亡一直比较激烈,其间有东林党与齐、昆、宣、楚、浙党的斗争,有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也有齐、楚、浙党之间的斗争等,当时的政坛可谓是错综复杂、混乱不堪、充满戾气,对明代后期的政局影响巨大。“朋党之兴起,其基础乃由皇权专制之衰落,士大夫以结党而求发展势力以自固。故凡党争盛行之时,必政治纷争之始”[23]。而明代党争表现最为明显的现象之一就是党同伐异、排除异己。如山东新城人(今桓台)王象晋,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任礼部仪制司主事期间,当时齐党领袖亓诗教、韩浚等“二三要人势烜赫,甚三事六曹而下莫不奉命惟谨”,他们想借机拉拢王象晋,王象晋却以“性迂拙”“弗能知”“弗能悟”的理由予以拒绝,齐党见未能如愿便“决计剪锄”,通过“其党某御史先为排击,羁(王象晋)邸中者数月”[24],随后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齐党以察典为由贬王象晋官品二秩,调外补江西按察司知事。王象晋虽未去赴任,但最终还是受到齐党的中伤后去官回乡。周延儒在东林党人的支持下被推举为首辅,然而他与逆案中的人并没有脱离关系。周延儒虽然在召还迁谪之臣等方面做了些善事,但还是因品行不端、揽权纳贿受到行人司副熊开元的弹劾,处理的结果是崇祯帝认为熊开元是“谗谮辅弼,必使朕孤立于上,乃便彼行私,必有主使者”[25],十分愤怒,乃廷杖熊开元,系狱后遣戍杭州。结合熊开元曾经任吴江的知县,与复社很有关系[26],我们臆测这一弹劾事件的发生与熊开元的忧国济民思想相关,也应有复社影响下党争的影子。党争中,天启年间阉党与东林党人之间的斗争最为惨烈,在反对阉党斗争的过程中,东林党人付出了惨痛代价,如东林党人或东林党的支持者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先后被掠死狱中,高攀龙、周起元、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遭谋害致死,其中遭受廷杖、谪戍的人员更多,如前文提到的赵南星由吏部尚书谪戍代州,邹维琏由吏部郎中谪戍贵州施州,还有文震孟贬秩外调、未赴返乡等均是受阉党打击的结果。张慎言因为疏荐东林党人赵南星,弹劾冯铨(因谄媚魏忠贤入内阁),遭冯铨忌恨。于是,冯铨便利用张慎言请假回家时,吩咐曹钦程论劾诬陷张慎言盗曹县库银三千,遂下抚按征脏,最后张慎言被贬戍肃州等。基于当时党争的激烈、残酷,使我们认识到制度之腐朽、皇帝之昏庸、正邪之水火、人性之险恶。
众所周知,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封建社会官场更是如此。前文所述的统治政策、政治事件、宦官专政等均含有矛盾斗争的特点,这里我们主要探讨官宦个体之间的矛盾导致贬谪事件的发生。当然,具体到每个贬谪事件发生的起因各有不同,有的较为明了,有的却十分微妙。如在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发生的“左顺门哭谏”事件中,吏部郎中刘天民并非当时活动的组织者,按照朝廷的旨意廷杖三十后不再进一步处罚,但是给事中陈洸上疏却说刘天民是率众参与哭谏事件者之一,要求严加惩处,最终刘天民被贬谪寿州。这件事情表面看来是因为刘天民参加哭谏之事被劾遭贬,那么为何陈洸违背事实而论劾刘天民呢?通过查阅相关史料,我们发现李开先为刘天民撰写的墓志铭中对事因有所交代:“给事中陈姓者,素短先生。因著补衣见部,先生斥之,乃假以‘进君子退小人’为名,上疏指摘先生,乃对品调寿州知州。”[27]原来是刘天民曾经斥责过陈洸,陈洸借此挟私报复。如果说仅此一则材料不能夯实此说,又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左给事中陈洸为给事中赵汉、御史蓝田等所劾,具疏自辨,因讦(篮)田及吏部郎中薛蕙、刘天民、员外郎刘勋等各不法事,都察院覆洸语无实,不足信。”[28]以及赵汉、朱衣等人“交章论给事中陈洸之奸”,御史蓝田“上诉言陈洸本尚书席书之党”,虽然席书上疏辩解“与陈洸素无交往”[29],但考虑到席书在大礼议事件中的表现以及陈洸在乡里的恶劣行径,陈洸弹劾刘天民的行为,不仅是他故意造谣、借机报复,背后还应有时任礼部尚书席书的影子。至于席书与刘天民有没有矛盾,据《明史》对席书的评价“书遇事敢为,性颇偏愎”,我们猜测或许两人在平时的交往过程中产生了某些成见,仍需进一步考究。如万历十一年(1583年),魏允贞在上疏条陈时弊四事时,言及“使辅臣不侵部臣之权以行其私,部臣亦不乘辅臣之间以自行其私,则官方自肃。自居正三子连登制科,流弊迄今未已。请自今辅臣子弟中式,俟致政之后始许廷对,庶倖门稍杜。”[30]内阁大臣张四维闻此疏论,大怒曰:“臣待罪政府,无所不当闻。今因前人行私,而欲臣不预闻吏、兵二部事,非制也。”[31]并乞请辞官,内阁辅臣申时行也进行疏辨,最终处理的结果是,责允贞言过当[32],由御史贬谪至许州通判。其实,从张四维的反驳意见来看,与魏允贞陈述的辅臣、部臣不能行其私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加之当时张四维的儿子张甲徵、申时行的儿子申用懋相继得举后将要参加廷对,因此张四维的反驳明显带有情绪化,应该说是有其私心的。再有,艾穆因张居正夺情之事,与主事沈思孝抗疏谏言:“自居正夺情,妖星突见,光逼中天……而元辅大臣者,纲常之表也。纲常不顾,何社稷之能安?……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何以对天下后世!……陛下诚眷居正,当爱之以德,使奔丧终制,以全大节;则纲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官万民莫不一于正,灾变无不可弭矣。”[33]洋洋洒洒,要求张居正守节尽孝,然而回乡守节尽孝并非张居正当时所想要的。因此,张居正十分生气,艾穆、沈思孝各遭八十廷杖。艾穆下诏狱三日后用门扇抬着出城,谪戍凉州,沈思孝则谪戍广东神电卫。即使到了万历九年(1581年),“大计,复置穆、思孝察籍”[34],可见张居正是何等衔恨他们。当时,因夺情事被贬谪的仕宦文人还有邹元标、张位等。由上所述,可知官宦之间的矛盾斗争盘根错节、复杂微妙,有借上疏议事打击他人泄私愤者,有因触及个人利益借权位打击异己者,也有因贪污事情败露迁怒于他人者等,均需细加考梳才能了解来龙去脉,识见其中的真实面目。
也有因仕宦文人严格执法得罪权贵(中官)产生矛盾而被诬遭贬者。如隆庆二年(1568年),李学道“为御史巡中城,颇有风力。(宦官)许义挟刃吓财,执而笞之,群珰殴汝致(李学道字汝致)于午门外,都御史王廷以身翼之,乃免。时华亭(徐阶)当国,戍首恶三人,杖九人,调汝致于外以两解”[35]。又如崇祯年间,王厈任滋阳(今兖州)县令时,某权豪仗势杀人,有司不敢过问,王厈闻讯下令缉拿凶手,痛打一顿后关进监狱,于是权贵们及趋炎附势之徒制造流言诬陷王厈,结果王厈被逮捕审讯后谪降睢阳(今睢县)为小吏[36];范兆祥因陈言大略,皇帝认为“事涉宫闱,非所宜言”,被下锦衣卫狱,赎杖还职,出为泾府长史,在泾王府“抗论捐冗赋、罢暴征,王每嘉纳之”,终“以不附中人,复下锦衣卫狱,谪戍永州”[37]。在这种正、邪势力的矛盾斗争中,正义被邪恶打败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屡有发生,然而,当这种现象在一个时期大量存在却又不能得到较好地纠正时,则预示着政权已经开始走向不归路。
因个性耿介、负气恃才不被当时的官场文化所容而遭贬者,其中有的因直言忤时受挫,有的是不屈权势受挫,有的是清高不俗遭受排挤,有的是恃才傲物而遭打击等。如正德年间,常伦因生性拓落豪放、耻为拘检,又负才凌傲,受到时人与当权者仇疾,以“假封事中之。遂用考功例谪外,补寿州判官”[38],最终他还是因“折辱御史”弃官归田;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刘凤由监察御史贬谪福建兴化府推官,与他“雅负气,不能折下同事者,而间出语或瑕适人”[39]有关,如因经筵直言触忌讳遭贬的何瑭、因刚直言事降谪的张谏、以直道屡遭贬谪的张鸣凤等。个体性情对他们的仕途命运影响较大,甚至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尤其对于古代官宦而言,亢直、负气、恃才等个性特点往往是为官者的大忌。
另外,与明代政治文化相关的仕宦文人遭贬现象还有许多,如被妒忌者以计谋之的俞彦贬谪夷陵知州,替同僚申辩的贾必选降谪九江府经历,主乡试以文体怪诞遭贬的焦竑降谪福宁州同知,藏匿方孝孺幼子的魏泽谪台州宁海典史,遭石享构陷的徐有贞谪戍云南金齿,坐武库失火(实际是不附张璁)的袁袠谪戍湖州千户所,赴任迟延被劾其怠慢君命的章焕谪戍广东等,名头繁多,情形多样,均表明了贬谪现象的复杂与政治斗争的残酷。
总之,在明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仕宦文人的遭贬命运呈现出多元的特点。究其原因错综复杂,其中以开罪皇帝、权臣、宦官而受贬者居多,彰显出权势的威力。对于史料中记载的贬谪原因,有些值得相信采用,有些仅是贬谪事件发生的口实,尚需细加考辨才能接近真实。对于多数遭贬的仕宦文人来讲,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也不管操权者出于何种目的,他们都是当时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成为被各层权要或势力碾压的对象,显现出政治斗争中权势的力度,暴露了皇权专制的弊端,亦体现出当时官僚机制的运行特点。作为政治文化中的统治、管理层,对于那些中饱私囊、贪赃枉法、违法乱纪的官宦文人,只有大加整治与打击,才能保障社会机制的正常运行,保证多数人的合法权益;对于那些因上疏直言、严格执法得罪权贵或者负气恃才、桀骜不驯的仕宦文人,则予以宽大、包容以促进良好官场文化氛围的营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