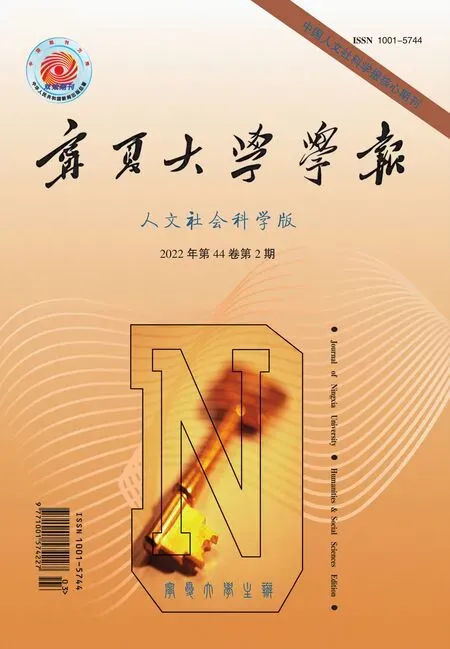俄罗斯文学中的“混乱时期”叙事:生成机制、发展历程与特征
石雅楠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混乱时期”(Смута 或 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 是指1598年留里克王朝末代沙皇费多尔逝世至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新建之间,俄罗斯发生的严重的王朝危机。在这短短15年的历史里,俄国社会一直陷于动荡之中:波兰入侵、王朝频繁更迭、各地饥荒弥漫、起义与暴动时有爆发。该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是俄罗斯文学书写的永恒主题:“俄罗斯生活中的伪德米特里时代和王朝更替时期(混乱时期——笔者注),携有其紧张性和纯粹的民族精神,无疑构成我们历史上最重要的部分……那个时代的‘模糊性’成为无休止争论和书写的主题”[1]。本文从俄罗斯文学中“混乱时期”叙事的生成机制出发,探究其书写历程与基本表征。
一 俄罗斯文学中“混乱时期”叙事的生成机制
“混乱时期”叙事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对16—17世纪之交的“混乱时期”的人物、事件进行的文学书写,关涉的是历史为何被书写及如何“叙述”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要考察俄罗斯文学中“混乱时期”叙事生成的机制。
(一)历史是文学的来源,文学中对历史的叙事受现实触发
在人类文化史上,历史往往是文学的叙事来源,尤以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为最。童庆炳曾对此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历史3”[2](其中,“历史1”是一种原生态的历史,即完全真实的历史原貌。后来史学家对历史进行选择与考证,将其记入史册的历史记忆便是“历史2”。而“历史3”是作家艺术地把主观创造和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统一起来,最终产生文学的历史叙事)。文学与历史的本质关系呈现于“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的巨大张力场中,文学对历史加以阐释之际,无需去恢复历史的原貌,而是解释“应该”和“怎样”,从而揭示历史中隐秘的角落。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3]。
历史题材的文学在指向对历史的回顾的同时具有强烈的现实张扬力度,“对过去的阐释成为对今天的敞开,对过去意义的发掘成为对当代意识的启示”[4]。作者对历史题材的选择是基于现实的语境,因为历史作为作者文化心理结构的一部分,在内心深处积淀已久,其激活的触发点正是作者所面临的特定现实。阿·托尔斯泰指出:“如果你们在构思一部历史小说,那么,这当然就是说,你们所以去构思它,是因为你们已经有了要把这部小说写出来的必要……而这种必要之由来,就在于希望理解现代生活”[5]。可见,历史题材的创作过程如下:现实触发→寻找历史文本→现实张扬。因此,作者创作历史题材的文本,不仅在于和历史的对话,也是和“缺席的在场”的现实的对话,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观照。
(二)俄罗斯文学中历史叙事的传统与经验
历史叙事在俄罗斯文学的起源和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俄国文学的起步乃始于对历史的叙述。俄罗斯文学发端于11 世纪,其主要原因在于基督教的传播和国家的出现使人们萌发了民族意识,从而对历史发生产生浓厚的兴趣。早期俄国文学代表作品有《往年纪事》《顿河彼岸之战》《伊戈尔远征记》等。其中《伊戈尔远征记》将伊戈尔的远征作为一个引线,描绘了150年以来,即“从昔日的弗拉基米尔”到“今天的伊戈尔”俄罗斯人民生活的整体风貌。此后,在俄罗斯文学的整个发展历程中,历史题材贯穿始终。正如别林斯基所言:“我们的时代主要是历史的时代。历史的观照声势浩大而又不可抗拒地渗透到现代认识的一切领域里去。历史现在仿佛变成了一切生动知识的共同基础和唯一条件:没有它,无论是要理解艺术或者哲学,都是不可能的。”[6]
(三)俄罗斯“混乱时期”自身具有强大的生产力
16 世纪末—17 世纪初的“混乱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时代之一,主要表现为王权频繁更迭,权力斗争复杂。在该时期短短15年的时间里,俄国竟历经5 任王朝——戈杜诺夫政权(1598—1605年)、伪德米特里一世政权(1605—1606年)、舒伊斯基政权(1606—1610年)、伪德米特里二世政权(1607—1610年)、七贵族政府(1610—1613年),且每一任政权均迅速以分崩离析之态结束。该时期既存在王朝内部的权力争夺,如莫斯科政府(戈杜诺夫、舒伊斯基)与大贵族的斗争,也有他国的入侵与本国民族解放的战斗,如波兰的侵占及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率领的民兵解放运动。而且,还有阶级之间的博弈,如农奴等下层民众反抗莫斯科政府的压迫。16—17 世纪之交的俄国社会堪称风云变幻,这种强烈的戏剧性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最好的源泉,自发性的冲突跃然纸上。
“混乱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具有强烈的模糊性与书写空白,这为文学叙事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譬如,拥有留里克皇室血脉的德米特里王子究竟是在玩“插刀入地”的游戏时意外而亡,还是因鲍里斯·戈杜诺夫的谋害而死,至今尚无定论。卡拉姆津认为,小王子是被戈杜诺夫谋杀的,而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和普拉东诺夫则对此提出质疑,否认戈杜诺夫谋杀的可靠性。但“戈杜诺夫的政权建立在小王子的鲜血上”的传统观点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文学中的戈杜诺夫形象,普希金的历史剧《鲍里斯·戈杜诺夫》(1825年)、阿·托尔斯泰的戏剧《沙皇鲍里斯》(1870年)等作品,均将戈杜诺夫塑造成嗜血的杀手。
“混乱时期”对俄罗斯历史进程发展的转折意义是其叙事的深层动因所在。该时期是俄国留里克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的过渡阶段,“与前一时期在其原因上有联系,而在其结果上又与后一时期相联系”[7]。纵观 17 世纪之前的俄国历史,留里克王朝君主的登基方式皆为血脉继承,“混乱时期”则开启了另一种产生沙皇政权的方式——“选举沙皇”(戈杜诺夫和舒伊斯基登基都是选举登基),它“使莫斯科罗斯政治发展面临重新调整和选择的机遇:是稳固和发展大动乱变局下的‘等级代表君主制’新趋势,还是重建和强化前朝的专制君主制”[8]。显然,该时期在俄罗斯历史发展的作用是激发“混乱时期”叙事的隐形因素,亦为其叙事的张力所在。
可见,“混乱时期”叙事建立在对历史题材的书写受现实触发的基础上,其发生受俄罗斯文学历史叙事传统与经验的深刻影响,始于16—17 世纪之交俄国历史强烈的戏剧冲突性、史学书写的模糊性,及其在历史进程的转折意义。
二 17—18 世纪“混乱时期”叙事起步:正统话语稳固与剥离
“混乱时期”叙事始于17 世纪,“混乱时期”的作家,同时也是该时期事件的参与者,对国家内部及统治的频繁更替作出了生动而独特的回应。该时期的作品种类丰富,据史学家普拉东诺夫统计,有 30 余部[9],其中包括故事、传说、传记、编年史和民间歌曲等。它们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和历史意义,“其中一些很珍贵,因为它们是‘混乱时期’本身的组成部分;另一些则因内容的丰富性或对那个时代的原始观点,即同代人表达的事实而著称,而且,作者的个性被彰显”[10]。
17 世纪的“混乱时期”叙事主要采用“纪事”(повесть)这一体裁来讲述“混乱时期”,例如:《沙皇、大公费多尔·约安诺维奇日常纪事》(《Повесть о честном житии царя и великого князя Феодора Иоанновича》)、《基督全能之眼报复鲍里斯·戈 杜 诺 夫 纪 事》(《Повесть како отомсти всевидящее око Христос Борису Годунову》),以及季莫菲耶夫 (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 的 《纪事》(《Временник》)等。“纪事”是 11—17 世纪古代俄罗斯文学中的一种独特的叙事体裁,“通常用来指具有宗教训诫特点的编年史”,如闻名遐迩的《往年纪事》。在17 世纪,历史纪事在叙事方面获得更多的自由,呈现出作者的主观态度,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作者的地位及所属阵营影响其对事实的解释,如《基督全能之眼报复鲍里斯·戈杜诺夫纪事》强调了戈杜诺夫谋取王位的不合法手段,其作者是谢尔盖三圣一修道院的斯塔希(Стахий),他是舒伊斯基的追随者。
同时,该时期“混乱时期”叙事的话语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书写于正统坐标体系,强调王朝血脉继承及东正教信仰的不可侵犯性,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对伪德米特里一世形象的刻画中。例如,季莫菲耶夫在《纪事》中称其为“狗”“蚊子”“敌基督”“撒旦”“毒蛇”,认为他不是雷帝的儿子,而是“真正的敌人”,就像袭击俄罗斯的“乌云”,指责他“亵渎信仰”“践踏王室的恩宠和婚姻”[11]。其原因在于季莫菲耶夫是从“真正的沙皇”(истинный царь)观点来描绘人的性格,强调血脉继承的合法性。在当时俄民族集体意识中,“真正的沙皇”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即“公正”“虔诚”(“正义”)“合法”[12],而“真皇”三位一体特征中,“公正”远不如“虔诚”和“合法”重要。“合法”,即拥有留里克血统。该时期的“混乱时期”叙事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伪德米特里一世常常被视为彻头彻尾的反面人物。
而发展到18 世纪,“混乱时期”叙事基本处于沉寂的状态,创作的数量极少,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出现了一颗耀眼的文学明珠——苏马罗科夫 (А.П. Сумароков) 的 《僭位王季米特里》(《Димитрий Самозванец》(1771年))(“Димитрий”又作“Дмитрий”,因此,有“季米特里”和“德米特里”两种译法)。该作品的出版使“混乱时期”叙事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文体方面主要表现为戏剧体裁,《僭位王季米特里》的面世是俄罗斯民族戏剧发展的产物,更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历史剧创作的重要实践,这是此后19 世纪整个百年频繁借历史剧体裁书写“混乱时期”的先声与重要经验。另一方面,它剥离了17 世纪“混乱时期”叙事的正统的话语框架,不再强调血脉的“合法性”,而是侧重君主的道德。其原因主要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18 世纪,尤其是具有德国血统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期间,在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政变和普加乔夫起义之后,有关王位继承问题更加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苏马罗科夫创作了《僭位王季米特里》,认为维护王权最重要的是君主的道德,而非门第和血缘,他借皮缅之口对伪德米特里说:“何时你能不乱施你的淫威,你是否是德米特里,人民无所谓”[13]。由此,消解了“自僭称王”的罪行。在苏马罗科夫笔下,德米特里王位被推翻的原因不在于他不是真正的王子,而在于其道德的败坏:“你做了很多野蛮和残暴的事情,你折磨自己的臣民,毁了俄罗斯,你在野蛮中畅游。流放并处决无辜者……”[14]。显然,他并不拘泥于皇权的血脉继承,而是认为道德决定王权宝座的稳固程度,行文中涌动的是他对君主的劝喻——担负起在国家体系中的义务,遵循道德的准绳。
总之,17—18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混乱时期”叙事,体裁主要为纪事和戏剧,在文体和风格上呈现出个人立场的倾向性。更重要的是,该时期“混乱时期”叙事主要指向正统话语体系,并呈现出从维护正统到剥离血脉继承的话语趋势,从而强调王朝统治者的道德状况。
三 19 世纪“混乱时期”叙事发展:叙事文体与内容繁荣
19 世纪不仅是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亦为文学中“混乱时期”叙事的黄金时代。该时期对“混乱时期”书写的作品大量问世,集中于19 世纪20—30年代、19 世纪 60—70年代以及 19—20 世纪之交,并与现实社会语境相关照。一方面,俄国的政治进程激发了人们对历史的兴趣,如1812年卫国战争、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19 世纪60—70年代农奴制改革,以及19—20 世纪之交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均刺激俄国作家回顾历史上的危机时期。另一方面,19 世纪20年代,“俄罗斯历史的哥伦比亚”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及19 世纪60—70年代,新一代史学家索洛维约夫和科斯托马罗夫针对“混乱时期”的史学著作的出版也引发了作家审视本国历史上最复杂的一段时期——混乱时期。对此,作家包戈金写道:“现在很多人都聚焦于僭位王时期,他们开始书写悲剧、戏剧、故事、小说……”[15]。
从文体形式方面来看,19 世纪“混乱时期”叙事的主要体裁是历史剧。尽管该时期依然有小说以及诗歌等形式存在,但事实上这些体裁作品数量极少,文学价值亦不高。该时期“混乱时期”的书写主要借助于戏剧形式,其中典型代表为普希金戏剧《鲍里斯·戈杜诺夫》、霍米亚科夫(А. С. Хомяков)的 《僭位王季米特里》《Димитрий Самозванец》(1832年)、阿·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僭位王季米特里和瓦西里·舒伊斯基》(《Дмитрий Самозванец и Василий Шуйский》(1866年)、《图西诺》(《Тушино》(1866))、《柯兹马·扎哈里奇·米宁—苏霍鲁克》(《Козьма Захарьич Минин, Сухорук》(1861年)),以及阿·托尔斯泰的《沙皇鲍里斯》(1870年)等。从叙事风格来看,该时期“混乱时期”叙事真实性与虚构性交织,并且在现实主义创作中彰显出浪漫主义的情怀。
一方面,就真实性与虚构性的交织而言,如普希金的《鲍里斯·戈杜诺夫》讲述了鲍里斯·戈杜诺夫登基、伪德米特里一世现身、双方博弈乃至戈杜诺夫死亡的事件,全剧23 场,人物约80个。剧本基本立足于真实的史实和历史人物,同时亦存在文学想象与虚构。譬如剧中的皮缅神父和作者同名主人公普希金等人的形象,他们是否参与了“混乱时期”的事件很难确定,至少现存的史料并未提及。但此二人是普希金文本中的重要叙事动力,对情节的发展和主题的深化均至关重要,在讲述伪德米特里的胜利时,作者就借剧中普希金之口道:“我们强大有力,并非因为将士英勇,不!也不是因为波兰人援助得力,而是因为民意,对!老百姓的公意”[16],由此强调人民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奥斯特洛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的戏剧亦是如此,他们均选取了“混乱时期”的一段史实,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研究历史资料,但同时在创作过程中又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合理想象,书写历史的“应然”,而非复刻实然。俄罗斯文学研究者维诺格拉多夫(А. А. Виноградов)以奥斯特洛夫斯基为代表,指出戏剧作家“通过分析选定的材料,将其转变为作品的艺术结构”,在此过程中,“首先关注该场景与历史真实的对应关系。剧作家创作中固有的客观性预先确定了诗体历史剧的体裁独创性,以及其历史和艺术价值。”[17]但是,剧作家“在‘借用’个体事实、姓名、情节、处境和语言表述等涉及历史资料时并未限制自己,而是力求深入并有机渗透进入历史时代的深处,融入其社会力量、阶级等级、风格和日常色彩之间的联系”[18],在一定的基础上进行文学想象与虚构。
另一方面,该时期“混乱时期”叙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呈现出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该时期的“混乱时期”叙事立足于文本与现实的观照,是俄国知识分子讨论国家转折时期道路选择,以及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的重大命题,但同时充斥着浪漫主义的情怀,主要表现为故事情节的浪漫化、人物塑造的浪漫化以及诗化的叙事风格。例如,普希金笔下“夜 花园 喷泉”一场戏讲述了伪德米特里对波兰贵族小姐马林娜求爱的浪漫场景,塑造出伪德米特里真诚狂热、一往情深的性格特征;奥斯特洛夫斯基《图西诺》一剧第六场中贵族小姐柳德米拉和没落青年尼古拉·列德里科夫的幽会,勾画出两个相爱之人情感的炽烈与勇敢;霍米亚科夫在《僭位王季米特里》第三幕第六场中伪德米特里和马林娜的倾诉刻画出他对所爱之人不断妥协的浪漫形象。而且,上述历史剧基本均采用多种多样的诗体语言书写。普希金随着情节的发展更替使用诗歌体和散文体,奥斯特洛夫斯基及托尔斯泰的戏剧既有近代俄罗斯诗歌语言,又在某些场景使用民歌等形式,尤其在演绎商人、农民和民间艺人的场景时,常常利用俄罗斯传统诗歌、民间歌曲等形式推进情节的发展,烘托舞台气氛。
在叙事内容方面,19 世纪“混乱时期”叙事呈现出的第一个特征为聚焦“混乱时期”的前期活动。俄罗斯历史学家普拉东诺夫将“混乱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争夺莫斯科王位的“王朝阶段”、破坏国家秩序的“社会阶段”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阶段”[19]。19 世纪有关“混乱时期”的文本,绝大多数都集中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历史人物及事件,尤以鲍里斯·戈杜诺夫和伪德米特里一世为最,其焦点均置于“系统危机”“失序”等维度。极少的文本将关注置放于后期的民族解放活动,这一点从众多作品的题目便可显著而直接地呈现出来。其原因与彼时俄国国内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19世纪的俄罗斯长期处于对国内问题,尤其是农奴制,以及俄罗斯走西方道路还是本民族道路等问题的讨论与反思之中,国际问题并未如国内问题那么显著,尽管面临拿破仑军队的入侵,但最终是俄军胜利,国内问题的突出性是该时期“混乱时期”书写聚焦前期活动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特征是女性形象的边缘化。19 世纪文本中的“混乱时期”主要侧重伪德米特里一世和二世、戈杜诺夫以及舒伊斯基等男性群体,讲述他们之间所映射的权力博弈、国家与个人命运等问题。女性在该时期的文学文本中基本处于被搁置和边缘化的状态,女性所参与事件的发生基本是偶发性的,且是为塑造男性群体形象的复杂性而服务的。如该时期众多戏剧中出现的波兰贵族小姐马林娜、戈杜诺夫之女克谢尼娅以及其他贵族少女基本涉及的是爱情主题,但是,“史剧中的爱情处于次要位置”[20]。由此可见,该时期文学中“混乱时期”叙事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是边缘化的。
该时期文学中的“混乱时期”叙事内容呈现的第三个特征是鲜明的“斯拉夫主义”倾向。19 世纪的“混乱时期”叙事是俄国集体反思国家道路选择问题的一种回响。值得注意的是,与整个文学界存在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论争不同,该时期“混乱时期”叙事堪称斯拉夫派的独白,其斯拉夫本位取向极为鲜明。
一为西方“恶”的塑造。“混乱时期”文本中的基本冲突之一为“邪恶”的西方与俄国之间的交锋,主要表现为伪德米特里和戈杜诺夫、舒伊斯基之间的冲突,前者被塑造为西方的代表,后者被视为俄国的代表。可以发现,在该时期的文本中除却普希金笔下的伪德米特里具有浪漫的积极色彩外,大部分文本对其负面描绘非常明显,甚至称其为“坏透了的恶棍”。例如,作家希什科夫(A.A.Шишков)借伪德米特里的母亲安娜之口控诉其恶行:“胆大的骗子,母亲的耻辱,整个自然的耻辱;你是地狱的奴隶!你在祸害故土!”[21]。同时,在斯拉夫主义者霍米亚科夫笔下,这种倾向就更加明显,舒伊斯基——“真正的贵族、俄国大公”,而伪德米特里是西方人,试图以欧洲的方式重建国家。他们的对抗是俄国与欧洲之间的冲突,其失败亦是西方化的失败,“他欧化俄国的意图看起来像是徒劳的乌托邦”[22]。这也似乎契合了他所言:“使俄国融入西方,但这并不是民众的意愿,西方的道路对俄国来说是行不通的,西方正处在灾难的前夜。”[23]
二为人民性的聚合与彰显。人民性是19 世纪“混乱时期”叙事不可忽视的问题,普希金的文本揭露了“民意”决定政权的建立与颠覆,但“沉默”的背后亦流露出这种力量的不确定性,这在19 世纪其他文本中亦常见。但是,在19 世纪中期,人民问题及作用在斯拉夫主义者那里愈发突出:“人民是国家整个公共建筑的根基、物质福祉的源泉,是外部力量、内部力量和生活的源泉,甚至整个国家的思想都在百姓中……”[24],这一点在阿克萨科夫(К.С.Аксаков) 戏 剧 《1612年 莫 斯 科 解 放》(《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Москвы в 1612 году》(1848年))中尤为明显。戏剧中的人民以两种形式出现:单独的人物,如安德烈、伊凡、安东等代表人民的戏剧人物,集体性的人民,如在第一幕第二场中,以旁人之口表达“人民都在聚集”。而且,剧作家通过人民的形象强调俄罗斯和东正教的不可分割性,“为东正教信仰和俄罗斯土地而战”的表达贯穿全剧,明晰地传达出“以东正教信仰的优越性来抗衡西方”[25]的斯拉夫思想。
综上观之,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针对“混乱时期”进行的创作是非常繁荣的,体裁上以历史剧为主,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相结合;在风格上呈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在内容上聚焦于“混乱时期”的前期,讲述男性群体映射的权力斗争、国家与个人命运走向的故事,从而造成女性形象的边缘化。同时,在讨论“怎么办?”和“向哪儿走?”的问题时,19 世纪文学文本中“混乱时期”的叙事话语展现出鲜明的斯拉夫主义倾向,明确传达出俄罗斯本民族道路和东正教信仰的重要性。
四 苏联时期“混乱时期”叙事革新:爱国话语张扬
苏联时期,几乎整个俄罗斯境内的历史叙事都沾染着浓厚的民族革命的色彩。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几乎重写了“混乱时期”的历史,他们似乎有意地忽视混乱前期王朝更迭中的权力争斗,而是浓墨重彩地叙述俄国人反抗沙皇、反抗波兰侵略者,由此,将该时期的性质定义为“阶级战争”和“农民战争”[26]。同时,这一历史书写倾向完完整整地蔓延至文学叙事中,即聚焦1612年的莫斯科解放事件,抑或混乱前期人们的抗争。文本中洋溢着共同的精神价值,即公民的爱国热情和为俄罗斯自我牺牲的精神,该主题“对于复兴俄罗斯的民族意识至关重要”[27]。
布尔加科夫(М. А. Булгаков)的歌剧脚本《米宁 与 波 扎 尔 斯 基》(《Минин и Пожарский》(1936年))探讨人民团结的主题,剧作家以自己的方式发展了俄罗斯民兵领导人的精神选择,塑造了人民捍卫者与民族英雄的形象:“哦,伟大的上帝,给我力量,用毁灭性的剑武装我……我要从国土上激发勇敢,带领他们与我一起作战,并把敌人驱赶出境!”[28]。该剧讲述了民众广泛参与的爱国主义运动,描绘了米宁和波扎尔斯基所领导的民兵与波兰侵略者进行的斗争,文本表现了人民、人民的运动和他们争取独立的反抗。
安德烈耶夫(Д.Л. Андреев) 的诗歌《警钟》(《Рух》(1952年))题目“Рух”一词源于波兰语“ruch”,意为“动荡、兴奋、焦虑”,作者在对本诗评论中解释为“警钟、警示,通常是在国家灾难之际进行防御的呼唤”[29]。在该诗中,哭泣与悲伤的主题一直重复,如“妇女的哭声……”“不幸的莫斯科——孤儿”“他们的悲伤是巨大的,就像条河流的哀嚎”[30],但哀嚎的画面绝非止于末日语境的勾勒,“‘哭泣’旨在引导人们觉醒,呼吁他们采取行动。陷入困境的人民必须团结奋斗”[31]。可以说,该主题指向鼓励人们团结起来、面对灾难以及用于抗争的功能。
此外,有关“混乱时期”作品的更名背后也折射出某种革命话语和意识形态色彩。例如,苏联时期,格林卡(М.Глигка) 的歌剧《为沙皇献身》(《Жизнь за Царя》)被指责宣传君主制和“忠君”思想而被取缔,进行了重大改动,并更名为《伊凡·苏萨宁》(《Иван Сусанин》)。在苏联时期,《伊凡·苏萨宁》的内容重点突出爱国英雄的形象,讲述1612年抗击波兰入侵时,一位普通俄罗斯农民苏萨宁为国捐躯的故事。
苏联时期,俄罗斯成为世界革命和国际无产主义的中心,莫斯科再次成为第三罗马——“进步人类”的中心。在此语境下人民英雄成为文学的主人公,爱国热情是文本书写的主要倾向。“混乱时期”叙事亦是如此,该时期的文学针对“混乱时期”的后期,聚焦人民的反抗活动。一方面,挖掘历史资源,塑造以米宁和波扎尔斯基为代表的民族英雄。另一方面,人民是叙事的主角,揭示人民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革命性与重要作用。
五 后苏联时期“混乱时期”叙事:自由化倾向
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意识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同时发展,再加上知识分子对历史人物的态度相对比较自由,因此,“混乱时期”叙事出现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对历史人物评价消解传统神话。在此之前,俄罗斯文学中“混乱时期”叙事基本处于卡拉姆津的史学框架内,如描写鲍里斯·戈杜诺夫时,始终围绕嗜血君主与阴险杀手的神话,讲述伪德米特里一世时,常常将他的“真实”身份设置为逃跑的僧侣奥特列彼耶夫。但事实上,这些事件的真实性至今仍未被确认,甚至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对此提出质疑。同时,文学家也在人物塑造时提出新的观点,如当代作家布别尼科夫(А. Н. Бубеников)在 《戈杜诺夫 血腥的宝座之路》(《Годунов.Кровавый Путь к Трону》(2018年))中缜密引用海量文献,尤其是对乌格里奇事件的记载,对戈杜诺夫杀害小王子的观点提出质疑,并留下开放的空间让读者自己回答“戈杜诺夫是谋害孩童的杀人犯还是伟大的政治家?”这一问题。
第二,对女性角色,尤其是伪德米特里一世的波兰籍妻子马林娜的重视。在21 世纪之前的俄罗斯文学中很少将“混乱时期”的焦点放置于女性形象之上,但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混乱时期”叙事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对女性的聚焦。例如,阿尔谢尼耶娃(Е. А. Арсеньева)的系列通俗历史小说《僭名者 美 人 的 王 座 》(《Престол для прекрасной самозванки》 (2002年))、《没有宝座的皇后》(《Царица без трона》 (2002年))、《诅咒成真》(《Сбывшееся проклятье》(2007年))等。但最有名的还是鲍罗金(Л. Бородин)的长篇小说《乱世皇后》(《Царица смуты》),该书于 2002年获得索尔仁尼琴文学奖,描绘了马林娜“晚期”形象的全新发展,将其描绘为西方思想的承载者,借其视界反射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并深深思考国家问题。作者提出了在国家生活和个人生活中克服“混乱”与“动荡”的方法,即政治家和人民放弃野心,并借助东正教的意识。正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说:“我毫不怀疑,如果东正教未能复兴,就不会实现民族团结。因为东正教是建立、发展和巩固俄罗斯国家的土壤”[32]。
第三,表现出后现代艺术的形式特征。当代的俄罗斯作家书写“混乱时期”时,在继承传统创作手法的基础上运用了新的技巧,较为典型的是阿库宁(Б. Акунин)的长篇小说《童书》(《Детская книга》(2005年))。该书讲述了一名6年级的俄罗斯小男孩如何从现代穿越到古代的故事,在古代他遇到伪德米特里等人物。作为科幻冒险类型的作品,该小说的后现代特征非常明显,恰如阿库宁的研究者所言:“在复杂的互文游戏中,阿库宁将后现代主义诗学的矛盾思维作为写作策略应用于经典作品与大众体裁,通过赋予文本以多重编码结构来营建了一个开放的多元审美空间”[33]。此外,电影艺术对经典“混乱时期”叙事的改编也呈现出后现代的特点,如俄罗斯导演米尔佐耶夫(В. В. Мирзоев)对普希金史剧《鲍里斯·戈杜诺夫》的改编于2011年搬上荧屏,将古代俄罗斯的故事移植到当代,在西装、汽车、电脑等现代背景下上演一出权力博弈的故事。
“混乱时期”的历史冲突似乎已成为俄罗斯现实的永恒特征,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混乱时期”的叙事话语既呈现出与以往叙事不同的特点,如对历史人物的书写态度、女性形象的重视、后现代的写作特征等。但同时,其思考的焦点仍然关涉国家与人的关系问题。
俄罗斯在“混乱时期”之后又经历了两次大动乱,即20 世纪初的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及20 世纪末苏联的解体,其间,影响程度不大的小动乱更是不计其数。显然,俄罗斯需要被警示新动乱的产生。因此,在这种语境下,再现“乱世”成为俄罗斯知识分子自觉的叙事策略。“混乱时期”叙事自产生至今已经历400 余年的发展历程,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在这4个世纪流动的书写场域中足以彰显“混乱时期”主题的永恒性与书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