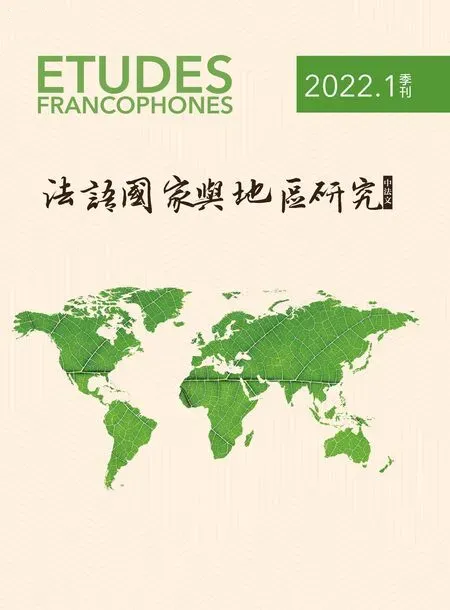论梅特林克戏剧中的“留白”①
邵 南
内容提要 19、20世纪之交,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首度在戏剧中创用“留白”,以静默为语言,以出人意料的阙如之法催人思考,实属对20世纪欧洲剧坛流泽深远的创造。事实上,梅氏所采用的“留白”,无论是思想还是运用,都是对于西方戏剧传统的一种颠覆,而反与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留白”不乏共通之处。因此,通过中国古典文学的视角,我们或许能更清晰地察见梅氏戏剧之奥妙,并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里探讨“留白”的形式和意义。
绪 言
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 1862—1949)在其早期创作(约1889—1896年间)中曾提出并践行了一系列崭新的戏剧理念,从各个层面反法语戏剧之传统而行,获得了极大成功。这些理念中与戏剧形式直接相关者,主要有“静默”(silence)与“不可见”(invisible),前者注重听觉,后者注重视觉(亦可视为知觉的代表),实为戏剧艺术之两大维度。对于这两个方面,西洋学者多分别论述,如莱克纳(Arnaud Rykner)《戏剧的反面:从古典时代到梅特林克戏剧中的“静”》(L’Envers du théâtre.Dramaturgie du silence de l’âge classique à Maeterlinck)专门从戏剧史角度讨论梅氏“静默”的革命性意义,葛尔赛(Paul Gorceix)著有《梅特林克:不可见世界的塑造者》(Maurice Maeterlinck.L’Arpenteur de l’invisible),专门讨论梅氏对“不可见”的呈现方式。但舍此而外,梅氏更致力于在情节层面营造一种“阙如”的感觉,以打破传统意义上的“完整”情节。此数者在西方语境中难以觅得一种共通的名称,仿佛属于不同门类,实质上却有相似的性质,即以某种刻意创设的空缺来令人惊愕,继而展开联想,从而取得滔滔陈词所难以取得的效果。这本是我国古典文学中常用的修辞手法,于绘画、书法、音乐等领域亦很常见,原理也基本相同,是为“留白”。所谓“留白”者,字面意思虽为“留下空白”,但实为“创造空白”,因为这种“留白”本身是匠心所为,即《老子》所谓的“为无为”。“留白”在我国传统文艺中应用广泛,是和道家思想深入人心分不开的。在本文中,我们借鉴古典文学的视角来考察这种梅氏戏剧的“留白”手法,尝试从一个新的侧面管窥梅氏奥秘,亦希望由此思考“留白”这一中国传统文艺手法的新形式与新可能。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梅特林克似乎未曾受过中国或者东亚文化的直接影响,然而间接影响则有迹可循。自19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典籍渐经译介而为西人所知,“留白”在艺术创作中,尤其是在文学创作中的特殊效果,开始受到了欧洲文艺界的重视——其中就有梅氏早年倚重的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然而在梅氏以前,“留白”的运用并未及于戏剧领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四大文学样式之中,戏剧本来是最“满”的,从而最难运用“留白”。从本质上来说,戏剧并非停留于纸面的文字,而是在舞台上综合呈现——通过演员的念和唱,伴随着表演,配合着音乐、布景和灯光,立体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虽然在19世纪以来的欧洲,戏剧文本渐被赋予独立的阅读价值,不再以舞台演出的效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但是戏剧的文体总须维持一定的舞台性,否则就不成其为戏剧了。尤其是,因为舞台演出的时长需要控制,而且需要有视听方面的吸引力,它必当在尽量减省的篇幅中呈现尖锐的戏剧冲突,因此语言必当精炼,场景和动作必当直观鲜明且易于理解。总之,其信息的密度必当较高,而不能像散文一样推演抽象的哲理,或像诗歌一样咀嚼细腻的感情,或像小说一样将长长的故事娓娓道来。也就是说,即便仅将戏剧当作诗歌、散文、小说那样的文本来读,它“天生”就比前三种文体更“满”。或许也正因此,哪怕“留白”在我国古典文艺中大行其道,但在古典戏曲中却难觅踪影。而在欧洲,法国古典时期戏剧对言语力量的崇拜又胜于英、德等其他民族,甚至于视对话为戏剧的全部。(Rykner 1996 : 320)因而,19、20世纪之交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在戏剧中开创性地运用“留白”,实堪称别出心裁之举,对于欧洲传统戏剧(尤其是法国戏剧)的改革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梅氏于1896年写过一篇《静默》(Le silence),是他毕生戏剧创作的纲领之一,其中关于“静默”的论述与道家思想时有契合。②梅氏所谓“静默”者,是和话语相对的,也就是“不言”的意思。因为戏剧主要是依靠对话来表现的,所以梅氏以提倡“静默”即“不言”为旗帜,以此批判传统戏剧并进而提出自己的革命性主张。需要注意的是,有“静默”未必就有“留白”。梅氏所涉及的“静默”,有时只是剧中人谈论的话题,有时只是辅助性的描写,都不属于“留白”范畴。关于“静默”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算作一种“以少胜多”的积极修辞,德松已作了详细到位的澄清。(Dessons 2005 : 65—67)也正因此,“静默”虽然或多或少地客观存在于所有的戏剧,而戏剧中采用“留白”则始自梅氏。如梅氏云:“一旦我们真正需要交流一些事,我们就不得不沉默。”(Maeterlinck 2008 : 20)其谓言语不如静默之深刻,正似庄子所谓“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庄子·齐物论》)。梅氏又认为,言语无法真正地达意:“如果我此刻和你谈论那些最沉重的事物,爱情、死亡或者命运,我并不能触及死亡、爱情或命运本身,而无论我如何努力,那未经道出,甚至我们全不知如何言说的真相,总是那样横亘在我们之间(……)而我们只可能从静默中窥见它。”(Maeterlinck 2008 :26)③梅特林克运用省略号非常频繁,而且其运用省略号大多别有目的和深意,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中将仔细分析。因此本文中但凡因笔者省略引文而加的省略号均用括号括起,以示区别。庄子也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故而不如反其心于静默:“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庄子·天地》)尤其是,梅氏以不言为言的整体设想,也颇近似道家追求“无用之用”的反常规思维。④在梅氏写出第一部戏剧《玛莱娜公主》的时候,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译的《道德经》(Le Livre de la Voie et de la Vertu,1842)已经风靡法语世界,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理雅各(James Legge)的《庄子》英译本则于1889年、1891年相继面世。兼通英法语的梅氏直接或间接地受其影响,亦不无可能。
总而言之,梅氏的“留白”从设想到运用,与我国古典文艺中的“留白”颇多相通之处。然则“留白”运用于戏剧乃梅氏之首创,既为我国古典戏曲中所无,又开西方当代戏剧广泛运用“留白”的先河,无论在中西剧坛都具有先锋意义,值得引起重视并一探究竟。⑤当然,戏剧的“留白”和戏剧本身一样,并非全由剧本作者决定,一旦搬上舞台,作曲家、导演和演员等多少都会进行再创作,也会产生新的“留白”形式。本文作为梅特林克研究,仅关注作家本人安排设计的“留白”。
一、插入对话的空白
梅氏戏剧之“留白”的第一种情形,也是最显而易见的情形,就是“静默”或曰声音层面的“留白”,即在对话中直接安插进一些长长短短的空白。这又可以细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在一段对话的内部,以诸多省略号来标示词句间的空白时间;第二种是在两段对话之间,以“静默”或“没有回答”之类的指令来插入空白时间。
无处不在的省略号堪称梅氏戏剧的一大明显的特点。梅氏在《梦境心理导言》(Introduction à la psychologie des songes)中的一句话可看作其意图的注解:“一句言语,永远只是巍巍大山的一个尖顶,偶然浮出自我那沉沉海涛,仿佛一座转瞬即逝的小岛。”(Maeterlinck 1999 : I 471)《佩雷阿斯与梅利桑德》(Pelléas et Mélisande)⑥该剧上演于1892年,是梅氏第一阶段戏剧的代表作,也是梅氏对欧洲文坛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其情节为,王孙戈罗在打猎时偶遇梅利桑德,爱上了她并带回城堡与之结婚,梅利桑德却爱上了戈罗之弟佩雷阿斯,最后二人在幽会时被埋伏的戈罗杀死。依托看似老套的情节,梅氏着意表现笼罩于人物头上的命运之阴影以及人物的反应,发掘人物的潜意识,并引人思索生命的神秘,以及动作与语言之外的真实。中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哦!它离我们多么远!……不,不,这不是它,……这不再是它……它已经消失了……只剩下水面上的一个大圆环……”(Maeterlinck 1999 : II 390)
“而且我还不曾与她的视线对视……如果就这样离开,我便什么都没有获得。所有的回忆……就好比我在纱囊中带走一些水……我得最后看她一次,一直看到她心灵的最深处……我要对她说所有我还没有说的话……”(Maeterlinck 1999 : II 428)
在这些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即便去除省略号,句子也是完整通畅的。也就是说,这些省略号并非用于句子成分的省略,而是在本来就完整的语句周边人为插入一段空白。⑦梅氏戏剧中的省略号在少数情况下也用于句子成分的省略,例如《七公主》中就有一些因讳言不幸而略去一些词语的情形。由于这种情况下省略号代替的对象比较明确而有限,并没有多少激发想象的功能,也算不上梅氏的独创,故而本文中不加探讨。对于读者来说,这种空白的形象是无处不在的点点省略号,适如海水一般,将原本连绵不绝的言语隔离成一座座孤岛,使之显得零碎而虚浮。传统的欧洲戏剧没有这种空白,那么对于剧本的读者来说,他们只需要关注语句本身,演员的对话加上作者关于场景和人物动作的说明,就是戏剧的全部内容。而今梅氏借助省略号而插入了这些空白,效果就大不相同了。一方面,它们为读者和观众提供了片刻停顿,提示他们思考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另一方面,它们又是一种“虚”的背景,既烘托出实在的语言,又勾勒出语言的局限。而且,正如作者在《静默》中所举的例子:“如果我告诉某个人说我爱他,他也许并不懂得这句我曾向千百人说过的话;然而倘如我真的爱他,随之而来的静默将会指明,今天这个词的根须扎得有多深,由此激发出一种无言的确信,而一个人终其一生,也不会经历两次雷同的静默和确信……”(Maeterlinck 2008 : 26—27)这也就是庄子所谓的“意有所随”,不过梅氏通过省略号将这些“不可以言传”的“所随”用省略号直观地标识了出来,形成了虚实相间的全新语句。不妨说,这些省略号,亦即句间空白的插入,促使戏剧的内涵大大超过了具体语言的范畴。
由于省略号是西方的发明,因此这第一种插入空白的方式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自然找不到对应的例子。而我们对第二种更加熟悉一些,那就是直截了当地指明某处有一段“无言”的时间。比如《佩雷阿斯与梅利桑德》的第五幕第二场,当王孙戈罗(Golaud)守候在他弥留的妻子——梅利桑德床前,一群女佣悄悄涌入房间:
戈罗:你们怎么来了?——没人叫你们来……你们来干什么?——到底是怎么了?——回答啊!……
(女佣没有回答。)(Maeterlinck 1999 : II 449)
作者何以特地写明“女佣没有回答”呢?在戏剧中,只要作者不写女佣的回答,直接续以下文,不就自然足以说明“没有回答”的事实了吗?然而梅氏的良苦用心正在于此:作者的这句话,等于让女佣以“没有回答”为回答,即以片刻的静默,一段短短的空白时间作为回答。(Dessons 2005 : 70)换言之,指明“没有回答”,除了表示没有回答这一事实本身以外,还暗示了“本应有回答”。若是不提“没有回答”而直接续以下文,那便是回答不存在;提示了“没有回答”,等于插进了一段作者刻意抹去的答辞,这便是有意义的空白。女佣们实际上是预感到了即将来临的不幸,即梅利桑德之死。梅氏认为,如命运和死亡这样的秘境是必须用心灵去领悟的,故此用空白作为回答,以促使读者自行想象女佣面对死亡的不可言说的体验。假如用大段的描述来解释这种心情,那就既失之繁琐,又不免浅薄了。
在《群盲》(Les Aveugles)的结尾部分也出现了类似的“留白”。剧中,作者写了向导死后,一群盲人如何在森林中迷了路,又如何试图联合起来而终告徒劳。在这个过程中,群盲的焦虑和绝望渐渐升级。最后,他们听见一个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也不知是人是物,于是:
年轻女盲人:请大家分开!请大家分开!(她把婴孩高举到群盲之上。)脚步在我们中间停下了!……
最老的女盲人:他们在这儿!他们在我们中间!……
年轻女盲人:你们是谁?
(静默。)
最老的女盲人:可怜可怜我们吧!
(静默。孩子更加无助地嚎啕大哭起来。)(Maeterlinck 2012 : 74)
关于《群盲》结尾的处理,凯尔克维(Fabrice van de Kerckhove)从梅特林克的手稿中发现如下的解释:“结尾之处,婴孩应当要哭——这是新人类望见新痛苦时的怨诉,或许,与此同时,还得让树林中透出几缕诡异的亮光。”(Maeterlinck 2012 : 185)凯尔克维接着评论道:“一些个体死了,但是人类还得延续……而同时如戏剧末尾所示的那样,新的痛苦又将来临。”(Maeterlinck 2012 : 185)⑧凯尔克维沿袭了波斯蒂克的观点(Postic 1970 : 62),在解读这部戏剧的时候,将脚步声解释为死亡的来临。但是,戏剧的结尾是否表明盲人们都真的死了,我们以为仍可商榷。《群盲》本身是一部象征性、寓言性很强的作品,梅氏既然选择对盲人的结局语焉不详,我们也大可不必强作猜测。重要的是,群盲以令人怜悯的、无知徒劳的尝试靠自身对抗神秘的外界,最终无可挽回地被命运(或痛苦)压垮。“可怜可怜我们吧!”这句最后的呼喊实乃绝望的哀求,已经等于放弃了一切努力,宣告了向环境的无条件投降——至于死或不死,其实无关宏旨。这里,作者以接连两个“静默”安插了两段空白。比照上一个例子,不难理解这两个“静默”都可看作脚步的神秘“主人”——亦即命运(或痛苦)——的回答。盲人的哀求和孩子的“嚎啕大哭”反衬出这一无言之物的强大,而作者不加解释,以此使读者在悬疑中作出种种不安的联想。
事实上,这一种“留白”的运用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比较常见。较为典型的例子是《琵琶行》,其中白居易写到曲中的一段空白时刻:“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四句中,前两句是对这段音乐中的空白时刻的客观描写,后两句则是作者的感悟和理解。当琵琶女弹完曲子以后,开始叙述自己的往事之前,诗人又插了两句:“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这一次是白居易在自己的叙事中加入了一段空白。它处于琵琶乐曲和琵琶女的自述这两大段“言语”之间,“悄无言”暗示了本欲有言却难以表达的场面,加之“江心秋月白”的意象,既是水中虚影,又是空灵的白色,实为“空白”之图像。由此,这短短两句诗看似无所“言”也无所“为”,但是却具有极强的暗示性,足以胜过长篇大论的抒情。对此,恰好又可以用作者自己的“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来解释。而梅氏戏剧中的“没有回答”或者“静默”,其效果也一样可以用这两句诗来囊括。“无声胜有声”亦可谓戏剧中“留白”的最佳概括。
二、对“不可见”空间的暗示
梅氏戏剧中第二种“留白”是对“不可见”空间的暗示,其最主要的手法当属错乱的对话。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各种与惯常思维习惯相左的对话,来暗示无法用言语描述的“不可见”之空间的存在。这是一种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较难见到的形式。如果说第一种“留白”方式是作者直接插入空白,那么在这第二种“留白”方式中,作者通过外形“实在”的词句来引导读者自行感受言外的“不言”。这种“留白”的具体情形较为多样,大略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一人发问,另一人作完全无意义的回答;第二类是两个或数个交谈者仿佛各自在不同的世界里发言,虽然字面上各人说的都有意义,但实质上难以真正沟通。
对于第一类情形,兹举《玛莱娜公主》(La Princesse Maleine)⑨《玛莱娜公主》发表于1889年,是梅特林克的第一部成熟的戏剧作品,也是其成名作。剧中,玛莱娜公主和雅尔玛王子分属两国,二人相爱,两国国王起初也决意友好通婚。不料,订婚宴上两王一言不合,一怒之下竟罢宴归国,兴兵相攻。玛莱娜公主为战败方,国破家亡,但仍心向爱情,不顾艰难险阻投身敌国,要和雅尔玛王子相见。雅尔玛王子仍然爱她,老王也颇为所动,但雅尔玛的继母安妮王后专权,为迫使雅尔玛王子娶自己的女儿,最终将玛莱娜公主谋害。全剧洋溢着梦魇般神秘恐怖的气氛,剧中人貌似尽力行事,而终被命运压垮。中的一例。该剧第二幕第二场,雅尔马王子(Prince Hjalmar)和他的继母即阴险的王后安妮(Anne)之间有如下对话:
安妮:您为什么这么冷淡?您怕我吗?可您几乎就是我的儿子;我像一个母亲那样爱您;——或许更胜于一个母亲;——把您的手给我吧。
雅尔马:我的手吗,夫人?
安妮:对,您的手;请看着我的眼睛;——您看不出我爱您吗?——您到现在都没有拥抱过我。
雅尔马:拥抱您吗,夫人?(Maeterlinck 1999 : II 113)
王后急于了解王子对自己的看法,王子却总是避而不谈。所谓疑问者,总是抛出一个未知的空间,而交给答者去填充,认知的领域藉此得到推进。对于“您为什么这么冷淡?”正常的回答必当是部分或完全填补“为什么”,即冷淡之原因的。对于“您怕我吗?”正常的回答必当是去填充“怕”这一情形的确实与否。至于安妮接下来的解释,按照一般的理解,只是补充说明提出这些问题的背景。然而,雅尓玛只是将安妮的言辞的最后部分,也就是问题解释部分的最后一两个词,再用疑问的形式抛还给了提问者。这一“答非所问”的情形具有丰富的内涵。一方面,回答没有体现出对提问人意图的理解,而仅将整句话的最后几个词像回声一样返还给提问人,这种没有意义的回答仍可视为一种空白。另一方面,这样的回答又是有形式的,即把提问者的问话反弹了回去,这一点上它不同于上面所说以“静默”为回答的情形。也就是说,如果说提问是一种填补未知、推进认知的努力,那么现在这种努力碰到未知的空间又弹了回来。于是,正如物理学家观测到射线的弹回而意识到原子核的存在,认知的弹回也暗示着一种不可言说也是不可见之境域的存在。雅尔玛王子当然不敢在他奸诈的继母跟前有所吐露,作者正是以这样的双重“留白”让读者想见其犹疑痛苦的复杂心境。在这第一类情形中,作者暗示的空白是在答者身上的。
第二类情形例子更多,形式也更为复杂。兹举《佩雷阿斯与梅利桑德》中的两段对话为例。剧中,王孙戈罗怀疑弟弟佩雷阿斯和自己的妻子梅利桑德私通,希望从儿子依鸟儿(Yniold)口中套出所谓“罪证”:
戈罗:他们在一起时都说些什么?
依鸟儿:佩雷阿斯和阿妈?
戈罗:对;他们说些什么?
依鸟儿:关于我;总是关于我。
戈罗:关于你说些什么呢?
依鸟儿:他们说我会长得很高。
戈罗:(……)当我不在的时候,佩雷阿斯和阿妈从不说起我吗?……
依鸟儿:对,对,阿爸;他们总是说起你。
戈罗:啊!……那他们关于我说些什么呢?
依鸟儿:他们说我会长得像你那么高。(Maeterlinck 1999 : II 415—416)
在这一组问答中,并不存在像上一个例子中的“回声”效果。相反,逻辑的接续表面上尚属顺畅。但是如果我们将其放置到情节中来看,就会明显觉出其中的荒诞。戈罗所谓“说些什么”,并不是如字面所示的那样,想听他们说的任何话,而带有言下之意,即“说些什么见不得人的话”或者“说些什么出轨的话”。要想理解字面之外的这一层意思,就先得理解戈罗所持的一整套伦理道德观念,即弟弟和兄嫂应当如何说话才合乎“规范”,如何可算“出轨”。这一套人为制定的规范,牙牙学语的孩子当然不懂。因此,他的回答在字面上是“完满”的,然而从提问者的期待来看则无异于空白。
另一方面,孩子的回答不再是纯粹的无意义,而是似有若无地暗示着一个神秘空间。这一点在下面的对话中更为明显——当戈罗把依鸟儿高高举起,教他偷窥佩雷阿斯和梅利桑德的举动,一边发问:
戈罗:他们没有什么动作吗?——他们没有对视吗?——他们没打什么手势吗?……
依鸟儿:对,阿爸。——哦!哦!阿爸,他们总是不闭上眼睛……我好害怕……
戈罗:闭嘴。他们还是没有动作吗?
依鸟儿:对,阿爸——我害怕,阿爸,让我下来!
戈罗:你到底怕什么呀?——看哪!看哪!……
依鸟儿:我不敢看了,阿爸!……让我下来!…… (Maeterlinck 1999 : II 420—421)
梅特林克认为爱情是人类最原始、最深刻,因而最神秘的感情之一,因而它是真正的“不可见”——偷窥必然无从获得真相。它更不可能像戈罗认为的那样用伦理去评判和约束,因为伦理至多只能限制其外在言行。因此,戈罗的问话是肤浅的,因为爱情作为一种隐秘的感情,它并非必然导致二人之间有什么“动作”,或者深情对视,或者示爱的手势等外在表现。反之,对于尚未受到世俗成见污染的依鸟儿,他一方面不“理解”戈罗的问话,另一方面天性使他离爱情的神秘更近一步,所以他“害怕”,他“不敢看”,也正是这种“不敢看”使得“不可见”具有了某种内容。至于依鸟儿为何作此反应,作者则无所补充,只说戈罗无法理解——“你到底怕什么呀?”可以说,梅氏正是通过依鸟儿对佩雷阿斯和梅利桑德的眼神的“害怕”和“不敢看”,以及戈罗的不理解,促使读者去猜测那是怎样的一种特殊而神秘的眼神,于是“不可见”的轮廓也就若隐若现了。而最终,作者都不加解释,而将神秘归于空白,以引起读者的震惊与深思。
与《玛莱娜公主》中的例子不同的是,这一次梅氏并非通过回答者将提问直接返还提问者,而是通过见证者的异常反应来暗示神秘空间的存在。在这一情形中,戈罗和儿子都是在自己的世界里说话,二人除自己的思路和感受之外都一无所知。而读者分明感觉到,有那么一个神秘空间笼罩着他们,也阻隔着他们;他们却既不能互相理解,又不晓个中原因。莱克纳曾如此描述梅氏笔下错乱对话的特点:“话语来自别处,穿越舞台,向它的周边发散,在隔离对话者的静默中获得回响,从而获得生命……有一个高高在上的角色,剧中人的话语被其静默的存在所吸收。” (Rykner 1996 : 299)在戈罗和依鸟儿的第二段对话中,那个“高高在上的角色”即佩雷阿斯与梅利桑德的爱情。也就是说,在这第二类错乱对话中,作者所暗示的空白不在某个人物身上,而在他们周围,阻隔着他们,环绕着他们。莱克纳以这种模式来概括梅氏错乱对话的一般形式,则略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是用它来归纳其中第二类情形产生的“留白”效果,就是非常恰当的了。
三、营造缺憾的结局
梅特林克戏剧的第三种“留白”形式体现在情节方面,是为一种令人感到缺憾的结局,这自然是相对于追求情节完整性的欧洲传统戏剧而言的。虽说如我们下文将要阐述的那样,梅氏戏剧也自有其完整性,但是比之传统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通常”意义上的“情节完整”则大不相同,以至于一个读者,哪怕是今天的读者,在初读其作品的时候,总不免对戏剧的结尾大感意外。这是因为,梅氏戏剧的最后常常没有我们所习见的称得上“结局”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令人感到缺憾的结局正是作者精心安排的一种“留白”。
我们将这种结尾的“留白”归纳为两种。
第一种,整个戏剧营造的紧张感不断增强,而戏剧落幕于“事情”将发生而未发生的那一刻,而将危机真正到来后的一切付诸阙如。这种情形主要见于梅氏以《死亡小三部曲》为代表的短剧,正如凯尔克维在《一个“死亡小三部曲”?》(Une “Petite Trilogie de la mort” ?)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在这三部戏剧中,紧张感都随着情节的开展不断增强,而到最终也不得消散:落幕的时刻,正是紧张感达到顶点的一刻。”(Maeterlinck 2012 : 275)以下我们选取三部曲中效果尤为震撼的后两部,即《群盲》和《七公主》(Les Sept princesses)作一分析。
《群盲》的大致情节以及作者在末尾中插入空白时刻的情形,我们已经在本文第一节讨论过了。而该剧的落幕时刻也值得一番分析。剧中,盲人们在徒劳地徘徊良久之后,迫于逼近的危险,想出了一个办法:把他们中唯一视力正常的一个出生不久、尚且不会说话的婴孩举到头顶,通过他的反应来推测周边的情形。临近末尾,盲人们仿佛听见了一些渐近的脚步声,而婴孩也开始转动身子,仿佛看到了什么,后来便开始哭。最终,如上面所引的那样,盲人们感到脚步停下了,询问对方是谁,不获回答,遂绝望而呼:“可怜可怜我们吧!”仍不获回答,与此同时婴孩大哭,随之幕落。
相比传统戏剧而言,《群盲》结尾的“留白”是双线的。第一,作者没有揭示盲人们到底遭遇了什么,下场如何;第二,作者也没有揭示,婴孩作为剧中唯一视力正常的人,却不会说话,他究竟何所见而大哭。如果说传统的戏剧致力于构造冲突,致力于描摹激情达到顶点的时刻,那么在《群盲》中,剧作家致力于描绘这段通向顶点的路,而将顶点本身交给了空白。事实上,现实中每一个人的结局乃是死亡,而死亡正是无法理解的神秘和空白。《群盲》本来就是人之处境的譬喻剧,以空白为结局,颇符合人生的真实。不妨说,梅氏藉此促使读者在猜测群盲之神秘命运的同时,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剧中人心态变化的过程本身,也就是人的生活本身。
另一个近似的例子是《七公主》。该短剧中,年轻的王孙游历归来,父母已经双亡,仅存祖父母(国王和王后),另外七个妹妹在一间几乎封闭的屋里沉睡。王孙担心妹妹们的健康,由于前门已无法打开,乃从屋后暗道搬开石块,进入屋中,六个妹妹相继惊醒,唯独王孙最爱的那一个已经死去。在王孙进屋探视的同时,其祖父母在屋外为不祥的预兆而恐惧,怀着越来越大的焦虑,从互相安慰到失控叫喊,甚至于敲打屋子的窗户,此时幕落。结尾是这样的:
所有人(摇晃着大门,敲遍了每一扇窗):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黑色大幕骤然降落。)(Maeterlinck 2012 : 105)
关于这个结尾,凯尔克维的解释非常精辟。他认为,除了不祥预感的不断升级以外,全剧的另一线索就是屋内和屋外两个世界的分裂和对立越来越明显,最终黑色大幕的突然降落标志着彻底的阴阳剖判。(Maeterlinck 2012 : 201)同时,从梅氏的手稿中,凯氏还发现,剧作家一度构思的结尾是屋外的人们把窗敲碎。(Maeterlinck 2012 : 201)可以推知,他之所以没有采用这一方案,而选择了让戏剧落幕于敲窗呐喊声中,大概是考虑到敲碎窗标志着两个空间的连通,焦虑的行为有所成功,也因之有所发泄,得到减弱。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梅氏为《七公主》制造剧终空白的思路:他希图在读者和观众最迫切地想得到答案,或者至少得到某些希望的时候,突然以落幕来结束一切,将悬疑永远搁置。
第二种结尾“留白”的类型较多见于梅氏四幕以上的长剧。这些戏剧都有传统意义上的情节,或者说相对完整的故事,但是就在人们期待的结局到来之际,出现了意外的事件,使得主人公此前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必须从头开始,全剧也在缺憾之中落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阿里安娜和蓝胡子》(Ariane et Barbe-Bleue)和《青鸟》(L’Oiseau bleu)。
在《阿里安娜和蓝胡子》中,阿里安娜成功地从黑暗的地下救出了蓝胡子杀死的五个前妻,同时赶来救援的乡民们也将蓝胡子制服,捆绑起来。当阿里安娜为受伤的蓝胡子松开绑,向他道了永别,并召唤五个前妻和她一同离开城堡的时候,读者满以为“解放战争”行将胜利,六个女人即将挣脱枷锁,获得自由,阿里安娜将获得英雄之名……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蓝胡子的五个前妻却犹豫起来,最后纷纷拒绝了自由,仍然留下来和蓝胡子一起生活,阿里安娜劝说无果,遂独自和乳母一起离开了城堡。戏剧最后的场景是这样的:
她快步离去;乳母跟在后面。女人们面面相觑了一会,目光转向缓缓抬起头来的蓝胡子。贝朗杰尔和伊格莱娜耸耸肩膀,走去关上大门。——片刻静默。幕落。(Maeterlinck 1999 : III 44)
“片刻静默” 的说明插入了一段空白时间,这种 “留白” 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剧中人最后的动作是尤其耐人寻味的。“面面相觑”者,乃惊异于阿里安娜决绝的离开。蓝胡子是强权与桎梏的化身,他“缓缓抬起头来”,暗示着控制又将开始。女人们“目光转向”蓝胡子,意味着效忠,也意味着甘愿重新套上枷锁。“耸耸肩膀”表示无奈,既无奈于阿里安娜的离去,也无奈于自己的未来。“关上大门”意味着城堡这个封闭空间将重新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转,阿里安娜的一度闯入终究无所改变,一切又将重新开始。阿里安娜临别时说,她要远走高飞:“……那边,还有人等着我的援手……”(Maeterlinck 1999 : III 43)并且永远不再回来。在这样的结尾中,我们看到的并非故事的“结束”,而是深深的缺憾,是令人心情沉重的周而复始。换言之,在戏剧的落幕时分,梅氏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的故事的开端。
《青鸟》的结尾也是类似的情形。仙女带着蒂蒂尔(Tyltyl)和米蒂尔(Mytyl)天上地下游历一番,两个孩子终于明白了“青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家里那只灰鸽子,一旦受到爱心的点染,就成了“青鸟”本身。乍一看来,孩子懂得了爱心和施予的重要,一场道德教育也行将完成。然而,就在蒂蒂尔试图向邻家女孩演示如何喂它的时候,青鸟逃走了。和《阿里安娜和蓝胡子》里一样,主人公都在大功告成之际,一篑未成,前功尽弃。再一次,圆圈在行将合拢的那一刻被打碎,故事的“结束”被交给了空白。
这种构思颇像西绪福斯神话,然而其用意却并不是告诉人们人生尽皆徒劳。阿里安娜没有气馁,明确表示自己还要去别的城堡解救被缚的公主。在《青鸟》的末尾,蒂蒂尔同样没有气馁,而是满怀信心地对小女孩说:“那没什么……别哭……我会把它抓回来的……”(Maeterlinck 1999 : III 398)并且走到前台,呼吁观众一起来帮忙寻找失落的青鸟。这正是将接力棒交给了更多的人。虽然剧中人寻找青鸟的全部努力终究落得竹篮打水,但是梅氏设置的结局的缺憾正有这种感染力,它召唤所有的读者和观众用心念和行动去填补它,去延续这个美好的故事。
其实,这种剧终“留白”的运用和作家的戏剧观紧密相连。在随笔《日常的悲剧》(Le Tragique quotidien)中,梅氏在批判传统戏剧专注于追求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情节之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只有当人们所谓的历险、痛苦和危机结束的那一刻,生命中的真正悲剧,那常在的、深刻而普世的悲剧方才开始(Maeterlinck 2008 : 118),并且补充道:
每当别人在故事末尾告诉我们“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的时候,不正应该是强大的焦虑登场的一刻吗?他们幸福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幸福或者哪怕片刻的休憩不是比热情澎湃的时候更能揭示严肃而恒久的事物吗?(Maeterlinck 2008 : 118)
这一点于擅长英雄史诗、激情大戏的欧洲戏剧来说固然是新鲜的,对于我们却并不陌生。历来文人往往在幸福之中察见悲剧的种子。《兰亭集序》中,“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亦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然后诗人笔锋一转,痛悼人生无常。《滕王阁序》中,“四美具,二难并。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而在此幸福达到顶点的时刻,“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人之为人的固有悲剧同样在幸福到极点的时刻得到认识。柳永的《夜半乐》一词的开篇,诗人自述其激情状态:“冻云黯淡天气,扁舟一叶,乘兴离江渚。渡万壑千岩,越溪深处。”此时诗人激情澎湃,兴致高涨,以扁舟飞度万壑千岩,可谓豪情万丈。然而“怒涛渐息,樵风乍起”,风波稍平,词人来到了生活安详宁静的村庄:“望中酒旆闪闪,一簇烟村,数行霜树。残日下,渔人鸣榔归去。败荷零落,衰杨掩映,岸边两两三三,浣纱游女,避行客,含羞笑相语。”于此平静之处,词人之悲感乃油然而生:“到此因念,绣阁轻抛,浪萍难驻。叹后约丁宁竟何据。惨离怀,空恨岁晚归期阻。凝泪眼,杳杳神京路。”这些经典,尤其是柳永的例子,都很好地佐证了梅氏的观点,即比起“热情澎湃”的时候来,在“幸福”或“片刻的休憩”中乃更容易察见人生本来的悲剧。这个道理若置于中国的诗歌或散文中看来仿佛平常,但是梅氏将其用于戏剧,却收到了奇效。
在梅氏看来,传统戏剧旨在演绎的“故事”——伦理的冲突、激情的碰撞、利益的斗争之类——和人的普世悲剧是不可兼容的。他认为,人一旦为伦理、激情或利益之类所摆布,就失去了自主的可能,失去了思考的余地,沦为这些外物的附庸或曰工具,这样的人本身已经异化。⑩诚如庄子所谓:“比牺樽于沟中之断,则美恶有间矣,其于失性一也。”(《庄子·天地》)譬如哈姆雷特受伦理的挟持,必须杀死叔父,哪怕玉石俱焚;麦克白受利欲的摆布,必然屠戮无辜直至自取灭亡——两个主人公人品星渊,但一样身不由己。更何况伦理会随时代而改变,因民族而不同,激情和利益则愈加偶然,探讨这些问题,于普遍人性的发掘不啻南辕北辙。(Maeterlinck 2008 : 120;Maeterlinck 1942 : 44—46)正是基于这一原则,《群盲》在人迫于激情与本能与神秘来客发生正面冲突之前结束,《七公主》于人们的焦虑变成疯狂的行动并带来实际的改变之前落幕。或者,梅氏让剧中人的行动获得一刻表面上的成功,然而他们将在成功带来的短暂幸福感中“兴尽悲来”,面对新的危机和更大的失望。因此他的《阿里安娜和蓝胡子》不结束于成功救人,而结束于救人的努力付诸东流;而《青鸟》亦不结束于获得青鸟,而结束于青鸟逃走,一切还得从头再来。简而言之,前两剧是结束于“故事”开始之前,后两剧仿佛一直写到“故事”结束,但所谓的结束却无非镜花水月,无非新的危机的开始。无论其中哪一种形式,传统意义上的结局都是阙如的,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予故事以无限的延续空间,才能够使戏剧成为日常的、普世的悲剧。这乃是梅氏屡屡营造剧终空白的深意所在。
结 语
梅特林克在戏剧文学中开创“留白”,其效果令人惊诧,也前所未有。事实证明了梅氏的尝试绝不仅仅是标新立异:他对戏剧界影响最深远的贡献正是“留白”的运用。他这方面的继承发扬者,在法语领域就有克洛岱尔(Paul Claudel)、科克托(Jean Cocteau)、尤奈斯库(Eugène Ionesco)、贝克特(Samuel Beckett)等,直到今天的剧坛还有不少追随者。那一时代的好几个剧作家如易卜生(Henrik Ibsen)、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连同梅特林克在内,都有“现代戏剧之父”之誉称,他们自然各有划时代的贡献;而梅氏之所以获此荣名,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的“留白”。不妨说,其成功既出人意料,也在情理之中:正是在最应该“满”的地方,“留白”才最出人意料,也最能获致强烈的修辞效果。
梅氏的这一贡献,对于西人来说固然重要,对于我们启发亦复不小。与西人不同,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崇尚“不言”“为无为”的老庄哲学,在文学、音乐、书画诸领域中“留白”运用亦多,但是梅氏的“留白”仍有其新意。首先,从指导思想的角度来说,先秦道家批判的对象是矫言伪行的浮躁世风,故其“不言”的主张旨在批驳“好辩”;梅氏则旨在改革一切都靠言语来表达的欧洲传统戏剧,因此他提出“静默”(亦即“不言”)不仅是为了批判,更是为了探讨在戏剧中如何具体运用“不言”来表达难以言传的意思。其次,从运用的角度来说,梅氏将“留白”有意识且大规模地运用于戏剧,不仅此前西方几乎未闻,在我国也甚为罕见。且其身为西人,以省略号为“留白”的道具,又别出心裁地构造各种形式的答非所问,并在故事结束的时机上大做文章,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比较新鲜的“留白”形式。因此,研究梅氏戏剧的“留白”,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索梅氏戏剧的宝藏,有助于促使我们重新认识“留白”的功用和各种不同形式,对中国古典文艺的研究,对中国戏剧的创新,当亦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