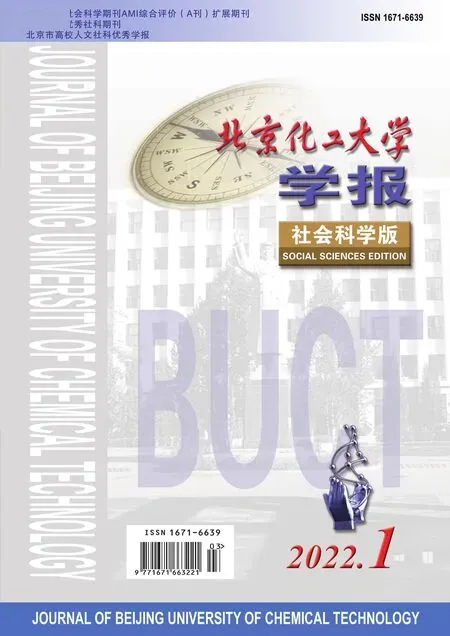从王安石的诗文剖探其道论与天人二分思想
刘洋
(中央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北京 100081)
一、引言
“道”的本义是道路。《尔雅》释为:“路、场、猷、行,道也”,“一达谓之道路。”[1]具有一定方向的路,叫作道,引申为人和物所要遵循的轨道。各种天体、日月星辰所遵循的轨道,天地自然的运行规律,统称为天道。人类生活所遵循的轨道、人类社会所应遵循的规律,统称为人道。“道”是宋代哲学中的重要概念,王安石对此做过详细的论述。王安石论“道”的重要文章有:《洪范传》《郊宗议》《河图洛书义》《杨孟》《对难》《礼乐论》《进洪范表》《推命对》《三圣人》《九变而赏罚可言》《对疑》《致一论》《大人论》《三不欺》《中述》《杨墨》《庄周》《易泛论》《九卦论》《卦名解》等。王安石还有《老子注》二卷,今佚(1)今人容肇祖辑有《王安石老子注辑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今人严灵峰著有《老子崇宁五注·王安石老子注》,台北成文出版社1979年版,为目前最多的王安石《老子注》辑本。今人蒙文通《道书辑校十种》,亦收王安石《老子注》若干条,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今人罗家湘将以上三个辑本合编在一处,成为王安石《老子注》,收录于 2017 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王安石全集》第四册。,《易解》二十卷,今佚(2)今人杨倩描作《荆公易解钩沉》,收录于《王安石<易>学研究》一书中,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刘成国作《王安石<易解>辑佚》,附录于《荆公新学研究》一书之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张钰翰辑录《易解》,收录于 2016 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王安石全集》第一册。。以上是王安石关于道的主要论著,下面笔者将通过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剖探王安石的道论和他的天人二分思想。
二、王安石的天道论:宇宙道气论
王安石认为“道”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原,是宇宙的本体,它自本自根,是超越一切的客观存在,这个“道”,王安石又称之为“天”。“一阴一阳之谓道,而阴阳之中有冲气,冲气生于道,道者,天也,万物之所自生,故为天下母”[2]。从引文中可以看出,在王安石这里,“天”与“道”同实而异名,天即是道,道即是天,“天道”是一体的,是一回事,是宇宙之本原,是他本体论的最高范畴。王安石还有进一步论述,他认为道的本体是“元气”。“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用者,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其冲气至虚而一,在天则为天五,在地则为地六。概冲气为元气之所生,既至虚而一,则或如不盈”[3]。王安石还有一首诗《和吴冲卿鸦鸣树石屏》,中间几句写道:“嗟哉,浑沌死,乾坤生。造作万物丑妍巨细各有理,问此谁主何其精,恢奇谲诡多可喜。人于其间乃复雕鑱刻画出智力,欲与造化追相倾。拙者婆娑尚欲奋,工者固已穷夸矜。吾观鬼神独与人意异,虽有至巧无所争。所以虢山间,埋没此宝千万岁,不为见者惊。吾又以此知,妙伟之作不在百世后,造始乃与元气并。”[4]“浑沌”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应帝王》,其文为:“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郭庆藩引述李颐的注解为:“浑沌,清浊未分也,此喻自然”。[5]可以看出,王安石认为,元气就是造化的开始,就是宇宙清浊未分时的状态。元气为道的本体,元气流行运动则为冲气,在天地间流转不息,阴阳之中有冲气,冲气产生出阴阳,进而化生了万物。宇宙万物的产生纯任自然。王安石继承了《老子》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6]和《周易》中“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7]的思想,提出了“道立于两,成于三,变于五,而天地之数具。其为十也,耦之而已。盖五行之为物,其时,其位,其材,其气,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声,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无所不通”[8]。
在《<洪范>传》中,王安石还写道:
北方阴极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阳极而生热,热生火,故水润而火炎,水下而火上。东方阳动以散而生风,风生木。木者,阳中也,故能变,能变,故曲直。西方阴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者,阴中也,故能化,能化,故从革。中央阴阳交而生湿,湿生土。土者,阴阳冲气之所生也,故发之而为稼,敛之而为穑……盖天地之用五行也,水施之,火化之,木生之,金成之,土和之。施生以柔,化成以刚,故木挠而水弱,金坚而火悍,悍坚而济以和,万物之所成也。生物者,气也[9]。
冲气与阴阳即所谓三。这三者相互作用,就产生出了五行。五行相生相克,就产生了万物。总体来看,宇宙(或称天,或称道)的本体元气,经过冲气、阴阳、五行,最终生化出了天地间的万物,这就是王安石的天道论,又可称之为宇宙道气论。宇宙的生成本于自然。
三、王安石的人道论:兼善天下与修身养性
王安石的人道论既注重经世致用,又注重道德修养,这是对孔孟之道的继承。孔孟之道比较关注现实人生,对神秘虚幻的东西较少涉及。孔子一方面注重以德修身,另一方面周游列国,希望能够得君行道。由于政治上无法实现理想,一展抱负,孔子晚年回到家乡继续修身养性,治学授徒。孟子那句著名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0]更是为后世儒者的出处进退,指明了道路,有条件就得君行道,泽被天下,没有条件就修身养性,独善其身。孔孟既关注政治功业,也关注人的道德修养的理论,对王安石影响很大。应该说,除了最后退隐江宁(今南京)的那十年,受佛禅思想影响较多之外,王安石的大半生都是把“达则兼善天下”当作自己的人生理想的,他也是这么做的。王安石青年时期写的《忆昨诗示诸外弟》颇能看出他当时的想法:“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11]努力奋斗,求取功名,得君行道,做古代稷与契那样的贤臣,泽被苍生,一直是王安石青壮年时期的理想。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以翰林学士越次入对,有机会与宋神宗第一次对面长谈。宋神宗首先问他:“‘方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对曰:‘以择术为先’。上问:‘唐太宗何如?’对曰:‘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知不远,所为不尽合法度,但乘隋极乱之后,子孙又皆昏恶,所以独见称于后世。道有升降,处今之世,恐须每事以尧舜为法。’”[12]“以尧舜为法”,就是王安石的政治理念。王安石认为,圣人之道在于立德修身和治理天下,这才是儒家经典中最核心的部分:“夫圣人之术,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不在章句名数焉而已。”[13]王安石眼中的圣人是“德业俱全”的,这也是王安石心中人道的最高理想。这一点,在他的《大人论》中,有详细的论述:
孟子曰:“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夫此三者,皆圣人之名,而所以称之之不同者,所指异也。由其道而言谓之神,由其德而言谓之圣,由其事业而言谓之大人。古之圣人,其道未尝不入于神,而其所称止乎圣人者,以其道存乎虚无寂寞不可见之间。苟存乎人,则所谓德也。是以人之道虽神,而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其德而已。夫神虽至矣,不圣则不显,圣虽显矣,不大则不形,故曰,此三者圣人之名,而所以称之之不同者,所指异也。……孔子曰:“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此言神之所为也。神之所为,虽至而无所见于天下。仁而后著,用而后功,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及其仁济万物而不穷,用通万世而不倦也,则所谓圣矣。故神之所为,当在于盛德大业。德则所谓圣,业则所谓大也。世盖有自为之道而未尝知此者,以为德业之卑,不足以为道,道之至,在于神耳,于是弃德业而不为。夫为君子者,皆弃德业而不为,则万物何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称神而卒之以德业之至,以明其不可弃。盖神之用在乎德业之间,则德业之至可知矣。故曰神非圣则不显,圣非大则不形。此天地之全,古人之大体也[14]。
王安石以“大人”“圣人”“神人”三名来指称“圣人”,应该是受《孟子·尽心》之启发。《孟子》书中,常见“大人”一词,但孟子并未指明“大人”与“圣人”的关系。王安石为了强调神人待德而后显,待业而后形的观点,为了提高德与业的地位,认为“神人”“圣人”“大人”三者“同实而异名”。应该说,王安石以事业来形容描述“大人”,强调“大人”之事功表现,仍是对孟子的继承和发展。在《答王深甫书》中他又写道:“某以谓期于正己而不期于正物,而使万物自正焉,是无治人之道也。无治人之道者,是老、庄之为也。所谓大人者,岂老、庄之为哉?正己不期于正物者,非也;正己而期于正物者,亦非也。正己而不期于正物,是无义也;正己而期于正物,是无命也。是谓大人者,岂顾无义命哉?扬子曰:‘先自治而后治人之谓大器。’扬子所谓大器者,盖孟子之谓大人也。”[15]可见,王安石把《孟子·尽心》篇中所说的“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16]这句话,作为“大人”一词的注解,以能自治而后治人者谓之“大人”,以此来强调“大人”经世致用的表现。在《三圣人》一文中,王安石称颂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人时写道:“圣人之所以能大过人者,盖能以身救弊于天下耳,如皆欲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则恶在其为圣人哉?是故使三人者当孔子之时,则皆足以为孔子也,然其所以为之清、为之任、为之和者,时耳。岂滞于此一端而已乎?苟在于一端而已,则不足以为贤人也。故曰:‘圣人之言行,岂苟而已,将以为天下法也。’”[17]综上所述,王安石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是德业并重的,一方面修身正己,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精神境界;另一方面,也要正物,匡正天下,为世间立法,淑世济民,建立事功大业。王安石眼中的大人、圣人、神人皆是如此。总之,修身养性和建功立业并重,德业并举,正是王安石“人道论”的核心。
四、王安石“天人二分”思想的内涵
王安石天道论的核心是“元气运行论”,王安石人道论的核心是“德业并重”。在王安石看来,天道有天道的运行规律,人道有人道的运行规律,二者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从根本上来看,二者是不相干的,是“天人二分”的。程颢和程颐曾经抨击荆公新学说:“言乎一事,必分为二。介甫之学也。道一也,未有尽人而不尽天者也。以天人为二,非道也。”[18]二程认为王安石主张天人二分说明其对道的认识不妥。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著录荆公《<洪范>传》云:“安石以刘向、董仲舒、伏生明灾异为蔽,而思别著此《传》。……大意言天人不相干,虽有变异,不足畏也。”[19]晁公武在这里也指出了王安石的思想具有“天人不相干”的特点,是很有见地的,而且他也指明了,与王安石的“天人二分”思想相对立的学说就是“天人感应论”。
天人感应学说最早可追溯到孔子的孙子子思。相传为子思所作的《中庸》一文中有“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20]。西汉初的伏生传《今文尚书》时,在《洪范》一篇的注解中,将天子的行为变化与自然现象的变化相联系,对后世影响很大。伏生之后的董仲舒又将这一理论概括为“天人感应”,记载在他所著的《春秋繁露》中。西汉末年的刘向进一步把春秋战国至秦汉的符瑞灾异集中起来,加以整理,编成《洪范五行传》,堪称“天人感应说”的集大成之作。晁公武指出王安石作《<洪范>传》是有推翻天人感应说的想法的,是具有天人二分即天人不相干的特点的,他还是看出了问题的症结的。王安石的“天人二分”思想大致包含三个方面,下面分而述之:
(一)天有天道,人有人道,各有各的运行规律
王安石认为,天有天道,天道尚自然,人有人道,人道重德业。在《郊宗议》一文中,他写道:
以天道事之,则宜远人,宜以自然,故于郊、于圜丘;以人道事之,则宜近人,宜以人为,故于国、于明堂。始而生之者,天道也;成而终之者,人道也。冬之日至,始而生之之时也;季秋之月,成而终之之时也。故以天道事之,则以冬之日至;以人道事之,则以季秋之月。远而尊者,天道也;迩而亲者,人道也[21]。
可以看出,王安石认为 “天道远,宜以自然”,所以祭天应该在远离人世的地方,在郊外,在圜丘;“人道近,宜以人为”,所以祭人应当在人多之处,在宣明政教的圣地,在明堂。上文中,王安石将天道和人道分而论之,界限分明。在《老子》一文中,他又谈道:
道有本有末。本者,万物之所以生也;末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万物以生,则是圣人可以无言也、无为也;至乎有待于人力而万物以成,则是圣人之所以不能无言也、无为也。故昔圣人之在上,而以万物为己任者,必制四术焉。四术者,礼、乐、刑、政是也,所以成万物者也[22]。
王安石指出,道有本有末,“本”为天道,“末”为人道。天道出之自然,崇尚无为。人道涉乎形器,圣人制四术“礼乐刑政”,以成人道。王安石又说:“夫道者,自本自根,无所因而自然也。”[23]“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所以长久者,以其不自生,任万物之所生;既任万物之所生,乃能长生万物,而无生之累也”[24]。“地法天之无为,故不长而万物育。天法道之自然,故不产而万物化。道则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无所法也。无法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25]。这是他眼中的天道运行规律,天道崇尚自然。而对于人道,王安石在《大人论》中又说:“世盖有自为之道而未尝知此者,以为德业之卑,不足以为道,道之至,在于神耳,于是弃德业而不为。夫为君子者,皆弃德业而不为,则万物何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称神而卒之以德业之至,以明其不可弃。”[26]他在这里强调了“德业”对于人道的重要性。关于王安石的人道论崇尚德与业,本文第三部分已论述甚详,兹不赘述。
总之,王安石将道分为“天道”和“人道”,他认为天道崇尚自然无为,人道崇尚道德功业,各有各的运行规律。
(二)灾异和祥瑞都不是人君行为引起的
王安石对董仲舒以来的“天人感应说”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认为灾异是自然界的反常现象,并不是由人主行为引起的。在《原过》篇中,他写道:“天有过乎?有之,陵历斗蚀是也。地有过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举有过,卒不累覆且载者何?善复常也。”[27]“崩弛竭塞”和“陵历斗蚀”等现象,是天地本身之过,属自然现象,并不是什么君主之过所导致的。同样,这些灾异的消失,是由于天地“善复常”而已,也是自然现象,这也不是由于君主迁善改过、有所作为,从而感动上天造成的。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把他所撰写的《<洪范>传》呈给宋神宗,其用意所在,是为了将他对《洪范》中“狂恒雨若”“僭恒旸若”二句的新解呈现给神宗。王安石认为这二句中的“若”,应从本义上来作解释,应该解释为“犹如”。王安石的新解,就将汉儒释“若”为“顺应”之义推翻,从而将汉儒附加的天人感应关系一刀切断。他想通过此文告诉宋神宗,自然现象的变化与政治毫不相干。
在给弟子们出“策问”题目时,王安石也不忘对汉儒“狂恒雨若”和“僭恒旸若”这两句的注解加以抨击:
《洪范》之陈五事,合于事而通于义者也,如其休咎之效,则予疑焉。人君承天以从事,天不得其所当然,则戒吾所以承之之事可也。必如《传》云,人君行然,天则顺之以然,其固然邪?“僭常旸若”,“狂常雨若”,使狂且僭,则天如何其顺之也?尧、汤水旱,奚尤以取之邪?意者微言深法,非浅者之所能造,敢以质于二三子[28]。
这道《策问》的大致含义是:汉儒对《洪范》中那种恶行招灾,善行招福的解释,是存在问题的。如果承认了汉儒的这种说法,按照他们对《洪范》的解释,那么人君的行为过于僭越了,就常招致旱灾;人君的行为过于狂妄了,就常招致水灾。可是,如果人君既有僭越又有狂妄这两种失德行为,那么天将如何做出反应呢?另外,既然尧和汤都是儒家标榜的古代圣王,然而尧时有连续九年的水灾,汤时有连续七年的旱灾,那么尧和汤究竟犯了什么严重的罪行,而惹来这么可怕的灾祸呢?这段话,对“天人感应说”的抨击相当猛烈,使持“天人感应论”的人难于作答。
在认为“灾异”不是人君失德行为导致的同时,王安石还认为“祥瑞”亦非人君盛德所致。这一观点,在他的《芝阁记》中被明确提出:
祥符时,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来告者万数。其大吏,则天子赐书以宠嘉之,小吏若民,辄锡金帛。方是时,希世有力之大臣,穷搜而远采,山农野老,攀缘狙杙,以上至不测之高,下至涧溪壑谷,分崩裂绝,幽穷隐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于九州、四海之间,盖几于尽矣[29]。
宋真宗在“澶渊之盟”后,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假造天书,并封禅泰山,而且喜欢大搞祥瑞之物。上有所好,下必甚之。于是,真宗朝上演了一幕幕“到处都是祥瑞”的闹剧。王安石对所谓“祥瑞”的揭露非常深刻,他指出,宋真宗撰造祥瑞,其实质不过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他还指出,当时四方以灵芝来献者数以万计,这并不是因为宋真宗有什么盛德感动了上苍,才产生出这么多的灵芝,而是因为皇帝对献芝者大加赏赐恩宠所导致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灵芝一时间能有那么多,是人们到人迹罕至之地,拼命采摘导致的结果。王安石通过《芝阁记》一文,想说明“祥瑞”和“灾异”一样,都是和人事无关的自然现象而已。
总之,王安石认为,灾异和祥瑞都是自然现象,都不是人君行为引起的,与人事无必然联系。
(三)虽然天人二分,但天人之间有时是会发生关系的,人们应以天道为依据,修人事来克服天灾
王安石在认为天道运行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同时,还是认为天人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的。在《九变而赏罚可言》和《<洪范>传》中,他又说道:
至后世则不然,仰而视之曰:“彼苍苍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几千万里,是岂能知我何哉?吾为吾之所为而已,安取彼?”于是遂弃道德,离仁义,略分守,慢形名,忽因任,而忘原省,直信吾之是非,而加人以其赏罚。于是天下始大乱,而寡弱者号无告[30]。
君子之于人也,固常思齐其贤,而以其不肖为戒,况天者,固人君之所当法象也,则质诸彼以验此,固其宜也。然则世之言灾异者,非乎?曰:人君固辅相天地以理万物者也,天地万物不得其常,则恐惧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为天有是变,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或以为灾异自天事耳,何豫于我,我知修人事而已。盖由前之说,则蔽而葸;由后之说,则固而怠。不蔽不葸,不固不怠者,亦以天变为己惧,不曰天之有某变,必以我为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征”之意也[31]。
在王安石看来,上古天下太平,政治清明,是因为尧、舜、禹等圣王按天道行事。而后世天下大乱,政治污浊,是因为后世的帝王不按天道行事,离仁弃义。王安石认为,如果君主行事,不以天为法,摒弃道德仁义,任意胡来,那么就会天下大乱。因此,“天人二分”不是说可以完全不管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规律,完全按君主自己的意志行事,为所欲为。相反,他认为,“况天者,固人君之所当法象也”,虽然自然运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君却应当遵循自然规律,遵循人道规律。王安石认为,自然灾害不是由人引起的,把“灾异”归咎于人事的说法,是错误的。但他又认为,“以为灾异自天事耳,何豫于我”的态度,即,在自然灾害面前,采取消极无为的态度,也是错误的。天灾的产生固然和人事无关,但天灾造成的后果,以及如何克服天灾,如何将天灾带给人的损失降低,却都和人事有关。王安石认为,在天灾的面前,正确的态度应是“以天变为己惧”,正确地对待天灾,重视天灾,积极作出应对,“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积极采取措施,改正政治上的失当之处,从而把天灾对人类社会的损害程度降到最低。这就是王安石对天灾的正确态度。
以上是王安石天人二分思想的主要内容,那么,形成这一思想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觉得,形成王安石“天人二分”思想的主要原因是变法事业。在王安石入朝执政之初,他刚刚制定变法计划之时,那些“反变法派”们,就常拿“天变”现象,来向宋神宗进行恐吓,希望以此来阻挠变法。带头的是御史中丞吕诲,吕诲在熙宁二年六月上疏给宋神宗说:“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于人。方今天灾屡见,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32]吕诲希望罢免王安石,停止变法的计划没有实现。没多久,翰林学士范镇也上疏说:“乃者天雨土,地生毛,天鸣,地震,皆民劳之象也。惟陛下观天地之变,罢青苗之举,归农田水利于州县,追还使者,以安民心而解中外之疑。”[33]
当时,这样的奏疏很多,仅举以上二例,以见改革之难。面对着“反变法派”总是借“天变”来破坏变法的谋划,王安石总是把“天人二分”的思想一再地加以阐释,作为反击政敌的工具,以此保护变法革新的顺利进行。在熙宁三年,王安石把《<洪范>传》加以整理和抄录,呈现给神宗,就是希望能对宋神宗产生作用,使他破除“天人感应说”的影响。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和宋神宗的一段对话,也很能说明王安石始终坚持“天人二分”的思想。
上以久旱,忧见容色,每辅臣进见,未尝不叹息恳恻,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
王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虽逢,但当益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
上曰:“此岂细故,朕今所以恐惧如此者,正为人事有所未修也。”
于是中书条奏,请蠲减赈恤[34]。
“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这是王安石一贯坚持的主张。他认为天变等灾异与人事无关,以此来开导宋神宗,不要忧虑,只要“益修人事,以应天灾”,积极应对就好了。可见,王安石正是运用“天人二分”的思想,作为自己对抗“反变法派”的“天人感应说”的主要理论武器的。
五、结语
王安石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的“荆公新学”就是为复兴儒学、回向三代而创作的。王安石的理想就是道法尧舜,得君行道,实现三代之治。余英时先生在他的著作《朱熹的历史世界》中谈道:“王安石则代表了北宋中期儒学的主要动向,即改革运动的最后体现。与古文运动(欧阳修等)的代表人物相较,他表现出三点显著不同之处:其一,他虽然接受了韩愈的古代道统论,但已不像古文运动领袖那样尊韩了;第二,他发展了一套‘内圣’(即所谓道德性命)和外王(即新法)互相支援的儒学系统;第三,由于因缘凑合,他获得致君行道的机会,使儒学从议论转成政治实践。”[35]在这本书中,余先生还指出:“如果进一步考察(王)安石的‘道德性命’之说,他似乎并不需要一个包罗万有的‘天道’或‘天理’来为人间秩序的实现作客观的保证。这一点与他不盲从‘天命’有很密切的关系。”[36]从上面的引文,我们可以看到:余先生指出了王安石在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他也指出了王安石学术中存在的“天人二分”因素。
笔者认为,王安石重视道德节操和建功立业,修身治国平天下,无疑是对孔孟之道的继承,但是,当和王安石大致同时的思想家们如周敦颐、张载、程颢等都在努力创建贯通天人的学说,通过赋予天道本体以道德伦理价值,希图将人间的伦理规范、纲常名教等人间秩序上升为必然的规律,并使之成为天道本体的属性,继而又以天道为伦理价值之源来论证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将天道与人道合而为一(即创建天人合一学说)的时候,王安石却主张“天人二分”,“天人不相干”,天有天道,人有人道,各有各的运行规律,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王安石是学术巨擘,贯通经史,出入百家,他不刻意提倡“天人合一”是有他的原因的。因为他明白,“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论”是相伴相生的,如果他过分强调贯通天人,就无法回避汉代以来形成的“天人感应论”和“天变灾异说”,如果熟读历史,“天人感应”这一理论,正是变法的大敌。因此,王安石只有坚持主张“天人二分”、“天人不相干”,他才能说服宋神宗,大胆改革,锐意进取,回向三代,实现尧舜之治,从而实现他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也许正是王安石的高明之处。
——《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简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