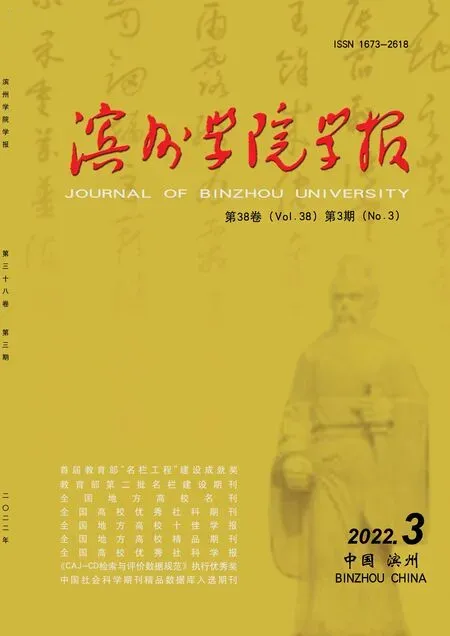以魏一鳌为中心考察清初汉官的仕隐
张 艳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甲申”不久,清代明立。如此巨变,给正统儒家士人带来了空前的打击与痛苦。在满洲贵族的统治下该如何自处,成为他们面临的巨大难题。明朝时业已居官的士人,或死节、或投降、或逃隐、或反清,应对相当明确。而数量庞大、未及做官的中下层士人,反而站在了十字路口。他们一生所学,皆为入仕。朝代更迭迫使他们必须做出抉择:是继续求取新朝的功名,进而至于做官?还是坚决不与新朝合作,未出即隐?他们并不像明季官员那样已经食君之禄,自然也未与前朝捆绑形成事实意义上的君臣关系。从单纯的士人责任看,入仕新朝,安民济世,理所必至。但是传统的儒家观念又使他们认为,他们无一不是前朝之“臣”,做清朝的官,必然成为贰臣,大损节行。在两种思维的挤压之下,除了少数坚决忠于明朝或只为做官的人没有太大的心理困扰,迅速做出隐、仕的选择,相当数量的士人都或久或暂地处于痛苦的犹疑徘徊中。他们的心理矛盾体现在行动上,就表现为仕而后隐,时仕时隐。在这些士人中,夏峰学派学者魏一鳌所经历的仕宦与归隐生涯,非常具有典型性。从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清初汉族部分中下层士人如何在政府、家族、师承等的影响之下出仕,又为何居官不久即辞归的情况。对这一情况的梳理,有助于了解与把握清初汉族士人对政府的态度、学派对士人仕隐的影响,以及中央的人才政策等。
一、魏一鳌的生平
魏一鳌,生卒年不详(1)据白谦慎考证,魏一鳌生活的年代约在1616年至1692年间。(参见《傅山的交往和应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页),字莲陆,亦作莲六,号海翁、酒道人等,亦称雪亭先生,祖籍滨州[1]册2(清初属济南府,今属山东滨州)。七世祖魏得春在明永乐时以军功显,徙家保定。曾祖魏陞迁新安三台(今属河北雄安新区),祖父魏朝官。父魏梁栋,不喜读书,力田为业,为人忠厚,知名乡里,与北方儒宗、容城孙奇逢为好友,共组耆逸社,日相过从。[1]册2魏一鳌为梁栋次子,自幼好学,不喜游戏。后应童子试,为保定府知府李晋徵录取为第一。
崇祯十五年(1642),魏一鳌中举,入都拜谒房师。权宦王德化派人传话给他,只要他约集同年前去拜访,即可得千金。魏严词拒绝。次年会试,至第三场第五策有“刑赏”一题。正值崇祯皇帝亲自审问吴昌时一事发生。(2)吴昌时,字来之,号竹亭,浙江嘉兴人。崇祯七年(1634)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吏部文选郎中。吴昌时依附权臣周延儒,遭御史蒋拱宸弹劾。吴的罪名之一是交接中官李瑞、王裕民等刺探机密,触犯了崇祯皇帝的大忌。崇祯亲自审问吴昌时,并命用刑。阁臣蒋德璟、魏藻德劝阻说:“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来未有之事。”崇祯说:“吴昌时这厮也三百年来未有之人。”坚持用刑,打断吴的双股。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参见文秉《烈皇小识》卷八,清钞《明季野史汇编》前编本)魏一鳌深不以为然,在策内直言批评“平台非行法之地,天子岂问刑之人?”[1]册2考官阅卷恐惧,不敢上呈。他因此下第,以后便乡居读书。
入清后,魏一鳌原本无意仕进。顺治二年(1645),他遭督催赴选。六月,参加部试,获一等。八月,授山西平定州知州。履职后,他尽忠职守,调停税役,革除弊政,为民纾困,又重兴社学、招流移、裁火耗、劝农桑、恤行户、惩衙蠹、禁士卒、平冤案等。百姓感激,为刻碑揄扬,并在嘉山立三贤祠拜之。魏氏自奉菲薄,每日菜止豆腐、白菜、豆芽三种。又古道热肠,常周济贫苦百姓与经济窘迫的同僚。以才略很受巡按王昌胤[1]册2赏识。魏一鳌任职平定州期间,结识了寓居当地、名动天下的傅山。两人一见如故,遂为知交。魏氏给予傅山人身与经济等方面很大的庇护。同年,魏一鳌正式拜孙奇逢为师。
一年后,魏一鳌以诖误降职,补山西布政使司经历,先后署沁州知州、太原府同知。顺治十年(1653)徙官泗州知州,以丁父忧未到任,居平定州守丧。适值傅山“乌衣道人案”发,魏一鳌不顾利害,竭力调停,解傅山于囹圄。
顺治十三年(1656)魏氏服满,归保定。十月二十七日任忻州知州,一个月后即引病辞归。
此后,魏一鳌便定居保定,而常赴孙奇逢寓居的河南辉县夏峰村,“率间岁一至,每至必留数月,后构屋以居”[2]卷3,与老师及诸同门读书论道。同时,魏一鳌又有意居间介绍乃师与自己的丙戌同年、此时已是朝廷重臣的魏裔介等人相交。
康熙三年(1664),孙奇逢卷入“《甲申大难录》案”,险象环生,众人震恐。魏一鳌周旋各处,依靠他此前牵线建立的孙奇逢与京城诸大员的关系,才终于弭祸。事后,杜越把他比为蔡元定、冀元亨。孙奇逢称赞他“明达莲陆氏,到手无棘事”[3]卷13。
这以后,魏一鳌继续他的退隐生活,以读书论学终身。其学主陆王,而兼采程朱,以孟子为把柄,上溯孔子。编著有《四书偶录》《诗经偶录》《北学编》《三贤集》《雪亭梦语》《雪亭文稿》《雪亭诗稿》等。
魏一鳌一生急贫济困,有侠义风,救助同僚、同门及百姓不可胜数。(3)如清初畿辅马政为大害,承担的百姓往往破家。魏一鳌刚刚中举的时候,恰好应当与同乡寒士王永述共同承差。他本可以举人的身份免除劳役,但是担心王氏不堪承受,仍然与之一起应役。其他侠义事参见王余佑《魏海翁传略》、《雪亭文稿》册二附录。他广交游,与当朝大员魏裔介、魏象枢、高景、梁清标等都有交谊;与其他官员,如汤斌、郝浴、赵宾、王紫绶、常大忠、杨思圣等都是好友;与名士傅山、侯方域、理学家李塨等私交甚笃;与夏峰诸同门王余佑、耿极、马习仲等更是感情深厚。从居官与处事看,魏一鳌相当有经济才。这当然与他长期为吏,深谙官场之道有关。虽然为官有日,但是他丝毫不热衷利禄,壮年即隐。总的来讲,魏一鳌有理想,能践履,又老于世故,是一位少见的集真儒与能吏于一身的士人。在夏峰学人中,他也是仅有几个的既能继承孙奇逢早年经世致用、任侠好义的践履精神,又能发扬乃师截断众流、回归孔子的理学观念的夏峰士人之一。
二、魏一鳌的出仕
魏一鳌在明崇祯十五年(1642)中举,崇祯十六年(1643)参加会试不中,此后乡居。然而天下扰攘,新安也并不平静,流寇、土匪、兵患、水灾(4)“新安三面皆积淀,唯城北陆居,而大溵等淀地势低洼,容城雨潦之水汇注为壑,岁失耕稼,闾阎凋敝。”(参见李卫修《畿辅通志》卷四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不断,民生多艰。魏家经济也相当困难,好在人口不多,尚可支撑。至崇祯十七年(1644)初,天下大乱。三月十九日崇祯帝自杀,大顺军占领北京。三月二十四日,保定为大顺军刘芳亮部攻陷。魏一鳌好友张罗喆(5)张罗喆,字石卿,清苑县人,明诸生,与孙奇逢、王余佑、颜元等也俱有交往。讲学以仁为主。清立,弃诸生身份。一门二十三人死于是役,张仅以身免。吴三桂降清后,大顺军力不能支,于四月二十九日撤离北京。五月初二,多尔衮率部进入北京。十月初一,顺治帝即位。清朝定鼎。在这一段时间里,新安因不在火线,受兵事蹂躏有限。魏一鳌的话也可以让人从侧面窥见一二:“保定先京师而守,后京师而亡,可谓忠且烈矣。余当日家渥水,于城之存亡、诸公之烈殉皆不详。有人问及亦茫无以对。”[4]卷3大体上,他仍算稳居乡间。但到次年五六月间,迫于清廷压力,魏一鳌已经不能置身事外,而不得不入都赴部试备选了。魏氏出仕,当然等于实际上认同清政府的统治。即便有关魏氏在明亡清兴的甲申、乙酉两年的历史记载非常匮乏(6)魏一鳌非常谨慎,很少记载自己的生平。记叙他生平最详细最可靠的文字当属他的同门知交王余佑所做的《魏海翁传略》。而这篇文章对魏一鳌甲申、乙酉两年的行事一语带过。,无论从他正统儒家士人兼明举人的身份考虑,还是从他以后的行动观察,都可以断定,出仕清廷这一行为与他的思想有强烈的冲突。因此,有必要考察他做出如此选择的原因。
首先,迫于政治高压。清廷甫立,为招揽人才和收拢民心计,迅疾举行部试,任用大量前朝已有功名的士人为官。不少士人为表达对新朝的反抗,抵制科举考试,已有功名的则拒绝出仕。如魏一鳌的夏峰同门好友杜越、王余佑、高鐈、申涵光、王之徵、马尔楹、耿极、赵御众等人都是如此。但这些人与魏氏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或者在前明只是诸生,如杜越、王余佑、高鐈等人;或者连诸生的身份也没有,如申涵光、王之徵、马尔楹、耿极、赵御众等人。因此,他们所承受的政治压力没有魏一鳌那么大。魏氏起初也拒不应试。但鉴于拒绝合作的士人太多,清廷旋即改诱为迫,强迫各地已有功名的士人或应试或出仕。魏一鳌也“蒙清檄,督催赴选。铨部行文各直省抚、按,有‘举人抗违不应试者,指名拿问,抚、按并参’等语。抚、按严檄府、州、县,差人护送入京”[1]册2。不应试,就要被指名拿问,地方官还要承担连带责任被参;应试,也要被官差强制押送入京。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只有屈服,魏一鳌也不例外。他不得不参加六月的部试,获一等。八月,授平定州知州。九月初九上任。对于这样的情形,陈寅恪评道:“盖建州入关之初,凡世家子弟著声庠序之人,若不应乡举,即为反清之一种表示,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险。……后世未解当日情势,往往作过酷之批评,殊非公允之论也。”[5]1142此是通达、富于人情的知世之论。
第二,为谋生计。如赵园所言:“士的谋生手段的匮乏,是士的历史的结果。当面对具体的谋生手段的问题时,士人自不难发现,作宦、力田、处馆、入幕,几乎构成了他们基本的生存空间。”[6]336力田,魏一鳌的父亲魏梁栋做过,“凡暑雨析寒之苦,无不备尝”[1]册2,也仅仅使家产稍有余裕而已,完全无法抵抗意外的风险,如家庭成员的疾病、地方豪猾的欺侮、胥吏的勒索、官府的沉重税赋与劳役等。处馆,魏一鳌的好友张罗喆、夏峰同门耿极等都在从事,经济上无一例外的相当困窘甚至不能糊口,而常需亲朋周济。并且,魏一鳌与父亲在家资不富的情况下都乐善好施,并以此知名。他们维持生计,自然更加艰难。魏氏在为官多年后后尚且感叹:“旧业已空,将何以糊口?”[1]册1入仕之前的情况可想而知。为摆脱经济和地位上的窘境,魏一鳌只能选择出仕。
第三,思治使然。明末清初,直隶、河南等北方省份受兵燹蹂躏极深。流寇、土匪、官军、满洲的侵扰与劫掠轮番登场,各项税赋劳役沉重不堪,自然灾害连绵,民间几乎没有一日安宁,百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完全没有保障。仅仅夏峰士人中,魏一鳌的同门与友人如保定耿极、永年申涵光、雄县李崶、新城张果中、定兴马尔楹、固安贾三槐、清苑高鐈、滦州赵御众等都由中产甚至巨富跌落到破家的程度;上蔡张沐的兄弟轸孙遭流寇绑架;睢县汤斌的母亲赵夫人为流寇所杀;新安崔蔚林的母亲刘夫人死于土寇之难,父亲被斩断三指。另外,孙奇逢的女儿为避清军侵害投井自杀,身边的幼子杨令名被掠。这些人大多是中等以上人家,尚且家破人亡,普通百姓的生活之动荡、痛苦自然更甚。因此,清初入仕的人中,除了有把自己实际的政治经济利益置于“气节”之上的人,也确有不少身经目睹二十余年战乱流离之痛后的士绅。这些士绅希望通过自己的积极参与,能够有所作为,尽快稳定地方秩序,恢复民生。魏一鳌和他的同门汤斌、耿介等都因此而选择了出仕。
第四,孙奇逢的影响。魏一鳌与老师孙奇逢的关系极深,前后相交三十年。在理学思想方面,他早年也像同门赵御众、马尔楹、崔蔚林、张沐以及后来的耿介等人那样,与孙氏还有抵牾之处,如在程朱与陆王的选择方面。但是,在从学老师多年后,他几乎全盘接受了孙奇逢兼容并包、回归孔子的观念,且终身服膺,这一点迥异于上述几人。孙氏身处明清之交,思想界歧异迭出。在经历了反复的痛苦思索后,他选择了截断众流、回归孔子的学术取向。孙奇逢深受孔子践履思想的影响,始终认为儒生应当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他多次表达大劫之际,选择活着比选择死亡更难、出仕比隐居更难的观点。如:“杵臼以死易立孤难,先死以为其易。”[3]卷4又如:“崔文敏有言曰:‘元有三儒,耶律楚才之谏杀,许平仲之兴学,刘静修之不仕,三公固各有得也。’予私谓为静修易,为楚才、平仲难。先生(按:指魏裔介)今日固为其难矣:维持世运,鼓舞来学。”[7]卷17孙氏认为,出仕清廷是比隐居乡间更加艰难的事情,因为需要忍耻且有为。也即既要时刻与内心侍奉二主的耻感搏斗,还要努力收拾鱼烂的天下,使之尽快趋治。这是身处易代之际的士人义不容辞的重任与苦任,对他们在修身与治平等方面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魏一鳌完全接受了孙奇逢的这一思想。顺治二年(1645)八月,魏一鳌赴平定州知州任前,特意到夏峰辞别老师。孙奇逢赠以“洁己奉公、爱民礼士”[1]册2八字,就是希冀魏氏对己身和外物做到兼顾与平衡,尽到一个真正的士人应尽的责任。
正是在政治高压、谋生、思治、孙奇逢的影响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魏一鳌做出了出仕清廷的选择。
三、魏一鳌的退隐
魏一鳌的仕宦生涯自顺治二年(1645)平定州知州任上始,在经历数次官场起落后,于顺治十三年(1656)任忻州知州匝月即引病辞归终。除去丁父忧的三年,魏氏实际的做官时间在八年左右,不能说太短。显然,起初他对自己在官场的作为是有所期许的。但是父丧期满之后,他迅速从忻州知州任上辞职。这不由不引人疑问,魏氏为什么会在长期为官之后忽然决然辞职,回乡归隐?个中原因值得探讨。
第一,是魏一鳌恬淡的性格使然。孙奇逢曾评价说:“(莲陆)善吏事,而能以恬退为心。”[7]卷19他的好友兼同门汤斌也含蓄地以颜回与孔子来比拟魏氏与孙奇逢的关系,评价魏一鳌说:“昔莲陆才大而养之以静,学博而守之以约,尝刺晋之大州,搜访隐遗,折节下士,去官之日,匹马双僮而已,世俗升沉得失无足介其胸中者。后日为师门颜子,必莲陆也。”[2]卷3汤斌的评价代表了夏峰同人对魏一鳌的普遍看法。魏一鳌自己也确以颜回为榜样。他任职平定州知州期间,躬自刻苦,日常生活极寒素。一年后遭免时,“闻命甚喜,每多设醇醪于座隅。有人劝以婉转,或以服官为美事者,辄以酒灌之,务至酩酊以塞其口。未几,新守到,而公竟飘然而归矣。”[1]册2这些都不是矫节啖名的行为。回乡后,他请魏象枢为书斋命名“广居轩”,正像孙奇逢解释轩名时所讲的“此居也,与人俱生,随在而足,在己不费,在人不忌,当下便有广大高明之象,直于乾坤易简中认出可大可久之业。孔之疏水曲肱,颜之箪瓢陋巷,所谓乐在其中不改其乐。天下万世,皆托以为居安资深之地。美富无穷,睟盎自若,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3]卷2。此是深知魏一鳌的确论。因此,魏氏尽管在科场一途相当顺利,任职山西期间也颇受上峰赏识。但是,他对名利的淡然,使他的归隐成为自然的选择。
第二,是魏氏不能摆脱侍奉“二主”的耻辱感,精神痛苦所致。顺治二年(1645)之前,魏氏不曾动念出仕清廷。如前所述,他的很多同门与好友都在明亡之后坚决不应试、不出仕,以布衣终身。他的好友张罗喆本是明诸生,又是清苑县名士,清朝建立后遭受巨大的政治压力。为了反抗,他干脆放弃诸生身份。尽管张氏此后贫窘异常,但是深受地方士人的敬重。这不可能不对魏一鳌形成一种刺激。张氏卒后,魏一鳌将他的牌位奉于五贤祠(7)五贤祠,保定五贤祠,魏一鳌建,用以祭拜二程、刘因、鹿善继、孙奇逢。祔食的行为,正是对这一刺激的反应。这一行为也昭示了他对仕隐的真实态度。顺治二年(1645)魏一鳌赴平定州知州前,亲到夏峰见孙奇逢。两人具体谈了些什么已不可考,特别是魏一鳌一方的想法与言语,一字无存。但是,从孙奇逢回复他的话“此时官虽不可做,然做亦自有方。唯在洁己奉公、爱民礼士八字”[1]册2,至少可知,魏一鳌必然是在出仕不出仕之间极度挣扎,迫切希望获得老师的开解,才有发问,孙奇逢也才有这样的回答;孙氏的观点还是以不出仕为优选,不得已出仕,则为官时要遵循八字原则。显然,从魏氏随后即奔赴山西的行为看,孙奇逢的回答对立刻就要被迫赴任的他起到了很大的安慰作用。与此同时,孙氏的回答也给予了他一个面对出仕与归隐选择时操作性很强的方案。因为孙、魏的共同看法是做清朝的官本是忍耻,但基于儒士的责任,如果能够做到八字原则,也还值得;如果连这也不可得,不如就此解脱,精神上也免除了如影随形的痛苦。魏氏后来的辞官,正基于此。
第三,对官场的厌恶所致。魏一鳌为宦八年,身经目睹了足够的官场丑恶。首先,是选官过程的折磨。顺治二年(1645)夏,魏氏被迫赴部试。恰逢广西恢复,急需大量地方官。参加考试的人都有可能被指派彼处。消息传开,众人恐惧。魏一鳌也不例外,他“归寓自思:广西在数千里外,余有老母在堂,无兄弟侍养,今补此地……不如自己毙命,以全老亲”[1]册1。面对可能被指派边疆的前景,恐惧到至于自杀的程度,在今人看来或许不太可解,但在当时却有着真切的现实原因。虽然后来魏一鳌幸免,但是凡与魏氏一同考试的人都不幸入选,“皆号恸归舍”[1]册1。这一番进入仕途门槛的体验,对魏一鳌来讲显然是很不愉快的。其次,是为官的凶险。诸多事例中,以好友张元玉之死对魏氏刺激最大。张氏是魏一鳌的直隶同乡、壬午同年、忻州同僚,“工书,喜为诗,善骑射,负经济才,倜傥有大志。……有古循吏风。不能媕婀以悦上官。”[1]册1张、魏两人感情非常深厚。张氏因卷入山西按察使娄惺伯“疏纵故明藩王”一案而遭冤杀。(8)娄惺伯,湘阴人,明崇祯时泾州知州娄锈之子,以父荫任明户部云南司主事等职。入清后任户部员外郎、山西布政使司参议、山西按察司副使管按察使事等职,顺治四年(1647)以庇护前明藩王的罪名遭弃市。(参见《清实录·世祖实录》卷六、卷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三十一,及嘉庆《湘阴县志》卷二十八、卷三十五)魏一鳌悲愤异常,完全不避嫌疑地“为立传,兼梓其诗,俾千百世后读元玉诗,曰静谷有友。是余又借元玉传矣”[1]册1。又请孙奇逢为张作传,多年不能释怀。眼见身为循吏的好友因为官场倾轧无端殒命,魏氏深受打击。再次,是某些行政事务的压迫。魏一鳌的工作主要是处理各类刑事、民事案件,繁剧自不待言。但给他最大压力的,当属清廷督催至深至严的清查、缉捕前明皇族与有反清复明嫌疑的遗民一类案件。这是他不想处理,又不得不处理的。感情上,他同情这些被查办的人,办案时常留余地;理智上,他又不能不敷衍上峰,使案子大貌看得过去。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左支右绌,常把自己置于异常艰难甚至危险的境地。魏一鳌对这一局面的发展前景很清楚。及时止步,势在必行。
第四,为母亲影响所致。魏一鳌之母杨氏出身巨族。她侍奉舅姑有节度,以孝知名乡里;治家宽严相济,克勤克俭,尽力支撑家庭经济的正常运转;厚待亲族邻人,对佣仆和善;对儿子的友人、同门热情有礼。魏氏受母亲影响很大,处世原则一出其母。好友王余佑曾总结说:“莲陆所奉以周旋者,皆母训也。……莲陆之庭帷养志实则之母……治繁理剧实则之母……善气迎人、远近沾洽实则之母。二十余年间,凡我同仁欣慕莲陆之德,皆母德也。”[8]卷15杨太夫人更为可贵的是,对利禄毫不挂心。顺治十三年(1656)十月末,魏一鳌最末一次为官——被迫赴忻州知州任,内心矛盾痛苦。随任的杨氏觉察到儿子的心意,不仅力劝其辞官,并且毅然先携儿媳归乡,以示决心。正是在母亲的支持影响下,魏一鳌才在任职仅一月余的时候即摆脱顾虑,归隐渥水。
从上述原因可以清晰看到,魏一鳌毅然退隐的决定是非常理性、自然的了。
四、结论
异族易代之际,在前朝已有功名的魏一鳌陷入彷徨。一方面,虽然他经历了明末政治的一团漆黑,对之并没有多少留恋,但正统的儒家士人身份使他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程度的忠君思想。另一方面,孔孟的积极入世、勇于作为,夏峰的注重践履与事功,又对他影响极深,使他期待在清初百废待兴之际能发挥自己的才干,安民济世。在第一种思想的影响下,他虽然没有像有些朋友那样舍身殉明或投奔大荒,而只是蛰居乡间,但不与新朝合作显然是他的第一选择。在面临清政府强逼入仕的境况之时,第二种思想又占了上风,既然官非做不可,那么尽量做循吏,尽到自己士人的责任,也未为不可。在魏一鳌为官期间,这两种思想始终彼此交战,随着他的心理状态与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互有胜负。两种思想的斗争体现在形迹上,即是他的时仕时隐。
魏一鳌的心理状态,也是同时期众多汉族士人共有的。面对朝代更迭和异族统治这样的双重困境,他们昔日的认知与定位都被打破,不得不反复调整,以适应全新的政治、文化等环境。这个调整的过程对多数人来讲,必然不是轻松愉快的。起初,他们自然是希望能在此时保有政治上的“清白”,以全名节。但是,谋生手段的匮乏以及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加上满清政府施加的压力,使得他们对入仕有了一定程度的接受。可是,在做官之后若未能实现他们的预期目标,“变节”的耻感就会凸显出来,归隐又成为他们新的取向。总之,明清之交的汉官无奈地身逢易代,使命感与耻辱感始终交织于心,如影随形。在内心的焦虑无法承受之时,他们只得以入仕与归隐来调整与纾解。从另一个角度看,具有如此心态的汉官往往有强烈的家国责任感。他们在居官期间勉力从公、勤政爱民,为稳定地方秩序,恢复民生做出积极贡献;归隐之时则常能协助地方官员,为行政事务出谋划策,同时还往往主动肩负起教化桑梓的重任。因此,无论仕隐,这些汉官都为清初的政经稳定与建设做出了努力,值得今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