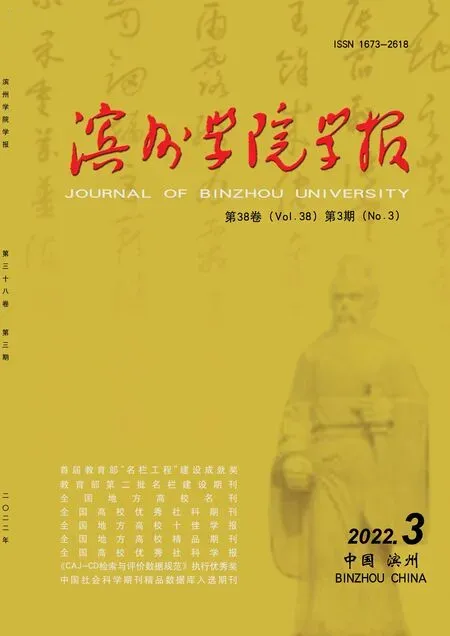从司马懿看道家思想对兵学文化的影响
姚振文,许 金
(1.滨州学院 孙子研究院;2.滨州学院 学报编辑部,山东 滨州 256603)
司马懿(179—251),字仲达,河内郡温县(今河南省焦作市温县)人,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权臣,西晋王朝的奠基人之一。历史上,人们对司马懿的评价褒贬不一,众说纷纭,然少有人从道家思想的视角审视其政治作为和军事活动。
在笔者看来,司马懿当是道兵家比较典型的代表人物,考察其家世背景和思想经历,他有一个明显的由“儒”向“道”转变的过程,而且这种转变对其军事思想和一生业绩具有重要的影响。
《晋书·宣帝纪》有云:“(司马懿)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再结合《三国志》的记载来看,司马懿青少年时代曾受过儒家教育是无疑的。他的父亲司马防是一个深受儒家礼教思想影响的人,“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三国志·司马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他的哥哥是司马家族第一个以经学入仕的人,并在后来独立承担起抚育诸弟的责任,“时岁大饥,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训诸弟,不为衰世解业。”(《三国志·司马朗传》)正是依据上述史料,陈寅恪先生认为,司马懿一生的思想信仰是儒家,而且将其视为“潜伏在曹魏王朝内部达40年之久最终取而代之的儒家理想主义者”。[1]144-146
然而,司马懿早年亦接受过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和熏陶。据记载,他年轻时的一位老师就是当时的大隐士胡昭。“晋宣帝为布衣时,与昭有旧。同郡周生等谋害帝,昭闻而步陟险,邀生于崤、渑之间,止生,生不肯。昭泣与结诚,生感其义,乃止。昭因与斫枣树共盟而别。”(《三国志·魏书十一·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裴注引《高士传》)而据《三国志·魏书》的记载,胡昭曾多次婉拒曹操的“礼辟”,终身不仕,“急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辞袁绍之命,遁还乡里。太祖为司空丞相,频加礼辟。昭往应命,既至,自陈一介野生,无军国之用,归诚求去”。胡昭的这种道家思想倾向和隐逸态度,不能不对司马懿产生影响。
再后来,司马懿受曹操所迫进入丞相府工作,历任文学掾、东曹属、主簿、军司马等职,时间长达12年。这段时间理应是其思想立场由儒转道的关键时期。当时曹操的丞相府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学术文化中心,一大批新黄老学派思想家云集曹操周围,形成了建安名士这一新型士人群体。司马懿进入这一文化中心,势必要受他们的深刻影响。更何况汉末的动乱和社会灾难也确实证明了新黄老哲学的现实有效性,司马懿是聪明之人,他不会感受不到这种社会趋势的变化。所以,由儒家的“内圣外王”向道家的自我生存哲学转变,这当是司马懿的理性选择。
有学者曾指出:“‘汉末新黄老派哲学’,是后来司马懿灵活运用刑名法术、儒术和一切权术,不忠不信、不仁不义地搞禅代、骗同党、杀降卒、弃发妻而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思想基础。”[2]在笔者看来,司马懿接受道家思想影响,并不单纯是新黄老哲学,它更多是以先秦道家哲学为思想根基的。比如,司马懿临终之时的嘱托之言就颇有老子思想的意味,“恒戒子弟曰:‘盛满者道家之所忌,四时犹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损之又损之,庶可以免乎’。”(《晋书·宣帝纪》)
鉴于此,笔者试图从先秦道家的基本思想立场(以老子思想为主)出发,更全面客观地解读司马懿的政治军事活动,并从中探讨道家思想理论对后世兵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一、冷眼旁观与战略卓见
《汉书·艺文志》有言:“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这句话的意旨很明确,出自史官的道家能够从历史的成败存亡中,把握事物发展的要害和根本,然后将清虚和守弱作为君主统治的要术。这是道家思想的一大优势。
李泽厚先生曾指出,《老子》思想是一种“以无事取天下”的积极的政治理论,“所以它的辩证法在实质上并没有失去主体积极活动性的特征。只是它不是在瞬息万变的军事活动中,而毋宁是在较为久远的历史把握中获得和应用,从而具有静观的外在特征,好像是冷静旁观似的”。他接下来还阐明了由此导致的道家对兵家的影响,“由于观察总结历史经验,由于它的似乎是冷眼旁观的静观气质,使兵家的冷静理知不动情感的特色在这里就更为突出了”。[3]
冷眼旁观最大的好处是理性认知和长远认知。它能在错综复杂的现实面前,使行为主体不为表象所惑,不为感情所困,不为认知所限,迅速舍弃次要和烦琐的东西,突出而集中地抓住矛盾的要害,进而抓住与战争活动有关的事物的关键和本质。道家的这种冷眼旁观思维在司马懿身上得以深刻体现。从历史上看,司马懿不仅是一个冷静、理性的人,更是一个有大略的思虑长远的人。
司马懿出身士族,且聪颖明理、学问广博,因而在年轻时有走上仕途的各种优势条件。然而,他却不急于入仕。《晋书·宣帝纪》有载:“汉建安六年,郡举上计掾。魏武帝为司空,闻而辟之,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司马懿为什么会拒绝曹操的征辟呢?因为他还不确定谁是雄主,他想再进一步观察和等待机会。《晋书·宣帝纪》言司马懿有“鹰视狼顾”之相也是很恰当的,“鹰视”就是形容像老鹰一样目光锐利,善于观察;“狼顾"就是像狼那样时常回头,防范别人。
后来,司马懿被迫进入曹操的政治中心之后,更体现出他冷眼旁观的理性眼光和战略卓见。
据《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第一次给曹操提出计策就颇显战略远见:“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意思是趁着刘备尚未立足于西川之时,一举攻下益州,便可提前占领整个西蜀地区!可惜的是,曹操没有采纳司马懿的计策,而是冷冷地言道:“人苦无足,既得陇,复望蜀”。曹操此人有时聪明,有时糊涂,这一次未听司马懿的计策,实在是铸下了历史大错,因为后来刘备在益州稳住了跟脚,天下三分之势遂成,在曹操的有生之年就再也没有机会攻进蜀地了。
又据《晋书·宣帝纪》记载,关羽发动襄樊之战,势如破竹,曹操惊恐,欲要迁都。司马懿进言曰:“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孙子有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高明的伐交可以借力打力、孤立对手,进而为战争胜利提供最有利的条件。曹操此次听取了司马懿的意见,一番外交活动之后,东吴吕蒙、陆逊设计偷袭荆州,诛杀关羽,吴、蜀矛盾激化,魏国被围困局不解自破。这就是战略卓见的功夫和成效。
通过上述两个例子,会发现,司马懿所提建议多是在战略层次,而且是在极为重要的关节点上提出,它往往能透过表象穿透至战略的最深层次,让整个局势发生扭转,最终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战略效果。若无一定的战略眼光,或者说若无道家冷眼旁观的功夫,恐怕也提不出这样的建议。所以,史家评论司马懿曰:“每与大谋,辄有奇策”(《晋书·宣帝纪》)。
二、守弱哲学与隐忍待机
道家思想本质上是一种守弱哲学,名曰“守柔曰强”,即特别重视“柔”“弱”“贱”“无”的一面。比如,“弱也者,道之用也”(《老子·四十章》),“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老子·七十六章》),“故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而以下为基”(《老子·三十九章》),“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老子·四十三章》),等等。老子还认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这句话用以形容司马懿的言行再合适不过,即始终是让人只注意到他“柔”“弱”的一面,然而其背后却隐藏着才能、力量和优势。
司马懿进入丞相府之后,面对心狠手辣的曹操,可谓危机四伏。而且“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晋书·宣帝纪》)然而,司马懿的“守弱”与“示弱”最终却能化风险于无形,逐步取得了曹操的信任。
首先,诚心拥护曹操篡汉。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向侍臣们出示孙权劝其称帝的书信,并言:“此儿欲踞吾著炉炭上邪!”司马懿则答曰:“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晋书·宣帝纪》)
其次,尽心做好职任上的每一件事,特别勤劳,像割草放马这类的小事他都亲自做。“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晋书·宣帝纪》)
当然,司马懿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多是有刻意伪装成分的。这也符合老子的示弱哲学,所谓“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四十五章》)这里的“若”本是好像的意思,引申理解就是“装傻”,其实质是韬光养晦、以退为进、以守为攻。所以,有人讲老子是阴谋家,“以为后世阴谋者法”(章太炎《訄书·儒道》)。当然,在道家看来,这样做是最好的生存哲学,它不但能使自己持久而有韧性,不会被对方转化掉,而且还能积蓄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得生存的可能性,直至最后夺取胜利。
在后来的政治和军事实践活动中,司马懿更是充分运用了这种“守雌”“贵柔”“守弱”的斗争哲学。
比如,诸葛亮第五次北伐之时,司马懿就采取了“坚壁拒守,以逸待劳”的战略方针。诸葛亮数次挑战,司马懿就是坚守不战,静观其变。是司马懿特别惧怕诸葛亮吗?显然不是。司马懿之弟司马孚来信询问前线军情,司马懿曾自信地言道:“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晋书·宣帝纪》)而且,“坚壁拒守”也不符合司马懿一贯的作战风格,他喜欢搞突然袭击,无论是之前的神速平孟达还是后来的远袭辽东,司马懿都是积极寻求战机,一旦时机成熟,则用兵如猛虎下山,正如他与魏明帝论兵时所言:“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
然而,此次对阵诸葛亮,司马懿为什么却如此小心谨慎呢?这是因为诸葛亮也是高明的军事家,且心思缜密,用兵几乎滴水不漏,所以他就只能步步为营,坚守待敌,避免出现错漏。高手过招,奇谋妙策的作用会大大降低,你能做的,对方也能做;你能想到的,对方也能想到。所以,这时候你只能做到尽量不失误,然后等待对方失误。如果对方一直不失误,那就是没有机会,就只能等,只能熬,只能隐忍,没有任何捷径,不要寄希望于侥幸取胜。这用孙子的话讲就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孙子兵法·形篇》)
对付曹爽,司马懿采用的仍然是守弱哲学,只不过变换成了老子的“将欲歙之,必故张之”策略,因为对手变了,曹爽此人外强中干,愚蠢至极,所以不仅是自己退让,还要让对手在疯狂中走向死亡。其一,在朝政和权力方面,司马懿一退再退,任由曹爽挤对自己。最后,让曹爽膨胀得连郭太后都不放在眼里(软禁了郭太后)。其二,在对外作战时,朝廷安排作战任务,司马懿都坚决服从朝廷任命,且亲自带兵出征。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通过战争的胜利,保持和提高自己的威望,而且这也是司马懿的比较优势(曹爽也领兵打了一仗,对蜀而战,大败)。其三,后来司马懿被剥夺兵权(但实际上依旧有自己的势力),于是又制造出种种假象,装病迷惑对方,司马懿就这样被曹爽压制了十年,也忍了十年,最后终于等来了机会,高平陵政变一举灭掉曹爽势力,曹魏政权也落到了自己手里。
后人都想领悟兵法的精髓,抑或从《老子》思想哲学中领悟兵法的真谛,而司马懿无疑是悟得了道家或兵家的“真经”之人。
三、因顺自然与权谋变化
道家贵因,“因”就是因循、随顺的意思。《老子》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这其实就是一个因顺、效法的过程。其所因、所顺的对象是自然之道,这是道家哲学的基本规定,同时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所谓“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淮南子·诠言训》)。
司马谈论及道家时,特别强调其为政在于“因循”,正因为有了它,无为与无不为才得以统一。“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论六家要旨》)王弼是历代公认的“解老”大师,他曾概括《老子》的大要曰:“因而不为,损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老子旨略》)
乐黛云提出:“中国道家哲学强调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不一定有预定的答案。答案和意义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和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之中。……最重要的就是不拘泥于人们以为是‘已定的’,其实仍在不断变化的‘确定性’,而是去研究当下的、即时的、能有效解决问题的、从现实当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可能性。”[4]
道家贵因的哲学思想在司马懿的用兵艺术中得以集中体现。孙权曾言:“司马公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晋书·宣帝纪》)这在神速平孟达的过程中已有突出的表现,而到平定辽东公孙渊时,此种“因变”的军事指挥艺术更是达于化境。
《晋书·宣帝纪》有载,景初二年(238)正月,司马懿率四万大军,攻打辽东,进至辽水。公孙渊带兵数万,坚壁高垒,以阻击魏军。司马懿先在南线多张旗帜,佯攻围堑,主力大军却秘密渡过辽水,逼近敌襄平大营。部将对这种“不专攻而设围”的方法颇有质疑,司马懿解释说:“贼坚营高垒,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计,此王邑所以耻过昆阳也。古人曰,敌虽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贼大众在此,则巢窟虚矣。我直指襄平,则人怀内惧,惧而求战,破之必矣。”这实际就是运用了孙子的避实击虚之策,正所谓“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孙子兵法·虚实篇》)。敌人见魏军抄其后路,急忙拦截,歼敌机会出现。帝谓诸将曰:“所以不攻其营,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纵兵逆击,大破之,三战皆捷。贼保襄平,进军围之。
《晋书·宣帝纪》又载:司马懿与公孙渊两军对峙之时,适逢连日大雨,辽水暴涨,魏军中有的将领主张迁营,司马懿不允。此时公孙渊军冒雨出城,打柴牧马,魏将领请求出击,司马懿又不允。司马陈圭问司马懿:“当年我们远征平定孟达叛乱时,靠的是速度取胜,这次同样是远征,为什么行动却缓慢了?”司马懿解释说:“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贼凭众恃雨,故虽饥困,未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惊之,非计也。”颇有意思的是,远在京师的朝廷众臣听闻征讨大军遭遇暴雨,“咸请召还”。而天子曰:“司马公临危制变,计日擒之矣。”可见还是皇帝更了解司马懿的因变和权谋。
司马懿的这种多变权谋及他自己的解释亦可归根于道家哲学的“道”和“无”。“道”“无”“虚”才是总体、根源、规律和真理,无数的变化和创新即由它们而来,它们绝对优胜于、超越于任何“有”“实”“器”。换言之,任何事物之“有”、实物之“有”或方法理论之“有”,无论其如何广大,都只能是有限的、暂时的、局部的、流动的。所以,政治或军事领域的指挥者和决策者如果不是处“无”而是占“有”,那他的运筹就被局限了,也就固守、机械和呆板了。
看司马懿的一生,他是深深领悟了道家上述思想要旨的,所以,无论政治和军事活动,他都能立足根本(道),在不接受任何“实有”的限定性中接受变化,进而“乘势而起,顺势而为”,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
四、刻薄寡恩与心狠手辣
道家是寡情的。《老子·五章》有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在老子看来,天地的运行变化是没有也根本不需要情感的,“圣人”的统治同样如此。
从这一点上讲,道家与法家是有源流承继关系的。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曾言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钱钟书亦言:“黄老道德入世而为韩非之刑名苛察,基督教神秘主义致用而为约瑟甫神父之权谋阴贼,岂尽末流之变本忘源哉?或复非迹无以显本尔。”[5]226总之,道家与法家可以说是源流或体用关系,老子是源,韩非是流;道家是体,法家是用。
李泽厚也认为韩非思想是承接《老子》的,“由冷眼旁观的非情感态度发展到极端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韩非把一切都浸入冷冰冰的利害关系的计量中,把社会的一切秩序、价值、关系,人们一切行为、思想、观念以至情感本身,都还原为归结为冷酷的个人利害。它成了衡量、考察、估计一切的尺度标准”[3]
此种源于道家而见于法家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想,曾经在战国及秦时一度占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汉至魏晋,它亦在政治传统和文化中得以延续,其与封建政治和兵家思想相结合,逐渐生成“刑名法术杂用”的新黄老哲学。司马懿晚年正是这种哲学的一个典型代表,他在各种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不断向道家的无情和法家的冷酷转变,最后终于变成一个阴鸷狠毒、奸诈虚伪、一辈子都在算计谋害别人的人。
襄平城被攻破之后,司马懿立即下令屠城,“既入城,立两标以别新旧焉。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之,以为京观。伪公卿已下皆伏诛,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收户四万,口三十余万。”(《晋书·宣帝纪》)高平陵政变之时,亦是大肆屠杀。司马懿违背诺言,一举诛杀了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等人(传言当时天下名士减半),并将他们夷灭三族,不分男女老幼皆杀,就连已经嫁人几十年的姑姊妹等也要全都杀掉,“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晋书·宣帝纪》)高平陵之变所表现的不仅是司马懿的残酷,更是暴露了他奸诈和阴险的政治嘴脸,可以说此次政变之后,司马懿虚伪君子的真面目尽显,并对后来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司马懿背信弃义,诛杀政敌,本是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不足为奇。问题在于,在秦汉至魏晋时期,社会风气依然比较淳朴,受宗法制度的影响,士人之间的交往还是比较讲究诚信的,司马懿如此不守诺言,大大降低了其在朝廷和士人中的威信和地位。比如,在诛杀曹爽之后的庆功宴上,太尉蒋济就拒绝晋爵领赏,而且从此以后,郁郁寡欢,很快病发身亡。晋人孙盛对此评论说:“蒋济之辞邑,可谓不负心矣。语曰:‘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蒋济其有焉。”(《三国志·魏书·蒋济传》)
司马懿阴狠毒辣及背信弃义的恶劣影响是极为深远的。西晋建立之后,司马炎及后继几位皇帝无不奢靡荒淫,且家族内部子孙之间为了争权自相残杀,最终导致八王之乱的发生及西晋的夭亡。此种悲剧的发生,与司马懿过于寡情、背离儒家政治理想应该有密切的关系。
《晋书·宣帝纪》所载的一件事典型地反映了这一问题:“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及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司马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虽然早期有儒、道双修的文化素养,但在残酷的政治博弈和军事活动中,其最终还是偏向了道家哲学(包括先秦道家和新黄老派哲学),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典型的道兵家人物。无论是其冷眼旁观的战略卓见还是其坚毅隐忍的为政作风,无论其权谋万变的用兵策略还是其残酷无情的内争手段,都能从道家哲学中寻找到最终的思想本源和理论依据。这虽然是个案,但从中可以看到,道家思想文化对兵家人物的影响是深刻而突出的,其对中国兵学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是无形而又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