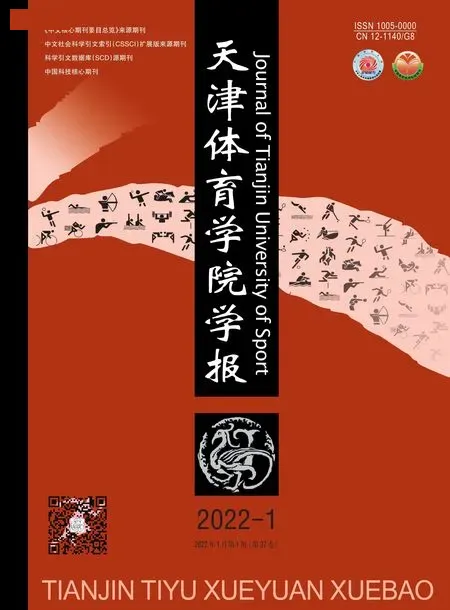强制体育仲裁之合法性要素探讨
郭树理
2020 年 1 月 28 日,欧洲人权法院宣布了对 5 起体育纠纷案件合并审理的结果[1],其中两起案件法院认定土耳其足球协会(简称土耳其足协)下设的仲裁委员会不具有中立性和独立性,其强制性管辖的体育仲裁程序无法保障球员或裁判员一方的程序权利,判决被告土耳其共和国政府(简称土耳其)败诉。这是欧洲人权法院继2018 年佩希斯泰因诉瑞士联邦政府案件(Pechstein v. Switzerland)之后[2],又一次对强制体育仲裁制度的合法性问题作出评判,不同于前一案件针对的是国际体育仲裁机制,本案针对的是国内体育仲裁机制,从涉及体育纠纷的范围上看,意义更大。本文将以土耳其案件为起点,就强制性体育仲裁制度的合法性要素进行分析,并探讨该案对中国强制体育仲裁机制的启示,并提出改革中国体育组织内部强制仲裁制度的具体建议。
1 基本案情
1.1 职业球员与俱乐部的雇佣纠纷案件
编号为30226/10 案件的的基本案情是,一名职业足球球员被土耳其一家俱乐部雇佣,后来该球员以俱乐部违反合同为由宣布提前解除合同,俱乐部将该球员告上土耳其足协下设的纠纷解决委员会。纠纷解决委员会裁决球员败诉,球员不服,上诉到土耳其足协下设的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维持了原裁决,只是减少了应当赔偿的金额。根据土耳其国内宪法和体育法规有关规定,足协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是最终裁决,不得接受土耳其国内法院的司法审查。该球员在土耳其已经无法获得进一步的国内救济,只能转向国际。2010年4月20日,该球员以土耳其为被告向欧洲人权法院起诉,认为土耳其未能有效保护自己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享有的寻求司法救济与公平审判的权利(right of access to justice and fair trail)。2020 年1 月28 日,欧洲人权法院作出裁决,认定土耳其足协的仲裁委员会不具有中立性和独立性,强制性管辖的体育仲裁程序无法保障该球员的程序权利,侵犯了该球员享有的《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所规定的权利,判决土耳其败诉,球员获得12 500 欧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
1.2 足球助理裁判降级纠纷案件
编号为5506/16 案件的的基本案情是,土耳其足协的中央裁判委员会根据足协裁判技术等级标准,列出了全国高水平足球主裁判和边裁的排名,前39名的主裁判和前70名的边裁可以执法新赛季的超级联赛。一名足球助理裁判曾是土耳其足球超级联赛的边裁,他在该边裁的排名(一共有83 位边裁)中位于78 名,未能进入前70名,下赛季只能执法低一级别的足球联赛。该边裁不服,认为每场足球比赛边裁的数量应当是主裁判的2 倍,既然超级联赛一共有39 名主裁判执法,那就应该有78 名边裁协助执法,自己应当能够继续执哨超级联赛。他向土耳其足联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推翻中央裁判委员会的决定,并请求仲裁委员会召开听证会,允许自己出庭陈述意见。仲裁委员会没有召开听证会就直接驳回了他的仲裁申请,理由是中央裁判委员会可以自由裁量修改每一赛季值哨裁判的数量,尽管每场足球比赛边裁的数量是主裁的2 倍,但联赛边裁的总数量不一定是主裁总数量的2倍。该边裁后来向仲裁委员会申请重新审理本案也遭到拒绝,仲裁委员会认为不存在可以重新审理的理由。2016年1月11日,该边裁向欧洲人权法院起诉土耳其,认为政府未能保障自己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6 条享有的寻求司法救济与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2020 年1 月28 日,欧洲人权法院判决土耳其败诉,理由和判决结果与第1 起案件相同,该助理裁判也获得了12 500欧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
2 质疑强制体育仲裁合法性的纠纷,国家政府为何成为了被告?
欧洲人权法院是根据《欧洲人权公约》建立的泛欧洲地区的国际法院,其管辖以《欧洲人权法院》缔约国政府为被告的案件[3],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34 条的规定:“如果任何个人、非政府组织、社团宣称一个缔约国侵犯了其公约和公约议定书所规定的权利,则法院可以受理该个人、非政府组织、社团的申诉。缔约国不得以任何形式阻碍该申诉权的行使。”目前,全部欧洲国家包括土耳其都是《欧洲人权公约》的缔约国(共47 国)。但土耳其球员系列案件都因球员和裁判员不服土耳其足协仲裁委员会的裁决而引起,土耳其足协是私法主体,并非公法主体,既非行政机关,也非司法机关,更非立法机关,而仲裁委员会只是土耳其足协的下设机构,甚至不具备独立法律主体资格,土耳其足协及其仲裁委员会的任何行为都不能视为是土耳其的国家政府行为。那为何土耳其会成为本案在欧洲人权法院的被告,要为土耳其国内私法主体的行为承担国家责任?
《土耳其共和国宪法》第59 条第3 款规定:“体育联合会涉及其体育项目活动的管理与纪律处罚的决定,只能通过强制体育仲裁制度提出上诉。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是终局的,不得向任何司法机关上诉[4]。”2009年5月5日,土耳其国会通过的《建立土耳其足协及其职责的第5894 号法律》第6 条(“仲裁委员会”)第4 款规定:“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是终局性的,对相关当事人具有拘束力,不得在其他任何司法机构就该裁决采取任何法律诉讼[5]。”《土耳其足协章程》第62 条与《土耳其足协仲裁委员会规则》第14条也规定了,足协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是与足球有关的纠纷的最终的、有拘束力的裁决,不得接受土耳其国内法院的司法审查。此外,土耳其国家宪法法院曾经判决土耳其足协强制仲裁的相关规则是合符宪法的[6]。根据上述规定和宪法法院的判例,如果土耳其足协强制仲裁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存在问题的话,本案原告土耳其球员和裁判员可能被剥夺了在土耳其国内寻求依法设立的审理机关进行公平公正的司法诉讼的权利,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的规定,寻求司法救济和接受公平审判的诉权是不得被剥夺的基本权利,土耳其由于涉嫌侵犯当事人在《欧洲人权公约》下的诉权,所以能够成为在欧洲人权法院诉讼的被告。
3 诉权保障对强制体育仲裁制度之基本要求
两起案件的起诉依据都是《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该条款规定:“在决定某人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或在决定对某人确定任何刑事罪名时,任何人都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到依法设立的、独立而公正的审判机关的公平且公开的审判。判决应当公开宣判……”
《欧洲人权公约》第6 条规定的“寻求司法救济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其实就是诉权,诉权作为一种程序性权利,是保障当事人实体权利而必须存在的“权利救济权”,因此,如果诉权的实现受到限制就会影响到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实现[7]。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6 条第1 款的规定,以及欧洲人权法院的相关判例,对诉权保障的基本要求有以下要点。
3.1 确保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
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access to justice)是诉权最基本的内容,是指当事人所享有的请求国家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利,即当事人在权利受到侵犯或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时,享有向国家司法机构请求进行诉讼、裁决其纠纷、予以司法救济的权能[8]。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的反面表述就是,国家负有不得拒绝司法(deny of justice)的义务,即不得拒绝受理和审理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的诉讼请求[9]。
但这项权利并非绝对的,当事人可以通过平等谈判协商一致达成的意思真实的仲裁协议,放弃向国家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而将纠纷提交民间性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10]。在欧洲人权法院审理的穆图诉瑞士联邦政府一案(Mutu v.Switzerland)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英超球队切尔西俱乐部与罗马尼亚职业球员穆图之间的雇佣合同中订立的将纠纷提交国际足联以及国际体育仲裁院进行仲裁的条款,是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自由协议,并非俱乐部一方强加给穆图的,穆图其实可以像其他球员一样,坚持不在合同中设置该仲裁条款,保留自己向国家法院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而通过该仲裁条款,穆图就已经明确放弃了将球员雇佣纠纷向国家法院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这一放弃是他自由意志的表现,是合法的,是符合《欧洲人权公约》相关判例的精神的。
但是,如果仲裁条款是强制条款,则情况会完全不同[11]。在佩希斯泰因案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速滑运动员佩希斯泰因之所以会把她与国际滑联之间的兴奋剂处罚禁赛纠纷提交国际体育仲裁院,是由于国际滑联的《反兴奋剂规则》中将兴奋剂处罚纠纷排他性提交国际体育仲裁院处理的强制性条款决定的,佩希斯泰为了能参加国际滑联举办的赛事,被迫接受这一条款的拘束,因为国际滑联控制了几乎全部的顶尖级国际滑冰赛事,这一强制性体育仲裁条款并非运动员真实意思的表示,有没有经过平等协商而签订,是一种格式条款[12]。所以,佩希斯泰因并没有明确放弃向国家法院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即《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赋予她的全部权利)。
土耳其系列案件中的仲裁条款性质不同于穆图案件中的仲裁条款,而与佩希斯泰因案件中的仲裁条款相同。土耳其足协仲裁委员会对本案纠纷的仲裁管辖权,并不是来自于球员或裁判员与足协之间自由平等协商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土耳其足协章程中的强制性排他管辖条款:所有足球事项的纠纷,都由土耳其足协的仲裁委员会专属管辖,且裁决不得向国家法院上诉,这一规定还得到了土耳其宪法第59条第3 款的背书(体育行业内部纠纷只能由体育仲裁机制专属管辖、不得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因此,不能将该强制体育仲裁条款视为是当事人放弃了向国家法院寻求司法救济的自由真实意思表示。结论就是,《欧洲人权公约》的相关条款在本案中必须适用,不得被仲裁条款排除。
3.2 受理案件的审理机关必须依法设立
欧洲人权法院在李思高诉联合王国案(Lithgow and Others v.the United Kingdom)中指出,《欧洲人权公约》第6 条第1 款的“审判机关”一词不仅仅指一个国家的标准司法体制中的传统法院,还包括“为了专门解决某些特定纠纷,提供相对应的保障而设置”的机构。“受理案件的审理机关必须依法设立”这一要求,是指受理和审理案件的机关必须是通过国家正式立法或其他法规设立的,要求法律规则对这些机构的机构设置、人员组成、任职条件、职权任期、审理程序等方面都进行详尽的规定。当然,审理机关的正式名称不一定要是“法院”,像欧洲各国国内劳动法设立的劳动纠纷裁判委员会、国内反垄断法设立的竞争委员会,只要其有具体管辖范围的规定、有对其中立性和独立性的保障,也可以视为是合法设立的“审理机关”。只有那些无法律依据的“私设公堂”——英文法谚称为“袋鼠法庭”(Kangaroo court)[13],即根本不符合法律规范、没有权威、不负责任、私设的公堂或非正规的法庭——的裁判,才会损害当事人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享有的诉权。
在土耳其系列案件中,尽管土耳其足协章程的规定(所有足球事项的纠纷,都由土耳其足协的仲裁委员会专属管辖,且裁决不得向国家法院上诉)可能会导致人们将土耳其足协仲裁委员会视为“袋鼠法庭”。但由于土耳其宪法和国会关于土耳其足协立法中对土耳其足协仲裁委员会裁决的认可,使得土耳其足协仲裁委员会成为土耳其国内足球纠纷事实上的“准国家审判机关”,还不好指责其为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的“袋鼠法庭”,在欧洲人权法院的诉讼中,当事人也没有就这一问题提出控诉。
3.3 审理机构必须是中立、独立的
法谚有云: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No one can be judge in his own case)。这是对审理机关和审理人员中立性和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包括2 方面:(1)审理机关必须独立于其他的国家机关(立法和行政机关),其他任何机构必须尊重审理机关的独立性,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司法裁判;(2)必须从审理人员的问责程序、豁免条件、人身保障、任期时限、薪酬待遇等方面,对审理人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给予必要的保障,审理人员(法官)必须独立任职,裁决案件时完全中立,与案件有利益关系的审理人员必须回避。
在土耳其系列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土耳其足协仲裁委员会在机构设置方面的中立性和独立性不够,无法保障具体的仲裁庭在审理案件时不受到外界压力,尤其是土耳其足协执委会的影响。土耳其足协仲裁委员会的委员(仲裁员)一共13 名,其中1 名主席,6名正式委员,6名替补委员,正式委员无法履行职务时由替补委员替补。委员会委员都由土耳其足协的主席推荐,由足协执委会任命,而足协执委会委员通常是足协成员俱乐部的前任职员,代表球员或裁判员而不是俱乐部利益的执委会委员数量非常少。尽管规则要求仲裁委员会委员必须拥有法学教育背景并有至少5 年的法律执业经验,但没有规定任何职业伦理方面的要求,对他们在仲裁工作中的职业操守进行保证。委员在任职时,也没有任何宣誓的要求(保证会独立、中立地履行仲裁员的职责)。此外,也没有任何规则保障他们的豁免权,保证他们不会因为在履行仲裁员职责过程中的行为而承担任何民事或刑事责任。另外,足协仲裁委员会各位委员的固定任期都没有规定,只是规定了仲裁委员会的任期和足协执委会及主席的任期一致,也没有禁止仲裁委员会的委员连续任职。最后,也没有信息披露规则要求仲裁委员会的委员在行使职责时披露有可能影响其独立性和中立性的任何信息,也没有回避规则(包括回避的理由和具体程序),规定当事人在质疑仲裁员的独立性和中立性时应当有权申请该仲裁员回避,以及仲裁员应当主动申请回避的情形。由于上述这些问题,无法保障土耳其足协仲裁委员会的中立性和独立性,足协执委会拥有对仲裁委员会巨大的影响力。欧洲人权法院正是以该重大瑕疵为由,判定土耳其足协的强制仲裁制度违反了《欧洲人权法公约》第6 条的规定。
3.4 审理程序必须公平
根据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诉讼程序必须公平这一要求主要通过双方当事人“武器平等”原则(equality of arms)来实现。“武器”是一个比喻,指在诉讼程序中审理机关提供给当事人的诉讼资源。“武器平等原则”的基本理念是:民事案件的原告和被告、刑事案件的控诉方和被告之间应当是平等的关系,审理程序中的每一方当事人均应拥有平等机会出庭,双方应有相同的机会在法庭面前陈述各自的观点,任何一方都不应该享有超越对方的任何实质利益,即双方当事人在审理程序中必须平等。该要求施加给审理机关的义务可称为“平等听证原则”(principle of equal hearing),即审理程序必须平等地对待和听取双方当事人各自的诉求和抗辩。在土耳其案件1中,当事人曾抗议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给予对方当事人的答辩时间长于给自己提出请求的时间,如果属实这就有可能违反了“武器平等”原则,审理程序未能做到公平对待双方当事人。
3.5 审理程序和裁决必须公开
法谚有云: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看到被实现(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其要求审理过程(诉讼程序)和审理结果(最终判决)都要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的监督。具体内容是:诉讼程序应当在公开的场合公开地进行,并最大限度地将听证过程和裁决结果公示于当事人和社会公众面前,包括从案件受理、举证、质证,到辩论、裁决等各个环节。审理公开可以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有利于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审理机构和审理人员的权力行使进行监督;有利于实现司法的社会教化功能,增进法治意识[14]。
欧洲人权法院在佩希斯泰因案中已经明确裁决:强制体育仲裁中如果所涉及的事项是纪律处罚方面的纠纷,则仲裁程序必须公开进行。土耳其系列案件中,案件2 中的教练员也抗议过足协仲裁委员会未举行公开听证会(甚至没有召开听证会),就驳回了他的诉求。如果属实,这有可能涉嫌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要求的公开审理和裁决公开的原则。
3.6 审理机关必须及时裁判
法谚有云: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司法救济必须及时,否则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会遭受更大的损害[15]。欧洲人权法院在判例中已经明确:缔约国审理机关对民事或刑事案件审理程序的不合理迟延,是对《欧洲人权公约》第6 条第1 款要求的违反。不过在土耳其系列案件中,当事人未提出对土耳其足协仲裁委员会“审理迟延”方面的指控。
4 强制体育仲裁之国际版vs 国内版:合法性不同?
在土耳其系列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否定了土耳其国内足球强制体育仲裁的合法性。但是在此前2018年10 月2 日裁决的佩希斯泰因案和穆图案件,以及2020 年3 月5 日裁决的普拉蒂尼案件中[16],欧洲人权法院都认可了国际体育仲裁院强制体育仲裁的合法性。欧洲人权法院对国际与国内强制体育仲裁的司法态度之所以不同,主要原因是国际体育仲裁院的中立性和独立性获得了欧洲人权法院的认可,而且国际体育仲裁院的仲裁裁决还有接受国家法院司法审查的可能性。
在佩希斯泰因案中,欧洲人权法院虽然认为国际体育仲裁的领导机构——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的人员组成上,来自体育组织的理事数量占优势,而且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员的任命是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负责的,体育组织可能对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和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员名单的制定具有影响力。但法院认为,这些影响并不足以让人质疑体育仲裁院仲裁员名单上300 多名仲裁员的中立性和独立性。这300 多名仲裁员并非全部是体育组织的利益代表者。而具体案件中3 名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中,双方当事人都可以自由指定己方的仲裁员。欧洲人权法院仔细审查国际体育仲裁院的章程与仲裁规则发现,体育仲裁院仲裁员的任职有严格的任期限制(4 年),尽管可以连续当选;对其任职资格和条件有严格的限制(体育和法律或仲裁方面的专业背景);就职时必须进行宣誓(保证会独立履行职责);有严格的仲裁员回避制度(当事人申请回避或仲裁员主动申请回避);有严格的仲裁员革职制度(渎职或怠于履行职务的情况下);有仲裁员法律责任豁免制度(仲裁员裁决案件中的职权行为免于法律责任追诉);有仲裁员信息披露制度(担任具体案件的仲裁员必须披露自己可能的利益冲突情形)等。另外,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裁决是可以接受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的,根据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对卡纳斯案的判例(Canas v.ATP Tour),强制体育仲裁中当事人不得放弃请求法院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利[17]。尽管如此,欧洲人权法院还是批评了国际体育仲裁院未能公开审理佩希斯泰因的诉求,因此判决运动员获得了8 000 欧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18]。
而在土耳其系列案件中,土耳其足协仲裁委员会的委员(仲裁员)人数只有13名,全部由土耳其足协执委会任命,而执委会的委员几乎都是各足球俱乐部的前任职员;当事人不得指定自己的仲裁员;仲裁员的固定任职期限没有规定;就职时没有宣誓独立性的要求;没有仲裁员回避制度;没有仲裁员法律责任豁免制度;没有仲裁员信息披露制度;没有仲裁员免职制度。另外,根据《土耳其共和国宪法》第59 条第3 款和国会对土耳其足协的立法第6 条第4 款的规定,足协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是终审裁决,不得接受国家法院的司法审查。所有这些情况,让欧洲人权法院审判本案的7 名法官一致裁决:土耳其足协仲裁委员会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存在重大缺陷,无法满足《欧洲人权公约》第6 条第1 款的基本要求,无法有效保障当事人的诉权。
因此,欧洲人权法院对国际强制体育仲裁制度合法性的认可,与对土耳其足协国内强制体育仲裁制度合法性的否认,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考虑到仲裁在解决体育纠纷时的专业性、便捷性、集中性、统一性和自治性优势[19],设置强制体育仲裁制度本身(per se)并不违法[20](否则土耳其宪法第59 条第3 款以及国会关于土耳其足协的立法第6 条第4 款对强制体育仲裁制度的规定都可能无效),但强制体育仲裁制度要接受《欧洲人权公约》第6 条第1 款对“公平审判”规定的严格审查[21]。该制度必须保障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和接受公平审理的权利,仲裁机构必须依法设立,仲裁机构必须中立独立,仲裁程序必须保障当事人的平等听证权,程序和裁决必须公开,必须在合理的时间内审结案件[22]。满足上述要求的强制体育仲裁制度是合法的,否则是违法的。
5 《欧洲人权公约》下强制体育仲裁制度的合法要素
总结欧洲人权法院对土耳其系列案件的判决,并参考佩希斯泰因案件,可以归纳出在《欧洲人权公约》框架下,强制体育仲裁制度合法性的必备要素[23]。(1)仲裁庭的仲裁员必须完全独立于仲裁员的任命机构、组织或人员。(2)仲裁员必须有明确的任期,理想型的设置是:每名仲裁员的任职期各自独立,而且要独立于其遴选机关的任期。(3)仲裁员中应当有相当数量的人士可以代表运动员、裁判员等弱势当事人的利益。理想型的设置是:双方当事人可以指定自己的仲裁员组成合议仲裁庭。(4)必须有明确具体的规则保障仲裁员的中立性和独立性,他们在任职时必须进行宣誓或签署中立性、独立性声明,在担任具体仲裁庭的仲裁员时,必须披露可能影响其中立性、独立性的任何信息。(5)必须有明确具体的规则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员回避的权利,以及仲裁员应当主动申请回避的条件和要求。(6)兴奋剂以及其他纪律处罚案件应当公开审理,允许社会公众旁听,裁决也应当向社会公开。(7)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可以向国家法院申请对该裁决进行司法审查。
笔者认为,根据上述要素(尤其是第1 和第3 要素),其实欧洲人权法院对佩希斯泰因案件的裁决亦非完美。该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已经看到了在机构设置上,体育组织会对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产生影响(前者可以直接任命后者20 名理事中的12 名,剩下的8 名理事又由前面12 名理事提名),且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会对国际体育仲裁院产生决定性影响(前者有权制定修改后者的章程和仲裁程序规则,决定后者的仲裁员名单人选)。但法院最终却认为,这种影响不足以对裁决具体案件的仲裁员的中立性和独立性产生影响,因为体育仲裁院仲裁规则的具体规定可以消弭这些可能的影响。法院这一结论的逻辑可能存在问题,仲裁机构的整体设置和仲裁庭的具体设置都必须保持中立和独立,才能够保障当事人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正因如此,该案中有2 名法官提出了不同于多数裁决的异议判决意见,他们认为国际体育仲裁院的中立性是存在疑问的。笔者认为,即使是获得了欧洲人权法院的支持,国际体育仲裁院也应当进一步改革,尤其是突出运动员、裁判员等弱势当事人在强制体育仲裁机制的制度设计和运作中的发言权和表决权,使国际强制体育仲裁制度确实符合《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的要求[24]。
6 中国强制体育仲裁制度的合法性——以中国足协的内部仲裁机制为例
6.1 寻求司法救济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是一项人权
中国不是欧洲国家,不是欧洲理事会成员国或观察员国,而只有欧洲理事会国家才能成为《欧洲人权公约》的缔约国,因此无论如何《欧洲人权公约》不会对中国产生拘束力。但中国是联合国1948 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国,《世界人权宣言》第8 条规定:当宪法或者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遭受侵犯时,人们有权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请求有效的救济;第10条规定:在确定当事人民事权利与义务或者审理对被告人的刑事指控时,人们有权充分平等地获得独立、公正的法院进行的公正、公开的审理。尽管《世界人权宣言》只是一般性国际法律文件,是软法(soft law)[25],不是国际公约,不会对国家施加强制性的拘束力,但由于它是对各国普遍承认的人权保护原则的编撰,具有类似国际习惯法的效力。《世界人权宣言》是国际人权法的基础,各国政府负有国际义务,尊重和保护《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的各项基本人权。1998 年,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14 条第1 款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事实上,1966 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 条第1 款的规定,是参考1950年通过的《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而来,条文的措辞几乎一致。目前,中国政府虽然尚未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根据国际习惯法的规则以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第18 条规定的精神,签署国际条约即意味着签署国有批准的可能性,签署国应当秉承善意原则,在该国明确表示不会批准该公约受该公约的拘束之前,其行为不得违反已经签署的国际公约的宗旨与目的;尽管国家并不会因违反该国际公约而承担国家不法责任,但签署国有国际义务采取最低限度的合作以使得公约对其生效[26]。2004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宪法》)修正案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地写入了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33条。因此,寻求司法救济,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作为一项国际人权法普遍认可的基本人权,在我国也理所当然地获得《宪法》和各项法律的保护。
6.2 中国足协强制体育仲裁制度的设置
与土耳其类似,中国国内各体育组织,如中国足协,也设有自己的强制体育仲裁制度。《中国足协章程》(2019年生效版)第54条(“争议管辖权”)第1款规定:除本章程和国际足联另有规定外,本会及本会管辖范围内的足球组织和足球从业人员不得将争议诉诸法院,有关争议应提交本会或国际足联的有关机构解决。该条第2款规定:争议各方或争议事项属于本会管辖范围内的为国内争议,本会有管辖权,他争议为国际争议,国际足联有管辖权。第11 条(“会员入会”)第2 款规定:“申请成为本会会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1.申请书。申请书须对以下事项做出承诺:……(2)接受本会仲裁委员会和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管辖。(3)保证不将在国际足联、亚足联和本会章程规定范围内的争议诉至法院,国际足联和本会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13条(“会员义务”)第3款规定:承认并接受本会仲裁委员会和国际足联争议解决机构对行业内纠纷的管辖权,并在其章程中载明。《中国足协章程》第4章“法律机构”中,第52条“纪律委员会、道德与公平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第1款明确了仲裁委员会是中国足协的争议解决机构。从上述《中国足协章程》的规定可以看出,中国足协内部的体育仲裁制度,并非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自由谈判后意思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的基础上,而是与足协成员的会员资格绑定,加入中国足协就得接受足协仲裁委员会对相关纠纷的强制管辖,否则会丧失会员资格,由于中国足协在国内足球职业赛事设置和管理上的垄断地位,职业运动员不隶属于中国足协下属各协会的足球俱乐部,就无法开展自己的足球职业。因此,中国足协的仲裁制度是典型的强制体育仲裁。这种强制体育仲裁制度,是否会侵犯当事人拥有的向国家法院寻求司法救济、接受公平审判的诉权这一基本人权?
6.3 中国足协强制体育仲裁引发之困局
事实上,中国发生过类似土耳其足球运动员、裁判员的案件。2013 年2 月5 日,李根以沈阳东进足球俱乐部为被申请人,向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俱乐部支付拖欠的薪酬。仲裁仲裁委员会认为,该案中申请人仅要求确认解除球员合同,未主张支付拖欠薪金问题,故作出了解除球员合同的裁决。后李根再次向足协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支付拖欠的薪金,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于是,李根向沈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人事劳动仲裁,但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定不予受理。此后,李根向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起诉,法院裁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简称《体育法》)原第33 条(现第32 条)认为,该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驳回起诉。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李根的上诉,指令此案继续由铁西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其后铁西区人民法院判决沈阳东进足球俱乐部支付李根薪酬。俱乐部不服,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维持一审判决。2016 年7 月8 日,铁西区人民法院对沈阳东进足球俱乐部的财产执行了判决。俱乐部不服继续申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申诉后,指令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2018年4月13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一二审民事判决书,驳回李根的起诉,理由还是《体育法》)原第33 条(现第32条)。司法途径失败后,李根再次向足协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支付薪酬。足协仲裁委员会于2018 年7 月11 日做出裁决:在中国足协年度中期准入审核中,沈阳东进足球俱乐部因未能支付欠薪被取消了中乙联赛的注册资格,裁定不予受理李根的仲裁申请[27]。
李根案件凸显了中国足协内部强制仲裁引发的中国球员内部救济不公、外部救济无门的困境,这也是中国体育纠纷解决的法律困境。一方面,运动员在进入体育职业市场时,俱乐部就单方面限制运动员只能接受足协内部强制仲裁机制的排他性管辖,否则俱乐部不会与运动员签署球员雇佣合同;另一方面,这种足协内部的强制仲裁尽管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外部“体育仲裁”,但辽宁法院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却认可了此类体育内部仲裁条款能够阻却法院行使司法管辖权,球员不得向法院起诉。李根面临和土耳其球员、裁判员一样的经历,在国内无法获得有效国家审判机关的司法救济,中国足协的内部强制仲裁、中国法院对受理体育纠纷的谨慎态度,是否会损害运动员的诉权?
6.4 足协内部强制体育仲裁与中国体育仲裁机制
1995 年制定的《体育法》第32 条(原第33 条)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有学者统计,在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的体育纠纷案件中,有非常大数量的案件法院是以《体育法》第32 条的规定为由拒绝受理的[28]。辽宁三级法院也是以这条规定为由,最终认为法院不应当管辖李根案,但辽宁法院将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视为《体育法》第32 条规定的“体育仲裁机构”,并不妥当[29]。目前,我国尚未建立有《体育法》32 条所指的外部“体育仲裁机构”。辽宁法院的态度是对《体育法》第32条的理解偏差,李根案不应当成为中国其他法院的范例。妥当的做法是,法院应当把中国足协规定的仲裁机制视为是一种内部听证救济途径,只要运动员用尽了这些内部机制,法院就必须要受理运动员起诉(除非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体育仲裁机制建立起来)。
目前,我国外部体育仲裁机制的建立遭遇法律障碍。虽然《体育法》第32 条规定:“……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此条款明确了中国体育仲裁机制的立法形式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但2000 年颁布,201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简称《立法法》)第8 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十)诉讼和仲裁制度……”,体育仲裁机制属于仲裁制度,只能以“法律”的法律渊源形式进行立法。根据《立法法》第7 条规定,法律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立法法》第9条还规定,司法制度事项不得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给国务院进行授权立法。体育仲裁制度作为“司法制度事项”,也不能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给国务院进行立法。
《体育法》和《立法法》的条文在规定“有权颁布体育仲裁设立办法的机构”上存在法律冲突。从制定时间上看,后颁布的法律应当优先于前法而适用(《立法法》第92 条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从法律性质上看,《立法法》属于宪法性法律[30];从法律位阶来看,《立法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而《体育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因此,《体育法》的位阶低于《立法法》。总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可能只能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建立。《立法法》实施后,针对特殊仲裁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中华人共和国仲裁法》之外,相继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但寄希望于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仲裁法》国家立法,似乎不太现实。因为体育纠纷的数量毕竟有限,体育案件的社会影响也是有限的,未来的中国体育仲裁机构也只有一家,不会像民商事仲裁委员会、劳动仲裁委员会、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一样数量众多,国家专门的体育仲裁立法需要考虑立法成本与立法效益[31]。
但困境在于,法院动辄以《体育法》第32 条为由,拒绝管辖体育纠纷案件(正如辽宁法院一样),而真正的中国外部体育仲裁机制又由于立法权限不明等诸多原因,一直无法建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事实上取得了终局性的强制体育仲裁裁决的地位,与土耳其足协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一样[32]。为此,一方面我们呼吁改进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的仲裁机制,使其独立性、中立性、公正性和透明性得到增强[33],就像欧洲人权法院要求土耳其采取切实行动促使土耳其足协仲裁委员会进行改革一样;另一方面,我们呼吁尽快以《体育法》的修改为契机,尽快建立中国独立的外部体育仲裁制度。
6.5 改革中国足协内部强制仲裁制度
根据上文对强制体育仲裁制度的合法要素的阐述,笔者认为,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的体育仲裁机制应当进行以下改进。
(1)足协仲裁委员会的委员必须相对独立于中国足协、各地方和行业足协、各俱乐部;其任职资格必须有明确规定;任职时要声明保证自己的中立性;担任具体仲裁庭仲裁员时要披露相关信息。目前,《中国足协章程》第52 条第3 款只是规定了:仲裁委员会的成员不得同时担任中国足协其他机构职务。《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第4 条只是笼统地规定了仲裁委员会独立审理案件。此外,《中国足协章程》第52条第3款只是要求仲裁委员会的主任与多数委员会应当拥有法律职业资格,最好改为全体委员都必须拥有法律职业资格。此外应当规定:仲裁委员会的成员在任职时应当签署法定声明,承诺以个人身份独立、中立、客观、公正地履行仲裁员职能;在担任具体仲裁庭的仲裁员时,必须披露可能影响其中立性、独立性的任何信息。
(2)足协仲裁委员会委员除有明确的任期限制外,还应当设置免职机制。目前,《中国足协章程》第48 条第3 款规定仲裁委员会委员的任期是4 年,可以连选连任,但没有规定在何种情况下仲裁员可以免职。应当规定:当仲裁委员会委员违反《中国足协章程》《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的任何规定,或其行为影响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的声誉,则应当被暂时或永久性地免除委员职位。
(3)要明确足协仲裁委员会委员的组成人数,委员会中应当有相当数量的人士可以代表运动员、裁判员等弱势当事人的利益。目前,《中国足协章程》第52条第3款只是规定了仲裁委员会由主任1名、副主任1名、委员若干名组成,未明确委员的具体人数。仲裁委员会最理想的设置可能是俱乐部、球员裁判员委员会、足协外部第三方都能够提名1/3 的委员。在受理具体案件时,最好允许双方当事人都可以指任一名仲裁员,由双方当事人或他指任的仲裁员来协商选择首席仲裁员。目前,《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第8条规定:“……由仲裁委员会主任在仲裁委员中指定包括首席仲裁员在内的3 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共同审理案件”。当事人不能自己指定仲裁员。另外,虽然《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第24 条规定:“仲裁委员会审理足球运动员与足球俱乐部之间的纠纷案件,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在当事人以外的足球俱乐部及足球运动员中各选择1~2名代表参加案件审理。足球运动员代表和足球俱乐部的代表参加审理的案件,各位代表均有权对案件的裁决独立发表意见,仲裁庭在裁决前应当充分听取各位代表的意见”。但这些代表并不能裁决案件,只起到了观察员和评论员的作用,无法切实保障弱方当事人(运动员、裁判员)在仲裁程序中与对方当事人(俱乐部)之间的平衡和对抗。
(4)必须有明确具体的规则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员回避的权利,以及仲裁员应当主动申请回避的条件和要求。目前,《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第24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庭组成人员的独立性、公正性产生具有正当理由的怀疑时,应当向仲裁委员会提交书面回避申请,说明引起回避请求的事实,并附相应证据。申请应在知悉回避理由后立即提出。仲裁员应否回避,由仲裁委员会主任决定,仲裁委员会主任的回避由仲裁委员会会议决定。在应否回避决定作出前,被请求回避的人员应当继续履行职责”。此条文未规定仲裁员的主动回避制度,而且对回避申请的决定直接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或全体会议决定,这有“自己裁决自己是否回避”的嫌疑,应当将决定权交给另外一个独立机构。
(5)兴奋剂以及其他纪律处罚案件应当公开审理,允许社会公众旁听,裁决也应当向社会公开。目前,《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第11 条规定,即使是开庭审理的案件,除仲裁参与人外其他人不得参加。
(6)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可以向国家法院申请对该裁决进行司法审查。目前,《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第4 条规定:仲裁委员会处理纠纷案件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应当增加条款规定:不服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可以向中国体育仲裁机构上诉,在中国体育仲裁机构未成立之前,可以就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
6.6 以《体育法》修改为契机,尽快建立中国独立的外部体育仲裁制度
2018 年9 月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公布,《体育法》的修改属于“需要抓紧工作、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第二类项目”,提请审议机关或牵头起草单位为全国人大社建委[34]。目前,体育法学界正在热议《体育法》的修改[35],学者们都建议修改后的《体育法》应当增加“纠纷解决章”[36],就中国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置和程序规则进行规范。在修改后的《体育法》中,专门就体育纠纷的解决包括体育仲裁制度进行规范,是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比较可行的立法思路[37]。2020 年5 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青少年球员转会赔偿案件时,发现体育纠纷管辖问题存在较大分歧,该法院分别向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发送了司法建议函,建议国家体育总局加快推进《体育法》修改准备工作,积极建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尽快审议修订《体育法》,尽早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体育仲裁制度;在我国体育仲裁制度建立之前,加强对各体育协会的监督指导,要求各体育协会不得限制其会员单位或运动员就体育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权利。2020 年9 月,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分别正式函复朝阳区人民法院,表示将继续配合全国人大社建委,加快推动修法进程,设立体育仲裁制度。2020 年12 月2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八次委员长会议原则通过了2021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修改《体育法》列入了2021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2021 年10 月23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布了《〈体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修订草案新增了第七章“体育促裁”,一共14 个条文。我们期待,以新修订的《体育法》为法律渊源的独立外部体育仲裁制度,将尽快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