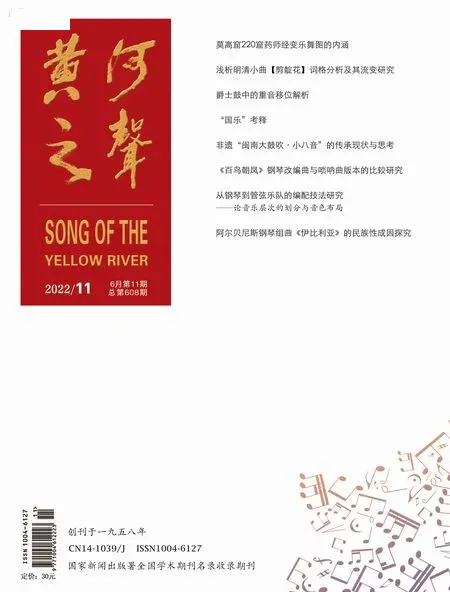阿诺尔德·勋伯格《期待》的叙事性修辞阐释
刘为叶
阿诺尔德·勋伯格(A·Schoenberg,1874-1951)是20世纪奥地利先锋派作曲家,也是新维也纳乐派的核心人物。《期待》是勋伯格1909年创作的单人剧(Monodram),也是音乐史上第一部“无调性”歌剧,该歌剧十分注重对内心情感的表达。勋伯格特殊的犹太作曲家身份导致他遭受巨大的心理打击,出于对现实世界极度失望,对当时的社会环境的极度不满,由此勾勒出音乐救赎的理想。即对自己犹太人身份的重塑以及通过“花园”“荒野”“女人”实现自我救赎的渴望。那么作曲家到底是用了哪些叙述性修辞策略来表现其自我救赎的?需要说明的是王旭青教授曾在其著作《西方音乐修辞史稿》中,提出了本文、潜文和衍文三个维度来探索作品中的音乐修辞。基于此,本文试图以“叙事性修辞阐释”为切入点,从“本文、潜文和衍文三个维度”来分析作曲家创作意图,探究文本的哲理意涵。
一、本文:音乐本体之维
勋伯格在无调性作品《期待》中采用性别化的公开表演,凸显了一位女子在森林中寻找爱人时焦虑、不安,陷入幻想的不稳定情绪。以此。立足于音乐本体,可以看到为了表明以女性表演者为特色来构思无调性音乐,勋伯格不仅在歌剧形式结构上进行了突破与扩展,更是巧妙地将声响与脚本密切联系,运用配器来表现女人情绪的变化。
(一)结构
音乐中的意识流是在心理学、文学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意识流式”的音乐作品,淡化传统作品所强调的旋律、和声以及调性等要素,以人的意识形态为支点,模仿人的意识形态的流动来呈现作品中的重要内容。
《期待》主要讲述的即是女人去森林中寻找情人。剧情走向十分简单,戏剧冲突集中在第四场,即女人几经波折终于找到了情人,但情人已死。全剧时长共30分钟,前面三场剧情内容并无诸多变化,仅是几个场景的更迭。由此可见,《期待》戏剧结构并不十分集中,若按照传统戏剧结构理论,将本剧前三场删除,只保留第四场也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剧情。整个单人剧仅出现一个女人,表现得也只是女人情绪的不断变化,而女人情绪的表达主要是通过其自言自语来完成。然而我们观察脚本可以发现,为了表达意识的流动性,即使是女人在自言自语中有所停顿时,剧作家也仅是用省略号来表示,而不是句号。这也说明,即使语言停顿,女人的思绪却并没有停止过流动。据此从戏剧情节走向的角度来看,《期待》是一种无休止的意识流戏剧结构,关注的是人内心的情绪变化。
(二)声响
音乐是一门音响艺术,勋伯格致力于探索将新奇音色融入音乐的一种音乐表现形式。配器适应结构和音色的需要,而结构和音色又随配器而改变,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关联。在歌剧《期待》中恰好印证了这一点,配器与脚本密切联系,配器的运用表现女人情绪的变化。
该部独幕单人歌剧虽篇幅短小,勋伯格为这部独幕歌剧安排了一个女高音声部,与以往不同的是,它还配备了一支庞大的管弦乐队。整个乐队的编制共需100多人,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瓦格纳乐剧的影响,在作品中巧妙发挥出管弦乐队的核心力量,运用管弦乐队的音响效果使音乐中的戏剧冲突达到理想化。以往传统歌剧中更重视弦乐的表现力,然而现在勋伯格却拒绝了这样的乐队编制。在《期待》中,弦乐的作用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虽然乐队里弦乐组依旧存在,但整体使用的时间非常少。管乐占据主导地位,在渲染环境氛围以及刻画女人情绪时具有重要作用。例如第三场开头女人在森林中突然说“黑色的东西在跳舞…有一百只手…别傻…这只是一个影子…”这是女人发现一百只手到意识到这只是自己的幻觉的一个自言自语。为了描述该段心理起伏,A调单簧管率先以连续的附点两分音符A音奏出,在两拍半的休止以后,♭B调低音单簧管三十二分音符相继奏出,两只单簧管的配合演奏表现了女人从惊恐到趋于平静的内心波动。
此外,还添加有钢片琴这种较为新颖的乐器。第四场中女人唱道:“月亮是阴险的…因为它是不流血的,它的红是涂上的…”此时钢片琴运用震音演奏一闪而过,力度极弱,这种轻巧的节奏型表现出月光也是极弱的,快速的节奏型则体现出女人心中期待破灭的一瞬间,随即而来的便是无尽的痛楚与绝望。
由于情节发展的“意识流性”,勋伯格将音色的地位大大提升,尝试各种新奇的音色效果,各种器乐的独特音色表现是他关注的重点。例如第一场“在森林的边缘,月光照亮四周,森林中的树木高耸而黑暗。一个女人穿着白色的长裙,长裙上覆盖着的红玫瑰,部分花瓣在凋谢。”此处的场景显得极为诡异阴森,勋伯格在此处要求用琴弓上的木头杆去敲击琴弦。巧妙运用刺耳的音效加剧了观众内心的恐慌,对于烘托诡异气氛具有重要作用。
歌剧《期待》中女人的情感是复杂的或者说是“歇斯底里”的,勋伯格为了更强烈地表现女人情绪的起伏变化,在配器运用中还采用了许多修辞性的手法(如拟人、写景等),即用乐器的各种独特音色细致的模拟表现女人的情绪起伏和大自然的景象。这种通过综合性的音乐要素(配器手法)来表现“音响”本身,成了叙述音乐情节的重要音响策略。
二、潜文:隐喻修辞之维
勋伯格在这部作品中要言说的难道仅是无名女人寻找“爱人”的经历吗?剧中描写的女人回忆中的美好花园,阴森黑暗的森林等仅是为了剧情需要而设计的吗?通过对歌剧《期待》本体的进一步探索,会发现剧中的花园、荒野与女人等隐藏着更为深刻哲理意涵。
(一)花园
当时欧洲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人们心中的乌托邦世界彻底覆灭。西方人的眼里的花园从古至今就被赋予了关于天堂、幸福彼岸的一切美好憧憬,来衡量他们的尘世生活。当它在奥地利艺术的关键时刻出现时,能够帮助我们分清艺术与社会结构、乌托邦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发展阶段。
“众武士:我们是他身边的火轮。
我们是你身边的火轮,是直捣
秘密堡垒的人!
众武士:领导我们吧,苍白之人。”
该段文字源自于奥斯卡·柯柯什卡创作短剧《谋杀者,女人的希望》中的一段台词,其中的文字语言显示出武士强有力的肌肉,如今却萎缩得让人无法承受并迸发出致命的能量。
当柯柯什卡通过戏剧、绘画等来触发花园中的爆炸时,勋伯格在同一年(1908年)也为音乐世界的爆炸埋下了导火索。(当然,笔者以为这种花园中的爆炸,其实是人们心中乌托邦世界的毁灭而所做的类比。)他运用传统的审美形式来掩饰自己的颠覆性作品——《空中花园诗篇》。勋伯格对自己所开启的充满未知的庞大国度进行探索,突破到了无调性中去,探索花园背景中青春期的性觉醒这个主题,仅隔一年,他又创作了独幕歌剧《期待》,这与柯柯什卡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有些不谋而合。也是在1909年,它记载了一段致命的爱情,只不过这一次是从一个精神错乱的无名女人寻找恋人开始的,当无名女人发现苦苦找寻的恋人已是一具冰凉的尸体,但爱人是被女人所杀,亦或是被情敌所杀?我们无从得知。这种方式打破了传统音乐艺术中那些抑制其呐喊的旧秩序,代表秩序的花园,对它的借用与瓦解,都成为其呐喊的媒介。勋伯格作为乌托邦花园的颠覆者,在现实社会中
无法消除自己压抑与孤独感的渠道,但他凭借超凡的能力,创造出庞大的力量,“将荒野恰当地展现成了心理之人那形而上的类比和隐喻性的理想。他给那些能够倾听的人,展示出如何才能将荒野通过声音组织起来,以取代他不遗余力想要毁掉的花园。”
(二)荒野
“尼采用他派给自己的角色狂人的话宣称‘上帝死了!上帝依旧死了!是我们杀死他的!”勋伯格身在其中,也就是前文笔者所说的对现实世界的失望,导致其亲手摧毁象征乌托邦的花园,用荒野取代之。而荒野可字面直译为“荒凉而人迹罕至的野外”。在《期待》中,它更是一种精神寄托。这里的荒野又与歌剧中频繁出现的森林不同,《期待》的剧本充满了森林的消极特质。森林充斥着混乱暴力和恐怖的氛围,传统的标准几乎扭曲成难以识别的形式。这或许正是勋伯格对当时社会现状以及糟糕的个人经历的另类表现。花园已摧毁,只有阴森黑暗的森林,面临着“上帝已死”的现状,对于迷茫的人类如何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勋伯格指出了一条“荒野”的道路。
“路仍在黑暗中,月光落在树林的一片空地(荒野)上。那里有高高的草丛,蕨类,大的黄色蘑菇。女人从黑暗中出来。”。歌词中出现的空地也可以理解为勋伯格所指的荒野。对现实世界失望透顶的人们离开了上帝的怀抱,也无路跨进被毁灭的花园般的天堂。如同剧中的无名女人在漂泊的旅途上忘却“原本那条通过屈服于世俗的信仰来拯救灵魂、到达幸福彼岸的天堂之路”这条“荒野”之路在《期待》中被预示为一条“自我救赎”之路。荒野的尽头,我们不得而知,或许是重返伊甸园,或者依旧是混乱扭曲的荒野。
三、衍文:历史绵延之维
纵观西方艺术音乐的历史,不难发现社会历史现象与作曲家的音乐创作总是密不可分。基于此,在关注音乐本体的叙述功能以及其潜在的隐喻内涵之外,给予一定的历史维度的关照,有助于进一步深入思索音乐本体之外的命题,诸如更为深入地对人生、世界复杂性的主体思索。
二战期间,由于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犹太人遭遇了大屠杀的灾难,许多犹太科学家、音乐家被迫逃往美国寻求庇护,勋伯格便是其中一员。作为被迫害的一员,勋伯格也曾一度陷入绝望之境,但也在绝望中找到了自我救赎之路,勋伯格面对时局曾谈到“艺术不是那些向(命运)妥协之人的呐喊,而是与命运抗争之人的呐喊;不是那些‘为黑暗势力’效力之人的呐喊,而是那些投身机器之中、力图掌握其构造之人的呐喊。”深信自己的感受与本能,他清楚此刻在为精神解放的权利而战,追求自由是他的使命,如同政治激进分子为社会与法律权利而战一样,他要通过呐喊与命运抗争。
随着抽象混乱的精神成了音乐中的主要焦点,作曲家也用新的隐喻(即荒野)取代旧的(即花园)来形容外部秩序。当然,勋伯格的《期待》的隐喻是内心的瓦解,属精神病理学。而对于创作该部作品的个人灵感前面笔者也有谈及,即是勋伯格此前让人心碎的个人经历。通过对其历史背景的深入探讨,可见《期待》在“女性”歇斯底里的呐喊中完成声音解放,同时宣扬了人性与革命精神。以无调性音乐(女性的呐喊)影射混沌黑暗的现实社会(即森林)从中寻求精神解放之路(即荒野),从而完成了作曲家的“自我救赎”。
结 语
勋伯格有意通过《期待》来呈现人类内心的表达,以该歌剧影射表现主义思想,并以此寻求一种超脱自我的哲理。因此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表现一个病态的、近乎疯狂的女人的内心世界上,采用“意识流式”的戏剧结构达到“表意”功能。歌剧中女人的情感是复杂的或者说是“歇斯底里”的,勋伯格为了更强烈地表现女人情绪的起伏变化,用乐器的各种独特音色细致的模拟表现女人的情绪起伏和大自然的景象。然而勋伯格绝不仅是为了体现女人的歇斯底里,而是以音乐影射混沌黑暗的现实社会(即森林)从中寻求精神解放之路(即荒野),在无调性这种新形式中找到了描写自己呐喊的方式,这种方式打破了传统音乐艺术中那些抑制其呐喊的旧秩序,代表秩序的花园,对它的借用与瓦解,都成为其呐喊的媒介。勋伯格作为乌托邦花园的颠覆者,虽然在现实社会中找寻不到可以消除自己压抑与孤独感的渠道,但他凭借不羁的能力,完成声音解放的同时找到了“自我救赎”之路。■
——评《勋伯格与救赎》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