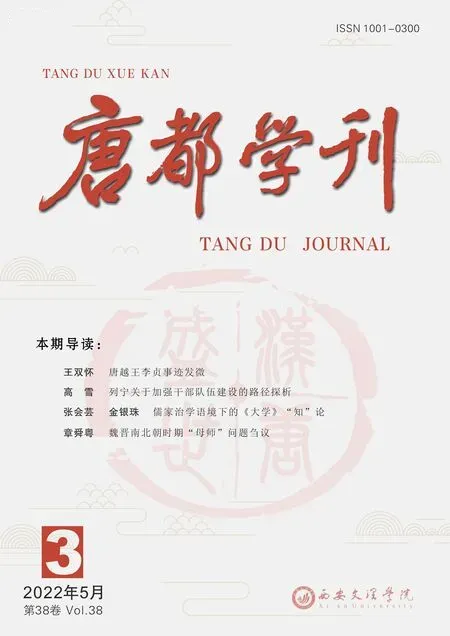论僧传中神异叙事的内在理论逻辑
——以《宋高僧传》为例
丁建华
(浙江工商大学 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杭州 310018)
宗教的发展往往伴随着神异事迹,作为经验科学的对立面,神异事迹往往被摈弃在学术研究之外,无法以是否是事实的态度严肃地考察其真实性,或者说,对神异事迹进行学术研究的前提就是否定其真实性。然而,当神异事迹被当做故事或传说记载下来的时候,神异事迹就不再是简单的过去事件,而是体现记录者、叙述者、传播者乃至整个社会的宗教认知,正如美国学者康儒博在其《修仙:古代中国的修行与社会记忆》中所揭示的那样。笔者认为,神异叙事不仅反映叙事者及社会普遍认知,同样也反映宗教理论,并且其主要的功能是作为传递宗教思想理论的中介。
佛教僧传中总是不乏神异事迹的记载,在《宋高僧传》中,赞宁将神异僧人归为“感通篇”,从18卷至22卷,一共记载了89人(正传),虽然比人数最多的“习禅篇”103人少了十几人,但是高于读诵77人、义解71人、名律58人、译经32人等。一方面反映了这一时期佛教发展以禅宗为主体、教下各宗式微的趋势,在社会层面仍旧非常关注在一般民众中传播极为重要的神异因素,正如康儒博所说:“从根本上说,这些作者(指中国历史上仙传故事的作者)并不能凭空制造叙事,也不会将此展现给没有任何准备而不得不将这些叙事看作全新作品的听众。”[1]11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为叙事转述者的作者的偏好,虽然无法据此判断出相比较作为佛教理论研究的义理,作者更为重视信仰传播助力的神异事迹,但是,起码他并不对神异抱持一种忽视的态度,从篇幅来说,还可以说他相当的重视。
中国佛教僧传中的神异叙事,虽然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一种外在表现,比如“长相怪异”这一描述就类同《庄子》中的人物,但其叙事的内核,仍旧是以佛教理论为核心的,在叙事过程中仍旧以传达佛教思想理论为主轴,而非单纯的事件记载。在《宋高僧传》中,神异都被归入“感通篇”,作者赞宁在《宋高僧传》“序”中这样形容“感通篇”:“逆于常理,感而遂通,化于世间,观之难测。”(1)可见,神异叙事一方面违背日常经验,被赞宁认为“逆于常理”;另一方面其目的又是针对生活在日常经验中的人的,又要回到日常生活中,所以赞宁说“化于世间”。笔者认为,“逆于常理”与“化于世间”应该是对僧传中神异叙事特征的最佳概括,既揭示其对日常经验的背叛,又说明了仍要回到日常经验的意图。
一、言行怪异:真谛的体现
神异的出现往往伴随着一系列不符合常识的现象,作为神异的主体,被记录下来具有神异的古代僧人们往往也带有神异叙事第一个特征:言行怪异。
在《宋高僧传·感通篇》中,赞宁对万迴的记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释万迴,俗姓张氏,虢州阌乡人也,年尚弱龄,白痴不语,父母哀其浊气。为邻里儿童所侮,终无相竞之态,然口自呼万迴,因尔字焉,且不言寒暑,见贫贱不加其慢,富贵不足其恭,东西狂走,终日不息,或笑或哭,略无定容,口角恒滴涎沫,人皆异之。”(2)参见赞宁《宋高僧传》大正藏第50册,CBETA电子佛典集成2016年版。在这类记载中,万迴完全是一个具备身体、精神疾病症状的形象。然而,通过考察可以发现,这种看似怪异形象的叙事背后,其实是立足于佛教思想理论的“不怪异”。之所以看似怪异,原因在于判断立场是立足于凡夫的认识层次——日常生活,实际上并不怪异的判断,则是立足于佛教本身的理论——真谛。在佛教理论系统中,“真谛”一般存在两种理解,可以概括为“空”与“有”,即在回答形而上的本体论问题时存在的两种回答:一种回答以否定存在本体、本源为核心,另一种则肯定存在本体性质的实体。前者以高扬缘起性空的中观宗为代表,后者则以近代判摄为如来藏系的理论系统为代表。唯识宗理论则位于两者之间,有时候被划分到“空”的一方,比如吕澂“性寂”与“性觉”的划分;有时候又被划到“有”的一方,比如清辨、月称等对唯识宗的批判(3)参见丁建华《近现代佛教空有之争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然而,不论是否定本体的存在,还是肯定一个本体,必然由此形而上的理论基础衍生出“平等”的理念。
平等,作为佛教的一个核心理念,几乎贯穿于佛教各宗派思想中,尤其被禅宗演绎得最为活泼生动。无准师范就曾以中秋这样的一个日常现象来演绎“平等”,他说:“中秋上堂,寻常月是中秋月,中秋月是寻常月,看来真个只寻常,道是寻常又还别,别,别,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4)参见宗会《无准师范禅师语录》卍续藏经第70册,CBETA电子佛典集成2016年版,第222页。在这段话中,无准师范通过一个现实的情境来表达佛教理论,中秋月既是寻常月,又并非等同于寻常月。中秋月是寻常月,因为中秋的月亮与寻常日子的月亮没有什么不同,揭示本体论层面上中秋月亮与寻常月亮的相同。但是,两者并非完全相同,而是存在着圆缺的差异,这种既相同又不相同的状态其实就是“平等”。《中论》开篇“不一不异”是对“平等”较为清晰的呈现,“不一”强调的是对相同的否定,因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事物,正如西方哲学“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命题所揭示的那样;“不异”是对截然不同的否定,基于相同本体论基础,不存在完全不同的事物,正如“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一禅宗话头的意味一样。
万迴和尚怪异言行中“见贫贱不加其慢,富贵不足其恭”这一描述,是佛教“平等”理念的最佳体现。贫贱与富贵是一组对立概念,描述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差异,而这种差异导致了一般人的态度与情绪,面对贫贱者会轻视、傲慢,面对富有的权贵会恭敬、顺从,由这种比较心态产生诸多烦恼。但是,贫贱与富贵只是人的二元对立的认识,两者本身是无常的,并没有使得贫贱者与富贵者恒常的保持这种状态的内在规定性(自性),贫贱者有其贫贱的原因,富贵者有其富贵的原因,原因的改变就会改变贫贱与富贵的状态。所以,贫贱与富贵本身是条件性的暂时性的偶然存在,体现佛教缘起性空的理论,所以并不需要恭敬富贵者,也不需要轻慢贫贱者,因为富贵与贫贱都是有条件的、暂时的。
在《宋高僧传·感通篇》中,类同万迴的怪异描述是颇为常见的,比如河秃“乍愚乍智”,阿足和尚“形质痴浊,精神懵然”,待驾和尚“作为诡异”,惠忠“不食荤腥、有异常童”,些些和尚“状极憨痴”,义师和尚“状类疯狂”,隐峰“稚岁憨狂”,契此“言语无恒、寝卧随处”,如敏“深悯迷愚、率行激劝”,怀濬“憨而且狂”等等。但是,并非每个人的“怪异言行”都有如万迴一样的详细描述,常常是一笔带过,即使如此,仍可从“寝卧随处”等记载发现真谛层面平等理念的体现。另一些怪异言行如哭笑无常,如果推测其在常人哭时笑,常人笑时哭,从而体现对差异性的消泯,也在情理之中。
二、言必有验:俗谛的符合
神异之所以称为神异,而非怪异,原因在于怪异的主角总能回到日常生活中获得更高的认可,这就是僧传中神异叙事的第二个特征:言必有验。
如果考察万迴和尚,就可以发现他怪异表现之后是“言必谶记,事过乃知”(5)。第一件获得认可的事件是关于他兄长的,“年始十岁,兄戍辽阳,一云安西,久无消息,母忧之甚,乃为设斋祈福。迴倏白母曰,兄安,极易知耳,奚用忧为?因裹斋余,出门径去,际晚而归,执其兄书云,平善。问其所由,默而无对,去来万里。后时兄归云,此日与迴言,适从家来,因授饼饵,其啗而返。举家惊喜,自尔人皆改观,声闻朝延。中宗孝和皇帝诏见崇重。神龙二年,勅别度迴,一人而已。自高宗末,天后时,常诏入内道场,赐绵绣衣裳,宫人供事。”(6)参见赞宁《宋高僧传》大正藏第50册,CBETA电子佛典集成2016年版。这一事件与其他神异记载一样,如果按照近现代经验的学术考究,则必然只能斥之为讹传与阴谋。但是,不论是将之作为真实事件的记录,还是剔除奇幻部分留下的事实,两种解释模式[1]8都不影响对神异叙事的考察,因为这一考察本身,正如康儒博所说,不仅代表作者的意图,而且反映当时社会听众的思想准备。为什么怪异的形象必然要回到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得到肯定,才能成为神异呢?
如果说怪异形象代表的是佛教真谛对世俗的超越,那么可以认为,言必有验这一特征意味着真谛并不能通过完全否定世俗而呈现出来,恰恰需要通过俗谛来做呈现的中介,在佛教理论系统中对此有很多表述方式,包括性空不碍缘起等等。在《大乘掌珍论》中,清辨建立了“真性有为空,如幻缘生故。无为无有实,不起似空华”(7)的观点,作为中期中观学的代表,清辨在这首偈颂中,通过形上层面作为永恒理念的无为法,与形而下层面变化无常的有为法两个方面凸显中观学理论的核心——空。有为法因为是因缘造作产生的,条件性的产物必然由于任一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所以,有为法是一种如同幻象一般的暂时性存在;无为法虽然以否定造作作为其内涵,但是正因为无为法是依据有为法而建构的,所以与空中之花这一比喻一样并不是真实的存在。然而,清辨这一首偈颂当中,除了“空”这个理论核心之外,还有一个重点,即“真性”两个字,以此强调在讲“空”的时候,必须要限定在真谛,因为如果连俗谛层面的现象都否定,就会落入类同虚无的断灭空错误之中,所以,清辨一直强调不能违背“牧牛人”之类的普通人的一般认识,他说:“此中世间同许有者,自亦许为世俗有故,世俗现量生起因缘亦许有故,眼等有为世俗谛摄,牧牛人等皆共了知,眼等有为是实有故,勿违如是自宗所许,现量共知,故以真性简别立宗。”(8)参见清辨《大乘掌珍论》大正藏第30册,CBETA电子佛典集成2016年版。这一段表述是很具有代表性的,清辨认为,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肯定的东西,佛教也必须在俗谛层面肯定,通过否定事物内在规定性而呈现出来的“空”只能是在真谛层面,所以他强调必须在空的前面限定范围于真谛。可见,在俗谛层面不违背牧牛人等一般人的常识理解是佛教理论系统的基本模式。
基于俗谛层面对世俗认知的肯定,再来审视神异叙事中万迴从怪异向神异的转变就比较清晰了,因为他的怪异重新又回到了世俗中。如果没有兄长归家后肯定万迴,那么,万迴仍旧要被众人判断为疯言疯语,只有当兄长代表世俗肯定他的怪异背后是有其真正合理原因的时候,甚至世俗层面最高代表的政府、官僚、皇室对其肯定,万迴才被认可为超越世俗之上的“神异”,而不是低于世俗之下的“怪异”。
在“感通篇”中,言必有验这一特征几乎处处可见,虽然作为叙事者的赞宁换了丰富的表述方式,但是其意思是完全一致的,比如难陀“时时言人吉凶,多是谜语,过后方悟”;普满“以言斥事,往必有征”;义师“所言人事、必无虚发”;师简“好悬记杭越间灾祸,初无信者,验尤合符”等等。在言必有验所代表的不能违背俗谛这一特征的叙事中,世俗最高权力的官僚、皇室对神异的肯定是最有效力的验证,也代表最普遍的认可,所以,一旦僧传中神异获得了皇室的认可,那么作为神异事迹的叙事者,对该神异的记载也会相对更为详细,这足以代表佛教理论中俗谛对传达真谛的重要意义。
三、正邪分辨:化俗的方便
通过《宋高僧传》中对万迴和尚的记载,可以发现,神异并不能突破佛教理论的界限,而且恰恰是体现佛教理论的。但是,神异当中确实也有看似不符合佛教理论的记载,比如对难陀的记载。在《宋高僧传》中,开篇对难陀的为人评价了四个字:“其为人也,诡异不伦,恭慢无定。”(9)这几乎就是一种完全的否定了,因为“不伦”不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而且在佛教内部都是不允许出现的禁忌。
在关于难陀的神异叙事中,难陀自述说得了神通,称为“如幻三昧”,他说:“我得如幻三昧,尝入水不濡,投火无灼,能变金石,化现无穷。”(10)这一自述一笔带过,整篇重点在于他与将领的一次交往,进入蜀地之后,难陀常与三个年轻的比丘尼同进同出,有时大醉狂歌,有时聚众说法,所以将领将他抓了起来,但是,难陀让三个比丘尼化妆嬉笑,歌舞陪酒,最后还拿刀砍下三人的头,不过,当众人惊异之后才发现,三个比丘尼只是三根杖而已。在整段描述中,难陀违背了佛教的诸多禁忌,包括炫耀神通、化现女尼并使其歌舞陪酒等,都是不被佛教所允许的禁忌,这与万迴怪异的表现截然不同。那么,是否意味着神异可以超出佛教理论的界限呢?也就是说,只要有超自然能力的神异事迹,即使不符合佛教理论,僧传的作者仍会对其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吗?
在难陀的记载之后,叙事者通过“系曰”对其神异进行了讨论,“系曰,难陀之状迹为邪正?邪而自言得如幻三昧,与无厌足王同,此三昧者即诸佛之大定也,唯如幻见如幻,不可以言论分境界矣,四神通有如幻通,能转变外事,故难陀警觉庸蜀之人,多尚鬼道神仙,非此三昧不足以化难化之俗也。”(11)参见赞宁《宋高僧传》大正藏第50册,CBETA电子佛典集成2016年版。首先以正邪质疑难陀滥用神通,但是由于如幻三昧是佛教果位的禅定神通,所以这一神通的获得本身就代表着难陀思想境界并不会如世俗所看到的那样低劣,而且作为叙事者的赞宁给出了合理的解释,难陀的目的是为了在崇尚神仙之术的蜀地应机教化、弘扬佛教,也就意味着难陀是根据教化对象的喜好,特意通过这种神异传播佛教的,所以作者赞宁对难陀进行了肯定,“褒扬难陀以如幻三昧化庸蜀之举”[2]。
《宋高僧传》作者的质疑与解释,显然是难陀的事迹已经超过了佛教理论的界限而不得不做的诠释,这种诠释是否符合事实,与本文主题并无关涉,然而,这种诠释背后所透露出来的神异叙事必须符合佛教理论的原则却显而易见,赞宁之所以在难陀神异事迹之后要加这样一段评述,原因不正是因为难陀的事迹看似已经不符合佛教理论的一种“挽救”么?挽救的方法正是基于佛教“方便”这一理论架构。
方便与究竟相对,如果说究竟是佛教对其所理解的真实世界的揭示,那么方便就是让一般人能逐步的、有阶段性的接受佛教所揭示的真实,所以方便一方面意味着趋向于究竟,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并非是究竟。所以,方便同时具备正确性和错误性两种性质,因为其只是一定时期、区域内的阶段性正确,与最终正确的究竟相比是错误的,但与一般世俗认知相比具有相对的正确性。赞宁通过“系曰”对难陀的评述过程,一方面肯定了神异在现象上的错误,不符合佛教理论的禁忌;另一方面又在更高的层面上肯定了神异的目标的正确性与正当性,甚至肯定其本身就是佛的境界,称其为“诸佛之大定”实际上就已经在究竟层面上肯定神异了。
可见,在普通民众当中,神异事迹一直是宗教传播信仰的重要元素,宗教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各种神异事迹的传说,然而,当神异事迹被记录下来的时候,神异事迹就从一个未被证明或者说难以证明是否是事实的事件,变成了记录者的叙事。神异叙事不仅代表记录者的意图、思想背景等,而且隐含有那个时代的普遍社会认知,因为记录者既不可能从毫无思想准备的民众中塑造出一个神异叙事,也不可能将记录下来的神异叙事转述给毫无思想准备的社会民众,正如美国学者康儒博所揭示的那样。然而,如果仅仅在社会学、历史学层面考察神异叙事,那就会忽略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即神异叙事本身是传递佛教思想理论的中介,不论叙事者是训练有素的佛学家,还是一个普通转述者,都不会在转述神异事迹的时候去违背佛教核心理论,以及那些重要的禁忌,这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宋高僧传·感通篇》的考察可以发现,僧传中的神异叙事,一方面表现出对日常生活经验的背离,不论是万迴童年时候的那些怪异言行,还是之后那些让人无法理解的预言,这一类叙事在“感通篇”中极为常见,因为“神异”本身就是以不同于日常生活经验为其主要特征的,究其原因,神异叙事必须凸显佛教与日常经验的不同,即“真谛”,表现为对世俗认知的否定,首先就是对二元对立的差别认知模式的否定。另一方面也必须注意到,神异叙事从来不是彻头彻尾地否定世俗认知,相反的,恰恰需要世俗认知的肯定,当然最好是获得代表世俗普遍性的皇权的认可,可见,虽然真谛表现为对俗谛的超越,但必须不违背俗谛,正如中观宗创始者龙树以语言为俗谛那样,肯定真谛必须通过语言为代表的俗谛才能得到展现,僧肇的名句“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12)参见僧肇《肇论》,大正藏第45册,CBETA电子佛典集成2016年版,第153页。。
神异叙事两个方面的特征,在赞宁所作的序中精准地概括为“逆于常理”与“化于世间”,但在僧传中,总有那么一些神异事迹看似不符合佛教理论,是否可以认为,只要是有助于信仰,即使不符合佛教理论,仍旧可以在神异叙事中获得认可?《宋高僧传》恰恰通过叙事之后的评述,对看似不符合佛教理论的难陀神异进行了补救,补救的方式就是佛教理论中“究竟”与“方便”的理论架构。意味着看上去不那么正确的神异只要符合正确的目的,还是可以获得神异叙事的认可的。
综上所述,佛教的神异叙事是以思想理论为内核的,很难发现只为了单纯信仰而被记载下来的神异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