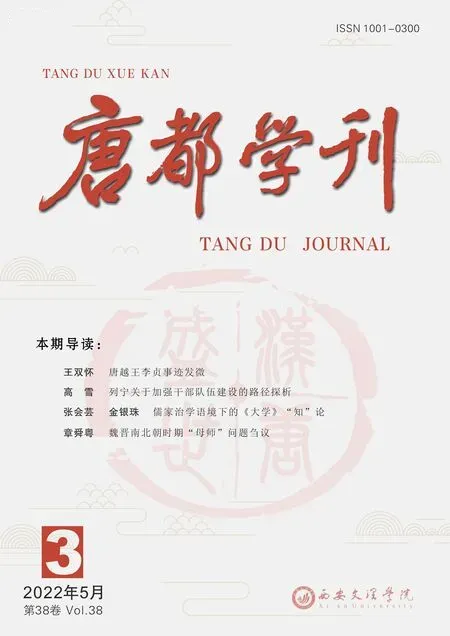魏晋南北朝时期“母师”问题刍议
章舜粤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着妇女通晓经史之学,并以母亲的身份积极参与到家族内文化教育的现象。这类妇女往往被称为“母师”,并得到了时人的赞扬。母教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母师”却有其特殊性。本文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母师”的存在与消亡主要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对女性性别角色的要求。因此,本文将试图从社会性别的建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再生产等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母师”性别角色的独特性
在传统的劳动性别分工中,妇女的工作与家庭关系更为紧密,教育子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正如清代蓝鼎元所总结的,“人子少时,与母最亲。举动善恶,父或不能知,母则无不知之,故母教尤切。”[1]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母亲历来在教育子女上扮演重要角色。早在《诗经·周南·葛覃》中,便有“言告师氏”一语,《毛传》认为“师氏”就是指女师。顾震福考诸古籍,认为古人因为“尊师重道,同尊敬父母的一般,于是称男师曰父师,称女师为母师”[2]。广义上的母师指女性教师,而狭义上的母师则指身兼母亲和教师两种身份者。在北朝墓志中,为子女传授学问的母亲便常被称为“母师”或“女师”,并得到高度评价。
如前所述,在家庭中承担一定教育工作的母亲即为普遍意义上的“母师”。相比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母师”,其他时期的“母师”尽管各有特点,但“在历史中,有一个很强的趋势,专以美德而不是才华来定义好母亲”[3]169。例如“孟母三迁”“断机教子”“截发延宾”等知名的母教故事里,母亲主要是对子女进行道德训诫。孟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认可的母亲典范,她教育孟子的事迹以“孟母三迁”“买肉啖子”“断机教子”等最广为人知。在这些故事里,孟母并没有直接教导孟子学术文化,而是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孟子的道德品质,以及激励、督促他用功读书。“以道德教化促学业事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为常见的母教内容之一[4]。又如宋代大儒程颐回忆其母侯氏对他兄弟二人的教育时,主要提及母亲的道德训诫:“居常教告家人曰:‘见人善,则当如已善,必共成之;视他物,当如己物,必加爱之’”。而在学习学术文化方面,并不是直接传授,而是加以鞭策、激励:“勉之读书,因书线贴上,曰:‘我惜勤读书儿。’又并书二行,曰:‘殿前及第程延寿。’”[5]。因而,就一般意义上的“母师”而言,母亲本人并不必然掌握学术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对子女在道德、为人处世、敦亲睦族等方面加以教导,完善子女的人格。
当然,有相当的“母师”属于知识女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母师”便是如此。但不同时代的知识女性在知识结构上有着极大的差异。章学诚注意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在经史之学上有杰出表现;而从唐宋开始,“妇才之可见者,不过春闺秋怨,花草荣凋,短什小篇,传其高秀”;到了明清,更是“舍其本业而妄托于诗”[6]182-185。高彦颐亦认为到明末清初时代,女性教育由传统的三从四德转向了“德、才、美”,其中的“才”主要也是指诗词歌赋[3]143。总而言之,在大多数时期,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之后,有学问的妇女更多地体现为精通诗词歌赋的“才女”。梁启超在对传统中国的知识女性做整体性回顾时便说:“古之号称才女者,则披风抹月,沾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成诗词集数卷,斯为至矣。”[7]31这类知识女性往往也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女师”的特点。例如明清时期“闺塾师”在性别角色方面与“母师”具有相似之处,她们都是有深厚文化修养的妇女,并扮演了教育者的角色。但“闺塾师”并不传授经史之学,而主要是教授“诗歌艺术”或者“基础的识字和绘画”,而她的学生也主要是“高官的女儿或妾”,而不是自己家族中的后辈[3]135。 显然,她们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母师”有着重大的区别。
因此,虽然母亲在每一个时代都承担起教育子女的功能,即“母师”是中国传统性别秩序中的一部分,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母师”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其特殊之处主要在于以下两点:首先,妇女所掌握的知识除了《女诫》《女训》等“女学”和文学诗词等传统上对妇女较为开放的领域,还包括了长期为男人所垄断的经史之学以及当时较为风行的玄学、佛学和道家学说。其次,妇女以母亲的身份直接将其经史之学传授于子女,而不是仅仅扮演劝勉子女努力向学或在道德上树立榜样的角色。
这一特殊性还体现在不同时代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母师”的评价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通晓经史之学的妇女归属于当时性别秩序的一部分,是被认可和赞扬的。例如前赵皇帝刘聪的两个妃子刘娥和刘英便是典型例证。刘娥是太保刘殷之女,“幼而聪慧”,在白天学习女子传统女工教育的基础下,夜里还勤奋学习,“昼营女工,夜诵书籍”。不仅不听傅母劝止,而且更加用工,“敦习弥厉”。刘娥的妹妹刘英,“亦聪敏涉学”,甚至比刘娥更有成就,“文辞机辩,晓达政事,过于娥” 。而对于刘娥、刘英学习儒家经典的举动,她们的兄弟不仅不加以限制,而且与其切磋经义。刘娥“每与诸兄论经义,理趣超远”,对于她的出色表现,兄弟们非但没有打压,反而是佩服赞叹不已,“诸兄深以叹伏”[8]2519。
北魏、北周之际的董荣晖,虽然学界对其出身于少数民族贵族纥豆陵部还是汉族官僚世家尚有争议,但属于贵族妇女是毫无疑义的(1)关于董荣晖的身份,参见束莉:《中古女性生活图景与才德观之重构——以〈王士良妻董荣晖墓志〉考论为中心》,载于《古籍研究》2014年第1期。。其墓志称她“箴规图史,分在难言,流略子集,皆所涉练”,对经史子集均有所涉猎,而且在教育子女方面,“咸加典训,俱得精称”。因此在她过世后盖棺论定时,得到了“母仪之师表,女宗之宪章”的高度评价[9]208。与之相似,北魏轻车将军封君的夫人长孙氏亦在学问、文辞颇受称道,她的墓志称她“志学出伦,擒辞入赏,昔赖班曹,今亦斯仗”[9]108。赵兰姿是史学家李德林之母、李百药的祖母,也是精通儒释的知识女性,“圣哲遗旨,又多启发”,被当时的大儒徐遵明评价为“夫人是内德之师”,时人也称赞她“道越女师,才侔博士”,“深仁至德,旷古未闻”[9]356。北齐官员刘宾,为汉初楚元王刘交的后裔,其祖、父在南朝也俱为达官贵人。他的妻子王氏和赵兰姿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通晓儒释两家,“识达苦空,洞明真假,修心八解,专精三业”。刘宾过世后,她亦成为“母师”,“抚育孤遗,教以义方,咸得成立”,使得亲朋邻里纷纷对她表示钦佩,“亲宾拭目,表里倾心,妇德母仪,佥望斯在”[9]553。
此外,更有妇女通过学习经史之学,具备了参与政治的条件。比如北魏渔阳太守阳尼的妻子高氏,“学识有文才”,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下敕令命其“入侍后宫”,辅佐后妃,传授知识,乃至代幽皇后起草表启, “悉其辞也”[10]1982。陇西人李淑兰出生于北朝末期的贵族世家,其夫身为宰相。而李淑兰在政治上也大有所为,对国家的内政外交均有所影响,“定策外弼”,有“建茅土”“启山河”之功,被称为“望古畴今,异代共荣”,在道德学识上则“规矩合于女师,识达称为博士”,被评价为“一代贤姬,千年贞节”[9]498。
然而,这批时人心目中的“模范母亲”“模范妇女”在后世却得到了颇为负面的评价。章学诚虽然认可她们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经典,发扬了经史之学,但却指责她们有违礼教,造成社会风气恶劣和天下大乱:“晋人崇尚玄风,任情作达;丈夫则糟粕六艺,妇女亦雅尚清言。步障解围之谈,新妇参军之戏,虽大节未失,而名教荡然。论者以十六国分裂,生灵涂炭,转咎清谈之灭礼教,诚探本之论也。”[6]182余嘉锡亦认为她们在学问上的出色表现恰恰体现了妇德的衰败,继而导致社会动荡:“考之传记,晋之妇教,最为衰敝。夫君子之道,造端夫妇。故《关雎》以为风始,未有家不齐而国能治者。妇职不修,风俗陵夷,晋之为外族所侵扰,其端未必不由于此也。故具列当时有识之言,以为世戒。”[11]779-780在后世人眼中,妇女从事学术文化研究和传授工作不再被赞许和鼓励。换言之,一个优秀的母亲、“母师”,不再有魏晋南北朝时期“母师”的那些特质。这正说明社会性别体制是历史性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母师”何以展现出这样的特殊性?这一历史的、特殊的社会性别体制是如何构建的?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要将其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
二、魏晋南北朝贵族社会的特征与“母师”的产生
近年来学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通经并以此教育子女这一现象已有所注意(2)张白茹梳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成为家族文化教育的接受者和传承者的现象,并指出它发展了教育事业,也提高了妇女地位。张承宗、陈群在其著作中专辟一节叙述妇女与学术文化,亦梳理了这一时期的妇女与经史之学和玄学清谈的情况。柳称在其博士论文《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教育研究》中,专有一章讨论这一时期家庭教育中的女性,梳理了女性接受教育的状况,并分析了其原因和意义。参见张白茹:《魏晋南北朝妇女与家族教育的历史考察》,载于《江淮论坛》2003年第1期;张承宗、陈群:《中国妇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柳称:《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教育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这些研究凸显了妇女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重要“在场”,并指出它“在推动当时家族教育的发展、妇女社会地位的改善以及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2]。但当论及这一现象的原因时,以往研究往往指称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地位较高所导致的。然而,与其说这是对问题的回答,不如说是对问题的一种重复。为什么这个时期妇女的地位较高呢?进一步的解释往往指出这一时期社会的分裂与动荡,“儒学一统局面的不复存在及胡风的南下”,从而使得妇女所受束缚较小[12]。这事实上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多元文化的碰撞固然可能使社会文化走向开放、融合,但也有可能出于“夷夏之防”,为与他者做出区隔而强调自己的文化,从而导致愈加保守。
事实上,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母师”是一种特殊的性别角色。它不是孤立产生的,而是与当时的社会结构有着密切关系。在章学诚、余嘉锡的论述中,社会的动荡是因为时人不守礼教,妇女不守妇德。妇女对学问的追求和因此展现出的风采反而成了社会关系变化的原因。笔者认为,事实恐怕恰恰相反,是社会关系的变动才导致了“名教荡然”“妇职不修”等现象的产生。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性质,学界尚有争议。以内藤湖南为代表学者的“唐宋变革说”认为,中国政治在清朝以前可以分为贵族政治和君主独裁政治两种形式,而唐宋之间则是二者的分界线。贵族政治即贵族阶级的联合政治,六朝贵族的基础是已成为地方望族的官僚世家[13]。宫崎市定与内藤湖南一样,将三国至唐末归为中古(中世),认为贵族制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从后汉时代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不仅世袭财产,而且世袭官职的贵族,经过三国六朝,一直到唐代都有很大的势力。文化也被这一贵族阶级垄断”[14]。陈寅恪则敏锐地提出了东汉末年、曹魏、西晋三个时代统治者的社会阶级问题。他认为“魏、晋的兴亡递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寒族的胜败问题。”[15]2“魏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晋则外廷士大夫阶级之代表。故魏晋之兴亡递嬗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16]甚至在“文革”期间发起的“评法批儒”运动,亦认为曹操、诸葛亮等为法家代表,代表庶族地主与豪强地主斗争,而司马懿则复辟了“儒家路线”[17],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守旧和革新的斗争”[18]。
以上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是一个与后世封建专制社会有所不同的社会。这一时期的贵族无论称之为地方望族、门阀世家、儒家豪族、士大夫阶级还是豪强地主,总之他们因家庭出身而与后世通过科举考试得以进身的官僚有所不同。而这些贵族,或者说世家门阀,其一大标志即为他们与儒家学说的密切关系,乃至形成不同的家学。钱穆曾指出:“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自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 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19]
门阀与家学的合流,“起始于汉末,成形于魏晋,至南北六朝则趋于鼎盛,并渐次衰弱。”[20]131例如被陈寅恪称为“汉末士大夫阶级之代表人”[16]的袁绍,出身汝南袁氏,“四世居三公位”[21]188,世传《孟氏易》[22]1517。再如弘农杨氏,自杨宝以来,世传《欧阳尚书》[22]1759。对于世家大族而言,家学实际上是其不可忽视的文化资本。通过家学,实现对某些学术文化的垄断,是保持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重要手段。同时,家族内的家学传承,也是保证其社会地位代际传递的重要工具。
而“母师”正可以起到巩固、延续家学的重要作用。首先,家学为“专门绝学,家有渊源,书不尽言,非其人即无所受尔”[6]179。换言之,它很难从外人之处习得,而主要依靠家庭成员的内部传承。而与此同时,因贵族社会另一种体现是基本不与庶族和低等级的士族通婚,即按照门当户对的原则缔结婚姻(3)对此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参见易图强:《两晋南朝士族门第婚姻的量化分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1996年第3期。。故而,女儿在家接受教育,学习经史之学便显得顺理成章。因为当女儿出嫁后,很有可能要承担起教育子女家学的任务,这就要求她要具有基本的文化学术素养。
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母师”往往出身于贵族家庭,她们有良好的接受经史之学教育的条件。如前文所述的刘娥、刘英、董荣晖、长孙氏、赵兰姿、刘宾妻王氏、阳尼妻高氏和李淑兰等等,莫不是世家大族出身。
北魏卢道虔妻元氏,聪颖过人,极有悟性,其学问甚至到了可以升堂讲座的程度,“甚聪悟,常升高座讲《老子》。”卢道虔出身卢崔郑王四大家族中的卢氏,他的从弟卢元明号称“涉历群书,兼有文义”,本来就是学问世家,而卢元明尚且“隔纱帷以听焉”,向元氏学习。这除了说明元氏的学问精深,亦说明其《老子》之学很可能是元家家学,而不为卢家所掌握[23]。
杨无丑是北魏大臣杨顺之女。杨家先祖自汉昭帝时就出过宰相,杨震更是东汉名臣,杨家可谓是汉魏南北朝时期最为显赫的世家大族之一。杨无丑死时年仅21岁,尚未出嫁,但已显露出一定的学术水平,被评价为“体兼四德,智洞三明。该般若之玄旨,遵斑氏之秘诫”[9]84。“三明”“般若”均为佛教术语,将传统女学的“四德”与佛学并举,一则说明当时佛教与儒学在妇女身上可能并行不悖,均为妇女可以学习的知识;二则也说明了她有较好的学问,甚至得以与蔡文姬相提并论,“渊意与文姬共远”[9]84。
这种儒学与佛、道等多家典籍共同为贵族妇女所学习、掌握和爱好的情况并不是孤例。元瑛,为北魏孝文帝的小女儿,她勤学深思,经常翻阅书籍,“加以披图问史,好学罔倦”,并同时学习儒释道三家思想:“该柱下之妙说,核七篇之幽旨。驰法轮于金陌,开灵光于宝树。”“法轮”“宝树”具为佛教术语,“柱下之妙说”即为老子的学说,“七篇之幽旨”中的“七篇”既可能是指《女诫》七篇,亦有可能指《孟子》七篇。她精通经史之学,思想开阔而不拘泥于一家,更体现出她的好学不怠,兴趣广泛,并且妙笔生花,辞藻华丽,在当时就为人所称道,“绡縠风靡,斧藻川流。所著辞诔,有闻于世。”[9]114北魏封氏,“勃海人,散骑常侍恺女也。有才识,聪辩强记,多所究知,于时妇人莫能及。”[10]1978
在魏晋南北朝时人眼中,这批贵族妇女的知识最初往往得于出阁前的家庭教育。例如北魏、北齐之间的宋灵媛除了符合传统的女德要求之外,在出嫁前就开始学习文史知识,“兼以窥案图史”[9]208。生于北魏的郑仲华的知识学问亦被认为是从娘家带来的,“夫人门有素业,世传博雅,名教之地,不肃而成。”时人不仅认为她的知识来源于其家学渊源,甚至女德方面的修养也是在家中得以潜移默化,“张氏前箴,班家往诫,周旋俯仰,暗与之合。”[9]365这可能是时人对贵族门阀世家的夸赞与吹捧,但同时也透露出贵族家庭环境与妇女受教育的密切关系。
这种贵族门阀世家内重视妇女教育的风气,有时也会影响底层妇女而使之受益。东汉末年的大儒郑玄家中的奴婢便是一例。《世说新语·文学》记载,郑玄有一次使唤一奴婢,而她办事不称郑玄的心意,于是郑玄便想鞭挞她。这位奴婢做了申辩,反而惹怒了郑玄,让人将她拖入泥地中。须臾,又有一奴婢路过,便问那位婢女:“胡为乎泥中?”那位婢女答道:“薄言往愬,逢彼之怒。”[11]228“胡为乎泥中?”典出《诗经·邶风·式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典出《诗经·邶风·柏舟》。主仆一问一答之间,竟均引用《诗经》,可见郑玄家的婢女亦有学问。此事的真实性历来颇受怀疑,但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又如同为三国时代的蜀汉的刘琰,也在家中教导侍女读书,“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诵读《鲁灵光殿赋》”,亦可佐证这一现象[21]1001。
如班昭在《女诫》中所说的,中国古代社会对妇女的要求一般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母师”们彰显出与这一传统妇女角色极不相同的一面,在学术文化的学习和传承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赞许。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社会对家学传承的要求即贵族社会的再生产是离不开的,社会性别的建构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在此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三、魏晋南北朝“母师”与贵族社会的再生产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社会的社会结构及其社会关系给了妇女学习学术文化的条件,即为产生“母师”的前提条件奠定了基础,那么,“母师”这一社会角色被纳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性别秩序更是这种社会结构的要求。“母师”不单单是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产物,更是其再生产的重要工具。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门阀多与家学互相依存,甚至传承数百年,直至隋唐才开始衰败。这与当时的世家大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密不可分。汉代实行察举制,“以仁孝礼让著称于乡里,是入仕的途径。取士与仁孝礼让或者说与德的结合,遂使名教成为豪族屡世必须奉行的圭臬与赖以自豪的门第的标志。豪族往往就是儒门。”[15]8这便是家学与世家大族合流的重要缘由。魏晋南北朝时代,贵族“在现实生活中以官人的形态存在”[24]155,取得官职很大程度上关系着门阀世家的维系,二者是一种互相依存、互相支撑的关系。因此,“家学的传承成为争取和维护家庭(家族)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25],“维系家族的时代特权和优越的文化地位”[20]131。而“母师”正是借由家学的传承,参与到世家门阀的再生产的过程当中。甚至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母师”这一颇显独特的社会性别角色的构建,是出于维系当时的社会关系及其再生产而存在的。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一旦遇到父亲早逝等家庭变故,为了维系门第,避免家学失传,母亲传授家学就显得尤为必要。因而,贵族制社会结构对家学传承的要求,就成了对贵族妇女学习和传授学术文化的要求。
三国时期魏国的钟会出身名门望族。父亲魏太傅钟繇过世时,钟会年仅5岁,因而他童年时期的教育是由母亲张夫人所负责的。据钟会回忆,他的母亲“性矜严,明于教训”“雅好书籍,涉历众书”[21]785-786。钟会从4岁起便跟随她读书学习,“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21]785从钟会受教育的履历来看,张夫人博学多闻,精通经史之学,比起当时的男性知识分子毫不逊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特好《易》《老子》”[21]786,而这正是钟氏家族声名远扬的家学。而钟会虽然不是钟繇的嫡子,但仍能成为曹魏政权的重要政治人物,和其兄钟毓一起延续钟家门第,不能不说与张夫人的教诲有密切关系。
前秦的韦逞,其母宋氏也是出生于以学术文化著称的书香门第,“家世以儒学称”[8]2521。因为宋氏家中无男,她父亲便将家学《周官音义》传授给她。他儿子韦逞年幼时,宋氏“昼则樵采,夜则教逞”,把儿子培养成才。后来还因《周官音义》的家传绝学,被官方在家中“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而受业”,号为“宣文君”,被视为一代儒学大师[8]2522。南齐时期的文凝,早年失怙,其母郑氏“亲教经礼,训以义方,州里称羡”[26]。不惟南朝,北朝也存在这样的现象。裴让之年十六丧父,家中“诸子多幼弱”,因此其母辛氏“广延师友,或亲自教授”[27]465。皇甫和“母夏侯氏,才明有礼则,亲授以经书”[27]468。张宴之“幼孤有至性,为母郑氏教诲,动依礼典”[27]468。陆仰之母为北魏上庸公主,亦承担起教育诸子的工作,“主教训诸子,皆秉义方,……然动依礼度,亦母氏之训焉”[27]469。西魏、隋朝之间的刘琬华是隋骠骑将军李椿之妻。李椿同样出身北朝贵族,家族历代显宦,到他父亲李弼已经位列北周的三公。刘琬华精通《诗经》、辞赋,“览葛覃之咏,躬勤浣濯;吟绿衣之篇,劬劳紃组”,在丈夫李椿早早故去后一手担负起教育子女的重任,“遂断机贻训,徙宅从仁,藐是诸孤,义方圣善”[9]518。这些世家都是借由“母师”,保证了家学不因父亲的突然去世等而中断,对门第的延续有着重要的意义。
此外,身为达官贵人的父亲工作忙碌,或出于别的种种原因,无暇花大量时间教子。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也可能承担起这样的工作。西晋著名学者夏侯湛兄弟七人、姐妹五人,便是由母亲羊姬所启蒙的。羊姬“宣慈恺悌,明粹笃诚,以抚训群子”,在夏侯湛“龀齿”也就是刚刚换牙的时候,就“受厥教于书学”。羊姬所传授的学问范围也颇为广博,“敦《诗》《书》礼乐,孳孳弗倦。”在羊姬的教育下,夏侯湛自感兄弟姐妹们“束脩慎行,用不辱于冠带,实母氏是凭”,全是母亲的功劳[8]1497。又如东晋豪门谢安家,就是由“谢公夫人教儿”。谢夫人曾向谢安抱怨,“那得初不见君教儿?”谢安回答“我常自教儿”,意为母亲言传,父亲身教[11]46。谢氏是著名的诗书世家、门阀士族,而谢安公务繁忙,由其夫人教儿,也是“母师”现象的一种体现。
在魏晋南北朝这一贵族社会中,士族之间的联姻也是维系其统治地位、进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重要手段。女儿掌握自家家学后出嫁到别的门阀世家,而别的门阀世家的女儿嫁入自家,这也能带来学术文化的交流,对其家族地位的维系也是有利的。前文所提卢道虔之妻元氏带来《老子》之学,便是一例。又如东晋、刘宋时期的何承天,“五岁失父,母徐氏,广之妹也,聪明博学,故承天幼渐训义,儒史百家,莫不该览。”[28]1701何承天不仅是经学、史学大家,而且在天文历法和音律上也有所成就。这显然与其母带来的徐氏家学有密切关系。徐氏为徐邈、徐广的妹妹,徐氏兄弟 “家世好学,至广尤精,百家数术,无不研览”[28]1547,亦是当时知名学术世家。何承天与徐家的学术传承关系是十分明显的。
从这些例证中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在学术文化上的学习和传授是得到认可的,是当时贵族妇女社会性别的一部分,但它产生的前提和目的,均是以男性为中心的贵族社会结构所决定的。换言之,是因为它对世家大族的延续有利,对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也因此当贵族社会崩溃之后,社会流动不再主要依靠家世门第,选官制度走向统一考试、统一学术观点的科举考试,家族自身独特的学术传统便不再成为优势,甚至有可能因与官方意识形态有所不同而成为祸端。例如唐代虽然也有寡母教孤的现象,但比起经学,更强调书法、诗赋,这与隋唐以来取士方式的改变是同步的[29]。随着科举的兴起,官学和私塾等教育形式成为主流,对母亲承担教师职能的要求也随之大大减弱。而这同时也使得女性学习经典的需求下降,其学习重点也就从带有浓厚家族学术传统的经典转向了女德为主的道德训诫,有学识的妇女也从“母师”慢慢变成了“才女”。
因而,我们可以见到“母师”与门阀世家、家学、贵族制社会的产生与消亡,几乎是同步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将“母师”理解为贵族制社会赋予妇女的一种角色,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关系的反映。妇女在这一时期被允许学习经典,承担传经职责,并得到社会的赞许,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妇女的地位高或社会文化开放等理由,更主要的还在于它契合了贵族社会维系自身和再生产的需要。当这一社会结构瓦解之际,“母师”原本拥有的学习和传授学术文化这一权力同时被抽离,不但不再是妇女的被接受乃至被赞扬的“属性”之一,反而成了“女德”败坏的表现,甚至要为社会的动荡负起责任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贵族妇女可能在客观上地位较高,但它并没有打破男性统治,反而维系和再生产了当时男性统治的社会体制,亦即贵族社会体制。正如以研究六朝社会著称的谷川道雄所提出的,“近代官僚的特质是官僚个人具有专门知识和专门权限,而这些恰恰使近代官僚不能不成为整个机器的一个零件、一只齿轮,从而发挥‘无主观’的机能。”[24]157魏晋南北朝的“母师”同样是这部机器的零件、齿轮,她们个人当然有其主体性和能动性,但作为一个整体则服务于贵族社会这部结构严密的机器。一旦机器解体,这些零件、齿轮在特定位置上的意义就被取消了。换言之,社会性别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在“母师”问题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除了前文所提到的时代变迁,地区差异也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社会结构对社会性别的影响。例如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因而也催生了以诗词歌赋等文学艺术为主的才女文化[3]。而山东地区的传统经济成分更重,“与明清江南文化世家对女子的教育相比,山东文化世家显然更重视妇德教育的内容,而对诗词文赋不太讲求。”[4]
而到了晚清之际,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兴女学”运动,社会重新提出对妇女学习学术文化知识(当然,是以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为主)的要求,并要求她们以此教育子女,妇女被要求成为“女国民”“国民之母”“良妻贤母”等等。而过去一度被颂扬的精通诗词歌赋的“才女”也被贬低,并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要为中国社会的落后负起责任。以往被赞扬的“无才便是德”的传统女性就更成为批评的对象,梁启超就认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7]30社会性别上的新变化,同样与晚清开始的社会结构大变革有着密切关系。兴女学是在现代文明的标准下兴起的运动,其“最终目标是强国”;在女性得到一定主体性的同时,“把女性裹挟进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30]。可见,社会性别的建构从来离不开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变迁。
四、余论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独特的“母师”之产生和消亡与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君主专制的权力取得对门阀世家等贵族的优势地位之后,“母师”便随之而去,并不再被性别秩序所高度认可。福柯指出,“权力关系根植于整个社会之网。”[31]“母师”这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角色揭示了中包含的权力关系:在这个场域中,国家、贵族社会、门阀世家中的男性家长之间的权力角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母师”的生死。换言之,“母师”的存在与消亡主要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对女性角色的要求。因而,对母师问题的考察,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妇女的“主体性”(无论是作为整体的“妇女”还是个体的妇女)层面,而且必须将目光投向这种主体性得以产生的外部环境。
因此,如果要对“母师”的产生和消亡进一步进行探究,则意味着需要对贵族制的产生与消亡,或者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转变过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从中我们可以找到经济关系与家庭分工、社会性别的构建之间的隐秘的联系,继而考察其后传统社会和近现代中国社会中社会性别秩序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