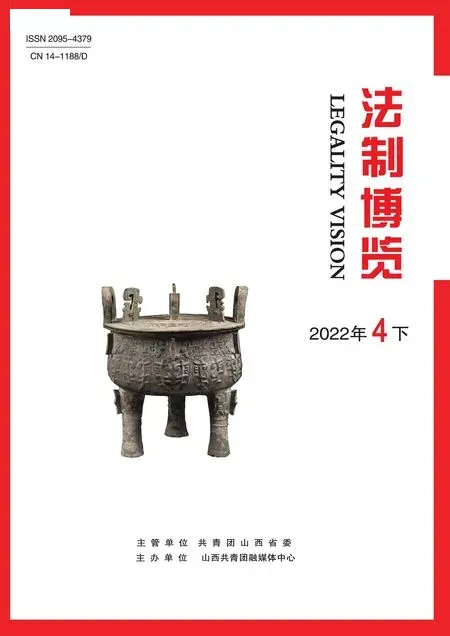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功能定位及控制路径分析
杨馨淼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天津 301830
法院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时,综合考察并分析与案件有关的连接因素,找出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并加以适用,这就是所谓的最密切联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具有灵活性,适用结果相对公正,自产生以来,便引起了国际私法领域的变革,被各国立法和实践所采纳。
我国201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规定了最密切联系原则,该法第二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依照本法确定。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法和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没有规定的,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依据该条规定,只有当“本法”及“其他法律”没有规定适用的规则时,才能适用与该民事关系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如果没有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适用特征履行和最密切联系原则。”可见,《法律适用法》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从合同领域的法律选择方法上升为国际私法补充规则,只起到替补作用。从本质上而言,我国与上述各国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理解不同,《法律适用法》第二条的规定缺乏原则所要求的全面适用性和立法根本性,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最密切联系原则”。
一、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立法实践和功能定位
(一)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立法实践
最密切联系原则源于美国纽约州1954年的“奥汀诉奥汀”案和1963年的“巴布科克诉杰克逊”案。这两个案例都是美国司法发展史上的经典案件,并对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的制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奥汀诉奥汀”案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引入了合同领域,而“巴布科克诉杰克逊”案则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引入了侵权领域。作为判例法的代表国家,美国通过以上两个案件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引入冲突法领域。在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过程中,法官除了考察地理联系,也始终利用“政府利益分析说”来寻找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197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里斯主持完成了《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与《第一次冲突法重述》不同,他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核心,贯穿始终。《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第六条确定了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1.法院在服从宪法的范围内,应遵循本州成文立法规定来选择法律。2.在没有相关立法规定时,法院在选择应适用的法律时应考虑因素包括:(1)州际和国际体制的需要;(2)法院州或国的相关政策;(3)其他利益相关州的相关政策;(4)当事人正当期望的保护;(5)特定领域的法律所依据的政策;(6)判决结果的确定性、可预见性和一致性;(7)将适用的法律易于查明和适用。”[1]可见,《第二次冲突法重述》融合了各种法律适用理论,在“最密切联系原则”法律选择上,并不限于地理联系,而是考察法律与案件的联系,并考虑了维护国际民商事交往秩序的需要((1)、(6))、国家和州的政策利益((2)、(5)、(3)),以及结果对当事人的公正性((4))。
同时,《第二次冲突法重述》分则很多条款都体现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如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次冲突法重述》并没有否定规则,而是对规则进行了改进,并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增加了法律适用的灵活性,以确保实现个案公正。例如,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在适用第六条规定某合同问题适用的法律时,需要考虑的连结因素包括:1.合同订立地;2.合同谈判地;3.合同履行地;4.合同标的物所在地;5.当事人的住所、居所、国籍、公司成立地和营业地。”[2]该条划定了合同法律选择范围,保障了法律与案件的联系,增加了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在具体案件中,各因素的重要程度不同,需要结合第六条所列的因素进行考察,确定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功能定位
1.原则高于规则,需要在规则之后适用
任何法律都应体现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统一,稳定性可以为社会秩序提供安全保障,灵活性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关于如何处理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即规则与原则的关系,学界的讨论由来已久。规则具有具体明确的特点,可以提高法律适用的效率,但易产生僵硬性,有时难以实现个案的公平,所以需要用原则加以调整。[3]国际私法也需要寻找两者的平衡,而最密切联系原则正发挥了此作用。
自国际法产生以来,冲突规范的制定都在寻求找到与案件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例如在合同法律适用上,无论是巴托鲁斯的“场所支配行为”,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还是“既得权说”,都是寻求与合同最密切联系的地方,从而适用该地的法律。只不过,这种单纯用“地理联系”来确定法律适用的方法,既不考虑法律的内容,也不考虑个案具体情况,会导致僵硬性和不公平。最密切联系原则以其灵活性的特点,避免了规则的僵硬性。
在具体适用时,制定合理的规则都会体现法律与争议的最密切联系,则可以直接适用规则,不需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加以考察;如果规则无法体现最密切联系时,则可以摒弃规则,而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寻找应该适用的法律,但需要证明所适用的法律与争议案件有更强联系,以不至于损害规则的确定性,又增加了规则的弹性。
2.规则应体现原则且具体化,以实现个案公平
与传统的方法相比,最密切联系原则通过自由裁量权设定使法律适用具有灵活性,有利于实现个案公正。然而,在具体的案件中,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选择主要依赖于法官的判断和分析,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容易由于法官法律专业素质和时间成本的考虑,导致法院地法的滥用,而有悖立法初衷。所以,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立法中,要明确法官确定最密切联系法律的考量标准,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加以必要的限制。但同时,考量标准应该具有弹性,正如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第六条之规定,要考察所涉及的国家的政策、当事人的正当期待等,不仅要考察连接点的数量,更要考察其质量。[4]
同时,作为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应该贯穿于国际私法法律适用的具体规则。规则具有确定性预见性,有利于提高司法工作的效率。如上文所述,各国在具体条款中列举了考量因素,而这些因素的选择应该具有弹性,避免僵硬,增强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可操作性,为审判工作提供了明确的依据。
3.强调司法适用,而不仅仅是立法层面
最密切联系原则不仅需要在立法中体现,更需要在司法中发挥作用。最密切联系原则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法官在确定准据法过程中要充分、合理地发挥能动性,不仅要找出与案件有关的连接因素,而且要对各连接因素进行重要性的分析和判断,进而确定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最密切联系原则寻找的是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应该考察法律的内容,而不仅仅是具有“地理联系”的“最密切联系的国家”。当然,地理联系是一个基本的指引工具,可以划定最密切联系的法律选择范围,进而考察各国法律,以确定哪一国法律与争议案件具有最密切联系。
同时,为了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需要对其加以限制,这种限制除了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如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标准和规则明确化、具体化,也可以通过司法的方式达到。如作为典型判例法国家的美国十分注重司法审判,通过严格的法官选拔制度和监督机制来确保法律的正确运用。以州法官的选拔为例,美国要求法官需要具备毕业于美国大学法学院、取得律师资格并具有丰富工作经验(12~15年的法律工作实践经验)、丰富的生活阅历(40岁以上)和较高的道德水平等条件。这些条件是司法审判工作所必需的,良好的法学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使法官能够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而丰富的生活阅历和较高的道德水平能够使结果更加公平。
二、我国最密切联系原则司法适用的问题
最密切联系原则由于其灵活性而被法官所偏爱,成为司法实践中法官常用的法律选择方法之一,但对该原则的理解、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认识都不够清楚,存在法条适用混乱、适用准据法推理不明确和过度依赖法院地法等问题。
(一)法条适用混乱
我国《法律适用法》第二条作为兜底性原则,没有规定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的情形,第四十一条没有明确最密切联系原则和特征性履行原则的关系,也没有具体规定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这便赋予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通过近年的司法案例分析发现,最密切联系原则法条滥用情形普遍,合同纠纷、继承纠纷、股东知情权纠纷等都适用过第二条,而各种类型的合同纠纷,如买卖合同、借贷合同、劳务合同、租赁合同等都适用过第四十一条。并且,存在大量的法条适用错误情形,比如,本该适用第四十一条,却适用了第二条,本该适用不动产买卖合同的特别性规定,却适用了第四十一条。
(二)推理不明确
最密切联系原则被滥用的原因之一是我国没有将该原则确定化、具体化。我国《法律适用法》虽然借鉴了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在合同领域中用“特征性履行原则”对最密切联系原则加以限制,但是,并没有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前文所述,与大陆法系国家一样,英美法系也规定了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的参考因素。由于具体规则的缺失,司法实践中参考因素的使用随意,造成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最密切联系原则较其他连接点更具灵活性,在适用的过程中更需要明确如何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而导致某国法律的适用,即要明确推理过程,而不仅仅是适用结果。
(三)过度依赖法院地法
最密切联系是一个富有弹性的连接点,适用极具灵活性,倘若适用规则规定不具体明确,法官便可以自行决定法条的适用、推理过程和参考因素,加上外国法查找和解释的困难,很容易导致出现法官过度依赖法院地法的现象。而由于在各国涉外民商事司法实践中,法官都存在适用法院地法的动机和倾向。从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发现,法官在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时,将近99%的案件都适用了法院地法,法官在判例中只是简单地罗列适用最密切联系的因素,并没有综合分析案情,没有考虑案件的其他因素。[5]
三、完善我国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控制路径分析
目前,我国《法律适用法》仅仅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补充规则,与美国、瑞士等国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理解不同,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最密切联系原则”。《法律适用法》分别在一般规定、民事主体、物权和债权这几章中使用了“最密切联系”,每条规则都仅仅规定应适用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但是却没有具体规定考量的因素和使用标准。这种模糊、不明确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难以指导司法实践,无法公正地解决国际私法问题。
(一)立法层面
可对《法律适用法》最密切联系原则条款进行适当修改,具体条款可以是:本法所有规则都应当体现最密切联系原则;如果本法规则所指引的法律在个案中不能体现最密切联系,则该规则不适用,而适用那个实际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法没有规定的,直接适用与该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上述建议条文用三句话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分成三个层次,既考虑了法律的稳定性、明确性和可预见性,又运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增加了司法能动性,弥补了立法的不足。第一款是一般性规定,表明每一种法律适用规则的连接点的选择都应当体现最密切联系原则,指引适用与争议案件具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这种规定使国际私法具有了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第二款是例外条款,借鉴了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典》的规定,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增加了灵活性,矫正规则的僵硬性。在司法中,法官若发现个案中规则所指引的法律不能体现最密切联系,那么,便可以弃用规则,而适用具有更强联系的原则。但是法官的裁量权是受限制的,即需要证明运用原则适用的法律与争议案件具有更强联系,以免损害当事人的正当预期。第三款是补充条款,可以补充立法不足。由于各国法律规定的不一致和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复杂性,任何立法者都难以预见所有的问题,故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可以弥补立法的不足。[6]
明确规定法官确定最密切联系法律的标准。可以依据我国国情,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增加如下条款:“对最密切联系地的确定,应当根据下列因素综合确定:1.国家的利益和法院地的相关政策;2.对当事人正当期望的保护;3.适用结果的确定性、可预见性和一致性;4.法律适用的便利性。这样,通过立法明确了法官确定最密切联系法律的标准,不仅为法官选法进行指引,而且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了适当的限制,更加公平合理。同时,细化《法律适用法》法律适用规则,增强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可操作性。只有规则具体可操作,才能为司法工作提供有效的依据和指导,最大限度发挥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作用。
(二)司法层面
1.明确推理步骤和方法,保证个案公平
正如前文所述,最密切联系原则不仅强调立法,更注重司法,只有落实到司法工作中,才能真正发挥其价值。正如学者所说:“如果没有具体的适用方法,那么最密切联系原则也只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抽象概念,无法完成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变。”[7]
最密切联系原则寻找的是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应该考察法律的内容,而不仅仅是具有“地理联系”。当然,地理联系是一个基本的指引工具,可以划定最密切联系的法律选择范围,进而考察各国法律,以确定哪一国法律与争议具有最密切联系。对于确定最密切联系地的具体步骤,本文比较赞同肖永平教授的观点,他提出:“将确定最密切联系地的过程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找出个案中所有连结因素;第二,考察连结因素在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分布数量;第三,对每一连结因素在特定法律关系中的重要性进行分析;第四,若上述三步仍不能确定最密切联系地,法院要特别考量个案中每个连结点对具体争诉问题的意义;第五,综合权衡,最终确定最密切联系地。”[8]其中,第一、二点属于连接点数量的分析,第三、四、五点属于连接点质量的分析。也就是说,审理国际私法案件需要首先分析连接点的数量,然后依据一定的标准评价连接点的质量,对量的考虑较为简单,但对质的评价则要求甚高。连接点数量的分析,即连接点在所涉各国的分布数量,可以先从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三个方面入手,找出案件的连接点,分别对应到其所在的国家。但质量的分析是对案件所涉及的连接点进行质量分析,即通过考察法律的内容,判断各连接点的重要性,衡量各要素背后的政策利益或价值,以确定哪一国法律与争议案件具有最密切联系。
2.培训法官,提升法官素质
最密切联系原则具有灵活性,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同时也对法官的素质提出了要求。如上文所述,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运用需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考量,量的考察相对容易,而质的考察就需要法官具有极高的专业素质。如果法官不正确理解冲突法,抑或是最密切联系原则,可能滥用对连接点的质的评价而排除了本应适用的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实践中法官过度依赖法院地法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由于我国部分法官专业素质不高。国际私法学科在我国大学法学专业开设刚刚40年,开设之初普及率很低,且开课时间一般设置在大三期间,这也导致了国际私法专业人才的缺失,进而导致了我国涉外案件法官的专业素质不高。另一方面,部分法官存在适用法院地法而逃避外国法的倾向。部分法官为了省时省力,不考察案件的外国连接点,仅仅列出本国连接点,或者混淆连接点与管辖权,直接适用法院地法,[9]将中国法作为准据法。
如上文所述,最密切联系原则只有在司法中得到合理运用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和价值,因此提高法官的专业素质和审判能力迫在眉睫。首先,建立严格的法官选拔制度,加强对法官的培训,提升法官对国际私法专业知识的理解,通过优秀案例的指导和分析,促使法官准确理解最密切联系原则,并正确运用。其次,要为法官提供审判便利,简化外国法的查明途径,减少适用外国法的成本,使法官能够平等对待各国法律。最后,建立监督机制,约束法官的行为。法院内部应该建立定期考核制度,对于法官适用法律不正确和失职行为进行处罚。同时,法官要接受外部监督,如新闻媒体、群众,保证自由裁量权的正当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