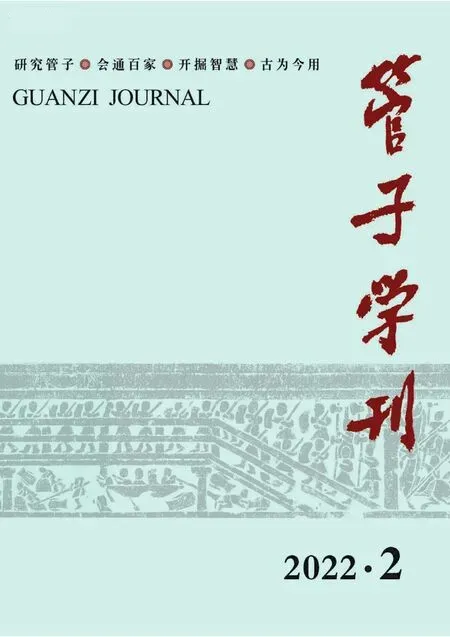《公羊》例学之大成
——何休义例研究
杨 昭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前言
义例之有无,在《春秋》的研究中历来是有争议的。观先秦诸家解读,皆未见“例”,孟子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5页。所重在义。《庄子·天下》篇谓“《春秋》以道名分”(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08页。,亦可谓重在义。及至西汉早期亦沿袭此风,董仲舒谓:“《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3)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6页。诸家解说均以正人为《春秋》之大旨,《春秋》的价值所在,就在于其中蕴含正人之义。但《礼记·经解》的说法却与此相异:“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郑玄注云:“属,犹合也。”孔疏的解释为:“属,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会同之辞,是属辞,比次褒贬之事,是比事也。”(4)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234页。由其解说可知,此处更多是从方法论角度来界定《春秋》。《春秋繁露》中也有此种说法:“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苏舆谓:“此董子示后世治《春秋》之法。”(5)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33页。“义”的解说与“属辞比事”的解说均有学者主张,前者言《春秋》之旨,后者论述通《春秋》大义之法。这里仍然未见“例”的身影,但“属辞比事”的解读已经为“例”的出现打开了大门,诸家所谓例,即是在归纳总结《春秋》辞、事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近人赵友林考证,“东汉时期,《左传》学者与《公羊》学者先后展开了三次论争”,以争取《春秋》的独家解释权,由此引发的是三传书法的不断条例化。《公羊》之条例完成于何休,《左传》条例完成于杜预,《榖梁》条例完成于范宁(6)赵友林:《〈春秋〉三传书法义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12页。。可见义例的兴起,颇晚于《春秋》,甚至晚于三传之分。因此,以例作为讲解《春秋》的唯一方式,并不被所有学者接受。宋代甚至由疑例而至疑传,彻底否定了例的合理性。但义例对于今日治《春秋》者而言,已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宋儒洪兴祖谓:“《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犹天本无度,治历者因周天之数以为度。”(7)皮锡瑞:《经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56页。此言甚是。
学界对《春秋》义例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涉及义例的方方面面。如葛志毅关注重心在《左氏》例:“汉代今文家攻驳《左传》不传《春秋》,古文家为强化《左传》的传经性质,努力缔构左传家的义例体系,因此《左传》凡例成为春秋学的研究关注重点。《左传》凡例由《左传》作者采辑相关史料撰成,并成为左传家说解《春秋》大义的义例体系核心。如果从形式上追溯其产生来源,礼例是其直接渊源之一,律例则是秦汉及其以后春秋家义例体系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8)葛志毅:《〈春秋〉义例的形成及其影响》,《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2期,第25页。认为《春秋》之例更多指的是《左氏》之例,而非其他二家。简逸光关注刘逢禄的例学,指出:“孔子作《春秋》,三传为之诠解,传以经言大义,后人理解‘微言大义’,或以孔子口传密授,仅公羊得之;或藉‘义例’褒贬言之。清人刘逢禄认为,阐释圣人微言大义,必须兼有师法传承与义例褒贬,方能彰明圣人著述思想。清代发扬今文经学,尤推何休,义例之学同时得到重视。论文认为除了经学内在的汉学溯源,清代对‘例’的研究,有一部分影响来自清代对‘律例’的不断修纂,深化了经学家对‘经例’的重视与诠释,同时将汉代藉经义以决狱的做法重新发扬,刘逢禄即具代表性人物。”(9)简逸光:《刘逢禄之“例”学》,《孔子研究》2017年第1期,第144页。刘宁讨论了义例在现实中的应用:“《春秋》学在汉代政治法律中发挥巨大经世作用,与判例法实践的关系尤为紧密。《春秋》的‘比事’之教,与判例法中的‘比’有密切联系,《春秋》义例学是以‘比事’为基础,总结归纳圣人的裁断原则,体现出‘无达例’的灵活面貌。《春秋》的‘属辞’,即书法、笔法,是‘比事’的体现。不能简单类比史书修撰体例理解《春秋》义例。董仲舒对《春秋》比事智慧做了深入的阐发,对《春秋》义例学做出重要贡献。”(10)刘宁:《属辞比事:判例法与〈春秋〉义例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74页。《春秋》义例的研究成果可谓丰富。
对何休义例研究的学者,当推赵友林,他认为:“何休所阐发的以三科九旨为代表的条例法则,使《公羊传》的书法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不断变化、进步的发展进程;他对于《公羊传》书法的扩充,使《公羊》书法更为繁富、系统,并使其褒贬惩劝功能得到加强;他运用‘属辞比事’这种方法探求《春秋》书法,并把书法的探求看成是一种符合逻辑的推衍,从而使书法不断条例化。”(11)赵友林:《何休对〈公羊传〉书法义例的改造与发展》,《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12页。笔者试图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探究何休如何发展《公羊》例学?《公羊传》书法如何不断进步?也就是何休在《公羊》例学的研究史中究竟做出了哪些贡献。
一、何休义例说的核心——三科九旨
何休之后的学者大多把三科九旨看作公羊学的核心,但对于三科九旨的解读,却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一类在徐彦疏中所记,这一类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何休自己所讲的:“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总言之,谓之三科。……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12)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另一种是宋均《春秋注》的说法:“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时与日月,详略之旨也。王与天王、天子,是录远近亲属之旨也。讥与贬、绝则轻重之旨也。”(13)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5页。两说看似不同,其实宋均只是在何休基础上,把三科九旨说发展为对条例的整体解读而已。在何休那里,其三科九旨说对于条例,有许多未尽的解读。
第二类是清儒孔广森给出的完全不同的解读:“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14)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9页。单从孔广森分析的三科九旨来看,其说完全背离了何休的传统,因此自刘逢禄起,即被斥为不守家法。如果详细分析这段文字,就会发现,孔广森与何休的区别仅在于二人所认定的公羊学核心不同而已。何休从例的角度分析,认为公羊学的核心为张三世、异外内以及存三统这样的三科九旨;孔广森则从《春秋》大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公羊学核心是合天地人的王道。六经本是一种完整的体系,各经都有各自的功效,《庄子·天下》篇谓:“《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15)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908页。《史记·太史公自序》亦谓:“《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16)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97页。除《书》以叙事外,《诗》以治志,《礼》《乐》以治人,《易》以治天,而《春秋》之义则在于统天人之正,在于论述天人合一的王道。孔广森指出:“《春秋》之为书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 但这一核心并不能齐备公羊学所有的内容,孔广森分析说:“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内外之异例,远近之异辞,错综酌剂,相须成体。”(17)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第279页。还是要将此天人合一的王道,通过内外远近的例表现出来。
何休与宋均所述,其实大体与孔广森之说相同。区别在于,孔广森将宋均演绎的诸例视作核心,而何休与宋均的核心,恰是孔广森放置于第二位的。宋均及孔广森之说,发展了何休的义例思想,使人们认识到日月时、讥贬绝诸例等不可或缺,完备了何休义例学说。在何休学说中,异外内等三科九旨,本就与日月时诸例圆融为一个整体。
(一)张三世
三世说在《公羊传》和董仲舒体系中已有说明,多指不同世中记述事件用辞的不同。三世说在《公羊传》中已经明确提出:“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18)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38页。董仲舒发展了这一说法:“《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义不讪上,智不危身。……畏与义兼,则世逾近而言逾谨矣。”(19)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9-13页。可以看出,董仲舒明确了三世具体何指,所谓异辞标准何在,以及不得不如此的原因,但二者都是将三世仅仅作为事件用辞不同来划分的。
这种说法在何休那里得到延续。何休的贡献在于,他立足经验的三世,将之理论化为王道由微至著的过程,使得“吾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的王道理想真正得到落实,且具有超越性,而不仅仅是对个别事件的褒贬刺讥。何休认为,孔子作《春秋》只是以那段历史为依据。何休的意旨在于说明王道的发展过程,载一代王法,是为汉室服务的。《春秋》之所以恰好三世、十二公,是因为这一时间恰恰是王道从微弱发展到成熟需要的时间:“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著治法式。”(20)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38页。
因此,“所传闻—所闻—所见”的传统三世说,被何休改造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王道发展三世说:“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21)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38页。传闻之世,新王初起,天下处于衰乱之时,这时圣王只能正自身及亲朋;所闻之世,新王稍长,天下升平,这时圣王不仅可以正自身,整个华夏都可教化;所见之世,王法大成,天下太平,这时无不教化,远近小大再没有区别,乃至大同。这种理想主义的论述,当然是面向未来的,但何休论述的并不是人类历史的整体,只是恰好选取了《春秋》这一段完备的王法由微至著的过程。他的三世说并不是在人类历史中的展开,而是在《春秋》之时的展开。何休认为,三世说的重心在于论述一代王法中各个时期每一等级的行为规范,这一点恰以内外例作为划分标志。
(二)异外内
内外例指的不是内外两个层次,而是内其国而外华夏,内华夏而外夷狄三个层次。《公羊传》带有很强烈的夷夏之防:“夏,公追戎于济西。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为中国追也。”(22)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287页。同时,《公羊传》本身有内外笔法之别:“《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23)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06页。
在此基础上,董仲舒明确提出三个层次之分:“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进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24)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116页。“是故于外,道而不显;于内,讳而不隐。于尊亦然,于贤亦然。此其别内外、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25)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12-13页。何休在吸收、继承这一说法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内外例:“‘如陈’者,聘也。内朝聘言‘如’者,尊内也。书者,录内所交接也。”(26)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312页。
何休的贡献在于,把内外例与三世说融合起来,将之发展为与三世统一、不断变动的内外例,从而体现王道的发展。《公羊传》文献中,已经出现内外例与三世说共同使用的例子,但这种共同使用只是混用,并不圆融。如:“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内大恶讳,此其目言之何?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27)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24页。可以看出,《公羊传》的例子中仍然是三世异辞,内大恶仍然书写的原因,是因为其时处于所传闻世,“杀其恩,与情俱”,直书而已。
到何休时,内外例与三世说开始圆融为一个整体,不同世之中,鲁、华夏、夷狄笔法皆不相同,同时鲁、华夏、夷狄内外笔法的不同,正好体现了三世的变化:“《春秋》始录内小恶,书内离会;略外小恶,不书外离会。至所闻之世,著治升平,内诸夏而详录之,乃书外离会。”(28)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41页。这样,在何休体系中有两种内外例:一种是如公羊一贯的与三世无关的内外例;一种是与三世统一的内外例。但三世与内外合一,分析的正好是王道的发展过程。何休以为《春秋》王鲁,因此《春秋》开始,为据乱世,鲁为内,华夏与夷狄俱为外,鲁小恶书,大恶不书,外大恶书,小恶不书;至升平世,华夏亦教化,与鲁俱为内,因此华夏大恶不书,小恶书;至太平世,则无内外之别,天下一同。《春秋》涉及的只有一种内外例,何休所谓三世不同,只是内外的范围不同,内外所包含的范围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
(三)大一统以至存三统
相比三统而论,董仲舒提出更为核心的概念是大一统,即道见过程中形成的、元之下的五始之正。大一统源自《公羊传》开篇:“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29)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6-12页。《公羊传》特别强调了一些组成元素: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认为这些都有重大意义,而非胡乱为之。董仲舒将之明确为五始之道:“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30)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70页。
这体现出两层含义:第一,董仲舒并不是在天之上又增添了一个实体(31)此处实体指的是在现象界实存之意。的元,形成层级的世界秩序。董仲舒认为,元包括天人在内整个世界的形而上依据,承载道。这样人就从天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有了实践的主体性,如后世宋儒所讲,由自我修养就可以实现元的先天禀赋。但元并非赋予所有人以自主性,这种权利只给予了王:“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32)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68页。其他诸侯、士大夫、民都依照顺序经过王才能达于元,他们不能获得自主性,只能靠天子的教化,因此形成了天(元)至天子至平民的大一统。
第二,董仲舒关注的重心并不在于人如何成为理想的人,而是讨论人类社会如何成为理想社会的问题,个人的修养问题是在政治哲学框架之下讲解的。董仲舒解释五始的材料,一些重要环节并不是王、诸侯、大夫这些人,而是王之政、诸侯之即位、境内之治这些政治环节。如果不从这个角度分析,就很难解释为何汉儒如此重视诸侯即位之正。因此,五始可以视作保持元之深、天之端、王之正、诸侯之即位,以及境内之治这些政治活动之正。
元只是形上依据,并非实体,而且元被董仲舒看作是天,整个世界也就是天、人两套系统。此处人指的是人类社会。董仲舒的天有二种含义:一指形上的天,即元;一指自然的天。由自然天的角度而言,人与天同具主动性;由形上天的角度而言,人在天统御之下。由之构成董仲舒的大一统,即天之下,与天同级,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王之政、诸侯之即位、境内之治,同时也正诸侯、大夫以至于平民的行为规范。
在天道流行中,由于自然天与形上天(元)存在矛盾,董仲舒又不得不提出三统说以弥补这种缺憾。元之道在自然中呈现出四季的轮转,在人类历史中会相应呈现出三统的不断循环实践。董仲舒的核心理论仍然是袭道的天人大一统。元之天是形上的,可流行万物而不失。但同时天又是阴阳二气组成的自然之天,流行当中会有变化。董仲舒认为:“天之志,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33)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336页。阴是不起作用的,因此当天流行至纯阴的太阴时,也就是冬季的时候,天的作用是空,是没有作用的。对应人类社会,道在现实中的流行,也必然会出现某一时期不能起到作用:“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34)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18页。每一世代对道的实践,到最后都会出现纰漏,需要其他措施来补救:“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35)班固:《汉书》,第2518页。夏上忠,及至其末偏于野;殷救以敬,敬指敬鬼神,及其末世偏于虚妄;周救以文,及其末世则只重文不重质;继周者当救之以夏忠,形成一种循环(36)当然,董仲舒的三统说更加复杂,有九皇五帝三王、商周质野以及三色不同体系的循环系统,此处为对应何休理论,只言及此。。
何休的大一统及三统思想,基本继承自董仲舒,只是这些思想在何休学说中显得比较僵化。董仲舒认为的天人两大系统之间的关系,在何休看来,完全变为天、王、诸侯以致大夫、民众强制之正,即对强制行为规范的遵守。何休说:
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37)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7页。
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38)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3页。
从中可以看到,何休与董仲舒的认识存在区别。何休将元解释为元气,可能何休因为气无形,所以以为元气比有形的天更先天一些。何休认为元气是在天之先的一种实体存在,可以看作是构成世界的质料,但何休又想用质料当形式使用,赋予世界以伦理色彩。而对董仲舒来说,既然元不再具有形上色彩,那么道也就无形上义,从而变成非普遍性的强制理论。同时,人也就完全丧失了自主性以及自我超越的可能,变成天命的被动接受者。因此,董仲舒虽然也是由元年、春、王、正月演绎出五始的观念,但其实也是自己提出的天人两大系统之间的关系。而在何休看来,天人关系完全变为天、王、诸侯乃至大夫、民众强制之正,于人世而言,即是自天子之下对强制行为规范的遵守。
何休认为,不存在道在现实中因实践而引起的三统循环问题,道只是僵死的理论规定而已。何休并不讨论统的循环,只是就一王而讲三统并存。从理论名称而言,何休称为存三统,而董仲舒称为通三统。存三统明显是立足于一王而进行的论述。何休的重心在于,以《春秋》这一代完整王法为例,恰好可以述说完整的王道义例。
综上可知,何休把三科九旨开始综合成一套完整的体系,旨在论说以《春秋》为王为例,及一代完备王法的行为准则,也就是论说《春秋》义例是什么的问题。
二、何休义例说的展开——多层次的义例
在公羊家看来,《春秋》有不修《春秋》及已修《春秋》的区别,孔子重新修订了鲁国原有的史书《春秋》,成为经之《春秋》。孔子修订的方法,是对原有的用辞及事件进行改造,以喻王法于其中,所谓“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孟子说得则更清楚:“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春秋》是通过事与辞以求其义的学问,整部《春秋》被何休建构为四个层次的义例大框架。首先,《春秋》是以隐公至哀公这段真实历史为依凭书写的史书,真实的齐桓晋文之事是《春秋》书写的基础。这是《春秋》义例的第一个层次。
其次,在事的基础上书写出来的就是文,但《春秋》之文并不只是记载事的史文,更是蕴含了大义的经文,原有的史文经过了孔子的重新挑拣与改造。在孔子那里,事呈现的文就有书与不书之别。《春秋》为正是非之书,孔子所记皆是有关是非的事件,因此无关褒贬的日常行为在《春秋》中均不记录,称为“常事不书”。《春秋》所见皆是非常之事,称为“有所起”,或有善起之是,或有恶起之非。根据具体事件的是非、善恶程度不同,《春秋》给予不同的判定之辞,如讥、贬、绝等。其中善起并不多见,更多的是贬损的违礼恶事。对于这些非常之事,每一类事件孔子都有恒定的判定之辞,因此可称为常例。这是《春秋》义例的第二个层次。
在这一层次中,除了“有所起”之事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的存在,即权。权与恶事一样,都是悖于常礼的,但二者的区别在于,恶事悖于礼归于恶,而权虽悖于礼却归于善,所谓“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39)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79页。。礼之本为道,所有遵循礼的行为均以道为根基,但并非所有以道为根基的行为均符合礼制规范。非礼之道即为权,礼与权是互相矛盾的两面,而同归于道。恶事则并非如此,仅仅是对常礼的违背。因此孔子在第二层次记载了三类文,即有所起之文、不书之文以及权之文。
再次,《春秋》于所书写的事,均冠以相对应的讥、贬、绝等评价性辞汇。此外,每一事件根据善恶程度的不同,都与相应的日月时及称谓等搭配使用,以上诸例均在常例之列。但这些评价性辞汇,以及日月时的使用与事件之间,并不是僵死不变的,《春秋》又通过日月时诸例的变化,达到对特定事件的讥、贬、绝。讥、贬、绝及日月时诸例可称为变例。日月时达到变,讥、贬、绝体现变的目的,这是《春秋》义例的第三个层次。
最后,《春秋》义例的第四个层次是道,即《春秋》大义。《春秋》为正是非之书,事与辞最终都指向义。在何休看来,孔子作《春秋》,并不局限于事与辞,而是通过对辞的运用来褒贬事,从而达到对义的掌握;反过来说,掌握了义,也就掌握了是非之本,所为之事都在可以然之域,对他人事件的评判也都符合义例的规范。因此,在何休看来,《春秋》义例的第四个层次是看不见的根本大义。
(一)常例
常例之中,有所起之事为重,何休此处着重探讨了关于战争、朝聘会盟、卒葬(40)《春秋》对于个人弑君或杀大夫等事,也都是作为重大事件进行记述,因与卒葬例有很多重叠,故一并论说。等非常之事的义例要求。
1.战例
战争本身是符合礼制之事,五礼当中即有军礼,但《春秋》中所记战事大多是贬损之文。“凡书兵者,正不得也。外内深浅皆举之者,因重兵害众,兵动则怨结祸构,更相报偿,伏尸流血无已时。”(41)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48页。这代表了孔子对《春秋》之战的总体看法。兵者本为消除不符合礼制的祸乱而发,必须自天子出,才不至于乱上加乱。《春秋》之中记载的大多却是诸侯皆举兵,互相攻讦报复,结果造成死亡与流血不止,所谓《春秋》无义战,“师还,善辞也”。
在战争的具体书写中,何休认为孔子书写时一般涉及四项内容:时间、地点、对立双方以及战争的类型。按照其危害大小,战争的类型包括侵、伐、战、围、入、灭以及取邑等。侵、伐虽然程度不一,但大体可视作一类,“以过侵责之”是谓侵,“侵责之,不服,推兵入竟”(42)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257页。谓之伐。侵、伐都有责过,即罚恶之意。
比伐例恶稍多一些的是战例。战,常例称为偏战:“偏,一面也,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43)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69页。约定好时间地点,双方摆开架势,互相对攻,虽然也会有伤亡,但未有权谋背信之举,仍不失为正。此常例之中,何休强调了两个变例:一为诈战,指背信弃义的战。“偏战日,诈战月。”(44)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90页。以使用日月的不同表示危害不同;一为内战,指王者鲁之战。“内不言战,言战乃败矣。《春秋》托王于鲁,战者,敌文也。王者兵不与诸侯敌,战乃其已败之文。”(45)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69页。战毕竟没有罚恶之功,只是双方单纯的对攻,对于王者而言,这种战争虽胜犹败。
围是包围外部而不入其国,《春秋》中围例使用的并不是很多。入即是攻占他国城池或国家之意,但与后一类灭的区别在于,虽入但最终城池仍为原国所有,因此入可视为不正义地进入一国城池,并不单指军队的进入,个人哪怕是本国臣民不正进入也称为入。最后一类是取邑和灭例,都指夺人所有。取邑指取人城邑,为恶尚小,因此《春秋》说“外取邑不书”。灭指灭人之国,为恶最大,有则必书,且毫不避讳。
对于以上战例,《春秋》常以记载的时间单位,及对立双方书写的顺序不同,来评价战争恶的大小。“战例时”(46)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89页。,一般记载战争发生的时间,有书月书日者以见其恶之加深。关于战争的对立双方,伐、围、灭等词汇描述,由主语见罪,而在战例中则不见其恶,实则双方皆贬。如果发动战争的是对立方,则书于前者罪大:“虞,微国也,曷为序乎大国之上?使虞首恶也。”(47)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378-379页。一般情况下,都是国大爵尊者书于前,因为相对而言其危害会更大一些。另外,观察记载的主语单位如何,可以看出战争的规模:“将尊师众称某率师,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将卑师少称人。”(48)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81页。
2.朝聘会盟例
五礼之中还有宾礼,会同之事本身符合礼制规范,而《春秋》所记会盟诸事皆含有贬损之义。何休认为,朝聘与会盟不同。朝聘是《春秋》前就有的礼仪,多专指拜会天子,《春秋》所见朝聘,做法符合大义,并不完全为恶,何休常以之论证王鲁说。会盟则是《春秋》时诸侯的肆意而为,孔子记载这些就是为了贬损之。
朝、聘本是两种不同的礼,朝专指诸侯拜会天子;聘则指诸侯之间派遣大夫互相拜会,天子也有派遣大夫聘问诸侯之礼。聘的范围更广,限制更少,大夫往来皆可言聘。但在何休看来,朝聘被看作一例,皆以显示鲁国的特殊性:“《春秋》王鲁,王者无朝诸侯之义,故内适外言‘如’,外适内言‘朝’‘聘’,所以别外尊内也。”(49)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08页。何休把聘从诸侯间大夫往来的通称,改造成其他国大夫适鲁的专称;同时把本指拜会天子的朝,改造成诸侯对鲁国的拜会。这两者都凸显出王鲁之义,何休认为其符合情理。朝聘书写常例大致相同,主要关注两部分内容:时间单位和所派人员爵位。时间大体书时节,“朝聘例时”(50)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312页。。
诸侯间除了朝天子之时,本无私自会面之礼,因此《春秋》中记载会盟例,基本是恶的:“凡书盟者,恶之也。为其约誓大甚,朋党深背之,生患祸重。”(51)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22页。诸侯间相约会盟,易生朋党,违背大一统之旨。同时,会盟按照其不正的程度,大致可以分为盟、会、离、遇、胥命等种类。其危害大小跟与会者筹划程度有关,筹划程度越高则危害越大,最接近正的是仅“结言而退”的胥命。
会盟例的书写一般需要三个部分:时间单位、地点以及与会者情形,寓含义例的是时间单位和与会者情形。时间用以序列其信的程度。盟会是不义的,但不义中有义,这个义就是信,虽不正,但既有约定在身,就要遵守。徐彦总结曰:“大信时,小信月,不信日,见其责也。”(52)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22页。与会者的情形,包含两处义例:一是与会者书写的先后次序。这点与战争例基本相同,“序上者,主会也”(53)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87页。,主会则罪大。二是与会者爵位的书写。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战争,以及整个《春秋》书爵位者,其可概括为:“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54)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261-262页。以此进行褒贬。
3.卒葬例
与战争、朝聘两例不同的是,作为五礼之一的丧葬礼,在《春秋》记载中出现丧葬之文时,并不与贬损之义相连,更多的是作为国之大事进行记载。丧葬的记录范围,男子是全部记录的,包括天子、诸侯、大夫、士的丧葬。而对于女子,《春秋》只记录三种情形:一是天子之女嫁给存三统中前两王的,或者诸侯之女嫁给其他诸侯作夫人的:“天子唯女之适二王后者,诸侯唯女之为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55)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217页。二是与鲁国有关的女子之亡:“秋,七月,齐王姬卒。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录焉尔。曷为录焉尔?我主之也。”(56)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211页。三是记载国灭族亡之女子,以显其国君之覆灭:“八月,癸亥,葬纪叔姬。外夫人不书葬,此何以书?隐之也。何隐尔?其亡国矣,徒葬乎叔尔。”(57)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332页。
丧葬礼中,最重要的是卒和葬两例。卒指死亡,《春秋》之文涉及时间、称谓诸要素。就时间而言,卒常例书日。称谓包含两个要素,即卒者的爵位及卒者死亡的名称。死者爵位按照其生前的爵位书写,所谓“卒从正而葬从主人”,因此天子称王,鲁称公,卫称侯,曹称伯,一切依照公侯伯子男之例。《春秋》改造了死亡名称的记载,丧葬礼中,本是“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58)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59页。,但《春秋》为了突出王鲁义,文中鲁公独曰薨,其他诸侯一律改称卒,以示区别。
卒、葬二例不同,“卒从正,而葬从主人”。为什么会如此呢?何休认为这是因为二者地位不同:“卒当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从君臣之正义言也。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59)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01页。诸侯、大夫卒是天子之失,在政治上会产生很大影响,因此按照大一统等级处理,以示其公义;葬礼则纯粹属于私礼,因此从主人。这样的差别决定了葬礼中的两项常例:一是无家无子者不书葬,所谓“有子则庙,庙则书葬;无子不庙,不庙则不书葬”(60)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09页。。以此类推,国君被弑而不讨贼,则不书葬,因为无臣子之心,以为无臣子。二是葬礼在亡者爵位上与丧礼不同。葬从主人,而亡者爵位依从其国内自称,如葬陈桓公、葬郑庄公之类。
(二)变例
1.常中之变:日月时、称谓
何休认为,《春秋》之文中,常例常以日月时或称谓的运用,体现对一类事件的评价,但这些日月时及称谓的运用,不是僵死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以应对在常例基础上对具体事件的评价。
《春秋》书写时间的原则为:单位越小说明事件的重要程度越大,或善或恶的程度也就更大。每一常例均有各自的时间书写义例,若在其时间常例上有所细化,则表明《春秋》此处有所起,善起其善,恶起其恶,不一而足。时间未有在其原有单位上粗化的例法,只有细化以示程度的增加。如朝聘常例皆书时,而宣公九年则书“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齐”。何休以为:“月者,善宣公事齐合古礼。”(61)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632页。在常例的基础上缩小时间单位,表明善之隆。
何休总结称谓的等级曰:“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62)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261-262页。州、国俱为夷狄称谓,已经不视之为人;氏、人、名、字一般指称大夫;子即子爵,指称诸侯。何休所谓七等之例,其实指称上述三种类型,基本包含了《春秋》所要褒贬的对象。当然诸侯之上还有天子,但天子是无错的,即便有错一般也使用讳例。诸侯最高为公,最低称人(称人即以为夷狄),视其善恶大小在常例基础上或褒或贬(63)诸侯一般不称名、字,称名者多为绝例。。大夫褒则称字,贬则称名、氏,最高者贤而称子。一般非君称人称国者,大抵指民众而言,如:“曹杀其大夫。何以不名?众也。”(64)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313页。夷狄之类,一般书国书州,有善事则称人:“荆人来聘。荆何以称人?始能聘也。”(65)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300页。
2.变例的目的:刺、讥、贬、绝
《春秋》乃正是非之书,所记之文一般要对一类事件加以评判。同样的常例中,变化时间及称谓,也是对具体事件进行评价,这是所有常例、变例之文的目的。何休认为,《春秋》中为评价事件,专门设置了刺、讥、贬、绝诸例,以及用以处理特殊情况的讳例。
罚恶诸例,按其深浅程度,第一是刺例,恶的程度最轻。刺例虽然在起人之恶,由于其恶浅,人物称谓还是如常例所示,只是在事件中凸显褒贬,如:“冬,公次于郎。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纪而后不能也。”(66)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215-216页。鲁庄公虽终未救纪,然本心是想要救纪的,所以只是刺而已,未过多批判其人。第二是讥例,恶的程度次于刺例。讥例与刺例相似,也是就事件而言,批评其行为非礼,如:“乙亥,尝。常事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尝也。”(67)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82页。第三是贬例。顾名思义,贬例即在其本来称谓上有所降低,已经对行为人本身进行评价:“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夫人何以不称姜氏?贬。曷为贬?与弑公也。”(68)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375页。罪恶重,已经不配拥有原有的爵位,因此配以降等的称谓以起其恶。第四是绝例,恶的程度最重。绝即绝其功,完全剥夺爵位:“卫侯朔何以名?绝。曷为绝之?得罪于天子也。”(69)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88-189页。“蔡侯献舞何以名?绝。曷为绝之?获也。”(70)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260页。可以看到,绝例皆是得罪于天子,或是有害夷夏之防这样大损礼制秩序的罪过,称名完全取消其贵族身份。
3.《春秋》大义
何休认为,一切常例或变例的运用,最终都是为了把握《春秋》大义。例从来都不是目的,只是通往大义的阶梯。文与事都指向义。反过来说,把握了《春秋》大义,其行为举事才不违礼,文字记述才不违例,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
在这一点上,何休与董仲舒的认识是有差异的。董仲舒通过对元的解读,达成了王以下对道德尊卑有序的等级实践,每一等级除了符合礼制规范的行为外,都有超越的可能。但何休认为,卑微等级已经没有了对道德的实践可能,君君臣臣之别变成了只是需要强制遵守的规定。最重要的范畴变成正,五始的秩序要归正,每一等级的行为也要归正,这比董仲舒的理念体显出更严格的规定性。当然,何休并非排除个人内心的作用,而认为心的作用不是对于道的理性追求,对道的实践变成内心对于秩序的严格遵守。判断善的标准不仅要看其行为是否符合礼制规范,即是否正,更要原心而见志,考察其内心是否也坚守秩序。因此可以说,何休把公羊家原来既有的、严密的大一统为正的秩序强化了,公羊完全变成一套义例准则大法。
结语
立足于《公羊》学史来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公羊》先师就是董仲舒与何休两位。董仲舒之学与何休之学是有很大差异的。首先,二人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董仲舒时国家已完成统一,但尚未建立起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他解决的问题重心是如何以《春秋》之学建构礼制,维护大一统的政权。何休面临的问题,则是左、榖二家“操吾矛以伐我”的《公羊》学危机,他的重心在整理、论述《公羊》学的真谛,以及论证《公羊》之学何以享有对《春秋》的独家解释权。
其次,从内容来看,董、何二人论述的《公羊》学有所不同。董仲舒之学大致包括两项内容:一是治《春秋》学的方法,即“五其比,偶其类”的属辞比事;一是义法,即“人道浃而王道备”的“礼义之大宗”。在董仲舒的论述系统里,义法的阐述多于方法的探究。但在何休那里,这两部分的比例颠倒过来,方法的探究成为重点。
何休的这一转变,其功不下于《公羊》经传之著于竹帛。何休奠定且完备了《公羊》的治学方法,使得《公羊》成为一门真正完整的学问。在何休之前,虽然也有先师讨论过《公羊》的治学方法,但这些讨论都是偶然出现和不系统的。《公羊》的治学方法并没有作为专门问题进行探究,严格说来,《公羊》并不能称为一门学问。很多《公羊》学者自豪又无奈地称公羊学为口传秘学,《公羊》当中很多论说被视为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其实这些都是公羊学本身无法可依、不被各家承认的体现,因此左、榖二家才会有机可乘。何休明确并系统化了治《公羊》之法,促使公羊学成为公认的平实学问,也防止了学者肆意发挥、以己意解经情况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何休造就了公羊之学。
何休以后的公羊学,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就是何休之学。仅从文献而言,《隋书·经籍志》记载:“《春秋公羊传》十二卷,严彭祖撰;《春秋公羊解诂》十一卷,汉谏议大夫何休注。”(71)魏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30页。说明此时何休《解诂》与《公羊传》可能尚未合著。现在看到较早的《公羊传》版本,抚州本及余仁仲本均为宋本,两者已经是《解诂》与《公羊传》合著本了。另外,宋代十三经注疏中所见《公羊传》,已经是《公羊传》与何休《解诂》、徐彦《公羊疏》的合著本,并成为延续至今的定本。而徐彦《疏》围绕的解释对象并不是《公羊传》本身,而是何休的《解诂》,何休取得了对《公羊传》的独家解释权。如果把时间往前追溯的话,可以发现,孔子以后“方法”与“义法”的探究,是各家视作《春秋》之学的主要特征。《经解》所谓“属辞比事”,说的是方法;《庄子·天下》篇所谓“《春秋》以道名分”,《孟子》所谓“丘窃取之义”,讲的是义法。在何休之学影响渐盛的情况下,其他学说如董仲舒之学是逐渐势弱的。何休之学的独大,可能也会造成学者对《公羊》其他方面的忽视,这是需要今人格外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