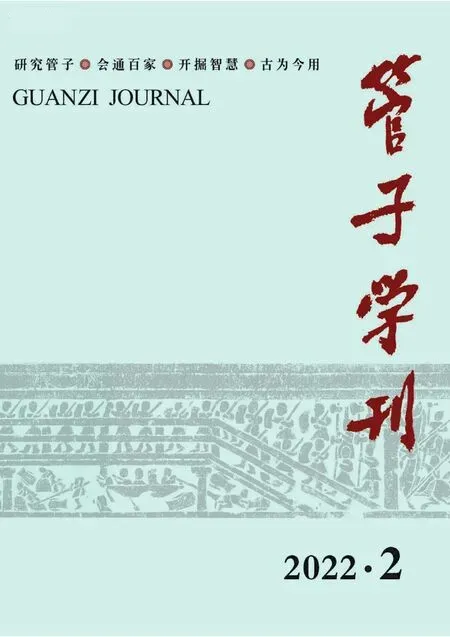天人之辨与中国儒家思想史的主题
沈顺福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人类文化或文明的重要形态是思想。讲述人类文化史或文明史的最直接、最典型的方式便是思想史。中国人所说的思想史,西方人称之为history of intellectual或 history of ideas。如果把它们直译为汉语的话,前者为学说史,后者为观念史。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自然有自身的特殊主题或研究对象,它因此区别于哲学、经济学、管理学、军事学、法学等专门科学,否则的话,思想史便无法区别于文化史或文明史等。那么,哪些思想可以进入思想史关注的视野呢?哪些思想又可能成为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史关注的主题呢?这是本文将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本文将试图指出: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史的基本主题。儒家思想史便是儒家的天人关系理论史。
一、思想史主题的重要性
思想史是一种观念史。观念,作为某种意识形式,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具有复杂的形态和丰富的内容。康有为的观念与“祥林嫂”的想法通常会迥然不同。由于普通人数量巨大,其所持有的观点也因此极为丰富,甚至是浩瀚如海。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我们几乎不可能将这些数量巨大的普通人的想法穷尽并记载。也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的观念或想法都可以进入思想史研究的视域。那么,思想史关注哪类想法或观念呢?思想史学家只能够选择某些类别的观念,对其进行整理和描述。
被思想史专家们所关注的观念至少具备两个基本特征,即“重要性”与“延续性”(1)[奥地利]弗里德里希·希尔著,赵复三译:《欧洲思想史·作者前言》,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ⅩⅦ页。。这些思想一定具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无论好坏。比如尼采的思想,弗里德里希·希尔说:“所有存在的事物中,最危险的是精神,尼采自认为是‘炸药’,实在不假。”(2)[奥地利]弗里德里希·希尔著,赵复三译:《欧洲思想史·作者前言》,第ⅩⅩ页。思想史上的思想不仅影响到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甚至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思想史上的观念或精神一定关乎大问题、大事情,甚至关乎人类的命运。“有文化有历史的民族,必然能对宇宙人生中某几件大事,某几个问题,认真思索。”(3)钱穆:《中国思想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2页。这些观念或精神聚焦于某些大问题、大事件上。比如中国历史上的董仲舒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其关注的中心乃是人类的前途问题:人类及其所创造的文明在宇宙生存体系中具有怎样的地位?这些问题关系到人类的命运问题。而作为思想家的康德提出“人是目的”的命题,从而将人的尊严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即每一个人都是目的,都值得尊重。这不仅影响到伦理学,更揭开人类理解的新篇章。
这些思想,在其开始阶段可能仅仅是相对的专业视角,比如属于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甚至是哲学思想等。可是,随着这些思想的延伸与影响,它们不仅对自己的专业领域产生了影响,而且进而影响到其他领域,甚至对人类社会的进程与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正是这些具有重要地位的思想,才是思想史关注的重点。比如霍布斯,最初仅仅是一位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理论表现出他展望世界时所感到的恐惧。他认为:人的自然状态就是生活在每个人反对其它一切人的战争中。如果一个总体国家——即利维坦——不能经由法律维持理性、和平、社会交往和财富的统治,人们就将退回到野蛮混乱的状态中去。利维坦乃是清教徒共和政体的再现,是世俗化的上帝之城”(4)[奥地利]弗里德里希·希尔著,赵复三译:《欧洲思想史》,第477页。。霍布斯的政治学说不仅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影响,而且影响到整个人类政治体制与人类文明。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理念由此而建立。同样,亚当·斯密最初是一位国民经济学家。他在《国富论》中“欢呼‘自由经济的统治’是地上的乐园。经济自由成为神圣的世界秩序和社会生活的最终意义和目标”(5)[奥地利]弗里德里希·希尔著,赵复三译:《欧洲思想史》,第484页。。这种自由经济学说通过影响经济而改变了整个社会基本形态,将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竞争的时代,从而影响到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思想家的作用绝不仅限于某个领域或某些领域。他们的思想或观念通常会影响到国家与民族甚至人类的命运和前途。“思想史最关注的,正是在重大历史事件的形成过程中,思想和行为之间的互动。”(6)[美]罗兰·N·斯特龙伯格著,刘北成、赵国新译:《西方现代思想史·导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思想史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在关注或解决某些重大事件中,这些观念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思想史研究者通常坚信,任何一个时代(各个时代不同)都有一种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影响着思想和表达的所有领域。柯勒律治写道:‘任何时代都存在着这样一种思考精神,这应该是宗教和道德的精神和基调,甚至是艺术、习俗和时尚的精神。’最近一位学者宣布:‘思想史学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勾画每一历史时代的思想前提,解释这些思想前提在不同时代的变化。’”(7)[美]罗兰·N·斯特龙伯格著,刘北成、赵国新译:《西方现代思想史·导论》,第5页。思想史家关注的是时代精神,是能够成为其他思想的基础的观念。
从中国思想史来看,比如孔子“是中国思想史上有最高领导地位的人。……世界上的一切宗教,似乎都想根据人死问题来解决人生问题,孔子则认为明白了人生问题,才能答复人死问题。世界上一切宗教都把奉事鬼神高举在奉事人生之上,孔子则认为须先懂得奉事人,才能讲到奉事鬼。这一态度,使孔子不能成为一宗教主,也使中国思想史之将来,永远走不上宗教的道路。”(8)钱穆:《中国思想史》,第8页。孔子最初仅仅是一位老师,讲授一些专业知识与理论,比如六艺和婚丧嫁娶的礼仪等。孔子不仅教授这些知识,而且对其进行了理论阐述并逐渐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化学说逐渐对整个时代的思想与观念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孔子的仁学思想逐渐转换为“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和信仰”(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成为普通人的信念与观念。孔子也因此而成为中国儒家思想史上的领袖级人物。大人物之所以为大人物并非生来如此。大人物的盛名产生于时代与社会。因此,思想史“决不能抹杀大思想家的关键地位”(10)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有学者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法律思想、军事思想等等,都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11)张岂之:《中国思想史·原序》,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他们将思想史看作是学说史、文化史的综合。从出发处来看,这一说法不无道理,即所有的思想家必定开始于某个领域。但是,这仅仅是起点,而不是全部。他们的观点开始于某个专业领域,进而对其他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最终成为影响一个时代甚至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观点。这些影响完全超出了其专业范围。只有这类能够产生如此广泛影响的思想或观念才能够成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影响力仅限于本专业的思想常常不能成为思想史关注的对象。思想史仅仅关注那些产生跨领域影响力的思想。
由于思想史和哲学史都研究观念,人们常常将思想史等同于哲学史。如钱穆曰:“西方思想,大体可分三系。一为宗教。二为科学。三为哲学。此三系思想,均以探讨真理为目标。”(12)钱穆:《中国思想史·序言》,第1页。由此来看,钱穆将思想史与哲学史不加区别。后来的胡适也这样做。虽然哲学史与思想史有时候会有些重合处,但是二者之间不仅研究对象不同,而且研究方法也有较大的区别。在西方哲学传统来看,哲学关注于存在(being),比如理念、实体、理性、思维方式、上帝等都是西方人对存在的解读。这个存在,在中国哲学传统看来便是本源,比如人性、天理、本心等。因此,哲学关注本源或追问本源。而思想史关注于现实中的大问题、大事情,它具有直接的重要性,而未必属于本源。尽管本源的东西通常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但是二者不可等同。西方历史上有个学者叫弗雷格,西方哲学史通常会提到他,而西方思想史界可能很少关注他。在中国历史上,韩愈、李翱、柳宗元、刘禹锡、梁启超、严复等,思想史界比较关注他们。但是哲学史却不怎么待见他们。没有人会否认佛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化,哲学史家十分重视,而思想史家却常常不重视。一般的中国思想史著作如程艾兰先生的《中国思想史》(13)[法]程艾兰著,冬一、戎恒颖译:《中国思想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谈论华严宗与天台宗的内容比较简略。而华严宗和天台宗对于宋明理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思想史不同于哲学史。如果强行等同,其结果可能会把哲学史变得不像哲学史。当然,思想史并不绝对排除哲学史。只有重要的、能够产生深远和广泛影响的哲学思想才可能成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如康德哲学常常也是思想史关注的对象之一,中国古代的禅宗不仅是哲学史讨论的内容之一,也常常是思想史关注的对象之一。原因在于禅宗不仅对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通过传播,对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生活方式等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因此而成为重要的观念。这种重要的观念自然被纳入思想史的视域中,并成为思想史的基本内容。
二、思想史主题的继承性
思想史不仅关注大问题、具有主旨性,而且具有继承性,即这个问题或这个问题所反映的主题贯穿于历史的始终。比如,“在欧洲的精神史上,从来都存在着‘上层’和‘下层’的斗争。‘上层’文化包括基督教、有教养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始终与人民大众的‘下层’文化进行着斗争。这个文化的底层包括人民大众的个人的深层人格和大众的风尚、信仰、生活方式等”(14)[奥地利]弗里德里希·希尔著,赵复三译:《欧洲思想史·作者前言》,第ⅩⅦ页。。在西方思想史上,上帝、教会等神圣存在与世俗人的关系开始于古希腊,一直延续至今,成为西方历史上的一个永恒的主题。“鲍默(Franklin L. Baumer)在其《西方近代思想史》(ModernEuropeanThought:ContinuityandChangeinIdeas, 1600-1950)中,认为欧洲有一些‘永恒问题’应当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中心,它们主要是‘上帝’、‘自然’、‘人’、‘社会’、‘历史’,这很有意思。”(15)葛兆光:《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文史哲》2011年第3期,第46页。这些主题,可能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形态,但是终究还是这个主题的某种形态。能够成为思想史研究对象的主题一定具有持久性与继承性,即它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态。
赵吉惠先生提出“社会思潮说”,认为思想史应该侧重以社会思潮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所谓‘社会思潮’,就是指那些反映某个历史时期思想斗争焦点和中心的社会思想潮流。……质言之,‘中国思想史’这门学科,主要研究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潮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和规律,研究社会思潮与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通过这种研究,从历史发展的纵横联系和总体上去揭示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历史规律性。”(16)赵吉惠:《试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第80页。虽然“社会思潮说”其实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它揭示了思想史的重要特征,即观念发展的延续性。思想史关注社会思潮的发展和演变,关注于该社会思潮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与规律等、关注于思潮的持续性关系。从中国儒家思想史来看,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足以称之为思潮。这些思潮不仅具有时代性、历史性,而且具有一致性、关联性与继承性,比如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等与宋明理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可以将这一贯穿始终的性质叫作思想史对象的继承性,即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可能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形态,但是它终究属于同一类存在。只是这一同一类存在本身并不直接呈现。它仅仅是一种隐形而“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1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第11页。。正是这种隐形的内容构成了各种思想话题的“背景”或底色。它也可以被叫作“平均值”(1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第11页。。这个“平均值”贯穿于思想史的始终。
思想史关注的问题既有历史性、时代性,更有逻辑性与持续性。它决不能够局限于某个时代、成为某个时代专有的问题。比如魏晋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想史问题是人才问题,即如何认识人才、选拔人才等。这个问题在当时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或主题。但是人才问题,只能是当时的话题,却不足以演化为贯穿于历史的重要议题。思想史的主题必须具有延续性或继承性。麻天祥先生说:“思想史研究,不仅要注重思想生成、存在、发展变化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生存方式等外在环境,尤其要注重思想的内在特征和逻辑必然性,即其与社会符契、反映时代精神的内涵,体现思维深度的逻辑框架以及昭示未来并与时俱进的厚度和张力。我是这样理解、应用或者说实践‘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原则的。”(19)麻天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理念与方法》,《史学月刊》2012年第12期,第8页。也就是说,思想史的发展具有内在特征和逻辑必然性。这些内在特征与逻辑必然性表明思想史对象自身的继承性或一致性,即它们延续了同一个线索演化而来。思想史的主题具有自身的谱系。
三、思想史主题的实在性与抽象性
在现有的学术体系中,思想史属于专门史,属于历史学。在历史学研究中,史料自然是最重要的材料,甚至成为研究对象。张荣明先生认为:“思想史研究有两重对象:直接对象与间接对象。直接对象,就是研究者所面对的客观实在。与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不同,思想史家在研究室或图书馆面对的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历史资料,史料是研究者直接面对的研究对象。间接对象,就是史料所投射的已然逝去的历史事件。历史事件一去不返,研究者永远无法面对消逝的过去。”(20)张荣明:《思想史研究指要》,《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2页。这一论断,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固化为历史资料,似乎书面文献才是思想史家们的研究对象。应该说这一观点揭示了历史与历史资料之间的关系。思想史是时代史或当代史。过去史实已然过去,无法直接在场。以往的历史史料是这些史实的再现,现在的历史研究何尝不是如此呢?尽管思想史家所面对的直接对象是史料,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客观事实的在场或曾经在场。
史料反映了客观的事实或史实。所谓的史实具有两个特征:一是确实存在,二是已经成为历史,如同川上之流。当我们去阐述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史实时,这个所谓的客观史实其实只能够通过思想史专家的思维与推理而被给出,这便是勾勒或建构出某种实在的史实。所以,思想史的对象并不能够被直观到。它只能够被想到并因此而成为史实,并进而成为事实。这如同人们对《红楼梦》的理解:厨师眼中的《红楼梦》是一部美食大全,其中所记载的美食美味等客观而实在,但是并非一般人所知晓,只有懂得美食的人才能够根据一些文本推测出某些美食。不懂得美食的人是看不出其中的美食与美味的,美食与美味需要人们的思维与推理。所以,丁为祥先生说:“实际上,哲学史与思想史虽然要面对同一对象,但其区别则主要在于不同的研究视角、解读方法与不同的诠释方向上;哲学的概念虽然源自西方,但哲学的方法却并不为西方所独有,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存在的。”(21)丁为祥:《简议哲学史与思想史之别——兼与葛兆光先生商榷》,《文史哲》2013年第3期,第74页。丁为祥教授强调思想史家与哲学史家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差异,此言不无道理。按照现象学理论,不同的视角或方法会产生不同的内容。这些被给出的内容便是其对象。
思想史主题的重要性依赖于建构。什么是主题的重要性?主题的重要性不在于话题本身,比如论述天人关系、论述神人关系等。而在于对这些问题的论述所产生的结论与这个结论所带来的影响。后来的影响决定了主题的重要性,或者说,后来的存在事实“给予”主题的重要性。没有一个议题天生重要,同理,思想史主题的继承性也依赖于建构。历史本身仅仅如川流而不息,只有在人类的主观建构中,川流的史实才逐渐演变为逻辑的事实与有序的历史。在这些逻辑的事实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思想史的主题,思想史的主题也依赖于人们对复杂材料的整理与勾勒。同一部《庄子》,哲学家读出哲学思想,文学家读出文采,而历史学家则读出历史事实等。我们不能因此而说《庄子》是哲学家的研究对象却不是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庄子》文本并不是研究对象,能够作为研究对象的只能是文本中所包含的某些东西(object)。在哲学家看来,《庄子》是齐万物、齐是非,这是哲学家关注的对象。在历史学家看来,《庄子》是“尧让天下于许由”的“史实”。这些所谓的对象隐含于陈述中、却需要思想者来找出或勾勒,这便是思想。
作为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史实只能够存在于思想史专家的思维视野中。在这些专家的推理中,人们或许可以勾勒出这些逝去的史实,没有人们的主观建构,史实可能永远是秘密。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太迷信客观材料了。材料也是人们整理后的产物,是一种主观建构。当然,我们说建构或勾勒,并不是说思想史专家可以任意虚拟某些史实。我们承认史实的客观存在,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非现实性。史实指事件,这些事件尽管是客观而实在的,但是,在它产生的瞬间便随着时间而流失或消失于我们的经验。它只存在于可能界,我们可以通过反思那些史料而让史实逐渐呈现。葛兆光先生说:“并不是说我们不准备写精英和经典的思想史了,我只是说,要注意那些精英和经典的知识、思想与信仰背景有些什么,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的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的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程,因此它也应该在思想史的视野中。”(2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第11页。这个所谓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便是所谓的“史实”,即确实存在着某种被当作历史进程中的基石或主流,却常常为人所忽略、所无视的存在。它虽然客观而实在,却从未直接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史实从未成为现实界的存在者,它仅仅是可能界的存在。当人们注意到它并将其纳入了自己的视野时,这个史实瞬间转化为现实,并从可能存在转化为现实存在。
四、天人之辨是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大事
在中国儒家历史上,哪些话题不仅是最重要的而且是最持久的主题呢?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3)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思想史家所言不外乎天人之际和古今之辨。宋儒邵雍曾曰:“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24)邵雍:《观物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天人之际即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儒家学术史的最重要的主题。它不仅是中国儒家思想上的大事情、大问题,而且是贯穿中国儒家思想史始终的老问题,并因此成为中国儒家思想史的基本主题或研究对象。需要澄清的是,这里所讲的天人概念有其特定的含义,即“中国古代学者提出的‘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就今天的科学水平来说,这个问题当然不见得怎么复杂,不过是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已”(25)李锦全:《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关系”问题──兼与刘节先生商榷》,《学术研究》1963年第3期,第8页。。本文所讨论的天人关系中的天主要指以天空为主的自然界,人主要指人类及其所创造的文明。换一句话说,天人关系说主要探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
从中国古代文明思想体系来看,探讨天人关系无疑是天大的事情。天人关系理论所反映的问题,说到底乃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它不仅包括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人类如何与自然界相处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同时直接关注人间事务,即,人类事务究竟由谁来做主?在早期的古人看来,天主宰宇宙间的一切,包括人类事务。天不仅是人类的主宰,而且是宇宙万物生存的主宰。人类只能够听命于天。这便是天命。天命观不仅直接决定人的生死寿命,而且涉及人间事务和人类事务,比如朝代的产生与更迭。《诗经》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26)孔颖达:《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22-623页。不仅商朝的出现出于天意,而且后来发生的诸多事实也是受命于天。天是人类历史事件的主宰者。
从政治角度来看,人类必定是一个群体的存在。群体存在,至少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需要一个领袖来组织这个群体。古人称之为君或王。现代人知道君王出自民主选举,中国古人并不采用这一方式。他们相信天意,认为不仅王朝的更迭决定于天,而且谁作君主也由天定。古人将王称为天子。董仲舒说:“故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复者,有三而复者,有四而复者,有五而复者,有九而复者,明此通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山川、人伦,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故圣王生则称天子,崩迁则存为三王,绌灭则为五帝,下至附庸,绌为九皇,下极其为民,有一谓之三代,故虽绝地,庙位祝牲犹列于郊号,宗于代宗。”(27)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00-203页。天子即苍天的孩子,君王是苍天的孩子,能够通察天意,由君主所主导的政治活动也是出于天意。由此,人们相信天下政治完全决定于苍天,如“文王受命作周也”(28)孔颖达:《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上),第502页。。文王对周朝的治理完全出自天意。从普通人的生活来看,人的生死祸福完全决定于苍天。“天保定尔,亦孔之固;俾尔单厚,何福不除?俾尔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尔,俾尔戬谷;罄无不宜,受天百禄。降尔遐福,维日不足。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29)孔颖达:《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上),第412页。人的祸福决定于苍天。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30)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0页。死生指生理寿命,而祸福则指人间遭遇。这一切,在儒家看来,完全取决于天。在天命观之下,人类只能够听从苍天的安排,从而丧失了主动性与进取心。后来的人们开始反抗这一思想,最终提出“人者,天地之心”的观念,从而主张人类对宇宙万物的主宰地位。人类与天的关系由早期的从命者转身成为天地的主宰者,人类的命运因此发生了革命性的逆转。
因此,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个人大事,真正的决定权,在早期的人们看来,几乎完全掌握在天的手上,天成为人类的主宰之天。天人关系,由于它关乎主宰权的问题,因此是人间的最大的事情。或者说,天人关系说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命运,属于大事情、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对天人关系的论述常常直接影响到个人的生活、国家的命运与人类的前途。这些大问题经由某些思想家的论述,不仅形成了某些观念,而且因此而改变了国家的前途与人类的命运,最终成为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它因此成为中国儒家思想史的主题。
五、天人之辨与中国儒家思想的发展
从中国古代学说史来看,从孔夫子到刘宗周,甚至更早或更晚,天人关系说一直都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在中国文明的初期,人们根据自己的认识,逐步形成了最早的天人观。这种天人观,我把它叫作“天主人从”(31)沈顺福:《天主人从:前孔子时期的天人观及其原因》,《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36页。论。在早期的中国儒家思想家们看来,天地生万物,人类也产生于天。天因此成为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的祖先或本源。按照中国传统的本源决定存在的思维模式,天因此成为人的主宰者。这便是“天主人从”。其表现形式便是天命观的出现与流行。从现有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来看,古人最重要的事情便是祭祀。祭祀的对象主要有三类,即天神、地祇和人鬼,而所谓的地祇和人鬼,其实都与天神相关。人们通常将地祇叫作地神,人鬼之鬼者,归也,是人失去生命力之后的气的形态,这两种气终究归属于天。因此,天依靠神与鬼来管理这个世界,听话的人给予神助,不听话的人派鬼来惩处。古人拜天、拜地、拜先祖等,终究体现了天对人类的主宰性,这应该是人们最初的天人关系观。
从孔子开始(甚至可能更早),一些思想家便开始重新思考天人关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思想家们,一方面依然相信或承认苍天对人类的主宰地位,相信天命;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分别天人的方式,力图减少苍天对人间事务的干涉,从而试图将人类事务的主办权和主宰权逐步交还给人类自己。孔子“不语怪、力、乱、神”(32)杨伯峻:《论语译注》,第82页。,即孔夫子很少谈论鬼神等问题,也很少论及“性与天道”(33)杨伯峻:《论语译注》,第52页。。孔子甚至明确提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34)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29页。事人远比事鬼重要。事鬼即侍奉苍天的“使者”。孟子则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35)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4页。信天不如信人,人类的事务最好相信人类自己。而荀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36)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2),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05页。,自然界的运行有它自己的原理或天道,人类社会运行原理不同于它,人道不同于天道。因此,天人之间要有区别,这便是“天人之分”。既然天人有别,那么人类的事务似乎和天道无关了。从此,在中国儒家思想史上产生了一种新的天人观。它的出现是一种“轴心突破”(37)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0页。,或开启了儒家人文主义的方向。“人一旦被天降生以后,就具有了独立的意义。人要为自己做主,要为自己立法,要证明人的价值和能力,天人相分的意义就在于此。”(38)陈代波:《试论孟子的天人相分思想》,《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天人相分的意义在于为人类寻找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提供了一定的空间,通过分别天人,尽量减少苍天对人事的干预,从而将更多的主动权赋予人类自身。“由主宰之天失落而形成的淡化神论,重人文的思潮,对于先秦天的思想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39)杨泽波:《牟宗三超越存有论驳议——从先秦天论的发展轨迹看牟宗三超越存有论的缺陷》,《文史哲》2004年第5期,第111页。人类自身与人类文明的地位与作用得到彰显,这便是一种儒家人文主义的诞生。
到了两汉时期,思想家们相信天人同类。天有仁道,人也有仁道。人类的仁道和天道一样是绝对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40)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518-2519页。人间的仁义之道因此具有了和天道相类似的性质与地位,天道绝对,仁义之道自然也是永恒而绝对的。这便是汉代儒家对儒家的贡献:它将以儒家仁义之道为代表的人类文明的地位与作用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即天、地、人并为三才而挺立于宇宙世界。“三才说的人文主义面向无疑肯定了人与天、地之地位的相同或接近。”(41)陈来:《儒学论“人”》,《哲学动态》2016年第4期,第5页。因此,汉儒看似尊天,其实是为了崇人,其中的人不仅指人类,而且更指向人的文化。人类及其所创造的文化也是宇宙人类生存的基础性要素,这便是董仲舒的三本说:“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42)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168页。三本说将儒家人文主义思潮推向一个新高度。
从魏晋时期开始,天人观产生了革命性变化,即人们开始形成了万物一体的观念。阮籍说:“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自然一体,则万物经其常,入谓之幽,出谓之章,一气盛衰,变化而不伤。是以重阴雷电,非异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异者视之,则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则万物一体也。”(43)阮籍:《阮籍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15页。大千世界的万物看似纷繁复杂而各不相同,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风雷水火等各司其职、各在其位,其实它们却能够合为一个存在体,此即“万物一体”。至此,天人一体或万物一体观便正式产生。在万物一体视域下,传统的天生万物说便发生了转变。天生万物的他生说便转成自己生自己的自生说:“万物皆造于自尔。”(44)郭象:《庄子注》,《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万物自生说因此而产生。在万物一体体系中,人与天的关系便不再是过去的主从关系了,它们转变为手足兄弟的关系。
到了宋明时期,“万物一体的命题……又几乎为理学家所普遍认同”(45)杨国荣:《仁道的重建与超越──理学对天人关系的考察及其内蕴》,《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第65页。。如张载说:“造化所成,无一物相肖者,以是知万物虽多,其实一物;无无阴阳者,以是知天地变化,二端而已。”(46)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0页。世上万物繁多,却最终统一于一物,这便是万物一体说或天人一体论。二程亦明确指出:“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47)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1页。天地万物与人类之间本无分离,二者本来便是一体的,这便是天人一体。胡宏说:“合以义,正合也,理不得不合也。不得不合而合,天与人一矣。合不以义,苟合也,君子不为也。”(48)胡宏:《胡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9页。这是说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即包括苍天在内的万物与我合为一体。朱熹继承了张载和二程的天人观:“天便脱模是一个大底人,人便是一个小底天。”(49)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26页天地万物如同一个人,天人是一个整体的生命存在。王阳明提出:“仁者以万物为体:不能一体,只是己私未忘。”(50)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仁者以万物为一体,或者说,在儒者看来,天下万物是一体的。一体便是贯通,贯通便是仁。在仁学视域下,万物贯通一体,既然贯通一体,人与人之间便如同手足而自然亲爱。
理学家的贡献不在于万物一体说,而在于重新确定了宇宙万物的主宰者。理学家相信宇宙万物合为一个生命体。对于生命体来说,本源是其基础,更是其决定者。这个决定者,宋明理学家们称之为“天地之心”(51)关于“天地之心”的起源及其内涵的演变史,参阅沈顺福:《“天地之心”释义》,《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4期,第28-34页。。从本源决定论来看,天地之心便是宇宙的决定者。在儒家看来,这个作为决定者的“天地之心”,便是“仁”:“仁、义、礼、智,皆天所与之良贵。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统四者,所谓元者善之长也,故曰尊爵。在人则为本心全体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无人欲陷溺之危。”(52)朱熹:《孟子集注》,《四书五经》(上),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1988年版,第25页。仁或仁义礼智等便是天地之心,而仁便是人道、是人。因此,以仁为心其实便是以人为主。朱熹曰:“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谓人者天地之心也。”(5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2243页。人类及其人文活动比如教化便是天地万物生存的主宰。王阳明提出:“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54)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79-80页。万物一体,人便是这个生物体的主宰(“心”)。传统的天命观认为苍天主管人类,而现在,即便是苍天也必须接受天理或良知的安排。天理或良知正在人的心中。至此,人类借助于其心中的良知而翻身成为宇宙的主宰,并最终实现了“以人统天”(55)张学智:《论王阳明思想的逻辑展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89页。的理想。在长达数千年的天人争权中,人类终于掌握了话语权,不仅成为自身的主宰,而且成为宇宙的主宰,从而确立人类在宇宙中的主导性或主体性地位。此时的人不仅是自然人类,而且包括人文文化。人类正是借助于对抽象天理的追求等人文活动,最终成为宇宙的主宰者。
结语:儒家人文精神的形成
从重要性与继承性来看,天人关系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儒家思想史的主题。天人关系史,表面上体现了人类与天地自然之间的关系史,其实反映了人类对自己的认识。在最初阶段,人类不太相信自己,以为在自己之外还有一种力量主宰着人间事务。从孔子时起,人们逐步自信,逐步相信人类的事务应该交由人类自己来解决。到了宋明时期,人们甚至提出“人者,天地之心”的观点,以为人类才是宇宙世界的主宰。这一命题是孔子思想发展的必然结论,或者说,这便是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理论学说的最终归宿。这一学说的最大贡献是突出了人类主体性,即在人类与其他种类的关系中,人类具有主导性、主宰性和决定权。人类不但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且能够决定宇宙万物的生存,或者说,在宇宙中,只有人类才是真正的主宰者,这便是人类主体性。人类主体性区别于以个人自由意志为核心的个体主体性,对后一个主题即个体主体性等,传统儒家选择了无视。传统儒家的重心放在人类的命运上。人类主体性便是人类存在的起点。儒家思想史便是一部人类主体性得以产生、弘扬与彰显的人类思想史,我们把这一思潮叫作儒家人文精神。儒家人文精神的最大贡献在于突出了人类主体性,并因此而区别于西方文化传统。同时,当西方人面对人与上帝的关系时,突出人类主体性的儒家人文精神完全可能对西方人思考人神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并由此而促生现代文明。或者说,西方文明中的人类主体性意识,可能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人类主体性思想有着莫大的关联。当西方人接触中国文化时,他们最惊讶的便是天人关系。“早期中国的基督教创始人利玛窦,允许人们用两个汉语即‘上帝’和‘天’来表达耶和华的‘上帝’。但是他自己却用天主一词。后来的传教士们对这种翻译有些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些汉语有其自身的内涵,且这些内涵明显与基督教的神概念不一致。不过,这些后来的传教士也逐渐接受了利玛窦的用法,即将天主一词当作天主教神概念的官方术语。”(56)Daniel J. Cook and Henry Rosemont Jr., Introduction,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Writings on China,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94,p.3.中国的天人关系类似于西方人最关心的神人关系。中国人的天人观应该对西方人思考神人关系有些启发。这可能是以儒家人文精神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思想的重要贡献。
——以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