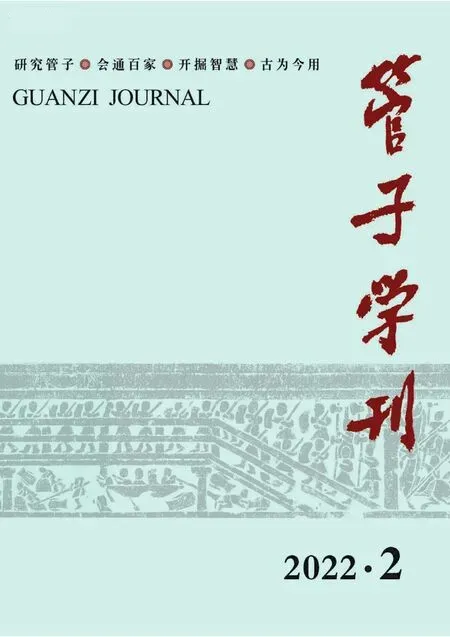走向“天的人化”:人学视域中的天人之辨
——从“类型说”与“阶段说”的困难谈起
张 恒
(山东社会科学院 国际儒学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02)
近代以来,在捍卫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中,“天人合一”逐渐成为标举中华文化殊胜之处的重要命题。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环保问题的凸显,“天人合一”又逐渐被赋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内涵。这些理解固然使天人合一观念具有了崭新的现实内容与实践意义,但也与其历史存在产生了一定错位。近年来,这种错位引发学界不断思考,相关研究从空间、时间等维度对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天人合一、天人之辨及相关问题展开细致分疏与严肃探讨,使之在思想史的发展演变中有了或清晰或模糊的定位。不过,这些研究或重视空间维度亦即类型划分,或重视时间维度亦即阶段划分,总还有些欠缺,其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派、不同思想家的天人观的自洽与互洽的解释效力也因此打了一些折扣。从根本上说,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一种新的整体性视角,透过这一视角,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天人之辨应当能够清晰展现自身发生、发展的逻辑线索、脉络及其背后的价值意涵。对这一新视角的探寻与应用构成了本文的主要任务。
一、“类型说”与“阶段说”:两种诠释思路及其困难
“天人合一”一语首见于北宋张载所作《正蒙》(1)张载言:“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参见张载:《张子全书》,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其20世纪以来的流行和标举则与学界对中国哲学、中华文化的评价、反思密不可分。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曾从反思角度提出,“中国哲学迄未显著的将个人与宇宙分而为二”,这种天人合一观导致狭义知识问题未能像在西方哲学中那样成为中国哲学的大问题,故而需要重建(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9页。。金岳霖1943年写就的英文论文《中国哲学》(ChinesePhilosophy)则更多从肯定角度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点”(3)金岳霖著,钱耕森译,王太庆校:《中国哲学》,《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第40页。。金文先是经冯著《中国哲学简史》英文版介绍,引起西方哲学界关注,后于1980年在国内正式刊发,成为学界围绕天人合一等问题论辩争鸣之滥觞(4)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71页。。论辩争鸣的高潮由钱穆促成,他在1990年的遗稿中“彻悟”,“天人合一”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5)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国文化》第4期,第93页。。对此,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论辩争鸣不断走向深入,迄今不衰(6)关于论辩争鸣的情况,刘笑敢曾做过梳理与分析,详见刘笑敢:《天人合一:学术、学说和信仰——再论中国哲学之身份及研究取向的不同》,《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67-85页。。
总的来看,以往关于天人合一、天人之辨诸问题的研究展现出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间或二者兼而有之。
所谓空间维度的研究,是指以“切片”方式对天人合一、天人之辨诸问题作横向剖析,其具体表现为类型划分,相关观点可概而言之“类型说”。“类型说”可笼统分为两类。一类观点将天人合一视为中国古代天人观的基本类型,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归宿或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如张岱年提出,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从先秦至明清大多数哲学家都宣扬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独特观点,它可分为两类——发端于孟子的“天人相通”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相类”(7)参见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第1页;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3页。。宋志明也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处理天人关系的基本思路,并将其划分为天人玄同、无以人灭天、天人相通、天人相交、天人相与、天人同体、天人一气、天人一理、天人一心等九种类型(8)宋志明:《论天人合一》,《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4期,第56-58页。。“类型说”的另一类观点注意到,天人合一只是中国古代天人观的形态之一,而非全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派、不同思想家往往秉持不同的天人观。如张岱年指出,老子哲学就不涉及天人合一问题,荀子“天人之分”、柳宗元“天人不相预”、刘禹锡“天人交相胜”等观点也都是不讲天人合一的典型(9)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第3-4页。。还有学者细致地指出,即便是同一位思想家也可能主张多种天人观,如孟子不仅有天人合一思想也有深刻的天人相分思想,荀子既强调天人相分也坚持辩证的天人合一观(10)参见陈代波:《试论孟子的天人相分思想》,《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66页;宋志明:《论天人合一》,《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4期,第57页。。
时间维度的研究则是从历史视角对天人合一、天人之辨诸问题作纵向梳理,其具体表现为阶段划分,相关观点可概而言之“阶段说”。“阶段说”也可笼统分为两类。一类观点在主张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天人观基本形态的前提下,进一步阐明天人合一的历史流变。当张岱年提出“天人相通”观念发端于孟子而大成于宋代道学,当李泽厚提出天人合一在先秦、汉代、宋代分别表现为人认同天、天人相通、伦理本体与宇宙自然相通合一(1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96-297页。,当章启群提出天人合一历经上古天地祖先崇拜、殷商天命思想、周朝以德配天、思孟董仲舒天道人道一以贯之、宋代道学天理人性相统一诸阶段(12)章启群:《“天人”如何“合一”?——用思想史的逻辑推演》,《哲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49-55页。,其中都隐现着历史的眼光。“阶段说”的另一类观点则进一步扩大视野,将天人合一视为中国古代天人之辨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即古代天人观的形态之一。如沈顺福提出,儒家天人观历经初期“天主人从”、先秦“天人相分”、汉代“天人相副”诸阶段后,至魏晋正式形成“天人一体”观念,并在宋明以“人者天地之心”的形式臻于成熟,此间天人关系由早期的顺天由命发展到人类主导天地(13)沈顺福:《天人之辨与儒家人类主体性意识的形成》,《江淮论坛》2019年第3期,第104-109页。。这实则将天人合一、天人之辨诸问题置于思想史逻辑发展的脉络之中进行考察。
作为两种基本诠释路向,“类型说”与“阶段说”诸观点通过各自视角的考察,多侧面刻画出了天人之辨在历史中的类型与流变,使相关讨论摆脱了浮泛之谈,进入了严肃的学理探究。从单一视角来看,这些研究中的大多数成果都能成立,有些剖析还相当细致、精彩、启人深思。但若整体概观,这些研究仍有尚待完善之处。一方面,“类型说”固然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派、不同思想家乃至同一思想家身上可能存在的多种天人关系形态做了细致的切片式剖析,但有时也疏于考察这些形态之间有无关系、是何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古代天人之辨图景的支离。以孟子为例,如果既可以说他主张“天人合一”也可以说他主张“天人相分”,还可以说他同时主张“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这不仅使类型划分失去了意义,还有可能导向逻辑谬误。另一方面,“阶段说”虽然大都能从历史流变视角对天人之辨作细致梳理,但有时也疏于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天人关系形态有无关系、是何关系,进而可能失去对个别形态的解释效力,比如当荀子以“天人相分”的面目进入天人之辨的历史,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元素就难以得到合理解释。“类型说”与“阶段说”面临的这些困难需要解决。
二、人学视域的敞开:“类型说”与“阶段说”的统一
天人之辨相关问题研究中的“类型说”与“阶段说”,一侧重于类型划分,一侧重于历史梳理,多数观点有其道理,问题主要在于其在更大范围内解释效力的不足。理论上说,“类型说”在时间之维上的不足似可通过引入“阶段说”得到一定弥补,“阶段说”在空间之维上的欠缺似亦可通过引入“类型说”得到一定修正,也就是说两种诠释思路可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一言以蔽之,他们需要整合或统一。但这种整合或统一不是简单相加,也不是否弃已有研究,而是找到一个新的逻辑起点——对天人之辨的历史存在与流变有更强解释效力的逻辑起点,从这一起点出发,已有研究中的抵牾应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解决。
新的逻辑起点关涉定义。纵观两种诠释思路下莫衷一是的观点,它们在起头处便展现出了对天人之辨诸概念如“天”“人”“合”“分”等千差万别的理解。就“天”而言,有学者提出“天”有物质之天、主宰之天、运命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五种含义(1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45页。,有学者主张“天”有最高主宰、广大自然与最高原理三种含义(15)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第1页。,有学者认为“天”有命定、主宰义与自然义双重含义(1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295页。,有学者强调“天”作为超越世界的超越性(17)余英时:《中国思想的特点:天人间的内向超越性》,《东方早报》2014年7月2日。,还有学者将“天”视作一个可以被经验的物质的苍天(18)沈顺福:《诠“天”》,《管子学刊》2018年第3期,第61-70页。,等等。“人”的内涵相对确定,但也可指人类或某些群体(如君主)、人类社会或其组织形式(如政治、伦理)、人类行为、人类文化、人类文明等。至于“天”“人”之间的关系如“合”“分”等,更是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合”指内在相即不离的有机联系(19)汤一介:《论“天人合一”》,《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2期,第10页。,有学者认为“合”指息息相通、融为一体(20)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还有学者认为“合”有符合、结合之义,与现代语言中所谓“统一”同义,指对立的两方彼此又有密切相联不可分离的关系(21)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第1页。。“分”可以指“人”与“天”各行其是、互不相干,也可以指“人”能违背天意,还可以指“人”认识、利用“天”来为自身服务。
天人之辨所涉诸概念展现出丰富内涵的同时,也带来了阐释的困难与理解的分歧,这构成了“类型说”与“阶段说”观点多样且有所抵牾的重要原因。不过,这些理解虽各各不同,却也并非非黑即白,一些看似对立的观点实则都有道理,在各自视角下均能成立。为使皆有道理的各方摆脱盲人摸象、自说自话的窘境,有必要对天人之辨所涉诸概念作出新的界定,这就需要新的视域。
马克思·舍勒说,人是什么以及人在存在、世界和上帝的整体中占据何种形而上学的位置,亦即“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是哲学所有核心问题的最终归宿,也是一系列老一代思想家所确认的一切哲学课题的出发点,当今全部哲学都被这一问题的内涵渗透浸润着(22)[德]马克思·舍勒著,魏育青、罗悌伦等译:《哲学人类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6页。。这一基于哲学人类学视域的发现同样适用于对中国思想史的理解,“人的本质”或“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二者实为一枚硬币的两面——正具体展现为天人之辨。司马迁曾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说法,这往往被视为中国古代较早关于天人之辨的学术自觉,它不仅是对同时代董仲舒“天人之际,合而为一”(23)董仲舒:《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69页。观念的回应,更是对西周以降所谓“轴心时代”以来“文明的突破”中思想主题的精炼总结,同时还启示了接下来两千年的思想史叙事。而从各历史时期、各学派、各思想家通过对举“天”“人”而对“人”所下的一系列定义来看,天人之辨正构成中国古代“人”的问题的思考背景。可以说,天人之辨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基本问题与主要线索,其目的是不断揭示“人的本质”并逐步提升“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当然,作为思想史基本问题的天人之辨在中国与其在西方是以不同的形式展开的。西方对“人”的理解范式可归结为神学的、哲学的与科学的几类。就“哲学的”范式而言,从古希腊哲学经笛卡尔到德国古典哲学,理性逐渐被确立为“人的本质”,人之为人是因为人有理性,而理性的发现主要是基于或围绕认识论展开的,在此过程中,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亦即所谓主客二分便是一种隐含的预设。或许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少学者将中西方在天人之辨问题上的思维特征作对立看待,因为表面看来主客二分与天人合一正相反对。事实上,中西方在天人之辨问题上的思维特征并不构成对立,这倒不是说他们一致,而是因为范式不同。尽管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理性”的觉醒,但此“理性”非彼“理性”,它从来没有预设也几乎没有实现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因此并不基于认识论尤其是狭义知识论而展开,对此冯友兰早已有敏锐发现。
中国古代天人之辨毋宁是生存论与价值论的。从思想史来看,先民所关心的始终是“人”的生存问题——如何生存下来、如何与禽兽相区别、如何处理人性与秩序的关系,如此等等。而“天”,更多只是解答“人”的生存问题的参照系,如果“天”“外在于”“人”,“人”就要将其“内化”,最终实现“天的人化”。由此,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天人之辨自从上古时期“以天释人”形态中“突破”出来以后,便进入漫长的“以人释天”的探索进程,这个进程始终朝向“天的人化”亦即“人即天”的终极目标,“人”最终要将自身法则或秩序确立为“天”的法则或秩序,此即宋儒所谓“为天地立心”境界,亦即明儒“天地万物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之精义所在。
在人学视域下尤其是在生存论视角下,中国古代天人之辨便不是一成不变的单一形态,其在历史中的形态也并非各自孤立、无章可循,而是呈现为逻辑演进的动态发展过程。基于此,对天人之辨所涉诸概念的界定需要遵循这样几个原则:首先,必须承认“天”“人”之间的相关性,尽管“天”作为标定人的本质、地位的参照系而存在,但“天”“人”之间的相关性是真确存在的,这也是天人之辨问题得以成立的前提;其次,必须保持天人之辨所涉诸概念在思想史上的开放性,亦即承认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派、不同思想家的运思差别,由这种“开放性”所决定,很难对天人之辨所涉诸概念给出实体性定义,最佳方法是给以功能性定义;最后,必须对天人之辨有所言说,承认千差万别的理解背后有某种统一性。
基于上述原则,不妨暂将“人”定义为人类及人为,将“天”定义为与“人”并存的宇宙主宰的竞合对象,“天”既可外在于“人”而又可按照某种规则内在于“人”,与“人”结成某种统一体。“天人之合”的总体倾向是“天”“人”共同分有宇宙秩序、规则的主宰权,不过它具有多阶性:低阶之“合”以“天”的规则为宇宙规则,高阶之“合”则以“人”的规则为宇宙规则。“天人之分”的总体倾向是“人”向“天”争夺宇宙秩序、规则的主宰权。这实际上形成了关于天人之辨所涉主要概念的广义界定,这种界定广泛包容思想史上各种观点的差异性,但不至于导向混乱,因为它预设天人之辨的人学指归尤其是生存论指归,即无论天人之辨的形态如何演进,它始终朝向人对自身力量与本质的发现,朝向人在宇宙中地位的提升,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类型说”与“阶段说”的困难。
以人学为视域,以“类型说”与“阶段说”的统一为基本运思方法,中国古代天人之辨的演进脉络便逐渐清晰起来,它整体上呈现为“合—分—合”的发展进程,这不是简单的重复与回环,而是具有“正题—反题—合题”性质的逻辑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由合而分”与“由分而合”的两次转折尤为关键,它们基本上可以勾勒出整个进程的脉络,下文尝试以儒家思想为主线,在具体分析中予以阐明。
三、走出“天即人”:从混沌到觉醒
雅斯贝尔斯以“轴心时代”标定人类文明早期的首次“突破”,如果不考虑他所赋予的“超越的突破”这一具体内涵,而是从更宽泛的“文明的突破”角度来理解,周朝的确可算作中国古代文明的“轴心时代”,天人之辨逻辑演进的首次转折便发生于这一时期。
已有不少学者指出,上古及至商朝的宗教信仰以祖先崇拜与上帝崇拜合一为主要特征,祖先或上帝不在别处,正在“天”上,《山海经》及上古岩画等资料都表明了这一点(24)有学者指出,中国上古时期鬼观念的核心是先以“帝”作为全族抑或全部落、所有人的代表,他永生于天上,后来渐渐把本家族的祖先也依附于帝而置于上天,虽然在人们的现实视野里人死之后确实归于土,但在信仰中还是执拗地认为先祖仍活在另一个世界里,这“另一个世界”的具体所在,一般认为是在天上或山野间。参见晁福林:《先秦时期鬼、魂观念的起源及特点》,《历史研究》2018年第3期,第7页。。“天”是上帝及“人”的祖先之所在,可以佑护“人”的生存与延续;“人”要想获得这种佑护,就必须通过巫术礼仪与“天”对话,向上帝与祖先祈福避祸,《墨子》《吕氏春秋》等所载“汤祷桑林”(25)《吕氏春秋·季秋纪·顺民》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剪其发,故磿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则汤达乎鬼神之化、人事之传也。”参见陆玖译注:《吕氏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53页。传说便生动记述了这样的情形。在这种互动中,“人与神、人世与神界、人的事功与神的业绩常直接相连、休戚相关和浑然一体”(26)李泽厚:《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页。。“人”融身于世界,但对世界无甚认知,对自身命运无甚觉解,只是、只能将命运系于“天”,“天”的意志决定了“人”的生存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天即人”,此即中国古代天人之辨最初的、作为“正题”的“天人之合”,当然这与后来作为“合题”的“天人之合”明显不同,后将详述。此种“天人之合”,不妨暂称之“天人杂糅”——这一用法亦可在“绝地天通”事件中找到依据。
作为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史研究重新“发现”的“思想史事件”,“绝地天通”在文献上最早见于《尚书》,是周穆王命人制定刑法时引述的一则神话传说(27)《尚书·周书·吕刑》载:“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刖、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参见郭仁成:《尚书今古文全璧》,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308-310页。。《山海经》亦提及这一传说,而这一传说首次得到详细解释是在《国语》楚昭王与观射父的对话中(28)《国语·楚语下》载:“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参见左丘明:《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76-378页。。周穆王、《山海经》与观射父的叙述略有不同,但总的来看,“绝地天通”传说对应的历史背景当是上古时期一次对苗民叛乱的镇压与政治秩序的重建,即蚩尤作乱以后,苗民社会滥用酷刑、滥杀无辜,颛顼怜悯受苦的苗民,于是发用威力,惩处暴虐,并命令南正重管理天以属神界、任命火正黎管理地以属民界,使天与地、神与民隔绝开来,以恢复人间秩序。此间,天人之辨是贯穿其中的重要线索:“绝地天通”之前,蚩尤作乱、九黎乱德,人人祭祀、家家作巫,民神杂糅、任意通天,这正是上文提到的“天人杂糅”状态的形象展现。从政治视角来看,“天人杂糅”导致神权与王权的分散,进而导致治理上的困难;而从人学视角来看,“天人杂糅”使“人”蔽于“天”而无心、无力认识外部世界、觉解自身命运,普遍处于蒙昧之境。故而,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都必须通过“绝地天通”方式切断“天”“人”之间的普遍联系,抑制“通天”之权的泛滥。固然,在政治或信仰层面或仍有“通天”之权的遗留,但就社会一般层面来看,“通天”之权的确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抑制,家家作巫、任意通天的状况不复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观射父认为“绝地天通”事件“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即人间秩序从“民神杂糅”状态“恢复”为“民神不杂”状态,其中所谓“恢复”并不符合人类学常识,“民神杂糅”之前并没有一个“民神不杂”的时期,这只是观射父的想象。“民神杂糅”或“天人杂糅”就是原始文明早期的普遍情形,是中国古代天人之辨的“正题”(29)陈来等学者已注意到这一问题。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4页。。
以“绝地天通”为主要标志,中国古代天人之辨进入了“反题”(30)这并非说“绝地天通”是一个确切的时间节点,而毋宁是一个醒目的思想史标识。。尽管“绝地天通”并非真实的历史事件,却真实反映了讲述者所处时代的思想观念(31)黄玉顺:《绝地天通——天地人神的原始本真关系的蜕变》,《哲学动态》2005年第5期,第8-11页。。具体而言,“绝地天通”反映了西周前期(周穆王所处时代)至春秋后期(楚昭王、观射父所处时代)要求人间秩序从“民神杂糅”转向“民神不杂”、从“天人杂糅”转向“天人相分”的普遍观念,“轴心时代”及稍后的几位重要思想家如孔子、孟子、荀子等都鲜明地展现出了这一思想面向。
当前学界一类观点主张,“天人合一”观念正式形成于先秦尤其是周朝,这主要体现在当时天人相通、会合天人之道、以德配天等观念中(32)认为“天人合一”观念形成于先秦者,张岱年、汤一介、张世英等学者皆是代表。如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中所谓“天人合一”有两种含义:一天人相通,二天人相类。天人相通的观念发端于孟子,大成于宋代道学;天人相类则是汉代董仲舒的思想。参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173页。汤一介认为,根据现在能见到的资料,《郭店楚简·语丛一》“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是最早最明确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表述。参见汤一介:《论“天人合一”》,《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2期,第5页。张世英认为,“天人合一”思想在西周的天命观中已有比较明显的萌芽,周公提出的“以德配天”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明确表达。参见张世英:《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求是》2007年第7期,第34页。。的确,当孔子说“畏天命”(3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1页。、“知天命”(3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56页。时,似乎承认“天”(天命)对“人”(人的命运)起着某种主宰、控制或至少是影响作用;当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3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27页。,似乎“人”(人心、人性)与“天”具有某种一致性或至少相通;当荀子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36)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15页。,“人”(人性)甚至是“天”所造就的;当董仲舒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以类合之,天人一也”(37)董仲舒:《春秋繁露》,第445页。以及“人副天数”“同类相动”,似乎“天”真是“人”的曾祖父,“天”“人”之间相感相应,不可遽分。总之,这些言说确乎展现了“天”“人”之间的某种贯通性乃至一致性,它集中体现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或“天命之谓性”的“性命”原则。
但是,从人学视域来看,“性命”原则所提示的“天”(天命)与“人”(人性)的贯通或相合只是周朝以降思想家的“神道设教”,即他们在为“人”寻找道德上的本原与根据时,“天”作为上古思想遗存承担了这一功能。庞朴甚至认为,能降命的天和天所降的命并没有什么具体面目,不主张什么也不反对什么,只是虚晃一枪,为“性”的出场鸣锣开道而已(38)庞朴:《天人三式——郭店楚简所见天人关系试说》,《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这一观察是敏锐的。实际上,正如当时思想家们所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39)郭仁成:《尚书今古文全璧》,第150页。,“天何言哉”(4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68页。,“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41)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10页。,“天”既不能视听,也不能言动,真正视听言动者是“人”。
可见,“天”固然还有些神学色彩的遗存及其在道德伦理领域的转换,但它毕竟不同于“天人杂糅”时期了,“人”在“天”以外发现了新的影响乃至决定自身命运的力量,或者说“人”从旧式“天即人”状态中走出来了。所以,孔子罕言天道,“不语怪、力、乱、神”(4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95页。,对于鬼神、生死之事亦有所保留,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4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19页。。鬼神、生死之事都与“天”密切相关,是“天”及其威力的具体化,孔子不明确肯认,而是搁置不论,并开始重视与其相对的“人”“生”之事,正展现出了与天相分的思想面向。孟子言“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4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60页。,“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4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19页。,并援引《诗经》“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及《尚书》“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等论述,强调“反求诸己”“自己求之”亦即“人”在“天”面前的能动性,“人”不仅可以自求多福,必要时还可以违背天意,“人”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荀子更不待言,“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46)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01、310页。已是非常明确的与天相分、利用天命的思想观念,“人”不仅与“天”分立、分职,而且可以通过对“天”的认识与把握来造福自身,其中已蕴含一定的认识论观念的萌芽。这些观念尤其是荀子的观念后被董仲舒大加发挥,他直言:“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47)董仲舒:《春秋繁露》,第646页。论地位、论能力,人可与天地比肩。
如此一来,尽管孔、孟、荀、董有天人相关、相通乃至一致的思想面向,但这并非他们思想体系的全部,甚至很难称得上是主要倾向,而更应视为对原始宗教思维的继承与转化。这种转化背后“与天相分”的思想倾向才是这些思想家的真正创见。总之,从结果来看,这一时期的天人观似乎又分又合、若即若离,其实质则是趋于相分,只是分而未得。这种状态或可借鉴荀子的说法,称为“天人有分”,“分”是职分。与上古时期混沌的“天人杂糅”相比,“天人有分”观念彰显了人对世界的一定认识与对自身命运的一定觉解,人的地位得到一定提升。
四、走向“人即天”:人的自决的实现
“轴心时代”以降,天人观整体上趋于相分,但此间始终有一无形的“束缚”,那就是“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或“天命之谓性”的“性命”原则。这一原则的存在使“人”总还是处于“天”的影响之下,尽管这种影响已缩小为“神道设教”的性质。如何进一步发现“人”的力量、摆脱“天”的主宰,便成为魏晋时期重要的思想主题,这一主题在长期政治分裂与社会动荡的现实中又展现为自然与名教之辩。魏晋玄学对先秦两汉的解决思路予以扬弃,通过对“名教即自然”的确认使“天”收摄于“人”,逐步走向“人即天”。
道家老庄思想的复兴以及佛学的传播促使魏晋玄学的思考展现出了思辨性,尤其是在天人之辨问题上,玄学家已不满足于经验性追问,试图给出思辨性答案。作为这种追问的理论前提,玄学家首先完善了“天”的定义。王弼说:“无所不周普,则乃至于同乎天也。”(48)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0页。“天”是无所不周普的、包罗万象的、至大无外的存在。而此前在董仲舒那里,“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毕之外,谓之物”(49)董仲舒:《春秋繁露》,第646页。,“物”并不在“天”之内,其宇宙化生图式看似繁复,实则尚未形成整全世界的观念。相比董仲舒的列举式定义,王弼的解释展现出了对世界整全性的认识。郭象更是直接提出,“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50)成玄英:《庄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页。,“天者,万物之总名也”(51)成玄英:《庄子注疏》,第26页。,这就确立了以“天”为代称的整全世界观念。
“天”越来越整全,其地位却进一步下降。王弼以“崇本举末”思维追问整全世界之本原,他说:“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也。物有往来,而执之,故必失矣……圣人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乱而物性自得之也。”(52)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第78页。作为万物之“本”的“性”不再直接是“天”,而是“自然”。这里的“自然”也不再是老子哲学意义上与人无涉、无关道德的“自然”,而是具有人间秩序的意味。王弼说:“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义可显,礼敬可彰也……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所成也;礼敬之清,非用礼之所济也。”(53)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第99页。“无形”“无名”即是“自然”,只要一任“自然”,仁义礼敬自可彰显,一任“贞”“诚”,仁义礼敬便厚重清正。既然仁义礼敬出于“自然”,“自然”因此具有了先天性与道德性,这正是儒家“德性自然”观念的另一种表达(54)张恒:《儒门内的王弼——对王弼哲学派别归属的一个阐明》,《孔子研究》2019年第2期,第126-135页。。如果说王弼有些欲说还休,郭象则把这种新的天人观清楚明白地讲出来了。郭象说:“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55)成玄英:《庄子注疏》,第26页。万物并没有一个共同的生成本原,每一物都是块然自生。尽管郭象仍将这种“自己而然”称为“天然”,但他明确表示,这只是为了强调万物自生的权宜用法,所谓“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岂苍苍之谓哉”(56)成玄英:《庄子注疏》,第26页。。“天”不是“苍苍之谓”,而是“万物之总名”,或说是一种“承诺”,其实质是万物,“物无非天也”(57)成玄英:《庄子注疏》,第126页。。反映在自然与名教之辩上,郭象认为:“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马乎?服牛乘马,可不穿落之乎?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58)成玄英:《庄子注疏》,第321页。在庄子哲学中,牛马四足是“天”(自然),“落马首、穿牛鼻”是“人”(人为);但在郭象看来,正因“落马首、穿牛鼻”是“人”,所以它便成了“天”。从王弼到郭象,名教与自然之辩逐步由“名教出于自然”走向“名教即自然”,天人之辨也逐步由旧式“天即人”走向“人即天”,这既是对秩序的渴望,也是对自身命运的进一步觉解。
玄学天人观的再度趋合,已不同于上古时期的混沌冥合,而是贯穿着鲜明的人类主体意识,因此这实际上正在走向中国古代天人之辨的“合题”。尽管玄学的思考具有一定思辨性,也在天人之辨问题上有进一步发展,但在佛道宗教面前,这些思考的思辨性仍嫌不足,经验性的“人”(“名教”)显然无法承当思辨世界的本原与主宰。如何在思辨意义上确立“人即天”的有效性,便成为留给宋儒的思想课题。
同玄学家一样,理学家普遍重视天人之辨,尤其强调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以其为本原追问的理论前提。张载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这是有史记载首次对“天人合一”命题的明确表述,还说“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59)张载:《张子全书》,第53页。,以天地之塞为体、以天地之帅为性,民胞物与,这些阐释形象而又生动。邵雍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60)邵雍:《邵雍全集》(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3页。,“事无巨细,皆有天人之理”(61)邵雍:《邵雍全集》(三),第1232页。,这都是对贯通天人的强调。周敦颐虽无明确表述,但他通过《太极图说》阐述的宇宙化生图式也隐含着万物一体观念。嗣后,程朱陆王深化了这一观念,如二程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62)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79页。,“仁者,浑然与物同体”(63)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6页。,朱熹说“天地万物本吾一体”(6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0页。,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65)陆九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3页。,王阳明说“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66)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页。。
理学家承认,在天人合一或谓万物一体的整全世界中,天地万物一气流通,这与先前中国本土哲学的思考一脉相承。但理学家也意识到,以“气”为本原或介质的“一体”或“相合”难以经受佛教的考验,这也正是玄学经验性的“人即天”观念面临的困难。早期理学家吸收借鉴佛教的“体相用”思维并将其创新发展为“体用”思维。在“体用”思维框架下,先前经验性的“性”被更加细致地分为两重:一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一为气质之性;一为天理,一为气质。在理学家看来,“人性”本然、实然、应然地是“天理”:“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67)程颢、程颐:《二程集》,第292页。“性即理”言简意赅地指出了人性与天理的一致性、统一性,也创造性地将具体的“德性”形式化为普遍的、超越的“天理”,“天理具备,元无欠少,不为尧存,不为桀亡”(68)程颢、程颐:《二程集》,第43页。。“性即理”的超越性使“人即天”在逻辑意义上得以成立。从人学视角来看,这无疑是玄学“名教即自然”观念的高阶发展,无怪乎朱熹要对“性即理”命题大加赞佩,称其为“千万世说性之根基”,并认为孔子之后无出其右者(69)朱熹:《朱子语类》(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60页。。
理学在中后期发展中进一步提出“心即理”,并将良知确立为“心”的“本体”,良知即心、即性、即理。良知最重要的特征是“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70)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第7页。超越的“天理”并非真的由“天”给出,而是人性、人心本然蕴含的。人心、良知由此成为世界的决定者、主宰者。朱熹说“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7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0页。;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72)陆九渊:《陆九渊集》,第483页。;王阳明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73)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第122页。,“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74)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第141页。。天地鬼神万物或说人身处其中的世界全都仰仗“人心一点灵明”,这一点灵明为宇宙提供了“生存之道”,人类由此成为宇宙秩序与规则的制定者、给出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即天”,人真正实现了命运的自决。
结语
20世纪以来,天人之辨问题被反复提出、论辩,足见其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重要性。在现代语境中,天人之辨往往被解释为生态伦理问题,“天人合一”被视为中国文化相较其他文化形态的殊胜之处,这些融入了现代观念的理解与天人之辨的历史存在有明显错位,这种错位引发了学界的深入思考。笼统而言,相关研究主要展现为两种进路:一是主要从空间之维立论的“类型说”,一是主要从时间之维立论的“阶段说”,其分疏之条理、研辩之精细,每每启人深思,然而在解释效力上仍嫌不足。通过考察中国古代儒家天人之辨的发展演变可以发现,“究天人之际”的重点在人而不在天,其终极诉求是不断揭示人的本质并提升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天人之辨基本不涉及认识论问题,也不应视为完全的宇宙论问题,而更多是关乎人的生存与价值的人学问题。
以人学为视域,以“类型说”与“阶段说”的统一为基本运思方法,以儒家为主要线索的中国古代天人之辨便整体呈现为“合—分—合”的发展进程,这不是简单重复与回环,而是具有“正题—反题—合题”性质的逻辑进程。此间,“由合而分”与“由分而合”的两次转折尤为关键:第一次转折以“绝地天通”为标志,先民从上古“天人杂糅”的蒙昧状态中觉醒,摆脱“天即人”的低阶相合;嗣后,先民不断发现自身力量,觉解自身命运,促成了第二次转折,其完成以“性即理”“心即理”相关命题的提出为重要标志,实现了“人即天”的高阶相合。从“天即人”到“人即天”,天人之辨的逻辑进程始终伴随着人对自身力量的发现,始终朝向人的独立与自由。对天人之辨人学意义的发掘,应成为今天理解、继承、发展古代儒家思想的重要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