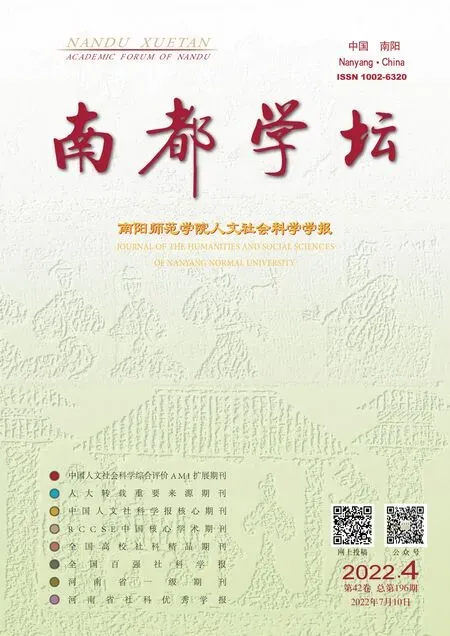《汉书》民族书写与班固的民族思想
刁生虎, 弓少潇
(中国传媒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24)
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继承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民族书写传统,设立《匈奴传》上下、《西域传》上下、《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等5篇少数民族列传,并在《李广苏建传》《卫青霍去病传》《司马相如传》《张骞李广利传》《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等传记中亦对少数民族史实多有涉及,因而在《史记》之后,《汉书》成功填补了汉武帝至西汉末期少数民族历史的空白,完整呈现了西汉时期中国境内外少数民族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历史,是研究西汉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一、《汉书》民族书写与班固的华夷一体思想
《汉书》中的民族书写客观反映了中原华夏族与周边少数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史实,体现了班固潜在的华夷一体思想,这主要表现在《汉书》的民族列传书写、民族同源书写以及民族关系书写等三个方面。
(一)《汉书》民族列传书写与班固的华夷一体思想
自中华文明源流伊始,少数民族就早已与华夏族展开了密切的互动,因而在上古典籍的记载中,少数民族的身影也多闪烁其间。其后在古老而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少数民族与华夏族一同参与了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发展,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失的历史板块。《史记》首创为境内外少数民族单独作传的史传模式,认为少数民族与华夏族同属于中华文明,正表明司马迁对少数民族历史地位的认同,反映了其朴素的民族平等观[1]。《汉书》继承《史记》为境内外少数民族设传的传统,表明班固在一定程度上对司马迁的民族观有所接受,并且认同少数民族与华夏族长期交流交融、密不可分的历史史实,因而将少数民族纳入西汉历史书写系统。
班固将《史记》中的《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调整合并为《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应是基于其对西汉后期国家政治格局发展以及中原政权与周边民族关系演变的考量。
《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将西南夷、两粤、朝鲜三方民族的历史合为一传,大抵是班固认为西汉对三者所采取的民族统治政策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据《汉书》记载,早在西汉武帝时期,汉朝即已在三方民族地区广设郡县,先后在西南夷地区设立犍为、牂柯、粤巂、沈黎、文山、武都、益州等七郡,在南粤地区设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址)、九真、日南等九郡,在朝鲜地区设立真番、临屯、乐浪、玄菟等4郡,由此正式将三方民族地区纳入西汉的疆域版图。同时,西汉还采取赐予夜郎、滇等地区统治者王印,将东粤“其民徙处江、淮之间”[2]3863等一系列统治手段,使三方民族地区得以平定,从而长期归属于汉朝。
武帝时期,为了钳制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虽结盟的目的并未达成,却对西域大宛、乌孙、康居、大小月氏等诸国的地理、风俗有了初步了解,从而拉开了西汉与西域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序幕。《史记·大宛列传》所载便以武帝时期的大宛国为中心,旁及周边西域诸国史实。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此时的西域与汉朝存在着政治往来、互通来使,但其尚未归属于汉朝,故此时西域仍被视为化外之域。直至《汉书》所载宣帝、元帝时期,“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2]3874,才正式设立西域都护府,“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工、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2]3928,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的统治疆域和统治体系中,成为西汉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此,班固将《大宛列传》调整为《西域传》,不仅是因为西汉后期对西域诸国的认识更为全面细致,故而不能仅仅以大宛一国之称代替西域五十余国,更是由于西域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属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式成为了西汉的属国。
《匈奴传》仍承《史记》旧名,但在内容上《汉书》进行了大量的扩充丰富,增补了从汉将李广利投降匈奴到王莽篡汉,汉匈关系恶化,再到更始三年,西汉灭亡一百多年间的匈奴民族史。而在此之间,宣帝时期“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2]3832,自呼韩邪单于始,匈奴一度臣服于汉朝。
由此可见,基于西汉后期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变化,班固对少数民族传记的传名进行了一定的继承与调整,同时其正文中对四夷宾服的史实进行了详细记载,正表明其认同周边民族隶属于汉朝,是西汉历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正是班固华夷一体思想的重要体现。
(二)《汉书》民族同源书写与班固的华夷一体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中建构了贯通古今、囊括四海的黄帝谱系。而作为《史记》的补充完善与发扬光大者,班固的《汉书》亦承袭这一认知系统,在民族起源问题上继承了司马迁《史记》的民族主张,认同各少数民族同华夏族一样皆为黄帝后代,各族同宗同源,同出于一脉,是血脉相连、手足情深的兄弟民族,这是其华夷一体思想的本质所在,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谱系建构提供了源流支持。如《匈奴传》载:“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2]3743指出匈奴民族是北迁夏朝遗民的后裔。而夏后氏最早的领袖为大禹,《史记·夏本纪》言“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3]49,由此匈奴最早的始祖便追溯到了黄帝。《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亦载:“闽粤王无诸及粤东海王摇,其先皆粤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2]3859而勾践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被称作“先禹之苗裔”[3]1739,故而东粤民族的始祖亦为黄帝。
在西南夷、南粤、朝鲜等民族的源流问题上,司马迁及班固虽未言明其民族始祖,但都强调其民族的统治者皆为华夏人,如《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庄跷者,楚庄王苗裔也。跷至滇池……因乃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2]3838这就说明滇王为华夏楚人之后。又如“南粤王赵佗,真定人也”[2]3847、“朝鲜王满,燕人”[2]3863亦说明这些少数民族的王族多为华夏人,其出于出使、任官、避难等目的,率领众多华夏人迁入少数民族地区并逐渐成为民族统治者,从而促进了当地本土民族与华夏族的大融合。故而这些民族的历史也与华夏族历史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认为这些民族与华夏族有着相同的源流。
(三)《汉书》民族关系书写与班固的华夷一体思想
《汉书》除记载各少数民族地域环境、民风习俗、生存状况等基本史料外,也对各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交流交融史实进行了翔实的记录,主要涵盖国家政治政策、经济贸易、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
国家政治政策除去上文所论设立郡县、西域都护府等在少数民族地区所实行的行政统治制度,还包括民族战争与民族和亲政策。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民族交流方式,几乎贯穿中国古代中原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交往历史的始终。频繁的战争,不仅增强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也推动了民族之间的汇融。在西汉两百余年的历史中,以战争方式对边疆民族进行征伐或镇压是汉族统治者对外交往的常态。据《汉书》记载,在西域,有赵破奴大破姑师、李广利攻打大宛等著名战役;在西南夷地区,则有郭昌与卫广诛灭且兰、平定南夷的镇压行动。除此之外,武帝时期更是派兵灭亡两粤、平定朝鲜,保障了边疆地区的安宁与稳定,也为民族的融合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土壤。
而作为自先秦时期就一直活跃在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由于受自然环境和生存方式的制约,匈奴多次侵扰边境、进犯中原,对中原政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而汉匈关系成为西汉最为紧要的民族关系。在西汉时期,汉匈战争更是长达百年之久。在《匈奴传》的记载中,汉匈战争前期,匈奴首领冒顿单于刚一统北方草原,正处于极盛状态,而汉高祖七年(前200)西汉经白登之围后一直处于弱势。直至汉武帝时期,以卫青、霍去病为首发动的对匈战争逐步扭转了汉匈形势,并在漠北决战中,迫使匈奴远遁。宣帝时期,匈奴由于内部矛盾,以呼韩邪单于为首的南匈奴“引众南近塞,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2]3797,向西汉称臣。到元帝建昭三年(前38),“都护甘延寿与副陈汤发兵即康居诛斩郅支”[2]3802,标志着北匈奴的彻底灭亡,从而使汉匈之间的和平局面持续稳定到西汉末年。从西汉时期的汉匈关系来看,长年战争促使两族人民对彼此的文化习俗、生活方式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以至于匈奴对于汉使的态度,《汉书》中都有所总结:“匈奴俗,见汉使非中贵人,其儒生,以为欲说,折其辞辩;少年,以为欲刺,折其气。”[2]3773其次,因战争而造成的两族边界频繁南北推移也使得各民族生存区域存在着长期的交叉和融合,而历次战争中的众多俘虏和降者所形成的人员互动也促进了汉匈之间文化的交流。到西汉后期匈奴臣服,汉匈之间长期的和平更是对民族的交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和亲作为一种政治策略,也广泛存在于民族交往的历史中。通过王室联姻,民族之间的矛盾得以缓和,交流也更加深入,从而实现和睦相亲。《汉书》主要记载了西汉与匈奴、乌孙以及龟兹等民族的和亲史实。西汉与匈奴边界接壤,长期的边境纷争必将损耗国力,不利于双方的持续发展,故而和亲便成为敌对双方缓和矛盾的有效手段。由于双方综合国力的变化,西汉与匈奴的和亲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据《匈奴传》记载,在西汉前期,西汉势微,面对匈奴的侵扰,“高祖患之,乃使刘敬奉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2]3754,这种妥协式的和亲一直持续到了汉武帝初年。虽然在这一阶段,和亲并不能彻底解决双方的矛盾,匈奴数次背约,但这一政策也为西汉前期边界的安宁以及国力的复苏创造了条件。武帝以后汉匈实力逐渐逆转,“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2]3781。面对西汉长年的军事打击,匈奴百姓苦不堪言,因而成为主动求和的一方。元帝时期,归附西汉的呼韩邪单于,为寻求西汉支持以巩固自己在匈奴的统治地位,“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2]3803,从而促成了“昭君出塞”这一象征民族和睦的千古佳话。
与匈奴不同,乌孙远在西域,西汉与乌孙和亲旨在联合乌孙以牵制匈奴,故汉武帝时期先后将细君公主、解忧公主远嫁乌孙王,此后解忧公主的侍者冯嫽也嫁与乌孙右大将为妻,并先后劝降乌就屠,三次出使西域,为乌孙臣服于汉立下汗马功劳。而解忧公主的长女弟史作为“汉外孙”[2]3916也嫁与龟兹王为妻,并积极将汉人的礼乐文化推广到龟兹。《西域传》载:“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檄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2]3916可见,西汉与乌孙、龟兹等国的和亲不仅在政治上增强了西汉对西域的控制,保障了西域的安定,随着和亲公主的西行,也为西域诸国带去了丝绸、布帛等财物以及中原的礼乐文化,促进了西汉与西域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层面的交流。
经济贸易也是民族之间交往的重要方式。据《汉书》载:“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莋马、僰僮、旄牛。”[2]3838“南粤食蒙蜀枸酱。”[2]3839“博望侯张骞言使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2]3841足以说明在西汉初年,巴郡、蜀郡民间已经自发与西南夷地区展开经济往来。巴蜀百姓购入西南夷的牲畜、奴婢,也借西南夷市场将枸酱、蜀布等特产远销南粤、身毒、大夏等地。在官方层面,西汉政府在边境所开设的关市以及纳贡与赏赐也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经济融合。在南粤的关市上,主要以汉地的金铁田器、牲畜换取犀角、紫贝等地方特产,而西汉初年,为缓和汉匈关系,汉室更是“厚遇关市,饶给之”[2]3765。此外通过贡赐,中原的丝绸布帛为各族贵族所喜爱,西域大宛、乌孙等地良马及葡萄、苜蓿等植物,南方白璧、犀角等奇珍异宝也进入中原。生活物资、地域特产的相互流通,不仅带动了各民族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也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
社会生活层面,《汉书》也真实记录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迁移与杂居。除却上文所提及汉人入少数民族地区成为统治者,促进汉人与其他民族杂居、通婚,并逐步融合的史实外,统治阶层的移民政策也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西汉以前,秦始皇在征服南粤地区后,就下令“徙民与粤杂处”[2]3847。武帝灭东粤后,“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2]3863,使两粤百姓内迁至中原。匈奴北遁后,武帝也先后“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实之”[2]3769、“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2]3770。外民内迁和移民实边政策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杂居与通婚,而社会生活不断融合,更是增进了彼此的社会与血脉联系,并逐步消弭了族群界限,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
《汉书》的民族关系书写真实地反映了西汉时期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以及民族融合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正表明在西汉时期,中华各族人民就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与共、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体现了班固潜在的华夷一体思想和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汉书》论赞书写与班固的华夷之辨思想
《汉书》传记结尾的论赞,评价人物得失,总结历史经验,寓含褒贬,是对《史记》“太史公曰”评述传统的承袭,同时也真实反映了班固的个人思想与观念。在《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等民族列传的论赞中,班固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民族观。此外在相关人物传记《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的论赞部分,班固称“汉兴,征伐胡越,于是为盛。究观淮南、捐之、主父、严安之义,深切著明,故备论其语”[2]2838,对于其所认可的淮南王刘安、主父偃、严安、贾捐之等人的民族观点,班固在传记中进行了详细记载。因此,将班固的论赞与刘安等人的民族观念结合起来研究,可以对班固的民族观进行深入研究。总体来看,两者都体现了班固的华夷之辨思想,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边疆无用论
自然地域使华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天然隔绝,班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中原与匈奴“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地”[2]3834,而西域更是“与汉隔绝,道里又远”[2]3930。刘安劝阻武帝不要参与两粤之争时,也强调汉粤之间“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2]2781。而自然地域的隔绝也使得各民族在文化习俗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由此班固等人以华夏文化作为文明的至高标准,以歧视性眼光审视外族文化。如班固认为匈奴为“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2]3834,刘安指出“越,方外之地,劗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2]2777,贾捐之请求弃置南粤珠厓郡时也指出:“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2]2834他们都认为其他民族与华夏族相比类于禽兽,无法接受中原的制度管理与文明教化。
除此之外,班固还指出盲目用武力征伐边疆民族、开发边疆地区只会损耗国力、困扰民生,甚至造成国家的颠覆。在《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论赞中,班固言:“三方之开,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发于唐蒙、司马相如,两粤起严助、朱买臣,朝鲜由涉何。遭世富盛,动能成功,然已勤矣。”[2]3868其将唐蒙、司马相如等人开发边疆地区的行为称为“好事之举”,足见其对边疆开发的贬斥。班固指出三方的开发正逢孝武盛世,虽然最后都成功将其纳入西汉版图,但西汉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匈奴传》论赞中,班固亦指出“当孝武时,虽征伐克获,而士马物故亦略相当;虽开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阳之北九百余里”[2]3831,认为是得不偿失之举。主父偃、严安则以秦始皇“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2]2811为例,指出穷兵黩武,贪外虚内,只会导致民生疲敝、国家灭亡:“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盖天下始叛也。”[2]2800
在这两种观念的影响下,班固得出了边疆无用论的结论。他认为匈奴“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2]3834,西域“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2]3930,南粤等地也如刘安、贾捐之所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2]2777,“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2]2834,此论从汉朝的自身利益出发,否定了边疆民族以及经略边疆地区的价值。
(二)怀柔羁縻政策
在边疆无用论的基础上,班固总结前代经验,得出了他认为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最佳策略,即怀柔羁縻政策。这种思想集中表现在其《匈奴传》的论赞中。首先,对于西汉前期的妥协式和亲,班固明确提出反对意见:“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也。”[2]3831认为面对匈奴的数次欺诈,一味地和亲讨好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其次,班固主张要严守边防,积极防御。汉元帝时期,侯应反对呼韩邪单于希望撤去边防的请求,班固称赞侯应之举“可谓盛不忘衰,安必思危,远见识微之明矣”[2]3833,即认为不加强边防而只期望凭借和亲与贿赂换取边疆的安定是不现实的。与此同时,班固还反对过度的武力征伐,他指出:“若乃征伐之功,秦、汉行事,严尤论之当矣。”[2]3833王莽时期,严尤曾总结周、秦、汉三朝的对匈政策:“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2]3824严尤认为武帝时期汉虽攻入匈奴腹地,扭转了汉匈形势,但却使中国兵连祸结30余年,虚耗了国力,是不可取的。而秦始皇以防守为要,征用百姓修筑万里长城,使国力衰竭、民心丧失,反而造成了江山颠覆,则更不可取。而周朝“视戎狄之侵,譬犹蚊虻之螫,驱之而已”[2]3824,是相比于秦汉而言的高明之策,这也被班固所认可。
由此,班固将以上措施总结为:“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2]3834这正是其所主张的怀柔羁縻的“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2]3834。
在《西域传》论赞中,班固又结合东汉光武帝的政策对怀柔羁縻政策再次表达了高度的认可:“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义兼之矣,亦何以尚兹!”[2]3930他认为光武帝对西域采取的羁縻政策是可以与汉文帝婉拒千里马等相提并论的高明之举。这种羁縻之策主张中央政权要与边疆民族保持联系,但并不对边疆地区进行直接而深入的治理,是一种相对消极保守的民族政策。这种政策实则根源于中原政权重内轻外、防范外患的统治心态,是对华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差异的承认,反映了班固的华夷之辨思想。
三、班固民族思想的成因、局限与价值
《汉书》的民族书写深刻反映了班固的民族思想,其思想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也有着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班固民族思想的成因
从《汉书》的民族书写可以看出,班固的民族思想蕴华夷一体与华夷之辨于一体,这一现象的出现与班固个人的著史理念、儒学观念以及其所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在著史理念方面,班固受司马迁影响颇深。一方面,《汉书》的民族传记书写和民族同源书写都是对《史记》民族书写的直接继承;另一方面,《史记》珠玉在前,班固作为优秀的历史学家,势必奉司马迁为著史楷模,以期达到对《史记》的超越。他在《司马迁传》论赞中高度赞扬了司马迁的史学实录精神,认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2738。因此,在《汉书》民族关系书写中,班固也坚持以实录精神对民族密切交往的史实进行如实描写。另外班固作为汉人史官回顾西汉历史,面对边疆等少数民族长期归属于汉的历史事实,自然而然地认同边疆民族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分子,是西汉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都导致了其潜在的华夷一体思想。
而在《汉书》官修的编纂性质影响下所生成的著史理念,也导致了班固民族思想的另一维度。据《后汉书》记载,班固其先“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4]1333,但被人诬告私修国史而入狱,后因为汉明帝欣赏其著史才华,他才得以继续完成《汉书》的修纂工作,这也使《汉书》由私人修纂变成受诏修纂。修史的坎坷经历使班固在某种程度上对明帝的赦免存在感恩戴德之情,再加上史书性质的变化,使得《汉书》在根本上代表的是汉代统治阶级的利益,并将宣扬汉德作为其根本宗旨,从而为汉朝大一统的专制政治服务。因此,当班固站在统治阶级立场审视民族关系时,自然生成了尊汉抑夷的民族思想。
班固的民族思想还来源于其儒学观念。班固出生于儒学世家,其父亲班彪“才高而好述作”[4]1324,范晔更是称其为“通儒上才”[4]1329。班固从小便开始接受儒学思想熏陶,9岁时便能“属文诵诗赋”[4]1330,等到长大后更是“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4]1330。这样的成长环境使班固自觉继承了先秦儒学经典中的华夷之辨思想。这种民族思想由来已久,儒家先贤将文明程度作为评判民族先进与否的主要标准,从而肯定华夏文明,贬抑少数民族文明。在《论语》中,孔子就提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5]26而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也提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6]孟子认为只能用华夏文明改变少数民族文明,不能用少数民族文明改变华夏文明,这都反映了儒家观念中的华尊夷卑思想。这种观念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班固对于民族的认知,他在论赞中也多次引用儒家经典,如《尚书》“蛮夷猾夏”[2]3830、《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2]3834,道出了少数民族侵扰中原、内外有别的历史,也成为了班固华夷之辨思想的理论根源。
班固民族思想的形成,也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据《后汉书》载:“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4]1334可知在班彪所修前史的基础上,班固奉诏修书的时间为明帝永平年间到章帝建初年间。其时正值东汉初年,刚经历易代纷争,国力衰弱,再加上王莽时期与各民族关系不断恶化,几近断绝。内忧外患的局势,使东汉初期的民族政策偏于保守消极。以西域为例,王莽时期“西域怨叛”[4]2909;东汉初立,西域诸国“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4]2909,光武帝“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4]2909;明帝时期“于窴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4]2909;而到章帝时期,再次以“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4]2909为由弃置都护。可见在东汉初期由于国力衰微,统治者在民族关系的处理上有心无力,整体上采取相对消极保守的羁縻政策,这正是《汉书》怀柔羁縻主张以及华夷之辨思想形成的时代根源。
而在《汉书》成书之后,东汉在和帝时期国力达到极盛,开创永元之隆的盛世。在民族政策上,窦宪大破北匈奴,使其溃亡西迁,班超平定西域诸国,复置西域都护府,这也使得班固后期的民族思想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和帝永元初年,班固随窦宪出征匈奴,大获全胜,班固作《封燕然山铭》,文中称赞此次军事行动为“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4]815,与其在《汉书》中所提倡的“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2]3834的保守思想全然不同。这大概是时代背景使然,当国力强盛之时,统治者便会展露大一统的政治雄心,民族政策也会变得更加积极开放;而当国力衰弱之时,统治阶级更加强调华夷之别,从而以保守的民族政策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
(二)班固民族思想的局限
班固民族思想中的华夷之辨思想继承先秦儒家思想而来,站在华夏文明优越的立场,对少数民族文化加以评判,实则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歧视。这种思想并不利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也严重破坏了民族平等,阻碍了民族团结,这是当今社会需要摒弃的民族思维。同时班固在该思想下所孕育而出的边疆无用论和怀柔羁縻政策也有其时代局限性。首先班固忽视了少数民族参与国家建设和缔造国家历史的功绩。如就东粤民族而言,“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粤归番阳令吴芮……从诸侯灭秦”[2]3859,“汉击项籍,无诸、摇帅粤人佐汉”[2]3859,粤人积极参与了灭亡秦朝的诸侯战争,并辅佐汉高祖刘邦建立了西汉政权。其后,“吴王濞反……东瓯受汉购,杀吴王丹徒”[2]3860,粤人又协助西汉刺杀叛王刘濞。可见,少数民族和汉族一同参与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构建,这都是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其次,该观念也忽视了少数民族守卫边疆的战略地位,汉高祖立赵佗为南粤王,就是为了让他“使和辑百粤,毋为南边害”[2]3834,惠帝时期辽东太守也曾与朝鲜王卫满约定,让他“保塞外蛮夷,毋使盗边”[2]3864,都是让他们维持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从而不侵扰西汉边境。由此可见,边疆少数民族的平定和统一必将稳固国家疆域边防、促进边疆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稳定。然而,由于受到当时保守的民族政策的影响,班固的民族思想并没有真正考虑到少数民族与边疆地区的经略价值。
(三)班固民族思想的价值
班固民族思想也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汉书》给不同少数民族分别作传,正表明班固对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以及地域分布等特质有所认识与区别,从而能肯定各个民族的相对独立性,起到了民族识别的积极作用。而这种民族思想根源于其所继承的儒家华夷之辨观念,儒家先贤虽以文明程度为标准,界定了民族的优劣,但该民族思想并未将华夏族与少数民族完全对立起来。如孔子曾经想去九夷之地居住,“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5]104孔子认为君子到少数民族地区居住,可以通过文明教化改变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状况。可见华夷之辨思想在本质上认可各民族之间的差异,但同时也认为通过文明的传播,各民族能达到合为一体的理想状态。这种民族思想被后人所继承,成为中原政权面临外族威胁之际,保卫华夏文化的有力思想武器,班固的华夷之辨思想正是如此。故该民族思想也潜在地促进了华夏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促成了一种凝重执著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促使各少数民族向汉文化靠拢而融合为一个民族”[7]。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了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8]
而《汉书》中各民族同宗同源、密切交往的民族书写则是中华民族自古一家的历史明证。其所反映的华夷一体民族观念贯穿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成为各族人民相互认同的集体意识,奠定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思想基础,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8]并强调:“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8]明确道出了中华民族发展的特质。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首次提出了与“社会”相对立的“共同体”的概念,他认为“共同体”包括血缘共同体、地域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等基本形式,是“古老的”“持久的、真实的共同生活”,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9]71,“所有亲密的、隐秘的、排他性的共同生活”[9]68都可以被理解成共同体中的生活。这一理念正与中华民族的发展特质相契合,从而衍生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及“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他指出“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 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0]。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对“中华民族”的性质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他强调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这一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 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11]。2017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正式写入中共十九大报告,报告指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12],这均体现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处理民族问题、进行民族工作的民族理念。2021年,徐黎丽、韩静茹也进一步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界定为“中国各个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共同的国家疆域、互补的生计方式、互鉴的生活经验、共有的历史记忆、共认的价值体系、共育的国民意识、共享的精神家园的实体与精神共同体”[13]。而这正与《汉书》民族书写中所展现的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相互依存、相互交融的史实遥相呼应,足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与《汉书》民族书写所体现的班固华夷一体思想一脉相承。《汉书》对西汉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记述,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国古代不断孕育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当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支撑。同时,其主张天下一家的华夷一体思想对于当下民族政策的制定、平等团结等民族理念的巩固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