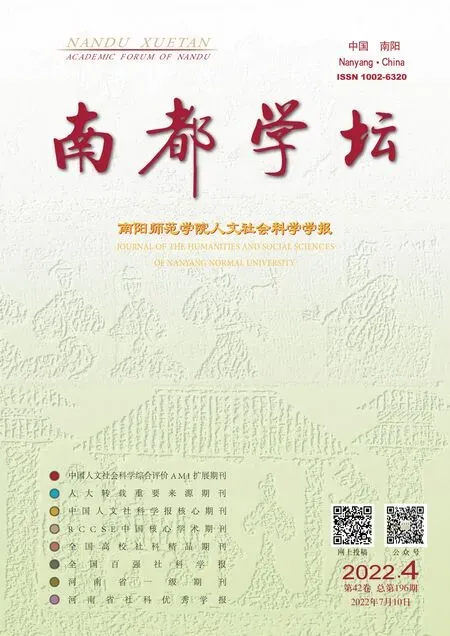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便衣队的主要活动与历史贡献研究
韩军垚, 王国欣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
便衣队全称为“武装便衣工作队”,是鄂豫皖军民在三年游击战争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下,在与国民党军的镇压作斗争的过程中,结合当时当地实际创造性地建立的一种独特的革命斗争组织形式,逐渐成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坚持鄂豫皖革命斗争的主要武装力量,对鄂豫皖根据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并成为这一时期中共创建的存续时间最长、保存力量最多的工农武装割据区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目前学术界关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研究多集中于红二十五军长征以前根据地革命事业的发展,有关该区后期游击战争时期的研究较为薄弱,对便衣队这一独特组织形式的研究更是欠缺,虽在一些综述性著作中有所提及,但多为表面性的介绍,未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入探究。有鉴于此,本文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便衣队的主要活动为切入点,总结其方式与特点,探究便衣队在鄂豫皖革命斗争以及中国革命事业中的历史作用,以期对深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便衣队的主要活动
尽管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便衣队产生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组建方式不尽相同,但各便衣队均围绕地方工作,承担多项任务,体现出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性质。便衣队的活动主要包括恢复与建立党组织,筹集物资和经费,安置与医治红军伤病员,补充红军兵员,建立与扩大游击根据地,配合部队作战等。
(一)恢复与建立党组织
在国民党军的反复“清剿”下,鄂豫皖边区的党组织尤其是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地方党的工作陷于瘫痪。因此,便衣队中的党组织成了所活动地区党的领导机构,其党支部一般都履行相当于工委、区委甚至县委或中心县委的职责。关于这一点,鄂豫皖省委报告称,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我们至今一切秘密工作群众工作侦探工作,党的大部分工作,都在这便衣队的组织当中”[1]。
各地便衣队为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做了大量工作。把在敌人白色恐怖中遭到破坏的党组织恢复起来,把被打散的革命力量聚集起来,同时积极审慎地把在斗争中经过考验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黄冈便衣队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通过对敌斗争和群众工作,发展了一百多名党员,组织了十几个党支部,建立了四个区委,成立了黄冈中心县委;皖西便衣七分队在黄梅、宿松边界一带活动时,帮助地下党发展党员,组织了三个支部,并建立了宿黄边区区委。各地便衣队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到1935年底部分恢复了各老区党的基层组织,随后又在新开辟的根据地逐渐建立了许多党的组织[2]700-701。
党组织的恢复和建立使边区各地都又有了党的坚强领导,老根据地的领导力量得到加强,新根据地的领导核心得以形成。党员组织的发展更加紧密地团结了革命群众,使基层有了进行斗争的领导核心,为边区各项工作的继续开展奠定了基础,这也是鄂豫皖边区革命斗争能够坚持和发展的根本保证。
(二)筹集物资和经费
由于国民党实行军事“清剿”和经济封锁,红二十八军长期处于不断流动的频繁战斗中,没有固定后方,活动和供应都异常困难,党政军后方机关的供应也濒于断绝。在这种情况下,便衣队担负起为红军和各级党政军机关筹粮筹款,提供经费与物资的重任。
便衣队筹集经费和物资的主要办法有三。一是经营工商业。“皖西潜山一带的便衣队,他们在大森林里,拉拢了很多买卖商人,在大山头上安了几个工厂,供给了很多正规红军”[3],皖西便衣二分队曾在鹞落坪办了一个修械所和一个帐篷被服加工厂,在孙家湾设了一个仓库,还与四分队在霍山包家河、潜山青天畈、舒城沈家桥等地开设起红军地下商店,由便衣队出资,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充当商店老板,经营红军需要的物资,秘密为红军采办粮、油、盐、布匹、电池、药品等物品。二是实行苏维埃的税收政策。便衣队改“打粮”为征税,按税率规定大、中、小地主按期交纳不同数量的粮食、现金,既分化了地主阶级,又能保证一定数量的经济来源。灵山便衣队还通过将佃户应向地主缴纳的地租一分为二,交地主一半,给红军一半,以此方法,很快筹到粮食两万多斤。该队在三年中,仅上交给主力红军的现金即达两万元。三是通过打土豪等途径规定缴纳一定数量的现款和物资,到敌占区或通过群众购买所需物资,这也是当时的主要渠道。例如,罗山便衣队在接到罗陂孝特委关于尽快给红军筹粮筹款的指示后,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抓到罗山县税务局长筹到一千块银元,请基层群众到敌占区购买相当数量的粮食送给红军。
通过以上途径,便衣队筹集到了大批现款和相当数量的物资,基本上保证了红二十八军的供应,连“二十八军的日常用品,如衣服、鞋子、牙刷、牙膏、电池、电筒、绑腿、雨伞等,都是便衣队供给”[3],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
(三)安置与医治红军伤病员
安置与医治伤病员也是便衣队的主要活动。红二十五军离开边区时留下的二三百名伤病员是由便衣队安置的,三年游击战争中,红二十八军和各地方武装在作战中负伤和掉队的伤病员,大多也是由便衣队收容的。
1935年以后,由于边区医院先后均遭到敌军侵袭,损失严重,幸存的医疗单位被迫化整为零,医务人员随部队行动或分散到便衣队中继续从事医护工作,打仗时有了伤病员就交给便衣队,医务人员留下来分头赴伤病员处进行医治。至1937年,由于在敌人反复“清剿”的恶劣环境中安置医治伤病员更加困难,便衣队即利用掌握的社会关系等条件对红军伤病员进行妥善安排。接到彩号后或巧妙地分别安置到联保主任、保长、地主家里,或灵活地迁移到外线分散隐蔽,将安置于群众家的伤病员在拂晓前背上山隐蔽,天黑后再背下来治疗。对此,袁德性报告称:“战时伤亡者均须抢回……伤者如时间许可,则抬往天台山总医院治疗或交各地便衣队收养,如被追剿过急,则沿途交与农民看护……其他如病匪不能行动者亦如此办理。故国军追剿每不易见到落伍匪兵,此乃其主要原因也。”[4]520-521
由于陆续收容伤病员较多,为了便于伤病员能够得到及时治疗和更好休养,便衣队还协助医务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因地制宜办起各种“临时医院”。皖西地区的一些便衣队因陋就简在深山野林里搭起草棚,在山洞里架设起床铺,办起了“山林医院”,医务人员负责治疗,便衣队负责采办药物及保障安全。黄冈地区便衣队也筹办了一所临时医院,先后将二百多名伤病员分散到群众家中,医护人员巡回医治。这些“临时医院”对红军的卫勤保障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在便衣队和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伤病员得到了比较妥善的安置和治疗,使得他们能够较快痊愈并及时重返战斗岗位,从而大大鼓舞了红军的士气,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四)补充红军兵员
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红二十八军和各地方武装不断与数倍于己的敌人频繁作战,部队减员很大,需要经常补充兵员。便衣队主动承担起这项重要任务。
便衣队不仅注重吸收活动地区的优秀青年和积极分子补充到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部队中去,还在地方积极组建游击队、战斗营等武装形式,以后逐渐补充到主力红军,使红二十八军拥有了更为稳定的兵源。如“黄岗的两个便衣队,以后组织了两个营补充了正规部队一个营……姚儿坪的便衣队,组织了小便衣队,小便衣队变成了游击队、特务队,以后编为正规部队”。又如1935年初,高敬亭政委在潜山县沙村河放下的以张作汉为队长的便衣队与当地党组织紧密联系,组织发动群众,成立了皖潜游击大队,到4月发展到180多人,以后又先后改编成独立营、游击师,并陆续补充到红二十八军中。各地便衣队不断以多种形式充实红军力量,成为红军补充的重要来源,“二十五军走后,二十八军打了三年,还保持一千多人,就是靠便衣队补充的”[3]。便衣队不断为红军和地方武装补充兵员,使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兵员消耗得到了及时的补充,起到了后备军的作用,从而有效保证了战斗力。
(五)建立与扩大游击根据地
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扩大游击区不仅是便衣队的一项主要活动,更是其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为此,便衣队充分发挥自身隐蔽分散、灵活精干,便于联系和发动群众,易在当地立足生根的特点,将活动区域逐渐发展成小块游击根据地,并逐步将各块连成一片。
皖西特委和后来皖鄂边区特委领导的22支便衣队,经过共同努力将舒霍潜太游击根据地逐步扩大到皖鄂边区,在十余县境形成纵横二三百里的大块游击根据地,“不到一年时间,由于主力红军与便衣队相互配合,我们在皖西建立了若干小块立足点以外,还在鹞落坪周围纵横百余里的地方,建立了一块较大、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鄂东北独立团领导的灵山便衣队在独立团、游击师和特务营的协助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在平汉铁路两旁的罗山、信阳、应山三县之间的地区开辟出一大片游击根据地。各便衣队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建立起一块块比较巩固的后方基地。这一块块基地“实际上已成为秘密的苏维埃政权”,便衣队“活动的地区成了红二十八军主力部队隐蔽的立足点”[5]115,在人力、财力和物力上给予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很大的支援。
由于便衣队的经营,使得红军所到之处大都有根据地作为依托,可以声东击西,变幻莫测,给敌人巨大打击。1936年6月28日《申报》刊登的《麻城民众请愿剿匪》惊呼:“最近匪以地方绝无抵抗实力,为久踞计,择地建设……现在(麻城)县境以内,匪已明目张胆,四乡皆有组织,匪区日见扩大,滋蔓难图……而切邻之黄冈、黄陂、礼山、黄安、商城、立煌等县,闻皆有一部分与麻城相同。”[6]这一报道也从侧面反映出便衣队建立与扩大游击根据地工作的成效。
(六)配合部队作战
便衣队作为坚持根据地对敌斗争的重要武装力量,除独立打击反动势力外,还充分发挥自身特点,通过侦察敌情、传送情报、带路打先锋;破坏敌人通讯联络和交通运输;伏袭小股敌人和敌人的增援部队;捣毁敌人的后方,截击敌军军用物资和军事设施;配合红军消灭敌人的据点,摧毁敌人的碉堡;到敌人据点周围骚扰牵制敌人等多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的作战行动,扰乱和牵制了敌人相当大的兵力。
便衣队利用自身特点及掌握的社会关系对所在地区的敌情进行深入调查,盯住敌人的兵力部署和活动规律,红军部队经过时走什么路线、住在什么地方、哪个据点可以打,便衣队都能根据掌握的情报提出符合实际的意见,使主力部队掌握主动权。对活动地区联保主任、保甲长、地主富绅的情况也都一清二楚。每次到什么地方打粮,打哪几家地主富农的粮物都是便衣队提前调查好的。为配合部队作战,便衣队还经常分成几个小组到敌军据点周围活动,有时在敌人炮楼附近打一枪,敌人的机枪就一夜不停地扫射;有时几个便衣队员能缠住敌军一个营几个钟头,甚至能牵制敌军一个团的兵力,使敌人感到红军无处不在,因而草木皆兵。国民党军第十一路军刘茂恩部就有“复令驻合肥之六五工兵营孙营长喜堂,负责清剿合、舒境内散匿残匪,以免与高匪呼应,再事滋扰”[7]497的指示。1934年11月,罗陂孝特委组织便衣队在罗山至汉口的公路沿线袭扰敌人,通过割电线、打汽车、破公路、毁桥梁等方式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因而把国民党东北军的两个师拖在罗汉公路上,并迫使敌人抽调一个骑兵团驻守公路南段,胜利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策应了红二十五军的转移[2]641-642。1935年1月,黄安、罗山、经扶三县便衣队和特务营等配合攻打了罗山县最反动的九里十八寨总寨香炉寺,全歼守敌,镇压了反动民团头子、伪联保主任陈仲良,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在坚持金刚台的三年中,便衣队配合红二十八军烧敌人的炮楼,割敌人的电线,阻截敌人交通运输,牵引国民党军三个正规师和地方武装十几个旅,分散了敌人的兵力,使红二十八军能蓄积更大力量在外围打击敌人。
便衣队的这些行动对主力部队多项活动的开展都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红二十八军和各地方武装在便衣队的配合下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边区的多次进攻和清剿,郑位三就指出“二十八军的力量是两个拳头,一个是便衣队,一个是二十八军大游击队,这也就是当时的组织系统”[8]25。
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便衣队主要活动的特点
在便衣队产生之初,郑位三就根据当时根据地敌强我弱的情况,给便衣队规定了“游击战争,昼伏夜动,两面政策,统一战线”[9]217四位一体的活动方针。便衣队的主要活动也是按照这一方针开展的,并在实践中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斗争对象,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活动方式。具体可概括为:游击战争,灵活奇袭;昼伏夜动,隐蔽活动;群众工作,由点到面;灵活多样,综合运用。
(一)游击战争,灵活奇袭
根据情况灵活地分散或集中兵力是游击战争的精髓。在对敌斗争战略战术上,便衣队利用大别山区层峦叠嶂、沟深林密的地形,采取灵活机动的奇袭等方式,不断打击敌人、惩办反动分子,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袁德性在其巡察报告中指出:“(便衣队)均采取流动方式,以其地形之熟悉,多利用夜暗行动,遇优势国军躲避正面,势弱国军即行奇袭。”[4]516有时一个便衣队力量不能奏效,就集中几个便衣队共同实施,或在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联合作战。各便衣队都以自己的活动区域为内线,以临近便衣队的活动区域为外线,与兄弟便衣队、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互相支援、互相策应、互相配合,形成许多夹击敌人的战线。林维先对此描述道:“他们昼伏夜出,分散活动,配合战斗营、游击师和红二十八军同敌人作战,到处打击敌人。他们时出时没,声东击西,搞得敌人晕头转向,摸不清我主力部队在何方。”[5]113
毛泽东指出,“会走”正是游击队的特点。“走”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方法。对付敌人主力“清剿”时,采取打圈子战术,内线、外线往返穿插作战,时东时西,忽南忽北,或插到敌人后方,或昼伏夜击,条件有利时就抓住战机伺机歼敌,打了之后立即走,使敌军难以掌握其行动规律,无法捕捉行踪,从而很快打开了局面。商南县委领导的各便衣队在游击武装的配合下,采取时分时合、避强击弱、声东击西等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寻机歼敌,平时各自为战,遇到时机就迅速集中起来,广泛展开游击战争,国民党军以大股兵力“清剿”时,就分散游击打“麻雀战”,牵着敌人兜圈子扰敌疲敌,这样不仅有效保存了自己,也不断打击了敌人,给国民党军带来了巨大困扰。《申报》曾报道:“查高俊(敬)亭股匪,全部精锐,不过千余人,在边区各县时集时散……现化整为零,部队追剿向前,匪又忽焉在后,以故大军过去,皆目为无匪。”[6]可见便衣队通过一系列灵活的战略战术的运用,使国民党军相当无奈。
(二)昼伏夜动,隐蔽活动
便衣队组织精干、灵活轻便,同时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打击敌人,在斗争实践中常采用隐蔽活动的方式。这也是小部队要击败强大敌人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据郭述申等人回忆:“老苏区内便衣队主要依靠老苏区,外面站不住脚就进出(去),有些主要靠地形,站不住脚的躲进大山里去,晚上出来活动,如潜山一带主要靠森林,很多主要依靠群众,如豫东南商城一带,躲在群众家里。”[3]鄂豫皖省委也曾指出:“便衣队都是白天隐藏在白旗下之地方,多是夜间进行工作,与群众关系很密切。”[10]曾参加红二十五军的老同志们回忆,由于国民党军的严密清剿,“那时坚持斗争的形式只能以便衣队、游击队的小分队化整为零开展活动……白天,便衣队东藏西躲,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设法保存自己,坚持下去。晚上就出去搞吃的,搞给养,打击富豪反动保甲长,形成昼伏夜出的斗争方式,长期坚持下去”[11]599。可见,隐蔽活动是便衣队的一个基本活动方式。
黄安仙居区于1933年成立的两支便衣队就是以老君山为依托,采取白天隐蔽在山林里,深夜下山开展工作的方式得以发展。张琴秋领导的便衣队来往于汉口、黄陂、孝感之间,依靠隐蔽在暗处的优势,遇到小股处于明处的敌人就果断出击,加上有群众作掩护,因而能够屡屡取得胜利。当时很多地区的便衣队都是携带短枪、匕首等武器利用夜间行动,奔走于山林和村庄之间,偷袭敌人的据点和碉楼,捕杀反动分子,由于他们队伍小行动隐秘灵活,加上善于隐蔽,敌人很难对付。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一部在其作战详报中无奈道:“军队至则化整为零皆为百姓”[12]477,足见便衣队隐蔽工作之成功。
(三)群众工作,由点到面
便衣队是一支掌握武装的游击小分队,但又不同于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它不是以打仗而是以群众工作为主,是隐蔽于群众中开展群众工作的武装工作队。关于这一点,鄂豫皖省委在1934年就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惟(唯)一的办法是坚决改造便衣队的活动方式,变成深入领导群众斗争,发展党和群众之组织,运用中央所指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策略与游击战争红军行动联系着。”[10]
便衣队把群众工作放在首位,一般是选择省界或几县交界地区地形条件和群众条件好的地方,依靠当地地下党和革命群众,白天隐蔽,晚上到群众家里做工作,采取逐个村庄的方式,先从单庄独户开始一人一户地进行发动,扎根在贫苦农民中,团结广大劳动人民,以遵纪爱民行动取得群众的信任站稳脚跟。立足之后再用亲串亲、邻连邻的方法由一个队到几个队,由一村到几村,使他们拥护共产党和红军,帮助便衣队开展工作。据郭述申等人回忆:“便衣队白天在大山上登(待)着,晚上就到村子里,先到一个群众家里带宣传带勉强的要住在他家里,并给他钱多。搞搞就与几家关系搞好了,慢慢争取群众,把全村都开展了工作。”[3]便衣队由一点到多点、由点到面开展工作,使点面开花连成一片,由山区到平原,由秘密活动(组织秘密农民小组、妇女小组、青年小组,发展地下党员)逐步到公开建立小便衣队和游击队,陆续在觉悟高的基本群众中发展党员,在有条件的地方成立党的领导机关,掌握基层政权,由隐蔽的游击根据地到建设比较巩固的后方基地,使工作的基础更为扎实,使游击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与发展。
(四)灵活多样,综合运用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当时客观环境下的具体斗争实践中,便衣队的诸多活动方式并不是截然分离的,通常是综合运用的。徐海东和吴焕先在指导团山便衣队工作时就曾指出,“(便衣队)能公开活动就公开活动,不能公开活动就暗地作(做)群众工作,建立群众革命组织,镇压反动分子”[13]241,并指示要抓住时机打击反动的乡保民团,但对大批敌人大股团匪不要轻易出击。例如,商固边境上的便衣队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分赴各地活动,与群众密切配合,加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因而能在极端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始终与敌人周旋于杨山、窑沟的丛山密林之中,不断地打击敌人壮大自己。在面对敌军1937年6月开始的“全面清剿”这一严峻形势时,为求得生存,各地便衣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各自为战,人自为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原来活动地区无法隐蔽时就转移到过去有些群众基础的地方隐蔽,白天在野外,晚上住到群众家里。由于采取了符合实际的斗争方式,又一次战胜了国民党军的清剿。
郑位三认为,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有三大特长,第一个就是“有几十个县的便衣活动,又是武装斗争又是群众工作,规模大”[8]25。由于便衣队斗争方式灵活多样,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其它武装形式不可取代的地位,因而可以说“便衣队是群众工作与秘密组织工作的一种最有效的极为适宜的游击武装组织”[9]217。
三、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便衣队主要活动的历史贡献
作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坚持鄂豫皖革命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便衣队以自身实际行动赢得了鄂豫皖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援助。这既是便衣队能在鄂豫皖边区站稳脚跟,不断发展壮大的先决条件,也为胜利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更重要的是,在长期坚苦卓绝的斗争中,便衣队紧密协同主力红军和各地方武装,采取正确的政策策略,锻炼出了一大批革命骨干力量,丰富了党领导革命斗争的经验,为大别山的红旗不倒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便衣队的活动获得人民群众积极支援,为胜利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便衣队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时刻关心群众生活,处处维护群众利益,既能号召和领导群众,又能为群众办事。所以群众拥护、并全力支援便衣队,积极协助便衣队开展各项工作,体贴入微地掩护便衣队,想方设法供给便衣队衣食。关于这一点,郭述申等指出:“便衣队所以能立住脚,坚持几年的斗争,主要依靠的就是群众。”[3]林维先也总结道:“便衣队所以能站稳脚跟,坚持斗争,发展壮大,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比主力部队更能接近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5]114
第一,人民群众积极协助便衣队开展各项工作。1934年初,鄂豫皖多地已出现“群众到处帮便衣队打民团、杀反动、分粮吃”,“有大部分群众现在已与我们的便衣队游击队秘密工作人员时相往来,向我们报告些敌情和反动的情形,接受我们之宣传”[10],“特别是在白旗下的群众,因为地主富农抬头的反攻反动统治剥削压迫使群众生活痛苦到万分,群众热烈要求恢复苏维埃政权,白旗下许多地方的群众配合着便衣队打民团杀反动[分子]跟红军一路(起)开仓分粮(尤其是鄂东北)”[14]的局面,群众与便衣队结成了相互协作的紧密关系。
便衣队在安置伤病员时,很多时候迫于形势只能“安插彩号……有的安插到群众家中”[3],伤员安置在群众家里经常长达数月,群众始终把伤员当成自家人精心照料,情况危急时还协助便衣队将伤员转移到山上,有些甚至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坚持送茶送饭。霍山县马家河一带的群众在被敌人为切断与该地便衣队联系,用移民并村、制造无人区等办法把当地一千多口人全部集中起来关在“木城”里严密看管后,还是想尽办法为便衣队掩护了二十多名伤员,并协助潜入“木城”的便衣队员了解情况、张贴标语、散发传单。1935年夏,在敌人“三位一体清剿”时,群众面对国民党军构筑碉堡网的胁迫仍在鄂东北地区便衣队的广泛发动下设法拖延,许多群众在敌人监督松懈时偷偷跑掉,没跑掉的也都虚以应对,白天怠工,夜晚拆毁碉堡、烧毁木材、破坏工具,为便衣队的活动拖延时间。
第二,人民群众体贴入微地掩护便衣队。边区群众不仅积极协助便衣队开展工作,还经常不顾一切地掩护便衣队员,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光山、商城一带当地风俗不准外人进入姑娘的房子,可当地群众有时为了掩护便衣队员躲避敌人的搜查,却主动让他们藏在自家姑娘的房中。蕲春将军山的便衣队安置红军伤病员在群众家中,群众一般是叫媳妇出来招呼,碰到民团清乡查问时,即以“这是我丈夫”为托词进行掩护。红安三区便衣队几名队员在一户群众家中隐蔽时,碰上国民党军搜查,刚从外面回来的男主人立即挺身上前,有意让民团把自己抓走以保护便衣队,并用暗语告诉其妻让便衣队赶快转移。1935年春,罗山县长岭岗群众曾少山全家与红军伤员、便衣队员一起隐蔽在山洞中躲避敌人“清剿”时,他的孩子突然惊哭起来,为了掩护红军和便衣队员,他含着泪水掐死了自己的孩子。1935年秋,国民党在夏青区“清剿”时,一个木匠把便衣队员藏在自家床底的石板下,别动队搜不到便衣队,就将全村人抓起来逼问便衣队的下落,并当场杀害三人,可群众面对敌人的屠刀宁死不屈,无一人吐露便衣队的藏身之所[2]714。由于群众的全力掩护,很多时候国民党军即使知道便衣队隐蔽的大概区域并大力搜剿也不能得逞,却又无可奈何,国民党军刘茂恩部就曾在作战报告中感慨:“前在汤池畈附近被我三八五团击溃之伪皖西北游击总队,现尚潜匿舒、潜交界一带,经我邢旅长率队连日搜剿,并无匪踪。诚以该处人民多数匪化,国军对于匪情不易明瞭。”[7]495
第三,人民群众想方设法供给便衣队衣食。边区人民虽然缺衣少食,生活极其艰难,但许多拥护共产党和红军的群众仍把少有的粮食、衣物拿出来支援便衣队。国民党为了切断便衣队同群众的联系,大搞“移民并村”,烧毁原来的山区村庄,把群众集体并入其管控之下的大村,被集中在移民村里的群众下地劳动时只准带仅够一人吃一餐的食物,并受到敌人的严密监视,无法直接把粮食、衣物交给便衣队。他们就把穿在脚上的鞋子连同自己的干粮一起留在与便衣队约定的地点,让他们夜间取走,自己赤着脚回家。在1937年国民党发动的三个月秘密“清剿”中,国民党军调动大量兵力对便衣队进行大规模全面“清剿”。便衣队原先控制的地区基本被敌占领,在敌人的层层封锁下,群众无法往山上送粮食,大多数便衣队经常处于缺衣少食、风餐露宿的恶劣环境中。在这最困难的时候群众想方设法供给便衣队衣食,许多便衣队就是靠着群众的支援才能够生存下来继续坚持斗争的。砖桥区便衣队被围困在山林中一筹莫展时,山下的群众将鸭子赶上山来给便衣队充饥,便衣队就是靠着这一群鸭子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
如高敬亭所言“广大革命群众,对敌人憎恨极深,对我红军(便衣队)非常拥护”[15]326,国民党也感叹“民匪形成合作性质”[7]477。在三年游击战争极为艰苦困难的环境中,便衣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援,正是紧紧依靠了人民群众,便衣队才得以度过这一艰难时期。当时“工作好点的区域,便衣队组织群众,发展党(员),带群众一路(起)分粮,帮群众一路杀反动,很有些成绩……群众工作最好之地,便衣队白天可以与群众一路耕种,匪军不能发觉,只有当地反动和民团出发才能发觉”[1],鹞落坪总人口不到两百,参加便衣队的就有四五十人,再加上交通员、采购员、情报员,在不到两百人中差不多有一半青年男女为红军服务[16]359。而广大群众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便衣队关心群众,处处以群众利益为重,与广大群众结成了情同鱼水的紧密关系,这也是便衣队能够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并不断发展的根本力量所在。
便衣队既能为群众办事,又能号召和掌握群众,在群众中实际起着政权的作用,它的广泛发展与农民小组的普遍建立,既改善了党组织活动的环境,得以广泛联系群众,更为红二十八军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使鄂豫皖的武装斗争形成广泛的人民战争,得到了坚持与发展。关于这点郑位三曾指出:“便衣队是一种很好的斗争形式,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起了很好的作用,打开了赤白区对立的局面,使我们和白区群众的关系搞得很好。”[17]112由于便衣队的积极活动,边区群众工作得以坚持,群众革命力量得到了发展,因此共产党与红军的影响更深入到群众中去,特别是过去未曾到过的地区,从而打开了斗争的新局面。
(二)便衣队的活动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并为中国革命锻炼了骨干力量,积累了宝贵经验
作为坚持鄂豫皖革命斗争的第二支重要力量,便衣队开展的各项活动,完成了主力红军不能完成的某些任务,密切配合了主力部队,促进了鄂豫皖边区的巩固与红二十八军的发展。
高敬亭肯定便衣队这一作用,“由于便衣队的积极活动,有时主力部队不能担负的任务,而便衣队不费什么力量就能完成了。这就增强了我们坚持大别山、桐柏山和周围平原地区斗争的群众条件和地理条件”[15]326。红二十八军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能坚持鄂豫皖的三年游击战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发展了便衣队武装到各游击区。主力红军作大范围的游击活动,便衣队以自己的活动区为内线,以其他武装的游击根据地为外线,就地坚持或配合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作战,形成很多夹攻敌人的战线,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变大部队作战为小分队游击作战,既担任对敌斗争的前哨,又充当保障供给的后方,成为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得力助手。有效地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武装、便衣队三结合的人民游击战争。因而可以说,“便衣队与红二十八军就是内线与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便衣队之间的相互关系亦然……积极地配合了主力部队,坚持了鄂豫皖边区的斗争,是红二十八军的左右手”[5]113,116。
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在便衣队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红二十八军转战于鄂豫皖边区的45个县,牵制国民党正规军最多时达68个团,约17万人,歼敌18个营、15个连和大量小股敌军,粉碎了敌人的四次“清剿”,使革命红旗始终飘扬在大别山区。同时,有力地支援了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配合了其他根据地红军和人民的革命斗争[2]728。国民党豫鄂皖绥署在检讨其清剿失利原因时也供认:“皆缘此等赤匪,多为本地土著,所到之处,又有人从而勾引通窝,以致行动自由,飘忽无定,兵来匪去,已成惯伎”[18],足见便衣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和牵制了国民党在鄂豫皖边区的活动,起到了配合主力红军的作用。对此,林维先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没有便衣队的配合,仅靠二十八军主力部队,要取得坚持鄂豫皖边区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5]116
在有主力红军作后盾并大量牵制敌军的情况下,便衣队协同地方武装一部分在老根据地坚持斗争,大部分在敌占区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不仅坚持了部分老区,还开辟了广大新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便衣队在活动的多数地区实际上控制了当地基层政权,形成新的游击根据地或稳固的立足点,成为主力红军的后方。
不仅如此,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便衣队造就了一大批忠诚坚定并善于巧妙运用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斗争策略的的军政素质相当高的党政军骨干。他们成为党的宝贵财富,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立下了不朽功勋。便衣队还锻炼出了一支打不散拖不垮的英勇顽强的革命武装力量,成为后来构成新四军的重要力量,为随后坚持华中抗日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保卫和建设边区提供了坚强的武装力量。
便衣队的活动还为日后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深入开展游击战争、大力发展游击武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抗日战争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民组建便衣队的经验在各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普遍地应用和发展。当时活跃在敌占区的敌后武装工作队无论是组织形式、开展活动的方式方法还是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都与鄂豫皖边区的便衣队极为相似。这也进一步证明了便衣队这一组织形式在对敌斗争中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