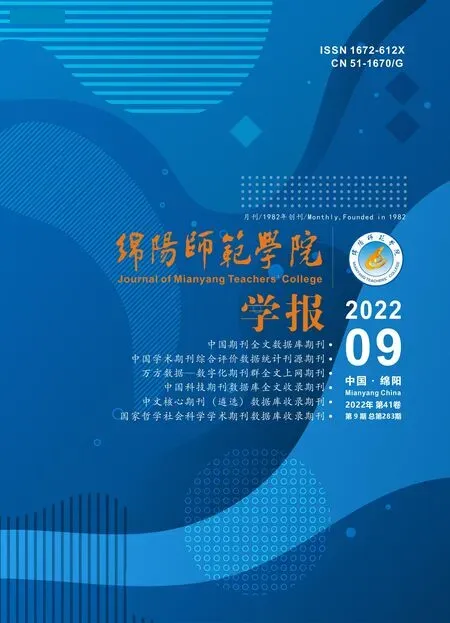无地突围
——论李佩甫《生命册》的精神困境
谢梦婷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207)
河南作家李佩甫以书写豫中平原闻名于文坛,他倾力对这块古老的土地和生长于此的各色人物的精神世界进行深刻挖掘和思考。《生命册》就是他在这一方面的积极探索,也是继《羊的门》《城的灯》之后,“平原三部曲”系列的收官之作。小说以一个从乡村走入城市的孤儿“我”的视角,通过描写平原乡村文化对个体独立性的精神侵蚀以及“突围者”的多种路径与心路历程,勾勒出中国平原乡村的生存氛围和人的复杂面相,在回眸中窥见城镇化进程中人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即个体精神自由舒展之境的无处寻觅。通过个体精神的突围历程形象地表明,乡村固然是精神困境的存在地,但城市也非精神自由的舒展地,突围的结果是无地突围。小说以之呈现出城镇化过程中,现代思想生长所需空间的缺失与构建之难。
一、作为个体精神的乡村
作为乡土作家,李佩甫一直执着于对生长于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精神给予一种深刻的表达,《生命册》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作家不是以以往那种单纯从血缘关系上透析作为个体的精神经验,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跳脱出以血缘为纽带的乡村社会来审视人们的精神脉象。小说中的“我”就与无梁村缺乏一种稳定的、天然的血缘关系,当作家以之来审视无梁村时,人们就会发现平原乡村文化环境中建立的乡村社会关系对于个体独立性的侵蚀,以及由此生成的整体压抑个体的环境氛围,使乡村成为难以摆脱的精神困境。
在乡村的精神场域中,个体对自我力量的确认与把握并非基于自律,而是通过干涉他人行为,甚至试图操控他人而获取精神满足。小说中描写的由城里下放的杜秋月和他的乡村妻子刘玉翠的关系就是典型的例子。刘玉翠是一位寡妇,经由老姑父介绍嫁给下放的杜秋月。两人婚后的相处模式并不平等,基本上是刘玉翠居于支配地位,杜秋月居于被支配地位,在生活中,刘玉翠喜欢罚杜秋月“请罪”——即让杜秋月弯腰站着背毛泽东语录,并且在长期的生活中,杜秋月“请罪”成为他们相处中的重要一部分。刘玉翠对杜秋月的不满缘于婚后她发现她嫁的这位知识分子并不如她所想像那般,而是“中听不中用,成了一个摆设”[1]300,由此把失落转化为对杜秋月的言语奚落和勒令他“请罪”的行为,在这些行为中获取精神慰藉。以至于后来,刘玉翠开了书店,“废物”杜秋月成为了她嘴里用于和书商讨价还价的一个符号——“教授”。但刘玉翠对杜秋月形式上的操控和支配,实则源于她内心深处的自卑和对杜的崇拜,那是一种下意识将自己摆在低位的对知识的臣服,这正是她嫁给杜的原因。因此婚后她在形式上将自己摆在高位对杜进行支配,不过是为了获取她虚无的精神意识中两人关系的平等。但这种平等,因为没有跳出其本身盲目依附的不合理逻辑,所以并没有能够让她得到真正的平等和精神自由,即使到最后已经成为手下有多位员工的书店经理,她依旧要拿杜的教授身份来标榜自己,还对店员小姑娘说:“你们可不能叫他‘废物’。我能叫,你们不能叫,要喊教授。”[1]317而平反后回城的杜秋月呢,只能一直像做贼一样躲着刘玉翠,连换了三家单位,每次都是被刘玉翠闹得颜面全无,只能灰溜溜地调走,这样东躲西藏无比熬煎的日子,终于在他得病一头栽倒在马路上被刘玉翠救起送医之后结束了:老杜复婚了,“他的老婆仍然是刘玉翠”[1]316。这所谓的结束,其实是前一个噩梦的回归,得了脑中风又穷困潦倒的他,只得又回到了刘玉翠的操控之下讨生活,也就是她口中的“废物”,他内心的苦和恨,也只能通过在马路牙子上大声咳嗽、大口吐痰宣泄排解,曾经那个围着围巾下放到无梁村的体面又儒雅的知识分子杜秋月,早就死在了那些无梁的夜里。
当然,有时这种操控并不以对抗的形式出现。小说中描写的另一种类型——“互助”,并非一个个体对另一个体基于友好的付出,而是乡民在取消个体独立性的乡村社会关系中操控他者的需求。梁五方是一位出色的匠人,因在镇政府盖大会堂时塑出麒麟而出名,他出色的手艺和张扬的性格得到了乡人“傲造”的评价。到了建新房的时候,梁五方不按乡村请人帮忙上梁的传统习惯,而是借助滑轮独自完成上梁,引来乡人更大的不满:
最后到了上梁时,人们觉得他总是得求人了吧?不然,那梁怎么上?可他还是不求。他借来了滑轮,一头吊在滑轮上,固定好了一处,再去搞另一处。那一天很多人围着看,看这狗日的怎样把梁放上?那是午时,阳光热辣辣的,我觉得在人们的目光里,陡然生出了很多黑蚂蚁。蚂蚁一窝一窝的,很恶毒地亮着……[1]120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很恶毒地亮着”的恨意,是因为梁五方独自完成了盖房,与乡村“互助”的氛围不符,让乡人既不能获得被求助的心理满足,也不能通过提供帮助获得对他一定程度上的干涉和操控。因而,当这种另类的操控机制在梁五方身上失效时,乡民背地里愤而称他为“长脖子老等”(眼里没有人)。正如叙述者在行文中所总结的那样——“在无梁,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是与己无关的,都可以说是‘闲蛋事’。可话又说回来,其实,真正的‘闲蛋事’,无梁人又是最愿意掺和的。比如:谁谁与谁谁……这是一种生活态度。”[1]374而在这种人人都想经由操控他人实现对自身力量的确认,从而获得精神满足的乡村文化环境之中,带给个体的,更多的不是乡邻互助的关系网所特有的淳朴乡情,而是处于被操控的非自由状态所导致的身心束缚与精神上的紧张、焦虑、敏感和缺乏安全感。在这种文化环境下,无论是操控他人或是被操控,都难以摆脱来自他人和自我的精神禁锢与生命扭曲,并在这种“染”人的风中逐渐扭曲。
群体传统对个体发展的压抑,导致其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不仅其生命能量难以完整呈现,甚至其身体和灵魂都会遭受集体力量的摧残。梁五方的悲剧结局就是如此。在小说中,梁五方因为在运动中被打倒,财产被没收,最后沦为上访专业户。而引发他悲剧的“运动”,小说中如是解释:“对于无梁村的人来说,‘运动’只是一个借口,或者说是一个契机。”[1]122而其深层的运作机制,其实还是整体对于个体的压抑需求。“表面上,梁五方是无梁村中脱离群体的一个另类,但他的故事是关乎一群或多群这样的人的故事。”[2]从梁五方越师在镇政府大会堂起脊的时候砌塑出精美的麒麟开始,村人的眼里心里已经开始积累对其不满的集体情绪,到他凭借自己的能量借来抽水机抽干水塘的水并建造起一栋房子,再到独自完成上梁,最后结婚时仍是没请村里人。他的才能、干劲、独立,都让村里人心生不满,在冗长又平庸的乡村日子中,这种集体性的嫉恨一经发酵,是很难消弭的,除非将这个所谓“各色”的人拉入深渊。终于,他们等来了运动,借着“运动”的契机,他们不仅用暴力发泄了长久积累的不满和嫉恨,最重要的是借“运动”将梁五方多年努力奋斗积攒的家业,全都摧毁了。梁五方一心只是想凭借自己的双手,不求不靠,打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这一合理的个人追求,却终因处在这个不容个体发展的环境中,不合众人嫉妒怨怼的情而破灭。他不仅被迫与心爱的妻子分离,还被逼踏上了一生颠沛穷困的上访之路,遭此变故,其精神信念完全崩塌,看清了乡村集体环境压抑个体的本质,认识到自己永无翻身的可能。绝望之后的梁五方,从曾经充满生活热情的有志青年,变成了一个赖皮上访户。
编席能手春才也是这样的牺牲者。小说描写了平原乡村在性这个问题上婚前婚后的两极表现:
等过去了很多日子之后,我才明白,在乡村,在我们的家乡无梁,对于性的态度是最原始、最保守、也是最开放的。姑娘们在未出嫁之前,那是禁地,是一个字也不能提的。可一旦结了婚,就像是破开了的瓜,是可以汁液四溅的[1]357。
婚后的女人在春才面前肆无忌惮地大谈性暗示的内容,看似和婚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但实际都受制于性压抑的大环境。已婚妇女婚后用各种性的暗喻进行交流,实则是基于性经验在性压抑环境中的一种发泄方式,而这最终也酿成了春才的悲剧。作为无梁村最帅气、壮硕的小伙子,到了开始出现性意识的年龄,在一群已婚妇女关于性暗喻的聊天中引发性生理反应,可是身处这种性压抑的大环境,春才不仅要忍受身体生理上的折磨,更难纾解的是内心萦绕着那种做错了事的羞耻感。在对蔡苇秀产生爱慕之情时,春才只能压抑自己的感受不敢承认,更不敢表白,直到后来真的做了错事:偷看苇秀洗澡惊动了老姑夫和全村人。虽然未被抓包,没人知道是他所为,但他自己心中那来自道德感的羞愧、谴责和惶恐已经让他背上了沉重到喘不过气的精神包袱。在这种环境和自我的双重压抑中,春才内心的痛苦已经超出了自身可承受的范围,以至于做出了割除自己生殖器的举动。
小说中乡村社会关系的建构是以牺牲个体空间为前提的,个体在操控他人中获得自我操控的精神快感,并在互相牵制中塑造了整体压抑个体的精神氛围,乡村因此成为了精神困境的存在地。
二、突围中的自我建构
这种困境和氛围,不仅弥漫在无梁村这一方水土上,更关涉着离家闯荡的“我”。叙述者“我”带着平原乡村整体压抑个体的生存经验,带着如何在城乡社会身份的转换中实现自我建构与自我确立的问题,并以此经验观照自身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即“突围者”们的多种面相和多样路径。
首先,是以狂热投入金钱与权力浪潮的姿态突入城市,以期实现对自身力量的操控和确认。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骆驼。在叙述者“我”的眼里,骆驼的人生经历是一个依靠经济积累突破乡村围城的样本。大学同学骆驼邀请“我”北上闯荡,给予“我”离开省城大学,逃脱来自乡村社会关系对个体精神羁绊的契机。在小说中,骆驼是一位来自大西北的中文系才子,行事果断、大胆,以命相搏要回了无良书商的欠款,而后和“我”一起炒股、公司上市,从而一步步积累了巨额财富,但最终却迷失在权力和金钱中,走上腐化和违法之路,坠楼自杀。金钱确实给骆驼带来了对人生的操控感——“光头骆驼在五星级的北京饭店大堂里大步走着,穿着一件黑色的油纱休闲褂,走路仍然是袖子一甩一甩的,不时摸一下光头,就像天生就该是走在红地毯上的人,天生就是领袖人物”[1]324,但这种虚无的操控感建立在权力与金钱勾结的不稳定结构上,正如“我”所反思的“我们都是百姓出身,上面没有‘伞’。就算有‘伞’,也是借人家的。朗朗睛空,自然无事。可一旦暴雨倾盆而下,借来的‘伞’还能用么?”[1]330以至于东窗事发,骆驼精神崩溃彻底绝望,以肉体消亡的方式结束了这一利用金钱与权力实现对人生把控的路径。
其次,是经由“入城后再返乡”实现的对于平原生存逻辑的主动适应,这种“自我补偿”式的主动适应,实则是对乡村生存逻辑的自我确证与再度维护。
小说中的虫嫂和蔡苇香,是入城后返乡的代表,不过她们“突围”的路径也有所不同。虫嫂是一位身高只有一米三四的外乡妇女,嫁给无梁村患有腿脚残疾的老拐,婚后生下三个孩子:大国、二国和国花。因为老拐腿脚不便,虫嫂为了养活一家人,多次偷窃农作物,屡被示众而不改,而后还为了获取养家的物质而出卖肉体,被村里的妇女围攻,成为村里品行最卑劣的妇人,不仅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也使得母子关系恶化,这一切屈辱和心酸,虫嫂和着血泪忍了下来。在无梁村,虫嫂成为众人鄙夷和孤立的对象,而后因为国花上学的原因,虫嫂随其去了城里,靠收破烂为生,其儿女也先后在城里安家。尔后虫嫂回村的举动,可视为对她早期在村里生活的自我补偿:
虫嫂这次回来,买了整整一布袋大白兔奶糖!每一家都去送了礼,一家一小袋大白兔奶糖[1]229。
临死前,她伸手去够那把破扇子,她说:扇子,这把扇子跟了我多年……她身上没有力气了,够了几次,没够着。临咽气时,她伸手指了指,喃喃地说:我不连累人。我还有把破扇子……待解了那缠在扇子把儿上的破布,那布黑污污的,一层一层的……发现里边裹着的竟是一个存折,存折裹在扇子把儿上,由一层层的黑布缠着,存折上有三万块钱![1]230-231
从早年靠偷盗养活家人到暮年对“我不连累人”信念的执着,虫嫂在由乡进城、由城返乡中寻觅自我确立之路。以一种类似于衣锦还乡的姿态分发大白兔奶糖,获得从索取者到施舍者身份的转变,通过为自己攒下三万块钱的丧葬费,获得“我不连累人”的相对独立的精神姿态。但虫嫂自我确立的方式,并没有跳出平原乡村的逻辑,不过是在整体压抑个体、取消人的独立性的大氛围中寻求对早年精神缺憾的弥补而已,一言以蔽之,是主动适应平原乡村生存逻辑。
相比于虫嫂只是追求通过以衣锦还乡的姿态站立在人们面前,以期获得对自己早期屈辱生活的心理补偿,蔡苇香的回归则带有挑战意味,挑战曾经压抑她整个童年乃至少年时期的平原生存逻辑:在由城返乡时带上了她的板材公司,这一相对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极有力地冲击了平原乡村的旧有秩序和生存氛围。蔡苇香是老姑父的女儿,早年因为“匪”(离经叛道)离开无梁村,进城成为一名洗脚妹。而这“匪”实则从她很小的时候,村里就漫天弥散议论其父作风有亏的闲言碎语,以及幼小的她无数次于黑夜中被母亲带着去“抓奸”的经历所致,在这种畸形的环境中成长,谣言、嘲笑和轻蔑一点一点在她的眼睛和心里割下口子,每个伤口都长满了仇恨的蚂蚁。因而稍长大成人些,她便决心逃离并反叛这乡村。后来在大城市闯荡发家之后,便又回到无梁村开木材厂,“匪了”的蔡苇香摇身一变成为板材公司的“蔡总”,无梁村的村民也被组织起来成为了板材公司的工人,当“我”想通过闲聊向村民打探消息时,却出现了不同于以往平原乡村的一幕:
国胜家的儿媳妇说:在这鳖孙板厂,成天三班倒,没明没夜的,人都活颠倒了。我啥也不知道。保祥家儿媳妇说:这你得去问蔡总,蔡总让咋说咋说。海林家儿媳妇说:我才嫁来两年,只要给钱,叫我干啥我干啥。水桥家儿媳妇说:现在的人,不狠能挣钱么?麦勤家女儿说:能走的都出去了,我是出不去,要不我也走了。管他谁谁呢。倒是兔子家儿媳妇嘴快,说:反正给了一百块钱,俺啥都不知道,也说不清。啥头不头的,人都死了,还问这干啥?[1]425
村民的反应更多集中在自己的生活而非他人的家长里短,虽然没有了往日平原乡村独有的亲密感,但却为个体留出来一定的私人空间,模糊的个体独立性看似在某种意义上被描画出来。蔡苇香的板材公司虽然冲击了平原乡村的生存氛围,但她自身却由于内在精神力量的薄弱而难于抵抗强大的乡村伦理逻辑的侵染,深陷于她将父亲的头颅种成石榴树的传言之中,遂成心病,郁结难纾。因此,蔡苇香才要为父母举办盛大的合葬礼为自己正名,直到乡人下坟捡老姑父遗骨时,当众证实头骨仍在她才得以释然。尽管板材公司以新的生产方式冲击了乡村的旧有秩序,但根植于平原乡村人心中的旧有文化秩序的作用依旧强劲——关于蔡苇香父亲头颅的传言,本可以用现代的科学方式查验和证伪,但为了使乡民接受,却需要大费周章以乡下传统的方式迂回自证。蔡苇香这个角色的塑造,也从侧面反映平原乡村的生存逻辑在文化层面上对个体的塑造,即使是蔡苇香式“入城—再返乡”的回馈模式,也难以从根本改变其文化氛围,反而被这种平原乡村的文化氛围所再度吸纳。
最后,通过叙述者“我”对乡村精神围城的自觉突围和突围至城市也难以构建个体精神空间的失败结果,揭示了城市也并非精神自由的舒展之地。“我”逃离乡村进城这一行动,可以看作对身处乡村精神围城的个体最朴素的信念和认识的揭示,即认为平原乡村这种吞噬个体的精神氛围是固定在乡村这个地理场域中的,城市便成了理所当然的可突围之地。因此,一开始“我”的确以为只要自己的双脚离开乡村踏入城市,就能够摆脱平原乡村那吞噬个体边界的文化氛围,就能把乡村的社会关系全都留弃在身后的土地,就能够在城市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清晰的、独立的自我。文中对“我”初进城的心理描写里分明可见“我”因为自觉摆脱故乡而深感欣喜:
不客气地说,最初,我走在省城的柏油马路上就像是走在红地毯上一样,很幸福。路两旁亮着一盏盏路灯,那光芒是五彩的,这就是我的未来。周围的自行车铃声也十分悦耳,公共汽车刹车后的那一声“嗞”很温馨,很生动……我很想给这个城市打声招呼,嗨一声:你大爷的,我来了[1]2。
然而,如愿突围至都市的“我”,仍难以摆脱来自乡村集体的操控感,才惊觉城市同样不是突围的目的地。当“我”刚入职省城大学时,在乡人眼里“我”已经是城里的“官”,可以为他们提供便利,便频频来电求“我”办事,从孩子上学、农用车撞人被扣到找工作、看病就医,这些求助的电话让“我”苦恼不已。那一张张“白条”就是从乡村长伸出来的手,不停地干扰着“我”在城市的自我建构的努力:乡人托“我”办事的条子,一次次将“我”置于道德的煎熬之中。一边是的确有恩的乡人,一边是刚刚开始的新生活,在“我”为求心安,替村里人几次三番的托关系“求助”之后,“我”初入单位所建立的微薄的人格凭信,便轻而易举地被瓦解。单位的人们拒斥的是“我”,更是“我”代表的这种平原乡村侵蚀个体独立性的社会关系和生存逻辑。“我”最终“陷入了精神受责与灵魂漂泊的困境中”[3]不堪重负,只能通过逃离省城的教职,切断与故乡的联系,另寻生路。
无论是骆驼式的金钱积累之路,虫嫂和蔡苇香“入城再返乡”的模式,还是“我”的“在城”模式,都以失败告终。作为个体,他们在意识到乡村是精神困境存在地之后,产生了突围的动力,却在突入城市和突回乡村都失败之后才惊觉:哪里都不是目的地。
三、个体凝望中的城乡同构精神困境
正如“我”回答蔡苇香关于回乡问题时所说的:“得找到一个能‘让筷子竖起来’的方法。”[1]433那究竟什么才是“让筷子竖起来的方法”?为何难以寻到?在小说的设定中,“我”的精神游离于城乡之间,借助“我”的视角,可以重新进入小说中关于城乡精神困境的探讨和反思,开启了对个体精神自由舒展空间为何在城在乡都难以寻觅这一问题的反思。
一方面,“我”的精神始终游离于城乡之间,这种“游离”,是糅合了平原乡村生存记忆和城市生活经验所产生的跨越城乡的生命思考,并借此剖析了平原乡村精神困境的成因。在经济上,物资的缺乏导致村民挣扎在生存线上,也正因为物资匮乏和生产方式的单一,虫嫂迫于养家的压力偷盗农作物而引发半世悲剧;在权力分配上,平原乡村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衍生出对“官”的敬畏和关系的迷信,这也导致“我”进城之后因乡人无休止的托关系办事而不得不被迫切断与乡村的关系;在文化氛围上,个体缺乏自由的精神空间,总体上平原乡村是一个致密联系的整体,微观上个体在缺乏独立空间的同时,还要受到其他人的越界“操控”。基于此,小说中“我”脱出平原乡村,走向省城都市,实则内含着寻觅个体精神空间,脱离侵蚀个体精神独立性的乡村文化氛围的希冀。这种希冀脱胎于“我”的平原乡村生存经验,却破灭在我的城市生活体验中。“我”初到都市,便难以摆脱这种来自整体的操控感和平原乡村施加于“我”的负担:
我身上背负着五千七百九十八亩土地(不带宅基),近六千只眼睛(也有三五只瞎了或是半瞎,可他们都看着我呢),还有近三千个把不住门儿的(有时候,能把死人说活,也能把活人说死的)嘴巴,他们的唾沫星子是可以淹人的[1]1。
而在后期,拥有充足金钱与较高社会地位的“我”,也似乎始终没有寻觅到离城入乡所想得到的东西,伴随着金钱而来的却是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我嫉妒窗外的树,我嫉妒健康人的笑声,我嫉妒自由来去的风,我甚至会嫉妒落在窗台上的麻雀……我告诉你我的感觉。首先是恐惧……要钱有什么用?一个一个的念头,纷至沓来的念头,逼得人想疯![1]392-393
另一方面,通过“我”立于城市对平原乡村生存体验的回望,反思了个体为何在城在乡都难以寻找到精神的空间,借助由城入乡知识分子的视角,探寻城乡发展所面临的更深层的共同困境。因为骆驼坠楼离世,“我”出车祸住院,在医院中,“我”对故乡无梁村进行了再梳理:
还有的时候,我还会想起童年的那些时光。那日子一幕一幕地在我眼前闪现……每每,在睡梦中,总觉得有人在喊我。一夜一夜,我听见有人在喊:孩儿,回来吧。孩儿,回来吧[1]396。
经过回忆的再加工,因车祸住院的“我”,记忆里的无梁村不只有侵蚀个体边界的文化氛围,不只有童年的饥饿和被边缘化,而是更多地回忆起故乡熟悉的风物:
我怀念蛐蛐的叫声。每当夜静的时候,蛐蛐就来给你说话了,一声长一声短儿,永远是那种不离不弃的态度,永远是那种不高不低的聒语,当你觉得孤单的时候,当你心里有了什么淤积的时候,你叹它也叹,你喃它也喃,就伴着你,安慰你,直到天亮。天一亮,它就息声了。
我怀念倒沫的老牛。在槽前卧着,一盏风灯,两只牛眼,一嘴白沫,那份安然,宁人。我甚至怀念牛粪的气味。黄昏时分,在氤氲着炊烟的黄昏,牛粪的气味和着炊烟在村庄的上空飘荡着,烟烟的、呛呛的、泛着一丝丝的日子的腥臭和草香,还有嚼过后老牛反刍的那种发酵过的气味,臭臭的,有一种续命的腥香……[1]397
平原乡村上的牛毛细雨、瓦沿上的滴水、半夜的狗咬声、蛐蛐的叫声、倒沫的老牛、黄土路上的老牛蹄印、静静的场院和谷草垛、钉在黄泥墙上的木橛儿、四条木腿儿的小凳、门搭儿的声音和有风的日子……对这些故乡景物的回忆,不是简单的风景描写,而在一定程度上是“我”经历了车祸和骆驼离世的变故后,对平原乡村生存体验进行的筛选和再整合。这种筛选和整合,偏重景物而轻社会交往体验,偏重熟悉感的挖掘而淡化不适感的描写。其中所传达的诉求,是立于城市回望乡村,从一个新的视角重审个体精神困境:何处是个体生命自由舒展的所在?显然,“我”对故乡风物的回望已经表明了都市无法提供这一空间,因此“我”与骆驼突围入城的结局早已注定了是失败的。而回望的对象——平原乡村呢?故乡风物确是美好的,能抚慰人心,但前提是将其与乡村取消个体独立性的社会关系和整体压抑个体空间的文化氛围完全剥离开,这美好才能生发。因此,这一永远无法抵达的不存在的乡村,显然也非个体生命自由舒展的所在,所以虫嫂和蔡苇香“入城再返乡”的突围路径也失败了。“我”既不能找到这一所在,不能找到一个“让筷子竖起来”的方法,便只能生出”一片干了的、四处飘泊的树叶,还能不能再回到树上”的绝望之感[1]433。对这一问题的叩问,凝结着“我”对个体跨越城乡寻觅精神舒展空间却最终失败的反思。
“让筷子竖起来的方法”,有了工厂的平原乡村没有找到,物质上大步走向“现代化”的城市亦无,通过个体精神的突围历程形象地表明,乡村固然是精神困境的存在地,但城市也非精神自由的舒展之地,突围的结果是无地突围。作家通过有乡难归,入城难融的离乡入城知识分子视角,揭示了城镇化过程中城乡面临的更深层的共同问题:缺失现代化思想生长所需的空间与此空间的构建之难。
四、结语
通过描写平原乡村文化环境侵蚀个体独立性的精神围城以及“突围者”的多种路径及心路历程,《生命册》勾勒出中国平原乡村人的多样面相和生存氛围,在回眸中窥见城镇化进程中人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即个体精神自由舒展之地无处寻觅。个体是如何经过从乡村精神围城到自我建构的突围失败,最终回到精神之围的原点,发现无地突围的现代困境与悖论。《生命册》凝聚了李佩甫一生对土地的了解和思考,完成了对乡村压抑个体生存空间的质询,指出了脱离乡土精神规训之艰难,展现了个体精神自由舒展空间之难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