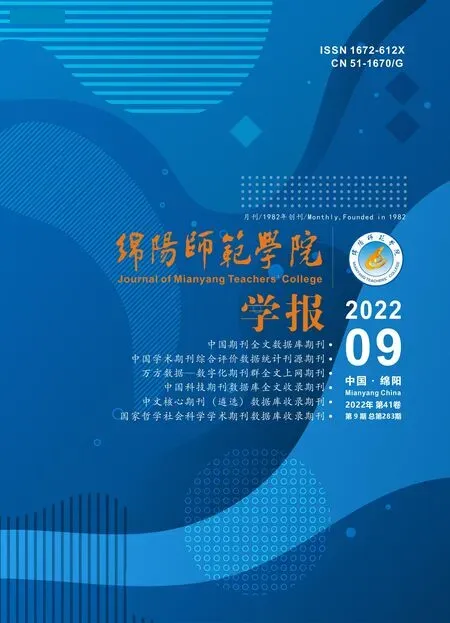论贾平凹新时期改革小说对现实主义的探索
江 河
(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襄阳 441053)
在费秉勋看来,贾平凹20世纪80年代写实的改革小说“不全合他的艺术气质,写起来失去了一些自由和灵气,乖违了他的创作心境”,而他的写意性的小说“与他的艺术气质更为相合,写起来更加自由和适意,充满创造快感,也更容易对中国文学做出独特的、新的贡献”[1]134。费秉勋是贾平凹的老师,对贾平凹非常了解,他的《贾平凹论》是研究作家早期创作的权威著作,但笔者对他上述观点有不同看法,主要在于笔者认为他过于认可“非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过于强调贾平凹艺术个性中“自由适意”的、追求审美愉悦的一面,而忽视了他创作追求中本来就有的追求责任感、使命感的一面,意即贾平凹的小说艺术追求里固然有唯美的、抒情的、写意的一面,但也有务实的、济世的、写实的一面。正如贾平凹所说:“个人的生活、环境、性情等等都可以影响到精神状态,但如果仅仅如此来建构你的艺术世界,那只能沦于小格局。写小说并不是一种完全的自慰,首先我不是这样的……一个作家得有情怀,个人的命运得纳入整个人类的命运,这才可能使作品有大境界。”[2]80-81笔者认为,贾平凹的艺术追求里有写意、抒情、自由适意与写实、叙事、责任使命两个方面,并且力图将两者加以结合。以下将以贾平凹新时期的改革小说为蓝本,分析其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探索及其贡献。
一、鲜明的批判精神
贾平凹在1979年至1982年的一批短篇小说就表现出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这一时期的作品由于作者人生阅历尚浅和深入基层不够,还显出浮泛和书生意气。当1983年贾平凹一头扎进商州的大山,深入到人民和生活的海洋中,其对现实和生活的感受自是不同。可以说,贾平凹对20世纪80年代家乡农村发展状况是满意的,对国家改革开放、包产到户、鼓励多种经营的政策是拥护的,因为他看到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面貌的改善,而这些都在他的改革小说里体现了出来。他在《秦腔》后记里也用散文的笔触,生动的、饱含情感的语言书写这种心情: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里,故乡的消息总是让我振奋,土地承包了,风调雨顺了,粮食够吃了……那些年是乡亲们最快活的岁月……他们很舒心……。改革头十年农民的幸福满足是实实在在的,于是他写了《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和《腊月·正月》。
贾平凹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小说顺应了改革的时代洪流,那是否就不具有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呢?回答是否定的。其批判精神主要体现在真实反映改革初期现实问题和对阻碍改革力量的批评上。这几部改革小说在揭示现实的力度、深度和广度上是逐渐递进的。《小月前本》还留有从写意向写实过度的痕迹,《鸡窝洼人家》和《腊月·正月》则减少了主体抒情写意的成分,变为纯正的写实,而到了《浮躁》却又注意在写实的基础上运用一些象征和意象,从而具有了20世纪90年代小说“意象化写实”的一些雏形。这些小说反映的现实问题主要包括:(1)改革初期政策的不确定、信息不通畅给农民带来的困扰。《腊月·正月》中,王才将自己的地转包给狗剩,公社王书记也拿不定主意,说县委讨论了三个晚上,谁也不敢说对还是不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而是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这就给了以韩玄子为代表的思想保守势力可乘之机。(2)土地经营承包责任制落实后,农民经济独立,各自为政,干部人浮于事,农村的基础建设和文化活动无人管理,基层治理出现了“真空”。土地承包后,村民把牛都卖了,地里没有可施的肥,化肥成了稀罕物。“韩玄子为此也发过牢骚,认定这几年,粮食丰产,那是人出了最大的力,地也出了最大的力,若长此以往,土地都板结起来,还会再丰收吗?”这段话反映出农业粗放式生产模式对土地的索取,而这种耕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农民自留地的中间,本有一条可以过马车的路,但禁不住村民的“蚕食”,变得歪歪扭扭,韩玄子在内心叹道:“人心都瞎了,瞎了,没人修路了!”本来是活跃村民文化生活的闹社火,却因为没有经费摊派到村民头上。土地经营承包责任制落实后,基层政府因为缺少资金或者不愿作为,使本应该由政府承担的基础设施维护和文化建设无人管理。(3)基层权力寻租和干部家族化现象。《浮躁》揭示了从仙游川、两岔镇,直到白石寨、州城的基层政权被田、巩两大家族所把持的局面,以金狗、雷大空为代表的“杂姓”家族要想在改革的时代赢得一些话语权要付出何等惨重的代价。(4)改革遇到的阻力。阻碍改革的力量,主要指王和尚、才才、灰灰、韩玄子、田中正、田有善、巩宝山等人。王和尚、才才、灰灰都是老一代农民,他们勤劳本分,吃苦耐劳,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但随着商品经济在山村兴起,他们重农轻商、不讲科学、思想保守、道德守旧的品性就成为了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阻碍。王和尚试图用父亲的权威强迫小月接受包办婚姻,才才在小月面前表现得懦弱畏缩、中庸内敛,一旦发现门门对小月的追求又变得反应过度。这样的家庭和婚姻是追求自由、美好新生活的小月所不能接受的,因此放弃才才接受门门是小月必然的选择。
具体到作品中,其批评角度又有不同。《小月前本》和《鸡窝洼人家》都将改革进程中两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选择,置换为爱情和婚姻的世俗化故事,将宏大的政治经济命题具象化为作家擅长的情爱故事,这是这篇改革小说最大的特点。《腊月·正月》中则是将韩玄子和王才的矛盾推演成新旧两种力量的正面斗争。韩玄子和夏天智类似,都是退休教师,桃李满天下,大儿子成了名人,是家族的骄傲,在当地声望很高,但在家事、村事的烦扰下失去晚年生活的平静,在他们身上都有贾平凹父亲贾彦春的身影。韩玄子是作为镇上改革新生力量的对立面出现的,他并不反对包产到户,只是对王才的快速致富感到恐慌,一是打破了自己大半辈子积累下的一人独大的名望,二是破坏了大锅饭时期共同贫穷的均势。他的性格缺陷是好面子和专制、自私。被称为“商字山第五皓”的声名增长了他内心的贵族意识,因此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声望,选择和公社的领导迎来送往,对王才这样的底层小民不屑一顾,更是不甘心在声望的竞争中败落。韩玄子和王才在买公房、闹社火、书记拜年等几次较量中都遭遇败北,旧观念遗老的身份显露无疑。《浮躁》的批判性主要体现在州河两岸家族权力垄断对新生力量的压制和扼杀上,具有整体性、宏观性和政治化的特点。仙游川乡党委书记田中正和嫂子私通、觊觎小水,白石寨县委书记田有善明知田中正意欲强奸小水的事实,仍然包庇他;巩宝山为了娶女学生将老婆逼得上吊,奸污欲救金狗出狱的石华;省军区司令许飞豹为了自己的心愿,拨专款为牺牲的老上级田老六修建烈士纪念亭。为了在纪念亭落成典礼上款待好上级领导,白石寨县委指示:必须拿出最能代表当地的稀罕之物,两岔镇乡组织村民猎熊,导致福运死于非命。巩宝山和田有善发现金狗利用他们的矛盾想整垮他们后,不惜动用公权力将金狗构陷下狱,借用黑社会势力杀死雷大空。从现实层面来说,与其说《浮躁》展现了改革初期人们浮躁不安的心态,不如说它揭露了州城地区宗法制家族势力阻碍改革新势力的事实。
二、写人物——普通人、“好人”、立体的人
贾平凹改革小说在人物塑造上既具有时代“共名”特点,也有自己独特的个人选择——那就是写普通人、“好人”和立体的人。
首先是写普通人。和20世纪80年代一些表现改革急先锋的小说不同,贾平凹的改革小说描写的都是城市和乡村的普通小人物,他们是农民、退伍军人、乡镇企业业主、记者等等。在新时期改革小说中乔光朴、李向南、龙种这些改革“明星”是厂长、市长、支书等政商翘楚,他们在改革的最前线进行着政治、经济的斗争,“引领”着群众走向康庄大道。贾平凹笔下皆是平民小人物,小月、才才、门门、禾禾、灰灰、麦绒、烟烽都是普通农民,王才是乡镇食品厂的小厂长,金狗、雷大空、福运、小水等都是出身于仙游川的普通农民。贾平凹出身农家,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并且对生活了19年的商州农村、农民十分熟悉,当他试图再现中国改革现实时自然就选择了他最熟悉的商州农村的农民生活。此外,从他后期的长篇小说《古炉》《老生》《山本》来看,他有着“反英雄”的历史观,他不认为历史是由少数英雄人物所创造的。这一点从他早期作品就可以看到端倪,即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小说来看,除了金狗具有一些“英雄”的气质和色彩外,其余人物皆为普通的平民。
其次,是写“好人”。贾平凹在一封信里写道:“《小月前本》中的门门、小月、才才都是好人,《鸡窝洼人家》中的灰灰、禾禾、烟烽、麦绒也是好人,《腊月·正月》中的韩玄子、王才亦都是好人,《九叶树》中的石根、兰兰又都是好人。正因为都是好人,他们在目前的变革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也正是这种微妙的变化才构成了当今农村最丰富的的内容。”[3]13-14贾平凹的改革小说中除《浮躁》以外没有一个“坏人”,写的矛盾也不是敌我、阶级矛盾,而是两种不同观念、思想之间的碰撞和斗争,如现代和传统、封闭落后与开放进步、只重农业和多种经营。虽然也用了革命文学惯用的二元对立的人物情节模式,但对立的双方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好人或坏人,而是他所说的“好人”,即好坏人或坏好人。
再次,是写立体的人。贾平凹说:“我表现出来的他们就是好人的形象,或是好坏人的形象。在具体描写的过程中,我喜欢用以坏人来写好人,以好人来写坏人的办法;目的只有一个,使所写的人更具真实。”[3]13-14对此,莫言也有类似的说法,他的一个演讲题目就叫《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这种写法一方面是对将人物政治化写法的摒弃,另一方面是要写出人的多面性,让小说人物更加真实可信。人无完人,“好人”也有缺陷,如门门沾染了一些世俗味和油气,没有定性;禾禾相比于对事业的执着坚韧,对待爱情上却表现得被动、胆怯和犹豫;王才善良宽容,但过于懦弱、忍让。“坏人”也有优点,作为他们的对立或对照面的人物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才才善良朴实、勤劳踏实,要不小月也不会在他和门门之间举棋不定;灰灰也善良宽容,要不也不会收留落魄的禾禾,照顾孤苦的麦绒母子,他也并不固执,当目睹禾禾搞副业致富后,他也从善如流,做起了挂面;韩玄子虽看不惯王才处处与他作对,但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关心村里的公共事务,调节纠纷,帮助弱小,兴办社火。贾平凹1983年之前的小说人物性格比较单一、平面化,缺少发展变化的过程,如《姊妹本纪》里的张盼儿、张兴儿、张水儿,《白莲花》里的夏西韦、延俊儿、田羊英,《二月杏》里的二月杏和大亮,《山城》里的礼平、高云、秀儿,《蒿子梅》里的高梅等,这些人物大多比较脸谱化,好坏分明,从出场到故事结束都是一个面目和个性。而在1984年后的改革小说里,人物性格变得更丰富,更立体,也更真实,除了上面提到的写出好人的坏和坏人的好外,人物的性格开始有发展和变化,如小月在比较门门和才才二人的品性能力后,从被动接受订婚到大胆地打破包办,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更不用说《浮躁》中金狗、雷大空、小水等人的性格蜕变和成长,都体现出贾平凹在现实主义小说中人物塑造方面的变化与发展。
三、介入现实的角度——文化、伦理、道德、人性
改革小说一般以改革的弄潮儿为中心人物,将他们置于改革事件的风口浪尖,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表现主人公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破旧立新的改革魄力和巨大成效。改革家们虽然也会遇到各种挫折和阻力,付出一些代价,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最终会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因此,整体来说,改革小说和伤痕、反思小说一样,都属于宏大叙事。但贾平凹的改革小说选取了更小的切入角度,是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如他所说:“这一组小说的内容全不在具体生产上用力,尽在家庭、道德、观念上纠缠。”[4]25也就是说,他的改革小说较少从政治、经济角度直面改革(《浮躁》例外),更多是从文化、伦理、道德、人性的角度来表现“风雨初至时各层人的骤然应变,其文化结构、心理结构出现了空前的松动和适应调整”[4]25。在写于同一时期,但未被列入改革小说的《九叶树》(1984)和《西北口》(1985)中,就表现出农民道德观的一些新变化。山村少女兰兰和安安受到来自城市的何文清和冉宗先的引诱失身,她们青梅竹马的恋人石根和小四虽痛苦万分,但还是接受了迷途知返的恋人和肚中的孩子,这表明新时期山地农民的道德观有了突破,新的道德伦理正在形成。《小月前本》中写到18岁的小月在河里裸泳,感受到自己生理和心理的变化,包括她对才才大胆的性试探,选择门门后热情的拥抱、接吻,都说明女性性意识的觉醒、主体意识的增强,以及农村传统封建意识的破冰。金狗和雷大空从道德上来说都是有瑕疵的人物,金狗为跳出农门有一番作为,和田中正的侄女英英发生性关系并订婚,以此作为到州城日报当记者的筹码。进城后又和有夫之妇石华发生肉体关系,形成一男三女的关系模式。这种一男多女的模式从《浮躁》开始,延续到《废都》《白夜》《高老庄》等,而以前的小说基本都是一女多男的模式,这表明了作者在男女关系观念上的变化。雷大空更是有“浪子”和“混世魔王”的习气,经济上攀附权贵、买空卖空、以劣充优,生活上也很不检点。尽管如此,贾平凹对他们表现得宽容甚至赞美,这从他给雷大空写的激情洋溢的祭文即可看出,他认为:“代表社会前进的力量,作为一个人来讲,并不一定就应该是通体完美的形象。”[5]28在贾平凹看来,像金狗、雷大空这类在社会大变动、资源大重组时代的“草莽英雄”是不该用一般的道德标准来规范的,他甚至可能认为道德的越界和冲撞是“现代意识”的体现,《废都》似可证明。
当然,贾平凹新时期的改革小说也存在一些局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维度单一。刘再复认为具有四个维度才是具有“整体观”的文学[6],贾平凹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小说只有“国家·社会·历史”的维度,缺乏“叩问存在意义”“超验”“自然”的维度,《浮躁》具有一些“超验”和“自然”的维度,不具备“叩问存在意义”的维度。另外三个维度只有在20世纪90年代《废都》之后才开始具有。二是观念先行、模式陈旧。贾平凹的改革小说都使用了二元对立的情节结构模式,事先就预设了一个改革派胜过保守派的理念。《浮躁》更是将“浮躁”的时代氛围笼罩在整个故事之上,对“浮躁”时风的理解和把握并不能与事件人物完全匹配。为了实现改革派的胜利,时常使用“清官模式”,显示作家并不能在现实中为人物找到胜利的理由,只好空降一个“清官”了事,《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都存在这种情况。三是理论思辨的薄弱。贾平凹并不是一个擅长理论思辨的作家,偏偏在《浮躁》中试图对80年代中前期的社会风气做一个整体的、哲理性的思辨,除了通过人物对话直白地评论时政,还不惜造出一个考察人对“浮躁”的内涵和成因大加评说。
基于以上对贾平凹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探索的分析,笔者把他的写实艺术概括为“抒情的写实”——这本是人们对《史记》的评价,如鲁迅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李长之说司马迁的人格精神是“浪漫的自然主义”,因此《史记》的创作手法可以解释为“浪漫的写实”或“抒情的写实”。之所以如此概括,是因为贾平凹的写实主义继承了中国古代悠久的抒情传统和以史传为源头的叙事传统,糅合了日常、魔幻、意象、史笔等多种元素,“表达心迹”和“记录社会”的写作诉求此消彼长、彼此交融,形成了开放多元、独具特色的抒情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