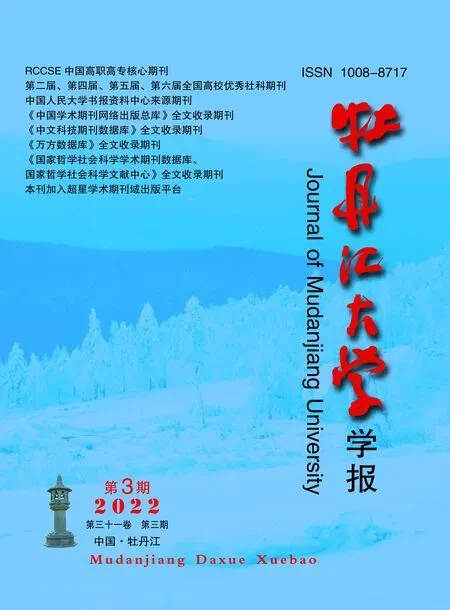《梅雨之夕》和《尤利西斯》中西意识流之比较
陈 珊
(兰州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50)
“意识流”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1918年,由英国小说家梅辛克莱首次使用。“意识流”主要指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和艺术表现手法,在英、法、美等欧美国家广泛流行的一种小说流派。最早的意识流小说通常被认为是1881年由法国作家艾杜阿·杜夏丹的《月桂树被砍掉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则代表了意识流小说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是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里程碑。
一、意识流的产生及发展
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活动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三个层面。“意识”是心理结构的最高层面,是心理中感知、情感、想象、回忆、意志、前意识及潜意识等一切因素的主宰,它控制着整个心理世界,协调它们的活动,使之有序展开。由于它的作用,人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生活才得以正常地进行。“前意识”位于意识之下,它是一度属于意识的观念、思想、印象等,因与当下实际生活关系不大或根本没有关系,被悬搁于心理的角落,好似暂无用而置于储藏室里的东西,在意识进行活动时被调了出来。弗洛伊德说:“我们可以把那些容易从无意识状态转换成为有意识状态的一切无意识的东西更好地描述为‘能进入意识的’,或是‘前意识的’。”因此,前意识又是联系意识与无意识或潜意识的中介环节。在意识与前意识之外,是“潜意识”,即被压抑在心灵最深处,自己无法觉知的部分,但其又很活跃,总是先到达意识层面。[1]心理学家对人们意识领域的关注也逐渐影响到文学界,意识流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了。意识流的产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是意识流的产生受现代西方心理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思想的影响,文学家也开始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状态。另外一个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受当时西方社会动荡和激化的社会矛盾的影响;二是受当时哲学思潮和心理直觉理论的影响;三是受传统文学变革的影响。20世纪后,西方文学转型,出现了整体“向内转”的趋势。
意识流文学在西方起源后,迅速流入中国。曾艳兵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概论》中指出:“意识流”流入中国经由两条路线,一条是间接流入,由西方途径日本“流”入中国;另一条是直接流入,由西方直接“流”入中国。间接流入路线稍早于直接流入。”[2]如果以时间来划分,“新感觉派”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运用现代派创作方法,特别是意识流艺术方法创作小说的独立的文学流派。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中的意识流文学特征是文学史上不争的事实,新感觉派作家同样与乔伊斯、普鲁斯特、伍尔夫、福克纳等创作的意识流小说有着许多的差异,他们表现出的是中国特色的意识流。
二、意识流文学的内心独白与内心分析
弗洛伊德关于艺术的基本看法,用一句话概括表述:艺术是艺术家未满足的欲望的幻想性实现。转移他所有的兴趣和力比多,构成幻想生活中的欲望。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本能欲望并不能任意发泄,它要受到代表社会伦理道德的“超我”的制约,同时它还需要得以发泄或求得满足的足够手段。于是幻想的生活就成了它求得实现的途径或手段。意识流小说也自然而生。我们这里引用美国评论家汉弗莱的定义,他在《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一书中指出:“……海平面以下的庞大部分才是意识流小说的主旨所在。”从这个层面上讲,意识属于冰山一角,而海平面以下大部分就是前意识与无意识。因此,我们可以给意识流小说进行如下界定:意识流小说描绘的“流动的意识”侧重于前意识和无意识,在于探索意识未形成语言层次的部分,主要是为了揭示人物的精神存在和内心活动的复杂变化。我们把改变本能的目标及对象成为一种更富有社会价值的东西,称之为升华。[3]
对意识流的研究和把握侧重点就要放在朦胧的意识部分,即不能以理性语言明晰表达的意识层次,这就要借助“自由联想”和“感官印象”,意识流作家凭借着个人的印象和幻觉来确定外在事物与内在意识的联系。意识流小说家认为,最好的表现手法是内心独白和内心分析。法国作家杜夏丹说:“内心独白是人物内心深处最接近无意识地带的思想,是摒弃逻辑关系的未加分化的状态……,意识流的内心独白不像传统小说、戏剧那样反映的是自我意识汇总在作者的叙述之中。”[4]因此,意识流小说的内心独白大多表现人物的无意识和前意识层面,一般杂乱无章,无规律可循,比较适合于刻画内向型、忧郁型变态的人物心理形象。
三、《梅雨之夕》和《尤利西斯》的心理描写分析
我国读者接触到的西方现代主义意识流经典作品较多,但它的晦涩难懂让很多读者都望而却步。与此同时,我国也出现了很多中国特色的意识流作品。那么,中国的意识流作品与西方的意识流作品究竟有何区别呢?我们以国内小说《梅雨之夕》与国外小说《尤利西斯》的心理描写段落来进行分析。
首先以施蛰存的经典心理分析小说《梅雨之夕》为范本来探讨这种本质的不同。《梅雨之夕》是施蛰存的代表作之一,描写了性心理、揭示了潜意识,文笔舒展,格调清新,艳而不俗,吸引了很多读者。《梅雨之夕》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上海,叙述了从下午四点到彻底的夜的降临的全过程,几乎没有情节,讲述了一位下班回家的男子在途中邂逅一位少女之后的一段心灵历程。作者对人物的心理进行层层剖析,描绘出了主人公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1.循规联想
引入施蛰存小说《梅雨之夕》中的一段话进行分析:“……我有着伞呢,而且大得足够容两个人,我不懂何以这个意识不早就觉醒了我……”这两句是“我”想共用伞的想法。“……我可以用我的伞给她挡住这样的淫雨,我可以陪伴她走一段路去找人力车。如果路不多,我可以送她到她的家……”主人公有了共用伞想法后在心中盘算着怎么实施这一想法。“……我应当跨过这一条路,去表白我的好意吗?好意,她不会有什么别方面的疑虑吗?或许她会像刚才我所猜想着的那样误解了我,她便会拒绝了我……”[5]“我”想实施想法又担心因误解而被拒绝,紧接着揣摸对方的心理,随后看着雨水其实还是内心在等待犹豫,想了半天还是犹豫不决,最后并没有实施自己刚开始共用伞的想法。
这是“我”的一段内心独白,从内心独白言语分析来看,“我”的内心始终是环绕着一个点或者一条线来独白思索,那就是“伞”或者是“怎样把伞撑到女子头顶”,没有迹象显示作者在这个时间流程里还有别的什么想法,即使看到地面上的雨积水时,多半是下意识的举动,心里还在惦记着的只有这一件事,其实这个过程中主人公在“我”内心的徘徊都是对女子心理的猜测,都属于联想,但这样的联想是一种相当规矩的想象,自始至终都像是在认真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心无旁骛,并未天马行空,不是自由联想,而是“循规联想”。
还有一段比较容易让人误解的类似的联想:“……啊,是了,我奇怪为什么我竟会想不起来,这是不可能的!我的初恋的那个少女、同学、邻居,她不是很像她吗?……”由女子想到了初恋女友,形象重合。“……这样的从侧面看,我与她离别了好几年了,在我们相聚的最后一日,她还只有十四岁……”进而回想起与初恋女友最后一次的相见情形。“……一年……两年……七年了呢。我结婚了,我没有再看见她,想来长得更美丽了……”内心推测初恋女友现在的长相,想起主人公在梦中陪伴着初恋女友一起长大,证明她对主人公印象至深,进一步幻想女子目前的音容。“……但她何以这样的像她呢?……”脑海中邂逅女子和初恋女友的形象再次重合。“……她为什么会到上海来呢?是她!天下有这样容貌完全相同的人么?不知她认出了我没有……”继续分析推测初恋女友的现状。这同样是一段“我”的内心独白。可以看出,“我”的思维无论怎样的跳跃也始终被圈在一个樊篱中。“我”的内心始终都在女子和初恋女友之间转换。换句话说,当时“我”的脑海中只能容得下她们两个。这种联想仍然属于“循规联想”。
2.道德印象
下面再分析《梅雨之夕》中的另外一段内心独白,进一步确认联想和印象的中国化特征。
“……一阵微风,将她的衣角吹起,飘漾在身后。她扭过脸去避对面吹来的风,闭着眼睛,有些娇媚……”女子在微风拂面时给“我”的感觉和印象:“……我记起日本铃木画得《夜雨宫诣美人图》,提着灯笼,遮着被斜风细雨所撕破的伞,在夜的神社之前走着……”写“我”记忆中的一幅图画带给自己的美妙感觉,这是由上一个情景引发的“我”的联想。“……现在我留心到这方面了,她也有些这样的风度……”由图画回到眼前的女子,紧接着写“我”心里很乐意与她亲近,并有点自我陶醉,并进一步表现了自我的陶醉,真实地坦露了小市民内心的欲望。仿佛闻到了花香,再次由近及远想到了诗,收敛了继续想下去的欲念,又一次转念写到了上面那幅画,同时想到了自己的妻子,暗含着对于妻子的一种欲念。“……我再试一试对于她的凝视,奇怪啊,现在我觉得她并不是我适才所误会着的初恋的女伴了……”女子已不是我如初的印象了,“我”的欲念沉淀下去了。“……她是另外一个不相干的少女。眉额、鼻子、颧骨,即使说是有年岁的改换,也绝对地找不出一些足迹来……”峰回路转,女子只是另一个女人,“我”对于她的欲念彻底退出。
这一段内心独白展示了“我”的联想和种种感觉印象。看起来“我”的思维是在不断地在初恋女友和妻子身上转换,并且最后得出的结论也是一个很大的跳跃,那就是女子一点也不像“我”的初恋女友,这种联想应该算是很自由了,但不应忽略的是,“意识流”的表现方法除了“自由联想”外还有“感官印象”,其实这两者在行文中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很难明确区分。比如在引文的第二段中其实也有比较明显的印象成分,之所以说是印象而不叫“感官印象”,可以从下面的分析中找到答案。这里主人公受到的刺激,包括视觉的画面美感,嗅觉的花香等,但在受到刺激的同时,也隐藏着一种节制,主人公从刚一开始内心就有了一种骚动,面对如此优雅的一个女子,这个男子的动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真正接近后,我的感觉始终是点到为止的,一种很纯粹的情欲在浮沉。当然,在此也不能怀疑主人公当时美好纯真的情感,但其实这似乎更应该理解为是一种道德上的节制,“我”的内心早已裹上了一层道德的面纱,我只能隔着面纱去感觉世间人情。“我”的原始欲望始终不会浮出水面甚至很肆虐地闯入“道德禁区”,这时的无意识没有出现而“我”的思考力尚存,因此将它称之为“道德印象”。
3.自由联想和感官印象
再以爱尔兰意识流文学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为范本来探讨这种本质的不同。《尤利西斯》于1922年出版,小说以时间为顺序,描述了主人公发生在都柏林一天十八小时中的种种事情,塑造了一个苦闷彷徨的都柏林小市民形象。广告推销员利奥波德·布卢姆这个人物形象与乔伊斯的其他作品一样,可以找到其生活原型。这篇小说大量运用细节描写和意识流手法构建时空,语言风格独特。《尤利西斯》是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也是一部很受关注,又备受争议的作品。其中最后一章有四十页没用标点符号,是意识流的经典作品,描写布卢姆妻子莫莉的情感独白,荣格称赞其是心理学的精华,没人能像乔伊斯这样把女性的心理分析得如此透彻。[6]
“……几点过一刻了,可真不是个时候……”这两句写钟声提醒摩莉时间已经很晚了。“……我猜想在中国,人们这会儿准在起来梳辫子哪,好开始当天的生活……”她的思绪跳到了中国,此时仍然与时间的意识相关。“……喏,修女们快要敲晨祷钟啦,没有人会进去吵醒她们,除非有个把修女去做夜课啦……”从中国人的起床联想到修女们不会有人打扰,而摩莉自己却被深更半夜才刚刚回家的丈夫吵醒。“……要么就是隔壁人家的闹钟,就像鸡叫似的咔哒咔哒地响,都快把自个儿的脑子震出来了……”即使没有丈夫吵醒她,也同样有邻居家的闹钟会打扰。“……看看能不能打个盹儿,一二三四五……”她仍旧试图用数数的方式使自己快点入睡。“……他们设计的这些算是啥花儿啊,就像星星一样……”她转而又注意到了糊墙纸上的花。“……隆巴德街的墙纸可好看多了……”从糊墙纸上的花又联想到了自己在隆巴德街上的旧居的糊墙纸。“……他给我的那条围裙的花样儿就有点儿像,不过我只用过两周……”继而又联想到了丈夫送给她的围裙上的花与糊墙纸上的花样有些相似。[7]
这是《尤利西斯》最后一章中很著名的一段内心独白,它鲜明地体现着意识流的自由联想和感官印象特征。汉弗莱分析说,这一段是以钟声和墙纸为中心引发的联想。读者可以看出这种自由联想有不合逻辑的、随意性、跳跃性的一面,比如为什么一下子会想到中国,接下来为什么又想到修女?中国和修女的联想与时间又有什么必然联系吗?没有,这是很随意的。不同于上文《梅雨之夕》分析中的情景,都是自然而然有规可循的联想。当然也不能否认这里也有内在逻辑的一面,比如由糊墙纸想到自己以前房子的糊墙纸,又由墙纸的花想到丈夫送给她的围裙上的花。但总体上还是组成了一个自由联想的流动过程。其实这个流程本身也承载了摩莉的“感官印象”。在此给“感官印象”这一概念作一个解释:“感官印象是作家记录纯粹感觉和意象的最彻底的要求,它把音乐和诗的效果移植到小说里,再现纯属个人性质的印象,这时,作家的思维近于消极状态,只受瞬息即逝的印象的约束,接近于无意识,无法用语言来表达。”[8]在这个概念里,大家注意“感官”二字,所谓感官印象就是外物对于作家眼睛、耳朵、鼻子及整个身体的刺激,作家的敏感也全在于此,这是无法控制的一种自我感触,作家在此时的思维之所以近于消极状态,就是被自己的身体控制了,他甚至没有了思考的能力也不需要在当时思考。也因此,这些东西很难进入逻辑的语言层次,换句话说语言在此是无能为力的。主人公摩莉听到看到了,伴随钟声她瞬间想到了中国、修女,看到糊墙纸上的花她觉得像星星,然后又想到了隆巴德街的旧居,最后定点在丈夫送的围裙,这种跳跃似乎不是很夸张,但却是属于主人公个人的感官印象。
四、《梅雨之夕》与《尤利西斯》意识流对比分析
(一)《梅雨之夕》与《尤利西斯》意识流的相同之处
首先,人物进入意识流动时的心理状态相似。《梅雨之夕》中,描写傍晚时分的梅雨之夕,霓虹灯闪烁,街面上雨水淅淅沥沥,街灯的忽明忽暗与街上行人车辆的忽远忽近,[9]说话声与嘈杂声产生一种迷糊不清的意识,“我”进入了一种半清醒半迷糊的意识流动状态;《尤利西斯》中摩莉深更半夜被丈夫吵醒,意识由睡梦状态进入觉醒状态,也是在一种意识不太清醒的状态下进行意识流动。其次,主人公的意识流动处于自我前意识和潜意识层面。《梅雨之夕》中,“我”意识流动因为一个美丽无助的女子激发了“我”潜意识里对快乐“本我”追求的欲望;《尤利西斯》对摩莉女性心理的描写,意识流动的激发物较多,由钟声、修女、中国、糊墙纸的花想到丈夫送的围裙上的花样,引发了摩莉潜意识深处对美好时光和情欲的回忆与向往。
(二)《梅雨之夕》与《尤利西斯》意识流的本质区别
首先,意识流的联想方式和印象形式不同。《梅雨之夕》采用循规联想与道德印象的表现形式;《尤利西斯》则采用了意识流典型的“自由联想”和“感官印象”的表现形式。其次,人物意识流动的深浅不同。《梅雨之夕》中,“我”的意识流动始终在意识和现实中不停的穿梭,处在意识与半意识状态之下;《尤利西斯》摩莉的意识流动是一种内心独白,是一种不太清醒状态下的意识流动。第三,表现出的情感不同。《梅雨之夕》中,“我”意识流动是本能性欲的瞬间表露,是追求本我在特定环境下的凸现,具有瞬间性;《尤利西斯》中,摩莉有对自己过往的回忆,有对丈夫深夜吵醒自己的厌嫌,转而又想到了丈夫对自己的关爱,意识的流动过程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细腻的情感。第四,意识流所折射出的社会、时代、环境的表现手法不同。《梅雨之夕》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上海,上海是当时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伴随小说主人公在都市行走路线的变化,其潜意识的思绪也随之流动,“我”内心的空虚孤独感也逐渐显露在读者的眼前,利用环境喧嚣来反衬托主人公此时的心情。《尤利西斯》中布鲁姆在奥蒙德旅馆酒吧无聊时想入非非,虽然酒馆里的歌声婉转动听,但也掩盖不住颓丧衰落的气氛,采用强烈的反差对比和象征手法表现出都柏林人在现代精神荒原上沉沦度日的心理现实。
五、结束语
综上,《梅雨之夕》独特的意识流表现手法已经清晰地显示出来了,其实这也是很多中国意识流小说的共同特质。《梅雨之夕》与《尤利西斯》的“意识流”表现形式有相似,但也存在本质上的不同。《梅雨之夕》中的内心独白和心理分析在形似的同时内在的神韵也是不同的,可以称为“中国特色意识流”。精神内核不同的两样东西无论如何是不能笼统地归纳撮合在一起的,中国意识流和西方现代主义意识流是完全不同的。意识流原本的“自由联想”和“感官印象”表现技巧发展到中国意识流那里便有了新的不同的变异,即循规联想与道德印象。虽然在中国读者看来这似乎很符合自身的审美眼光,但是,要通过反思与批判,才能真正把握意识流小说深刻的精神内涵,也只有在开放的思想环境之下,意识流小说才能真正为大众所接受和喜爱,在中国本土扎根并获得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