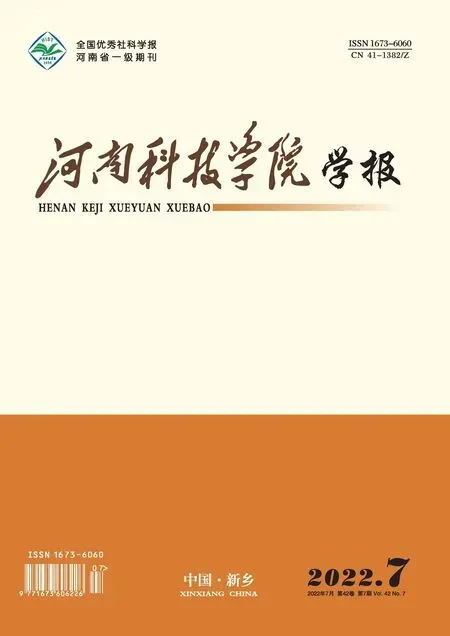柯勒律治:一个被忽视的保守主义者
杨颖
(山东建筑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1)
柯勒律治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正如他一生中经历的“反转”一样,作为湖畔诗人的他,在其早期不介意别人称其为共和主义者,其实年轻的他,“先是一个革命派,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失望,最终成了保守派”[1]5。但事实上,学界对于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还是存在一定质疑的。著名的保守主义学家柯克在梳理了保守主义的历史脉络后,给出了六项衡量标准作为保守主义者的准则[2]6,以这六项准则来衡量柯勒律治,就可以看出其作为保守主义思想家的身份。
一、柯勒律治确信存在一个统领事物的“理念”
在柯克看来,柯勒律治的探求原则之路比伯克走的更远。柯勒律治认为,存在着某种主导社会生活和个人良心的神圣意志,他也一直致力于寻找能够适用于所有事物的解释,在他的理论中将该种意志称为“理念”。
柯勒律治关于理念的建构,是知性与理性的结合,他在知性与理性的分离中完成了他的哲学建构。他反对流行于当时英国的机械哲学,反对洛克及其追随者所主张的所有知识都是经验的总结,这会导致吞噬一切的工业主义和庸俗的物质主义。这容易使道德退化为动物感官的盲目冲动、退化为精明的推理算计[3]71。如果一个民族用洛克来代替逻辑,用佩利来代替道德,用他们两个来代替政体、哲学和神学,这个民族只能是奴隶。他也反对普遍理性,过分的理性主义使得人类的情感受到阻碍,遮蔽了人类运用其他方式如哲学、宗教和艺术方式认知世界的能力。在他看来,仅有知性或者仅有理性的构建都是片面的,只有将经验(知性)和理性结合才能够合理地主导社会生活。柯勒律治将“理念”作为了一个统领性的具有至上地位的原则,“这一区分显示了他哲学的两个总体倾向,这两个倾向对他的政治思想影响巨大。第一个是他对于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个性和统一性之间的动态平衡的关注,这在浪漫主义学者中十分普遍。第二个便是他强调思维在理解现实中的积极作用,以及人类在这些活跃官能方面的不平等。第一个倾向使他成为一个宪制主义者,第二倾向促使他拥护贵族政治”[1]40。
他还通过历史的角度对“理念”的建构进行论证。在其最后的作品《教会与国家》的开篇第一章就提出:“因为我国自阿尔弗莱德以来的全部历史都表明,该理念或终级目标一直影响着我们祖先的思想,它存在于他们作为公共人物的特点或职能中,也存在于他们想抵制或要求的事物中,亦存在于他们建立的制度和政体形式中,以及他们成功战胜的制度和政体形式中;亦因为其结果是在理念逐渐现实化过程中取得进步,尽管这种进步过程不一定总是一帆风顺、平和宁静;而且,它可以在真实存在的万事万物中得到真实的体现,尽管作为理念,它无法得到充分体现;因此,我们可以说、并且完全有权利说:理念本身是真实存在的,即作为原则,它以原则能够存在的唯一方式存在——它存在于人的思维和良知中,规定着人的责任,决定着人的权利。”[4]19
他将“理念”原则与民族特性进行了关联:“我再次回归理念,……一位古时的文人将之称为‘Lex Sacra,Mater Legum'[神圣法则,所有法则之母],(他宣称),没有什么比它的基础更加牢靠,没有什么能比它孕育更多结果,没有什么比它存在更多内在的和谐理性;它与该民族天生的、内在的性情同质,是其内在固有的,且在其形成过程中(如同蚕茧),没有任何别的法则能约束它——这一法则并非源于阿留雷德(Alured)、阿尔弗莱德(Alfred)或者克努特(Canute),或其他更为古老、或者后来某个法则的制订者,它可能会这样描述自己:理性和上帝法则第一个到来,随之而来的则是我。”[4]21-22对于理念的应用,特别是在政治中的应用,柯勒律治根本不相信民意,对于柯勒律治来说,民众的声音(vox populi)永远不可能是可靠的。他既可能是魔鬼的声音(vox diaboli),也可能是神的声音(vox dei)。他认为,理念是所有衡量现行意见、制度、需求的标准[1]91。
柯勒律治看到了物质主义、商业主义对人及社会的破坏,看到了社会失衡,他认为存在一个道德秩序,任何否认道德意志的政府理论都是站不住脚的。柯勒律治在其《朋友》中写到,“道德的客体不是外在行为,而是我们行为的内在准则”[5]194。在《教会与国家》中,他进一步提出:“作为根本理念,它同时也是评判政府机制的终极标准,因为我们只能在它身上,才能找到我们代表性体制根本的建构原则。单单依照这些原则,我们就可以断定哪些是赘生物、失调和退化的症状,哪些是原始萌芽逐步发展过程中自身的生长和改变,哪些是免疫而非疾病造成的症状;如果土壤或者周围因素存在不可改变的或者只能逐步改善的缺陷时,在此种最糟糕的情况下,亦可以根据这些原则判断哪些是由于这些缺陷造成的改变。”[4]20拉夫乔伊在《柯勒律治和康德的两个世界》中提出,柯勒律治区分理性和理解就是为了“从哲学层面论证人类道德自由和可靠性”[6]228。
所以,“在柯勒律治漫长的探索旅程中……柯勒律治试图寻找一个统领性的原则,即事物的理念,它根植于意志中,并且在他看来,也因此根植于道德和宗教中,从而能够解释整体之目的”[7]72。
二、柯勒律治对传统价值的强调
对于保守主义者来讲,遵守传统是一个基本的标识。柯勒律治非常珍视传统,这可能与其自身的生活经历相关。他出生于牧师家庭,在婚姻生活中虽与妻子不和睦,甚至在起始也没有爱,但在他对骚塞的信中均提到,他会根据传统道德要求肩负起他的责任,可见传统对于他的影响。
穆勒评论边沁与柯勒律治的差异时,提出:“对于思索某种已成定论的观点,边沁总是会问:真是这样吗?而柯勒律治则会问:它的含义是什么?这是伯克的遗产——永不因为他们是成见而贬低成见,而是在思虑他们时视之为人类的集体论断,并努力弄清楚潜藏于其中的含义。”[2]117柯勒律治认为,学说只要能取信于有思想的人,被全国人或几代人所接受,就说明他不完全是谬论;一种信仰的长期存在至少证明人类心灵的某些部分已经适应了它[3]62。在柯勒律治看来,这些已有的成见、习俗和论断都积累着民族的智慧,并且已经内化到民众心中,为民众所接受,说明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没有证明是错误之前,不应该随意地丢弃和改变。
柯克提出,在一个革命的世代,有时人们会尝试各种新奇的想法,对它们感到厌倦之后会重新认同古老的法则[2]7。这个论断不仅仅指出了伯克的转变,也对浪漫主义的“湖畔诗人”的转变做了良好的注脚,他们也一度是“成规质疑者”,柯勒律治与骚塞曾经要去美洲践行“大同社会”之乌托邦,他们也曾用自身的笔触和实际行动来支持法国大革命发生前夕的法国,谴责英国对法国的攻击。虽然他们认清法国大革命不如伯克那样来的早,但是当巴黎恐怖的到来促使他们开始反思:反思英国宪制的稳定。尽管他们也可能存在穆勒所指出的英国人的退缩本能,“英国人的心中,从思考到实践,都有一种强烈的从所有极端的有益退缩。但这种退缩不是洞见的结果,而是一种下意识的本能”[3]90。但柯勒律治的退缩,不仅仅是下意识的本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其对历史、哲学的掌握,他分析英国历史上的革命,认为“有一件事是千真万确的,所有基督教世界的划时代的革命,宗教改革以及和它们相关的公民的、社会的、内部的民族习惯的改革都与那些形而上学体系的起起落落相一致”[8]428。柯勒律治反对较大的起落,因而其将法国大革命视为“梦想发掘或者炸掉房子的地基,用拆除的材料来修补房子的墙壁”[9]217,这种治疗可能比疾病本身更可怕。所以,柯勒律治更容易容忍人类事物中的不完美,偏爱那些能够产生变革的方案,而不是造成暴风骤雨般的突变,柯勒律治分析了英国宪制的优点,探索出了英国平衡的理念,承袭了英国的基督教思想传统。
对于英国为什么没有走向法国这种剧烈革命的形式,的确与英国自“光荣革命”后的渐进式改革有着很大关系。法国人托克维尔这样描述了英格兰:“初看起来,英格兰的旧宪法似乎有效;不过,细看之下,这种幻觉消失了。忘记那些旧名字,无视那些旧形式,你就会发现,英国的封建体制早在17世纪就已基本上被废弃:所有阶层相互之间都自由交往,贵族势力已被削弱;贵族身份向所有人敞开。财富成为最重要的权力来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税赋均等,媒体自由,辩论公开化——所有这些现象都是中世纪社会未曾有的。年轻的血液被巧妙地注入旧封建体制,因此延续了旧体制的生命,并赋予它新的活力,同时还保持着它古老的外观。”[2]19
三、柯勒律治承认文明社会等级的存在
承认文明社会等级的存在,是柯勒律治坚守的重要观点之一。他在《教会与国家》中提出,“我们将国家的臣民分为两种秩序,农业阶层或者土地的所有者;商业、制造业、分销业和职业群体,可统归为市民”[4]26。对于这两种秩序,他又进行了进一步阐述:第一种秩序可分为两个阶层,模拟古代法律书籍用语,可称之为大男爵(the Major Barons)和男爵(the Minor Barons)。二者通过他们的利益或状况、环境的影响以及他们的从业性质,与国家的永久性,即国家的制度、权利、习俗、方式和特权等诸如此类之事物有着实质性的联系;而港口、城镇和城市的居民恰恰相反,他们以类似的方式,出于类似的原因,与国家进步性密切相连[4]27。等级的划分是建构国家理论的基石,他认为健康国家是一种各主体利益的平衡,是主体代表的永久性利益与进步性利益的平衡。
关于国家治理,他提出国家利益被信托给议会。关于议院与国王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上议院代表着持久性利益,代表着土地持有者,完全由大男爵组成;下议院则代表商业和进步利益,主要是商业、制造业者、分销业和职业阶层,持久性力量和进步性力量对立且平衡,国王则是这个“天平的横杆”,将对立的矛盾进行统一。下议院的四个阶层,柯勒律治用“个人利益”进行称呼,属于所有可移动且归属个人财产的表现物。
对于市民权利,柯勒律治虽然认为是无条件赋予的,但是“这一权利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获得某一同样数量的相对财富和独立,并且允许周期性的改变和再次调整”[4]76。实质上他主张财产是权利享有的基本资格,在《教会与国家》中,他进一步阐释了其在《朋友》第一卷中的一个观点,这样写道:“最初由社会纽带维系的人民首次形成国家,在社会关系上添加了一层政治关系,其主要目的不是保护他们的生命,而是保护他们的财产。”[4]83可见,其对于财产资格的重要关切,将财产资格作为划分阶层的重要基石,也是其政治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石。
他主张,政治权力不能给予没有财产的人,他对无财产人存有担心,也许是他看到的法国大革命后期暴政之现实的担忧,由于没有财产,这类群体在获得权力后,就有可能使用权力弥补自身的贫困或发泄愤懑,可能会引发贫民暴政。作为保守主义者的柯勒律治清醒地观察到英国已经产出了革命的火花:在当时的背景下,英国已经出现了传统农业的土崩瓦解,受圈地运动压迫的很多无财产英国农业劳动人不得不涌入城市;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的进步,但是对财富的攫取,对于工人生存条件缺乏改善,在北部矿区出现了可怕的生存状况和新兴资产阶级的非人道待遇;由于天主教的解放问题,爱尔兰积累了多年的怨恨。在这种背景下,支持抽象平等原则的风气在英国日益兴盛,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理想主义的煽动性,更容易激发该类群体的躁动。当然他也并不是决绝地拒绝了无财产者,也指出国家应该致力于教育,赋予无财产者获得财产的机会,获得财产则有机会获得政治权力。只是他反对通过强制立法实现所谓的均等,比如上下议院人数的绝对均等,对国家财产的平均分配。在柯勒律治看来,平衡并非体现在数量之上,健康的国家是要达到一种比例上的平衡,体现在代表的利益上的均衡,他提出为了在议院中获得平衡,下议院应占有明确有效的多数,以和持久性力量相抗衡。忽视利益的很多平等化努力,不但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甚至有的形成了特权阶级的垄断,或者引发暴民的统治,导致了自身转化成自身的敌对者的状况。
所以,柯勒律治的观点在当下看起来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但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对于财产以及财产背后所形成的对人的素养的认知,以及与此进行阶层的划分,并通过这些阶层的代表在议院中达成不同阶层间的利益平衡,进而完成对国家的治理,还是具有着一定的价值。
四、柯勒律治主张自由和财产的不可分割性
关于财产与自由,柯勒律治主张财产和自由关系是紧密的。关于私有财产这个词汇“proprietage”①,1933年版的13卷本的《牛津大词典》认为是柯勒律治创造的词,可见柯勒律治对于私人财产的重视。他认为私有财产不仅和政治自由不可分割,而且对道德发展、个人独立至关重要,这是财产最重要的道德理由。他认为财产最根本的存在理由在于“需要一个自由活动的空间”以“获得负责任的自由意志”。个体家庭如果不拥有实质性的财产,便不会有有效的潜在力量,因为个人不独立,便不能坚定地对政府的政策提出实质性的质疑或进行抵制。这也就意味着个体的财产实质上是对抗强大的国家的根基,也是个人所有权的合理理由。如果消灭私人财产,自由将不复存在。所以他提出,“根据国家理念,国家权力的合法客体是私人财产(proprietage)的全部利益和相关物,既包括土地的、也包括个人的;无论是家族中可继承的,还是个体公民的,都包括在内,并且只有这些。国王,作为国家的首脑兼臂膀,即使在臣民的生命中,也拥有财产利益;只要这些利益遭到非法入侵,国王总会以原告的身份出现”[4]83。也就意味着,国家应该尊重和保护所有的个人权利,特别是私有财产的合法权利,应把它作为国家权力的合法客体。
当然,他认为仅仅重视个人财产是不够的,国家的构成不仅仅是个人财产利益,还有国家财产,在ReliquiaeBaxterianae(1696)的页边注中,柯勒律治提出“这个国家的衰退和进步”取决于能否恢复“可以与可自由支配、可继承的私人财产相制衡的民族的、可流通的财产”[4]36。可以看出,柯勒律治主张国家也应有可与私人财产相对抗的国家财产,以防止私人财产权的滥觞,即认为私有财产和国家财产作为联邦的两个构成因素,相互对立却又保持一致且互惠互利、互为条件,是联邦的平衡力量;一方的存在是另一方合法存在的条件,也是其完善途径。
关于自由,保守主义并不否定自由,柯勒律治就十分崇尚自由,不过他所崇尚的自由是财产基础上的自由,这种崇尚自由实质上是对财产权的利益保障。查理二世在治内通过法律宣布每位王国国民生来享有自由,在柯勒律治看来,这项法律仅仅是在批准一项opus jam consummatum(已经完成的工作)。“柯勒律治在他的作品中始终如一地为自由辩护,这种无法遏制的对自由的渴求,是他整个生命不容置疑的源泉之一。他憎恶雅各宾主义,因为它是对真正自由的歪曲,他痛恨雅各宾主义的‘狂热’、它‘邪恶的骚动’、它‘粗俗的、经验主义的原则’。他将为自由辩护的强烈欲望带到他所探究的每一个领域,他声称:‘如果世上存在这么一个人,除了一件事情之外,我在其他一切事情上都应当承认自己不如他,不乏这样的人——但是在如下事情上我不会承认:即我对个人的真理和共同体中的自由的热爱’”[10]。柯勒律治还提出,国家应该让公民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意志,这是立法的根本原则,它与所有人的自由意志是一致的,并且不会颠覆它作为国家存在的目标②。也许正是柯勒律治对于自由的关切,对于自由的热爱,以及把自由看成立法的原则,学者才会把柯勒律治视为“自由的国教徒和自由的保守派人士”,把他的思想看成“自由的保守主义”[11]41。
五、柯勒律治反对“诡辩家和算计者”
保守主义不信任“诡辩家和算计者”。18世纪是科学快速进步的一个世纪,包括哲学家们也深受科学的影响,经济学这门学科也随着兴盛,普遍理性与科学的融汇,使得利己的计算及其物质主义哲学更加深入人心,虽然尚未达到言必称数字,但是功利计算已经渐成气候。
“柯勒律治是英国第一个向处于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派的物质主义提出质疑,并要求经济学必须将整个人类和社会的需要纳入考虑范围的学者。事实上,他提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健康不能只衡量其商业的繁荣,正如衡量一个人的健康不能只看他的腰围。在他看来,英国真正的健康已经被那些经济学家破坏了,因为他们用‘市场’来衡量所有的事物”[1]15。他提出,用经济利益、用数字来作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是导致社会动荡的深层原因,无拘束地运用理性来思考重要的问题是毁灭性的。他提出“政治经济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它是从如下对于人的看法开始的,即把人看作抽象的东西,而将人的那些不能服从于技术性计算的特点排除在外”[1]16。人毕竟不仅仅是物质性的,不仅仅是抽象物,而“作为政治经济学,它热衷于增加食物,但通常忽视食用者的品质甚至感情。作为伦理哲学,它不承认义务……作为一种自鸣得意的化学,如果它不是从一开始就错误地把被毁灭的产物——死尸——当作合成要素的话,那么我很可能上当受骗了,毫无疑问,它以丧失与生命和自然精神的交流为代价来购买少许卓越的发明”[12]76。
在柯勒律治看来,科学家们现在忙于无休止地收集事实,却不愿意探索事实之间的联系,使得人类无法理解物理世界的整体框架。的确基于这种事实的原则,可以厘清大量的困惑或误解,但也易衍生对该种理性的错误崇拜,陷入诡辩和算计,脱离了情感或信念,特别在要求考虑道德影响的地方就无所适从了,或者导致道德退化或败坏的下场。
当然,针对其不足,柯勒律治列举了三种传统上可以与商业价值制衡的文化态度:对贵族政治和其法规的尊崇,宗教感情和对真正的哲学和科学知识的激情和尊重[1]19。尽管贵族新增了新鲜血液——新兴的财富群体,而使得传统的贵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这些家族对古风的崇敬仍然能够制衡对财富的疯狂迷信”[9]183。关于宗教,“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启蒙运动的发展来看,近代历史呈现为两大趋势,即教会的威信衰落下去,科学的威信逐步上升”[13]3。这种趋势,柯勒律治不可能看不出来,他看到了在普遍理性冲击下对宗教的质疑及教会的败退,他也哀叹“圣经”是当代新教神学弥漫的错误,是基督教巨大的绊脚石,但不能否认建立在洞察力之上的信仰仍然是对物质主义的防护剂。对于真正哲学和科学知识的激情和尊重,他希望社会引导科学家不仅仅沉迷于有利可图的技术革新,哲学应该提供促进健康社会的理想,之所以这样,在柯勒律治特有的知识阶层体系中,或者对于教会的思考中,这些正是知识的传播者,他们的片面,将会导致教育的衰退,导致社会的分裂。人所在的社会,不仅仅是个理性社会,还是一个知性社会,在给詹姆斯·吉尔曼牧师的信中,他试图构建起一个融知性与理性等概念的“逻辑五元素”的体系③,可见作为保守主义的柯勒律治似乎更加强调社会有机体的整体观。柯勒律治认为,道德社会必须能够在法律中保持习俗制度,在市民行为中保持“人”和“物”的根本区别,因此,道德社会为“人”的培育或“使人成为人的各种品质和官能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条件”[4]43。他便自然地得出结论,如果一个经济理论不考虑道德、文化和心理因素,那么这一理论既不可能理解,也不可能治愈英国的弊病。
六、柯勒律治主张和平平稳基础上的变革
关于社会改革,保守主义者从不拒绝变化,也不拒绝改革,只不过他们反对过于激进的改革或者革命。保守主义们认为,“一个人永远都有自卫的权利,不过他并没有随时随地佩戴脱鞘之剑的权利”[2]21。
他们对于“激进”保持着一种异于寻常的“冷静”,尽管这里面有着穆勒所言的英国人喜欢旧事物,不翻陈年旧账。但事实上,也与英国存在一种类似妥协的体系有关系,希望变革保持在习俗的框架内,这是一种审慎的态度,也是一种哲学观。毕竟习俗,不仅仅是一种通常性的习惯,更是一种集体性智慧,在潜移默化的遵守中从而保持着整个社会链条的某种连续性,尽管它也存在一定的惰性,但这种对于惯常的遵守,如若通过外力打破,就有可能激发其内在的一种反抗。其实保守主义者们基本上都意识到这一点,不排斥变化,但要调和变革与旧时代最好的东西,从而达到一种自我革新,虽然是旧的事物但属于好的仍可以持续,切斯特菲尔德曾评论说:“成见绝非谬误(尽管它通常被认为如此);相反,成见也许是最毫无疑问的真理,尽管它对那些未经审视便凭信任或习惯接受它的人来说,不过是成见。……大多数人既没有闲暇,也没有足以进行恰当推理的知识;为什么要教导他们去推理?比起半吊子的推理,难道诚实的直觉不能更好的提点他们,合意的习俗不能更好的指引他们么?”[2]41对于创新的事物,需要在大多数人普遍认为需要变革时进行,而不能仅仅是一种构思精妙的抽象理论,创新要在习俗的或者是原有的框架内,就像人的身体一样,身体作为一种既定框架,但永远都在进行着自我更新。
柯勒律治特别指出,“一个民族只有在国民利益的代表机制中才会团结一致;基于个人的激情与愿望的代理机制是不可靠的”[2]140。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保守主义者们不支持变革,而只是对于过于激进的变革以及可能带来的破坏力保持一种审慎。保守主义者们也认识到了,所有人都必须遵从变革的大法则。它是最为强有力的自然法则,而且可能还是自我保护的手段。我们所能做的也即人类智慧所能做的,只是确保变革以让人感受不到的方式到来。这样,就能享有随变革而来的所有可能的好处,而非任何变异的不便。一方面,这种方式会防止即刻剥夺旧有的利益集团:那样做会在那些立即被剥夺影响力和报酬的人中激起难以排解的严重不满。另一方面,这种渐进的过程将阻止长期受压迫的人因新获得的大量权力而冲昏头脑,因为他们肯定会放肆嚣张地滥用这样的权力[2]44。柯勒律治接过了伯克的衣钵,尽管其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缺少了伯克的那种预见,但柯勒律治还是意识到了激进式变革带来的问题,他看出了国家“持久”(Permanence)和“进步”(Progession)之间矛盾,其权宜理论,即是基于经验和特殊环境下进行一定的权宜,以及关于国家平衡观的提出,就是为了进行这些矛盾的协调,而使得国家不陷入混乱或者有剧烈的革命之虞。比如,关于爱尔兰解放运动,柯勒律治并不完全反对,只是想将这一问题和根本原则联系起来,同时将当前对保障措施的呼声放在更实质的层面上看待。对于法国大革命,柯勒律治指出:“……如果我清楚自己观点的话,那么它们完全与法国的形而上学、政治、伦理以及神学无涉。”[14]395可以看出:柯勒律治并不反对变革,但是变革不能无视原则,无视古老的准则。面对变革,要聆听本性关注,而不能被当下所蒙蔽,不能仅仅听任国内外激进思想泛滥,那可能会导致现有社会秩序的覆灭。和夸夸其谈的经济学家组成的民主寡头集团统治相比,最劣等的贵族制也是一种祝福。正如卡莱欧所言,在19世纪的英国,对于当时的变革,“保守派做出的反应十分独特,极富创造性。保守派政治家们富有想象力的行为并非是不自觉的行为,而是来源于一种保守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虽然由伯克最先提出,但柯勒律治给出了最贴切和系统的表述。正是在伯克和其后世的保守主义者的顽强坚持下,英国是唯一一个避免了彻底革命的西方大国,他们不仅仅清楚地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对激进派做出妥协,更是坚守了审慎的原则,坚守了权力的运用和范围取决于习俗和环境”[1]6。
总而言之,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柯勒律治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他能洞悉过去,更在于他能知晓未来。今天采用民主宪制的西方民族国家,与柯勒律治所勾画出的理想十分接近,而与他的革命派对手们的勾画相去甚远。真正理解现代国家道德基础的是柯勒律治,而非潘恩或边沁。最知晓未来的,是保守派的伯克和柯勒律治[1]9。
注释:
①这是柯勒律治创造的一个词汇。1933年出版的13卷本的《牛津英语词典》中指出:“proprietage”意为全部私人财产,私人财产的总和,是柯勒律治创造的词汇,并且引用了《教会与国家》的一段文字。
②参见1823年8月的一个长长的注释:“为了确保与整体的安全、稳定和统一相匹配的自由的每个伟大领域,这是(并且也常常被称为是)国家的正当目的和真正目标,因此也包含着这个词语之定义。——貌似很有道理,包含很多意思,并且曾经有段时间,并且这段时间延续了很多年,它意味着一切;但我担心,以后它可能不值一提。在所有事情上,我的思想体会到了更多东西,并且十分肯定,一个国家真正的目的和目标,以及它的隐含定义是——通过对所有的限制——扩大内部自由的外部领域,以同时增加外部领域受到压缩的那些人的内部自由。”
③柯勒律治写于1830年《教会与国家》第二版第150-161页的页边空白处,如今存放在耶鲁大学拜内克古籍善本图书馆,在这个页边空白处,其将融知性与理性等概念的“逻辑五元素”进行了数学逻辑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