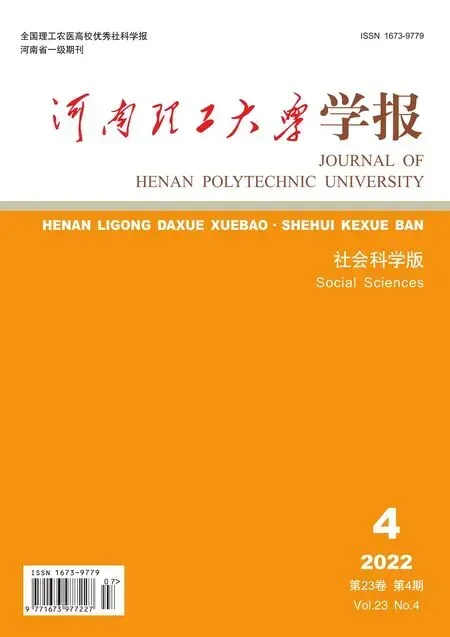元代丧服制度与多元丧礼文化交融
张钰铭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春秋左传正义》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1]礼仪规范与服饰等级构成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秩序,其中丧礼作为“五礼”之一,在传统礼仪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为世人所看重。宋末元初人称:“礼之行由于俗之厚,俗之厚由于丧之重。周公所以成周家忠厚之俗,亦惟丧、祭之重而已。丧、祭之重,民俗之厚也。”[2]对丧礼重视程度成为时人评判一个人是否忠厚的重要标志。进入元代后,汉人丧礼习俗及其丧服制度并未因统治者是蒙古人而废止,其中丁忧制度更被元政权吸纳作为统治手段的一种。这与蒙古人与色目人进入中原后,受到儒家思想影响息息相关,汉人丧服制度与丧葬礼俗迅速融入这些外来族群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的风俗习惯,进而影响到上层统治者采取的治理国家手段。此外作为从北方草原上来的统治者,元朝统治者以国俗施行五礼,“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3],其“薄葬简丧”的丧葬习惯也逐渐改变着当时厚葬的社会风气。对元代丧服制度与汉人丧礼文化进行梳理并与宋代对比,发现其基本沿袭前代,并对蒙古、色目人中儒化者产生深远影响,同时自身也吸取其他族群丧葬习惯,体现了当时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社会现象。
一、《家礼》与元朝丧礼
在许衡、刘秉忠等多位儒士努力下,忽必烈建元后确立了以理学为主导的治理方略[4]33,试图通过理学礼法治理国家,“以礼防民”[5]7。元朝统治者虽不断提高理学地位,借助其力量巩固在汉人族群中的统治,但因统辖疆域之大、族群之多,不同族群之间处于文化交融状态中,受外来风俗文化影响,汉人之丧礼与丧服随之发生变化。同时,蒙古、色目人接受汉人儒家文化影响,改变了自己原有的丧俗,朝廷对整个元朝社会丧礼的管理也在不断调整着。这些儒生所推崇的理学思想被运用到元朝治国理政之中,宋代盛行的朱熹礼仪之说也在实践中被继续推行,比如在婚礼方面,元朝政府曾在至元八年(1271年)九月规定汉人婚礼继续沿用朱熹《家礼》内婚礼规定,“外据汉儿人旧来体例,照得朱文公《家礼》内婚礼,酌今准古,拟到下项事理”[6]。
朱熹作为宋朝著名理学家,其所著《家礼》博采众家之长,因取材广泛且适应当时社会环境,故而深刻影响着宋元时期社会礼法秩序。龚端礼在《五服图解》中也称赞其“《家礼》所载前项丧服皆案古宜今,当世士大夫家多遵此而为之”[7]5,可见元代士庶进行丧礼时多按《家礼》所载进行。《家礼》规定丧礼程序主要为初丧、治丧、出丧、墓葬和丧祭五个阶段,这些也成为元代丧礼的主要程序。
二、元代丧服制度
丧服制度作为丧礼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中国传统经学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儒学发展的同时也在被世俗化、平民化的佛教信仰所不断冲击,加上风水堪舆之学兴盛、其他族群风俗交融,民间丧葬习俗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宋代儒生有感于当时礼法凌夷之乱象,重新整饬丧服制度,重建了儒家丧礼体系,在其努力下,宋朝政府颁行《五服敕》,从国家层面统一服制,为后世留下了可参照服制诏令。元朝建立初期,并未从国家层面规定服制,只到成宗大德年间才规定为亲守孝,英宗时期修《大元通制》成书,官方将五服制度正式确定下来,“国家初得天下,服制未行,大德八年饬中外官吏丧其亲三年。至治以来,通制成书,乃著五服于令”[5]3,在中国法制史上第一次把五服在法典中列有专条[8]。
《五服图》是丧服制度最直接的表现形式,较为常见有菱形《本宗五服图》。菱形《五服图》最早出现于何时无法考证,龚端礼在《五服图解》中认为汉代已有,在马王堆汉墓中也出土了一份记载有“丧服之礼”的简帛,从其中破碎残片可模糊辨认出其与现世流传的菱形《五服图》相仿,以证明龚端礼其言非虚。然在现存史料中所见较早菱形五服图的记载,只存于宋元时期朱熹之《家礼》、黄榦《仪礼经传通解续》、杨复《仪礼图》、车垓《内外服制通释》以及龚端礼《五服图解》等文人著作中,此之前完整的五服图已不可见。
据《家礼》《五服图》记载,服制分为五等,在大殓之明日,即逝者死亡第四日,五服之人各自穿着自己相应服装,在相应位置朝哭、相吊,“厥明,大殓之明日,死之第四日也。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然后朝哭,相吊如仪”[9]908。根据《五服图解》及其他元代儒士论著对《家礼》注解可见,其丧服服制为。
(一)斩衰三年
斩衰,斩为断、不缉,即不缝合之意,衣、裳旁和下际皆不缝合故为斩。衣裳不相连,皆用极粗生布制成。衣长过腰,向外缝合。衣背后有负版,负版用方为0.32m制成,垂于领下。衣前有衰,用布长0.32m、宽1.4m制成,缀于左衿之前。衣左右皆加辟领,各用布方0.32m,弯曲两头相叠为0.16m,缀于领下、负版两旁,各挽负版0.04m。衣两腋下有衽,各用布1.4m,上下各留0.4m正方,左右各裁入0.24m,缀于衣旁时使两方交叠,垂直向下,形状如同燕尾,以遮挡裳之上际,使其不外露。裳前三幅、后四幅,每幅各有3个衣褶。
穿丧服需戴冠与首绖。斩衰冠之顶以纸糊为之,宽0.12m,以布裹之,制作冠所用之布比衣裳布稍细。冠顶上作三陬,皆向右缝之,再用麻绳一条结成冠卷以将冠顶固定,多余绳子垂下作为垂缨系于下颌。首绖以有子麻绳制成,围长3.6m,从额前向右围,过头顶后将绳末,系在左边绳端,又用绳作为垂缨如同斩衰冠一般固定在下颌。
腰绖是穿丧服时所用麻带,类似古人着革带时所搭配的大带。带围周长0.28m有余,两股相交,两头相结,有绳缨垂散长1.2m,其相结处两旁各用细绳系之。其绞带用有子麻绳所制成,将腰绖中屈,分为两股,各0.4m多长,其大与腰绖基本相当,从左向后至前,将腰绖贯串起来。
服丧期间需要持杖,斩衰苴杖用竹,高齐心,本在下。关于为何持杖,龚端礼在《五服图解》中认为:“孝子爱亲哭泣无数,服勤三年身病体羸,以杖持助,其病故也”[7]9,而斩衰之杖用竹,是取“父是子之天,象天内外有节能贯四时不变,象子内外之痛亦经寒温而不改也”[7]9之意,同时竹子也有斩断不可接却本性不改之特点,为士人所推崇,希望孝子如同竹子一般不改其孝行,竹杖齐心是希望孝子心存其节。
女性穿着用极粗生布制成的大袖长裙与盖头,衣裙皆不缝合,盖头为布头巾,戴竹钗,穿布屦,妾穿褙子代替大袖。
(二)齐衰三年
齐衰,齐为缉之意,即有缝合之处。其衣、裳、冠之样式基本如同斩衰,但布料用次等粗生布,以显示与斩衰之不同,此外还有多出细微不同:衣旁与下际皆缝合;冠以布制作冠卷及垂缨;首绖用无子之麻制成,绳结在右,绳末系于绳结下的垂缨;绞带不用麻而用布,屈右端0.4m。此外齐衰亦需要持杖,杖以桐木为材,因“桐”与“同”同音,取“内心悲痛一与父同,以桐外无节,象家无二亲尊”[7]9之意。
杖期、不杖期、五月、三月皆穿齐衰之服。杖期守孝一年,因需持杖,故称杖期。杖期与齐衰服制基本一致,只布料改用次等生布。不杖期同样守孝一年,但不需要持杖,故曰不杖期,服制与杖期相同。五月、三月根据守孝时间而定之名称,不持杖,服制与杖期相同。
(三)大功九月
大功九月即需要守孝9个月,服制与齐衰相似,用稍粗熟布。背后无负版、胸口之衰以及辟领,首绖之围也改为0.2m,腰绖为0.16m。
(四)小功五月
小功五月为守孝5个月,服制与大功九月基本一致,但用稍粗细布。冠顶上三陬,改向左缝之,腰绖之围也变为0.12m。
(五)缌麻三月
缌麻三月,守孝3个月,服制与小功五月相仿,但用极细熟布,首绖之围改为0.12m,腰绖为0.08m,与垂缨皆用熟麻制成。
由于朱熹理学思想受到宋元二代儒生推崇,元代士庶基本沿袭《家礼》对丧服制度的要求,但在其基础上略加改动以适应当时社会环境。同恕在《答王茂先经历论丧服书》中曾称:“今人无受服及练服,故《家礼》亦不言练服制度。今士大夫家一遵《家礼》,小祥但以稍细熟布改为一冠,去首绖。衰服则去负版辟领,衰如此而已。首绖一除,无服再用,盖去古已远,岂能一一尽如《礼经》”[10]。认为元代士人仍是遵守《家礼》,在小祥中,将冠之布料改换为稍细熟布,同时去掉首绖;衰服去掉负版和辟领。龚端礼在其著《五服图解》中提到“朱文公《家礼》所载前项丧服皆案古宜今,当世士大夫家多遵此而为之,惟下俚之人或不能备此衰裳之制,俗作粗布宽袖襕衫、布头巾,然绖带故不可阙,盖礼之不下庶人故也”[7]5,即士人多遵《家礼》,然普通百姓并没有能力购置衰裳,只得用粗布宽袖襕衫和布头巾等代替。金履祥在《为师吊服加麻议》一文中称“布襕之服,俗服也。今之服缌功之上者皆用之。生绢钩领之衫,俗服也,今之服缌麻者亦用之”[11]。可见元代士庶并未完全按照朱熹《家礼》所记进行丧礼,而是结合当时社会情况以及自己经济状况挑选最适合自身的丧服制度,不同儒士之间关于丧礼也会有不同看法。
三、元代丧礼文化
“多元”是元朝社会主要特点,出现此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多地区、多族群民众主动或者被动进入到中原地区。其中,蒙古人、色目人中接受汉文化较深者开始学习汉人丧礼文化,为亲守孝期间穿戴丧服。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这些进入中原地区的其他族群群众,也给中原地区带来了他们的丧葬风俗,使元代丧礼文化呈现多元盛象。
(一)蒙古、色目人学习汉人丧礼文化现象
多族群之间文化交融导致的丧礼文化互相影响,进入中原地区的部分畏兀儿人开始学习汉人丧礼风俗,引起元朝统治者不满,随即颁行禁令,“休似汉儿体例行者。搭麻花、挂孝、穿团头,都休穿带者。烧了收骨殖呵,休似人模样包裹者。休煖墓儿者。休引灵者。或是拣莫那个七条里,休依汉儿体例,纸做来的金银、纸房、纸人、纸马、襖子,休做者”[12]1060。由禁令来看,当时已经有畏兀儿人如汉人一般穿戴丧服,同时有些人将畏兀儿人改学汉人丧礼归结于自身丧事体例落后,“这汉儿田地里底众畏吾儿每,丧事体例有呵,自己体例落后了,随着汉儿体例”[12]1060,规定在“汉地”的畏兀儿人不准采用与汉人相同的丧礼。
外来族群学习汉人丧礼在元代是十分常见的现象,有大量蒙古、色目人在礼俗方面学习汉制,以丁忧制度为例,元朝规定汉人、南人为官者必须丁忧,而蒙古人与色目人则各从本俗即可,但还是不乏自愿辞官为父母丁忧者。如回回人丁鹤年,戴良《九灵房山集》和乌斯道《春草斋集》曾记载其为父母守孝丁忧之事;高昌人廉希宪,《元史》中称为父母守孝时,按古礼不饮不食;蒙古人达理雅饬为母丁忧放弃更高职位,等等。这些事迹,充分说明了当时非汉族群中已有人接受儒家文化中关于丧礼与丧服的内容,学习当时汉人礼俗,并深刻践行。大量西域人进入到“汉地”,他们在带来自己文化的同时也受到汉人文化影响。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在元朝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在此情况下,内迁蒙古人与色目人逐渐崇尚儒学,成为包括丧服制度与丧葬文化在内儒家理论的践行者。
(二)汉人受蒙古丧礼文化影响
元朝政府开始限制汉人丧礼中的一些“奢靡”行为,如在至元七年(1270年)十二月禁止丧葬纸房子等物,认为“民间丧葬,多有无益破费。略举一节,纸房子等,近年起置,有每家费钞一两定钞底,至甚无益。其余似此多端”,要求“除纸钱外,据纸糊房子、金银、人马并彩帛、衣服、帐幎等物,钦依圣旨事意,截日尽行禁断”[12]1061。同时也如前文所提到的禁止“汉地”畏兀儿人丧葬纸房子、纸马等。民间奢靡之风由来已久,元初胡祗遹曾作文讨论过此事,认为朝廷需要“禁断奢侈淫丽,定立等级聘财、桑薨、屋宇、衣服、筵宴程试”[13]。在葬礼中,元朝亦大有铺张之现象,涂全周曾在至大元年上书称:“切见江南流俗,以侈靡为孝。凡有丧葬,大其棺椁,厚其衣衾,广其宅兆,备存珍宝、偶人、马车之器物,亦有将宝钞藉尸敛葬,习以成风。”[12]1068有鉴于此,朝廷要求:“除纸钱外,据纸糊房子、金银、人马、财帛、衣服、帐幙等物,钦依圣旨事意,截日尽行禁断。”[12]1068
蒙古人自来追求简丧薄葬,只用普通棺材收敛,下葬之冠服“一如平时”[14]230,然后“被密密地埋葬在他们认为是合适的空地上”[15],没有汉人死者亲属斩衰、齐衰、大祥、小祥以及斋戒等丧葬礼仪。进入中原地区的蒙古人继续采取此种丧葬风俗的同时,又如上文所引一般,统治者通过行政手段禁止厚葬久丧,使汉人丧礼出现明显变化,出现“不求安死,而求利生”[16]的呼声,虞集也曾嘱咐其子“以深衣敛,毋用浮屠”[17],以求简葬。
(三)元代丧礼不规行为
按照朱熹《家礼》记载,宋元时期丧礼都是通过厚葬逝者、劳苦生者方式,达到使生者心安之目的。如丧礼初终仪式中,逝者的亲人要“易服不食”,用穿粗布衣服和不吃饭的方式抵消心中的悲痛。然据元代监察御史王奉训发现,在江南地区出现服丧期间,“去古日远,风俗日薄,近年来,江南尤甚。父母之丧,小敛未毕,茹荤饮酒,略无顾忌。至于送殡,管弦歌舞,导引循柩。焚葬之际,张筵拍宴,不醉不已”[12]1064的饮宴响乐现象。同时,在送殡出殡时,无品官者使用仪从和乐队也都是不合规制之行为,“若品官遇有婚丧,止依品职,合得仪从送迎。外,禁断无官百姓人等,不得僭越,似为中礼”[12]1063,以及“上位承应的乐人每,依着在先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圣旨体例里,死人每根底,休迎送出殡者”[12]1063。
(四)元代丧礼僭越行为
元代江淮地区曾出现将幞头等公服作为丧服的现象,延祐二年(1315年)时监察御史刘承直称“切见江淮之间习俗,丧服有戴布幞头、布袍为礼者”[12]1065。幞头在宋代虽是公服一种,“公服。凡朝服谓之具服,公服从省,今谓之常服……其制,曲领大袖,下施横襕,束以革带,幞头,乌皮靴。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18],但也被允许士庶在日常生活中穿戴,只是对其规格有所限制,“幞头巾子,自今高不过二寸五分”[17]3574。在南宋时期,朝廷同样对婚丧冠服进行管理,要求“凡士大夫家祭祀、冠婚,则具盛服。有官者幞头、带、靴、笏,进士则幞头、襕衫、带,处士则幞头、皂衫、带,无官者通用帽子、衫、带;又不能具,则或深衣,或凉衫。有官者亦通用帽子以下,但不为盛服”[17]3577。
元朝承袭部分宋朝舆服制度,亦将幞头作为公服之一,“百官公服……幞头,漆纱为之,展其角”[19]。同宋朝一样未将幞头归入祭服之列,朱熹在《家礼》中仅称幞头可用作凭吊之服,“凡吊皆素服,幞头衫带,皆以白生绢为之”[9]913。穿戴幞头作为丧服在时人看来是不符规制的,按照朱熹在《家礼》中所提出丧服规制,丧服头冠应是斩衰、齐衰冠和首绖,“丧礼,斩丧、齐丧以至缌、功,自有官服之制,亦有轻重之差”[12]1065“其幞头公服,乃人臣服于朝廷,拜贺之吉服也。今愚俗无知,乃敢以布素为之于凶服之际。揆之礼经典故,皆非所宜,理应禁捕”[12]1065,这一提议被朝廷认可,规定“方今丧服未有定制,除蒙古、色目人各从本俗,其余依乡俗,以麻布为之。外据江淮习俗,比依公服制造,如准御史台所呈,禁治相应”[12]1065。此现象明显僭越了当时朝廷所指定的服饰秩序与礼法规定。其实在元朝服制僭越现象已是屡见不鲜,包括权势之家公为私用、士庶之家则花钱雇佣祗侯充当迎亲送殡仪从之举,也并非元仁宗年间特例。在世祖朝时,王恽曾在《上世祖皇帝谕政事书》中提到“今也臣民衣饮逾于公侯,妇女衣着等于贵戚”,并认为要“定制度以抑奢僭”[20],以后也多有文人上书讨论奢靡僭越之事。
(五)元代火葬丧俗
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时,北京路同知称“伏见北京路百姓,父母身死,往往置于柴薪之上,以火焚之”[12]1062,类似的记载也曾见于《析津志》,“城市人家不祠祖祢,但有丧孝,请僧诵经,喧鼓钹彻宵……孝子家眷止就寺中少坐,一从丧夫烧毁,寺中亲戚饮酒食肉,尽礼而去。烧毕,或收骨而葬于累累之侧者不一。孝子归家一哭而止,家中亦不立神主。若望东烧,则以浆水、酒饭望东洒之;望西烧,亦如上法”[14]209。火葬之俗由来已久,在临洮寺窪山新石器时代遗迹中曾发现有火葬痕迹[21]73。据前人学者考证,自隋唐以降火葬在中原地区传播开来,宋代更是中国历史上火葬最盛的时代[22],但是此行为是当时儒士所不能接受的,朱熹曾告诫弟子,“用僧道火化……或火化则不可”[9]3009。元朝受宋代火葬流俗影响,除却上文在大都附近有火葬现象外,江南地区也存有。在《马可波罗行纪》中,马可波罗曾记述在杭州所见火葬之事,“人死焚其尸……及至焚尸之所,取纸制之马匹、甲胄、金锦等物并尸共焚之”[23],可见在火葬的同时还会焚烧金银珠宝、纸人纸马等物,同样违背前文所提元朝政府反对随葬铺张之物。
四、结 语
总体看来,元代汉人丧礼与丧服制度基本沿袭宋代,尤其是朱熹《家礼》一书对当时影响最大,颇受当时儒生追捧。但宋元二代社会环境始终不能同一而论,士人与平民生活条件也不尽相同,故出现“当世士大夫家多遵此而为之,惟下俚之人或不能备此衰裳之制,俗作粗布宽袖襕衫、布头巾,然绖带故不可阙,盖礼之不下庶人故也”[7]5的社会现象。
汉人丧礼与丧服制度作为儒家文化中最重要的“五礼”之一,不仅深刻影响着当时汉人,还改变包括蒙古人、色目人在内的外来族群丧俗习惯。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色目人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亲人守孝时披麻戴孝。蒙古人作为统治者也将中原丧礼文化中丁忧制度采纳为统治手段,规定官员要严格遵守规定为亲守孝,还在官方层面将五服制度正式确立下来。汉人丧礼中厚葬风尚,也受到蒙古薄葬简丧习俗影响,使社会风气发生变化。这种文化交融情况被当时文人赞叹为“混一之盛矣”[24],成为多样性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