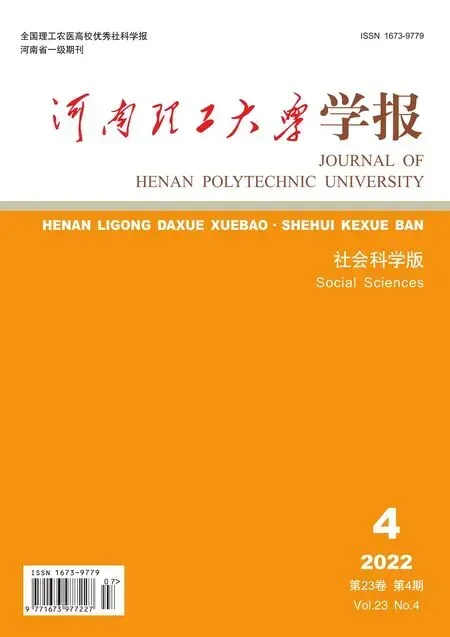“文化记忆”博物馆建构:《荒谬斯坦》中的大屠杀后叙事
何柏骏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在欧文·豪等文学批评家“唱衰”美国犹太文学的声音持续已久之际,新世纪美国文坛涌现了一批新生代犹太文学力量,其中包括以加里·施特恩加特(Gary Shteyngart, 1972—)、安妮亚·尤里尼奇(Anya Ulinich, 1973—)、拉拉·瓦彭亚(Lara Vapnyar, 1971—)等为代表的俄裔作家群。施特恩加特是其中公认的文学明星,其处女作《俄罗斯社交新丁手册》(TheRussianDebutante’sHandbook, 2002)的问世标志新生代俄裔作家在美国文坛的强势登场。《荒谬斯坦》(Absurdistan, 2006)是施氏第二部小说,出版当年被《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评为年度最佳图书之一。[1]其情节主要围绕三十岁的俄国犹太青年米沙·温伯格——俄国黑社会寡头之子——从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经在里海边某虚构国度荒谬斯坦的游荡,尝试返回美国纽约展开。国外对这一新生代犹太作家群体及施特恩加特个人的关注相对较早、较多,对该作品的探究主要集中在犹太性、身份问题、跨文学传统的互文性等多方面。国内近几年来对该作家群、施特恩加特以及《荒谬斯坦》的研究和论述开始兴起,但以综述为主,鲜有的对作品的探讨则聚焦其叙事技巧。
大屠杀是犹太文学乃至美国文学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大屠杀”(Holocaust)一词狭义上通常指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的种族灭绝行为,也称“犹太大屠杀”或者“纳粹屠犹”,为行文便利,本文采用“大屠杀”。大屠杀书写指文艺作品对这一历史性事件的表征,方式是多样的,文学作品是其中的重要形式。此外,大屠杀的文学书写也能细分,一类是见证文学或亲历者文学,通常以此事件亲历者的日记、回忆录为载体,比如《安妮日记》(TheDiaryofAnneFrank); 另一类为非见证文学,对大屠杀题材的显性或隐性描写主要源于非亲历者的间接经验,当代美国犹太文学的大屠杀书写也以此类别为主,同时也孕育了诸如“大屠杀后叙事”(post-Holocaust Narrative)、“大屠杀后意识”(post-Holocaust Consciousness)以及“大屠杀后记忆”(post-Holocaust Memory)等以“后”为标志的术语。“后”既是时间向度,表示时间上同历史上二战大屠杀事件的距离,又与当代以后现代、后殖民为代表的“后学”思潮类似,也有产生流变、对源话语的反拨、重构之意。作为出生在二战后的非大屠杀亲历者,施特恩加特也没有回避这一文学主题,《荒谬斯坦》对大屠杀相关内容进行了书写,本文从“文化记忆”入手,兼论扬·阿斯曼及其他学者的“记忆”理论,对《荒谬斯坦》中的大屠杀后叙事进行解读。
一、“历史”到“记忆”的演进
不管在学术论域还是日常生活中,“记忆”和“历史”两词的使用实际上存在互相替换的混乱。历史学教授克莱恩(Kerwin Lee Klein)在《论记忆在历史话语中的出现》一文中指出:“如果‘历史’(history)是客观表达最冰冷和最生硬的意思,那么‘记忆’(memory)则是主观的携带最温暖、最吸引人的涵义。和‘历史’相比,‘记忆’同丰满的存在共振。我们了解这些联系,但我们假装它们没有对我们使用‘记忆’产生影响。”[2]117以犹太大屠杀而言,学界讨论时少有细究“大屠杀历史”和“大屠杀记忆”两种用语差别引发的理解含混,但应对两者作一些区分。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认为它们不是近义词,而是反义词,其指出记忆是生活,一直在发展,而且它还是一个当前的现象,而历史代表着过去。席卷人文学界的后现代思潮进一步助推了关于历史与记忆的“记忆潮”讨论,催生了“记忆转向”。彭刚教授认为:“现代历史学力图成为与实证科学具有同样学科资格的一门学科,它自觉地追求客观性,将过往历史理解为一元的整体。从后现代主义的批评立场来看,这种伴随着民族国家一同兴起并且以为民族国家进行辩护为自身宗旨的史学,已然成了一种压制(女性、被殖民群、边缘群体等的)工具。”[3]也就是说,现代史学将历史进行整体化、一体化的尝试实际上使得“属下”的历史、话语受到了忽略和消解,这也正是宏大叙事或元话语在后现代语境中遭解构的一大缘由。这一反拨的结果冲击了整体性的、正统性的历史,各种小门类的历史开始出现。换言之,除了本质上的概念差异,后现代语境中的历史还易导致压制和被压制的话语霸权,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小众、多元的声音,而对本就和历史息息相关的记忆的书写则试图缓解这一困境。大屠杀文学不同于官方记载,其提供了各类话语。对此,克莱恩解释道:“我们曾称之为民间史、大众史或口述史或公众史或者甚至于神话的,现在记忆作为一种元史学范畴,将这一切都囊括进来。”[2]113
记忆最初只是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一般指人脑对过去发生经验的识记、保持和再现。历史从根源上讲,也关于记忆,但大屠杀历史是对大屠杀这一事件的尽可能还原,它只会接近于已发生的“历史”,却不能将其完整再现。一般受官方意志和意识形态影响的大屠杀历史侧重于事件日期、发生地、起因经过和结果以及总体的伤亡人数等冰冷的“数字化”内容。而对应集体超越个体的历史通常不会细致到记录某家庭所经历的大屠杀、大屠杀亲历者所体验的某天的天气或者心情,冷静而理性的历史难以覆盖的这些感性、丰富的部分,或许纳入到“记忆”的解释范畴更加贴切。既然提到记忆,不得不考究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20世纪初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首先提出了“集体记忆”这一概念,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讨论个体记忆与他人记忆之关系时,其认为:“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4]69在其看来,人也正是在社会中,通过和其他人的联系才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记忆。他还表示:“既然我们已经理解了个体在记忆方面一如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都依赖于社会,那么我们也就可以很自然地认为,群体本身也具有记忆的能力,比如说家庭以及其他任何集体群体,都是有记忆的。”[4]95概言之,即个体记忆依赖于集体记忆,后者又同前者具有记忆能力, 记忆所带有的社会性特征是哈布瓦赫记忆理论的基石,也为之后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里海博物馆中”的“文化记忆”
哈布瓦赫主要将集体记忆置于个体与集体的范畴区分,未过多将其延展到文化领域之中,于是“文化记忆”应运而生。首先,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文化记忆》一书中划清了该词和“历史”的研究界限,其认为,文化记忆关注过去的某些焦点,它不能将过去依原样完全保留,于是过去被凝结成可供回忆的象征物,那么出埃及、取得迦南土地、流亡都是这样的回忆形象,对于文化记忆而言,重要的不是有据可查的历史,而只是被回忆的历史[5]46。前文中提到记忆基于人体大脑的生理机能,但其必然同社会文化范畴密不可分。再者,阿斯曼严格区分了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前者的存在依赖于同代间的和代际间的社会交往,那么问题在于,一旦这种交往随着见证人的离世和代际交替该如何传递。阿氏认为:“这种记忆所储存的内容、这些内容是如何被组织整理的、这种记忆被保留的时间长短,却远远不是用人体自身能力和调节机制就可以解释的问题,而是一个与外部相关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是个和社会、文化外部框架调节密切相关的问题。”[5]10旨在从文化角度对记忆进行研究的“文化记忆”这一概念,最早是扬·阿斯曼与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基于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共同提出。需要说明的是,“文化记忆”只是阿斯曼对记忆分类的第四种维度①(1)①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一书中将“文化记忆”分为摹仿性记忆、对物的记忆、语言和交流:交往记忆、对意义的传承:文化记忆等四个维度。。文学,若按新历史主义所提出的“文本历史化”与“历史文本化”的观点,文学文本也是一种“历史”建构,但基于前文的比较论述,记忆相较于历史具有感情、个人、丰富等特征,那么作为文化现象的文学也应看做是记忆的载体,同时,考虑其记录和书写的工具性特征,也符合文化记忆理论中的媒介。对此,阿斯曼也作了关于文化记忆承载者的阐述:“文化记忆始终拥有专职承载者负责其传承。这些承载者包括萨满、吟游诗人、格里奥,以及祭司、教师、艺术家、抄写员、学者、官员等,这些人都掌握了(关于文化记忆的)知识。”[5]48文学作为一种文艺形式,作家实则与吟游诗人、艺术家扮演着类似角色。
《荒谬斯坦》中以“一个适度的提案”为标题的第三十五章实际上是一个关于“里海大屠杀研究所,又称‘塞(翁)-犹(太)友谊博物馆’”的提案,[6]307为作区别,本文在论述中简称其为“里海博物馆”。犹太主人公米沙·温伯格被虚构民族——荒谬斯坦国的塞翁族聘为多元文化事务部部长,目的是与以色列建立良好关系,于是温伯格提出这一方案。这样一个博物馆又为何能承载或建构文化记忆?首先,博物馆是一种纪念的仪式形态。“普遍意义的纪念仪式具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行为模式,另一种是建筑模式。行为模式是指悼念、回忆、祭奠、公共讨论等活动……建筑模式则是指纪念碑、公共雕塑、纪念公园、受保护遗址等具有象征意义、能够激发回忆的物理实体。”[7]里海博物馆恰好包含这两种模式,首先它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实体建筑,如文中所描述,地理上它位于里海之边,一个温和的环境,具备了修建教育基地的理想氛围。其次,在以大屠杀为主题的博物馆中还将开展一系列悼念、展示、教育活动,例如,提案中设计了少儿版的大屠杀展览:“少儿版的大屠杀展览将传递这么一个经过仔细推敲后定下的情感混合:恐惧、愤怒、无能即歉疚,十岁以上的孩子都适于观看此一展览。”[6]311所以,它满足了博物馆作为一种纪念仪式形态的条件。另外,关于仪式对于文化记忆的作用,又如阿斯曼所言:“仪式属于文化记忆的范畴,是因为它展示的是对一个文化意义的传承和现时化形式。这一点对那些既指向某个目的,同时也指向某个意义的物同样适用——象征物和圣象——对某物的再现,如纪念碑、墓碑、庙宇和神像等。”[5]12里海博物馆以其行为和建筑两种模式构成仪式,而后者又属文化记忆的范畴,于是该博物馆某种程度上拥有了解释文化记忆的“合法性”。此外,还需阐明它如何建构文化记忆,完好地传承还是重构。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中有一部分东西是传统、是传承,但对其的肯定不可忽视其他现象,比如“接受”“中断”“遗忘”和“压抑”等,换言之,所谓悼念并非“依传统而为”[5]27。对此,阿斯曼认同哈布瓦赫对于“过去”的看法,即“过去”并不具备自主性,其受当下相关框架的文化建构所约束。作为新世纪作家的施氏受其当下认知和经验影响,时间上距离二战大屠杀事件已过近半世纪,自然对于此事的“还原”也是鲜活的。换言之,里海博物馆并非仅呈现“死历史”,而是构造一种“活记忆”。
三、声誉、文化创伤和反犹主义:“里海博物馆”的分支记忆
文化记忆所包含的记忆是十分庞杂的,讨论具体的大屠杀书写文本时有必要做记忆分类的尝试,这也与记忆同历史相对的多元、个人和丰富等特征相一致。以《荒谬斯坦》中的里海博物馆为例,下文将观照其对声誉记忆、文化创伤和反犹主义记忆等分支记忆的构建。
“声誉记忆研究关注的是个人(特别是重要的历史人物)或其他声誉承载者(如组织或作品等)在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声誉塑造和变迁。”[8]施特恩加特对此提案的编码耐人寻味,首先是建筑实体。“这个逾越节除酵饼中的主要陈列空间展示的是一个用金属钛包裹的小羊腿(提示:想想弗兰克·盖瑞的设计)。”这里提到的弗兰克·盖瑞(Frank Gary)是国际著名犹太裔建筑师,以钛金属为建筑设计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是他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就建筑设计而言,作者的方案试图借鉴犹太人中的知名建筑师的理念,使得作为记忆场所的里海博物馆将犹太人中声誉承载者的优秀成果纳入其中。此外,文中也写到:“博物馆的展览在高亢激昂的音符中结束——展示诸多引领潮流的优秀美国犹太人的生平,比如:‘大卫·柯波菲尔德:神话及魔术’……”[6]311同样,此处的大卫·柯波菲尔德( David Copperfield)是享誉全球的犹太裔魔术师。以大屠杀为主题的里海博物馆兼顾了声誉记忆,它表现为将犹太人中对社会有较大贡献的名人及其成就进行展示和促发联想,从而达成为文化记忆中一条“金线”的效果,以表对后世的激励。
讨论大屠杀难以回避创伤,学界对创伤的研究已是汗牛充栋,本文沿着“文化记忆”的建构主义思路,选择“文化创伤”的观点讨论其在《荒谬斯坦》作为一种记忆存在。杰弗里·亚历山大( Jeffrey C. Alexander) 对“文化创伤”的定义为:“当一个集体的成员感到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这个事件在他们的群体意识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永远地标记了他们的记忆,并以根本的、不可挽回的方式改变了他们未来的身份时,文化创伤就发生了。”[9]1亚氏的界定首先肯定了这一术语的记忆特征,其次强调其深远的、对当下和对未来的影响。此外,亚历山大不认为创伤具有自主性,而为社会文化系统所书写。他说:“诀窍在于获得反身性,从被普遍经历的感觉到可以使我们进行社会学地思考的陌生的感觉上去。因为创伤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它是被社会所建构的。”[9]2里海博物馆同样书写创伤,在此不妨考察其结构设计,它呈分成两半的逾越节除酵饼状。“前半个饼列举的史实名称都有点饶舌:克里斯透纳克特、克因德兰斯珀特、克拉考贫民窟、切尔诺维辛、华道维斯、德娄侯拜斯……”[6]310所列的这些事实均同犹太人的苦难经历相关,比如“克里斯透纳克特”是指“水晶之夜”,即1938年德国境内爆发的反犹暴力事件,导致犹太人住所、店铺被毁,数百犹太人丧失;华道维斯是波兰南部小镇,曾被德国纳粹占领,大批犹太居民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海博物馆这一记忆场所将犹太民族群体意识中若干耸人听闻的重大事件集合起来,从而以当下的话语重塑了文化创伤,起到了呼应犹太大屠杀的核心主题的效果。
事实上,当大屠杀话语被视作记忆时,不能忽视苦难背后的罪恶之源——反犹主义(anti-semitism)。徐新教授认为:“反犹主义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有过的所有仇恨中持续时间最长、散布范围最广、后果结局最惨的一种以一个民族为其对象的仇恨。”[10]其指出反犹主义具有普遍性、持续性、暴虐性、潜意识性和再造性等特点。若大屠杀可视作一种文化记忆,那么反犹主义也应是文化记忆,而且是记忆中的记忆,作为最早能追溯到上古时期的文化社会现象,其历史跨度、存在都比大屠杀要久、要广,它深深地存在于犹太人的集体记忆之中,被各种媒介不断地提及、塑造。里海博物馆将包括题为“以为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的附加展设计以指涉大屠杀事件:“是吗,你是这么认为的?朋友,再好好想一想吧。这块立意大胆的概念恐空间将展出几十个法籍阿拉伯青年,他们向过往的参观者投至石块,并威胁说:‘再死六百万’!”此处表面上谈到“这种事”,将其和失去六百万犹太同胞的大屠杀联想起来,实则是在提醒反犹主义的“阴魂不散”,警醒“大屠杀遗忘症”。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民族“负资产”,反犹主义也不完全是另人担忧、恐惧的,与声誉记忆相似,它也能产生积极作用。反犹主义在持续地给犹太人带去苦难的同时,也是迫使犹太人团结、凝聚和发展犹太文化的外部诱因,里海博物馆声援了这一立场。现实中犹太人的确以设立机构、组建利益共同体等方式,一直持续地同反犹主义作斗争,“特别是关系到美国犹太人人切身利益的利益集团,如犹太人大会,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建立,进一步抵制反犹主义,成功捍卫了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利益”[11]。
四、节日与身体:“里海博物馆”的记忆机制
与此同时,除了记忆的分支,里海大屠杀博物馆还体现出颇为明显的记忆机制意识。前文谈到博物馆作为仪式形态所开启的悼念、祭奠等行为模式,记忆机制是指记忆如何作用于个体,侧重于突出参与者作为主体如何接受或者被传递记忆,可以视为对该行为模式的一种细化和补充。
里海博物馆对节日机制的运用首先体现在将周期性节日与大屠杀相联系。在“建筑设计”这个版块下,作者写道:“里海大屠杀研究所将采用一个巨大的、掰成两半的逾越节除酵饼的形状,以此来纪念我们民族遭受到的这场大难并且提醒我们记住逾越节晚餐……”逾越节(Passover)是犹太人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以纪念先知摩西率领犹太人出埃及一事。文化记忆理论强调神圣形象和宗教意义,而这一强势的符号则同时携带宗教性和文化性,因为逾越节是《圣经·旧约》“出埃及记”中的内容,犹太教本就是犹太民族的重要精神宝库;此外,作为仪式的节日在周而复始的重复之中发挥其作用机制。对此,其重要性被扬·阿斯曼着重阐述,其在论述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的不同时,指出:“两种形式的集体记忆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在时间层面上表现为节日与日常生活的根本性差异……”[5]50前者主要源于日常生活,一个人同他人之间的交往,然而节日与普通日子不同在于其仪式性,强调集合成员的在场,而这是获取文化记忆的重要形式。其认为,在无文字社会中除成员亲自参加集会外,无其他途径供集体成员获取文化记忆,而节日为集会提供了理由。节日的周期性保证巩固认同的知识的传递与传承,由此保证文化意义上的认同的再生产[5]52。在里海博物馆,逾越节与大屠杀记忆交织,既推广、传承了这一节日,加之其本身能发挥再生产记忆与认同的作用,又将大屠杀这一经历融入节日之中,大屠杀记忆的传承也就拥有了具有重复性、隆重性的载体。
其次,身体也作为记忆的机制。从生理学角度看,身体机制生效时调动的是身体的生理机能,例如感官。大屠杀博物馆作为一种景观化的场所,参观者的视觉、听觉、味觉等感官功能会自然而然地运作。小说介绍少儿版的大屠杀展览时写道:“研究表明,越早给小孩子看骷髅以及赤身裸体的妇女在波兰的雪地里被追赶的影像越好。”[6]311大屠杀影像展览就同时促发了视觉和听觉刺激。再比如,“这块立意大胆的概念空间将展出几十个法籍阿拉伯青年,他们向过往的参观者投掷石块……”[5]311石块投掷到人身上激起了参观者的触觉,会产生疼痛等感觉,而身体对疼痛是有记忆的。此外,包括作为逾越节传统食物的除酵饼,尽管这里没有实物而只是建筑物的外观,也能促发是一种味觉联想。但是,施特恩加特对于身体如何记忆的认识不止停留于此,他还强调身体的生殖功能。从“提案概述”开始,他写道:“鉴于美国社会人口纷杂、着装暴露,该国内长相国关的非犹太伙伴人数众多,从而使得说明年轻的犹太人在彼此间进行繁殖性性交活动变得日益艰难,即使不是完全无望的话。”[5]307这里其实暗含了这所里海博物馆以大屠杀为主题的一部分目的,该点在提案中的“合欢帐”一栏一览无余:“此处是整个展览开花结果的地方,它突显的是‘繁衍延续’这四个字。处在生育期内(三十四到五十一岁)的犹太裔观众在进入帐篷后,只需提供一份血样和通过信用审核,就可以让希特勒及其爪牙们的‘最终解决方法’去见上帝。”[5]312结合以身体政治、身份政治等为标志的“泛政治”后现代语境而言,作者所“倡导”的发挥人类繁衍能力的身体实则具有了社会和政治意识,或者说上升为一种权力,只是身体成为了权力的主体,而非受压制的客体,它是对创伤记忆的宽慰,同时也是对旧权力话语的挑战。
犹太人在当下美国的同化使得纯正的犹太人越来越少,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改变宗教信仰,二是和异族通婚。另外,此处提及的“最终解决方法”(Final Solution)是指德国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于是,大屠杀记忆又同族群的延续相结合。事实上,在当今保守的犹太教正统社区中犹太女性仍承担着较重的生育任务。依小说的思路,倘若最实际的解决犹太“人口流失”的办法是让身体行动起来,那在此过程中身体也获取了这一苦难记忆。其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指出:“我尤其抓住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不妨,因为我想论证,正是对它们的研究使我们明白,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12]40但是,显然这里的“合欢帐”设计更多是仪式性和具有象征意味的,其实施效果恐怕难以估量。如果将对“最终解决办法”的反击和弥补犹太人死去的六百万同胞作为战略性目标,该行为或许只是种大胆的设想。康纳顿也认为:“仪式是表达性而非工具性艺术,就是说,它们不指向战略性目标,或者,即使他们指向战略性目标,例如对生殖仪式来说,它们也不能达到自己的战略性目标。”[12]49
五、结 语
西奥多·阿多诺曾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对此论断的理解有很多,笔者认为,此话至少透露了一个讯息,即在经历像大屠杀这样的惨剧后,去记录和描写它是件困难的事情。事实上,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未止,关于大屠杀的讨论也未停歇,说明学界普遍认为大屠杀是有必要继续书写的,此举既是对受难过去的悼念,也是对后世的警醒。二战之后大屠杀议题并未在文学作品中匿迹,相反,这一叙事在众多作家笔下涌现,成为不少犹太作家表露身份、彰显犹太性的重要元素,加里·施特恩加特作为新世纪犹太作家凭借其后叙事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前人的写作传统。从“历史”到“记忆”的转向讨论是后现代语境下的产物,也体现文学作为重要记忆载体的思维路径。相较于宏大的、官方的数字记录,大屠杀叙事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将那些私人化的、情感上的经验通过作品向世人诉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记忆便为这一表达方式提供了有利的媒介。《荒谬斯坦》中的里海大屠杀博物馆作为“文化记忆”建构的场域,以节日、身体等记忆机制形塑了声誉记忆、文化创伤和反犹主义记忆等分支记忆,同时也表达了对民族、文化等话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