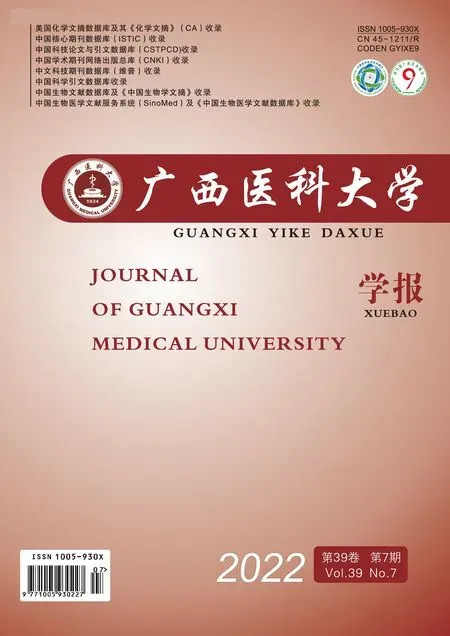终末期肾病患者血脂异常危险因素的研究进展*
刘春晓,孟晓燕,吴春香,施宗湖,尹瑞兴
(1.广西柳州市工人医院,柳州 545007;2.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宁 530021)
终末期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是一种慢性的复杂性疾病,常见合并血脂异常[1](dyslipidemia,DLP),其DLP 患病率超过50%,高于非ESRD患者[2]。据统计,心脑血管疾病是ESRD患者主要死亡原因,约占死亡负担的30%~50%[3-5];而DLP又是心脑血管疾病进展的独立的、传统的危险因素,特别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升高增加其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血清LDL-C 水平可降低其冠心病患病率[6-8]。本文针对ESRD患者DLP的危险因素进行综述,以期早期发现并干预,改善ESRD患者预后。
1 肾小球滤过率降低与DLP
ESRD 患者肾小球滤过率降低改变其血脂谱,主要表现为高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血症和高甘油三脂(triglyceride,TG)血症。部分患者血浆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脂蛋白a、极低密度脂蛋白水平降低,TC/HDL-C水平升高。少数表现为HDL-C、脂蛋白a水平和HDL-C/apoA-I升高或低TC血症[9-10]。肾小球滤过率改变与DLP 的联系机制尚未完全阐明。ESRD 患者血脂紊乱的病理生理因素复杂,可能包括胰岛素抵抗、脂肪细胞因子、内皮功能障碍、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激活和氧化应激等[11]。胰岛素抵抗可能是其DLP 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环节。研究发现肾脏病早期就存在胰岛素抵抗,其机制可能与氧化应激、炎症反应、肾脏血流动力学改变、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不适当的兴奋、维生素D 缺乏、代谢性酸中毒、贫血、脂肪因子紊乱和微生物毒素等有关[12]。此外,ESRD 大多数患者可有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血清甲状旁腺激素水平增加,可引起脂蛋白酯酶、肝酯酶合成、释放及活性下降,最终导致外周TG清除受损,引起TG水平升高[13]。同时,高水平的甲状旁腺激素使胰岛细胞内钙水平增加,抑制胰岛素分泌,引起胰岛素抵抗及糖耐量降低。另外,肝脏分泌极低密度脂蛋白增多,TG水平升高,通过胆固醇脂转移蛋白的作用降低HDL 水平[14]。因此,笔者推测在ESRD 患者中,显著降低的肾小球滤过率导致ESRD 患者代谢紊乱,增加其胰岛素抵抗风险,导致其DLP发生。
2 ESRD 的病因与DLP
糖尿病是大多数发达国家ESRD 的主要病因[15]。2016 年“中国慢性肾脏病的流行趋势”研究报告显示,2010—2015年我国糖尿病肾病的比例为21.3%,已成为慢性肾脏病的首要病因。伊海玥等[16]报道,糖尿病肾病患者DLP 的患病率为90%,主要表现为血清TG升高(72%,144/200),血清TC(60%,120/200)和LDL-C(52%,104/200)升高,而HDL-C水平降低(64%,128/200)。Hirano等[17]提出,糖尿病患者肾功能衰竭是富含TG脂蛋白相关的DLP的独立危险因素。然而,导致终末期糖尿病肾病如此高的DLP患病率的原因,尚未完全阐明。这可能主要与糖尿病存在胰岛素抵抗、肾小球滤过率降低、炎症反应等因素有关。内脂素是由Fukuhara 等采用差异显示技术发现的一种脂肪细胞因子,其在内脏脂肪组织中高度表达,可在肾小球足细胞和近曲肾小管细胞中合成。2006年有研究表明,内脂素的生理功能主要与胰岛素受体上的非胰岛素的结合位点结合,激活胰岛素信号传导途径,发挥降低血糖的作用。因此,内脂素具有类胰岛素活性,与脂代谢素乱、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同时,内脂素主要由内脏白色脂肪中的巨噬细胞释放,推测其可能也是重要的促炎性因子。近期研究[18-19]表明,糖尿病肾病患者的血清内脂素水平比单纯糖尿病患者高,在其尿微量白蛋白正常时已开始升高,并且随着其肾小球滤过率降低而增加;有研究[20]发现,血清内脂素与尿素、肌酐水平呈正相关。由此推测,糖尿病肾病ESRD患者的DLP与其血清内脂素水平升高起到的促炎作用有关。
IgA 肾病(immunoglobulin A nephropathy,IgAN)约占我国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的24.3%,是我国ESRD的主要病因。许园园等[21]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小儿肾病中心确诊为原发性IgAN的患儿资料,发现慢性肾脏病1期和慢性肾脏病2~5 期IgAN 患儿伴发DLP 的比例分别为65.0%和84.4%,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伴高血压和低血清白蛋白是IgAN 患儿伴发DLP 的风险为2.734 倍和1.193 倍。国内众多研究表明,成人的IgAN 的DLP患病率与儿童的相近[22-23]。IgAN 和DLP 目前均被认为是与遗传、环境等多种因素有关的一组综合征。CMIP基因位于第16 号染色体16q23,编码Cmaf 诱导蛋白,研究认为CMIP基因主要作用于T细胞信号通路。而T细胞受体可识别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上结合的抗原,激活T 细胞,参与炎症反应,促进IgAN 的产生和进展。此外,潘玲[23]研究阐述了CMIP基因与血清TC、LDL-C 及HDL 水平有紧密联系,其研究发现IgAN患者的CMIP单核苷酸多态性rs16955379 和rs2925979 点突变及组成的单倍体增加其DLP 风险。因此,IgAN 终末期的高脂血症可能与炎症反应和基因易感性等因素有关。
3 微炎症状态与DLP
微炎症状态是机体在各种微生物、内毒素、化学物质、免疫复合物、补体等刺激下,以单核巨噬细胞系统激活,C-反应蛋白、转铁蛋白、肿瘤坏死因子α 和白细胞介素-6等为主的促炎症细胞因子释放为中心的缓慢发生和持续存在的微炎症反应[24]。微炎症状态是诱发ESRD 患者并发症的中心环节,也是影响残余肾功能和透析充分性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ESRD 患者脂蛋白a 与C-反应蛋白水平正相关关系,HDL-C与C-反应蛋白水平呈负相关关系[9],腹膜透析患者的TG与超敏C-反应蛋白水平呈正相关关系[25],而其它血脂与超敏C-反应蛋白无相关性[26]。Rohatgi 等[27]报道部分ESRD 患者HDL-C 水平降低与炎症性疾病风险增加相关,这与HDL在急性和慢性炎症状态时表现出的生物功能有关。这些功能包括逆向胆固醇转运、抑制炎症和氧化以及抗糖尿病特性[27]。因此,微炎症状态与ESRD 的异常血脂相互影响,是其DLP 发生的危险因素,也是导致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中心环节[28]。
4 低氧诱导因子减少与DLP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贫血患病率为86.67%,腹膜透析患者贫血患病率为94.21%,其血清TC 和LDL-C水平与贫血程度呈正相关关系[29]。低氧诱导因子(Hypoxia-inducible factor,HIF)浓度变化可能是联系ESRD患者贫血与DLP的中间环节。研究证实,HIF参与了肾性贫血的作用机制[30-31]。肾性贫血时组织缺氧,氧依赖性的脯氨酸羟化酶被抑制,HIF-1a水平升高,异位至细胞核并与HIF-β形成二聚体,激活EPO转录,刺激内源性促红素生成。同时,HIF-1α也上调促进肝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相关蛋白1表达,导致大鼠血浆的TC、TG、LDL-C和HDL-C升高[32]。2019 年上海瑞金医院的陈楠教授等在ASN杂志上公布了一项Ⅲ期临床研究结果,表明在透析患者中低氧诱导因子脯氨酰羟化酶抑制剂(罗沙司他)显著降低TC、LDL-C、TG水平和LDL/HDL-C比值。这与低氧诱导因子—氧依赖性的脯氨酸羟化酶轴的下游靶基因调节血脂相关[33]。该药物研究结果从另一方面提示ESRD患者中HIF-1α浓度降低,增加其DLP风险。
5 其他细胞因子失衡与DLP
成纤维生长因子21(fibroblast growth factor,FGF21)是多肽因子,有促进细胞增殖分化及多系统效应的功能。大量研究表明,FGF21 通过多种机制发挥降脂作用:(1)FGF21 通过激活腺苷一磷酸激活的蛋白激酶—转录沉默信息调节因子1通路增强线粒体氧化,促进脂质氧化,维持脂肪细胞内的能量稳态[34];或通过转录沉默信息调节因子1/去乙酰化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PAR)γ 辅激活因子1α 通路改善棕榈酸酯诱导的细胞线粒体损伤以及炎症反应以降低脂肪堆积[35]。(2)FGF21同时也是PPARα 和PPARγ 的关键下游靶标,介导PPARα激动剂及PPARγ激动剂发挥降脂、降糖和增加胰岛素敏感性作用[36]。(3)FGF21单独调控肝细胞胆固醇基因表达和胆固醇合成限速酶β-羟基-β-甲基谷氨酰-CoA还原酶通路改善血脂谱;也可通过FGF21受体和β-klotho受体结合形成的复合物抑制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转录因子2 基因,以抑制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9 基因表达,降低小鼠的血清TC 水平[37]。(4)FGF21 作用于下丘脑促皮质酮释放,并诱导脂肪细胞中脂联素分泌和表达[38],以脂联素依赖方式,逆转胰岛素抵抗、高血糖、高血压和炎症反应[39]。然而,临床观察到的是,血清FGF21 水平随着肾小球滤过率下降而升高,慢性肾脏病患者的FGF21水平较健康对照组高20 倍,ESRD 患者FGF21 水平与血脂水平变化呈正相关关系[40],提示高浓度的血清FGF21与DLP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具体的机制尚不明确,这可能是ESRD患者处于DLP状态时,机体通过自身调节升高FGF21浓度来改善其血脂谱。
ESRD 患者常并发血清1,25-(OH)2D3 水平降低。其血清1,25-(OH)2D3水平降低时,可发生胰岛素抵抗或胰岛素分泌缺陷导致高TG 血症;或通过上调代谢途径中相关基因(如脂蛋白脂肪酶基因)的表达来降低肝细胞内TC含量[41],或增加人肝癌细胞系、人单核细胞系巨噬细胞衍生的泡沫细胞中肝脏X 受体以及三磷酸腺苷结合膜盒转运蛋白A1 和G1 的表达,促进胆固醇的外流导致血清TC 浓度增加。研究发现,给高TC 血症的小鼠注射1,25-(OH)2D3 可持续降低其血浆中TC 的水平。1,25-(OH)2D3 药物疗效观察结果从另一方面提示,ESRD 患者血清1,25-(OH)2D3 水平降低是DLP 发生的危险因素。
6 肾替代方式与DLP
血液透析(hemodialysis,HD)和腹膜透析(peritoneal dialysis,PD)是ESRD 的常见替代方式。HD和PD 患者的DLP 患病率不同:132 例HD 患者中65%存在至少1 项DLP,女性、年龄<45 岁、透析龄<12 个月、糖化血红蛋白>6%是其DLP 的危险因素[10];PD患者DLP患病率(63.89%)较HD的患病率(57.78%)高[29]。患者接受HD治疗后较其治疗前的血清TG 水平升高,而接受PD 治疗后较治疗前的TC、TG、LDL 水平和LDL/HDL 比值升高,提示PD较HD 患者更容易出现脂代谢紊乱。然而,也有报道HD 或PD 治疗的患者血脂代谢无差异[26]。除了前面综述的原因,HD 患者的DLP 发生也与其长期使用肝素有关。肝素增加ESRD 患者DLP 风险,是因为肝素使脂蛋白脂肪酶和肝三酰甘油酶含量减少;抑制卵磷脂—胆固醇酰基转移酶的活性,使脂肪降解障碍[42]。上世纪七十年代DeFronzo 等运用高糖钳夹试验发现那些没有明显糖尿病的血液透析患者存在严重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部位定位于骨骼肌,当胰岛素抵抗改善后可明显提高透析疗效,这也说明胰岛素抵抗存在于HD患者中,可能也是其DLP发生的原因。PD患者的DLP异常与其腹透超滤时白蛋白大量丢失,及其使用含糖腹透液导致脂代谢异常有关。研究表明,ESRD 患者接受HD 或PD 治疗后,存在小分子物质肉毒碱的丢失。肉毒碱有促进脂类代谢,将长链脂肪酸带进线粒体基质,并促进其氧化分解为细胞提供能量,减轻炎症因子水平改善微炎症等作用[43],ESRD 患者肾替代治疗后肉毒碱的不足也是其DLP的危险因素,适量补充可降低其DLP 风险。此外,HD 治疗模式不同对血脂影响有明显差别。HD和血液透析滤过不能清除TC 和TG;低通量透析不清除血脂,而高通量透析后的血清TG、TC 和脂蛋白a 水平较前降低。树脂吸附联合HD能有效地清除血清TG,而不能清除TC。这与透析器膜材、孔径或吸附柱孔筛分或电荷作用对不同分子量的脂质清除的能力有关。
ESRD 患者DLP 的危险因素较多,与其肾小球滤过率降低、ESRD病因、胰岛素抵抗、基因易感性、微炎症状态、细胞因子失衡和选择肾替代方式等危险因素有关,这些危险因素可能改变ESRD 患者的脂代谢途径、影响其脂代谢途径中的相关基因表达。这些危险因素相互作用,增加ESRD 患者DLP的风险。深入研究这些已知的危险因素,探索发现ESRD 患者DLP 的未知风险因素,积极寻求管理DLP 的策略,这将在降低ESRD 患者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持续改善其生存质量和延长生存期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