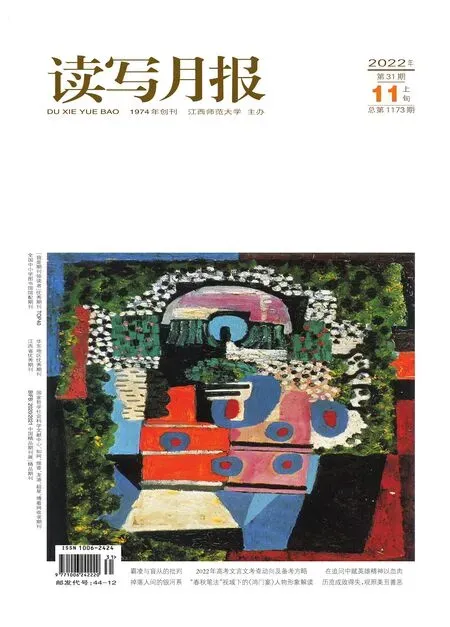掉落人间的银河系
深圳育才中学高二(6)班 黄浩翔

高一下学期,我决定当个自闭青年,老老实实地为分数而闭关修炼。
从一个主动者变成接受者之后,再观察那些或陌生或熟悉的面孔,我顿时感觉自己踏入了一个新大陆:穿行在人满为患的走廊,每向前走两步,就要避让来来往往的行人。然而与本班同学相遇,我们却总是默然无语,素不相识般擦肩而过。于是,我一方面在走廊中近乎寸步难行,一方面却又是“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
不过也正常,毕竟才刚刚分班,班里又有三十多个女生,会主动跟我打招呼才怪(我的颜值还没有到人见人爱的高度)。
就这样与大家静默了个把月,总算有人过来踹破了我的沉默。一个坐我正前排的女同学。她个子不高,头发偏长,脸蛋则与李白诗中的“白玉盘”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大又圆又漂亮。如果只在她静坐时看其侧脸,那么她就飘然若仙。然而她平日里嗜聊如命,红嘟嘟的小嘴一张,顿时就如脱缰的野马、下山的猛兽,一下就把方圆十米内搅得天翻地覆、哄笑不止。我们熟了以后自然免不了要说几句话,我在她身上发现,原来异性之间最让人感到亲近的打招呼的方式,不是礼貌真诚的问好,而是对彼此阴阳怪气的嘲讽,如:“哟,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我真是担当不起呢。”她说这话时眼睛无辜地直视着你,洁白的脸上搭配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然而嘲讽的神色从她那似有若无的微笑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像极了一个魔鬼披上了可爱企鹅的外衣,纯真中带着讥讽,讥讽中又沾点滑稽。久而久之,我们每次见面,都仿佛能在对方的脸上看到一些好笑的东西,然后把彼此当作喜剧人尽情嘲笑一番。这样下来,我们竟然没有丝毫距离感。要是老祖宗知道男女互尊互爱的优雅礼数已经沦落到现在这步田地,只怕是要捶胸顿足,气到掀翻棺材板了吧。
后来男女生之间变得熟悉了,打招呼的范围变广了,方式也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相熟的女生见了我,如果是内敛一点的,会把她缩在衣袖里的手掌举起来,朝我挥挥,嘴角也许还会勾起一道浅浅的弧度;大方一点的呢,就会迎上我的目光,露出一副礼貌又不失温度的微笑,有的还会主动向我招手,浑身上下都彰显出一股亲善的气息。
男生间打招呼的花样就更多了。他们大多数不会向朋友挥手或是问好,而是选择一种超越传统的大胆手法:拍屁股。关系越亲近,力道就越大,那沉闷的声响有时让我感到不寒而栗(听着都疼,幸好我还未受此殊荣)。不但讲究力度,拍的时机也很讲究——毕竟人家不会呆呆地等着你去拍。有的时候是从受害者的身后突然发难,并在其反应过来的一瞬前逃之夭夭;有时候是先光明正大地与对方打招呼,与其虚与委蛇一番,然后趁其不备,攻其要害,然后看着对方狂怒的样子大笑。
当然也有文明人打招呼的方式,然而大抵没有拍屁股有趣,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从不主动向别人问好,但是对于别人的问好,我必定会回应。不过,既然有主动向我问好的人,那自然也有不向我问好的人。有的同学呢,因为确实不熟,见到我之后,匆匆瞥了一眼就离开了;还有的人呢,跟我认识,然而见面时往往敷衍得很。看见我了,只是把目光从左到右往我脸上一扫,好像要把它划成两半似的,然后漫不经心地摆摆手,权当结束语。还有更离谱的,见面了,把胸一挺,一句话不留下,旁若无人地、优雅高贵地从我身边踏过。还有的人呢,平时跟我聊得挺欢畅,但是每次看到他,他都在边走路边专注地眺望远方,目光没有一丝偏转,只留下半个侧脸。我好奇地顺着他的目光望去,结果看到的除了树还是树。没啥好看的呀,然而就在我发愣的当儿,人家已经从我的身旁轻轻地飘过去了,挥一挥衣袖,果真没带走一片云彩。
倒不是说我对别人有什么意见,毕竟在某些方面,我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这类现象倒是引发了我对一个问题的思考:为什么打招呼的方式有如此多样的不同呢?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挥手或者微笑只需要消耗人体一点点的ATP,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对于有些人而言,面带微笑地打招呼似乎比让别人杀了他还难。有些人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俗称社牛,在他们看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经过一番较浅的观察,我初步发现了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它来自人们本身。如果你对那些所谓的社牛有过观察,你就会发现,他们带有一种特殊的能量,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光源。在他们与别人交谈时,这种散射光就会渗透在他们的一言一语中,一些原本平淡的语句,在他们口中就会变得幽默有趣;这种光还会依附在他们的每一个动作上,使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与他们对视时,你还能感受到他们的勃勃生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这种光源并非单属于社牛的专利,它其实埋藏在每个人的心里,只不过埋藏的深度和位置不同,表现出来的亮度和形式也各不相同。有些人能把心中的光源发掘出来,于是即便远在百米之外,人们都能感受到他们的活力。他们就像光芒四射的太阳,光耀照人、独具一格。有的人呢,虽然平时很少表现,但是在他们的一颦一笑之间,你也能够感受到一股属于他们的力量,坚韧特别且不外显,这是属于他们的隐藏光源。我称他们为月亮,他们总是能在潜移默化中把能量传递给他人。
那么那些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挥袖公主呢?我称之为黑洞,他们对于光总是来者不拒,然而又只进不出,真可谓宇宙第一祸害。
开玩笑的。一般情况下不存在什么黑洞,这些人应当属于星星。他们的光亮往往不明显,但是会去照耀他们想照耀的人,会回报主动照耀他们的人。于是,太阳、月亮和星星就构成了我们所见到的整个世界。在宇宙中,星星的光聚在一起可以成为绚烂的星云,加上太阳与月亮则可以构成美丽庞大的星系。这美丽星系在现实世界中的投影,就是我们的校园(其实说是整个人类社会也不为过)。
开学一个半月后,我在班上遇到了第一颗太阳——我们班一位身高一米九的男同学。此人声音洪亮,上衣纽扣总不扣。平时见到我们,他总会露出一张灿烂的笑脸,大手一挥,问候我们一番。他愿意把别人的欢乐与愁绪放在自己的心里,他会记得我哪个周末要过生日,他会记得前两天我曾问他怎么取我文章的标题,他会把自己的能量传递给他遇到的每一个人——他是一颗当之无愧的太阳。
再后来,我遇到了第一位可以称之为月亮的人。她是一位女同学。初见时,我听说她性格不热,就先入为主地把她当成了冰山女王,对她爱理不理的。后来接触的时间长了,我发现她其实很温和善良,而且极具同理心。当时我的座位靠里,每次出操回来,我都能看到她静静地伫立在座位一旁,给我让出空隙,一直等我蹭进了那个犄角旮旯里她才坐下;她说话的声音很轻柔,仿佛是怕惊走了静鸟,而且不论我是不是在向她问话,她都会贴心地“嗯?”一声,询问我有什么问题。我极爱自言自语,有时还喜欢飙几声冷笑,但坐在她旁边我愣是忍了两周也没敢胡乱念叨。印象最深的是一次英语测试,语法题我错了一大半,上课又没听老师讲,于是就向她请教。课间十分钟,她用甜美的声音把每道题的每个选项都仔细地讲给我听。她的耐心如同一汪源源不断的泉水,绵绵无尽,一直到把所有的选项讲完,预备铃都已响起。我饱含歉意又带着几分小心看向她,却只见她的微笑温暖依旧。
我从来没见过像她这样婉约体贴的女生,估计她也很少见到我这种低调沉闷的男生,所以那段日子里我们相处的样子就像两个玻璃人,碰彼此一下似乎就得担心对方会不会碎,一点裂痕都不敢在对方身上留下,每时每刻都很礼貌很小心。现在想想,那段时光其实挺好笑的,不过更多的还是难以忘怀。
说到难以忘怀,以现在为界限,回头看,其实我已经遇到了不少令我难忘的人。他们当中有太阳、有月亮,更多的是星星。他们发出或明或暗的光亮,划进我的星空,然后一个个或高调或悄然地化作一个微弱的亮点,最终消失在我的视野里。在这片小小的星空里,在不断交替的明暗间,我最终得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呢?不过是数道日益消散的微痕而已。我曾经尝试着去追寻他们的轨迹,想借助他们身上的光亮改变自己;但是在尝试了很多次之后,发现太阳依旧炽热,月亮依旧温柔,我仍旧是那颗不明不暗的星星(偶尔还带点刺),在浩瀚的银河系中,茫然而无所适从。
后来我才明白,成为月亮或是太阳,不是取决于他人,而是取决于自己。光源就埋在你心里,只有你自己可以把它挖掘出来。
其实,做一颗星星又有什么不好呢?不用太亮,也不用太温暖;没那么多期望,也没那么多人把期望压在你身上。对于那些光芒万丈的太阳,你可以羡慕,但不必去仰望;对于那些温柔可亲的月亮,可以去追寻,但别彼此勉强。至于那些已经逝去的星光,虽然不可能不缅怀,但最终还是要学会放手,去探索新的光亮。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与其计较来去匆匆,不如燃起点点星光。
【简评】善于观察,重复的日常里也有风景,如作者看到的多样有趣的打招呼方式。勤于思索,平淡的现象背后也有发现,如作者从打招呼方式的不同中窥见个性的不同。作者将不同的人比作不同的星体,形象生动,照应了标题。文末关于做一颗星星的领悟升华了文章内容。
【他山之玉】知名画家黄永玉也是命运坎坷。1953 年,黄永玉携家人入京,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执教。他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被批判过,被毒打过。在那段“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人们的身心难免被扭曲,而黄永玉始终以艺术家的性情,尽量过得春风满面——该养狗就养狗,该听音乐就听音乐,该谈古今名著就谈古今名著,该讲笑话就讲笑话,该到草地上翻几个筋斗就翻几个筋斗……他是个名副其实的乐天派,自称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哪怕身在泥沼,处世亦带春风。
朋友们喜欢和黄永玉在一起。黄老成了大名人,仍然玩性不改,叼着大烟斗,聊聊经典、讲讲笑话,偶尔还会哼唱20 世纪30 年代的歌曲,大家有说有笑,好不惬意!
俗话说:“野花不种年年有,烦恼无根日日生。”
做人就得不断地摒弃烦恼,像黄永玉那样,让春风永在脸上、永在身上、永在心里。
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处世带有春风,能让他人、让自己尽快时来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