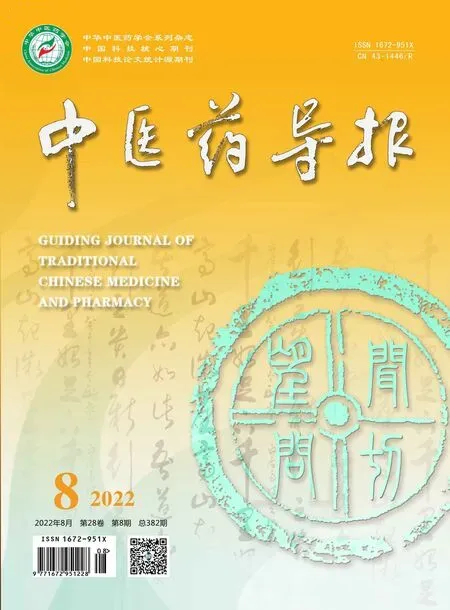陈士铎《石室密录》从肾论治用药探析
朱 悦,许银坤,林育纯,张定华,鄢晓婷,吴翠敏,肖 赟,王一凡,李梓媛,符文彬,5
(1.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康复临床医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2.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 广州 510006;3.肇庆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4.江西中医药大学,江西 南昌 330004;5.广东省中医院,广东 广州 510120)
从肾论治作为中医重要的辨治方法,在临床中有极为广泛的适用性与显著疗效。历代医家从肾论治的认识虽有各异,却都重视对其观点的阐述与临证切用。《素问·上古天真论篇》中就提出“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以藏之”,强调从肾论治脏腑的重要性[1],并在《素问·藏气法时论篇》中记载了“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致津液,通气也”的相应用药思路[2]。汉代张机在《伤寒论》中提出了少阴病脉证并加以从肾论治,如“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附子汤主之”[3]。名医傅山治产后失血呕吐,从肾胃阴亏令虚火上炎加以辨治,倡导养血滋阴以敛阳,补肾养胃而止呕的治疗效果[4]。当今将从肾论治与现代疾病相关联,如:刘如秀等[5]从肾论治心律失常,高月球等[6]从肾加以论治自身免疫性肝炎,薛冰洁等[7]以从肾论治角度对胚胎移植的成败因素加以分析并总结经验。
陈士铎(以下简称“陈氏”),号大雅堂主人,明末清初时期著名的从肾论治医学大家。陈氏性好游善学又访师交友甚广,故其文思立论多有新奇,辨治有据而方药常随证化裁,形成具有典型的陈氏从肾论治用药风格[8]。陈氏著作《石室秘录》对于从肾论治具体方法与用药阐述颇为详尽[9]。故通过对本书的研究,总结陈氏从肾论治的宝贵辨治经验,以期为临床施治与方药研发提供必要的思路参考。
1 辨证特征
陈氏从肾辨证,注重从命门水火学说加以阐发肾水(真水)的重要性,并关注肾与异常水液(邪水)的联系。此外,陈氏还善于从肾与各脏腑间生克关系加以辨治。
1.1 辨真水与邪水
1.1.1 命门真水 真水,又被陈氏称为命门真水(肾水)。肾者主藏精,为人体封藏之本,其所含藏的先天之精,肾阴与肾阳,切合于历代大多数医家对于命门功能的见解[10]。如《灵枢·根结》最早记载:“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11]。李梃《医学入门·脏腑赋》中言命门“以藏真精,男女阴阳攸分,相君火以系元气,疾病生死是赖”[12]。张介宾《景岳全书·传忠录》云:“命门为元气之根,为水火之宅。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13]陈氏在《石室秘录》中在总结前人对于命门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主张命门与肾同为人体根本,其中寓含的肾阴即为命门真水(或言肾水、命门之水),肾阳则称为命门真火(即肾火或先天之火),与真火相对应的火热邪气则称为邪火。陈氏重视从真水(肾水)与真火、邪火的生克关系加以论述。如《石室秘录·论命门》[9]论述为:(1)真火为无形之火,为无形真水所生,并居于真水之中。故维续真火,需滋养真水,使阴中求阳,以益火之源。(2)天下有形之邪火,为真水所克。故清除邪火,亦需注意对于真水的顾护充养,以壮水克火。由此可见,陈氏从真水生真火、克邪火的理论观点,对于水火的生克关系加以界定厘清,更利于临床对于水火理论的运用与发挥。
1.1.2 肾之邪水《素问·逆调论篇》言:“肾者水脏,主津液。”[1]可见肾主水,调节人体水液作用是肾脏发挥其功能的重要体现。而肾主司水液发生异常时,就会使水液无法正常代谢,变生邪水,如《素问·水热穴论篇》云:“肾者……聚水而从其类也,上下溢于皮肤,故为胕肿。”[1]陈氏主张肾中邪水与真水是相互对立关系,应对肾中邪水加以祛除,则肾中真水得以顾护,肾火与心火方得生养。《石室秘录·伤寒门》言:“盖肾之真水,心藉之养,肾之邪水,心得之亡。”[9]《石室秘录·阴治法》云:“肾中之火,必得水而后生。以水非邪水,乃真水也。邪水可以犯心而立死,真水可以救心而长延。”[9]可见陈氏对于真水功用关注的同时,对于邪水伴随所产生致病危害也加以明确认识。故真水与邪水为肾主津液功能正向与反向体现,两者在辨证中需一体看待,再加以明确甄别应对。
1.2 辨脏腑全生全克 陈氏将命门水火思想进一步延伸,提出肾与各脏腑间存在全生全克的关系。其一,脏腑赖肾水以全生[14]。陈氏认为因“无一脏不取资”肾水[9],故肾不单是生肝且对各脏腑都有生养的作用。《石室秘录·论五行》言:“心得肾水,而神明始焕发也;脾得肾水,而精微始化导也……六腑亦无不得肾水,而后可以分布之。此肾之不全生,而无不生也。”[9]故陈氏在辨证各脏腑虚证时,多考虑肾水对于其的滋养影响并加以分析。其二,肾邪之火全克脏腑。肾火虽可温熙五脏六腑,若其不能顺利归藏肾中则易变生邪火,对于各脏腑都会产生克伐的侵害。陈氏将此论述为:肾邪之火无一脏不焚烧危害,如心得肾邪之火而躁烦生;脾得之则津液干;肺得之而喘咳痰;六腑得之而燥渴多见[9]。由此可知,肾邪之火对于各脏腑的正常功能均有明显克制作用,可使脏腑津液流失,继而产生烦渴躁动、咳逆喘嗽等病症。如上所述,陈氏从肾中水火对于各脏腑的全生或全克影响,加以分辨其与各脏腑生理功能与病理病症关系。可见陈氏对于由肾辨理脏腑整体的机能与病变异常的独到见解[15]。
2 治法特色
2.1 联系水火互用,利水存精
2.1.1 水火相须互用,交通心肾 陈氏在论述阴阳时尤为重视肾阴与心阳,常以肾水与心火加以代指,且认为两者相须为用[16]。如《石室秘录·脏治法》云:“肾,水脏也;心,火脏也。视心肾二经为仇敌,似乎不宜牵连而一治之。不知心肾相克,其实相须。无心之火,则成死灰,无肾之水,则成冰炭,心必得肾水以滋养,肾必得心火而温暖。”[9]陈氏认为对于肾水的顾护是水火相须为用的重点。如《石室秘录·假治法》言:“上焦之热,直至肾宫,肾宫不热,则上焦清凉,火自归舍,又何患喘与痰作祟哉。”[9]故陈氏在临证中善用熟地黄、山茱萸补肾水以补心火。如《石室秘录·抑治法》云:“不补肾宫之水则肾宫匮乏,水归而房舍空虚,难以存活,仍然上泛,故必用补水以补火也。”[9]陈氏拟方多用纯补肾水的熟地黄、山茱萸为配伍,佐以有“引下之绝品”的牛膝为使药,沟通心肾水火,可令肾水有心火的温熙,心火又有肾水的濡养,使水火相交以发挥两者相须互用的功能。
陈氏重视交通心肾并主张“心肾不交,阴阳俱耗”则易外感邪气或加情志忧愁抑郁,乃成大毒以致病。如《石室秘录·偏治法》云:“阴寒直入肾宫,则必挟肾水上犯心君之火。君弱臣强,犯上自所不免。若不用大热之药,急救心君,则危亡顷刻。”[9]陈氏治疗心肾水火不交为病时,善以肉桂温阳御水,莲子清热等,以达御水救心,温肾散寒之效。如《石室秘录·本治法》中用肉桂补火以交通心肾,使“心气下行,君火相得,自然上下同心,君臣合德矣”[9]。陈氏在《石室秘录·闭治法》中言:“莲肉尤能清心……使心肾相交,为关玉门之圣药。”[9]由此可见,心肾同治、水火相交乃陈氏治法的重要特色。
2.1.2 利水存精 陈氏认为水湿类病理产物是肾精损耗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利水祛湿可以更好地闭存肾精并促使疾病的转归。如陈氏在《石室秘录·闭治法》中言:“车前利小便而不走气,利其水则必存其精。”[9]《本草新编·车前子》载其在临证中配伍诸药(如配伍熟地黄补精血,配伍肉桂温阳通气等)可起到“用通于闭中,用泻于补之内”达到“水窍开,而精窍闭,自然精神健旺”[17]。此外,肾精的充养又可促进人体水湿的排出。陈氏认为水湿所致的病症乃阴精不足,而阴邪又乘虚犯之导致的。如在论治老人体虚水湿病症时,陈氏常用六味丸补益肾水,以健脾胃之气,去肾中邪水[9]。由上可知,水湿得利,可助肾精固存;肾精得充养,则水湿类病理产物易被祛除。利水与存精是对于肾主水与藏精功能的重要体现,两者相互促进并共同维系着肾脏生理机能的常态运行[18]。
2.2 胃肾相关为用,从肾专治
2.2.1 胃为肾之关,胃肾相关为用“肾为胃之关”为《素问·水热穴论篇》首先提出的观点,但陈氏在总结前人经验与自身临床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胃为肾之关”更切合临证实际[19]。陈氏持此观点的理由有:(1)肾阴肾阳需赖胃以补养。肾与胃为人体先后天之本的关系,后天有濡养先天的作用。人体由口腔摄入饮食,通过的胃腐熟消糜后,再经各脏腑协作方能最终化生精微并供给于肾脏,充养贮藏为肾阴肾阳[20]。如陈氏在《辨证录·虚损门》论述虚损病时强调:“胃为肾之关门,胃伤则关门必闭,虽有补精之药,安能直入肾宫,是补肾必须补胃也。”[21]明代张介宾在论述玉女煎时也认为阳明胃热气火有余,热邪耗伤胃阴也会进一步致使肾中阴精不足,当先清胃热,再滋肾阴以达胃关得闭,肾阴得补,诸症得愈。可见胃腑功能的正常与否会为影响肾脏得到充养的重要因素。(2)胃为肾中邪气出路。如《辨证录之遍身骨痛门》言:“风湿入于经络则易去,风湿入于骨髓则难祛,以骨髓属肾,肾可补而不可泻,祛风湿则伤肾……虽肾不可泻,而胃与大肠未尝不可泻也,泻胃与大肠之风湿,而肾之风湿自去。”[21]陈氏在临证治疗肾经腰痛时,认为白术健脾胃,可使水湿邪气不留存而免于侵犯肾经,故最利腰脐疼痛病症。如《石室秘录·顺医法》载陈氏在治疗气虚湿着肾中,善用白术利胃且能祛湿以护肾的功效,使大小便得脾胃之气而能合,肾中邪气得以随二便排出[9]。由此可见,胃为肾中邪气的排出的重要路径,是维持肾脏功能正常运行的关键。综上可知,“胃为肾之关”是以肾脏补养以胃的饮食摄入转化为重要来源,又以胃为肾中邪气出路的方式加以实现胃腑对肾脏的调控作用。胃肾间存在紧密的联系,需相互关联为临床辨证运用。
2.2.2 从肾专治 从肾专治,在《石室秘录·专治法》中论述为“专治一脏,单刀直入之谓也”[9]。在陈氏的临证治疗中体现有二:(1)寒中阴经,治肾当专直。人病直中阴经寒症,此病势侵袭如奔马般峻猛,出现“舌黑眼闭,下身尽黑,上身尽青,大便出,小便自遗”[9]等症。倘若多脏用药则药力分散则难以遏止病邪进一步入里,不如“只用一二大将,斩关直进”[9],从肾施治来得奏效迅捷。陈氏在《石室秘录·霸治法》中论述此法为寒邪直入肾宫,死亡倾刻,不可用王道多方缓治,必由肾单刀直入,推荡逐除邪气,方能转危急为安然。(2)纯补肾阴,消弭虚火。陈氏在《石室秘录·阴治法》中提出:“用纯阴之品,一直充进肾宫,滋其匮乏,则倦怠之形,不上焰于口舌皮毛之际……自然阴长阳消,不治阳而自安也。”[9]陈氏纯补肾阴,可以视为其对肾阴全生各脏腑,肾中邪火全克各脏腑理论的重要运用。如陈氏认为脐与齿俱是肾经循行所过的部位,而脐与齿出血皆是肾火外越的表现。其多用六味地黄汤并酌加有专能止窍之漏、补肾益骨功效的骨碎补,滋肾水以使虚火自息[22]。
3 方药运用
3.1 君药重用,长治久服 陈氏探讨的从肾论治病症多属虚劳内伤,成非一日,则治亦非一日可以取效。故需对于治疗主症的君药加以重剂量运用,以久服汤药丸饵渐达病愈。陈氏又将此方药总结为王治法,即以王道中正平和治之。君药重用久服,药力与日渐增,看似平常,用之有治本守正的妙处。如全生至宝丹中以山药为君药,用量达两斤,其余用药有“芡实一斤,薏苡仁一斤,黑芝麻八两”等;《石室秘录·完治法》[9]中用黄芪半斤为君药,配合“杜仲一两,防风五钱,茯苓五钱”等加入黄酒共煮温服以治疗腰痛足痛;治疗阴症痈疽的阴阳至圣丹中,金银花一斤为君药,辅药有“生地黄八两,当归三两,玄参五两,麦冬三两”;利腰丹中用“白术二两,杜仲一两”,酒煎服10剂等。其余方剂还有:定风去晕丹、养阳汤、断梦止遗丹、敛汗汤、补气消痰饮、黑鬓仙丹、安火至圣汤等[9]。以上诸方中君药的用量都为最大且明显超过于其他药物,体现君药在其中对于功效与作用的主导性。且臣药、佐药与使药的药味虽多,药量却依次递减与君药形成一定配伍比例,可见陈氏处方以药量明确裁定君臣佐使,协调药物的整体作用,值得临床加以借鉴。此外,上述方剂用药剂量整体偏重,又以久服固本,持续见效为特点。可见陈氏从肾论治病症不拘泥治疗常病所倡导的“一剂知,二剂已”的快速奏效,而以切合患者主症酌君药重用,久服以利长远治疗[23]。
3.2 善用对药“偶治” 陈氏称二味药(对药)兼而治之为“偶治”法[24]。偶治法既可以弥补单一药物性味药功效的不足,且可助发挥两味药的各自优势,取长补短。陈氏以阐释对药偶治的方式将从肾论治理论加以发挥,主要体现在命门水火学说和脏腑生克变化。陈氏从肾论治常用的对药偶治有人参-附子、玄参-麦冬、熟地黄-巴戟天、山药-芡实等。陈氏用补气药人参、温里药附子二味治疗中寒之证,阴寒迫阳气外越。《石室秘录·本治法》言,人参、附子二味相合则无经不入,补真火以“救心肾,而各脏亦无不救之”[9]。用人参以挽真火于绝续之顷刻,附子可直入心肾驱寒,两药偶治共奏补火救逆、益心温肾以祛寒之效[25]。人参-附子药对涉及到方剂如参术附桂汤、逐寒回阳汤、祛寒至圣丹、消冰散、救心荡寒汤等。此外,陈氏还常用清热药玄参与补阴药麦冬合用,退虚邪火热,补肾中真水以滋肺阴,可用治如斑疹清虚热以消斑,如方剂双补至神丹、清肃至凉汤、安火至圣汤、消阴坚骨汤等;熟地黄配巴戟天以补肾益精,滋真水养真火,常用于阳痿、梦遗与早泄类男科病,可见于方剂益心止遗丸、引火升阴汤;补阴药山药配伍收涩药芡实在治疗虚劳、不孕不育、阴萎诸病症中,以两个不同药类间的相互配伍以增大药物间差异性,拓宽功效范围,最终共同达到补肾健脾、祛湿固精的作用,涉及方剂有心肾同补丹、遗忘双治丹[26]。
4 病案举例
一患者为双蛾病,喉门肿痛,痰如锯不绝,茶水一滴都不能下咽,然而疼痛虽甚,至早上则症状有所减轻。病者“喉虽肿,舌不燥,痰虽多,却不黄而成块,此乃假热之症也。若以寒凉之药急救之,下喉非不暂快,少顷而热转甚。人以为凉药之少也,再加寒凉之品,服之更甚”[9]。陈氏以少商穴刺络放血以急泻热邪。方用消火神丹:“附子一钱、熟地黄一两、山茱萸四钱、麦冬三钱、五味子三钱、牛膝三钱、茯苓五钱”[9]。水煎服,药下喉则其火势热症立时消散,声音恢复响亮。
按语:患者症见喉咙肿痛、痰多,甚至茶水不下,归属于中医“喉痹”范畴。此病属于临床常见病种,内感外伤皆可引起,《素问·阴阳别论篇》云:“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1]现代医家普遍认为喉痹是由于外邪来犯,侵袭喉门,或脏腑受损,咽喉失养,或虚火上炎所致[27]。陈氏认为此患者因肾水枯竭,心火失肾水润养,正虚则邪热相火上越,蒸灼津液,凝练成痰,致使喉门窄小,郁而肿痛。方中以附子补心温阳[28],以安君火。熟地黄、麦冬以补肾滋阴,配伍收涩山萸肉与五味子,补敛相合,壮肾水以消邪热。再佐以牛膝引火下行,活血通络消肿,茯苓益气利水宁心,既可防补益滋腻敛邪,又可交通心肾。诸药共用使肾水得充养,心火有肾水之润,又有引导交通之使,心肾自安然而虚火无上泛,故喉肿热势自消,声音恢复响亮。
5 结 语
陈氏在继承前人经验与自身临证体会的基础上,对从肾论治的相应辨证与治法用药加以灵活变通运用[29]。形成陈氏所著《石室秘录》中从肾辨证疾病,主张辨命门真水与肾之邪水,并将命门水火思想进一步延伸,提出肾与各脏腑间存在全生全克的关系。治法包含:水火相须互用,交通心肾,利水存精;胃为肾之关用,从肾专治。方药运用以君药重用且久服,善用对药“偶治”为特点,涉及方剂有全生至宝丹、阴阳至圣丹、利腰丹、养阳汤等,常用药对有人参-附子、玄参-麦冬、熟地黄-巴戟天、山药-芡实等,值得临床加以借鉴运用。通过对本书的研究,总结陈氏从肾论治的宝贵经验,以期为临床施治与方药研发提供必要的思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