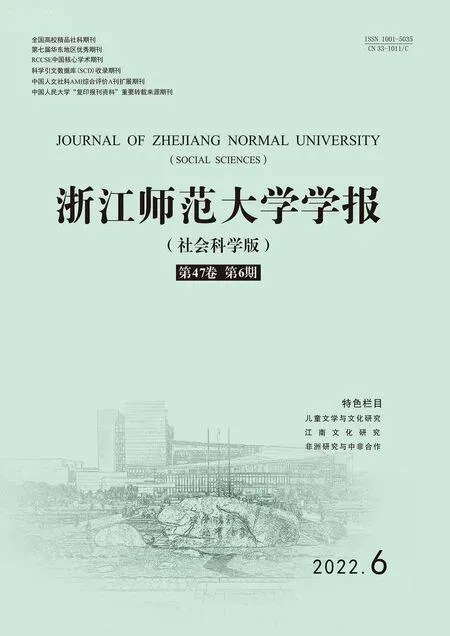敦煌蒙书《武王家教》中唐代童蒙“形象”教育解析
——以“八贱”为中心
金滢坤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引 言
笔者新近围绕敦煌文献中发现的《武王家教》,①就唐代家教中存在的“七十一条”子弟常犯的不良、不当行为举止,即“教条”及其“益己”之教和“明哲”之教等问题,发表系列文章《敦煌蒙书中的儿童警示教育——以〈武王家教〉“六不祥”为中心》《敦煌蒙书〈武王家教〉中的唐代富贵贫贱观念解析——以“十恶”为中心》《唐代〈武王家教〉中的儿童“自知”教育解析——以“三痴”为中心》等,②对相关问题进行解析,探讨《武王家教》在中国蒙书史、家教史和家训史上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典型性,对现代家教和童蒙教育均具有启发意义。本文将围绕《武王家教》中有关个人“形象”的八种贱行,分为三类,结合敦煌蒙书与古代传统文化,对其相关的深层文化含义及其与童蒙教育的关系进行深度探讨,并就唐代家教中的“形象”教育展开论述。
《武王家教》中太公认为影响“人命长短不一”的原因之八为“八贱”:“行步匆匆为一贱,跷脚立尿为二贱,坐不端正为三贱,你我他人为四贱,唾涕污地为五贱,着杂色衣裳为六贱,不自修饰为七贱,坐不择地为八贱。”这里的“贱”,大致可以理解为“贱行”和“作贱”之义。“贱行”之义有二:其一,在社会中被看低、遭人鄙视的职业和事。如《史记·货殖列传》云:“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1]卷129,328《礼记·坊记》曰:“民犹贵禄而贱行。”郑玄注:“行,犹事也;言务得其禄不务其事。”[2]卷50,1292其二,卑劣、低下、无德的行为。宋卫湜《礼记集说》云:“无德者也谓之贱,则无位者也。”[3]结合“八贱”之诸种行为,此“贱”盖指轻薄、低贱之意。如伯二五一五号《辩才家教·善恶章第十二》载:“居家何以贱?兄弟妯娌相谗□。居家何以贵?兄弟妯娌常欢喜。”可见唐代世人眼中的“贱”行,还包括谗说之言等,即招人生厌、轻视的行为。
与“八贱”之名相类的有“六贱”。赵蕤《长短经·察相》云:“夫人有六贱:头小身大,为一贱;目无光泽,为二贱;举动不便,为三贱;鼻不成就,准向前低,为四贱;脚长腰短,为五贱;文策不成、唇细横长,为六贱,此贵贼乎骨骼者也。”[4]赵蕤所言“六贱”为人的天生缺陷,属于六种“贱”相,与本篇“八贱”所指有所不同。“八贱”指世人常犯的不当、不良等招人生厌的八种行为举止,取世人不听劝教,自我作践之义。《百行章·凡行章第五十二》所载“人多敦者皆轻,非理而谈,贱亦不听,容止无则”的问题,大致与“八贱”所指的不听劝教、明知贱行而为之相类,都属于自我作践、不顾“形象”的行为。下面我们分别对“八贱”的文化内涵与观念进行考释。
一、“行步匆匆”的文化内涵与观念考释
“行步匆匆”看似无伤大雅,却被列为“八贱”之首,其原因值得探究。敦煌变文《八相变》云:“天帝释知太子游观四门,各化一身……才出东门之外,陌上忽逢一人,行步怱怱,极甚忙切。太子见已,遂遣车匿迎前问之:‘公是何人,行步怱速?’”[5]卷4,501显然,“行步怱怱”与“行步匆匆”义同。笔者在明清小说中找到近义词“行色匆匆”“赶路匆忙”等。③三者看似都与匆匆走路、赶路有很大关系,多与社会底层人民走路形象有关,但仍不足以解释其何以为“贱”行的缘由。显然,“行步匆匆”不仅仅是形容走路匆匆的样子,更是指代隐藏其后的举手投足之间的气质与行为习惯以及日常起居的行步状态。
中国古代有日者通过观察士人的起居行步来推算、预知其名相的传统。《史记·日者列传》记载:有日者褚先生通过观察唐代士大夫“起居行步,坐起自动”,[1]卷127,322判断其大体性格,以卜筮其前途,在当时很有名。这说明个人起居行步等日常习惯养成之后,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了其性格、志向乃至命运。如宋代圆极禅师尝赞“十智同真”曰:“生铁面皮难凑泊,等闲举步动乾坤。戏拈十智同真话,不负黄龙嫡骨孙。”[6]言从其举步之间可见气宇轩昂,动乾坤,是帝王之相。因此,“行步匆匆”看似小事,实则不然,它关乎个人“形象”,与个人的品格和志向有很大关系。
“行步匆匆”的行为在中国古代相书里被视为社会底层的卑贱之行。敦煌《相书》云:“行步第廿六:凡人如龙行,三公。虎行,将帅。似鹅行,大夫。似龟行,三公。似小儿行,贵。似雀行,下贱。似蛇行,女妨夫。似蟹行,妨夫,贱。似鹊行,为人贱。”[7]从敦煌《相书》来看,以“似鹅行,大夫;似龟行,三公”,说明唐代社会行步迟缓为贵。雀行、鹊行的特征是快捷、迅速,故而“下贱”——这大概是“行步匆匆”为“贱”相的原因所在——这是基于民间相书和文化传统的认知所致。
中国古代对君子的行步有明确规定。《礼记·玉藻》记载,古代君子出行须中规中矩。[2]卷30,820西汉刘向《说苑·修文》载,古代有“五事”,其首事为“貌”,核心是男女在重要场合须“行步中矩,折旋中规”。[8]故《后汉书》讲到东汉名士陈伯敬“行必矩步,坐必端膝”,[9]以此来称赞其有君子之行。隋代何妥《定乐舞表》云:在皇帝入庙祭祀等重要场合,奏乐要合皇帝、众臣等“行步之节”。[10]卷70,1713-1714
中国古代朝堂上须缓步而行。萧梁孙柔之《瑞应图》曰:“鸾鸟凤皇之佐,鸣中五音,肃肃雍雍,嘉则鸣舞,人君行步有容,进退有度,祭祠有礼,亲疎有序。”[11]以鸾鸟肃雍鸣舞,引人君“行步有容,进退有度”的气度,正好可以说明朝堂之上要尊卑有别、井然有序,以彰显庄重、庄严氛围。《唐语林·补遗》载:“勤政楼前,尚容缓步;开封桥上,不许徐行。”[12]卷6,598明确点出唐代勤政楼等朝堂重要场合,出入需要“缓步”,这体现了官场的行步文化。如宋仁宗因病久不视朝,忽然通知上朝,召见群臣,百官纷纷速行觐见,唯有宰相吕夷简“缓步”而行,仁宗为此专门表扬其得辅臣之体,[13]卷2,16遇事“缓步”持重。而“速行觐见”“行步匆匆”正好与其相反,容易导致混乱、紧张,不庄重、不威严。
“缓步阔视”是世族之家的行步规范。如《列子·黄帝第二》载:“子华之门徒皆世族也,缟衣乘轩,缓步阔视。”[14]“缓步阔视”用来形容世族子弟缓步行走、从容不迫的样子。又《隋书·刘炫传》云:“玩文史以怡神,阅鱼鸟以散虑,观省野物,登临园沼,缓步代车,无事为贵。”[10]卷75,1722-1723以“缓步代车”形容游园从容不迫的样子。不过,唐代武官若是“行步迟缓”,则被视为有“失本体”之举。[15]《杂纂》卷上,3在盛唐以降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下,“行步匆匆”代表武官之行步特征,自然为士大夫所不齿,正反映了开元以后武官没落、文官崛起的时代风气。
在生活中行走匆匆,或被视为落魄之相、穷人之相。《伍子胥变文》云:“女子泊沙(拍纱)于水,举头忽见一人。行步獐狂,精神恍惚,面带饥色,腰剑而行,知是子胥。”[5]卷1,3行步獐狂,谓行步惊慌失措之状,是落魄之相。又宋赵师侠《促拍满路花》云:“任乌飞兔走匆匆,世事亦何穷。”[16]故“行步匆匆”就成了士人行走的大忌。
在古人看来,行步不守规矩,行步不端,必招祸患。如《晋书·五行志上》云:“魏尚书邓扬行步驰纵,筋不束体,坐起倾倚,若无手足,此貌之不恭也……后卒诛也。”[17]卷27,820又北魏天赐六年(409),道武帝性情怪异,“朝臣至前”,“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18]卷2,44
与“行步匆匆”相对的是“投足”须慎行,在唐代可以引申为士子对求谒、投刺对象的选择。开元以后,随着科场行卷之风的流行,举人持行卷投谒权贵、名公之门,以期获得延誉机会,也就是士人常说的“投足”。中晚唐士人常以“投足皆安,终身不忒”[19]的观念为指导,深谙“可疑之地,投足莫践”[20]卷234,2364的奥妙之处。韩液称赞公孙宏开东阁,以“美其投足之始,名以才着高因下起”“多士拭目,群英倾耳”[20]卷407,4166比喻举子行卷获得权要、文宗美誉和赏识的重要性。在此情形之下,举子若“行步匆匆”,自然有损个人形象,不利于“投足”、求谒,事关科名、仕途。
中国古代对士人行步礼仪的规范教育十分重视。《论语·乡党》记载,孔子“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21]卷19,645-648孔子以身作则,为士人的行步礼节和事项作了示范。据《三国志·魏书》注引《先贤行状》,赞美王烈办学育人有方,其门人出入不得“行步有异”,[22]卷11,355可见他对门人的“行步”规范教示之严格。其实,中古在童蒙教育方面和家教类蒙书中也很重视“行步”方面的教育。如斯五四七一号《千字文》以“矩步引领,俯仰廊庙”来教示蒙童的行步规范。斯一九二号《百行章·缓行章第廿八》亦云:“行步邕容,无劳急速。言辞理定,务在敦明。刻罪惟愆,皆须审究。君王问答,诣实而陈。”可见“行步邕容”为世家大族、高官显位之行,故唐初宰相杜正伦训诫子弟切莫行步“急速”。又伯二五六四号《太公家教》云:“行则缓步,言必细语。”
综上所论,“行则缓步”实为朝堂皇帝、将相之规范,既是世家大族的行步规范,也是世人教示蒙童和子弟的准则。与之相对的“行步匆匆”,则成为贫贱、落魄和劳苦的“形象”,是“贱”相的典型写照,故被列为“八贱”之首。
二、“跷脚立尿”的文化内涵与观念考释
“跷脚立尿”属于中古时期的一种民间生活禁忌,目前尚未查到“跷脚立尿”连用的记载,但与“跷脚”“立尿”相关的资料比较丰富,多与中古以来佛教、道教的禁忌有关。随着唐代儒释道三教融合,这一禁忌也成为世人日常生活的忌讳。
跷脚,或作跷足、翘脚,指翘起一脚的不雅行为,有损个人“形象”。唐代冯翊《桂苑丛谈·方竹柱杖》记载,甘露寺有高僧在床上跷足而眠,甚是自在,对前来拜访的前宰相、浙西观察使朱崖毫不理会,颇为傲慢,朱崖对此很生气,以“书空跷足睡,路险侧身行”的诗句讽喻相讥。不难看出,“跷足”含有贬义。又宋人罗泌《路史·前纪八》云:“跷脚弄目,筋斗祼逐夫,又安知名教之乐邪?当此之时而乐几祸矣!”[23]可见“跷脚弄目”是低贱之行,不是名教子弟之举。
跷脚的行为在中古时期逐渐变为贬义,与佛家文化传入中国有很大关系。据东晋《摩诃僧祇律·明众学法之余》记载,为翘脚者说法,有辱佛法,会为世人所讥笑,故佛不允许为诸翘脚者说法。所谓“翘脚”,就是“髀着髀上膝着膝上,膊着胫上脚着脚趺上”;跷腿可以分为躺着、坐着两种姿势。[24]卷22,411无论跷脚坐还是翘脚躺,都是很不礼貌、缺乏教养的行为,也是轻浮、粗俗的表现。后凉神鼎二年(402),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载:“有外道辈,或常翘足求道、或常立、或荷足……如是狂狷,心没邪海,形不安隐;以是故,佛教弟子结加趺直身坐。”[25]批评外道“常翘足求道、或常立、或荷足”是狂狷无礼、傲慢无知之举,并要求佛教弟子结加趺直身而坐。
“立尿”为站着小便之义,即“立小便”。《说文·尾部》云:“尿,人小便也。”[26]唐初著名医药学家、道士孙思邈《保生铭》中谈论有关大小便禁忌,如“饱则立小便”,而忌“坐漩溺”,更要注意“向北大小便,一生昏幂幂”之禁忌,[20]卷158,1621-1622足见道教禁忌影响明显。晚唐李商隐将“对日月大小便、散发”列为人生不祥之事,[15]《杂纂》卷上,9也是世俗文化受道家影响的例证。
道教文化有关大小便的禁忌很多。中古道教《老君说一百八十戒》第六十六戒曰:“不得立小便。”[27]卷39,853显然,“立尿”禁忌受到了道教文化影响。道教还禁忌大小便向日月和西、北二方。如《养生传》曰:“永久之忌,勿向西、北二方大小便,露赤也。”[27]卷36,797又《仙道忌十败》云:“一勿好淫……十勿向北大小便,仰视三光。”[27]卷32,739又《杂戒忌禳灾祈善》云大小便朝向西、北、日、月和星辰为“五逆”。[27]卷32,723-724道家《养身经》亦云:“小便向西,一逆;向北,二逆;向日,三逆;向月,四逆;大便仰头,视天日月星辰,五逆。”[28]可见道教对“大小便”禁忌之繁琐。在唐代全面崇奉道教的情况下,有关“立尿”的影响,应该与道教“大小便”禁忌文化有很大关系。
中古时期佛教经典中也有很多有关“立尿”的戒律与禁忌。据北魏慧觉等译《贤愚经》载,一比丘尼当众“裸形立溺”,让全国女性蒙羞,[29]此乃后来佛祖禁止立溺的主要原因。唐玄奘译《大乘广百论释论·破边执品第六》有“边鄙人立飡立溺。便痢不洗”[30]的讨论,显然“立溺”为边鄙人的不良习气。另一种说法是,比丘立大小便,为世人所讥,故佛祖禁立大小便。东晋《摩诃僧祇律·明众学法之余》记载佛陀训诫诸比丘犹如牛驴等牲畜一般站立大小便的行为,不知遮丑,被世人所讥笑,是败坏道法的行为,故要求比丘“不得立大小便”。[24]卷22,412因此,佛教将禁止比丘立大小便纳入戒律中。如后秦竺佛念等译《四分律·百众学法三》亦禁止比丘尼不得立大小便——只有病患在身不能蹲厕者除外——违者犯应忏突吉罗罪。[31]值得注意的是,唐道宣撰《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记》卷四《律》,明确将“立大小便”纳入《四分律》第五十一戒。其下注:“立大小便如牛马猪羊骆驼,比丘举过,佛因诃制戒。”可见立尿亦是佛教禁忌。
综上所述,“跷脚立尿”应该是民间俗语。随着中古时期佛教戒律中有关不许为“翘脚人”说法等观念的传入,世俗社会受其影响,也视翘脚、跷足为不雅、粗俗之举。“立尿”,即“立小便”,该词最早见于孙思邈《保生铭》中的“立小便”,其说应该受道家有关“大小便”之“五逆”禁忌观念的影响,同时也受佛教禁止比丘“裸形立溺”“立大小便”等戒律的影响。从上述对“跷脚”“立尿”的考释来看,二者均为不雅、粗俗的行为举止,若两者叠加,则更容易招人生厌,被人轻贱,故被列为“八贱”之二。
三、“坐不端正”的文化内涵与观念考释
“坐不端正”主要指个人落座不合礼仪而招人厌的不雅、不当行为。中国古代礼仪制度基本上都是在周礼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有关就座的礼仪制度也可从《仪礼》《礼记》中找到相关依据。《仪礼·士相见礼》载:“若父则游目,毋上于面,毋下于带。若不言,立则视足,坐则视膝。”[32]可见君子侍父坐,要正坐视膝,以保持端正。《礼记·玉藻》云:“君子之容舒迟……足容重,手容恭……立容德,色容庄,坐如尸,燕居告温温。”[2]卷30,834士人坐姿不仅要端正,而且仪容还要恭敬端庄,并对手、目、口、声、头、气、立、色等诸多方面都有具体要求。在坐姿端正、仪容端庄的基础上,还要有恭敬之心。《礼记·儒行》云:“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2]卷57,1400如孔子平日若是座席摆放方位不正,就不会就座。[21]卷19,636又西汉韩婴《韩诗外传》载孟母自悔言曰:“吾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适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33]卷9,306其中的道理也是一样的。胎教从妊娠时就开始了,母亲应该注意座席摆放端正等细微的行为举止,这样才能从点滴之间培养幼童的正确行为习惯。
坐姿、坐相也是公众场合塑造个人信誉、品行的具体方式。如开元中,玄宗早朝,“见张九龄风仪秀整,有异于众,谓左右曰:‘朕每见张九龄,精神顿生’”。[12]卷4,347宴会场合不仅是交际场所,也是考选贤能和追逐名利的场所,坐姿、坐相是一个重要的考察要素。唐代韩晋公滉久镇浙西节度使,在选任一幕僚时,“燕而观之,毕席端坐,不旁视,不与比坐交言。后数日,署以随军,令监库门。使人视之,每早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无敢滥出入者”。[13]卷4,347-348在唐代,若是百官在朝堂之上起坐失仪失序,轻则罚俸,重则追责。[34]卷14,423
“坐不端正”实际上违背了中国古代“形端表正”的价值观念。管子在总结世间万物“形势”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得出“形端势直”“状危势倾”的规律,从而告诉世人形端、状危等点滴细节会影响将来的发展趋势,所以若能从源头做好“形端”,其“势必直”。[35]董仲舒也认为“影正则生正进”,身正与影正即身正影直是相辅相成的。[36]《金楼子·立言篇》曰:“身曲影直者,未之闻也。”[37]说明身曲、状危不可能影直。唐代马总也主张:“本正则末茂,源净则流清。内修则外理,行端则影长。”[38]并认为人品和格局的培养应该从最基本的言行起坐着手,“行端则影长”。
唐代有关“行端影长”“形端表正”的观念在敦煌蒙书中很常见。《百行章·凡行章第五十二》云:“君子不重则不威,唯须自严正。”在杜正伦看来,君子的持重威严来自“严正”,由“心正”到“行正”,进而形成“严正”。据《辩才家教·十劝章》云:“但以心中行正直,非理谁人何所及?”辩才大师是讲心中正直,才能行得正直。伯二六一二号《文词教林》卷上并序对“正心”感悟曰:“若正得意,则祸患不入其心。世人悉[知]补屋,以却风雨;不知正心,以除祸患,何其愚惑者矣!”教示子弟“心正”则可以避祸患,好比人修补房屋,就是为了遮蔽风雨,防患于未然。
基于唐人对“心正”“行直”的普遍认知,“行直”主要表现为“影直形端”。如伯二五五七号+伯三六二一号+伯二五九八号《新集文词九经抄》引太公曰:“影直形端,心坚道正。”(第三九一条)唐代敦煌蒙书中关于“形端影正”的说教,最透彻的是《百行章·政行章》。在该章中,杜正伦认为,“形端影正,身曲影斜”,因此,立身之道,关键在正身,而正身需要从个人的起坐开始,要做到“形端影正”。其实,杜正伦的看法,应该受《千字文》所云“德建名立,形端表正”的影响。据敦煌本斯五四七一号《千字文注》引《杂语》曰:“夫形正者影必端,表斜者影必曲。”“形端表正”,含义十分广泛,“坐席端正”正是其中之一,旨在教育子弟,修身须先树立威信、形象,这样才能达到“形端影正”的目的,以“德建名立”。斯五九六一号《新合六字千文》将“形端表正”改作“形端无移表正”。
显然,坐必端正已成为唐代世人居家生活、外出应对、处事、仕宦,乃至礼佛等诸多场合都必须具备的礼仪,也是个人形象的具体体现。人若“坐不端庄,则昏惰之气必生”,[15]《居业录》卷2,18自然被家庭、社会,乃至佛家所不能接受,难以获得认可和尊重,并被视为贱行。这一观念甚至影响到了中国古代胎教,认为孩子出生愚蠢,是孕妇怀胎时“行坐不端,则浊秽气重”。[39]要是子弟“坐不端正”,则意味着心不正、身不正、影不直,正应了“形端影正,身曲影斜”之语,违反了《周礼》所言“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的观念,也就难以在社会上立身、正行,获得认可,会被归入低俗、不入流的贱类。因此,唐代童蒙教育和家教对子弟的起坐、坐席教育十分重视,坐必端正是塑造子弟个人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蒙书中也保留了较为丰富的相关资料。
四、“你我他人”的文化内涵与观念考释
“你我他人”为“八贱”之四,与其前后的“行步匆匆、跷脚立尿、坐不端正、唾涕污地、着杂色衣裳、不自修饰、坐不择地”等七“贱”看似完全不相干,为三个人称代词与“人”字组成的一个俗语,其意义颇为费解。“你我他”若不与“人”字连用,可分别表示三个人称代词。如《绿牡丹·第三十回天鹏法堂闹问官》:“谅二娘亦是青年,岂有不爱风月?你可硬行强奸,倘若相从,你我他皆一道之人,省得提心吊胆,且二娘手中素有蓄积,弄他几两你用用也好。”[40]考虑到《武王家教》中的“八贱”均为个人在生活起居、应对中的行为举止和穿着等方面的不当、不雅乃至招人厌的粗俗行为,则“你我他人”也不能简单地从字面含义解释,须从中古俗语、谚语着手考虑。若是将“你我他人”诠释为以你我为他、不分你我他,引申为与人相处中遇事不分你我的招人厌的不当行为,就可与其他七“贱”之含义相符合了。
考稽史籍,在唐宋以前,均未能找到直接的史料支持,但元代赵文《青山集》中有“而我他人”四字与本篇“你我他人”文义甚似,可以解释其为“八贱”的含义所在。据赵文《曾一山修屋序》载:
吾友曾一山辟地上城,上城诸公推屋以居之。一山居上城,警则去,安则复……余谓一山:“此岂可以责诸公哉?是亦一山有罪焉。古人处客馆一日必葺,去之日如始至。君家一唯翁之居武城也,而一唯翁。”室曰:“我室墙。”屋曰:“我墙屋,而一唯翁。”室曰:“夫岂不安其分,而我他人之物者,其在我也。”推之以及人,其在人也,视之如我,忠恕之学,正如此尔。今君居敝甚,君诚安之,独不为恶少之骑屋虑乎?夫诸公惟未之知尔,君何不告于诸公修我墙屋?诸公或相工或共费,谁为君爱力,又岂惟诸公将自诸公之外,凡为一山故人与?不识一山而知一山者,谁独无武城大夫之心?而君乃若是乎,爱于一言也。[41]
赵文以拟人口气,用“室曰:‘我室墙。’屋曰:‘我墙屋。’”来表述室墙屋各自突出自我的心态,但不管如何强调自我,也只是“一唯翁”而已。室又云:“夫岂不安其分,而我他人之物者,其在我也。”室墙和墙屋都只是这间房子的一部分,各自强调自我的做法就是“而我他人之物”,即你我均为他人之物而不自知,自以为是。“而我他人”与“八贱”之“你我他人”含义相近。
考虑到“八贱”均属居家和在外应对中不识时务、不自知、不自觉而招人厌的行为举止,其实就可以结合其他七“贱”,对比出“你我他人”的含义。伯二七二一号《杂抄》中“世上略有十种札窒之事”条枚举“见他(人)着新衣,强问他色目”等十种不识时务、自讨没趣、唐突他人而招人厌恶的不良、不当行为举止,盖与“你我他人”有很大相关性,均为不分你我他人界限、拎不清自己、不把自己当外人,未经他人允许擅用他人物品、擅自为人做主、瞎掺和等诸种行为举止。
其实,“你我他人”包含诸种不自知、不自觉,不分彼此的招人生厌行为,与唐代蒙书和家训教育子弟慎莫多事的内容很相似。《武王家教》第三大问云:“慎莫多事,多事被人憎;见事如不见,无言最为能;莫为无益事,莫居无益邻;莫听无益语,莫亲无益人。”与不分“你我他人”的劝教类似。两者视角不同,但所劝教的内容类似,均意在教示子弟未经他人同意,切莫多事、多言、多看、多闻。
五、“唾涕污地”的文化内涵与观念考释
“唾涕污地”即将唾涕掉在地上,弄污地面,属于缺乏教养、粗俗的不当之举,堪称贱行,故入“八贱”。
关于唾涕问题,早在《礼记》中就有相关记载。《礼记·内则》载:“在父母舅姑之所……升降、出入、揖游……不敢唾洟……不有敬事,不敢袒裼。”[2]卷27,734可见,中国古代,妇女在家侍奉父母、公婆时,不能唾洟。这一记载虽然面向妇女,但也为后世的唾涕行为准则提供了依据。
秦汉以降,随着官僚政治不断完善,唾涕也被纳入了朝堂礼仪约束的范畴。如《魏书·毗陵王顺传》云:“太祖好黄老,数召诸王及朝臣,亲为说之,在坐莫不祗肃,顺独寐欠伸,不顾而唾。太祖怒,废之。”[18]卷15,383皇权之下,毗陵王顺公然“不顾而唾”,竟被北魏太祖废除王位。为了避免朝官“不顾而唾”的不雅行为,北魏朝堂、重要会议还出现了专门的“唾壶”,以解不时之需。《魏书·徒何段就六眷传》云:“诸大人集会幽州,皆持唾壶。”[18]卷103,2305又南朝刘宋武帝竟然让侍中大儒孔安国在朝堂为其执掌御唾壶。

中古道教认为唾、涕为体内“六液”之三四。《太清诰》即云唾液是“玉醴金浆”,主张“终日不唾”。[27]卷56,1228又《诗赞辞》认为“仰天而唾”是行恶,反污自身。[27]2133孙思邈传授养生秘诀“每去鼻中毛,常习不唾地”,[20]卷156,1621-1622也把“不唾地”作为世人养生的一个注意事项。
唐代儒释道文化对“唾涕”的认识有着很高的相似性,都将其视为污浊之物。然而,唾涕是人在生病时或不经意间易犯之错,稍不留意就会养成习惯,有损个人形象。因此,唐代童蒙教育和家教都十分重视卫生习惯的培养,告诫子弟切莫“唾涕”。《百行章·饬行章第卅七》云:“人前莫听涕唾,同食勿先漱口。”可见杜正伦认为衣着和唾涕、漱口等个人卫生习惯是需要从小训导的,不能放纵。《太公家教》在训诫子弟时也特别强调:“对食之前,不得唾地,不得漱口。”《杂抄》“十无去就者”中亦告诫子弟,在应对活动中让人十分尴尬的事莫过于“局席不慎涕唾”,足见对唾涕的重视。
六、“杂色衣裳”的文化内涵与观念考释
“杂色”即颜色杂乱,多种颜色混杂不均,花色不一,其色之华彩者为彩衣。“杂色衣裳”在唐代为社会底层所穿,故子弟着杂色衣裳为自降身份、有失体面的行为,有损“形象”,为“八贱”之六。中国古代以“杂色衣裳”为贱观念的形成,不仅与尧舜以来“垂裳而治”的传统有着紧密关系,而且与佛家禁杂色衣裳、古代乐伎杂服、儿童服彩衣的文化亦有一定关系。
(一)与“垂裳而治”传统服制观念的关系
传说黄帝观天上气候五色变化而做衣裳之制,“垂衣裳而天下治”。[44]中国古代君王借用黄帝法天地,以衣裳之辨来治理天下的理论,[45]卷20,865将服制与国家治理联系起来,通过服制来区分人的贵贱、尊卑、等第、社会分工等,以实现治理天下的目的,影响深远。
隋唐时期的服制亦如此。大业元年(605),炀帝始诏,“宪章古制,创造衣冠,自天子逮于胥皂,服章皆有等差”。[10]卷12,262大业六年,隋炀帝“诏从驾涉远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已上,通着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10]卷12,279明确了官服辨贵贱、等级的作用。官服用五色,尚纯色,若五色集于一衣,则乱制,乱则为贱。故伍子胥曰:“食不重味,衣不重采。”[1]卷31,1471唐因隋旧制,“天子宴服,亦名常服,唯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34]卷45,1952显然,隋唐时期,品官之外,吏干可以穿青衣,庶人穿白色衣,屠商穿皂(黑)色衣,士卒穿黄色衣,可以说衣服颜色是用来辨别身份、等级的,不能随意乱穿。
唐代男子弱冠之后,若未获官入仕,按照相关服制规定只能服白衣,故着杂色衣服者,看似与服色无关,实为僭越服制的行为。如唐代赵璘《因话录·宫部》载:唐武宗准备赐宰相杜悰子无逸衣,所司上奏不知衫色,武宗只好以“年小未有官,又难假其服色”为由,先赐“青衣无衫”,[15]《因话录》卷1,5正好可以说明唐代服制对士庶子弟限制相当严格,即便皇帝赐衣,也不可轻易僭越,商贾和百姓均不得穿色样绫罗及紫皂杂色衣服,戴金色带。由于士庶子弟不能随便穿有色衣服,只能穿白色或灰色衣服,故唐代举子在未及第之前,也只能穿白衣,被称为“白衣公卿”“一品白衫”。[46]卷1,4
(二)与佛家禁杂色衣裳的关系
“杂色衣裳”为“贱”行的观念应该还受到了中古佛教禁止杂色衣服观念的影响。北魏南印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载:“近女人坐,着杂色衣,而入他家。若比丘等……能断灭之?”[47]卷59,349可见僧侣着杂色衣,恶念很重,很难断灭。同书卷六一载:僧侣“不着杂色革屣,杂色衣服,若他破戒……”,[47]卷61,361即犯者破戒。又隋代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载耶输陀罗公主云:“舍背我行……又更不着杂色衣服。从今已后,不着杂种诸璎珞具。”[48]僧人也不能使用“衣帔杂色褥等”。[49]佛教还规定“诸比丘尼畜种种杂色衣”犯突吉罗罪。
(三)与乐伎杂服的关系
中古时期乐人、艺伎演奏时多穿彩衣。如北魏孝明帝泛舟天渊池,命宗室诸王陪宴,乐浪王忠“愚而无智,性好衣服,遂着红罗襦,绣作领;碧裤,锦为缘”。孝明帝谓曰:“朝廷衣冠,应有例程,何为着百戏衣?”显然,乐伎才穿花花绿绿的“百戏衣”,孝明帝为此对乐浪王忠的杂色衣服颇为不满,称其为“人之无良”的行为。[18]卷19,452又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鼓》云:“其声坎坎然,其众乐之节奏也。祢衡常衣彩衣击鼓,其妙入神。”[50]由于乐伎地位低,故多穿彩衣;若是士人也穿彩衣,自然不是件体面之事,属于自我作践的行为。此外,唐代鬼神故事中,侍女、仆从也常穿杂色衣服。
(四)与儿童穿彩衣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服制框架下,按照相关服制规定,儿童属于未成年人,通常不能参加官员选拔,应该归入庶民,服白衣。但历代对儿童服饰的要求不是很严,儿童彩衣的情况比较常见。如《孝子传》曰:“老莱子年七十,父母犹在,莱子常服斑襕衣,为婴儿戏。”[51]班襕衣,盖为童装。又伯二六二一号+斯五七七六号《事森·孝友篇》云:“老莱子,楚人也。为人至孝,年七十,不言称老,恐伤其母。衣五彩之服,示为童子,以悦母情。至于母前,为童儿之戏,或服伏或服与母益养,脚趺化作婴儿之啼。”唐代亦然。刘禹锡《元日感怀》诗云:“燎火委虚烬,儿童衒彩衣。异乡无旧识,车马到门稀。”[52]通过描绘唐人在元日升篝火、儿童“衒彩衣”欢度节日的场面,说明儿童过年穿新衣以彩衣为时尚。
老莱子彩衣的典故,在唐代常用来指代省亲。唐代王绩《老莱养亲赞》云:“老莱父母,白首同归。欣欣爱养,慊慊无违。宛转儿戏,斑襕彩衣。笃哉孝思,心精且微。”[20]卷132,1326此类记载举不胜举。唐代诗句以老莱子“彩衣”的典故为喻,表达回乡省亲之情及孝事父母之意,反映了儿童穿彩衣的文化传统在唐代仍然很普遍。
唐代童蒙教育强调依法服装,不得僭越。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儿童服制不明的情况,故儿童穿彩衣一般不会被视为僭越行为。但是若富家子弟成童之后仍穿“彩衣”,就会招人嘲讽。如唐代长沙窑瓷器有题诗《衣裳不如法》云:“衣裳不如法,人前满面羞。行时无风彩(采),坐在下行头。”[53]说明诸如“着杂色衣服”的“衣裳不如法”行为,实际上是招人生厌的丑陋之行,并不能增添光彩,更无个人形象可言。《百行章·卿大夫章第四》曰:“相国三台辅,官连九寺卿。大夫依法服,非道不曾行。”杜正伦要求子弟应该按照国家有关服制“依法服,非道不曾行”,也就意味着少年儿童亦应依服制穿衣,否则难以养成良好的习惯,此盖为将“着杂色衣裳”归为“八贱”的原因之一。
教育子弟强调重德行轻“衣服”。《新集文词九经抄》藉名孔子曰:“内无君子之德,外服君子之衣者,犹以犬羊之鞹,虎豹之皮,此谓之绣外而麻里也;不服君子之衣,而怀仁贤之行,此谓之锦中而纻表也。”(第三八八条)以“绣外而麻里”为喻,说明人与动物有别,不能本末倒置,不仅要重视衣服光鲜,更应该重视内在的品德,劝诫子弟重德行,轻衣着,做到“锦中而纻表”。因此,衣着的品位和装扮,的确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品行和格局,故有“人惟旧,物惟新;衣贵新成,不尚故朽”之说。又诗圣杜甫劝诫儿子宗武要好好学习诗文,“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54]告诫其子要精熟学业,切勿专事玩乐。
综上所论,“着杂色衣裳”是指子弟不辨服制、无视“依法服”的礼制,而“着杂色”衣,着“彩衣”,与中国古代圣君“垂衣裳而治”、用礼法制度规范社会秩序的观念相悖,有违中国古代服制定尊卑、辨贵贱的礼法制度,属于僭越违制行为。在唐代服制观念里,朝服以五色服为贵,用于品官,杂色衣服为贱,通常为乐伎、奴婢等服用;加之中古以来,佛教也视服杂色衣服为破戒,因此无论从道德观念还是从服制和佛教信仰等层面,“着杂色衣裳”都被视为僭越违制行为,属于贱行,自然无“形象”可言。此外,开元以后,随着进士科社会地位的提高,虽也出现了声名高的进士高调穿“彩衣”的现象,却是受人诟病的行为,被称为“浮薄”,[55]故犯此行者,其“形象”堪忧。
七、“不自修饰”的文化内涵与观念考释
“修饰”指梳妆打扮。“不自修饰”字面上指对个人仪表形象不太在意,不修饰个人衣装仪表;但其深层含义却不限于此,小到文字语言润色,大到道德修养,内容颇为丰富。
(一)修饰与饰行相辅相成
君子的形象和仪容,往往是通过个人衣冠和容颜来展现的。《礼记·儒行》云:“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2]卷41,1400因此,君子必须通过修缮容貌、严正衣冠以树立个人威严形象。君子修容的意义在于“自修饰整威仪”。[1]卷117,3041-3042《论语·尧曰》载,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21]卷39,1371言君子衣冠严整,可让人瞻视尊严,望而生畏。汉代韩婴《韩诗外传》云:“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俨然人望而信之;其次闻其言而信之;其次见其行而信之。”[33]卷3,127可见君子衣冠对树立信义而言,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言行,故有“衣冠堂堂”是“伟丈夫”的说法。[56]如《魏书·封轨传》载:“(封轨)善自修洁,仪容甚伟。或曰:‘学士不事修饰,此贤何独如此?’轨闻,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视,何必蓬头垢面,然后为贤。’言者惭退。”[18]卷32,764君子衣冠整洁是获得世人尊重的基本要求,足见修饰对学子的重要性。又北周独孤信少年时,“好自修饰,服章有殊于众,军中号为‘独孤郎’”。[57]卷16,263
明镜修饰,良友饰行。《楚辞·九辩》云:“今修饰而窥镜兮,后尚可以窜藏。”[58]屈原以世人用“窥镜”修饰容颜,喻人的道德品行也需要修饰。又《荀子·君道篇》云:“故君子之于礼,敬而安之……其于仪也,谨修饰而不危……其交游也,缘义而有类;其居乡里也,容而不乱。”[59]荀子所说君子谨修饰而不危其身,结交有义的朋友,则须在乡里注意自己的仪容,明确地阐述了饰行与交友的意义。“内行修饰”在汉代也成为品评人物的一个标准。[60]
(二)修饰仪容、言语对童蒙教育的重要性
修饰仪容、言语在童蒙教育以及家教中的重要性,以敦煌蒙书为例,有以下几个层面:
其一,强调蒙童与人相识,须先正仪容。《太公家教》云:“与人相识,先正容仪;称名道字,然后相知。”教育子弟与人相识,首要之事就是正仪容,然后才介绍各自情况。正仪容不仅是展示自己形象的重要方面,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其二,告诫蒙童衣冠平常恒须整洁。《百行章·饬行章第卅七》云:子弟饰行,应当从家庭环境整洁做起,儿童修饰衣冠需要从小做起,出门不得赤身裸体,恒须整洁,这样才能养成整洁干净的生活习惯。就算“纵居私室,恒须整容”,告诫子弟整容须要恒守,即便在家,也不能放松。
其三,劝诫蒙童观容止而交友。教示子弟在与人交往过程中要懂得识人,察言观色,通过容止判定其人品。如杜正伦就告诫子弟对“颜貌俨然”德高望重者,要有敬畏之心,与人交往中要学会“容止进退,观而则之”,要掌握好分寸。《百行章·凡行章》载:“人多敦者皆轻,非理而谈,贱亦不听,容止无则。”教示子弟通过观察他人容止来判断是否为轻薄之徒,避免交无益友。
其四,劝勉蒙童以镜饰容,以友修德。《太公家教》云:“女无明镜,不知面上之精麄;人无良友,不知行之亏失。”明确指出女无明镜不能治容,人无良友不知行为过失,告诫子弟师友的重要性。又《新集文词九经抄》藉名《庄子》曰:“镜以照水,以证清察;人以智静,物以蔽藏。”(第一六七条)也是在论述以明镜照物、师友清察,方能知过而改的道理,劝诫子弟修饰仪容仅仅是正身,修饰德行更为重要。
其五,劝诫蒙童衣破须补,有错须改。《辩才家教·贞清门一》云:“既要立身,须得良友。近贤者德,近贱者忧。衣破须补,屋漏须修。好事即须勤学,恶事不可。”辩才大师告诫世人,德行之失好比衣破屋漏,必须及时修补,修补的办法就是结交良友、贤德,向贤思齐。又《文词教林》以世人通常在意“衣弊之恶”而忽略“言行之失”为喻,告诫子弟更应该重视言行,只有这样,才能去辱得荣。
综上所论,“不自修饰”有悖中国古代“垂裳而治”、士庶需衣冠严正的观念,指个人对仪表形象不太在意,不修饰衣装仪表、不注意言行举止、不修德行,属于自我作践、招人生厌的行为举止。有关修饰衣冠、德行的观念主要源自“修饰而窥镜”“谨修饰而不危”等。唐代童蒙教育和家教中对少年儿童有关“不自修饰”的教育,主要从饰容和修行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强调“与人相识,先正容仪”,教示子弟要重视个人仪容,尊重别人,这对树立自己的形象非常重要;二是劝诫子弟“衣冠恒须整洁”“衣破须补,屋漏须修”,以树立整洁形象的观念,保持积极心态。在中国古代“相由心生”观念的影响下,修饰己身尤为重要,若是“行不修饰,名迹无愆”,[61]放浪形骸,定为士大夫所不齿,无疑是自我作践、招人生厌的行为。
八、“坐不择地”的文化内涵与观念考释
“坐不择地”,与中国古代“坐地而食”“不择地而息”和“恶木盗泉”等多则典故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包括在生活中随意而坐、参加局席不辨位次等看似无大碍的不明事理、招人生厌的个人行为。
(一)与“坐地而食”的关系
“坐不择地”为贱行的观念应该与齐景公“坐地而食”的典故有很大关系。春秋时齐景公出外打猎,休息时直接坐在地上进食;上大夫晏子后至,“灭葭而席”,即踩在芦苇草(葭)上面,坐于其上。齐景公问晏子为何如此,晏子表示直接坐地的情况有三:介胄坐陈不席、狱讼不席、尸坐堂上不席,均为令人忧虑的不善、不祥之事,暗喻齐景公不席之举不合礼法,故他不愿直接坐地。于是齐景公令人在地上铺席而坐,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62]卷2,119-120据《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记载:晏子臣于庄公,庄公对其不满,喝酒时请晏子赴宴,晏子入座之后,庄公令人责难晏子,晏子便起身“北面坐地”。庄公问其故,晏子对曰:“婴闻讼夫坐地,今婴将与君讼,敢毋坐地乎?”[62]卷5,294可见坐地是讼夫之举,说明坐地行为不仅仅是简单的生活习惯问题,更有深厚的礼法准则。故晏子“灭葭而坐”“北面坐地”的故事,为《武王家教》“坐不择地”的立意提供了礼法支持,作者的用意就是担心子弟“坐不择地”,有违礼法观念,轻则遭人嫌弃,重则招致祸患。
(二)与“不择地而休”的关系
“坐不择地”与曾子事亲“不择地而休”的故事有一定关系。[33]卷1,1西汉刘向《说苑·建本》记载,子路跟孔子说:“负重道远者,不择地而休;家贫亲老者,不择地而仕。”子路为了侍养双亲,百里路上背米送粮,只好“随所处而安,无所择地而安”,[63]后来有“子路负米”的典故。这两个典故说明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理:若是因为遇上“百姓孝为首”的亲要事,因路远、家贫,可以“不择地而息”“不择官而仕”;但子弟在无“当务为急”的日常生活中“坐不择地”,则被视为懒惰、不辨善恶的不良、不当行为。
(三)与“坐须合礼”的关系。
“坐不择地”不仅仅是指不择地(方位、座次等)的问题,还是在讲坐席礼法的问题。晏子“灭葭而席”的典故,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坐须合礼”。关于宴席的座次文化,《礼记·曲礼上》对世人常见就席的座次及相关礼仪有详细记载,此处不再介绍。[2]卷1,20;卷2,36-37;卷3,64
中国古代局席之上辨主位次席的主要目的是为别尊卑、贵贱的礼法服务。《孔子家语·问玉》载:“昔者明王圣人,辨贵贱长幼,正男女内外,序亲疏远近,而莫敢相逾越者,皆由此涂出也。”[64]可见席分上下,坐分主次,主要是为了辨贵贱、长幼,序亲疏,为中国传统的礼法制度服务,明确了世人在社会秩序中的位次,有利于国家的统治和家庭的和睦。但凡宴集局席,都是不同身份的人在社会秩序中身份地位的体现。如汉文帝虽然一世英明,但让嬖妾慎夫人与皇后同席,即为“乱尊卑之伦”,被史家评为“通而蔽”。[65]足见古人对正席、座次礼法的重视,其背后是对尊卑、贵贱礼法制度的尊重。
古人还讲究“正席而坐”。《论衡·命义》云:“故《礼》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时,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视,非正声耳不听。”[45]卷2,54把“席不正不坐”作为胎教的重要内容,实际上是劝诫年轻母亲坐立起居要合礼法,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从妊娠时就传导给胎儿,将来也好给幼儿做典范,足见古人对“择地而坐”观念的重视。中国古代局席十分讲究礼法,局席之上注意的事项很多,诸如“坐不累席”[22]卷10,311“坐不安席,食不甘味”[22]卷36,944食不二味,坐不重席”[66]等等。
(四)择善同席
席上既然以尊卑、长幼排序,德高望重之人自然就常坐上席。“据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虚无寂寞”,往往可以达到“制事因短,而动益长,以圆制规,以矩立方”的效果。[67]故申徒嘉云:“久与贤人处则无过。”[68]唐人重与贤者同席。如中晚唐高郢多次知贡举,深得品鉴、选拔士人之要领,故作《沙洲独鸟赋》,以沙洲独鸟尚且知择木而栖为喻,认为士人更应该择地而处,弘扬“盗泉不饮,得廉士之风”。[20]卷449,4591-4592又唐贞元中,侯喜作《鸟择木赋》,以鸟择木为喻,来阐述中唐进士行卷之事。开篇就说明了鸟择木不在乎得高枝,而在于“得所履”,就好比进士行卷,选择投谒对象,“避恶之阴,同志士之不息”,深感行卷之艰难,需“如智者之千虑,叶君子之三思”,[20]卷732,7550要百般慎重。他赞美凤凰栖桐是“择善而从”,渴望得到明君赏识,期望“以良木可期,倘主人之见纳”。
(五)与“不与恶人同席”的关系
中国古代常以“鸟择嘉木而栖”喻人当“择地而席”“处必择地”,避免与恶人同席。北周寇俊“性又廉恕,不以财利为心。家人曾卖物与人,而剩得绢五匹。俊于后知之,乃曰:‘恶木之阴,不可暂息;盗泉之水,无容误饮。得财失行,吾所不取。’遂访主还之。”[57]卷37,657以恶木、盗泉之典故明其节操。不与恶人同席、断席以明志是中国古代常见的劝诫子弟远离恶人的典故。如西汉任安、田仁“断席别坐”;[1]卷104,2780东汉许敬拔刀断席,誓言“不忍与恶人同席”。[12]卷69,1206又汉末有管宁“割席分坐”的典故。[69]此类典故中割席分坐的目的,均为不与品行有问题的人同坐,这些典故成了唐代童蒙教育中的经典故事。
(六)唐代童蒙坐席之教的特点
唐代对蒙童进行“坐不择地”的教育,主要体现在坐席礼法知识、择善而坐及慎行等方面。先是教授蒙童坐席的礼法知识。一卷本《王梵志诗·亲家会宾客》云:“亲家会宾客,在席有尊卑。诸人未下筯,不得在前椅。”(二〇)教导蒙童坐席时应该注意长幼、尊卑及谦让等礼仪。同书《亲还同席坐》云:“亲还同席坐,知卑莫上头。忽然人怪责,可不众中羞。”(二一)主要向童蒙传授坐席上的尊卑礼仪。又同书《尊人立莫坐》云:“尊人立莫坐,赐坐莫背人。坐无方便,席上被人嗔。”(二二)此为谦让之教,让子弟懂得坐席的基本礼法和忌讳。
再是树立择善而交、远离恶人的观念。一卷本《王梵志诗·结交须择善》云:“结交须择善,非谙莫与心。若知管鲍志,还共不分金。”(四八)《太公家教》云:“以善人为交,如入兰芳之藂;以恶人为交,如同鲍鱼之穴。”以兰芳、鲍鱼为喻,教导子弟择善而交,弃恶割席。又《语对·朋友》“兰芷”也是记载此则故事的词条。《朋友》“弃金”条还收录管宁“割席而坐”的故事,以劝诫子弟慎择良友。一卷本《王梵志诗·恶人相远离》云:“恶人相远离,善者近相知。纵使天无雨,云阴自润衣。”(四九)可见“择地而坐”的本质是“恶人相远离,善者近相知”。
综上所论,“坐不择地”不仅是单纯地指个人不择地而坐的有关就座礼法、形象的问题,也包含了行不择地、入席无礼等招人鄙视的不当、不良举止,引申为行事无道、欠考虑、目无尊卑之序、不守礼法、与恶人交等因为不慎而招致祸患的行为。该条目与中国古代“坐地而食”“不择地而息”“恶木盗泉”等多则典故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内涵颇为丰富。特别是在唐代开元以后,随着科举的兴盛,行卷之风盛行,“择地而行”“择地而坐”又被赋予了更多的功利性。进士奔竟于权贵、文宗之门,投谒行卷之前,为了“避恶之阴”,绞尽脑汁,再三斟酌,可谓深得“择地而行”的精髓。
结 语
《武王家教》所谓“八贱”,是在中国古代“垂衣而治”的观念下,对关乎个人“形象”的八种不良、不雅的举止和着装仪表的概括,意在强调以辨尊卑、贵贱来规范社会秩序,劝教子弟远离并戒除此八种贱行,以实现富家、长命的目的。由于中古时期正处在贵族政治向文官官僚政治转变的过程中,衣冠华族把持朝政,更是重视衣冠、言行,故上述有关个人招人生厌的“八贱”行为,更是别有意味。其主要着眼于子弟个人“形象”的塑造,对个人习惯和志向的养成十分重要,也关乎来自家庭、师友、邻里及社会诸多层面的评价。
“八贱”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其一,行步匆匆、跷脚立尿、坐不端正三项,属于个人修身、立身和立信等均有负面影响的行为。在中古时代衣冠华族把持朝政的情况下,“行步匆匆”与世族之家“缓步阔视”“逶迤行步”的形象迥然不同,是社会底层贫贱、落魄和劳苦之命的典型形象,成了命相“贱”的表征。在唐代科举行卷之风盛行,重视延誉的情况下,举子“行步匆匆”,其声誉、仕途堪忧。“跷脚立尿”属于中古时期的一种民间生活禁忌,与佛教和道教文化有很大关系。“跷足”“立尿”分别为中古以来佛教、道教的禁忌,合在一起,说明两者为同一类粗俗不雅的行为。“坐不端正”主要指个人坐无形象,不合礼仪,如是“则昏惰之气必生”,与中国古代“形端影正,身曲影斜”等观念相悖,故被列为“贱”行。
其二,你我他人、唾涕污地两项,为个人行事不管不顾、自以为是、不知丑陋的行为。“你我他人”很难从字面含义解释它与其他七“贱”的类同性,是三个人称代词加“人”字构成的特定俗语,可诠释为“以你我为他、不分你我他”之义,引申为与人相处时不分你我,招人厌的不当行为。针对“你我他人”所包含的诸种不自知、不自觉之义,也是唐代蒙书和家训重点训诫的常见内容。“唾涕污地”相对较好理解,就是随意唾涕在地上,弄污地面,属于缺乏教养的粗俗行为,故入“八贱”。
其三,着杂色衣裳、不自修饰、坐不择地三项,为世人居家或出门应对时穿着、举止不当,自甘堕落,自我作践,损毁“形象”的行为,均违背了中国古代服制定尊卑、辨贵贱的文化传统。“杂色衣裳”是指子弟不辨服制,无视“依法服”原则的行为,不仅存在僭越违制之虞,而且招人厌,遭人鄙视。“不自修饰”,指不在意个人的仪表形象,不梳妆打扮,与中国古代“垂衣而治”的观念相悖。受“修饰而窥镜”等观念的影响,训诫子弟懂得以明镜正衣冠、以师友明察行为举止的重要性,谨言慎行。“坐不择地”,与中国古代“坐地而食”“不择地而息”和“恶木盗泉”等多则典故关系密切,可引申为行事无道、欠考虑、不守礼法、与恶人交等容易招致祸患的行为。在唐代开元以后行卷之风盛行的情况下,子弟若“坐不择地”、行不三思,必将前途暗淡。
总之,“八贱”是针对子弟在行、立、坐、穿、饰等日常生活应对中,容易出现的有损个人“形象”的行为,告诫子弟应该注意待客、做客等应对之道,避免行步匆匆、坐不择地等八种容易让人生厌、轻视的“贱”行,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以达到修身、立身的目的。与之对应的是中国古代有关缓步阔视、逶迤行步、行步有容,坐起恭敬、行必中正,慎莫多事、莫为无益事,就食不唾涕,衣冠端正、不服彩服,与人相识,先正仪容,衣冠恒须整洁,人生需要谨言慎行、三思而行、慕敬贤良、择地而坐等观念。子弟若能远离“八贱”,举止儒雅、衣冠楚楚、文质彬彬、志向远大、博学多识、积极向上,就是君子“形象”,可进而金榜题名,成为“白衣公卿”。[46]卷1,4
注释:
①本文中《武王家教》以P.2825 号为底本,以下不再说明。本文所引敦煌文书(如《百行章》《新集文词九经抄》等)主要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14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14册),1992—2001;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5。录文,请依据卷号查询。以下不再加注一一说明出处。同一部蒙书,第二次出现不再加卷号。
②金滢坤:《唐代问答体蒙书编撰考察——以〈武王家教〉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金滢坤:《敦煌蒙书中的儿童警示教育——以〈武王家教〉“六不祥”为中心》,《敦煌学》2021年总37期;金滢坤:敦煌蒙书《武王家教》中的唐代富贵贫贱观念解析——以“十恶”为中心,《敦煌研究》2021年第6期;金滢坤:《唐代〈武王家教〉中的儿童“自知”教育解析——以“三痴”为中心》,《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③《西游记》第五十四回《法性西来逢女国心猿定计脱烟花》:“女王见他不受,又取出绫锦十匹,对行者道:‘汝等行色匆匆,裁制不及,将此路上做件衣服遮寒。’”吴承恩:《西游记》,曹松校点,中华书局,2009,第379页。《醒世姻缘传》第五十三回《期绝户本妇盗财,逞英雄遭人捆打》云:“拾起一块石灰,在那路旁大石板上写道:‘响马劫人,已被拿获。赶路匆忙,不暇送官正法,姑量责捆缚示。’”西周生:《醒世姻缘传》,武璋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09页。
——福建农林大学建校
——弋阳腔传统曲牌抢救性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