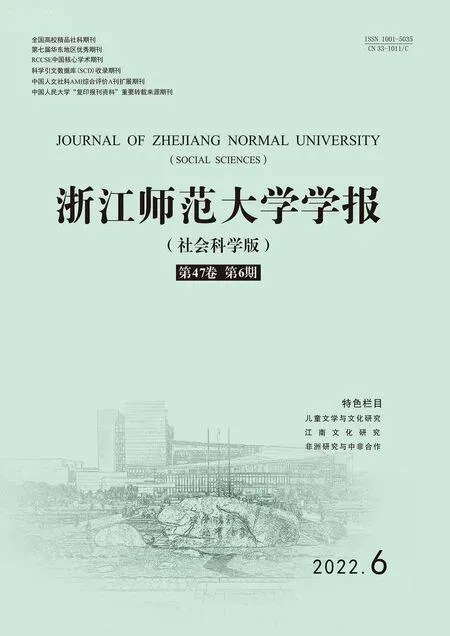《读书日程》中的人才培养模式
罗玉梅, 王照年
(1.闽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2.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三卷(另有《读书日程》《读书工程》《程氏读书日程》《家塾日程》等名称,本文统一用《读书日程》),元代程端礼撰。端礼,字敬叔,号畏斋,又号敬礼,元庆元路鄞县人。①生于南宋咸淳七年(1271),卒于元至正五年(1345)。自幼聪慧而爱好读书,青少年时期已“能记诵《六经》,晓析大义”。[1]4343师从承袭朱子理学见长的静清学派创始人史蒙卿,[2]184故“其学以朱子为宗”。[3]2216先后从事教育工作长达四十余年,致力于儒家传统经典的研读与教学。最初程氏是在赤山精舍教王元戴读书,直到大德四年(1300)春,“东严王公为广德建平宰”,[4]654以其学识之优而被选任为建平②县学教谕,③始步入政府官学系统的教学生涯。初迁台州路、衢州路儒学教授,再迁稼轩、江东书院山长。晚年经时人程荣秀荐举,任江浙儒学副提举,至正元年(1341),以将仕郎、台州路学儒学教授④致仕,自此结束了官学生涯。回归故里后,又被当地郡守王元恭礼请为师,直至终老。毕其一生,为人刚毅方正而不失其宽容,为学博闻强记而尤勤于撰著,为师授徒甚众而特善于教导,故被当世之人所推崇,声望日隆,遂与其弟程端学合称“二程”,又因程颐、程颢兄弟之故而被元代学人尊称为“后二程”。[5]348《元史》有传,平生行实,详可据之。今有《读书日程》《畏斋集》《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等著述传世,其中以《读书日程》一书特为称著,流布既广而又影响深远,不仅是一部在元明清时期教育教学领域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地位的力作,而且是一部堪称我国现存产生时间较早的、内容较为全面的、可定性为元代较为完备的汉语文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⑤
究其著述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程氏著述的初衷,是为了在元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能够将传统儒学更好地传承下去,故不得不制定一个可以实践的整体规划,或可供参照的执行标准,或可用以指导的行动纲领,旨在以此为依据或准则并严格遵循,方可承之有范,行之有效,传之久远。二是程氏著述中确定的培养目标,取决于当时应对科举考试的社会总需求,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时人渴望成才的美好愿景。故在当时的儒学教育体系下,程氏通过其著述要较为全面而合理地解答三个现实问题:一是为何要读书?即读书人要面对的学习行为目的性问题;二是怎么读书?即读书人必须要面对的学习行为有效性问题;三是读什么样的书?即读书人必须要面对的学习行为任务性问题。事实上,程氏所涉及的这三个问题,应为自古及今的读书人都会在读书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要进行追问的问题。这是因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三个问题,都直接关乎读书人对自身读书行为合理性的拷问。也正是本着对此类问题的现实性思考与解答,程氏才会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探索,并总结成功经验,逐渐辑成《读书日程》一书,正所谓“余守此与朋友共读,岁岁删修”,[6]123旨在“与朋友共读,以救斯弊”,[6]1实现元代更好地传承传统儒学教育的愿望。
总之,该书的核心内容及其呈现出的内在逻辑表明:从明确既定的读书目的到遵循已有的读书方法,从确定完成的读书任务到设置相应的课程体系,都清晰、完整地体现了处于当时儒学教育体系下,应当具有的一种相对合理而又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模式。
一、元代儒学教育的处境
元代将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个社会地位不同的等级,整个元代的教育大环境也存在着十分明确而森严的等级划分。一直处于第一等级的、倍受强制力所认同的官方通行语言是蒙古语,官方通行文字同样也是蒙古文。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探讨元代教育问题时,得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当时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所谓“国学”,乃是天下统一推行的蒙古学,而不是汉学。
二是在元朝灭南宋之后,先得到元朝政府许可,在当时教育体系中,特别是基础教育中可以合法存在并得以传播和发展的语言文字,乃是仅次于蒙古学的回回学,而不是汉学。
三是在元朝灭南宋前后,在国家层面成立的主管教育的管理机构或行政部门国子监,最初只有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创立的蒙古学国子监,之后又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设置了回回学国子监,与蒙古学国子监并存,属于可参与教育管理的机构或部门,而以传统儒学教育为主的汉学国子监起初并未见有设置。直到大德十年(1306)才出现了与蒙古学国子监和回回学国子监并列的汉学国子监,专门开设《诗》《书》《礼》《易》《春秋》《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之类的传统儒学经典课程,进行传授生徒。再至皇庆二年(1313),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故在延祐二年(1315)时,才有了第一次不以蒙古学为主的开科取士。尽管放榜时规定有左榜和右榜的尊卑之别,但是自此正式恢复了类似于唐宋时期的以儒学为主的科举取士制度,同时也逐渐恢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与儒学教育体系相一致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机构,断续近三十年的儒学传统教育才得以逐步恢复。
可想而知,程氏处在儒学教育不受重视的境遇下从事儒学教育四十余年,精通的是传统儒家经典所承载的基本思想与主体精神,娴熟的是儒学教育体系下进行的教育管理与教学工作,积累的是地方官学教育到私塾教育的教学经验与教育体会,故最终在著述中所体现的总体思想与核心内容均与之息息相关。尤其《读书日程》一书,堪称是程氏毕生从事教育教学的实践经验总结,该书中所确立的因何读书的明确目的,所秉持的怎么读书的有效方法,所确定的读什么书的学习任务,不仅直接针对唐宋以来承载儒家教育体系的传统经典学习,而且具体设置了一个从学前幼儿教育到大学教育,乃至终身教育要先读什么书、后读什么书的整体程序。
二、秉承朱子读书目的来解决因何读书的目的性问题
由于程氏《读书日程》著述的针对性十分明确,故其所秉持的读书目的也就相当明了。在其卷首的《自序》中,开宗明义地称:
今父兄之爱其子弟,非不知教,要其有成,十不能二三,此岂特子弟与其师之过?为父兄者,自无一定可久之见,曾未读书明理,遽使之学文。为师者,虽明知其未可,亦欲以文墨自见,不免于阿意曲徇,失序无本,欲速不达。不特文不足以言文,而书无一种精熟。坐失岁月,悔则已老。且始学既差,先入为主,终身陷于务外,为人而不自知,弊宜然也。[6]1
显然,程氏对当时恢复科举考试后,存在诸多家族急切盼望子弟能够迅速成才而出现急于求成、违背常理的读书时弊,认识很清晰。事实上,这也是科举制推行以来难于避免的痼疾。早在程氏之前,朱熹就明确指出,往圣先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之为学者,既反是矣”。[6]2而在程氏之后的明清时期,这一弊端更是愈演愈烈,正如清人张伯行所云:“自圣人之学不传而世俗之所以教子弟者,止知有科举之业,否则惟词章之尚耳。此其意不过为取科第、拾青紫之计,即一旦得志,其所知所行亦不过为肥身家、保妻子之谋,问其所为内圣外王、明体达用之学,竟安在也?又悉望其功盖天壤、泽被生民乎哉?”[7]1
前有朱子所言,后有张氏之论,将这一弊端与《读书日程》后文中程氏论述的相关内容结合起来,便可以更为明了地看清楚程氏当时所面临的实际情况,集中体现在两个不同阶段上的弊端:
一是处于读书初学阶段的弊端。在“读书”⑥尚未达到“明理”要求的情况下,就急功近利地想要“学文”以求速成,无疑是不合乎进学常规的空想,终究不会得到任何理想的“读书”结果。也就是说,处于读书的初学阶段,程氏完全不主张“学文”。这便是程氏据朱子之说,“使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以便志道之士”,[6]1即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读书”是为了科举考试,可对于这一阶段“学文”的态度,依旧不变。否则,因急于求成而“失先后本末之序,虽曰读书作文,而白首难成者,可以观矣”。[6]24
二是读书岁月既久阶段的弊端。在“读书”已至于“精熟”之时,其“读书”的目的也逐渐趋于实现中,依据实际情况虽然可以进入开始能够“学文”的“读书”阶段,但是明确的要求依旧是一边“读书”,一边“学文”,而并非一旦进入“学文”的“读书”阶段,就可以放松“读书”的要求和不再抓“读书”目的的落实。即便在这一阶段进行“学文”两三年之后,可以参加科考且有幸博得功名,也仍要求“读书”的进学之途依旧如前,至少是必须继续坚持边“读书”边“学文”的学习方式。尤其是在考取科考之名之后,切不可束之高阁,放弃读书之功。程氏称:
专以二三年工,学文之后,才二十二三岁,或二十四五岁,自此可以应举矣。三场既成,却旋明余经,及作古文。余经合读合看诸书,已见于前。窃谓明《四书》本经,心用朱子读法,必专用三年之功,夜止兼看性理书,并不得杂以他书,必以读经空眼簿,日填,以自程。看史及学文,必在三年外,所作经义必尽依科制,条举所主所用所兼用之说,而推明之。[6]23
从程氏所针对的读书时弊的具体情况来看,即便当时多数的读书人将“读书”视为求取科举功名的唯一手段,而程氏也依然故我,自始至终都把“学文”当作“读书”的根本目的。程氏坚持认为,“学文”充其量不过是“读书”行为本身的延伸,依旧是进学修身的手段或途径,不是目的。若不加以区分,则“读书”定然会失去目的之所向,终究对读书人贻害无穷。程氏又称:
方今圣朝科制,明经,一主程、朱之说,使经术、理学、举业三者合一,以开志道之士,此诚今日学者之大幸,岂汉、唐、宋科目所能企其万一。第因方今学校教法未立,不过随其师之所知所能,以之为教为学。凡读书才挟册开卷,已准拟作程文用,则是未明道已计功,未正谊已谋利,其始不过因循苟且,失先后本末之宜而已,岂知此实儒之君子小人所繇以分,其有害士习乃如此之大。呜呼!先贤教人格言大训,何乃置之无用之地哉!敢私著于此,以待职教养者取焉。[6]24
于今观之,读书明理与文以载道之间,至多是层次上的差别,而在本质上是趋同的。因此,程氏针对“读书”所要求“明理”,或“明道”“正谊”等的根本是为了立大志,要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好人”。[6]19否则,便是舍本逐末。究其原因就在于:“欲经之无不治,理之无不明,治道之无不通,制度之无不考,古今之无不知,文词之无不达,得诸身心者,无不可推而为天下国家用。”[6]19之所以产生这一认识,一方面是因为程氏一贯秉持“孔子之教序,志道、据德、依仁,居游艺之先”[6]1的原则;另一方面也与程氏毕生所学以承袭朱子学派的理学思想为主有关。程氏依据朱子之语称:“端礼窃闻之,朱子曰:‘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6]120《读书日程》卷前《纲领》首列朱熹“集圣贤之成训”而成,堪称“学问之宏纲大目”的《白鹿洞书院教条》;次列程端蒙、董铢定为读书人“群居日用之常仪”,可以“使人有所持循”[6]1-3的《程董二先生学则》;续列为学有传承、立朝有声望、教子有良方的理学家真德秀的《西山真先生教子斋规》;最后列《朱子读书法》和《古人读书法》。这一切又与程氏长期在元代教育官学体系中从事儒学教育教学实践所始终坚守的原则、追求的目标相一致。也就是说,程氏亲力亲为的教育教学实践都是在印证其所持“读书”的基本要求在于“明理”,[6]19其终极目的是实现远大的志向。
三、秉持朱子读书方法来解决怎么读书的有效性问题
《读书日程》所秉持的读书方法,皆源于朱子,并以语录体的形式摘录出四条,陈列为该书总纲的一部分,单独编目为《朱子读书法》。具体内容有“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敛身正坐,缓思微吟,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宽著期限,紧著课程”“未熟快读促遍数,已熟缓读思理趣”[6]7-8等相关读书准则。深细考量“此法似乎迂阔,而收可必之功,如种之获”。[6]24
朱子堪称理学之集大成者,而理学又名道学,乃是两宋时期继承前代儒学发展成果、融汇释老思想而后有所创新的儒学,实属中国古代至为精致而完备的主要思想理论体系,对后世的影响之深巨,毋庸置疑。因此,程氏作为朱子之学在元代的后继者,秉持的所谓“朱子读书法”,[6]7自然是朱子在其读书与教学过程中获得的成功经验总结,完全顺应当时已更新为理学的儒学教育体系。也就是说程氏将“朱子读书法”确定为研读儒家经典的方法,不仅是毫无疑问的有效读书之法,也是紧扣之前已明确的读书目的,更为明确地回应当时的社会需求。尤其是《读书日程》中的第一条所列六法,几乎成为自元代以来儒家学子都普遍遵循的基本读书心法,常常被上升为“纲领”的高度而奉行之。清代四库馆臣在《读书日程》提要中称:
是书有延祐二年自序,谓“一本辅汉卿所萃《朱子读书法》修之”。考《朱子读书法》六条:一曰居敬持志,二曰循序渐进,三曰熟读精思,四曰虚心涵泳,五曰切己体察,六曰著紧用力。端礼本其法而推广之。虽每年月日读书程限不同,而一以六条为纲领。史称:“所著有《读书工程》,国子监以颁示郡县。”即此书也。[3]1222
及至明清时期,随着程朱理学盛行于世和科举制度的一度强化,该书更被诸儒奉为准绳,各地一再刊刻,流布益加广泛,几乎成为天下士子无人不晓、公私学堂无不参照的一部教育教学方面的纲领性文件,对元、明、清三代官学及书院儒学教育影响深远,不但关涉学人从教、治学及个人研修等诸多方面,而且后世公私教育机构在制定相关学规时,均多有所参照,一度被奉为秉承不移的范式。《元史》载:“所著有《读书工程》,国子监以颁示郡邑校官,为学者式。”[1]4343实践证明,《读书日程》所秉持的“朱子读书法”[6]7切实可行,正好解决了如何读书才能够行之有效的问题。
四、设置儒学教育的进学之序来解决读什么书的任务性问题
有效的读书方法要落实到一个合理的实施过程中,才能真正体现其有效性,这正是通过课程体系设置、实施及其考核来最终达成其目的的有效途径。在程氏确定读书目的时,就已经针对时弊阐明了“读书”与“学文”都是手段,二者的先后次序不能颠倒,否则就会“失序无本,欲速不达”,[6]1最终的结果自会适得其反。而在程氏依据目的确定读书之法后,又结合不同年龄段学习者的认知特征,从整体上相应地设置先读什么书、后读什么书的程序,包括学前幼儿教育阶段、入学后的小学教育阶段、大学教育阶段以及之后终身教育的整个过程,都是如此,并将方法分年月日落实在每一个阶段的进程中,正如《读书日程》载:“《日程》节目,主朱子教人读书法六条修。其分年,主朱子宽著期限、紧著课程之说修。”[6]1特别是在每一个阶段的进行过程中,规定用空眼簿⑦进行记录进程情况,形成可供查证的类似学习档案袋的过程性评价材料。
(一)学前幼儿教育阶段
《读书日程》规定:
八岁未入学之前:读《性理字训》(程逢源增广者)。日读《字训》纲三五段,此乃朱子以孙芝老能言,作性理绝句百首,教之之意,以此代世俗《蒙求》《干字文》最佳。又以朱子《童子须知》贴壁,于饭后(行饭时)使之记说一段。[6]1
可见,这一阶段,程氏并不主张用传统的《蒙求》与《千字文》,而以能够明确体现理学思想在其内的启蒙教材《性理字训》和《童子须知》取代之。
(二)小学教育阶段
《读书日程》规定:“自八岁入学之后,读小学书正文。日止读一书,自幼至长皆然。此朱子苦口教人之语。”[6]1既然这一阶段所读之书的内容与朱子苦心教导人相关,那么所读小学书到大学书中所渗透的思想,肯定与理学的关联十分紧密。事实上,进入到入学后的读经时期,具体的内容以读四书为主,设置的次序为:先读《大学》正文及《章句》《或问》,而后依次读《论语》《孟子》《中庸》。这与朱子的《四书集注》中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排序情况有所不同,应当更适合小学入学后的认知规律。“小学毕,次读大学经传正文”,[6]7依次有《论语》《孟子》《中庸》《孝经》《易》《书》《仪礼》《礼记》《周礼》《大学》《春秋》《诗》《小学》。此外,又逐渐增加了秉承理学思想的往圣时贤针对经文进行注释、讲解、梳义、考证等所形成的典籍,作为参考书目。于是,从所读主体教材到辅助教材,形成更为契合理学传承的读四书之法与要求。很显然,这是一种以理学先入为主的承接方式,一方面是在衔接学前教育阶段的课业设置与学前准备;另一方面是在为过渡或深入到小学阶段要读儒家经典做思想准备。具体方法及相应的要求需要落实在不同的过程当中,依次分为前后各有侧重的三个时期。
其一,以学生读经为重的时期。相应的要求是老师督促学生读经的遍数,重点在于不断地重复,要读得“句句字字要分明,不可太快”,还要时刻注意“读须声实,如讲说然。句尽字重道则句完,不可添虚声,致句读不明,且难足遍数,他日信口难举”。[6]3具体以学生读经为重的“日程”经过,必须以程氏所设计的每人一部空眼簿上的要求为准,如实记录。《读书日程》载:
随日力、性资,自一二百字,渐增至六七百字。日永年长,可近千字乃已。每大段内,必分作细段;每细段,必看读百遍,倍读百遍;又通倍读二三十遍。后凡读经书仿此。自此说小学书,即严幼仪。大抵小儿终日读诵,不惟困其精神,且致其习为悠缓,以待日暮。法当才办遍数,即暂歇,少时,复令入学。如此可免二者之患。[6]1-2
其二,以老师说经为重的时期。相应的要求是老师说经通透,学生理解。无论“小学书”还是“大学书”,均强调学生试说并力求说到明了通顺。以老师说经为重的“日程”经过,仍旧以程氏所设计的每人一部空眼簿上的要求为准,如实记录。《读书日程》载:
假如说小学书,先令每句说通朱于本注,及熊氏解。及熊氏标题已通,方令依傍所解字训句意说正文。字求其训注中无者,使简《韵会》求之,不可杜撰以误人,宁以俗说粗解却不妨。既通,说每句大义;又通,说每段大意。即令自反覆说通,面试通乃已。久之,才觉文义粗通,能自说。即使自看注,沉潜玩索。使来试说,更诘难之,以使之明透。如说《大学》《论语》,亦先令说注透,然后依傍注意说正文。[6]3-4
其三,以学生读经和老师说经并重的时期。相应的要求是老师监督学生读经,说经到位,重点在于思索章句文义渗透的性理,参照标准是朱子一脉的理学家注解,既要做到“字求其训,句求其义,章求其旨”[6]5,还要做到体会在心,力争达到理解透彻且融会贯通的地步。以学生读经和教师说经并重的“日程”经过,依旧以程氏所设计的每人一部空眼簿上的要求为准,如实记录。《读书日程》载:
随双、只日之夜,附读看玩索性理书。性理毕,次治道,次制度。如大学失时失序、当补小学书者,先读小学书数段,仍详看解,字字句句自要说得通透乃止。小学书毕,读程氏《增广字训纲》(此书铨定性理,语约而义备,如医家脉诀,最便初学)。次看《北溪字义》《续字义》,次读《太极图说》《通书》《西铭》,并看朱子解,及何北山发挥。次读《近思录》(看叶氏解)、《续近思录》(蔡氏编,见《性理群书》)。次看《读书记》《大学衍义》《程子遗书》《外书》《经说》《文集》《周子文集》《张子正蒙》《朱子大全集》《语类》等书。或看或读,必详玩潜思,以求透彻融会,切己体察,以求自得。性理紧切书目,通载于此。读看者自循轻重先后之序,有合记者,仍分类节钞。若治道亦见西山《读书记》《大学衍义》。[6]6-7
按照此上三个时期的顺次进行,学生将会循序渐进地学习一整套读书过程中所用的具体方法。此法不只是从读小学书开始就刻意培养的结果,也是在读大学书的过程中依旧坚持不懈、加以引导的结果,甚至作为一种读书有效的基本方法,将会固化为一种提升自我、完善自我的发展定式,内化为终身学习的一种品质。
此外,小学阶段重在识字与写字,以上方法的学习过程也是完成识字任务的过程。尽管写字是有相对独立的时间安排,一般按周期穿插在以上过程中,但同样有与之相应的具体要求。《读书日程》载:
小学习字,必于四日内,以一日令影写智永《千文》楷字。如童稚初写者,先以子昂所展《千文》大字为格,影写一遍过,却用智永如钱真字影写。每字本一纸,影写十纸。止令影写,不得惜纸,于空处令自写,以致走样。宁令翻纸,以空处再影写。如此影写《千文》足后,歇。读书一二月,以全日之力,通影写一千五百字,添至二千、三千、四千字,以全日之力,如此写一二月乃止。必如此写,方能他日写多,运笔如飞,永不走样。又使自看写一遍。其所以用《千文》,用智永楷字,皆有深意,此不暇论,待他年有余力,自为充广可也。盖儒者别项工夫多,故习字止如此。用笔之法,双钩、悬腕、让左、侧右、虚掌、实指、意前、笔后,此口诀也。欲考字,看《说文》《字林》《六书略》《切韵指掌图》《正始音韵会》等书,以求音义、偏旁、点画、六书之正。每考三五字,或十数字,择切用之字先考。凡抄书之字,偏旁须依《说文》翻楷之体,骨肉、间架、气象用智永,非写诗帖,不得全用智永也。[6]4
在《读书日程》中,有关写字有一整套专门的、针对性很强的方法以及相应要求,尽管在此无需详尽述及,但还是有必要强调四点:一是写字有助于识字,对文字义韵的深层理解与认识亦有益于写字,两者相辅相成。二是程氏在读经中往往设置抄读,所以写字与读书也能够相互促进,并得以共同提升。三是写字与演文同步,相互结合,一道进行,且为“读书”达到一定程度方可转向“学文”做好准备。《读书日程》有明确的“日程”安排:“小学读经三日,习字演文一日,所分节目,详见印空眼簿。必待做次卷工程,方许学文。”[6]2四是写字与读书贯穿始终而不废。
(三)大学教育阶段及之后终身教育的整个过程
进入大学阶段后,读书者年龄已经十五岁左右,除了在规定时间温习之前所学内容之外,据《读书日程》规定,需要依次深耕细读的书目设置为《孝经刊误》《易》《书》《诗》《仪礼》⑧《周礼》《春秋》⑨等儒家经典,具体读书方法及其相应要求悉数不变,依旧遵照之前所述“朱子读书法”。不过,随着学习者年龄、阅历等的增长和知识、经验等的积累,在这一阶段的要求中开始逐次加强了理学思想的接受,集中体现在学习过程中该如何积极主动地转向,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从注重儒家经典字词的含义转向注重经典章句表层的理解体认与深层的性理探索。重视宋代以来理学家对儒家经典经义的体察与阐释。《读书日程》载:“前自八岁,约用六七年之功,则十五岁前,小学书、《四书》诸经正文,可以尽毕。既每细段看读百遍,倍读百遍,又通倍大段,早倍温册首书,夜以序通倍温已读书,守此决无不熟之理。”[6]8-9及至读到滚瓜烂熟之后,“倍读熟书,必缓而又缓,思而又思”,[6]6即开始提出了“已熟缓读思理趣”[6]7-8的要求,具体的做法有“倍读熟书时,必须先倍读本章正文,毕,以目视本章正文,倍读尽本章注文,就思玩涵泳本章理趣(凡倍读训诂时,视此字正文。凡倍读通解时,视此节正文)”。[6]6尤其是“此法不惟得所以释此章之深意,且免经文注文混记无别之患”。[6]6可见,此法是在放缓读书节奏的前提下,刻意强化思考所读已熟的内容,且为了避免打扰,将此类读书过程安排在相对较为安静的夜晚进行,曰:“夜间玩索倍读已读书,玩索读看性理书,并如前法。”[6]9或曰:“夜间读看玩索,温看性理书,如前法。”[6]17
二是从注重儒家经典的正文转向注重承载理学思想的著述,明确讲求读书为学,乃至为人的志向。强调以朱子的《四书集注》为尊,旨在以程朱理学思想为指引,传承宋代以来的儒家思想传统。《读书日程》载:“自十五志学之年,即当尚志,……自此依朱子法读《四书注》。”[6]9这一阶段为解经所列书目,均据程朱理学一派,如“《六经》正文,依程子、朱子、胡氏、蔡氏句读,参廖氏及古注、陆氏音义、贾氏音辨、牟氏音考”。[6]8至明清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日益兴盛,则由此所发挥的影响力更是不容小觑。
三是从注重学习的遍数转向注重思考能力的习得,在强调诚心向学的同时,注重知行合一。重视持志向学与以身任道之间趋于统一的考量,追求实质性的提升。《读书日程》载:“必以身任道,静存动察,敬义夹持,知行并进,始可言学。不然,则不诚无物,虽勤无益也。”[6]9若将程氏此处提出的“知”界定为认知,将“行”界定为实践,则所谓“知行并进”,至今也是能够增进真知、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学习过程。何况这还是谨遵往圣先贤教导,为了实现远大志向而读书。所以,程氏在总结前贤教导的基础上提出“知”与“行”的理念,具有不同于寻常的先进性,不仅提升了对学习本身的要求,而且讲求学习过程中习得的实质性进展。体味探求完全可以从一字一句到一节一章,再到不同书本之间的内容识记须要“烂熟”,讲解须要“精确”,考索须要“明透”,诸如此类的具体要求中得以证实,即曰:
每一节十数次涵泳思索,以求其通。又须虚心以为之本。每正文一节,先考索《章句》明透,然后摭《章句》之旨以说上正文,每句要说得精确,成文抄记旨要。又考索《或问》明透,以参《章句》如遇说性理,深奥精微处,不计数看,直要晓得记得烂熟乃止。仍参看黄勉斋、真西山《集义》《通释》《讲义》,饶双峰《纂述》《辑讲》《语录》,金仁山《大学疏义》《语孟考证》,何北山、王鲁斋、张达善《句读》批抹画截……诸说有异处,标贴以待思问。如引用经史先儒语,及性理、制度、治道、故事相关处,必须检寻看过。凡玩索一字一句一章,分看合看,要析之极其精,合之无不贯。去了本子,信口分说得出,合说得出,终身心体认得出,方为烂熟。朱子谆谆之训:“先要熟读,须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道是,更须反覆玩味。”此之谓也。[6]5
四是从注重书本知识转向注重实现志向,明确指出读书不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禄和赢得个人荣誉之类的小事,而是为了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志在以身任道、心系天下而兼济苍生。读书人要树立远大的理想,一方面是从年龄上要求,即从十五岁左右起,读书应当有明确的志向,基本导向是“为学以道为志,为人以圣为志”。[6]9另一方面程氏反复引证朱子之语,一再告谕天下读书人,读书既不是要死记硬背书本上的知识及其所表达的基本义理,也不仅仅是为了独善其身,而是要在谨遵往圣先贤嘉言懿行的前提下,通过深入探究并广泛吸纳儒家经典所蕴含的修齐治平之大智慧,最终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即曰:“学者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真是无著力处。只如今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须反覆思量,究其病痛起处,勇猛奋跃,不复作此等人,一跃跃出,见得圣贤千言万语,都无一字不是实语,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积累工夫,迤逦向上去,大有事在,诸君勉旃,不是小事。”[6]9
随着大学阶段这四个转向的逐步完成,在小学阶段行之有效,且已初步成型的读书之法得以逐步更新,读书的实质性也将随之提升。于是,自此之后的读书,才能够渐入佳境而与众不同,方可真正领略到“朱子读书法”的高妙所在。特别是如果能够进一步明确因何而读书,更加坚定自己心性,则持志向学者终究会如同《读书日程》所云:“前自十五岁读《四书》、经注、《或问》、本经传注、性理诸书,确守读书法六条,约用三四年之功,昼夜专治,无非为己之实学,而不以一毫计功谋利之心乱之,则敬义立,而存养省察之功密,学者终身之大本植矣。”[6]14
一旦具备了以上读书的根基,则在读完传统儒家四书五经及其经注之后,就可以进入到一种相对独立而随性的读书发展阶段。这是学习者学到一定程度后,必须要经历的一种前景较为开阔而学习较为自主的拓展阶段。读书方法虽然依旧,但会有更多的选择。程氏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先读《通鉴》,之后依次读韩文,再之后可读《楚辞》,亦可根据个人情况的不同,有选择地广泛阅读自己所感兴趣的书。特别是程氏还为持志向学者开出了一份内容丰富、附带有指导性建议的书单,按其性质可大致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诸经注疏、诸史志书”,[6]18既充分考量与之前所读之书衔接,又有重点地向史书类典籍过渡,并强调读史书尤重其志书类。
第二类是通书。在通读史志之后,需要读一些通典、通考和通志之类的典籍,旨在将所读之书既融会贯通又不失专精。须读“《通典》《续通典》《文献通考》、郑夹漈《通志略》”[6]18之类的书。
第三类是专书。在一定读书基础上转向具有考辨源流和探究原委的书籍,以期所学有专深。如可读“甄氏《五经》《算术》《玉海》《山堂考索》《尚书中星闰法详说》、林勋《本政书》,朱子《井田谱》、夏氏《井田谱》、苏氏《地理指掌图》、程氏《禹贡图》、郦道元《水经注》、张主一《地理沿革》《汉官考职源》、陆农师《礼书》《礼图》、陈祥道《礼书》、陈旸《乐书》”[6]18之类的书。读这一类书,须要选读得法,即“先择制度之大者,如律历、礼乐、兵刑、天文、地理、官职、赋役、郊祀、井田、学校、贡举等分类,如《山堂寺索》所载历代沿革,考核本末得失之后,断以朱子之意,及后世大儒论议;如朱子《经济文衡》、吕成公《制度详说》”等。[6]18否则,就会失去继续读下去的兴趣,终将半途而废。
第四类是韵书、字书和律书。主要是因为读书读到一定阶段,自然会产生各种创作之需,须通过阅读此类典籍来熟悉汉语言文字表达的特征与音律协和的基本规定,以及由此直接关涉需要了解汉语言文字自身的特性与历史上形成的规律性。须读诸如“蔡氏《律吕新书》及《辩证律准》《禋典》《郊庙奉祀礼文》、吕氏《两汉菁华》、唐氏《汉精义》《唐精义》、陈氏《汉博议》《唐律注疏》《宋刑统》《大元通制》《成宪纲要》《说文》《五音韵谱》《字林》《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戴氏《六书考》、王氏《正始音》、陆氏《音义》、牟氏《音考》、贾氏《群经音辨》、丁度《集韵》、司马公《类篇》《切韵指掌图》、吴氏《诗补音》及《韵补》《四声等子》、杨氏《韵补》”[6]18之类的书籍。
此外,在依据个人读书志向、遵照各自兴趣进行的拓展阅读过程中,还特别强调记下个人读书心得与体会,即“每事类抄,仍留余纸,使可续添,又自为之著论。此皆学者所当穷格之事”。[6]18如此一来,只要在“《通鉴》、韩文、《楚辞》既看既读之后”,学生大致“才二十岁,或二十一二岁”[6]19即可臻学问小有所成。若“仍以每日早饭前,循环倍温、玩索《四书》、经注、《或问》、本经传注、诸经正文,温看史,温读韩文、《楚辞》之外”,再加“以二三年之工,专力学文”,则“既有学识,又知文体”,至此又有“何文不可作?”[6]19“如此读书、学文皆办”之成效至为显著,一般在二十几岁时,应付科举考试早已是绰绰有余,“若紧著课程,又未必至此时也”。[6]24也就是说,按照程氏的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实施,一位当时社会上二十出头的青年人,只要努力向学便可做到“读书”与“学文”并成的地步,自此而后,既可以胸有成竹地参加科举考试,效力国家,也可以继续学习,实现自我修养的不断完善与提升。总之,程氏的这一人才培养模式若能够如实坚持,最终培养出时代所需之才俊,应是毫无疑问的事。
结 语
鉴于历史局限性的存在,程氏《读书日程》中的人才培养模式,一贯以朱子之学为本,以传统儒学教育为主,承载着宋元以来的传统儒家教育的基本思想与观念,势必被打上一些不够完善、不够先进的旧时代的烙印。但是,细究之,其所秉承读书“明理”的目的是树立并实现远大的志向,可视之为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其所秉持的“朱子读书法”而持志向学的诚心及其行为,可视之为实现目标的相应要求与手段;其所确定的学习任务及其设置的整体的进学程序,可视之为达成目的的过程与途径。可见,《读书日程》所体现的核心内容及其精要,应当是一个基本要素构成比较完备的、整体程序设置合理且具备可操作性的人才培养模式。
元代如此,明代更是与人才培养的得失相关。“《读书分年日程》三卷,元程畏斋先生依朱子读书法修之,以示学者。朱子言其纲,而程氏详其目。本末具而体用备,诚由其法而用力焉,内圣外王之学在其中矣。当时曾颁行学校,明初诸儒读书,大抵奉为准绳,故一时人才,虽未及汉宋之隆,而经明行修,彬彬盛焉。几乎中叶,学校废弛,家自为教,人自为学,则此书难存而由之者鲜矣。卤莽灭裂,无复准绳,求人材之比隆前代,岂不难哉?”[6]1再至清代,从时人张伯行对《读书日程》一书内容及其功效的赞同之中,又可以得到最好的证实:由于张氏对当时的科举取士极为不满,认为存在着很严重的弊病,即“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难;古之取士也已实,今之取士也以文。古之时,乡举里选,故入务实学,争琢磨于仁义道德中,处为纯儒,出为名臣;今则不然,所取者时文已耳。父教其子,师教其弟,惟以时文为兢兢,非不读五经四书,究其所以读之者,亦不过为时文之用,初未尝取而体之于身心也。幸博一第,并其所为时文者而弃之,五经四书,束之高阁,诩诩然夸于人曰:‘吾已读尽天下之书!’而不知彼固未尝读书也。由所以教之者,未尽其道也”。然而,真正的读书必须“尽其道”的要旨何在?直到张氏在友人书斋里看过《读书日程》一书后,“心窃喜之,以为堪为后学津梁”,[6]1不仅可救科举时代之弊端,而且对现今只看重成绩的应试教育也有很深的警示。
总之,以《读书日程》的性质而言,“并非元代的课程表,或教学计划之类的古代教育文献,而应以秉承朱子读书之法为宗旨的基本理念、以研习汉语言文字为中心的教学运用、以传承儒家文化为己任的教育目的等特征,将其定性为产生于元代的一部较为完备的汉语文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8]再以元代以来该书在儒学教育体系中形成的重大社会效应,以及由此产生的深远社会影响而言,这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其成功的经验而论,至少对于新时代该如何制定和确立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一体化课程体系,建立终身教育的全范围育人模式,应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字号、出生地等的考订,均据池秀云编《历代名人室名别号辞典》(增定本),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第674页。又元代庆元路,隶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所辖,治所在鄞县,下辖鄞县、象山、慈溪、定海四县和奉化、昌国二州,辖境相当于今浙江省宁波、奉化、象山、定海等地。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第27-28页。
②元代的建平,为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所辖广德路之下的属县,即今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元代的台州路,隶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所辖,治所在临海县,下辖临海、仙居、宁海、天台四县和黄岩一州,辖境相当于今浙江省临海、仙居、宁海、天台、黄岩等地。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第27-28页。
③教谕,学官名。据称:“设于县学中,掌文庙祭祀、教诲、考核并管束所属生员。元制,直学任满经考试可升此职,此职任满经考核可升任学正、山长。宋京师小学和武学中设。”详见邱树森主编《元史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第724页。
④教授,学官名。据称:“元于各路、府和中州之儒学、蒙古学、医学等均置。京师国子学、太史院、司天监等官署中亦置。枢密院所属诸卫、诸都指挥使司则设有蒙古字教授及儒学教授等。品秩自正八品至九品不等。”参见邱树森主编《元史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第724页。
⑤有关该书的性质及其影响,今人谢德雄、马镛、郭齐家、熊承涤、毛礼锐等的著作中均有论及,此不赘述。亦可见拙作《试论〈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的性质》,刊于《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93-97页。
⑥《读书日程》此处所谓的“读书”,应以背诵为主的学习课业的行为,在一定意义上属于特指,与现今的阅读、读书等有别。另在《读书日程》后文中有所谓的“看书”,常与“读书”“学文”“习字”“演文”等相提并论,应与现今的阅读、读书等相近。
⑦程氏所用“空眼簿”,应为学生人手一本、用以记录其日常学习课业量与进度的日志,具有档案袋记录的评价特性。《读书日程》载:“以前日程,依序分日,定其节目,写作空眼,刊定印板,使生徒每人各置一簿,以凭用工。次日早,于师前试验,亲笔勾销。师复亲标所授起止于簿。庶日有常守,心力整暇,积日而月,积月而岁,师生两尽,皆可自见。施之学校公教,尤便有司钩钤考察,小学读经、习字、演文,必须分日。读经必用三日,习字演文止用一日。本末欲以此间读书之日,缘小学习字、习演、口义、小文词,欲使其学开笔路,有不可后者故也。假如小学薄纸百张,以七十五张印读书日程,以二十五张印习字演文日程,可用二百日。至如大学,惟印读经日程。待《四书》本经传注既毕,作次卷工程时,方印分日读看史日程。毕,印分日读看文日程。毕,印分日作文日程。其先后次序,分日轻重,决不可紊。人若依法读得十余个簿,则为大儒也,孰御?他年亦须自填以自检束,则岁月不虚掷矣。今将已刊定空眼式连于次卷,学者诚能刊印,置簿日填,功效自见也。”
⑧此处所读《仪礼》中,应包括《礼记》在内。
⑨此处所读《春秋》中,应包括《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