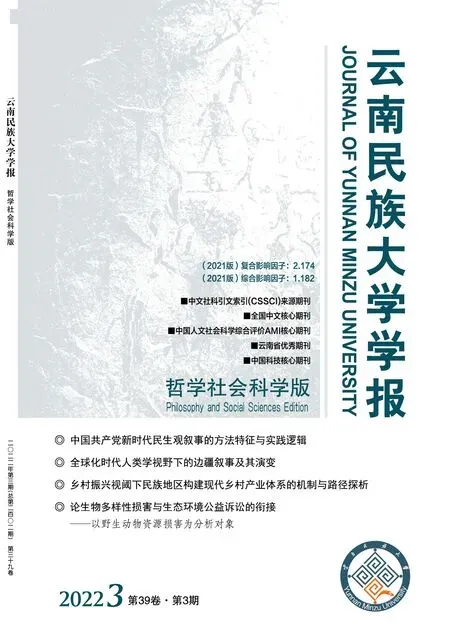中华民族历史观与“四个共同”研究论纲
王文光,胡 明,马宜果
(1.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91; 2.云南艺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第七次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习近平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高度,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作为统领,首先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年来中国民族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突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用“四个共同”(1)即“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详见《习近平在全国第七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来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2021年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了十二个“必须坚持”,其中的第四个“必须坚持”就是“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2)参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载《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由此可见学习和研究中华民族历史观的重要性。
学术界关于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研究经历了 “树立”“培养”的孕育发展阶段,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等理论命题是什么亟待回答。
从“树立”阶段来看,学术界主要以维护中华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中国人民历史使命开展讨论,这一阶段的讨论主旨基于维护祖国统一,确保社会稳定以及反对分裂的角度,并且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述梳理中华民族历史观对于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性,代表性论著有2003年卢高彬发表《应在各民族中梳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3)卢高彬:《应在各民族中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载《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03年第6期。及2004年田忠福发表的《新形势下树立中华民族历史观应坚持的观点》(4)田忠福:《新形势下树立中华民族历史观应坚持的观点》,载《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同时,也有从加强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教育角度来强调中华民族历史观对于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进行战略对策研究的建议,(5)徐杰舜,徐桂兰:《加强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现状考察与对策》,载《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以立法、确立中华民族“国族”地位、将中华民族历史观列入国策等9条对策建议来强化中华民族意识,初步显示了中华民族历史观对于中华各民族认同及中华民族发展历史认识的重要性。
从“培养”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发展阶段来看,学界认为坚持正确的历史观与党和国家事业的稳固基础息息相关,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中华民族和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强大自觉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自强之路的根本保证。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才能理解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在五千年历史中的自在、自觉和自强三个维度的发展进程。(6)吴孝刚:《把握中华民族历史观的三个维度》,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年第10期。如何认识中华民族应该从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和精神品质,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并对世界文明作出了伟大贡献等三个方面出发,(7)瞿林东:《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民族报》2022年1月11日。并且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决定因素,需要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把握历史叙述权和话语权,(8)史金波:《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自古有之》,载《中国民族报》2022年1月11日。同时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有三条内涵主线:中华民族之于人类历史文明进程的重要性,中华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的前景展望,因此加强中华民族史研究,此三方面通过方法论以及具体实践中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民族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9)李国强:《正确认识中华民族需要大历史观》,载《中国民族报》2022年1月11日。从宏观角度及不同层面对中华民族历史观进行分析,并强调了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历史观对于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重要性。
学术界相关讨论以大历史观的纵深视野和宽阔背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史进行梳理,认为大历史观的研究视野可以准确定位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得出科学结论。(10)陈金龙:《大历史观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载《求索》2021年第3期。同时,从学术史角度讨论新中国民族史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民族史相结合的研究基本框架,对于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研究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11)王娟:《重建“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叙事 20世纪中国民族史观的形成、演变与竞争》,载《社会》2021年第1期。为如何诠释中华民族历史观研究的相关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目前学术界初步将“四个共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问题结合讨论,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认识基础,是通过开展面向全民普及“四个共同”,并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来正确把握“四个共同”的丰富内涵,(12)周智生:《以“四个共同”为核心:全面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7期。结合“四个共同”讨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13)许烨:《“四个共同”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载《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新向度。(14)于玉惠,周传斌:《“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阐释的新向度》,载《贵州民族研究》2021年第6期。有关“四个共同”与中华民族的研究多为结合二者为“一体”的学术研究,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是连续性的,本文的讨论核心是如何从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解读“四个共同”与中华民族历史观之间的内在逻辑,在“四个共同”的前提条件下突出中华民族历史观超越差异性的主体性,从中华各民族的动态关系中归纳中华民族历史观中蕴含的“四个共同”,使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基础。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习近平为民族工作提出的工作目标,同时也给学术界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研究命题,需要我们去回答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等理论命题。历史观是人类认识历史发展的系统理论,同时也是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从这个意义来看,历史观是哲学问题向社会科学领域的延伸,是从哲学角度对历史观的根本性认识。从历史观具体的研究对象来看,历史观主要关照社会和人(民族)这两个主体,由于社会和人(民族)的存在必须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具有文化意义的人口等基本要素发生关系,这些基本要素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变量,因此也就是历史观研究的主要内容。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中华民族历史观就是对中华民族发展历史认识的系统理论,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评价和判断,具体而言就是要通过研究对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特征,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特征,以及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规律进行理论概括,从哲学意义来讲,中华民族历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
“四个共同”的落脚点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疆域、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和共同精神,本意即在于立足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以中华各民族共同性特征、表现为起点和归宿,通过梳理基于各民族“共同”基础上的历史进程,强调的是“共同”思想理念和理论视野,(15)于玉慧,周传斌:《“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阐释的新向度》,载《贵州民族研究》2021年第6期。使中华民族历史观充满着哲学意味,有利于从哲学的高度把握中华民族发展的话语权和中华民族历史观研究的叙述权,有利于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
一、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
世界各民族的发展历史总是在某个特定的空间内发生的,每一个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具体而言,地理环境决定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影响着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生活和生产方式,因此在对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具体研究中,我们看到中国自然地理环境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多民族中国的民族国情,中国自然地理环境的多样性还决定了多民族中国南北民族的基本关系特征及其走向。与此同时,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还导致了中华各民族发展的诸多差异。此外,中华各民族的发展与自然地理环境具有十分密切的相关性,其基本特征是随着中华各民族对自然地理环境认识的深入,并在不同区域内创造具有地域特征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就是说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华各民族的内部差异和地域文化差异。
多民族中国有着辽阔的疆域,高大的山脉主要集中在中国西部,因为山脉而形成的海拔高度,使中国的地形成为了明显的三级阶梯状态,中国主要的河流也基本上是自西向东流向大海,因此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便存在着众多的大河三角洲,中国的海洋基本都在东部和东南部,所有这些地理要素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空间。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华各民族就共生共存在这个具有内部结构完整的自然地理空间中。
虽然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空间具有内部的相对完整性,但是由于地理环境形态的复杂多样,决定了中华各民族生计方式的差异,因此也决定了在中华各民族生存空间中因为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了文化特征各异的民族群体,这些民族群体被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从文化的角度概括为“华夷”民族共同体,对此,《礼记·王制》有十分明确的记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16)郑玄注:《十三经注疏·礼记·王制》,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38页。文中提到的“中国”一词在商周时期还不是国家概念,指的是华夏族,华夏族与“戎夷”在多民族中国的疆域内构成了最早的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因此,“华夷”就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而正是“华夷”在历史过程中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礼记·王制》之所以说“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就是因为“中国戎夷”分布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中,所以“皆有性也”指的就是文化差异。故中华民族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自然地理环境紧密相关,例如东方和南方的民族群体因为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所以都有“文身雕题”的文化习俗,饮食文化的特点是“不火食”,即常常食用生食;而生活在西方和北方的民族则因为气候寒冷,穿厚重宽大的衣服,又因为以游牧经济为主,不生产粮食,故“不粒食”,通常以肉制品和乳制品为主食。
除了《礼记·王制》外,《汉书·地理志》也记载了先秦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在发展过程中是如何认识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空间结构的:“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是故《易》称‘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书》云‘协和万国’,此之谓也。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17)班固:《汉书·地理志 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23页。文中的九州(18)九州分别是扬州、荆州、豫州、青州、兖州、雍州、幽州、冀州、并州。就是中华民族的先民在治理水患的过程中,在对生存空间的认识过程中,根据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划分出来的,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对生存空间和空间中物质的依存联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从自然地理环境的角度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其与自然地理环境关系是中华民族历史观最重要的观点之一。
如果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看,中国东部和东南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气候温和、降雨丰沛,各种自然环境条件适合农业经济的发展,由此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内聚力的地区之一;此外,由于中国处在东亚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环境中,东北部有渤海、黄海,东部有东海,东南部有南海;西部和西南部是山地,山高水急;北方是广袤而寒冷的大草原,因而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民族关系的演进中形成一种民族的自然内向性。”(19)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页。古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也就以南方的农耕民族群体与北方的游牧民族群体的关系为主,具体表现为南北方民族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的交往交流交融,因此由中国自然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内聚力和内向性就成为中华民族发展最基本的客观条件,制约和影响着中华民族发展的基本走向。
总的来说,客观外在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使不同区域内的民族产生了相互的依赖性,必须要进行物质的交流,文化的交往,北方民族希望与南方民族交换粮食,而南方民族则希望与北方民族交换马匹等物品,中华各民族正是在这样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向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孕育发展的,这就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趋势,这样的历史趋势是由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给中华民族形成发展所定下了历史基调。
二、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发展
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从民族形成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能够有国家支持,民族的发展就有了强大的动力,就有了凝聚力,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过程与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发展关系紧密,具有相互的依赖性。
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的长时段历史来看,秦汉时期、隋唐时期、元明清是三个以大一统为主的时期,在这三个时期内中华民族获得了巨大发展,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在这三个时期同样达到了不同高度,特别元明清时期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和中华民族发展的关键时期,为近现代多民族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秦汉时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其标志是先秦时期的华夏族在秦汉时期大一统国家政权支持下,华夏族开始向汉族转变,汉族在汉朝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成果,使汉族成为推进中华各民族融合的一个主要力量。在秦汉时期通过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诸多的民族群体形成并且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民,丰富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内涵,例如《史记》《汉书》的民族列传中没有记载过的羌族、乌桓、鲜卑,在《后汉书》中成为了东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民族群体,而且还影响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经过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加快了民族融合。此外,《史记》《汉书》中的《匈奴列传》不再出现,而是出现了《后汉书》的《南匈奴列传》,随着南匈奴进入中原地区,接受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权的治理,采纳了农业文化,最后发生了民族融合,虽然消失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但是却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内涵,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也向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扩展延伸。
隋唐时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时期,其重要标志中华民族不论是人口数量还人口质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使中华民族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文化独特、经济发展具有优势的民族。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权的有效治理下,唐朝的疆域超过了汉朝,唐朝的国家力量亦同样超过了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文明中心地区之一。生活在唐朝疆域的中华各民族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中华各民族内部的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亦更加深入,经过民族的分化与融合,北方地区出现了突厥、回纥、沙陀等推动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民族群体;在南方地区民族的分化与融合则更为明显,在华南地区出现了承上启下的僚族,在西南地区出现了承上启下的乌蛮,僚族和乌蛮在大一统国家内经过交往交流交融,向着现代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和藏缅语族的相关民族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注入了诸多新鲜血液,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动力。
元明清时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时期,其标志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开始由自在向自觉转变,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元明清王朝的治理下,近现代中华各民族的雏形开始形成,疆域内的各民族都纳入了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政权的行政体系之中,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国族”,共同创造着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历史,推动着中华民族快速发展。如果从历史文本的书写角度来看,在《元史》《明史》中就已经没有了专门的民族列传,中华各民族在这个时期绝大多数都已经纳入了郡县的治理,相关的民族发展历史已经写入了《元史·地理志》。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和辽宋西夏金时期是中华各民族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虽然这两个时期统一多民族中国处于多个政权分立的状态,但是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却更加充分,更加有质量,在这两个历史时期通过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多个政权的政治家都以自己为正统,都在各自的辖境内发展经济,为下一个历史时期更大规模的大一统国家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研究中华民族历史观值得充分关注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因此,在中华民族发展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发展历史中,隐含着民族融入、疆域扩大、国家内涵变化、中华民族内涵更加丰富的内在逻辑,即随着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国家的发展,诸多的民族纳入王朝国家的疆域范围,因此统一多民族中国的边疆扩大,构成国家的相关要素亦随之变化。也就是说,随着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发展的深入,不断有新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内涵亦随之发生变化。具体变化为中华民族的人口越来越多,中华民族生存的空间更加广大,中华民族的内涵更加丰富。虽然其间有过多个政权的分立,但这些政权都是在中华民族分布空间之内,而且还为下一个历史时期更大规模的统一在进行着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发展的质与量的积累。(20)王文光,尤伟琼:《汉代边疆民族与国家发展关系研究——以民族历史文本书写的视角》,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4期。
三、维护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的大一统思想与中华民族的发展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大一统思想观念有密切关系。 产生于春秋时期的大一统理论的背景是当时周天子政治地位下降,周天子的号令已然出不了王畿。诸侯政治势力不断强大,部分政治家为了使天下统一于周天子,消除诸侯割据,提出了保证国家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因此,强调大一统就是要在思想上确立周天子的地位,保证天下统一于周天子,保证国家不分裂,消除诸侯割据,这样的政治主张在当时是无法推行的,但却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意识形态,是保证国家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是顺应“天意”的。(21)王文光:《多民族大一统中国发展历史与中国边疆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4期。
汉景帝时出现了“七国之乱”,大一统汉朝面临着分裂的威胁。到了汉武帝时期,一个强大的国家发展需要大一统理论支持,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大一统思想成为了保证和推动大一统中国发展的精神力量。董仲舒在《春秋公羊传》中找到了大一统思想,论证了大一统思想的历史作用,董仲舒在《公羊传》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大一统思想的阐释,并且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可,这说明随着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发展,大一统思想具有新的意义。
“大一统”思想在古代中国的实践,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其中已经孕育着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国家发展与民族发展的角度来看,能否真正实现中国的大一统,把边疆各民族真正纳入大一统中国,是需要中华各民族的政治家共同努力的,从这个意义来讲多民族大一统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就是中华各民族的政治家对边疆进行治理并且不断巩固的历史过程。(22)王文光:《多民族大一统中国发展历史与中国边疆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4期。在所有的这些行动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得到了发展,因此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历史才从来没有中断过。
随着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疆域的扩大,中央王朝对中华各民族的治理越来越深入具体,因为中华各民族都已经纳入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格局之中,相关民族群体的发展历史被记入相关的郡县,这表明在大一统国家内中华各民族的差异性在减少,共同性在不断增加。
四、“华夷共祖”民族思想与中华民族的发展
“华夷共祖”民族思想是司马迁在《史记》的文本书写中表现出来的,从结构上讲,司马迁的《史记》开篇就是《五帝本纪》。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系统地记述了五帝世系,并且在其后的相关“本纪”“列传”中阐述了以五帝为中心的“华夷共祖”思想。《史记·五帝本纪》认为建立夏商周三朝的夏族、商族、周族是黄帝后裔:“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23)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5页。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吴人、越人、楚人、秦人亦为黄帝后裔,《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24)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第1445页。《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25)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第1739页。《史记·楚世家》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26)司马迁:《史记·楚世家》,第1689页。《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27)司马迁:《史记·秦本纪》,第173页。司马迁把吴人、越人、楚人、秦人全部与黄帝联系起来,都是五帝的后裔,具有同源同根的亲源关系,建构了一个完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谱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建立了政权,“华夷共祖”民族思想被“五胡”建立的政权实践,都把自己与五帝相联系。《晋书·刘元海载记》说“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28)房玄龄:《晋书·刘元海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50页。因此刘元海以恢复“汉”为政治目的,“乃为坛于南郊,僭即汉王位,……乃赦其境内,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29)房玄龄:《晋书·刘元海载记》,第2645页。赫连勃勃亦强调自己是夏后氏的后裔,“(赫连勃勃)僭称天王、大单于。赦其境内,建元曰龙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今将应远而兴,复大禹之业。”(30)房玄龄:《晋书·刘元海载记》,第3205页。刘元海与赫连勃勃的行为实际上都是“华夷共祖”民族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实践。
辽宋西夏金时期,契丹、党项、女真的政治首领为了有效治理辖境内各民族也接受了“华夷共祖”民族思想。《辽史·表一·世表》载:“伏羲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31)脱脱:《辽史·表一·世表》,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49页。这是契丹认为自己是炎帝的后裔。党项李元昊亦说:“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服。”(32)脱脱:《宋史·夏国传 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995、13996页。即党项亦是是五帝之后。这样的认识是“华夷共祖”民族思想的实践。
元朝和清朝虽然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是也有 “蒙汉一体”“满汉一体”的民族思想,虽然不能说这样的思想就是“华夷共祖”民族思想,可却具有“华夷一家”的含义,与“华夷共祖”民族思想与诸多契合。
以“华夷共祖”民族思想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体表现为“华夷一家”“满汉一体”,这些民族思想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由自然环境所决定的内聚力和内向性在民族思想上的表达,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
五、小结
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关系、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发展与中华民族发展的关系是中华民族历史观最基本的问题,讨论的是中华民族历史观需要研究的地理环境因素、社会存在问题;维护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的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华夷共祖”民族思想及其实践是在统一多民族中国社会存在基础上产生的与中华民族历史观有关的社会意识,是保证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社会意识。其中的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发展与中华民族发展的关系问题与“四个共同”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
第一,必须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从中华民族历史观和“四个共同”论述为基点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可以避免简单把中华民族等同为“一体”的学术争论,突出“共同性”,强调“共同体”,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在理论上已经有了发展。中华民族历史观是统一多民族中国重要的思想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现实状态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具有连续性的,研究中华民族历史观可以让我们充满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民族自信,研究中华民族历史观可以让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的现实,在对中国现实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便可以洞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第二,必须关注“四个共同”论述中所表达出来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对“四个共同”的阐释所表达出来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如果从中华现代国家的角度来分析中华民族历史观与“四个共同”论述之间的内在逻辑,可以发现习近平为什么首先强调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疆域,这是因为疆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具有强烈的国家属性,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文化、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发展的必要前提,因此中华民族历史观还表达了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思想观念,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意义非凡。
第三,中华民族历史观与“四个共同”论述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极高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四个共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因为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伟大祖国的疆域、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文化、共同培育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这是从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归纳出来的,其中已经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四个共同”的前提下追溯中华各民族的动态关系,也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过程的概括,从中华民族历史观的角度强调中华各民族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是对差异性的超越。由此可见,在未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疆域完整、不断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仍然是需要中华民族历史观与“四个共同”论述的理论指导,唯有如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够不断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