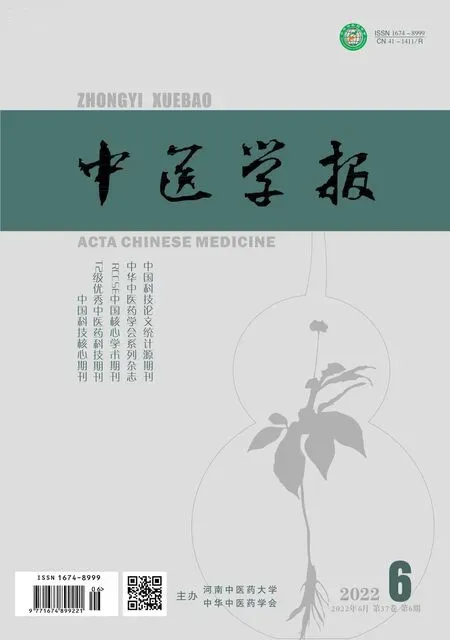宋立群运用补益固涩法治疗膜性肾病经验*
杨梦凡,范桢亮,尹日平,宋立群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150040; 2.浙江省中医院,浙江 杭州 310000; 3.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40
膜性肾病为临床常见肾脏疾病,近年来随着肾脏病疾病谱的变化,膜性肾病在我国的发病率不断增长,十几年内在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中所占比例由15%迅速上升至30%~40%,而1/3的患者可进展至终末期肾脏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1-3]。膜性肾病为肾病综合征常见的病理类型,其在临床主要表现为蛋白尿、水肿、低蛋白血症、高脂血症,由于本病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现代医学的治疗方案主要为运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等药物,但很多患者对此类疗法并不敏感而病痛无法得到缓解,或容易复发,并常伴随诸多不良反应[4-5]。针对此类情况,中医药疗法以疗效显著、鲜有不良反应的优势,受到广泛认可[6-8]。目前,已有大量临床研究表明中医药治疗膜性肾病不仅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症状,而且可以有效降低膜性肾病的复发率[9-13]。同时现代实验研究显示,中药在保护足细胞、减轻肾纤维化、抑制炎症反应、改善高凝状态、缓解激素不良反应等方面均有良好的作用[14-17]。
宋立群教授为我国知名肾病专家,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肾病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宋教授从事中医医疗、教学、科研工作近40年,以中医药治疗肾病为研究方向,对多种肾系疾病的诊治深有体会,临床治疗卓有成效。针对膜性肾病正气虚损的核心病机,宋立群教授提出“固护正气、补益脾肾、收涩固精为重”的学术理念,在临床治疗膜性肾病中,运用补益固涩法,结合解毒祛邪、祛风除湿、活血通络之品,常获奇效[18]。笔者有幸随师侍诊学习,收获良多,兹将宋教授的经验介绍如下。
1 膜性肾病的中医病因病机
中医古籍中并无“膜性肾病”之名,但随着现代研究的不断深入,现代医家根据其临床表现与病机特点将其归于中医“肾风”“水肿”“腰痛”等病辨证论治[19]。本病病因病机较为复杂,究其根本病因在于正气不足。《素问·水热穴论》云:“勇而劳甚则肾汗出;肾汗出逢于风。”先天禀赋不足、劳累过度、情志过极等因素,均可导致本病的发生。卫气出于下焦,肾气亏虚而至卫气不足,外邪可乘虚而入,从而进一步导致邪伤肾络、肾精亏损,精微不固,临床则见大量蛋白尿[20]。正气亏虚贯穿膜性肾病发展的始终,初期多见脾肾气虚、肺肾气虚之证,而精微下泄日久可致气阴两虚、肝肾阴虚,病久及阳,则致脾肾阳虚,终可阴阳两虚[21]。
宋立群教授认为,本病的基本病机为本虚标实,脾肾不足、气机失调为其发病之根本,而湿、毒、热、瘀等病理因素则为本病之标。在临床辨治中,一般按照本虚证加标实证组为复合证进行辨证。本病之证初期多为肺肾气虚、脾肾两虚型,中后期则多见精微不固型、肝肾亏虚型、阴阳俱虚型等,兼以标证如水湿内停证、湿热内蕴证、痰浊困阻证以及血瘀阻络证等,治疗则以健脾益气、补肾固精、疏肝理气、凉血止血为总治则。
由于本病多起病隐匿,病程缓慢,患者常不能及时知晓,故临床就诊患者多见类型为精微不固型、肝肾亏虚型。在治疗时,宋教授常常将补虚、收涩类药物同用,以补肾健脾、涩精止血,再根据患者具体病程不同,灵活配合解毒祛邪、祛风除湿、活血通络之法等[22]。
2 临床治法治则
2.1 补益固涩同用,标本兼治针对膜性肾病脾肾不足、气机失调的核心病机,宋教授在治疗水湿内停、精微不固、肝肾亏虚之证时,常将补虚、收涩类药物同用,包括黄芪、白术、覆盆子、女贞子、芡实、金樱子、白果、菟丝子、沙苑子、甘草等,以补肾健脾、益气固精为基本治法。再根据患者具体病程、病情结合他法,如发病初期见风水水肿之证时,加以麻黄、浮萍、防风固表祛邪;中期水湿内停则加以路路通、冬瓜皮等品利水消肿;后期瘀血阻络则加以穿山龙、龙葵、苏木、丹参、姜黄、土鳖虫等品解毒活血通络。
膜性肾病临床常以蛋白尿、水肿等症状为主要表现,即为精气滑脱,治标当用收敛固涩之法,兼以利水消肿、解毒活血等,以固其精微而祛邪浊,但究其本皆因正气亏虚、气机失调所致,应补益正气以补肺健脾益肾,以补益收涩药相配伍为基础治疗膜性肾病,实为标本兼顾之法。
宋立群教授运用补益固涩法治疗膜性肾病之时,常取四君子汤之意化裁,以黄芪、白术、茯苓配伍为核心药物组合,取其健脾补肾之用,三药入肺、脾、肾经,在益气固表的同时有健脾利水渗湿之功,补益脾肾使正气生化有源,以此针对膜性肾病正气亏虚之根本。其中黄芪用量往往较大,其为治疗肾系疾病的常用药物。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其可以通过调节人体免疫功能、促进蛋白质的合成、抗氧化损伤的状态等机制,对膜性肾病起到治疗作用[23]。且此三味药均有利尿的作用,可缓解膜性肾病患者水肿的症状。
另外,在此基础上加用收涩药,如芡实、金樱子、桑螵蛸、分心木等药,使正气不仅得补,更使得固,以针对肾虚不固之精微外泄之症。菟丝子与沙苑子、芡实与金樱子为宋教授治疗膜性肾病常用补益收涩类药对。菟丝子、沙苑子虽同归为补阳药,但均兼有收涩之效。沙苑子性降而补,《本经逢源》中称其为“泄精虚劳之要药”。菟丝子补而不燥,《本草经疏》谓之“补脾肾肝三经之要药”,其在滋补肝肾同时可使肾精得固,此两味药相须为用,共奏扶助正气而固涩精微之效,相得益彰。而芡实、金樱子配伍,即《洪氏集验方》中 “水陆二仙丹”,二者均入脾、肾二经,有补脾固肾、涩精缩尿之功。现代研究表明,“水陆二仙丹”中有多种活性成分在膜性肾病发病中的氧化应激、炎症损伤等多种机制都可产生作用[24]。
2.2 以肝脾肾为先,五脏同调宋立群教授在运用补益固涩法治疗膜性肾病时,根据五脏相生理论,重视五脏同调,尤以肝脾肾为先[25]。膜性肾病病程较为漫长,久病不愈与肝、脾、肺三脏有关。肾气亏虚可影响脾胃之受纳运化;肾虚精亏,水不涵木,可使肝之阴血亦亏;而肺卫气虚,卫外不固不仅与发病有关,更为影响其病情反复之主要因素。肾失封藏、脾不能升清气,或肝肾阴虚扰动精室,精气外泄,则出现蛋白尿之症状;肾气亏不能束水,脾不能运化水湿,水湿外溢于肌肤则为水肿。
在膜性肾病临床治疗的过程中,起病初期患者往往以肺脾气虚多见,另外部分患者病情容易反复发作则应责之肺气虚卫外失司。宋教授常用白果、桑白皮、紫苏等品入肺经以益肺气、宣气机,使卫气得固而气机调达。而因本病起病隐匿,大部分患者在起病初期因症状较轻并不予以重视,在就诊之时往往病情已经发展至中后期,故在临床辨证治疗过程中发现本病更多见肝、脾、肾三脏不足之证。宋教授在临床治疗中往往在以黄芪、白术、茯苓、甘草等药补脾益肾的同时,加以覆盆子、女贞子、杜仲、熟地黄等品共用同补肝肾。
综上,在宋立群教授运用补益固涩法治疗膜性肾病的常用药物中,黄芪、白术、茯苓、芡实、金樱子、白果、菟丝子、沙苑子、墨旱莲、女贞子等各药,分别入肺、肝、脾、肾,各有所长,共同收敛外泄之精微,固护虚损之正气。《脾胃论》云:“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脾肾相互资生,脾之清气得升,肾中精元得藏,气机升降有序,水液代谢通调。而肾病治肝、肝肾同治,为滋水涵木之法,补敛肝肾精血,可使精血化生有源而不至外泄。
2.3 重用平补之法,补而不滞膜性肾病发病者多为中老年患者,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言:“女子五七,阳明脉衰……男子五八,肾气衰。”随着年龄增长,脾肾亏虚亦是自然的生理改变,而本病之正虚在发病之初往往重在气虚,故临床多见脾肾气虚兼夹实邪而导致水肿、蛋白尿等症的情况。偏于阴虚或阳虚之证临床往往较为少见,在久病之时多见阴阳俱虚之证[26]。另外,临床也常以中西医结合配合治疗,患者在接受激素、免疫抑制剂的治疗日久之后,常有肝肾阴阳俱虚的表现,与此同时接受中药汤剂治疗,可起到增效减毒、巩固疗效的作用。故在补益之品的运用中,宋教授注重用平补之法,首先以黄芪、白术、茯苓、甘草补肾健脾,以益气为重,另外,在治疗阴阳俱虚之证时,应阴阳双补,以墨旱莲、女贞子等滋阴降火的同时,加锁阳、菟丝子、沙苑子以温肾阳,另外可加以杜仲、牛膝、川续断、桑寄生等药平补肝肾。
此外,宋教授在临床治疗膜性肾病的过程中,注重调畅脾胃气机,一者在运用大量补益固涩类药物应用的同时以助脾胃之运化,可使补而不滞,再者正所谓“四季脾旺不受邪”,而脾胃强健,气机得运,元气化生有源,则有助于患者病情缓解以及防止疾病的复发,三者膜性肾病患者病程往往较长,需要经过长时期的用药,易出现脾虚不受的情况。故而在临床治疗膜性肾病的过程中,宋教授非常重视顾护脾胃、疏理气机,常在基础方剂中加用焦三仙(焦山楂、焦神曲、炒麦芽)、陈皮、山药、鸡内金等品以理气健脾、和胃消滞,使脾胃气机调达。除此之外,亦嘱患者以大枣一枚、生姜三片入煎剂,助诸药入气分和营卫,并调和脾胃。
3 验案举隅
于某,男,36岁,2014年12月3日初诊。主诉:双下肢水肿半年余。患者于2014年6月7日因下肢浮肿,遂就诊于当地某西医院,行尿检示:尿蛋白(+++),患者未予重视,未接受治疗。2个月后因水肿加重于当地某西医院治疗,2014年8月4日行肾穿刺活检,病理诊断:Ⅱ期膜性肾病。遂在当地西医院治疗,服用环磷酰胺片及美卓乐(甲泼尼龙片),治疗效果欠佳。目前环磷酰胺片已停药,甲泼尼龙片减至每天4片,治疗效果仍不显。现症见双下肢水肿明显、面目略浮肿,腰痛、乏力,饮食一般,睡眠尚可,二便正常,舌质暗苔白腻,脉沉数。尿常规:尿蛋白(+++),尿潜血(+)。诊断为:水肿(肝脾肾不足、水湿内停证)。处方:黄芪30 g,炒白术15 g,茯苓30 g,覆盆子15 g,女贞子15 g,芡实 15 g,金樱子15 g,菟丝子10 g,沙苑子10 g,白果 10 g,桑螵蛸 10 g,穿山甲30 g,重楼20 g,苏木 10 g,山楂 30 g,陈皮20 g。生姜、大枣为药引,14剂,水煎服。
2015年1月7日二诊:患者水肿明显减轻,口苦、口干,大小便正常,舌脉同前。甲泼尼龙片减至每天3.5片,尿常规:尿蛋白(+-)。处方:上方加水飞蓟20 g,田基黄20 g。14剂,水煎服。
2015年3月11日三诊:患者忌口不严,症减不著,仍有水肿、乏力、纳差,舌质暗苔白,脉沉。甲泼尼龙片减至每天2.5片,尿常规:尿蛋白(+-),尿潜血(+)。处方:原方去生山楂,加秦皮20 g,马齿苋20 g,丝瓜络15 g,14剂,水煎服。
2015年4月16日四诊:患者水肿基本缓解,舌脉同前。尿常规:尿蛋白(+-),尿潜血(+)。处方:原方去穿山龙、重楼、苏木、生山楂,加生地炭 20 g,熟地炭20 g,大蓟炭20 g,小蓟炭20 g,侧柏炭 20 g,地榆炭20 g。14剂,水煎服。
2015年7月9日五诊:患者自述已无明显不适,水肿完全缓解,饮食、二便均可,舌暗苔白,脉沉。尿蛋白转阴,激素减至每天1片,处方:原方去生山楂,加杜仲15 g,后随证加减续服1个月后,由汤剂改服丸剂,后每隔6个月随诊1次至2020年9月,5年内一直未出现复发情况。
按语:该患者因显著下肢浮肿症状,中医诊断为水肿,辨证为肝脾肾不足、水湿内停证,其来就诊之时病程已久,以水湿停滞为标,正虚为本,若一味以化湿利水治疗则反不当,可能使患者正气更虚,故治以黄芪、白术、覆盆子、女贞子等药补肾健脾养肝、益气固精,并加以穿山龙、重楼、苏木解毒化瘀通络,另以陈皮、山楂、生姜、大枣等行气健脾令补而不滞。可见,治疗中以固护正气、补益脾肾、收涩固精为重的治则贯穿了始终,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但同时此并非一成不变,“久病必瘀”,在初期患者兼见血瘀证,治疗加以解毒活血通络,后期兼见湿热,则加以秦皮、马齿苋、丝瓜络等清热燥湿利水。在临床应用补益固涩法治疗膜性肾病的过程中,也不必拘泥于此法,应根据患者病情变化随证加减。
4 结语
膜性肾病比之临床其他疾病而言,其病程较长,故治疗周期往往长达数月甚至数年。宋教授认为,膜性肾病为本虚标实之病,其本在于五脏不足,脏腑功能失常,标实则为湿、热、瘀、毒等多种病理产物蓄积肾络。由于患者正气亏虚,肾失封藏,脾失健运、肝阴亏虚、肺失宣降以及湿、热、毒、瘀等病理产物阻碍气机,损伤肾络,导致精微外漏。宋教授在临床以补益固涩法辨治膜性肾病中,以肝脾肾三脏为重,以健脾补气、补肾固精为先,常将补益药与收涩药相配伍,而或再加以祛风除湿行气、活血化瘀通络之品,则可使正气盛而邪气自去。